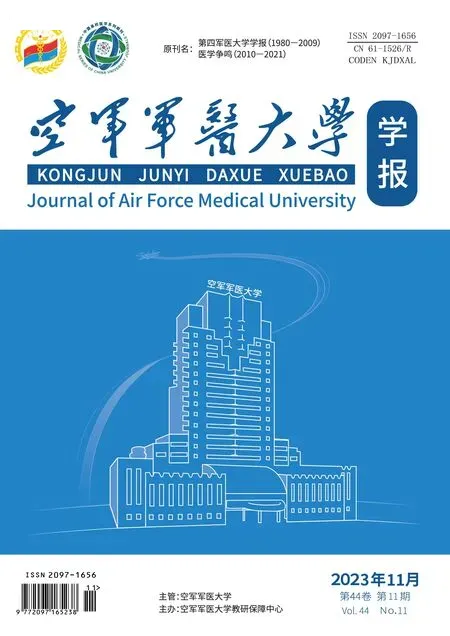创伤后应激障碍物理治疗潜在脑区靶点的研究进展
刘 斌,陈 晨,宋 磊,马续龙,高 幸,李西萍,杨 群
(空军军医大学:1军事医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教研室,2教研保障中心,陕西 西安 710032)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个体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类精神疾病,其临床表现主要有四大核心症状群,包括创伤体验的反复侵入、对与创伤事件有关刺激的持续回避、对创伤事件有关的认知和心境方面的负性改变以及警觉性或反应性的显著增高[1]。PTSD是一种全球流行的精神疾病,一项全球性调查研究表明,PTSD的终身患病率为1.3%~12.2%[2]。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暴发给各个国家居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PTSD的患病率也由此上升。2020年一项包含266名社区居民的研究发现,有60.2%的居民显示有PTSD临床表现[3]。PTSD不仅会严重损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还会对患者家属及社会造成重大负担。因此,对PTSD的有效治疗方法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目前临床治疗PTSD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用于治疗PTSD的药物主要是2种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帕罗西汀和舍曲林[4]。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在药物治疗后出现了延迟效应、体质量增加、失眠等药物不良反应,有20%~30%的患者对SSRIs类药物反应不足,并且有20%的患者在6个月内出现了症状的复发[5-6]。PTSD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是基于创伤的心理治疗,包括暴露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等,但是研究发现大约有2/3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仍然符合PTSD的诊断标准[7]。此外,研究表明PTSD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于PTSD患者的疗效主要来源于焦虑及抑郁相关症状的缓解,对PTSD核心症状的作用并不大[8]。
物理治疗自1938年面世以来,一直是一种可靠的精神疾病辅助治疗手段,它包括电休克治疗、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迷走神经刺激多种形式。物理治疗共同的作用模式是可以作用于特定大脑区域,调节该区域内的神经兴奋性,从而引起功能状态或连接状态的改变,进而恢复脑区正常生理状态,最终达到治疗目的。近些年来,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大量研究证据表明,PTSD是一种脑回路紊乱疾病,特定大脑区域的功能异常或连接异常是导致PTSD核心症状的重要原因[9]。因此,使用物理治疗作用于与PTSD核心症状相关的功能异常或连接异常的特定脑区,通过改变脑区异常状态,恢复其正常生理状态,可能会有效地解决PTSD的核心症状。这些功能异常或连接异常的特定脑区可作为物理治疗PTSD核心症状的潜在脑区靶点。本文旨在总结与PTSD核心症状相关的功能异常或连接异常的脑区,以为后续PTSD的物理治疗提供可针对的脑区靶点。
1 功能状态异常的潜在脑区靶点
1.1 杏仁核(amygdala,AMG)
AMG是位于颞叶的椭圆形结构,由不同的核组成,具有特定的连接和功能。AMG可分为中央核(central amygdala,CE)、内侧核、嵌入神经元群和基底外侧AMG复合体(basolateral amygdala,BLA),BLA中包括外侧核、基底核和副基底核[9]。BLA接受皮层下和初级新皮层听觉、视觉和躯体感觉区的广泛投射,这个核复合体负责整合外部和内部线索,因此,它涉及合并厌恶事件与非威胁情况。来自BLA的信息传播到CE,并从CE传播到下丘脑和多个脑干区域。下丘脑参与自主反应并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活动,脑干区域中包括导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PAG),PAG则参与运动行为的表达如冻结现象[10]。在条件恐惧的情况下,AMG中的CE区发生神经可塑性的改变,使得恐惧记忆得以长期储存。因此,AMG被认为在恐惧记忆的习得和表现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1]。神经影像学发现,PTSD患者在接受负向刺激时,AMG区域表现为过度激活,这造成了PTSD患者加重的恐惧反应和持续的创伤记忆[12]。此外,研究还发现AMG的激活程度与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13]。可见AMG与PTSD核心症状的产生与进展密切相关,因此,AMG可作为治疗PTSD的一处重要脑区靶点。一项使用DBS治疗PTSD的研究报告,1例难治性战斗相关PTSD患者在接受了8个月双侧AMG基底外侧DBS治疗后,患者PTSD核心症状改善了35%以上[14]。截至目前,使用AMG作为物理治疗靶点的研究较少,这可能与AMG所处位置较深、不方便直接刺激有关。
1.2 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PFC)
PFC可分为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研究表明,PTSD的本质是一种恐惧消除失败的病态恐惧条件反射[15]。对人类和啮齿类动物的研究证实,条件性恐惧的消除并不是消除或掩盖原始的恐惧记忆,相反,这种消除涉及到一种新的学习,称为“消除学习”。消除学习是一种暴露疗法的实验室模拟,消除学习和暴露疗法都依赖于个体反复暴露于恐惧的刺激中,但不出现恐惧的后果,这使得大脑形成了“消除记忆”,也被称为“安全记忆”[16]。在恐惧学习过程中,个体学会将刺激与厌恶事件的发生联系起来;而在消除学习过程中,个体学会将相同的刺激与在安全环境中防止厌恶事件的能力联系起来[17]。因此,消除学习的目标是形成新的安全记忆,这种记忆可以被回忆起来以抑制与最初创伤相关的恐惧反应,而这种在消除学习后能回忆起安全记忆的能力被称为“消除保留”,在这个过程中,后来习得的安全记忆可以继续抑制最初习得的恐惧反应,以避免PTSD症状的复发[18]。因此,消除学习的异常、消除记忆的异常以及消除保留的异常,广泛地与PTSD相关。vmPFC被认为是消除学习和消除保留的大脑区域,同时也是抑制恐惧反应的大脑区域[19-20]。首先,在消除学习过程中,vmPFC的激活预示着消除学习的成功,并且正常的vmPFC与消除保留能力密切相关。此外,vmPFC可以控制调节AMG的恐惧反应,使得恐惧反应减轻,恐惧记忆时间缩短[21]。研究表明,PTSD患者vmPFC反应低下,消除学习和消除保留出现明显异常,并且vmPFC不能对AMG进行有效调节,这使得PTSD患者的恐惧反应持续存在[22-23]。此外,使用物理治疗分别刺激左右侧vmPFC区域会导致不同的刺激结果。一项健康人群的研究发现,使用tDCS刺激右侧vmPFC可以促进被试回忆正向记忆,而刺激左侧vmPFC会促进被试回忆负向记忆[18]。并且已有研究表明,使用tDCS作用于PTSD患者的右侧vmPFC区域后,患者的PTSD核心症状严重程度显著降低[24]。因此,目前常将右侧vmPFC作为PTSD物理治疗的一处脑区靶点。
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为了获得特定目标而经历、评估和改变情绪反应的一系列过程,例如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就是两种常见的调节策略[25]。OLSON等[26]研究发现dlPFC功能活动的正常与个体情绪调节的成功相关,并且发现dlPFC功能活动在PTSD患者中处于异常低活跃状态。同vmPFC区域一样,使用物理治疗分别刺激左右侧dlPFC也会产生不同的治疗效果。研究发现,使用rTMS刺激PTSD患者右侧dlPFC区域可以有效缓解PTSD的核心症状,而刺激左侧dlPFC仅会引起情绪改善[27-28]。因此,右侧dlPFC也是目前PTSD物理治疗的一处脑区靶点。
1.3 海马体(hippocampus,HPC)
与恐惧学习相比,恐惧反应很容易在不同的环境中泛化,而恐惧消失是特定于环境的[29]。这意味着虽然消除学习成功发生并产生了消除记忆,但这种消除记忆是基于特定环境的,并不容易推广到其他环境中,在那些没有发生消除记忆的环境中,恐惧反应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对于PTSD的治疗,特别是基于暴露疗法的治疗,应该发生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以更有效地减少PTSD的症状。研究发现,HPC是个体记忆形成过程中处理环境情景信息的关键大脑区域,也就是说,PTSD症状的缓解依赖于HPC功能的正常[30]。此外,除了HPC本身,HPC到vmPFC的连接与恐惧学习和消除学习中的情境加工功能相关[31]。有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PTSD患者的HPC体积相较于正常个体有所缩小[32]。GILBERTSON等[33]发现,HPC体积缩小是个体经历心理创伤后出现PTSD的家族性危险因素。也有研究报道了PTSD患者在静息期时HPC的糖代谢率和活跃状态降低,在成功治疗后HPC的糖代谢率和活跃状态显著增加[34]。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支持PTSD患者HPC体积缩小和激活不足。WERNER等[35]发现PTSD患者HPC激活增加。SHIN等[36]发现HPC激活程度与PTSD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这些相反的结果表明HPC可能在PTSD的形成机制中扮演了更为复杂的角色,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同时,目前缺少物理治疗作用于HPC的研究证据,这可能与HPC所处位置较深和其在PTSD形成机制中的作用不明有关。
1.4 岛叶皮质
研究发现,AMG、岛叶皮质和vmPFC组成了所谓的“恐惧环路”,岛叶皮质在这一环路中参与恐惧条件反射和消退、对厌恶刺激的反应以及对负面图像的预期[37-39]。ETKIN等[40-41]发现,PTSD患者的岛叶皮质处于过度活跃的状态,并且这种岛叶皮层的活跃程度已经被发现与PTSD症状严重程度相关。目前缺少物理治疗作用于PTSD患者岛叶皮质的相关研究,但由于其在PTSD发生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存在作为潜在脑区靶点的价值。
1.5 背侧前扣带回皮质(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dACC)
研究发现,dACC在条件恐惧的编码和表达中起着重要作用,dACC的厚度与恐惧表达呈正相关[42]。LINNMAN等[43]研究发现,个体dACC的静息态代谢率越高,个体的条件反应幅度也就越大,这进一步支持其在恐惧表达中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PTSD患者的dACC区域呈高激活状态[44],这可能是PTSD患者反应性显著增高的重要原因。因此,dACC也可作为PTSD物理治疗的潜在脑区靶点。
1.6 外侧颞叶皮质(lateral temporal cortex,LTC)
PTSD的核心症状之一是对创伤事件的重新体验,大量研究表明,LTC与这一症状有关。首先,组织病理学研究发现AMG、岛叶皮质和LTC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神经影像学发现,这些结构是同一功能网络的一部分,这表明AMG、岛叶皮质和LTC形成了一个反馈环路[45-46]。其次,研究发现在神经外科手术期间对LTC区域进行直接电刺激可以引发个体多器官的、生动的“闪回”[47]。此外,有研究报道LTC的结构完整性与PTSD患者创伤性闪回的频率相关[48]。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报道,在静息状态,与未患PTSD的退伍军人相比,患有PTSD的退伍军人右侧LTC内神经元活动过度并且具有区域内的高连接性[49]。ENGDAHL等[50]发现当PTSD患者不再符合PTSD诊断标准时,LTC区域内的神经元活动减弱。综上所述,PTSD患者的LTC功能存在障碍,并且这种功能障碍与对创伤事件的重新体验这一核心症状直接相关,由此可知,LTC也可作为PTSD物理治疗的一处潜在脑区靶点。
1.7 其他大脑区域
最近研究发现外侧缰核区(lateral habenular nucleus,LHb)和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参与个体的压力应激反应调控。临床前模型PTSD小鼠LHb脑区神经元活动增强,同时与记忆相关的分子水平增加,而VTA区则表现出活度下降[51-52]。目前这两个区域参与个体压力应激反应的调控机制尚不清楚,但因为压力应激反应失调是PTSD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因此,这两个区域存在作为潜在脑区靶点的价值。
2 连接状态异常的潜在脑区靶点
根据以上研究表明,PTSD的核心症状涉及多个特定脑区的功能状态异常。此外,特定脑区之间的连接状态异常同样会导致PTSD核心症状的发生,这一观点可以从离散神经网络的角度来解释。神经影像学的综合研究结果表明,PTSD中多个大规模的功能网络被破坏,主要包括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显著性网络(salience network,SN)和执行控制网络(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ECN),即“三重网络模型”[53]。DMN的核心区域由vmPFC、内侧顶叶区域、后扣带皮质和HPC后部连接构成,其主要功能是参与自我参照加工和情景记忆,在PTSD患者中DMN的连接性降低,这可能与患者恐惧学习和记忆功能障碍有关[54]。SN的核心区域由dACC、岛叶前部、AMG和HPC前部连接构成,主要参与对于显著环境刺激的检测和注意方向,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PTSD患者的SN连接性显著增加,这导致了威胁检测的增加和ECN连接性中断[55-56]。ECN的核心区域主要由dlPFC和外侧后顶叶区域连接构成,主要参与包括情绪调节和工作记忆在内的执行功能,在PTSD患者中ECN有不同程度的连续性中断[57]。由此可见,当这些由特定脑区连接构成的功能网络连接性出现问题时,同样会导致PTSD的发生。目前关于颅电刺激疗法的作用机制就被认为是通过改变边缘系统、网状激活系统、下丘脑活动性以及DMN连接性,最终通过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肾上腺髓质轴而产生治疗效应[58]。因此,使用物理治疗作用于连接状态异常的功能网络内的相关脑区靶点,通过降低异常高连接状态、增强异常低连接状态,进而恢复其正常生理状态,最终可能会有效改善PTSD核心症状。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PTSD是一种脑回路紊乱疾病,特定大脑区域的功能状态异常或连接状态异常是导致PTSD核心症状的重要原因。在PTSD患者这些功能状态异常的脑区中,AMG、岛叶皮质、dACC、LTC以及LHb表现为过度活跃状态;vmPFC、dlPFC以及VTA表现为活动低下状态;HPC在部分患者中呈现高激活,在部分患者中却表现为低激活。在PTSD患者脑区间连接状态异常的功能网络中,DMN表现为脑区间连接性降低,SN表现为脑区间连接性显著增加,ECN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中断。使用物理治疗作用于上述特定脑区,通过调节脑区内神经兴奋性,例如抑制异常高功能激活状态、增强异常低连接状态等,最终将功能异常或连接异常的脑区恢复至正常生理状态,可能会有效治疗PTSD核心症状。目前上述一些脑区靶点已经被应用到物理治疗PTSD核心症状的研究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例如AMG、vmPFC和dlPFC。另外一些脑区目前缺乏相关研究证据,例如岛叶皮质、HPC、dACC、LTC、LHb和VTA。这可能与这些脑区所处位置较深,不易直接刺激有关,但根据上述其在PTSD发生机制中的作用,这些脑区存在作为潜在脑区靶点的价值。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不同物理治疗方式的作用机制及原理有所差异,刺激不同脑区时使用何种物理治疗方式才能使治疗效果达到最佳尚不明确;HPC在PTSD机制中的作用复杂,对该区域进行物理治疗时应该使用抑制性治疗还是增强性治疗目前尚不清楚;一些研究表明刺激单侧脑区即可达到显著治疗效果,另外一些研究却表明需要同时刺激双侧脑区才能产生治疗效果,物理治疗时单双侧脑区的选择问题尚未解决;同时刺激多个异常脑区能否增加治疗效果缺乏研究支持。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以为后续临床上PTSD物理治疗的标准化和高效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