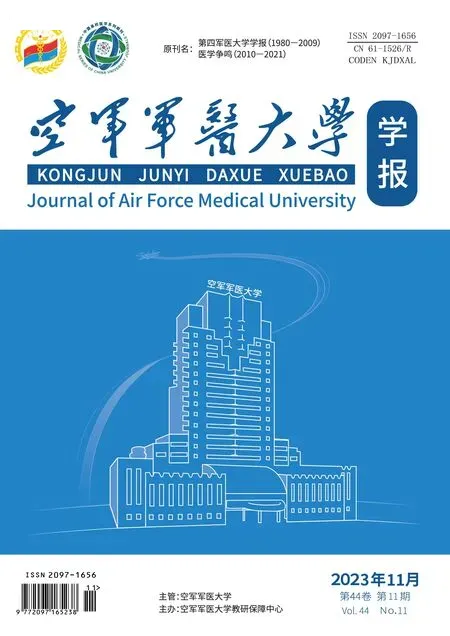神经病理性痛等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的特征、机制和治疗研究进展
潘语绮,董子意,赵 艳,卢广泉,连逸蕾,韩静仪,高 方
(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1神经生物学教研室,2学员四大队,陕西 西安 710032)
睡眠是一项重要的生理活动,帮助恢复脑力和体力,对记忆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常生理睡眠包括不同的分期,分为非快速动眼睡眠期(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以及快速动眼睡眠期(rapid eye movement,REM)。其中NREM睡眠又分为4期,1、2期为浅睡眠期,3、4期为深睡眠期。睡眠障碍指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主观不能正常睡眠的情况,通常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的睡眠-觉醒节律紊乱、睡眠行为异常和睡眠质量降低等。其中,睡眠质量评价的指标包括有主观睡眠感受、客观睡眠时长、入睡时长和睡眠效率(即总睡眠时间占总卧床时间的比例)、睡眠分期数据、日间功能及嗜睡状态等。睡眠障碍可以是独立存在的原发性疾病,也可以继发于神经病理性痛等伤病情况,其主要表现有入睡困难、睡眠维持障碍、早醒、节律障碍以及异态睡眠等。长期严重的睡眠障碍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脑力和体力,例如大脑认知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给患者甚至官兵的生活和作业效能造成负面影响[1-2]。特别是慢性疾病造成的继发性睡眠障碍,通常具有明确的诱因和规律,对其特征和机制进行观察和研究,会为睡眠障碍的认识和治疗带来很多提示和帮助。因此,本文就神经病理性痛等伴发的继发性睡眠障碍进行论述,针对相关睡眠特征变化、睡眠障碍发病机制和现有治疗方法进行总结。
1 神经病理性痛伴发睡眠障碍
神经病理性痛是指躯体感觉神经系统损伤而造成的疼痛,临床上可以由脊髓损伤、椎间盘突出、糖尿病或病毒感染等疾病引起。神经病理性痛是慢性痛的一种,其具体表现有自发性疼痛(无刺激引起)、痛觉过敏(轻微刺激引起)和触诱发性痛(非伤害性刺激引起)等。神经病理性痛的治疗十分困难,对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均造成极大的痛苦。
多项研究均表示神经病理性痛通常伴有睡眠障碍,而睡眠障碍的发生又会加剧痛觉过敏[3-5]。神经病理性痛带来的睡眠障碍包括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及睡眠-觉醒节律障碍。具体表现有夜间失眠、夜间清醒期延长、睡眠效率降低、NREM持续时间减少[6]以及白天嗜睡等。
神经病理性痛导致睡眠障碍的神经机制复杂多样,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包括参与调控的脑区和参与调控的神经递质。
1.1 参与神经病理性痛相关睡眠障碍调节的脑区
首先,神经病理性痛中参与痛觉调节的脑区已经被广泛地研究,包括有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岛叶皮层、海马、杏仁核、丘脑、中脑等。在这些脑区中,有很多也同时参与调节了疼痛引起的睡眠障碍变化。例如,PFC和中脑中缝背核(dorsal raphe nucleus,DRN)之间存在神经纤维联系,参与调节疼痛引起的睡眠觉醒增多[7]。DRN的5-羟色胺能神经元投射至PFC,在疼痛刺激下,释放至PFC的5-羟色胺含量升高,促进小鼠觉醒。另一项研究则揭示了ACC脑区、尤其是ACC中的生长抑素和小白蛋白阳性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神经元在疼痛和睡眠的相互调节中发挥作用[8]。ACC脑区的上述两种GABA能神经元的激活既能提高睡眠相关的delta慢波的功率,也能降低机械痛阈值导致痛觉敏化,从而可能在疼痛和睡眠的演化中发挥调节作用。外侧缰核作为大脑中的反奖赏中心,会被疼痛信息激活[9];另一方面,外侧缰核表达大量褪黑素受体,接受褪黑素这一重要睡眠调节因子的调控。在神经病理性痛的情况下,患者褪黑素激素分泌异常,通过对外侧缰核的调控而调节患者的睡眠和疼痛。
1.2 参与神经病理性痛相关睡眠障碍调节的神经递质
研究提示,神经病理性痛的发生机制为损伤神经相关的抑制性神经递质下调、兴奋性神经递质上调,使得痛觉敏化。睡眠障碍则与中枢神经系统特定结构的破坏及类似的神经递质传导异常相关。例如,在选择性坐骨神经损伤的神经病理性痛模型中,小鼠产生痛觉敏化的同时睡眠发生紊乱。进一步的神经机制研究发现,ACC脑区细胞外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10-11],对疼痛传导的抑制作用降低,痛觉敏化发生;同时对睡眠的促进减弱,导致睡眠减少。与此同时,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释放增加[8,12],谷氨酸等兴奋性神经递质在觉醒系统中有重要作用,调节促醒。并且导致该脑区GABA神经递质降低的原因在于星形胶质细胞也发生活化[10-11],GABA转运蛋白的表达增加,将GABA转运至星形胶质增加,从而降低了细胞外GABA浓度,参与了神经病理性痛时睡眠-觉醒的变化调节。此外,研究发现另一参与睡眠唤醒神经系统的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也有变化,其在模型小鼠的大脑PFC分泌水平上调,当给予去甲肾上腺素受体抑制剂后,小鼠痛敏下降、清醒期缩短、NREM延长并恢复正常[13],由此推测去甲肾上腺素的变化也参与了神经病理性痛相关的睡眠障碍,并且是具有潜力的治疗靶点。
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神经病理性痛伴发的睡眠障碍主要采用药物治疗,包括加巴喷丁、普瑞巴林等GABA衍生物,米氮平类的兴奋性神经递质拮抗剂[14]以及作用于褪黑素受体的新型药物钩吻碱[15]。
2 情绪障碍类疾病伴发睡眠障碍
神经病理性痛患者除因感觉异常导致睡眠障碍外,也经常会出现情绪障碍,包括焦虑障碍、抑郁等。这些情绪问题也可能是导致睡眠障碍的重要原因。
2.1 焦虑障碍中的睡眠障碍
焦虑障碍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惊恐障碍、场所恐惧症等。焦虑障碍患者通常具有睡眠相关问题,而睡眠障碍患者也常引发焦虑障碍等各类精神疾病。据统计,高达50%的原发性失眠患者存在焦虑症状[16],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分清两者之间原发与继发的关系。基于两者的紧密关系,本文中以伴发疾病来进行描述。
2.1.1 GAD伴发睡眠障碍 GAD又称慢性焦虑,伴有自主神经紧张、肌肉紧张和运动不安。在焦虑障碍各亚型中,GAD与失眠的关系更为密切。失眠不仅是GAD患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同时也是GAD的前驱症状之一[17]。
GAD患者和健康人群对照相比,其睡眠障碍特征是入睡困难以及睡眠维持困难,具体表现为入睡时间长、睡眠连续性低、梦魇频繁、夜间觉醒时间延长、白天睡眠增加、白天觉醒困难、睡眠质量和睡眠效率降低等[18]。同时,患者的多导睡眠图显示,24 h内睡眠所占比例降低,REM的持续时间与周期减少,NREM中1、2期浅睡眠增多而3、4期深睡眠减少[16]。
虽然女性GAD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但以往GAD和失眠共患病的研究显示,GAD相关失眠的发生率不存在性别之间的差异,同时发现年龄越大的GAD患者更容易出现失眠问题[19],这与中老年人失眠总体发病率较高的研究结论一致。
2.1.2 惊恐障碍伴发睡眠障碍 惊恐障碍又称急性焦虑障碍,是指突然发作的、不可预测的、反复出现的、强烈的惊恐体验,伴濒死感和部分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症状。
夜间惊恐发作是惊恐障碍患者中常见的睡眠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睡眠体验和生活质量。夜间惊恐发作后,患者再次入睡困难,同时发病时强烈的恐惧体验使患者出现继发的预期性焦虑或回避行为,害怕睡眠。这反而会引起慢性间歇性睡眠剥夺,从而加重患者睡眠紊乱和惊恐发作次数及症状。患者多导睡眠图显示惊恐发作常见于浅睡眠向深睡眠过渡期间,即NREM 2期向3、4期转换时。多导睡眠图还显示惊恐障碍患者睡眠效率降低、REM潜伏期(即从入睡到发生REM睡眠的时间)缩短等[16]。
2.2 抑郁症中的睡眠障碍
抑郁症表现为持续而显著的情绪低落、抑郁悲观。在抑郁症患者中,睡眠紊乱是一项重要的临床症状。同时,睡眠障碍有很大的概率会早于抑郁症发作出现[16]。在一般人群中,将近20%的失眠患者与大约10%的睡眠过多患者存在抑郁相关性睡眠障碍[20]。据国外一项研究显示,重度抑郁症患者中,失眠等睡眠障碍的患病率高达90%[21]。
抑郁症患者的睡眠特点表现为:入睡潜伏期延长,夜间觉醒增加,导致睡眠碎片化、睡眠效率低下;同时患者REM潜伏期缩短,REM时间延长,导致REM比例总体增加。在患者一级亲属(未患病)中也发现REM睡眠潜伏期缩短的现象。另一方面,患者的NREM缩短且分布异常。脑电图数据显示,健康人群在第一个睡眠周期中出现最大的NREM峰值,而抑郁症患者则在随后的几个周期中产生[22]。
根据目前研究,与抑郁症睡眠障碍相关的神经机制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单胺类神经递质。正常生理睡眠由NREM过渡到REM是伴随着单胺能神经递质(儿茶酚胺、5-羟色胺)的降低,同时有胆碱能递质的增加[23]。重度抑郁症患者中往往会发生单胺类神经递质失调,因此也导致了患者REM睡眠的异常[24]。其次是谷氨酸神经递质。抑郁症患者体内谷氨酸神经递质缺乏,然而在NREM睡眠的丘脑-皮质缓慢震荡期间,谷氨酸能信号传导起着重要作用[24]。最后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22]。研究表明,生理状态下,HPA轴主导分泌的皮质醇在深睡眠中分泌减少;治疗方面,对于皮质醇缺乏的抑郁症患者,其恢复正常REM睡眠需要皮质醇替代治疗,而对非皮质醇缺乏的患者给予皮质醇会减少REM睡眠的同时增加NREM睡眠,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22]。
3 发育性疾病伴发睡眠障碍
除了神经病理性痛以及情绪障碍外,一些神经发育性疾病中也常常伴随有睡眠障碍。
3.1 精神分裂症相关睡眠障碍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与发育相关的精神疾病,患者表现出感知觉、情感与行为的异常。精神分裂症患者具体症状表现为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阳性症状包括幻觉、妄想、明显的思维障碍及行为紊乱;阴性症状包括感情平淡、意志活动减退等。
睡眠障碍在精神分裂症中十分常见[25]。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睡眠启动和睡眠维持的障碍,总睡眠时间减少以及睡眠效率降低。在机制方面,不同研究[26-28]都发现阳性症状与REM睡眠和NREM睡眠的改变均有关,但可能由于各研究睡眠参数的量化不同、样本量小、患者异质性,研究结果尚不能获得完全一致的结论[29]。此外,华西医院精神科报告1例发作性睡病共病精神分裂症患者,其首发症状主要为白天嗜睡,后出现幻觉、妄想、异常言行等精神病性症状[25]。这一案例提示了精神分裂症和睡眠障碍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此外,严重的睡眠障碍与精神分裂症症状及预后都存在相关性[25]。有研究表明NREM睡眠3、4期和REM睡眠时长缩短,可能导致患者认知受损[30]。患者NREM睡眠2期纺锤波密度的减少也被证实与患者记忆巩固等认知功能减退有关。在治疗过程中,NREM睡眠的适当增加对患者陈述性记忆功能的改善有一定作用。
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氟哌啶醇、利培酮等)主要阻断中枢多巴胺受体,第二代药物(奥氮平、氯氮平等)能同时阻断多巴胺和5-羟色胺受体。前者可以延长患者睡眠总时间与REM睡眠时长;而第二代药物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可以额外延长NREM睡眠,这不仅改善患者睡眠状况,也可改善患者的陈述性记忆功能。
3.2 孤独症中的睡眠障碍
孤独症是神经发育障碍所导致的神经疾病,其核心特征表现为社交障碍和重复刻板行为[26]。睡眠障碍广泛存在于孤独症儿童中,可以导致患儿症状加重[31]。
孤独症中睡眠障碍具体可以表现为睡眠失调和异态睡眠。睡眠失调是指睡眠启动和维持的障碍。睡眠启动障碍又包括入睡时间延长或睡眠潜伏期延长,而睡眠维持障碍包括总睡眠时间的缩短、一次持续睡眠的时长减短、夜间觉醒次数增加以及早醒。异态睡眠则包括NREM和REM两个时期的障碍。NREM相关障碍可表现为夜惊,REM相关障碍包括有REM时长缩短、REM潜伏期延长、REM相关睡眠行为障碍(REM sleep behavior disorder,RBD)等问题[32]。
目前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睡眠障碍的神经病理发病机制包括睡眠-觉醒调控异常、昼夜节律相关基因突变和褪黑素代谢异常等。从睡眠-觉醒调控异常来看,孤独症患儿在REM睡眠时,肌肉活动增加,并伴随着RBD的发生[33],而单胺类神经通路参与肌肉活动的调节同时已被证实抑制REM睡眠,故提示孤独症中睡眠-觉醒异常调控可能主要存在于单胺类递质相关的神经通路和突触活动。其次,相关研究发现部分孤独症患儿存在昼夜节律相关调控基因的突变,例如PERIOD基因家族、TIMELESS、NPAS2等[34]。另外,褪黑素是由松果体分泌的激素之一,参与机体的昼夜及睡眠节律的调节。孤独症患儿的褪黑素合成通路以及相关调控基因发生突变,导致褪黑素昼夜节律延迟、分泌高峰降低[35]。
孤独症患儿睡眠障碍目前尚无特异性的有效治疗方法,临床上采用的是综合干预模式来进行治疗,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相关症状。综合治疗模式主要包括家长教育[36]、行为干预、药物治疗等。常用的药物包括镇静催眠药、抗抑郁药、抗癫痫药等,其中褪黑素的使用最为广泛[37]。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神经系统疾病与睡眠障碍关系密切。一方面,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睡眠中枢紊乱,昼夜节律异常,例如普遍发生的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睡眠效率降低等。另一方面,这些患者发生睡眠障碍后常常会使原有的神经疾病症状恶化。故深入了解神经精神疾病伴发睡眠障碍的特征和神经机制,从而助力于解决或缓解患者的睡眠障碍等,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在神经病理性痛伴睡眠障碍中,如何平衡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递质及神经通路是治疗研究的方向。除了GABA衍生物及兴奋性递质拮抗剂外,一些人工合成物、生物制剂及中药提取物正被逐步开发并运用于临床。对于情绪障碍类疾病,早期临床筛查和疾病诊断是一大难点,同时对诱发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也并不足够明确,因此还需更大样本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以明确疾病的诱因和标志物等,帮助临床医生实现疾病的早期干预,促使相关研究能够有所突破。目前关于孤独症儿童伴睡眠障碍的神经病理学机制研究还不够充分,需要深入解释其发病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研发靶向药物以实现对致病靶点的定向干预,从而减轻患儿的痛苦、获得最优疗效。总而言之,更多相关神经机制的揭示,将会促使出现更多可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伴睡眠障碍的特异性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