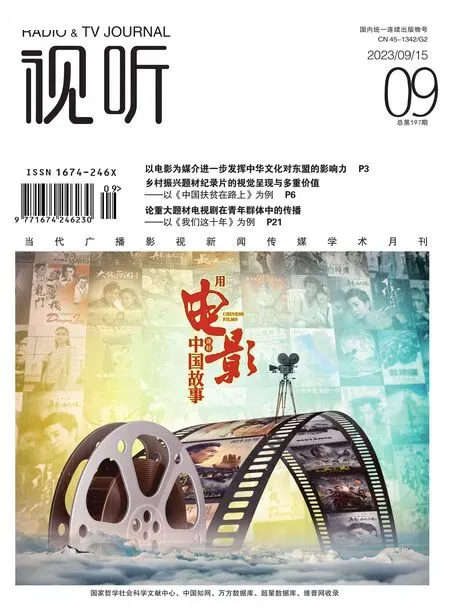人机传播共同体:“中之人”的自我呈现和场域关系
◎黎锦
在技术发展和粉丝经济的推动下,虚拟主播在各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其中以动作捕捉技术为主的虚拟主播已经从青年亚文化圈走出来,成为新的文化现象。随着“初音未来”和“洛天依”在青年群体中的广泛传播与崛起,腾讯、爱奇艺、哔哩哔哩网站(以下简称“B 站”)等众多资本平台开始布局虚拟偶像①,并呈直线上升趋势。VTuber 虚拟主播作为虚拟偶像分化出来的新样态,成为极具商业价值的资本焦点。与纯技术AI 主播不同的是,VTuber 背后需要和“中之人”(指在虚拟形象背后表演的人)互相协作共同完成一场表演。创作团队通过捕捉“中之人”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相关数据,利用技术使虚拟形象达到同步化的效果。“中之人”立场、性格、魅力、言语方式的差异,将会影响所塑造的虚拟主播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场域空间里,“中之人”通过虚拟主播形象这一媒介进行自我表达和呈现,并以此为“媒介”,与粉丝之间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中之人”作为动作捕捉型虚拟主播的核心,创造了更多的关系和情感流动。
目前,关于虚拟偶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虚拟偶像的生成路径、困境、技术视角下的人机关系等方面,研究个案基本是以“初音未来”和“洛天依”两个影响力较大的虚拟偶像为个案。综观相关文献,虚拟偶像的研究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学科领域,但是整体而言,研究者大都是从偶像粉丝、技术、消费主义相关角度出发,且相关论文大多发表于非核心期刊,说明学术核心学者对于虚拟偶像的关注还较少。
虚拟偶像作为二次元青年亚文化,活跃于“Z 世代”亚文化群体中,较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随着虚拟主播带货、虚拟AI 新闻主播的出现,以及江苏卫视于2021 年推出国产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2060》,青年亚文化进一步台前化,大量国内虚拟形象进入大众视野。虚拟主播是由虚拟偶像分化而出的一个门类,相关的研究不仅包括虚拟主播产业链发展现状、对虚拟偶像人格设定的分析、从技术角度出发探讨角色开发和运营模式,还涉及新闻AI主播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基于动作捕捉技术,由“中之人”扮演的虚拟主播。为此,笔者于2023 年3 月2 日在知网分别以主题、关键词为项目,以“中之人”“VUP”“VTuber”“虚拟UP 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涉及本文研究内容且关联度较高的仅有18 篇。关于“中之人”的研究大多数是在虚拟偶像、虚拟主播的相关文献中被提及,多数探讨动作捕捉技术,而对于“中之人”在虚拟主播表演中扮演的角色大多只是略微提及,并未以其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
“中之人”作为动作捕捉型虚拟主播的核心,创造了更多的关系和情感流动。正如彼得斯所说,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身体在场的焦虑就会出现。在和机器交流时,我们很难在一台机器和人之间作区别,甚至不确定是否在模仿交流(图灵测试)。②近几年,“冲塔”事件、“中之人”被孤立、“中之人”诋毁虚拟形象的问题频发。“中之人”作为虚拟主播的灵魂,是不可忽视的环节。“中之人”的隐私保护隐患、“中之人”培养体系、发表不当言论无人担责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让“人—机—人”和谐相处是虚拟主播、虚拟偶像产业有序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试图探索VTuber虚拟主播背后的“中之人”如何利用虚拟形象进行自我呈现,“中之人”和粉丝的互动关系如何构成,当前面临何种困境和伦理问题,以便更好理解虚拟主播的运营逻辑,构建人机共同体。
一、一场预设的表演
(一)虚拟IP与“中之人”
虚拟主播背后的扮演者“中之人”赋予虚拟主播更丰富的“人性”特点,在人机交互中凸显身体的在场感。“中之人”在“前台”完成一场预设的自我呈现,并在其中模糊其社会身份。虚拟主播可以根据人设、性别、技能、所在社团进行分类,并在发展中形成虚拟IP。“中之人”扮演型虚拟主播最大的特点便是虚拟形象和真实人物虚实融合、一体两面。③相对应地,根据关联程度,可以将“中之人”分为虚实一体型和虚实分离型两类。
虚实一体型,即虚拟形象约等于“中之人”。虚拟主播的皮囊和“中之人”的灵魂混为一体。当虚拟形象进入粉丝视野时,便是按照“中之人”的性格塑造,或者是由“中之人”不断填充,丰富虚拟人物的性格,通过“中之人”的性格魅力吸引粉丝。这一类型的“中之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可以结合自身和虚拟主播的人设,不断为粉丝输出内容;或者在交互过程中透露“中之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经验。当然,如果“中之人”所塑造的虚拟主播受到粉丝的欢迎,企划公司甚至可以选择性地公开其身份,开展相关企划活动,开启附加的产销模式。在VTuber“绊爱”A8事件中,粉丝对于“绊爱”的关注大多来源于初始的“中之人”春日望,因为加入了新的“中之人”而引起了粉丝的不满。这一类“中之人”大多数极具个人魅力和明星特质,和虚拟形象绑定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企划公司一般不会轻易选择更换“中之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之人”就是虚拟主播,虚拟主播就是“中之人”,“中之人”对虚拟形象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虚实分离型,也就是虚拟主播本身大于“中之人”。虚拟主播形象是通过绘画、3D建模、输入相关人设数据塑造而成的,制作团队对其的外在、性格、肢体动作具有自主权,也会考虑受众和市场的需求去定制虚拟形象。这种类型的虚拟主播由整个团队共同建设而成,一旦被设定便具有了内在灵魂,其本身存在的商业价值大于“中之人”。“中之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虚拟形象提供面部数据、动作数据等,对虚拟主播进行输出,“中之人”的行为、言语方式受到虚拟主播本身人设的控制,在表演时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类“中之人”和虚拟形象的密切程度较低,制作方将大量资本投入到塑造和运营虚拟主播形象中,一旦“中之人”中途退出或者受到其他不可控因素影响,制作方可以选择更换“中之人”。例如,在“新科娘”事件中,投资方可以选择更换“中之人”以维持虚拟主播的运营。
(二)自我呈现:被颠覆的“前后台”
在虚拟主播实时直播的场域空间里,“中之人”具有多重身份。一方面,“中之人”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支点,有个人性格、行为习惯;另一方面,作为虚拟主播背后的动作表演者,“中之人”又兼具虚拟主播的属性和人设身份。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对虚拟主播而言,“中之人”通过技术设备(具体技术),捕捉动作或面部数据,将身体的某一个元件转移至虚拟主播中重构身体,进而介入自我表演的场域中,与粉丝产生连接。
戈夫曼在20世纪提出“拟剧理论”。他认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表演。生活中的每个人,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场景,按照一定的要求,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角色呈现。”这种角色呈现指的是人们为向观众展现他们所期待的形象而所做出的策略和表演。为了更好地在直播情境中向粉丝展现虚拟主播的形象和性格,“中之人”作为虚拟主播背后的“演员”,需要在创作团队为其搭建好的“前台”中按照“剧本”“人设”进行表演。如果是内容输出相对自由的“中之人”,则可以借助虚拟主播的形象,更为真实地进行自我呈现,在实时互动过程中,其双重身份随时切换。“中之人”处于屏幕后方,可以不必像女团成员一样时刻保持自己的状态和表情,因为在技术加持下,虚拟形象是完美的,这也让“中之人”的表演更为自然和放松。虚拟主播“奈璐”的“中之人”所呈现的虚拟主播魅力既包含了创作组的设定,也包含她自身的内容输出,但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有预设的表演。④
“前台”与“后台”是戈夫曼拟剧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前台”指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进行表演,向身边的观众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后台”则是没有观众时放松的自我。假设虚拟主播所在平台是表演的“前台”,“中之人”在“后台”进行操作,但实际上“中之人”在动作捕捉现场的表演场域又属于个人的“前台”表演,其并未将自己的“后台”展现给大家,那么“中之人”在现场进行动作捕捉的表演到底是属于“前台”还是“后台”?不能明确的是,网民在网络上是否将无意识、无观众的自我进行呈现。实际上,在“中之人”进行自我呈现时,戈夫曼提出的“前台”和“后台”的概念被颠覆,“前台”概念明确划分了表演者进出角色的所在区域,具有二元对立的嫌疑。⑤正如有学者提出,是否会有一个相对中间的地带可以连接两个区域?在虚拟直播的场域里,幕后工作室就是相对中间的地带。在虚拟主播进行自我呈现的过程里,“前台”和“后台”二者的界限不再明显,“前台”已经不再是戈夫曼笔下的“前台”。与其分清二者的边界,不如考虑“前台”和“后台”可以相互帮助,从而达到所期待的效果。
青椒叶片小,蒸腾量小,一般在坐果前不需浇大水,出现干旱时可浇小水。每次浇水要在晴天上午浇,提高棚内温度,中午将潮气放出,避免棚内湿度过大造成病害流行。底肥施足后,坐果前不用追肥,防止徒长,造成“三落”现象。
二、媒介化的关系
在“中之人”赋予情感的这场表演中,“人—机—人”的关系是一段被编码的关系。虚拟形象既作为一套被编码的符号系统而存在,又作为人与人关系形成的中介而存在。学者刘海龙认为,对于传播而言,肉身的在场是至关重要的。⑥此处,身体在场指的是虚拟形象的具身性。企划公司通过绘画、3D建模、输入虚拟主播人设数据,再将“中之人”身体的某个元件移植到虚拟形象中,从而在直播过程中形成一个“类人类的身体”,给观众一种新奇的在场感。在这场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的交互表演中,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以虚拟主播为纽带,“中之人”、虚拟主播和粉丝形成了不同模式的关系,而关系存在的前提是虚拟主播“身体”的在线。
(一)作为媒介的虚拟主播:不被看见的关系
在“中之人”、虚拟主播、粉丝三者的动态交互过程中,一般企划公司会对“中之人”的身份进行保密,控制“中之人”和粉丝的距离,在表演中也会要求“中之人”尽量不透露个人经历等隐私问题,仅通过内容输出和人设维持着和粉丝的关系。在5G 时代的人机传播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考虑人机关系,更要考虑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个体间的关系。虽然“中之人”和虚拟偶像存在表征差异,但是“中之人”在进行表演时会不断向虚拟主播填充自己的内容,甚至当作是自己的舞台。人大脑内的思维——这个过去我们认为始终与人这一物质不能分离的对象,也开始出现了脱离人体的可能。⑦“中之人”的思想、性格等身体元件转移到了虚拟主播身上,模糊了其社会身份的特征。“中之人”与粉丝的情感交流汇集在虚拟主播身上,虚拟主播只不过是类似于手机、电脑等人与人交互的中介,但实际上和粉丝构成间接关系、发生情感流动的是虚拟主播背后的“中之人”,这种间接的关系时常被忽略。
(二)作为偶像的虚拟主播:粉丝与偶像的关系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2 年中国虚拟偶像行业研究报告》显示,虚拟偶像关注者多为90后二次元爱好者,对UGC(用户生成内容)认同度极高,具有较强的付费意愿,认为虚拟偶像最重要的三个元素是人设、外形和才艺水平。虚拟主播在青年尤其是二次元群体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粉丝通过关注、点赞、弹幕与虚拟主播发生情感流动。除了“中之人”和数据采集设备之间的人—机关系,虚拟主播作为技术“机器”,在交互中形成了偶像和粉丝性质的人—机关系。此外,粉丝在观看某个虚拟主播的直播时,可以通过非排他性的弹幕实时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交流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内容,粉丝和虚拟主播形成关联后,会自动形成新的虚拟社群。V兔波(虚拟主播爱好者社区)将虚拟主播进行分类,并设置相关的讨论专区,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寻找社群,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由此得以连接。
三、余论与冷思考
虚拟主播的发展压缩了真人的网络直播空间,技术黑箱和包括“中之人”在内的创作团队的存在,依然会在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中之人”作为动作捕捉型虚拟偶像的关键环节,其本身的权益存在被侵犯的风险,也是引发伦理问题的缘起,虚拟偶像的产业发展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空间。其次,“中之人”的自我呈现也极大影响虚拟主播的发展。二次元群体中有许多人不能接受“冲塔”行为,即便企划公司做好了保密工作,依旧会出现“中之人”的真实社会身份被曝光的情况,“中之人”的隐私保护存在一定的风险。最后,现实与虚拟的壁垒被打破,祛魅后的“中之人”,如果其真实社会身份与虚拟主播塑造的人设不符,其虚拟主播身上的特质就会逐渐从神坛上褪去,上文谈及的以虚拟主播为媒介构建的关系就会面临破裂的风险。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并未明确由“中之人”扮演的虚拟主播所进行的直播是否被纳入规范管理范畴。模糊的“前台”和“后台”边界,加上“中之人”具有相当程度输出内容的自由,虚拟主播极有可能成为“中之人”的发声器。Guzman研究发现,当人与虚拟助手交互的时候,人们自然地认为是在与机器而非设计程序的程序员进行信息交互。⑧粉丝不会觉得虚拟主播是个“虚假存在”,而是会认为其真实存在,“中之人”赋予的“人味”正是虚拟主播存在的真实性依据。虚拟主播背后的“中之人”是引发伦理问题的重要因素,存在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有必要对虚拟主播直播产业进行规范管理。此外,企划公司要在“中之人”选拔的过程中严格把关,不仅要考虑其专业水平,还要确保表演者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开展企划活动。
在媒介化的社会里,虚拟主播顶着完美人设光环,扮演着偶像的角色,以新奇的在场感吸引了众多的青年受众。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下,虚拟主播无论是一体型的“中之人”还是分离型的“中之人”,其自我呈现更像是一场运营者提前预设的表演,一场为了迎合市场的完美表演。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以虚拟主播为媒介中心展开的一场表演,以及在这个场域中发生的新的关系勾连和情感流动,资本逻辑正是以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中。理解虚拟主播运行的内在逻辑,理解新场域中的虚拟主播在“前台”的自我呈现过程以及关系构成,对于规范行业发展和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监管,共同推进人—机的协调发展,实现人—机共同体具有一定的意义。
①黄婷婷.虚拟偶像:媒介化社会的他者想象与自我建构[J].青年记者,2019(30):28-29.
②[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35-341.
③周港回.虚拟偶像:产业驱动与粉丝参与下的新商品[J].视听,2021(04):116-118.
④中之人:虚拟偶像下的真人到底是怎样的?[EB/OL].虎嗅,2021-03-16.https://www.huxiu.com/article/415196.html.
⑤田雅楠.戈夫曼“拟剧论”的再思考——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谈起[J].中国报业,2017(08):83-84.
⑥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02):37-46.
⑦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J].新闻记者,2019(12):4-12.
⑧王睿.作为传者的人工智能:自动化新闻业中人机角色的再认识[J].东南传播,20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