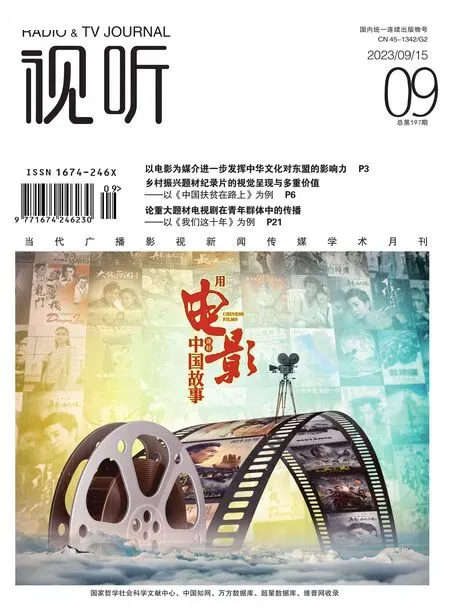弥合、厘革与在场:参与式影像在乡村纪录片中的嵌套探究
◎陈昊
纪录片是故事的影像形态,是一种传递重要讯息的艺术媒介。基于当下受众临镜自照的审美愉悦,承载艺术情感教育功能的影像就通过镜头组接与时空重构去企及审美主体的文化预设,从而达到观者认同。随着影像的呈现媒介不断下沉,参与式影像在纪录片中的钳扣又使得艺术呈现形式趋于多元,极大拓展了纪录片叙事的建构路径。
西方早期纪录片的制作多为真实的个人化记录,如《印第安人》《五至七时的克莱奥》,这时已经出现了参与式的叙事雏形:拍摄参与、视角参与、对话参与。参与式影像在中国纪录片中的应用有迹可循,早在20世纪80 年代中日合拍的纪录片《望长城》中就出现了“对话破壁”的参与指征。该片体现了我国乡村类纪录片赋权主体的叙事向度:主体视角开放性、矛盾构建弱化性、交互受众参与性。作为主流影像话语的影像再延展,参与式影像更多地实现了“自我表达”。在当代乡村振兴的视域下,参与式的嵌套和缝合影像双重视角,能够为乡村纪录片带来全新的创作视角。
一、弥合:乡村纪录片的元素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提出,故事的诸要素包含有具体的结构、事件、场景、节拍、序列、幕与情节。在这七大元素中,结构、时间、场景和情节主要服务于叙事内容,导演的艺术再造依赖于结构、序列与幕有意味的拼贴。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①笔者认为,乡村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主要在结构和情节两大元素中提纯。在故事镜头语法中,参与式影像的适宜嵌入,可使影片更为个人化,更贴合受众后现代的审美视野,这也是影像得以国际化传播的重要“在场”因素。
(一)叙事基因的重组
乡村纪录片的叙事展现得益于故事结构、故事场景的生产与再生产。它能将纪录片的故事基因内化,更赋予内容戏剧张力,同时它也是创作主体对纪录片主人公生活事件做出的一系列有逻辑性的筛选。首先,叙事结构的顺序式、交叉式和板块式以不同的语法样态展现了思想者的自我历程,这是乡村纪录片的影像基石。纪录片《沙与海》就以复线交叉式结构将不同时序的主体安置在同一幕中,将海洋地区的渔民刘丕成和远郊沙漠中的刘泽远对比展现,延展出人文生态的叙事主题。其次,场景在故事本体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保持亲切感,受众的生理感官(听觉、视觉)层级迅速代入,激发情感认同。事件场景能够赋予人物价值,且其在场景内发生了能够改变主题价值的社会行动。例如,《龙脊》关照了偏远的广西西北山区,《最后的山神》呈现了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人的原始状态。
影片结构同样受现场取材的摄制手段、旁支视点的影响。乡村纪录片主要探讨人与自然、社会百态等问题,反映人性和社会现实,拍摄中要求即刻捕捉,影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构图与视角混乱。但纪录片以反映真实为首要目标,此刻融入个人化的参与视角,如Vlog等影像,能够有效避免叙事带来的空缺。最后,影片结构与主题的延展互联,素材的精细化剪辑所呈现出的具象的情感能够激发受众特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类型迥异的纪录片传递的主题不同,结构的布局与设计就必须在此基础之上将受众的心理预期置于其中。弗拉哈迪就曾在《北方的纳努克》中主张以探险者的视角去拍摄对象,用虚构与非虚构的叙事框架完成对影片的排列。中国乡村纪录片从西方纪录片中汲取叙事营养,既摆脱了单品极致之上的单元式结构阐述,又巧妙地以全球化的自然地理视野去呈现东方美学。
(二)戏剧情节的扬弃
纪录片情节可分为戏剧性情节和非戏剧性情节,它们都属于故事中的“小情节”。戏剧性情节有一系列的环节,如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并且人物通过语言和行为来向受众传达情绪,这是戏剧性情节在影片中运用的典型特征,在有限的空间叙事中厘定了接受者的情绪与观看体验。非戏剧性情节没有定向给予受众更多的导演意识,没有给予观者多元的思考空间。为了使故事更接近本身,人文纪录片更多地从生活细节中挖掘情节,不依靠人为干预的二次加工,在影片中更多地追求客观主体自我表现的本质生活。在冷静平实的镜头拍摄下,以画面留白的方式给予受众无限的思考空间。
乡村纪录片具有非戏剧性情节叙事的倾向,较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90年代电影史的第三次变革:技术革命的鼎新。夺目和绚丽的特效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狂欢,让其置于一种短促的幻觉之中。在此环境的渲染中,中国第六代导演认为虚拟建构的视觉文化会蚕食现实本身,着力于本真、自然的纪实美学更能够引发人文思考。长镜头美学、客观记录式影像的拍摄方式引发了大众思潮,同时也极大地辐射到了纪录片的创作领域。以非戏剧性情节为索引的纪录片打破古典叙事,以平缓叙事的叙事策略,不强调散点式的影像框架,而是直接聚焦于被摄者,呈现其完整模样。影片多数没有中心思想,可以让受众在主观认同的同一性与偏差性上产生陌生异化,实现更高层次的审美升华。以《第三极·大山儿女》为例,导演以海拔为5154米的绒布寺为故事线索,阿旺桑杰是寺庙的守护者,他对于藏在寺庙里的神圣洞穴有着特殊的个人情愫。该片以阿旺桑杰为中心点,向周围扩散他的亲属是如何看待这份对洞穴特殊的“守护”的。影片情节以一拖多的叙事魔盒形成了闭环,这种非戏剧的手法既避免了传统好莱坞一波三折的情节,又避免了纪录片中顺承的单线陈述,这是凌驾于第三人称凝视之上的记录。它通过蒙太奇式的组接与重构,实现了导演意图的传递。同样,《寻路乡村中国·开山》介绍了西藏的墨脱县被喜马拉雅山脉、岗日嘎布山脉阻隔,以个人化的视角展示了生活中的自然障碍,这是一种非戏剧性的自然再现,主体在其自身场域中的社会行动被毫无保留地悉数记录。
二、厘革:参与式影像的嵌入
巴赫金在狂欢化理论中提出,因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弥补,所以颠覆性和抗争就成了最显著的特点。其最终指向是个体的生命自由,饱含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短视频美学的盛行使得个人主义空前盛行,大众对于影像的凝视多停留在私人化领域。参与式影像的出现则是“去权威化”思潮的解放。普通人拿起相机,记录自我的真实生活,继而呈现在社交媒介平台。“小”影像是恣行无忌的,而纪录片却具有现实审美与教育功能。将两个看似矛盾的主体相互联结补偿,组成一段互联共情的影像让它们互为条件,这便是参与式影像的植入价值。
双重影像的跨界对话可以带来情感的错位,能够拓展有限的叙事时空,在视角的相互移位中实现主体人物弧光的升华。在影像语言现代化的思潮下,参与式影像内容应当承担起情感社会化指涉的风向标功能,建构起个人与当代的思想链接。而乡村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引领,向大众输送着边缘人物或社会事件最为原始的情动样态。下文分别从身份凝视、社会反思两个层面探讨二者的价值互文。
(一)社会身份再定位
故事的序列排布能够使主体身份从认同到迷思再到认同回归,形成一种正向循环。参与式影像的融入,激化了关于自我社会身份的再定位,能够升华主体的人物弧光。乡村纪录片的一个序列包含两到五个场景,且每个序列内的场景的跳跃也暗示着故事情节的加剧。正常的序列最少相当于一个较为完备的事件,它不同于文本的序列设计具有单个完整的时空,影像的序列可以前后冲突与矛盾。场景的交叠构成了巨大序列,它们的集合就承载着下一个更有价值的序列。正常序列的顺序与事件发展逻辑相符合,与线性剪辑并行。非正常序列出现在板块式结构和交叉式结构的纪录片中,非线性剪辑的方式赋予影片更为深刻的主题。拆分单个序列可以得到至少两个故事场景,纪录片里的单个序列包含人物的原始身份和人物面临的核心问题、事件当中的问题与目标之间的落差、此事件行动该如何进行等。选择一个场景,将其用参与式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使此序列内容异化于传统记录方式,表现的内容多为主人公克服困难的征程,画面呈现形式别致新颖。它一方面能够以内视角展现故事主人公面临的困顿场景,另一方面能够在时间结束后回归外视角,与下一故事场景自然缝合。参与式影像以“我”的视角去解决困难,更能印证自我身份的社会性。
乡村纪录片《窥山》以江西省吉安市的青原山为叙事轴心,故事地点有黄龙塘、彭家坊等。全片拒绝解说词,以平静的“个人”观察视角记录下漫散于青原山外的工业、农业,破败与繁荣。其中融合《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恒河沙,一沙一界”的佛儒文化,为东方伦理国际传播制造了突围可能。笔者认为,此类乡村影像与《天地玄黄》所阐述的保守主义文化是有共通之处的。他们以知识考古学的第一视角,不断地去“解密”蕴藏在一花一木一菩提背后的文化,而这也是目前乡村纪录片创作亟须研究的内容:若融入参与式影像或视角为第一人称的影像,那么如何赋予普通参与者真实影像的权利,使其身份在纪录片中被完备白描?
(二)乡村权利再显影
参与式影像融入了自我书写的影像,将口述中的日常具象化地还原,填补了当下的故事空白。其拍摄具有较强的即时性和随意性,多数是聚焦于主体此时此刻对于当下事件的思考与理解。创作者会直接将故事的“因”与“果”通过平铺直叙的方式传递给受众,呈现出扁平化的叙事视野。从影像本质出发,乡村纪录片中的主体趋向重视聚焦于具有仪式感的日常体验。创作者试图向外界袒露较为私域化的信息,在认同方面也能够获取共感的情感氛围。这种“去旁观式”的记录将私有的情感穿插于纪录片中,凸显出生活美学的韵味。当把参与式影像重新放回到纪录片史中时,参照当时的纪录美学潮流,我们看到了参与式纪录片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同时也关注到它与直接电影在作者权力、技术观念等方面的一致性。②20 世纪80 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纪录片《望长城》通过“发现与寻找”的公路式叙事模型,用一名记者的客观口吻将北部地区的民俗与风韵呈现于影像之中。影片运用参与式影像,用发现的眼光对记者的探秘过程进行原貌展示,再现民族化的原生态表达,以声画并重的方式进行纪实美学式的主题建构。在“寻找山声”的桥段中,摄像模拟观众的第一人称视角上山、坐车,整片的排布像是主人公的Vlog,探寻长城遗址风俗文化的变迁,延展出高度的文明价值。非戏剧性情节的铺陈,能够缝合观众与传统一波三折式影像的审美断代,它是一种真实的荧幕显影。片中,记者的“直接参与”被镜头放大,这种现实的在场与叩访直接催发了影像主体更为自我的乡村见解。而他在乡村中的思想生产过程也代表着乡村本体的社会价值衍生,并与当代乡村的跃升征程触动扣合,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拒绝虚构的社会权利显影。
三、在场:民族寓言的现代复魅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此后几年中,脱贫攻坚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功。社会空间的剧烈变革带动着村民个体、集体逐渐从困苦中抽离。乡村集体记忆纪录影像是对农村社会风貌、农民乡土生活的直接呈现,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优秀的乡村题材纪录影像对乡村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发挥着关键作用。③影像空间再现了中国从伤痕记忆体到小康社会的历史跨越,这种跨越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确认,连接着家与国的精神认同。
民族视角的建构不仅来源于时间积累和空间沉淀,还来源于个人口述。首先,乡村纪录片的拍摄要建立在文献阅读与田野调查的时间长度中;其次,需要在具体的叙事空间内找到与民族性、风俗化相关的故事场景;最后,转述村民的口述,间或让其与镜头对话形成参与性,这种民族视角就形成了建构模型,辅之以民族情怀的内容延展,便能取得纪录片影像民族化的跃升。参与式影像在乡村纪录片中的应用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中就已现雏形,它的内容形式作为一种后现代的生活美学,成为个人对未来希冀的感性载体。从《望长城》《沙与海》《娃儿》到《大山深处的画家村》《神山村的“凡人歌”》等,各类影像将镜头对准了自我的家庭社会生活,形成一次非正式记录的人格化影像实践。而其在人文纪录片中的钳扣,也是实践呈现样态之一。在具体影片中,影像填补了叙事空位,以自传的方式重回故事时空,增强影片的现场感,为纪录片的“真实”烙上印记。此后,参与式影像的应用再现时空与浓缩生活,构架起一座关乎民族与世界的第二精神记忆体。
当代国际化语境中,文化自信的建构发轫于集体的民族记忆。集体记忆需要媒介作为“记忆之所”来承载,而纪录影像的真实客观特性使其更好地成为人们对记忆进行社会表述的承载物,同时也将集体记忆广泛地传播开来,召唤出人们逐渐消逝的过去的记忆。④民族视角的国际外延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共同记忆——自然、动物、信仰,如纪录片《王朝》里的狮豹猴、《第三极》里的佛儒伦理等。这种影像来源于田野乡村间,从人类本体出发,影片的精神价值触碰到受众从“本域”到“全域”的认同血脉。所以,乡村纪录片的国际化视角突破路径可以从全球受众的共同体文化、民族意志、精神家园入手,尝试去探讨个人与社会、自然、文化遗产之间的耦合。
《众神之地·荒野上的轮回》重新审视了青藏无人区村落牦牛的神祇之位,以一种“让位”式的视角使野生动物回归自然。拍摄前期,曾海若导演率团队在科考站、救助站进行调研,且身处无人区,这是拍摄主体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远古图腾文化的敬仰。其中民族符号不乏有牦牛首领、狼图腾、羊族群等,这是对自然生灵万物的一种“复魅”。《山神归来》以寻找东北虎为线索,将承载了几万年的物种生存史完备记录,场景选择在温带针阔混交林的大兴安岭乡村,向人类阐述着自然景观与本我的强关联。其中的民族符号包含人参文化、萨满文化等,表达了对自然强劲生命的敬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的现代社会,此类乡村影像能够溯源到人类共通的伦理价值,从单一化到多元性的文化寻根之旅中,构筑起“命运与共”的精神场域。
四、结语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探讨了影片素材的甄选,提出电影创作工作的实质一定程度上可以界定为雕刻时光。电影人同样从包含海量生活事实的时间巨块中剔除所有不需要的部分,只留下能成为电影要素的部分,只留下能清晰描述电影形象的部分。乡村影像的民族性契合了这一类别的选择,它在东方伦理的构建下形成新型的现代叙事,且其破圈与出海路径皆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乡村纪录片剔除了好莱坞式英雄人物叙事、一波三折的跌宕结构,保留了世界文明共通认同的文化。这一剔除动作中蕴含着艺术的选拔,艺术选拔在任何一门艺术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由璀璨技术的簇拥带来的影像的视觉特效离不开形式化剪辑,但乡村纪录片的创作以真实饱满的风俗、人文和民族素材积淀与再现,传递着全球文明的当代价值。
注释:
①[美]罗伯特·麦基.故事[M].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54-55.
②王庆福,刘文卓.理解“参与式纪录片”[J].电影艺术,2023(02):122-128.
③陈新民,杨超凡.论乡村集体记忆的纪录影像叙事:主体、空间、媒介[J].当代电视,2021(05):71-75.
④张宗伟,石敦敏.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纪录片的意象之变[J].中国电视,2023(02):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