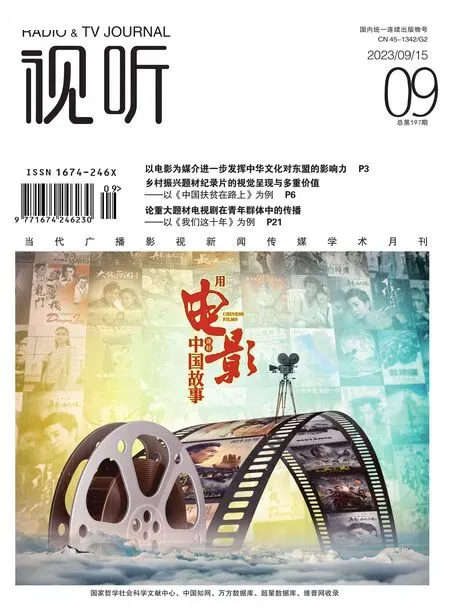《去有风的地方》:治愈系影视的共情传播
◎郑兰心
“共情”一词源于心理学,也可称之为“移情”,是指相同情绪或者情感传递扩散的一个过程。共情传播在新闻报道上要求报道诉诸真实情感的表达,从而达到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传播效果。而事实上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共情传播的策略也常常应用在影视剧的创作中,通过塑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来与受众实现共情。治愈系影视与共情传播密不可分。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视听语言的温柔诉说下,情感通过缓慢流淌潜移默化地治愈着每一位受众。
一、治愈系影视的前世今生
“治愈系”一词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于日本。日本学者木村传兵卫和谷川由布子在《新语·流行语大全》中对“治愈系”进行了如下的定义:“它并非指治愈某个东西本身,而是指带有治愈特征的事物(人物及作品等)。”①这一词之所以在日本流行,与当时日本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泡沫经济崩溃下的生活重担,新旧观念碰撞中人际关系的冷漠,社会发展达到瓶颈而趋于停滞,这些现实状况使得日本民众的心理防线岌岌可危,为缓和社会矛盾,调节民众压力,治愈系文化应运而生。
如今,我国社会步入了快速转型期,工业文明给现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异化”感和“失衡”感。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青年一代陷入了无边的空虚与迷茫之中。当下流行的“内卷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们通过玩“梗”和自我调侃来达到反抗的目的。为了缓解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压力,除了以玩“梗”反抗,人们还会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于是以“治愈系”为特色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受到了广大民众的青睐。治愈系文化在日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业制作体系,在治愈之风的吹拂下我国相关作品也开始萌芽。在工业化社会继续稳步发展的情况下,治愈系影视会以精神慰藉的形式长期陪伴在每个人身边。
二、创作本意:压力与释放
《去有风的地方》是2023年出品的代表性治愈系影视剧作品,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许红豆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单调,只有和闺蜜的相处会让她得到短暂的放松,可是闺蜜却不幸得病去世。突然失去至爱之人的打击让许红豆陷入了巨大的迷茫和不安中,于是她决定辞职,然后到闺蜜生前一直想去的云南,为自己进行一段疗伤旅行。她来到云南大理云苗村,在这里遇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感受了淳朴的人文风情,并邂逅了一段美丽的爱情。许红豆在这些力量的支撑下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决定致力于云苗村的旅游事业发展,她在有风的地方获得了重新出发的勇气。
《去有风的地方》主打温情、治愈的创作理念,是工业化社会的一次返璞归真。该剧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顺带还刮起了一阵去往大理的“风”。这证实了在青春剧、古偶剧、悬疑剧等爆款剧集火遍荧屏后,治愈系剧集以一股清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成为缓解社会矛盾、开阔个人心境的一种精神解药。编剧立足于当下的现实情况,针对受众的情感需求来进行剧集的创作构思,在各种快节奏、碎片化的信息传播中,以一种缓慢叙事、娓娓道来的治愈系风格来赢得一席之地。治愈系影视以远方、美好、诗意等文学母题来激发受众的共情,让受众从繁杂琐碎的生活中暂时脱离,得以喘息,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叙事呈现:想象、代偿与超越
治愈系影视之所以“治愈”,是因为剧中勾勒了一幅重归自然、万物和谐的理想生活图卷。剧中总有无数的美食呈现来满足人们的感性食欲需求,以此来对抗工业化之下的过度理性;剧中总会有一帧画面让人想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用自然风景勾起乡土回忆;剧中总会出现志趣相投的同伴,从而成为当代复杂人际关系下想象中的心灵绿洲。这些剧情要素是治愈系影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想象性、代偿性和超越性的共情书写,来助力剧集的叙事呈现。
(一)想象性:乡土记忆的共情
治愈系影视注重视觉的审美体验,因为在慢节奏的叙事中,缺乏跌宕起伏的剧情也许会导致观看乏味,所以打造高端的视觉享受,丰富受众的视觉体验便成了治愈系影视创作的必要条件。在剧集内容的呈现中,往往会出现超乎现实的如想象般美好的事物。
首先是对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的展现。《去有风的地方》取景点是云南大理,剧中经常会出现碧空如洗的蓝天,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草地,晨曦微光中行人三三两两从古老的石拱桥上走过,溪水潺潺正如这里的生活节奏,好不惬意。有风小院中微风轻拂下的树叶沙沙作响,还伴随着清脆的风铃声,似有一种鸟鸣山更幽的静谧感。还有夜晚浩瀚的星空,在洱海边支一帐篷,在布满繁星的夜空下,在烛火跳动的篝火边,三两朋友共享心事。这些乡土自然风光和生活状态无疑是深居城市的人们所不可见的,因此这种“审美距离”会引发个人无限的遐想,使其不由自主地将脑海中所有美好的风景都投射到剧中的“云苗村”里。于是,在影视拍摄的一次创作与受众想象的二次创作中,剧作本身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导演与观众共同建构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除了自然风光,民风民俗也是构筑乡土记忆共情的一大支柱,民俗风情中牵扯着千丝万缕的乡愁,而乡愁正是受众共情的关键。《去有风的地方》拍摄地所处的云南大理,主要是少数民族白族的聚集地,少数民族的独特性会显示出更浓厚的风土人情味。小镇上的老一辈都身着白族的服饰,木雕、扎染、刺绣等白族的传统手工艺也在剧中得到呈现。也许受众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缺乏认同感,但撕开地域文化的标签,根植于乡土文化中亲近友好的邻里关系,夜不闭户的民风民俗,这种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交流实际上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缺乏人际沟通的当代社会更能引起部分受众对于儿时生活的追忆,从而在观看的过程中感受到熟悉的温情。
除此之外,满足个人最基本口腹之欲的食物在想象性的建构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大多数治愈系影视中都会有大篇幅关于吃饭的剧情,例如《深夜食堂》《小森林》等。进食作为一种既神圣又世俗的仪式,会以最生活化的方式消解人们一天的疲劳,无数颗疲惫的心灵也会在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食物中得到安抚。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也出现了许多与食物有关的剧情,例如许红豆和大麦在阿桂婶和宝瓶婶的指导下做出了口感绵密的鲜花饼,通过对和面、摘花、洗涤、烘焙的特写镜头展现,放大了食物带给人的心灵慰藉。再如奶香浓厚的乳扇、口味地道的米线、具有云南风情的水性杨花汤等,受众由视觉体验移情升华到味觉体验,对食物美味的想象平添了观影时的满足感与幸福感。
《去有风的地方》通过对自然风光、民风民俗、地道美食三个方面的呈现,在受众的审美想象中勾勒出人们心底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以云南的乡土记忆唤醒个人内心深处对于家乡乡土记忆的共情,在观影过程中内心缺失的记忆与温情得到了补偿,继而这种想象性的乡土记忆共情成为治愈系影视疗愈的第一层。
(二)代偿性:人生体验的共情
曾几何时,一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刮起了一阵远行的浪潮。然而,要想完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既需要物质也需要精力,整日奔波于都市快节奏工作与生活中的人们无法实现这一愿望,于是就会将这种期待转移到治愈系影视中,以期找到一种代偿性的满足。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首先人物的设定就具有十分强烈的代偿性。主人公许红豆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缩影,她整日奔波于工作只为干出一番成绩,心中有想去的地方却只能无数次搁置,久而久之成了庞大工作体系中一颗生锈的螺丝钉。受众将自我代入角色,因此许红豆的大理之行也成了无数受众心中的代偿性旅行。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在当今社会中都变得越来越珍贵,而这三个主题在剧中都以第一视角得到了展现。
在友情方面,许红豆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好朋友,却在云苗村的有风小院收获了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遗失的友情得到了补足。曾被网络暴力的娜娜,有些社恐的网文创作者大麦,在商业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马爷,还有遭遇了婚姻失败的晓春,这些人物的遭遇也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网络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体验或了解过网络暴力、各种来自“键盘侠”的言语攻击,娜娜的人物设定代表着这一类人的情感代偿。热爱写作却又没有名气的网文作者大麦,代表着职业选择多元化的时代下个人职业身份认同的问题。遭遇创业失败的马爷则是追梦路上惨遭劫难的个人真实写照。这些人物带着满身的伤痛与疲惫聚集在有风小院,正如无数受众带着心灵的伤痛聚集在影视剧前,剧里剧外的人们相互治愈、彼此成长。
在亲情方面,谢阿奶的慈祥与淳朴让许红豆想起了小时候与姥姥相处的感觉,老人身上自带的那种经过时光沉淀的安稳与豁达,让许红豆内心感受到了亲情的呼唤。阿桂婶的热情与活泼,让身处他乡的许红豆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也让云苗村极具“人情味”。随着剧情的推进,情感在缓慢流淌,平实而又温和地治愈着每一个人。
在爱情方面,谢之遥与许红豆相知相守的纯洁爱恋,没有现代都市剧里戏剧化的矛盾与冲突,更像一旁洱海中的湖水一样静静流淌。两人丰富却又克制的情感,坚定却又理智的选择,与当代社会夹杂着物欲与利弊权衡的爱情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平淡又真实的情愫满足了人们内心对于美好爱情的想象。
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与琐碎的日常生活,是治愈系影视摒弃“狗血”叙事后更细水长流的叙事手法。受众借助治愈系影视剧的力量,将自己代入主人公的第一视角,与主人公共同经历、共同成长,以此来弥补自己心中缺失的情感。这种代偿性的人生体验的共情,是治愈系影视作品疗愈的第二个层面。
(三)超越性:个人价值的共情
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求分为低层次需求和高层次需求,其中高层次需求是人的自我实现,即一种超越性的个人价值体现。而治愈系影视所带给人的宽广境界并不仅限于情感共鸣,而是剧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个人与时代的对话。同样,超越性也是在想象性与代偿性的基础之上的更深层次的共情。《去有风的地方》并非一部只刻画爱情与风景的糖水片,而是立意在更深的社会问题之上:留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回到贫困的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发扬?乡村振兴何以实现?人文与商业的平衡怎样考量?这些问题都是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剧中人物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一份答案,也给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新范式模本。
剧中,谢之遥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家乡发展云苗村的文化旅游事业,在建设家乡的途中遭遇了父亲的极度反对、村民的不理解、资金短缺等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都没有迫使他放弃。谢之遥一方面大力招商推进旅游产业,另一方面又会小心翼翼地呵护云苗村的原始状态,避免云苗村沦为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人工景区。谢晓夏是木雕工艺的传承人,他身上有着年轻人想要外出闯荡的偏执与欲望。在看透了大城市繁华假象背后的虚无后,他才决定沉下心来专注于木雕工艺的传承与发扬,找到了人生的落脚点。黄欣欣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一头栽进云苗村的建设中,将云苗村本地的木雕、扎染、刺绣等传统手工艺品发扬光大,还畅言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许红豆原本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失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却在云苗村这块新天地里重拾了理想信念,最终离开北京,留在云苗村开起了有自己理念的特色民宿,也为云苗村的旅游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剧中的角色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遭受过打击或者失败,但是他们在打击中成长,在失败中重生,在一次次微小的成功中感受到个人价值在时代中的体现。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受众会从角色真实而又复杂的人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对影视作品的感悟中提升自我认知,找到从“现实的我”通往“理想的我”之间的桥梁,会因感知到个人奉献会在时代的洪流中荡起微微一层涟漪而产生自豪感与满足感。治愈系影视一方面通过描绘理想中的生活图景使受众的愿望得到代偿性满足,另一方面又让受众在艺术想象中不断提升和超越现实中的自我,让受众在汲取心灵力量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的升华,这便是治愈系影视疗愈的第三个层面。
四、治愈系影视的共情反思
相对于其他亚文化而言,治愈系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形式,不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而是更贴近生活,更注重对人内心的正向引导,有如一束照进湖底的光一般和煦温暖。但当治愈系影视为了引起受众的共情一味地诉诸感性而回避理性时,就会陷入虚有其表的美好假象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麻痹剂”。
(一)共情建构下的集体沉溺
圆满又和谐的中式温情是治愈系影视的“杀手锏”。哀而不伤的体验,细腻又柔软的感情牵挂,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让受众心里升起阵阵暖意。但是很多时候,当困境降临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治愈,更多的是现实的解决办法,逃避或许可以带来一时的舒适,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影视剧在建构共情的过程中会对现实进行美化处理,一旦受众过度沉溺于剧中所建构的想象中的乌托邦,逃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根源,那么治愈系影视本身所具有的抚慰心灵的力量就会成为促使个人变成“容器人”的催化剂,与现实社会产生割裂。
(二)表面美好下的情感疲劳
剧中许红豆辞去工作到大理一待就是三个月,不去管家里的琐事,也不担忧职场的竞争,还能得到家里人的支持和理解,这其实是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最理想化的处理,刻意回避了一些矛盾。最后许红豆收获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然而,这样的圆满结局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诚然,电视剧需要通过艺术化处理来实现特定价值观的传递,但治愈系影视要想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单靠呈现表面的美好是行不通的,久而久之反而会让受众陷入“被欺骗”的烦恼中,产生抵触情绪和情感疲劳,治愈系影视也就失去了其本质意义,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中。
五、结语
《去有风的地方》不同于戏剧化冲突的剧集模式,它用塑造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细腻温润的情感表达实现了与受众乡土记忆的共情、人生体验的共情、个人价值的共情。在想象性的基础上完成的代偿性的体验,又在代偿性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性的升华,是治愈系影视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范本。治愈系影视从情感需求上来说,安抚了个体对现实压力的焦虑情绪,使个体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通过对多元价值观的宣扬,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不同的渠道,促进了社会沟通和理解。共情体验是治愈系影视能够获得荧屏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在未来的影视剧发展中,回归真实的个人体验,尊重现实社会本身,在平淡的细节中挖掘深层的力量,才是治愈系影视永葆生命力的长久之计。
注释:
①齐青,余璧轩.治愈系影视:向阳而生的温情哲学[J].电影新作,2018(05):8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