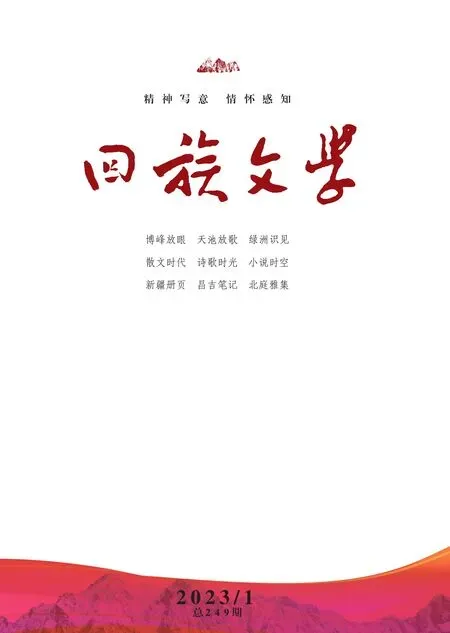娘啊娘,你抱抱我
毕化文
林儿是个空当里的孩子。
所谓非空当里的孩子,是指那些兄弟姐妹齐全,且兄弟姐妹又各自被爷爷奶奶和父母大人所宠爱着,而空当里的孩子呢,原本就不被爹娘稀罕,如果相貌差点儿,性格顽劣点儿,不善解人意点儿,再缺少眼色点儿,结果就更不妙,这样的孩子,不是被大人轻视,物质上慢待,情感上忽略,就是一竿子“发配”到姥娘姥爷家,或别的亲戚朋友家,逢年过节时接回来团聚一下,再接着送走,或者是这连接一下的程序也省略了,任凭这样的孩子如浮萍,在别人家“自由自在”存在着,成长着。
林儿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跟别的孩子比起来,林儿打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如果爷爷奶奶活着,或许林儿这个空当里的孩子会好些,可以依偎着爷爷奶奶,寻找到人间本应有的温暖,像别的孩子那样,爹娘下地干活去了,或者忙乎别的去了,抽不出时间照顾孩子了,而正在跟别的孩子们玩耍到半腰上,突然肚子饿了,四周庄稼又青黄不接,没有随手弄来填填肚子的青杏呀,豆角呀,地瓜呀,玉米棒子呀等,就会一下子跑到爷爷奶奶家,猴儿一样叫一声“爷”或“奶”,然后抓起一块蒸馍便狼吞虎咽一番,如果吃得噎了,再呼哧呼哧倒上一碗半温不热的开水,咕咚咕咚一气灌下肚,随后又一下子跑出门,直到玩得娘沿着村街扯着嗓子喊:
这才泥巴鳖肚地滚回家,洗洗手,或者连手也不洗,端起饭碗就吃,边吃还边喊: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这一切,林儿压根儿都没有。
其实,林儿是个非常正常的孩子,也是长得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四肢齐全,并不比别的孩子少一样东西,无非是皮肤黑点儿,眼睛小点儿,四肢短点儿,个儿矮点儿。论长相,林儿跟他大哥差不多,但大哥是爹娘的第一个孩子,是娘把捂着长大的,有娘一把伞罩着,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活得很是“娇气”;二哥呢,长相出众,皮肤白嫩,被村里的娘儿们或所有的亲戚们一见,就“罗成”(古时的美男子)呀,心肝儿呀,宝贝儿呀夸赞个不停,自然也是爹的掌上明珠,想吃什么,想要什么,一句话的事儿;林儿底下的两个妹妹呢,也来得正是时候,正在林儿的爹娘嫌家里的“和尚”太多,想闺女的时候,她们一前一后来到家里,自然双双成为爹娘手心里的宝儿,要吃一声,要喝一句,什么要求稍稍迟慢一点儿,轻则就地撒泼,哇哇大哭,重则上手就抓大人们的脸,或朝着大人吐口水。每当这时,大人们会赶紧放下手里的其他活计,百般哄劝,并立即满足她们的各项要求。
林儿呢,对这些都不怎么眼气,因为他知道,眼气也没用,只好躲得远远的。
出事儿那一天,正是寒冬腊月。那天是林儿的生日,就在前一天,邻居大娘见林儿放学回来了,就在路口拦在林儿的前头,说:
“林子,明儿个就是你的生日了,你可记得大娘的好?”
林儿是个腼腆敏感的孩子,他一低头从邻居大娘身边过去了,却没有回答邻居大娘的话,因为所谓“大娘的好”,林儿多多少少是听说过的。据说,在林儿出生那天,邻居大娘跟村里的接生婆陪伴在娘的身边。等林儿一出生,娘听说又是个小子,“呜”地号一声,随即挺起身子,拎着林儿的两条小腿儿要往尿罐子里扔,幸亏邻居大娘眼疾手快,林儿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儿。
但林儿在心里是牢牢记住自己生日的。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因为娘一提起林儿,就想起生林儿的时候。娘把生林儿的那天当成了自己的受难日,怨天怨地控诉说:
“天哪,您老人家咋这么不公呀,天寒地冻不说,生的还是个‘小丑儿’。”
娘总是这样将“受难日”挂在嘴边,如果你再跟她提生日的事情,那不是找不自在吗?
林儿的伙伴儿,包括林儿的同学里,每当生日这天的早上,家里总会给他们煮一个鸡蛋,那鸡蛋上面还要涂了红色,看着就让人舍不得吃。他们把红皮鸡蛋放在口袋里,一疯起来就把鸡蛋的事情忘了,直到不知不觉地将鸡蛋弄破,甚至揣着鸡蛋玩儿“挤尿床”(当地孩子的一种游戏,大家贴着墙根排成一队,使劲儿地往中间挤,谁被挤出来了就算出局),将鸡蛋挤扁挤碎,等到鸡蛋的味道从口袋里飘散出来,才知道口袋里还装着生日礼物呢。
在分享伙伴或同学的生日鸡蛋时,他们就会问林儿:“林子,你的生日是啥时候,怎么从没见过你的红皮鸡蛋呢?”林儿一听,鸡蛋也咽不下去了,将分得的鸡蛋还回去,抹着眼泪走掉了。
爹娘不给林儿过生日,不等于不给哥哥妹妹们过。相反,他们的生日过得比林儿见过的任何一个伙伴儿或同学的都好。虽然每回给哥哥妹妹过生日,林儿都陪着吃一顿又香又大的猪肉萝卜馅儿的饺子,但那是沾了哥哥妹妹的光,林儿吃得一点儿也不舒畅。每回吃了别人的生日饺子,林儿的心里反而更加难受,一难受就是好几天。
爹娘不给林儿过生日,林儿就想办法自己给自己过。去年林儿生日那天,做早饭的时候,林儿坐在灶前烧锅。林儿趁娘不注意,偷偷掀开锅台背后一个腌鸡蛋的坛子盖,伸手捞出一个半漂半沉的鸡蛋,用水瓢舀水冲洗一下后,再掀开馏馍的锅盖,放在锅沿边上,等锅烧圆气,他再冒着被烫的危险,将鸡蛋取出来,藏在棉袄的口袋里,然后,趁着天黑,跑到河沟边,敲碎蛋皮剥剥吃了。
娘从腌蛋坛子盖儿位置的异常,断定有人动了坛子,结果娘一数,发现鸡蛋果然少了一个,就怀疑是林儿偷拿了鸡蛋。吃晚饭的时候,娘突然从林儿背后揪住了林儿的头发,不由分说,掂起一把秃了毛的笤帚就打。娘打起林儿来向来不分轻重,怎样解恨怎样来。这回打的时候,大概是娘嫌这把破笤帚分量太轻,她扔掉笤帚疙瘩,抓起一根烧火棍,还没打几下,只听“啪”一声,那根烧火棍被打断成两截。娘索性将两半截烧火棍并在一起,将林儿的屁股、大腿根儿,还有腰部,打出了一道道红痕,火烧火燎地痛。
挨打的时候,林儿是号了几声的,但他知道号叫并不能停下娘手中的烧火棍,干脆就不号了,咬着牙硬撑着,直到娘打累了,打得“呼呼”喘气,才把林儿拎了个趔趄,喊了一声“滚”,自己又坐到矮凳上哭天抹泪去了。娘哭着说:“老天,您为啥让我生下这样一个孽种啊!”
娘无论啥时候,都是将一腔怨气撒向头顶那个不言不语的老天。
林儿跟别的孩子一样,也喜欢过年,并且也跟别的孩子一样,过年图的是吃好吃的东西,穿好看的新衣裳。可是,自从林儿记事以来,过年就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裳,都是两个哥哥穿破了的旧衣裳,娘将破洞用补丁修补修补,就当作了林儿的“新衣裳”,林儿不穿都不行,因为除了光着腚,林儿就只有这打着补丁的衣裳。
随着天空中鞭炮的炸响声越来越多,香甜的硝烟味儿越来越浓,林儿知道,新年又要到了。每到这种时候,林儿一颗幼小的心就会越绷越紧。他知道,娘又要开始给几个孩子截新布做新衣裳了,只是,这几个孩子中不包括林儿。
村里有家裁缝铺,每年林儿哥哥妹妹们过年的新衣裳,都是在这家裁缝铺里做好的。裁缝家有个儿子叫小宝,跟林儿一个班上学。这天,天气非常寒冷,以往夜里上的冻,等到太阳一出来,地面的冰就开始化了,到了近晌午的时候,泥泞的道路两边也就有了“路沿”(阳光下干得早点的地面)。可是,那天却因为太阳一直不肯露头,路面结的冰始终没有化开,直到学校下午放了学,路面依然结实,太平车走在上面发出“隆隆”声,几个轱辘也如同跳舞。
林儿跟着小宝来到他家,腼腆的林儿话并不多,而是左一眼右一眼地往缝纫机那里瞟。小宝的娘笑了,问:“林子,是不是来看你家过年新衣裳的呀?”林儿的脸一红,把头深深地低下去,一句话也没说。
到了年根儿,裁缝铺里的活儿特别多,小宝的娘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一个破小子说话,她的双脚踩在缝纫机踏板上,脚掌和脚后跟伴随着缝纫机“嗒嗒嗒”的欢叫声,一起一伏;她的脖颈一伸一缩,全身也跟着一起一伏;双手呢,也随着机器声,一前一后地运动,前边的手徐徐地拽着要缝的布边,后边的手轻轻地将布料往前送着,这种活儿要的就是全神贯注,容不得丝毫马虎。林儿想从她嘴里得到更多的关于过年新衣的消息,偏偏她又低下头忙自己的去了。
林儿想:你再忙,总有吃饭的时候吧。那我就等,等着你从机子上下来,端着饭碗的时候,看你说不说。
林儿的主意没错。到了天色开始抹搭眼儿,屋里的光线暗下来的时候,小宝的娘终于从缝纫机后头走出来。她来到院子里,刚刚伸了一个懒腰,扭头就把站在门旁的林儿看到了。她有点吃惊,以为林儿早就回家去了,哪知道他一直守在缝纫室门旁,像个影子一样,一声不吭。
“回家去吧,孩子。”她走过来,弯下腰,用手抚摸几下林儿的毛毛头儿,“婶儿也不想哄你,你娘送来的布料,还是只够你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的。”说着,她又轻轻拍了拍林儿的后背,叹了口气,“你娘也真是,五个孩子,截了四个孩子的布料,难道就差一个孩子的新衣裳钱?”
林儿拼了命地忍住才没哭出声来。他低着头,屏住呼吸,一步一挪地走出小宝家的大门。路面更硬了,他走得磕磕绊绊,趔趔趄趄,好几次差点儿被突出的冻泥块绊倒。白天躲在最高处的猫头鹰,开始在高高的树梢叫唤。林儿想起一句不祥的谚语,谚语说:
“猫头鹰,住宅子,不死大人死孩子!”
回到家里,全家人已经喝过茶(当地人晚饭的说法)了。灶屋里一片漆黑,有只偷吃嘴的野猫听到动静,“出溜”一下顺着门脚贴着墙根儿跑掉了。林儿适应了一下屋里的黑暗,看见一只饭碗孤独地搁在灶台上,里面的稀饭早就冰凉了。林儿没有一点儿胃口,他端起饭碗,将稀饭倒进锅灶下面的草木灰里,悄没声地上了床。
那天晚上是个黑月头加阴天。外面的夜空比屋内还要黑。临窗而睡的林儿望着窗外。他什么也没看到,只闻到了铁窗棂发出的血腥般的铁锈味儿。先前,临窗而睡的是二哥,但那是几个月以前的夏天了。那会儿靠着窗户,夜风吹拂,可以将白天的酷热吹得远远的,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现在是冬天,吹进窗户的风可不是什么享受,这时的风像刀子,割得人皮肤“刺啦刺啦”疼,林儿见过村里的屠户杀猪,牛耳尖刀在猪皮下游走,在挑断那些相互交织着的神经和毛细血管时,发出的就是那样的声音。有一天,头场霜快要下的时候,二哥拎着一卷儿林儿的被褥扔到了靠窗的小床上,气势汹汹地说:“我靠窗睡了一夏天了,该轮到你去睡了。”
林儿知道争不过他,默默地搬到了靠窗的小床上。
林儿没有丝毫的睡意,他小小的脑子里在放着一场“电影”,内容是关于今年小满会上发生的一幕。

《依 偎》 康 剑 摄
每年的小满节气那天,离林儿家不远的镇子上,都要举办罗马物资交流大会。在那个地方,除了春节前的“轰隆集”(旧历年底的最后一次集会),就数小满会最热闹了。镇政府为了举办好小满会,提前半个月就预定好了几台大戏,分别在镇子的东南西北搭了高台,提前三天便开始登台唱戏。那些商贩们也是提前找好摊位,到市管会那里交了摊位费,便将杈耙扫帚扬场锨,凉席草帽割麦镰等家伙儿或竖或躺地展示在摊位上,就等着人们赶会时交易了。那时候的镇子提前好几天就变成了不夜城,一天到晚锣鼓喧天,响器齐鸣,街道两边也摆满了各类小吃,有炒凉粉,水煎包儿,馄饨锅,烧饼炉,香喷喷的胡辣汤,让人垂涎欲滴的大碗烩面。街道中央,有扛着稻草扎成草把子的民间手工艺人,草把子上插着糖稀吹成的各类玩意儿,有公鸡报晓,有悟空三打白骨精,有哪吒闹海,有蹦跳的小兔子、贪吃的肥猪、腼腆的山羊、眼睛晶晶亮的老鼠等。林儿最喜欢的要数小贩们用面做成的“面花花儿”了,他们将一个个捏好蒸熟后又晾干的面偶用食用颜料涂得花里胡哨,非常好看。几年前,那会儿林儿的姥娘姥爷还在,他被姥娘姥爷领着去赶会,姥娘姥爷给他买了好几个面偶,有小兔儿,有花“嘛噶”(当地对喜鹊的叫法),有小狗儿,还有小猫儿。那些干成棒棒的面偶被他玩了好长时间,最后才舍不得地将它们一点儿一点儿啃着吃掉了。
想起面花花儿的香甜,林儿禁不住地吧唧了几下嘴。
为了显示小满会的隆重,到了小满会那天,学校提前半天给孩子们放了假,让他们赶一个快快乐乐的小满会。
而家长们呢,哪怕家里再拮据,也会给自家的孩子几毛钱,让他们到会上吃小吃,喝汽水,成群结队地去听大戏。
那天在赶会之前,娘先后给哥哥妹妹们发了钱,让他们随着村里的人群去赶会,却将一个差不多跟林儿一样高矮的荆条筐扔到林儿面前,呵斥道:“还愣着弄啥,下地给猪薅草去!”
林儿㧟着荆条筐,几乎是一路哽咽着,才摸到庄稼地头的草地里。
有个近门儿婶子,对林儿的娘如此对待林儿很是看不过去。但林儿到底是他自己娘生,自己娘养的,旁人恐怕说多了也不好。但她实在可怜林儿,就给他出主意,她说:“林子,你也十来岁了,就不会想想办法,长长心眼儿,让你娘也心疼心疼你。”
那会儿,林儿虽然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娘心疼自己,但婶子的话算是说到了林儿的心坎里。那该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娘也像对待哥哥妹妹们那样,心疼心疼自己呢?
躺在窗前的林儿知道,自己不是皮孩子(当地对非亲生孩子的叫法),也是娘亲生的。娘曾经多次都在人前说过:五个孩子都是从她的肚子里爬出来的,五根指头咬哪一根她都会疼的。想到此,一个想法突然跳进林儿的脑子里。
之所以想到这样的法子,是林儿无数次看见,家里的两个哥哥或两个妹妹,无论是哪个病了,娘总是将他们搂在怀里,不停地用自己的脑袋贴贴病人的脑袋,看看还热不热,有多热,还不厌其烦地询问病人:想吃点啥呀,是好面叶儿,还是鸡蛋汤?好面叶儿里放不放香油?鸡蛋汤里加不加白糖?
林儿多次设想:要是被娘搂在怀里的那个人是自己,该有多好呀!
林儿的想法是:让自己也病一场。如果因为病而被娘搂抱在怀里一回,他就是少条胳膊断条腿,甚至是就算命都没有了,也是值得的。
可是,如何才能生一场病呢?林儿想起来了,一个人只要着凉,就能生病,发烧、感冒、咳嗽。现在正是一年里头最冷的时候,要想感冒发烧,就只好让自己冻上一冻了。
于是,在黑夜里,这个刚刚十来岁的林儿,用脚挑开了盖在身上的被子。
起初,陡然而至的寒冷让林儿有点儿受不住。他第一次感觉到,寒冷竟像烈火一样烫人。他下意识地将被子重新盖在身上,但刚才被窝里的些许暖意已经一扫而光,被子像铁皮一样冰人。林儿一个激灵,牙齿“咯嗒嗒”一阵响后,刚才的寒冷劲儿竟减弱下去。
窗外响起一阵细细碎碎的树枝晃动声,林儿知道,起风了。院子里的好几棵大树上,堆着酷霜后林儿爹挑上去的红薯秧子,红薯秧子堆里,有好多的麻雀窝儿,每一团红薯秧子犹如一个蜂窝儿,厚厚的红薯秧子替雀儿们遮风挡寒,成了雀儿们的“乐土”。或许是刮起的夜风惊扰到了它们,让它们有些惊诧;要不就是有些雀儿正在做梦,那些传进林儿耳朵的“叽叽”声,是雀儿们的呓语。
林儿躺在冰凉的床上不敢动,此刻他仿佛睡在了冰窟窿里,唯有保持静止,身体的折磨才会减少到最低。不过,林儿很快就有了一个减少折磨的良方,那就是想象着娘的怀抱,想象着被娘搂抱在怀里,用娘给予的幸福来抵消寒冷带来的痛苦。
他在心里祈祷着,再冷点儿吧,快把我冻病吧!
可是,当他设想着自己果真病了,想要品味娘的体味儿时,记忆里却空无一物,仿佛从来就不曾有过。
失望让林儿的内心一点一点凉下去。忽然,他的眼角一凉,就像有一次在镇子上看铁匠打铁时,飞溅的火星迸到脸上时的感觉一样。他知道那不是自己流的泪,这让他稍稍聚集了一下注意力,等着再一次的凉意来临。
果然,约莫三两分钟的样子,它像个幽灵一样地再次出现了。这回林儿明白了,它来自高远的天空。如果是在白天,又是在正常的时候,林儿会高兴激动得又蹦又跳。毕竟,随着年节愈来愈近,如果天上再下一场雪,大雪,过年就过得更有味儿了。
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林儿喜欢下雪,尽管下过雪后,太阳一出,满是泥泞,胶泥会像恶鬼一样拽着人们的脚步,让人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吃奶的力气,就连刷过桐油的棉鞋,也会早早就被泥汤子泡透,被烂泥拽破。为了免受这个罪,他们那里不知啥时候兴穿泥屐子,就像日本人的木屐,但比木屐腿高、长,分别用麻绳捆绑在左右脚上。这样走在泥水里,便很难被泥水打湿棉鞋了。但这是一道烦琐的程序,人们非常不情愿,尤其是跟林儿大小差不多的孩子,天一下雪,就跳着脚子唱道:
“老天老天别下雪,黑心黑肺你没爹!”
可是,林儿特别渴望下雪。大雪一下,冬天的死气沉沉被一派崭新的世界所取代,总让他幼小的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希望。尤其是在无边的洁白里,村西河畔的那片竹子,才显出它的苍翠、碧绿,显出它的生命力。下过大雪过年,鞭炮炸响后,花花绿绿的碎屑落在雪里,也让年的味道保留得长久一些,好像洁白的世界里开满了五彩缤纷的花儿。
有一次,林儿就因为喜欢下雪,跟不喜欢下雪的二哥杠上了。二哥说:“下雪,下雪下雪下雪,下雪天叫你个眯缝眼一脚踩到井沿上,滑进水里冻死你。”
林儿说:“冻死谁,谁活该。”
天上下的不是雪片,而是雪粒,当地人叫这种雪为“霰”。霰就像大雪到来前的轻骑兵,是为大雪打前站的。如果下雪时,一开始就是大的雪片,这样的雪下不持久,也下不厚。如果在下雪前,天空中先是三三两两地往地上撒霰,这雪一定会下大。霰落地后又跳又蹦,活像一个个小生灵,然后越撒越密,半个时辰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后,就变得密密实实,地面密密麻麻一层,一颗颗一粒粒,浑圆饱满,晶莹剔透,好像老天给人间播撒了无数的糖丸儿。
下着下着,就是漫天飘飘洒洒的大雪片了。
林儿已经在窗户的寒冷中坚持了一阵儿了,起先还能感觉到霰打在皮肤上的劲道,可以感觉到霰的欢快和结实。但慢慢地,他的皮肤温度已经降到不容易感知凉与热的地步,也就是说,林儿已经冻得有些麻木了。处在麻木状态的林儿眼前出现了幻觉,他仿佛看见娘就站在窗外,那无边的黑暗是娘的身影,娘是怕林儿给冻着了,替他用身子遮挡着刺骨的寒风。
感觉不到寒冷的林儿,眼前开始不停地出现一团火光,像球形闪电,一会儿出现了,一会儿消失了。林儿不想让它这么快消失,就去追。他追得越快,那团光跑得越快,每每在快要追上的时候,那东西便瞬间不见了。有一次,林儿在差点搂抱住那团光的时候,有点激动,浑身骤然痉挛了一阵,睡的小木床竟跟着窸窸窣窣颤抖了几下。
窗户虽然上下左右横竖着几根撑子,却对雪片和冷风起不到一点阻隔作用,有时候甚至起到的是指示方向、集中力量的作用。比如此刻,加大的夜风裹挟着雪花儿,“呼呼”地往窗棂里吹进来,因为窗撑子的作用,那些雪花儿好像分成了几列纵队一样,扑向小床,扑向身体早已麻木的林儿。要搁在平时,以林儿的体温,那些雪花儿一碰上他的身体就会融化,变成小小的一滴水,说不定林儿还会兴奋地大叫起来。可是眼下呢,林儿似乎跟雪花成了朋友,双方达成了协议,林儿让自己的体温越来越接近雪花儿的温度,这样一来,雪花儿再落到林儿的身上,就不会融化,这样,就会一直待下去。林儿的朋友越来越多,慢慢地,这些雪花儿朋友把林儿打扮成了它们喜欢的模样。
林儿的脑仁越缩越紧,最后的一闪念是娘的笑脸,笑脸好像无数片雪花,一片一片扑向林儿,最后把林儿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娘搂着林儿对他说:“林子,娘知道你喜欢雪花儿,它们可都是娘送你的生日礼物啊。”
那晚,林儿睡得非常香,睡着的林儿非常幸福,脸上是心满意足时才有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