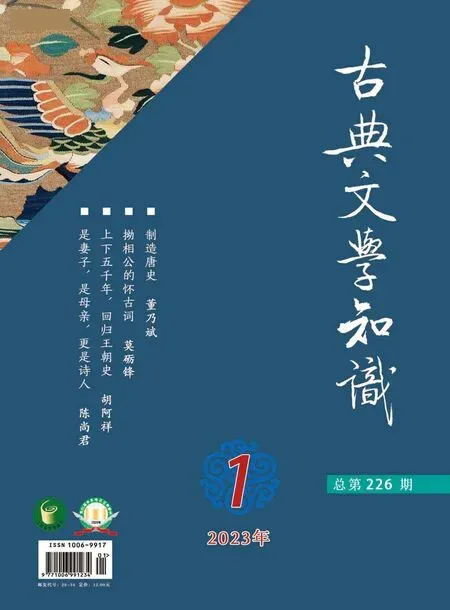瞬间与永恒的桃花
——由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说开去
◆ 张小路
宋代的诗僧惠洪在《冷斋夜话》里说:“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后来人们常常用“老妪能解”来说明诗写的清浅,通俗明白,人人能懂,这也就成了白居易诗风的标志之一。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也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元轻白俗,郊寒岛瘦”,这里的“白”即白居易,苏轼的这个“俗”字引起了后人的许多误解,让人误以为白居易的诗歌既然如此清浅,而且一生写的诗歌这么多,写诗对他来说,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作者既随意写来,读者不妨随意读之,明白了大概的意思,以为已经探到了诗作的核心,不作深究,便匆匆结束这首诗歌。
在白居易传世的诸多名篇之中,《大林寺桃花》又被当成是“易懂中的易懂”的诗歌,向来被当成是童稚读物,其“能解”程度,估计老妪尚且不予重视,一些普通的白居易诗歌的选本,甚至被列为“蒙学”的《唐诗三百首》都不会去选它。致使这首诗,被诵读了千年,也被误读了千年,似乎没有哪首诗比这一首更多享受世间繁华,也没有哪首诗比这一首更领略诗国落寞。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常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一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引用这首诗,接着说:“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南宋的祝穆编写了部有名的地理类著作《方舆胜览》,记录白居易这首诗,并作了简要的说明:“云山高地深,时节绝晚,初到恍若别造一世界者。”科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此诗的理解,正暗合后来的科学原理,所以常常被人们提及,这只是在平实地讲解一个知识点,在完成一份关于环境、气候与植物生长关系的考查报告,是自然科学家所关注的事情。这并不是艺术创造,不是用艺术形式熔铸出来的诗歌,内容也起不到感发的作用,读者读后,只记住了一个知识点。
当然,读者都知道这是一首诗,而不是一份科学考察报告。正如《周易》阴阳,不能推出计算机二进制原理。所以人们的眼光会聚焦在诗的写景与抒情上,由“人间”而到“仙境”,将“春光”拟人化,抓住白居易在诗中的情绪表达,由“芳菲尽”而产生的“怨恨”“恼怒”“失望”,后来发现了桃花,就“由一种愁绪满怀的叹逝之情,突变到惊异、欣喜,以至心花怒放”。
这样的解读,已经慢慢靠近了“诗歌”的本质,但这也是一种值得反思甚至是警惕的诗歌阅读方法。一个诗人,不是一个单纯的风景欣赏者与摹画者,也并非只是简单的见花落而愁、复见花开而喜的受外在环境支配的自然共情者。如果仅为花开花落而或喜或悲,则诗人心灵应对外在自然的机制,是简单的、机械的,像风中飘落的树叶,或江河所裹挟的一粒沙子,人成了自然的奴仆,哪里还有什么主体性可言呢!作为诗歌的欣赏者,也不应形成固定思维程式,只为找到标准答案,将一些惯用的情感,套在几乎是每一首诗上面。这是一种远距离的、冷冷的、打量的欣赏方式:画面是作者看到的画面,作者真是幸运,而我的生活里却没有;这样的情感是作者的情感,而读者,只需要背下几个表示情感的词语,便足够说明读过了这首诗,并且读懂了这首诗。诗人与景,只是泛泛之交;读者与作者,近乎萍水相逢。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指出: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真正的诗人,不是观物,而是感物,用的不仅仅是眼睛,更重要的是拥有能感物的心灵。这样,他会由此及彼,甚至跨越自然现实、人文艺术、精神世界之间的畦町。接着,进入了艺术创造的过程,描摹事物的时候,要随物而变化;发为声诗的时候,写出内心最幽微的念头。如果一种艺术样式——特别是诗歌——缺乏了艺术抒发者主体心灵的表达,那将是最浅层的表达;没有经过作者内心世界倾注的对象,也将失去它最美好的面目。
针对苏轼的“白俗”的评价,葛兆光《唐诗选注》为之辨白:“可能批的是他诗歌语言的‘通俗’,因为在诗史上很少有人像白居易那样自觉地把诗写得明白如话平易浅畅,且不说那些乐府诗,就连已经惯于使用紧缩凝练句式及象征暗示语词的近体诗,在白居易笔下也被写得很浅切自然。”
在这里,葛兆光给读者提出了要求,就是诵读诗歌的时候,要具备一些欣赏的知识,如“紧缩凝练句式”,还有“象征暗示”。诗人在创作的时候,“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在精神上达到极高的境地,虽然看似信手写出,而实际包含了无限的创造意义。读者在面对这首诗的时候,何尝不是面对一个客观的对象,只是这个对象由“桃花”转而为“诗歌”,当我们把这诗歌当成是客体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也应像作者一样,“随诗宛转”“与心徘徊”。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阅读的知识或心灵的修炼,是读不懂诗歌的。
二
一首诗歌的创作,不能没有诗歌作者自身前后经历的参与。诗歌,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最直接的反映,是诗人的心灵秘史。
白居易性格耿直,得罪了权贵,趁母丧在家守孝三年,远离朝廷。公元814 年冬天,白居易守丧结束,回到长安。第二年,爆发了一件震撼整个长安的大事件:宰相武元衡被暗杀。白居易直接上疏皇帝,请求全力以赴,尽快捕获贼人。这个做法抢了其他丞郎、给舍、谏官、御史等人的职责,引起了他们的攻击。这些丞郎、给舍、谏官、御史们很快联合起来,找到一个攻击白居易的理由:
先是居易母因看花堕井死,时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名教之士讥焉。(《册府元龟·罪谴篇》)
根据高彦休的《阙史》记载,白居易每年春天都会写一些咏花的诗歌,而《新井篇》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所作。这竟然也罗织成了白居易的罪状。将政治之争,上升到人伦之争,白居易的内心是极度痛苦的,他以“名教”自守,他以“人伦”自厉,政敌偏偏在这个方面让他蒙受不白之冤,又因涉及母亲不能争辩。于是在中书舍人王涯的上疏中,他已经被安排好了新的职位:追诏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在江州排解内心苦闷的方法是读一些佛家、道家书籍,空闲的时候,就结交僧俗,和友人四处游览。根据白居易《游大林寺记》,这一天,他们十七人一起“登香炉峰,宿大林寺”,他对于大林寺最初的感受是:“悄然若别造一世界者。”这个远离现实的世界,在白居易内心所引起的,或者是“终焉之志”,或者是——人生还有可能,现实人间的世界或许是“精神家园花园飘零”(杜维明语),像现在自己的遭遇,但还是应该相信,在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桃花依旧盛开,那里便是希望所在。
写花曾让白居易蒙受不白之冤,但他却不就此束手不写,还是要写这“桃花”,还是要借写花来表明自己还有希望——就是这样,白居易借这样短短的一首小诗,写出自己的不屈服,写出了自信与希望,让自己的生命,立体而开放。
公元820 年春天,唐宪宗去世,太子李恒继位,白居易曾担任过这位太子的赞善大夫。入夏以后,任期没满的白居易受诏再回长安。
三
一个优秀的读者,首先必须是贴近了原作来读。如果说作者“写气图貌”要“随物以宛转”的话,在阅读的时候,这里的“物”,就变成了“作品”,读者面对这部作品,也要“随物以宛转”。要贴近了读,摒除自己的意见,看看作品里到底写了什么。陈寅恪就阅读提出过一个要求,要求读者在阅读一部著作时,“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里对读者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设身处地,二是表一种同情。
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哈姆雷特,不会变成林黛玉,这就是阅读的客观性。
但仅有客观性是远远不够的,书里写的是什么,与读者自己想到了什么,不要求必然要画上一个等号,有时候,读者所想,是大于作者所要表达的。——这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读者,他拥有艺术家的眼光,来发现甚至连作者都没有发现的独特价值。
美学家朱良志在解读《大林寺桃花》时,曾这么说:
他要表达的绝不是物质层面的桃花盛开,也不是写时间季节的流转,他要讲的道理十分深邃,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万古如斯,真实的桃花是永远不落的,要我们重视那种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的真实生命呈现。那种永恒的精神,我们叫瞬间永恒,世界的真实从外在形貌上把握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靠心灵去体会。
在日本,每年春天到来,樱花会自南而北,次第盛开。于是人们绘制了“追樱地图”,从最南部开始,观赏樱花的灿烂,在樱花凋落的时候,坐在树下,饮酒,唱歌,大哭一场,感叹最美好的生命的逝去。接着,循着樱花开放的轨迹,一路向北,一路饮过去,唱过去,哭过去,到达最北方的时候,这一季追樱之旅结束,收拾行囊回家。但是,樱花是不是就没有了呢?可以在更北方的俄罗斯,樱花又在开放,或南半球的某个地方,樱花也在静静待放,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九江城的桃花凋谢了,大林寺的桃花正在盛放;等到大林寺的桃花也凋谢了,是不是就没有桃花盛开了呢?也许只是白居易不知道,西藏林芝的桃花开得正盛,之后,更高远荒寒的土地,桃花也在静静待放。这就是朱良志所说的“青山不老、细水长流的真实生命呈现”,就是“瞬间永恒”。
这样的解读让我获得了一种永恒的瞬间,一刻瞬间的永恒。由此而推及人的一生,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这样,才能达到一种对于生命的感受,而这样的感受,言人人殊,各有不同,读者因此而获得了个人化的解读。
前辈艺术家的生命早已远逝,他们把光辉的生命留存在自己的作品中,但是,那是凝冻了的生命;他们真正的复活,他们的生命的不朽和高扬,完全在于今天的读者每一次打开他们的作品,与他们进行深入的对话。在这样不断的对话中,读者确立了自我。
作为读者,最可自豪的地方,是能够不断地从阅读中,体认自己在历史和社会上的地位,从而赋予自己以深广的时空意义,巍然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