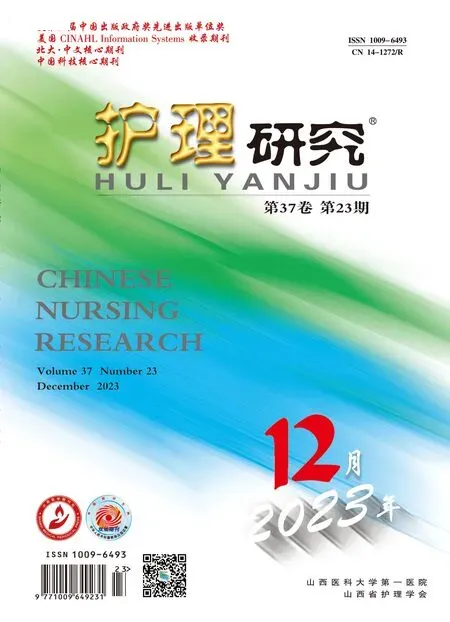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的研究进展
方 杰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四川 637000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全球最受关注的健康问题之一。2017 年,心血管疾病导致全球超过1 700 万人死亡,3 560 万人残疾[1]。据合理估算,预计到2030 年,心血管疾病将会导致全球超过2 300 万人死亡[2]。2019 年,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仍为居民死亡首位原因,农村、城市心血管病分别占死因的46.74%和44.26%[3]。全球80%以上的心血管疾病负担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但对危险因素重要性的了解主要来自发达国家[4]。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HD)是构成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美国2020 年冠心病年龄调整后的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5],我国冠心病的死亡率2002—2011 年波动上升,从2012 年开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6]。2017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道,我国冠心病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增加了20%以上,在我国疾病负担排名由1990 年的第7 位上升到2017 年第2 位[7],降低了个体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增加了我国疾病防控成本。了解我国冠心病危险因素流行特点,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降低个体冠心病发病风险,减少我国冠心病疾病负担。危险因素的聚集是指同一个体有≥2 个危险因素并存[8-10]。冠心病是由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一种慢性疾病。研究发现,多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常常在同一个体并存,其在个体聚集时产生的致病作用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叠加,而是存在一种正向的交互和协同作用导致患病危险成倍增加[11-12]。我国研究也发现,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其在个体的聚集在我国成年人群中普遍存在,不同生理性质的危险因素组合时所产生的“协同”作用强度也不同,危险因素个数相同但组合不同,冠心病发生的危险也有差异[8]。对危险因素聚集性的评估有助于更准确地预测心血管病危险并采取适当防治策略、集中治疗高危病人、提高价/效比[13],而许多国家并没有对危险因素聚集性的流行情况进行监测[14]。冠心病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研究其危险因素的聚集可以了解多种危险因素协同致病的机制,将疾病防控从单因素干预转变为多因素的综合干预,从事后干预转变为预见性干预,减少危险因素暴露,降低冠心病发病风险。本研究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流行特点、危险因素的聚集及干预措施进行综述,旨在为减少我国冠心病危险因素暴露、降低疾病负担提供参考。
1 概述
目前,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聚集现象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可以了解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更好地进行疾病防控。来自巴西[15]、北美[16]、意大利[17]、亚太队列研究合作组织[14]、伊朗[18]、不丹[19]、孟加拉国[20]的多项研究均报道了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聚集现象。危险因素聚集导致的疾病危险远大于单一危险因素作用的叠加。研究显示,具备高血压、血脂异常、当前吸烟、超重4 个危险因素中1 个、2 个、3 个和4 个危险因素者其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全因死亡率与没有危险因素个体的相对危险比分别为1.65,2.61,3.25,3.74[21]。我国研究发现,1992年中国人群中危险因素聚集者占38.4%,有2 个、3 个、4 个和5 个危险因素的个体发生冠心病的相对危险比分别是6.2,14.8,13.8,91.0[8],危险因素聚集个数越多,个体发生疾病的风险越大。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群中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聚集处于相对较低的 水 平。Gu 等[22]调 查 结 果 显 示,80.5%、45.9% 和17.2%的中国成年人分别有1 个、2 个和3 个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和超重)。我国普遍存在明显的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2种)[13,23-28],冠心病防控工作仍然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对个体进行早期、综合干预,减少危险因素聚集程度,降低疾病风险。
2 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模式
不同年龄、地区的人群因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率不同,导致其主要危险因素不同。在暴露人群中,不同的疾病危险因素常以某种组合聚集出现在多个个体身上。瑞士南部18~20 岁应征男性士兵中最常见的聚集模式依次是久坐+吸烟、高血压+久坐、高血压+吸烟、腰围增加+吸烟[29]。意大利海员中自我报告最常见的2 种危险因素聚集模式依次是当前吸烟/(超重+肥胖)(30.9%)、超重或肥胖+高血压(27.5%)、当前吸烟+高血压(17.5%)[17]。这种聚集模式在我国人群中也同样存在,成都居民中最常见的聚集模式为高 血 压+ 高 胆 固 醇(13.0%)、高 胆 固 醇+ 超 重(12.9%)、高胆固醇+吸烟(12.2%)[13];西北地区5 省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5~75 岁心血管病高危人群中最常见的危险因素聚集模式是高血压+超重/肥胖(21.3%)和高血压+超重/肥胖+糖尿病(17.8%)[30]。高血压、超重/肥胖、血脂异常和糖尿病之间的任意组合表现在人群中的多个个体中,提示这些危险因素在个体的发生机制中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Reaven[31]研究发现,高血压、高胰岛素血症、糖耐量受损、血浆三酰甘油浓度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降低常并存于冠心病病人身上,常伴有胰岛素抵抗,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证实了脂肪、糖以及内分泌代谢异常的致心血管病作用。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98 年提出了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的概念,但对代谢综合征的组分及内涵未达成统一共识。在此期间,各组织基于不同角度和适用目的分别提出过不同的代谢综合征定义和组分。我国于2004年根据我国人群特点提出了代谢综合征定义,规定空腹血糖/餐后2 h 血糖、体质指数、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收缩压/舒张压4 个组分中至少3 项达到判定标准即可诊断代谢综合征[32]。随着糖尿病学发展,对胰岛素抵抗与心血管疾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2005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在综合了各方意见后提出了代谢综合征全球统一定义[33],以中心性肥胖为核心,合并血压、血糖、三酰甘油升高和/或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并对各组分的判定界值及诊断代谢综合征的组分组合进行了明确定义。这一全球定义为临床筛查2 型糖尿病和/或冠心病高危人群提供了简便实用的判断依据。代谢综合征定义反映了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聚集现象,提示个体由单一代谢性危险因素向多个危险因素聚集发展的较大可能。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34],加强对于具备任何单一代谢性危险因素个体的早期、定期筛查,提高人群健康意识和体检意愿,将目前的单一危险因素干预发展成多因素综合干预,减少代谢性危险因素的聚集可能和聚集程度,将有助于冠心病的防控工作。
3 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的影响因素
3.1 性别和年龄
多项研究显示,男性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性高于女性,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性随年龄增加而增加,超过65 岁以上聚集性风险最高[20,23,27-28,35-37]。我国研究结果显示,男性聚集的总体患病率高于女性,但60 岁以上女性高于男性[10]。女性预期寿命较男性长,随着年龄增长,绝经期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其罹患高血压、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大[38-39],≥60 岁女性与男性在危险因素暴露程度的差距不明显。但2018 年我国深圳居民的横断面调查显示,女性心血管疾病生物危险因素(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中心性肥胖、超重)聚集性高于男性[28],与前述研究结论不一致。该研究中女性收缩压、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均高于男性(P<0.05),与Ford 等[40-41]研究结果一致;另一方面,该研究未将吸烟因素纳入聚集性分析,导致男性危险因素聚集程度降低。提示冠心病防控工作中不要忽视代谢性危险因素聚集对女性的影响,应加强对老年女性的健康筛查和综合干预。
3.2 种族和民族
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群因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基因不同,各种心血管危险因素暴露不同[42-47],聚集程度也不同。不同民族有特定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血管健康状况[48-55]。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受环境和传统习俗影响,饮食中摄入的酒精、脂肪更多,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吸烟和饮酒者较多,在遗传背景和基因-环境相互作用下导致其暴露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更多[54-55]。
3.3 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
多项研究显示,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聚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家庭收入较少者、文化程度越低者发生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的风险越大[17,19,26,48,51]。但在城市和农村居民危险因素聚集风险上,国内外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国内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发生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风险更高[24,26-27,50-51,56],与国外研究结果[19-20,47]不一致。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中青年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以老年人居多;另一方面,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一项来自中国生理常数和健康状况(CPCHC)数据的研究显示,调查人群中女性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风险随文化程度增高而下降,但男性聚集风险随文化程度增高而增加[50]。高学历男性因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可能形成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如饮酒、吸烟、高脂饮食、缺少锻炼等,更容易发生危险因素聚集。高学历者本身经济收入较高且具有较强健康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加强健康宣传和定期筛查并纠正不良生活方式,可有效减少危险因素暴露。对低收入群体,政府应主导完善社会卫生保健资源分配和养老体系覆盖,加大社会福利投入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
4 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的干预策略
4.1 加强对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的监测
不同地域、种族、经济水平的人群暴露的主要冠心病危险因素及暴露水平不同,危险因素的聚集风险和模式也不同。因此,监测区域人群主要冠心病危险因素流行特点对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疾病防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进行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烟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评估,各国也相继出台各项指南用于指导临床和疾病防控[57-59]。21 世纪初,为了监测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病率和死亡率,WHO 提出了非传染病危险因素的阶梯式监测法(STEPS)供各成员国采用,以便逐步建立一个包含核心变量的、数据可比的一体化、可持续的调查、监测和追踪系统,作为低中收入国家制定、实施和评价慢性非传染病控制规划的基础,改善和提高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资料质量和可比性[60]。各国采用STEPS 监测工具建立各自的慢性病监测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61-64]并用于指导疾病防控实践。我国在STEPS 的基础上,多举措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我国居民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2015 年的18.5% 下降至2021 年的15.3%,年均降幅接近全球平均降幅的3 倍[65],但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全程管理仍然是薄弱环节,中西部地区“示范区”建设质量较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整体差距,农村地区较城市更为薄弱[66],需要政府主导完善工作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加强队伍能力建设[67]。
4.2 加强生活行为方式干预
加强生活行为方式干预是多重心血管病危险防治的基础[68]。行为生活方式具有可改变性,通常作为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一级预防的切入点,血压、血脂、血糖等慢性病的生物学危险因素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改变[69]。生活行为方式干预主要包括戒烟限酒、保持膳食平衡、适宜增加体力活动、缓解精神压力[70]。全球目前有11 亿烟民,做好控烟干预,将有利于减少冠心病危险因素暴露和聚集。2008—2010 年美国全国健康访谈调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NHIS)显示,当前饮酒者占64.9%,当前吸烟者占20.2%,超重/肥胖者占62.1%,缺乏运动者占53.9%[71]。全球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0 年、2018 年中国15 岁以上成人吸烟率为28.1%、26.6%,呈下降趋势;2010 年、2018 年戒烟率分别为16.9%和20.1%,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72-73]。有研究显示,中国目前约有50%的当前吸烟者存在烟草成瘾,30%的饮酒者存在酒精依赖[74]。除了进行健康宣传外,美国、巴西、中国、韩国等多国采取了其他烟草控制政策,如提高香烟税、建立无烟环境、禁止烟草广告、在烟草包装上印刷健康警告图片、支持反烟草大众媒体运动、药物治疗戒烟、管制电子烟在内的新兴烟草、建立新媒体(如微信)违法烟草使用监督举报渠道、开通国家戒烟热线等,各有成效[75-78]。
4.3 早期筛查,将防治节点前移
为了减少危险因素的聚集,早期筛查非常重要。韩国推出基于人口的2 年1 次国民健康筛查服务,有效减少了未来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事件的发生[79]。除此之外,也有以不同调查目标开展的健康筛查,如女性心血管健康筛查[80]、儿童血脂与心血管健康筛查[81],体现了对特定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注。但也有研究认为,在政府或组织主导的高危个体的早期筛查上应注意筛查策略,避免没有针对性的大规模筛查,使用靶向筛查策略(筛查同时生活在贫困社区且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的个体)比大规模筛查成本更低,筛查45%的个体可识别高达84% 的高危个体,筛查效率更高[82]。从个体层面上来看,受到个体自我健康意识、身体机能、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我国老年、农村男性参加健康体检参与度较低,严重影响其远期健康状况[83-85]。山东省面向社区推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体检报告进行个性化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并制定规范、科学的干预措施,通过此项服务能有效提高老年人健康体检利用率[86]。徐益荣等[87]研究通过智慧社区“健康小屋”为平台,以跨理论模型指导指定、实施健康干预,有效提高了老年居民对于健康体检的认识和参与度。对于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的高危人群,国家应加大卫生资源投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其危险因素暴露。
5 小结
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暴露水平均较高,发达国家的暴露水平近年来趋于稳定,但发展中国家暴露水平仍有上升趋势,冠心病负担居高不下。冠心病危险因素聚集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并且以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等代谢性因素中至少2 个的聚集最为常见。因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及遗传和生理机制的不同,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在不同人群中的聚集趋势也不同;不同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的人群,其危险因素聚集的风险不同;老年、男性、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更容易发生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聚集。因此,减少冠心病危险因素的聚集应加强对不同人群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的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制定符合本地区人群特点的冠心病防治措施;加强对人群生活行为方式的干预,有利于减少人群尤其是重点人群(老年、男性、低收入等)的危险因素暴露程度,降低聚集水平;加强人群健康筛查,尤其是已经确定有单一危险因素暴露的人群,采取多因素筛查,将冠心病防治节点前移,减少或延缓个体危险因素的聚集。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危险因素聚集对病人致病风险和远期预后的影响,加强对病人的综合评估以发现潜在风险,积极进行健康宣教,提高病人及家属健康意识,指导病人采取正确措施积极配合临床治疗并进行自我管理,降低冠心病危险因素暴露,减少危险因素聚集,降低发病风险和疾病严重程度,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