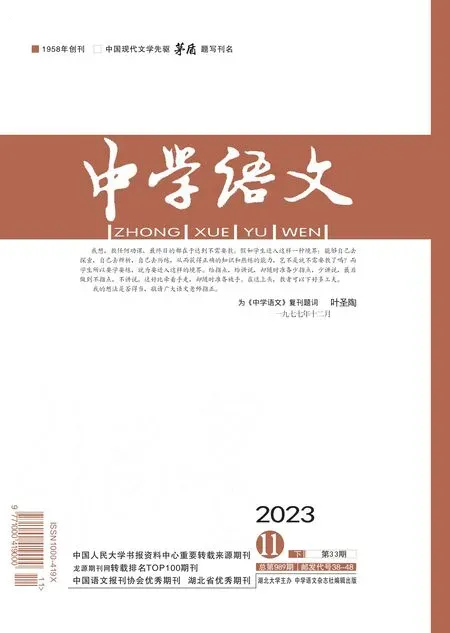落后:《台阶》父亲形象的另类解读
梁 建 孙自见
李森祥的小说《台阶》成功塑造了一位农民父亲形象。长久以来,很多人对父亲形象的解读都停留在要强、勤劳、坚韧等闪光的层面。我们对这些闪光点并不否认,但总觉得仅作这些解读意犹未尽。小说固然讴歌了父亲坚忍不拔、艰苦创业的精神,但是文字背后更有一种凄楚、辛酸的情感笼罩全篇。父亲的结局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他努力大半辈子造成高台阶新屋,却依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父亲可能从没觉得,导致他悲剧性结局的不是造台阶本身,而是他自己的落后。
那么,父亲的落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台阶地位观的执念者
文中说,在“我”的家乡,家家户户都有台阶。对于造台阶的目的,作者解释道:“屋基做高些,不大容易进水。另外还有一说,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台阶高地位就高,这本来就是一种旧观念,甚至乡人们自己也不全信,从“乡邻们在一起常戏称”中的“戏”字可看出,这句话多少带有戏谑的成分。但父亲却信了,而且深信不疑。高台阶等于高地位,这一观念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小说开头:“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一个“总”字道出了父亲执念之深。“我们家的台阶低”这句话父亲不知说了多少遍。老实厚道低眉顺眼一辈子的父亲,并不是一个话语太多的人,但却反复念叨这句话,足见台阶地位观对他影响之大。“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所以他日夜盼望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父亲造高台阶新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别人也让自己觉得自己有地位。这个念头激励了他大半辈子的辛苦“造阶”行动。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父亲通过造阶满足需要、实现人生价值无可厚非,但是把台阶和所谓的地位等同起来且对此念念不忘,则不能不说父亲价值观念的落后。
父亲的这种落后观念,正是他悲剧性结局的最大根源。因为高阶新屋造成之后,父亲并没有感受到地位的提高,高高的台阶反而让自己倍感不自在。这种不自在既有身体上的,更有心理上的,他追求了大半辈子的最大愿望反而落空了。如果说身体老了、腰伤了这些现实他还能接受的话,那么精神上的落差是他无法接受的,但又是他想不通的。父亲也许始终都没弄明白:一个人的地位并不取决于屋子台阶的高低,至少不是所有人如此。像父亲这种谦卑了一辈子的人,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并没有通过几级台阶感受到地位的真正改变。
父亲的落后还体现在他对数字的迷信上。“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为什么是九级?因为按过去“阴阳”之说,“九”是阳数中最大者。因此,古代皇家建筑多含“九”。如,北京内城最早是“九”个城门,北海和故宫九龙壁都是“九”条龙。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都是九丈九尺,所有大殿的屋脊有特征不同的小兽,这种灵感来源于龙生九子。父亲选择“九”这个数字除了图个吉祥,是否更暗含“地位高”的寓意呢?由三到九,恰好高出两倍,这些数字显然不应是一种巧合。
小说临结尾处写道:“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父亲失掉了什么呢?父亲的失落也许不止一种,但并未找到自己地位升高的感觉是一定的。这种失落正是他的落后观念导致的。父亲是一个谦卑惯了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台阶地位观的执念者。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冲突让他在台阶建好之后格外“不自在”。
二、造阶运动的落伍者
父亲尽管对台阶地位观深信不疑,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算不上先行者。从文中可以看出,在他准备造新阶之前,家家都有台阶,而且“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即便此时父亲拥有了九级台阶,也不是最高的,更不是最早的。“父亲坐在绿荫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说明已有邻居家造阶成功;“我们家的台阶低”,显然也是父亲一次次横向比较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村子里已造、正造和准备造高台阶的应该不止一家。在这场造阶运动的队伍中,父亲显然不是第一个,甚至不是前几个。靠出苦力、攒角票造新屋的他充其量是个追赶者,甚至不排除是个落伍者。因为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劳动力是最大的生产力,而文中的父亲似乎是家庭里造屋的唯一劳动力。他一个人砍柴,种田,攒角票,捡拾砖瓦、卵石……等父亲凭一己之力花费大半辈子完成这一“壮举”的时候,村子里一些劳动力富足的人家也许已经抢在了父亲前头。
小说后半部分的两处细节似乎也印证了父亲的落伍。在台阶造好的当天,父亲坐在高高的台阶上抽烟,本已觉得“不对劲”,而这时邻居的一声招呼则彻底打乱了父亲的心理预期。父亲满心期望高高的台阶能抬高自己的地位,能听到邻居满是惊讶的赞叹和恭维,尤其在新台阶刚刚造好的第一天。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邻居间一句再平常不过的招呼:“晌午饭吃过了吗?”父亲不知怎么竟然回答错了。看似不经意的一处闲笔,实则大有深意。此外,新台阶开工“典礼”上,“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这里的“仿佛”一词也暗示了父亲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关注。随着村子里高台阶的增多、普及,邻居们也许见多不怪了——父亲在乡村造阶运动中已经落伍了。
三、男权主义的践行者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但是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男人的尊严和责任促使他试图通过一己之力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在那个年代,作为从封建社会过来的农民,父亲身上不可避免地笼罩着浓厚的男权主义色彩。
男权主义也称男权制或父权制。在一个家庭里具体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女性被彻底边缘化。父亲的男权主义在造屋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是个勤劳的人,家里几乎所有的重体力劳动都由他一个人承包了。三块三百多斤的青石板,他一个人分三趟扛到家;造屋的那些日子,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早上天没亮,他第一个起来踏黄泥;就连捡鹅卵石、编草鞋、挑水这样的活儿也要自己来……读者不禁要问:在父亲造屋的时候,家庭里的其他成员呢?母亲呢?子女呢?在小说中,父亲和母亲的“交流”极少。无论是造屋前的决策,造屋中的劳动,还是造屋后的庆祝,母亲始终是这些重大活动的缺席者。理论上能顶“半边天”的母亲只是坐在门槛上干活,为父亲烧洗脚水,用土方治疗父亲的腰痛。这些活儿当然不能说不重要,但在父亲造屋的壮举面前,在这个男人为中心的家庭里,母亲的行为被彻底边缘化了,至多只能算是父亲“高大”形象的陪衬。
这种男权主义泛化在子女身上,就是父亲对子女劳动权利的无视。父亲有几个子女?小说中并没有交代,但至少有一个“我”。如果说,父亲准备造屋时“我”还小的话,在经过大半辈子造成新屋的时候,“我”分明已经成人了,完全可以参加体力劳动了。但纵观全文,除了给父亲倒洗脚水和开工前放鞭炮,“我”竟然很少有劳动表现的机会,而仅有的两个劳动机会发生的概率又极小(因为父亲一年只洗一次脚,而开工典礼更是多年难遇一次)。即使在父亲因年老体衰而挑不稳一担水的时候,还把上前帮忙的“我”粗暴地一把推开。父亲似乎完全忽略了子女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在这方面,父亲甚至不如两千多年前发动全家参与移山的愚公。
人多力量大,这简单的道理父亲真的不懂吗?显然不是。父亲是想极力彰显自己这个男人在家庭里的主心骨和顶梁柱地位。无论是家庭决策,还是体力劳动,他都“独当一面”,以至于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妻子儿女的存在。
小说中有两处父亲的貌似自言自语,一处是“我们家的门槛低”,另一处在结尾:“这人怎么了?”前者是父亲的感叹,是激励父亲造阶的驱动力,是造阶前的宣誓;后者也是父亲的感叹,是造阶后深沉的人生思索,是略显悲壮的喟叹。这两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分量极重。作者为什么要强调“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问我”呢?这是因为在重大问题上,父亲根本没有同家里人尤其是和妻子商量和诉苦的习惯。在他这个伟岸的男人潜意识里,自己永远都是家庭的主角,而妻子和子女都是配角。
父亲的男权主义意识让他承担了家庭里几乎所有的“重任”,不知疲倦的体力劳动让“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结果也正如此,父亲这种“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行为,过早地压垮了他的身体,加速了他的衰老。
四、生活陋习的坚守者
父亲是个农民,一年到头辛苦操劳。劳动之余,抽烟似乎是父亲一辈子唯一的爱好。也许是为抽烟找个借口,父亲把抽烟称作“磨刀”,“烟吃饱了,‘刀’快,活做得去”。正因为此,父亲只要一有空就会坐在台阶上抽烟。抽烟无疑是生活陋习,但父亲却非常享受,他不仅享受吞云吐雾时的快感和旱烟雾在头上飘来飘去的“美感”,也享受去烟灰时烟枪铜盏敲击青石板的嘎嘎声。父亲不停地抽,不停地敲,经年累月,坚持不辍,以至于在坚硬的青石板上敲出了深深的凹凼,而烟枪也用旧了三根。
无论父亲如何享受抽旱烟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但毫无疑问这一陋习对父亲的身体绝对有害无益。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加上不停地抽烟,一点点侵蚀着他的身体健康,父亲的过早衰老自然不可避免。
陋习对父亲的影响还体现在恪守“大庭广众之下,夫妻从不合坐一条板凳”的旧俗,以及通过针刺九洞的土方治疗腰痛,等等。这些旧习背后折射出当时农村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父亲则长期陷在农村旧习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笔者对父亲形象的另类解读并非要丑化、贬低父亲,而是试图通过另类视角观察、分析父亲略显悲剧性的结局,以及背后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在小说里,父亲只是当时农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的落后有一定的个人主观因素,但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作者后来在给教材编者的信中写道:“即使富裕起来的农民,他们最终的命运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我个人仍然认为不能。这就牵扯到另一个层面,如人生的两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顽疾……”
也许,父亲的落后就隐含在作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顽疾”里吧。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