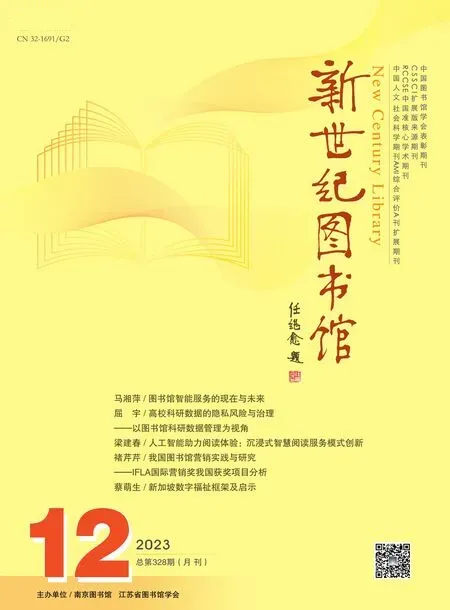中国图书馆社团史研究的力作:评《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
黎 飞
0 引言
民国时期,新式图书馆的大量建立和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刺激着图书馆社团的产生。1918 年12 月21 日,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揭开了民国时期开设图书馆社团的序幕[1]。自20世纪20 年代初期开始,一大批图书馆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这一时期,各类图书馆社团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谋划图书馆的协作为宗旨,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社团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1946 年《汉口通讯》复刊后刊发的《中华图书馆协会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对该协会1925 年成立以来开展的各项活动进行了梳理[2],这是我国学界最早专门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成果。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多个方面。然而,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个别地方性图书馆协会的研究,属于个案研究,图书馆社团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付之阙如。可喜的是,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阿陶博士长期耕耘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研究。从2009 年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开始,王阿陶就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研究对象,产出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以2022年8 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为代表。该书作为王阿陶博士主持的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是作者在其2012 年博士毕业论文《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1925—1949)》的基础上,经过十年时间打磨而成,这是学界第一部从整体上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专著。此书于同年12 月28 日入选2022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十佳图书,得到学界认可。可谓是“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鉴于该书的重要价值,本文通过分析其特点与不足,以期对民国图书馆社团和图书馆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的特点
姚乐野教授认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的特点是区别于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演进过程中考察图书馆社团,作者以图书馆社团为基准点对近代图书馆事业史和学术史进行观察,通过多个方面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贡献做出公允的论断,避免了“为贤者讳”的问题,同时也呈现出图书馆社团与当时政府的交流[3](序)2-3。
1.1 系统梳理民国图书馆社团的历史
据王阿陶博士统计,这一时期见诸报端的图书馆社团共有43 个。然而,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上海图书馆协会、天津图书馆协会、北碚图书馆联合会、延安图书馆协会、兰州图书馆协会、重庆市图书馆协会等图书馆社团的个案研究上,缺乏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系统梳理与整体研究。虽然顾烨青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会考略》[4]一文对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图书馆研究会、天津图书馆学会、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会和中国图书馆学社等进行了梳理,但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员研究所、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以及各图书馆协会、图书馆联合会、图书馆研究会等学会和社团并没有提及。笔者拙作[1]通过挖掘档案、民国期刊、报纸、今人论著、资料汇编,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民国时期的北京、上海等31 个图书馆协会进行了梳理。囿于史料挖掘不够,南宁、苏州、杭州等图书馆协会,以及一些图书馆学会、图书馆研究会、图书馆联合会被遗漏,并且对各图书馆协会的介绍较为简略,未能完整展现民国时期图书馆协会的面貌。
相比之下,王阿陶博士在书中将图书馆学会、图书馆联合会、图书馆研究会和图书馆协会统称为图书馆社团,并首次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社团,包括广东图书馆管理员教育研究委员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北平图书馆协会、浙江省图书馆协会、南阳图书馆协会、开封图书馆协会、天津图书馆协会、南京图书馆协会、上海图书馆协会、江苏图书馆协会、济南图书馆协会、广州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43 个图书馆社团的成立背景、成立过程、开展活动、活动成效等内容。特别是对很少见诸于各类研究中的北京图书馆联合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员研究所、杭州图书馆协会、中央大学区图书馆联合会、杭县图书馆联合会、南宁图书馆协会、浙江第三学区图书馆协会等地方性图书馆社团进行了梳理与考证。总之,王阿陶博士关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历史的梳理“在资料方面是有补于学术界的”[3](序)2。
另外,王阿陶博士还将研究视野转向日占区,对民国时期日本人在华设立的(“满铁”)奉天图书馆研究会、台湾图书馆协会、“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伪满)奉天省图书馆联合研究会、(伪满)“满洲”图书馆协会和(伪满)新京地区图书馆事业联合会等6 个图书馆社团进行了梳理与考证,认为这些图书馆社团“为殖民侵略服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给中国的图书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损失”[3]122。虽然这不是学界首次提到沦陷区的图书馆社团,但却是首次系统考证与研究了日本侵华时设立的图书馆社团。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首次从整体上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及其活动与贡献,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 采取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范式
1962 年,美国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释了“范式”(Paradig)概念。他认为“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活动所遵循的规范、模式、模型、范例、方法,这被称为“范式理论”。“自托马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后,这个简便又高度概括性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历史研究”[5],包括图书馆史。目前,图书馆史研究有内史和外史两种研究范式。内史范式指的是研究图书馆内部发展史,包括图书馆藏书、管理、运转等内容,探索图书馆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外史范式指的是研究图书馆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即图书馆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寻图书馆与社会互动发展规律。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注重采用内史研究范式考察民国图书馆史。南京大学谢欢博士认为“我们在研究图书馆史时,除了从内史的视角探寻图书馆内部系统运行、发展理路外,更要从外史的角度,从整个社会大系统探究图书馆与其他机构的关系。”[6]他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为例,指出霍瑞娟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和李彭元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史稿》都是沿袭内史研究路径,建议今后的研究应采取外史研究范式,关注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同时期其他同类机构间的往来关系。
与前人研究有所不同,王阿陶博士的《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将“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相结合,从而全面展现这一时期图书馆社团的面貌。在内史研究方面,该书第三章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例,探讨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内部管理与运行,包括:(1)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制度建设,如制定《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大纲》《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细则》《中华图书馆协会总事务所办事简则》《中华图书馆协会委员会规程》等;(2)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组织构架,如设立决策、执行、监督与权力部门,总事务所、委员会、通讯处、办事处等机构;(3)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职员与会员,如会员数量与类型、入会要求与征集登记、会员福利与优待;(4)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经费收支,如经费的组成、经费困难与应对;(5)中华图书馆协会召开的数次年会。此外,第四章“图书馆社团的学术成果与学术研究活动”考察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地方性图书馆社团创办的刊物、出版的书籍、形成的调查报告与统计报告、举办学术演讲等内容。这些内容展现了图书馆社团自身的建设、运行与管理、学术研究等情况,是采用内史研究范式的成果。
同时,王阿陶博士也采用外史研究范式呈现图书馆社团与政府间的互动图景。在第五章“图书馆社团在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作用”部分,作者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例,探讨了图书馆社团与教育部等机构关于年会提案的往来关系。如1929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中提出有关图书馆标准的议案,并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1930 年,教育部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呈请做出了批复。“由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图书馆标准化进程中所做种种努力,成为图书馆标准化建设的领导者和主要倡导者,教育部也开始将有关图书馆标准问题交予中华图书馆协会研讨。”[3]258此外,中华图书馆协会还就开办图书馆学校、培养图书馆人才问题上呈请教育部。教育部表示同意,并通令各国立图书馆、各省市学校施行。不仅如此,中华图书馆协会、北平图书馆协会还在力请庚款用于图书馆事业,上海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争取图书馆经费保障,中华图书馆协会争取改进图书馆员待遇与社会保障,中华图书馆协会、安徽图书馆协会抗争图书加税与邮票加价,中华图书馆协会古籍保存与保护等方面与教育部、交通部、行政院、内政部等部门进行交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见,中华图书馆协会、北平图书馆协会、上海图书馆协会、安徽图书馆协会等图书馆社团与政府部门在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有着频繁的互动。这些内容是以往研究不曾关注的地方,但却是全面认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重要方面。
1.3 提出颇具创见性的观点和论断
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创新,如新观点的提出。王阿陶博士提出了一些创见性的观点。
一是作者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共召开八次年会。现有的研究都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召开过六次年会。李彭元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史稿》一书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召开1929 年南京年会、1933 年北平年会、1936 年青岛年会、1938 年重庆年会、1942 年重庆年会和1944 年重庆年会[7]。霍瑞娟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一书也持同样的观点[8]195-201。此外,其他很多文章也都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共召开过六次年会。对此,王阿陶博士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其存在的24 年时间里共召开过八次年会的观点。当然,此观点是在七次年会的基础上提出的。2012 年,王阿陶在论文《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1925—1949)》中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共召开过七次年会,分别为1929 年1 月南京年会、1933 年8 月北平年会、1936 年7 月青岛年会、1938 年11 月重庆年会、1942 年2 月重庆年会、1944 年5 月重庆年会和1947 年10 月南京年会[9]。此后,王阿陶博士对中华图书馆协会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作者在《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中认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从成立到最后无形解散的24 年中,仅召开八次年会,分别是在1929 年(南京)、1933 年(北平)、1936年(青岛)、1938年(重庆)、1942年(重庆)、1944 年(重庆)、1945 年(重庆)、1947 年(南京)。”[3]172该书介绍了历次年会的筹备、召开、提案、影响等,内容详尽,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作者对“图书馆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与补充。自20 世纪80 年代起,程焕文、吴稌年、叶继元、范并思等著名学者对“图书馆精神”进行了研究,其中以程焕文教授为代表。1988 年程焕文首次提出“图书馆精神”,其内涵包括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与自强精神,强烈的自爱、自豪与牺牲精神,大胆地吸收、探索、改革与创新精神,读者至上精神,嗜书如命精神[10]。1992 年程焕文在《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一文中将“图书馆精神”概括为爱国、爱馆、爱人、爱书[11]。此后,程焕文还有多篇文章对“图书馆精神”进行阐释。总体来看,程焕文的“图书馆精神”研究从整体视野出发,立足于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人群体和图书馆事业。由于“图书馆精神”发端于民国时期,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这一时期“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展现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的精神风貌。王阿陶博士以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创办的专业刊物《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发表的陈长伟、沈祖荣、黄星辉、吴敬轩、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李钟履等学人的文章为史料进行分析,将当时图书馆学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来源归纳为以“奋斗精神”“坚持精神”和“公仆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图书馆精神”[3]368-369,这是对程焕文提出的“图书馆精神”的补充与拓展。
三是作者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功能发挥不充分的原因进行了新的阐释。此前,有学者研究阐释了中华图书馆协会解散的原因,如霍瑞娟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解散归因于社会动荡不安、经费来源匮乏、群众参与度低、基础不够稳固、管理能力不足、协会组织松散等[8]18-22。其实,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解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功能发挥不充分,王阿陶博士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她认为民国时期很多地方性图书馆协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或成立时间短,或开展活动少,或几经停滞,原因有三。一是政党的挤压。当时的政府试图通过参与群众性社团对其加以控制,避免演变为政治性社团。自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政府通过立法,严格控制社团的活动,“图书馆社团的各项正常活动同样受到极大限制”。二是由于战乱频仍、动荡的政局及图书馆社团会员分散,导致会员对社团的归属感和依附感不强,因而缴纳会费的意愿也不强,所以“以会员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图书馆社团往往经费掣肘,难以为续”。三是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社团职员均为兼职且四散分布,难以全力投入社团事务,并且具有专业图书馆学识及社团管理经验者较少,社团的组织、管理、运行呈现出非专业化特点,导致其开展工作延误迟滞[3]377-381。综上可见,与其他学者相比,作者从政党政治、职业情感和专业化三个方面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功能发挥不充分的原因进行了解读,具有一定的新意。
2 《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的不足
2.1 史料挖掘利用不够
王阿陶博士的《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一书以档案、报刊、史料汇编、回忆录、评传、纪念文集、学术论著、网络文献等多种史料为基础,通过整体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社团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该书中出现的图书馆社团数量统计不全、考证不完整等问题,表明作者的史料挖掘力度不够。
一是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数量统计不够。作者在第31 页统计出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社团有43 个。但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社团至少有44 个,还包括1940 年成立的北碚图书馆联合会。笔者在整理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档案时发现西部科学院档案(全宗号:0112)和北碚管理局档案(全宗号:0081)中有数件关于北碚图书馆联合会档案,涉及该会的成立、规章制度、历次执行委员会及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的往来等方面的内容。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写成《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地方性图书馆社团探究——以北碚图书馆联合会为例》[12]一文,探讨了该会的成立背景、成立过程、开展活动、历史评价等,展现了北碚图书馆联合会的历史。王阿陶博士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也曾查阅过重庆市档案馆藏图书馆事业档案,书中也有相关档案的利用,但并未出现北碚图书馆联合会的相关内容。史料的充分挖掘是进行数据统计的基础,这也给我们一个暗示,民国时期很可能还有其他图书馆社团,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集、挖掘相关档案或原始文献。
二是关于四川图书馆协会的梳理有欠完整。作者在第109 页指出:“然而十天以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阶段,四川图书馆协会的筹备工作也未能继续。”实际上,抗战爆发后,四川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并开展活动。关于成立具体日期,现已很难考证。但是,笔者在相关资料中找到了四川图书馆协会的信息。1938 年11月27 日至30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大礼堂召开第四次年会,四川图书馆协会作为机关会员出席会议。此时四川图书馆协会会址位于成都四川中山图书馆,代表人为陈福洪[13]。也就是说,四川图书馆协会再次成立于1937 年7 月8 日至1938 年11 月27 日之间,会址也从原来的成都市立图书馆迁到了四川中山图书馆。
另外,关于四川图书馆协会存在到什么时候?何时解散?作者亦无提及。可以肯定的是,四川图书馆协会至少存在至1940 年初。因为在1940 年1 月30 日印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刊登的《抗战以后本会会员调查录》的机关会员中,四川图书馆协会赫然在列,仍然位于成都四川中山图书馆内[14]。这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图书馆协会成立后依托四川中山图书馆运行,馆长陈福洪很可能是四川图书馆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因为陈福洪热心图书馆事业,曾创办四川中山图书馆,并兼任馆长,有管理图书馆社团的经历。1934 年3 月13 日,四川图书馆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福洪当选为执行委员[15]。1938 年11 月27 日,他还作为四川图书馆协会代表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次年会。鉴于四川中山图书馆、陈福洪与四川图书馆协会的密切关系,笔者猜测四川图书馆协会很可能于1944 年解散。因为1944 年陈福洪去世后,作为四川图书馆协会依托的四川中山图书馆随即解散。当然,这还需要史料进行佐证。作者在梳理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相关史实中大量利用了各类图书馆学专业期刊,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是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重要史料,也被作者大量引用。但其中关于全面抗战时期四川图书馆协会的内容却未能呈现,说明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
三是关于成都市图书馆协会的史实亦不完整。作者考证显示,1942 年文华图专成都同学会在春熙路青年会召开三十一年度年会,决议发起组织成都图书馆协会,以加强和推进成都市图书馆工作,“但未有后续讯息”。虽然目前各类史料中关于成都市图书馆协会的记载很少,但还是有迹可循。笔者发现,民国晚期,美国图书馆专家沙本生(Charles Bunsen Shaw,1894—1962)来蓉考察图书馆事业的史料提到了成都市图书馆协会。1947 年10 月,美国图书馆学专家沙本生来华调查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员情况。11 月20 日,沙本生抵达成都。11 月22 日,《新新新闻》报道了沙氏在成都的行程,其中就涉及成都图书馆协会。11 月24 日,沙本生“参观省市立图书馆及女职校,成都图书馆协会公宴,午后二时请新闻界公开讲演。”[16]这是自1942 年文华图专成都同学会决定组织成都图书馆协会后关于该协会的报道。可见,成都市图书馆协会成立是毋庸置疑的。图书馆社团作为图书馆界的专业组织,负有对外交流的职责,比如此次沙本生来华考察,中华图书馆协会邀请演讲。同时,重庆图书馆界为了接待沙本生而成立了重庆市图书馆协会[17]。因此,成都市图书馆协会接待沙氏也表明了该协会是战后成都地区重要的图书馆社团,积极参与了国际交流。
11 月25 日,沙本生博士参观结束后与成都市图书馆协会人员合影。对此,1993 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中公布了照片,成为我们了解成都市图书馆协会的重要史料(图1)。

图1 沙本生与成都图书馆协会人员合影照片
从图1 可以看出,成都图书馆协会至少有19 位人员。然而,这些内容在《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中没有出现。《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是研究民国四川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作者在梳理成都市图书馆协会时并未参考。由此可见,作者需要加强相关史料的挖掘,这样才有可能完整地考证成都图书馆协会的历史。
另外,虽然作者在梳理与研究中华图书馆协会时挖掘了大量的民国期刊、报纸,也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档案,但其他档案馆藏中华图书馆协会档案未被利用。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显示,“重庆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等重要档案机构所藏民国图书馆事业档案中就包含部分中华图书馆协会档案,应大力挖掘与利用,发挥其价值。”[18]
2.2 史实表述存在错误
《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中涉及民国时期一些著名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发展重要事件、著名图书馆学人的相关史实,学界已达共识。然而,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并未注意到一些细节问题,出现了史实表述有误的情况。
一是关于国民政府决议筹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时间有误。作者在第120 页考证重庆市图书馆协会时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筹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时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教授的严文郁被委任为秘书长,负责筹建工作。”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国民政府决定筹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是在1945 年5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的,而并非是抗战胜利后。关于这一点,当时一些报刊都有报道。如194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突于四月十二日以脑充血症逝世,巨星陨落,举世同悲。我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月间在重庆举行会议,特通过议案一件:为纪念故总统罗斯福,筹设罗斯福图书馆,决议交政府办理。”[19]《华北日报》报道,“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纪念美故总统罗斯福先生,曾有设立罗斯福图书馆之决议。”[20]此外,《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教育通讯》(汉口)中也有相同内容的报道。不仅如此,当今学者杨玉麟在《民国时期“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研究》一文中考证显示,1945 年5 月5日至21 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一些文化教育界人士提议,会议通过了创设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决议,旨在纪念刚刚去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21]因此,筹设国立罗斯图书馆的决议是在抗战胜利前形成的。
二是关于全面抗战初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向国外征募图书的时间有误。作者写道:“抗战胜利后,袁同礼亲见各地公、私立藏书损失巨大,且后方教育文化界人士所需精神食粮迫切,毅然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名义(时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向欧美各国图书馆协会征募图书。”此处存在两个明显的错误:(1)袁同礼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名义向欧美各国图书馆协会征募图书时间有误。研究表明,1937 年11月19 日到1938 年1 月21 日,袁同礼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名义向美国图书馆协、德国图书馆协会、新西兰图书馆协会、英国图书馆协会、法国图书馆协会致函征书[1],并不是抗战胜利后。(2)“抗战胜利后后方教育”的表述错误。因为大后方的概念是相对于战争前线而言的,“随着抗战的演变而演变,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结束”[22]。所以,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已不复存在。笔者查阅作者引用的原文:“为抗战军兴之后,先生目击各地公私藏书损失之巨,与夫后方教育文化界人士需要精神食粮之切,又慨然以中华图书馆协会名义(先生为该协会理事长)向欧美各国图书馆协会征募图书。”[23]引文中的“抗战军兴后”指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是抗战胜利后。很明显,王阿陶博士对原文解读有误。
三是关于文华图专创办档案专业教育或中国档案教育产生的时间有误。作者写道:“1941年,他(沈祖荣)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办档案管理科,此举为中国档案学专业教育之创始”。这样的叙述与史实不符。关于中国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发端,学界众说纷纭,尚有争论,主要观点有三种:(1)1934 年秋,文华图专在教育的支持下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被认为是中国档案教育的起源[24];(2)有学者根据湖北省档案馆藏文华图专档案研究认为,1939 年教育部在文华图专附设档案管理科是中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开始[25];(3)1940 年教育部在文华图专设两年制的档案管理专科,此举成为中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开始[26]。虽然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档案专业教育产生时间未能达成一致。但是,学界多数学者都认为1934 年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是中国档案教育的起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代中国档案专业教育肇始于1934 年文华图专档案教席普遍为学界所接受。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中国档案学专业教育产生于1941 年的说法,更没有相关资料记载。仅有的记载也是1941 年12 月20 日,教育部同意文华图专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次年3 月至5 月正式办理第一期的消息[27]。从时间上看,文华图专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时间晚于该校其他形式的档案专业教育。因此,中国档案学专业教育开始于1941 年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2.3 引用遣词出现错误
王阿陶博士是一位勤奋的图书馆史研究者,她以坚持不懈的精神,花费长达十年的时间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爬梳,此种学术研究态度难能可贵。然而,可能是时间紧张或是笔误,行文中出现了一些人名或字词错误的地方。鉴于文章篇幅,笔者按照先后顺序列出数端。
(1)51 页脚注第二个注释出现人名错误,作者把《本市图书馆应办的几件事》一文的撰写者“萧纲”写为“萧纲季”。查阅史料,作者引用的是1934 年《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第2 期“论著”栏目的文章,原文作者为“萧纲”,并非是“萧纲季”。
(2)228页“分类法”下面的一句话说道:“民国时期,尤其是19 世纪20、30 年代,对于分类方法的研究,初步分为辨体与辨义两大类之间的定夺。”这里的时间明显错误,19 世纪20、30 年代不是民国时期,应为20 世纪20、30 年代。
(3)232 页正文第二个引用部分:陈长伟认为杜定友的分类法“保罗新旧学术,简单精细,易于记忆也。”笔者查阅1928 年第2 卷第4 期《图书馆学季刊》上陈长伟的《小图书馆组织法》一文进行核对,此句中的“保罗”应为“包罗”,属于笔误。
(4)262 页提到中华图书馆协会历次年会通过有关通俗图书馆的议案,包括第一次年会通过的《呈请政府讲庙宇改设通俗图书馆案》。笔者查阅《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中有关年会的提案发现,陈长伟提出了《呈请政府将庙宇改设通俗图书馆案》,王阿陶博士行文中将“将”误写为“讲”。
(5)294 页正文中提到了世界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然而,王阿陶博士在支撑引用史料中却写为斯文·赫丁。两处的人名不统一,应是笔误造成。查阅原文和相关资料,应为斯文·赫定。
(6)343 页写道:“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拉尔夫·尤而凡林(Ralph A. Ulveling)特就袁同礼访美一事致函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以示感谢。”这句中的人名出现错误。笔者查阅《美国图书馆协会感谢袁理事长访美》一文记载:“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尤尔凡林及执行秘书米兰姆,为袁理事长访美事,特致行政院宋院长一函表示谢意。”因此,当时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应为“尤尔凡林”,而不是“尤而凡林”。笔者认为王阿陶博士可能该把“尔”的繁体字“爾”误认为“而”。
《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中关于字词错误的地方不止以上几点,囿于篇幅,这里不再列举。对于一部数十万言的著作来说,出现一些字词错误无伤大雅,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阅读体验。因此,笔者本着学术研究应精益求精的态度,将书中的一些字词错误指出,希冀对此书的完善有一定的帮助。
3 结语
《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研究》一书是近年来学界整体上研究民国图书馆社团的一部力作。作者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端正的学术研究态度,通过梳理大量史料,系统研究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社团的发展历史,填补了民国图书馆社团整体性研究的空白。该书同时结合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史和外史研究范式,提出了一些颇具创见性的观点和论断,这对于拓展民国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它的出版在中国图书馆社团史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将会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