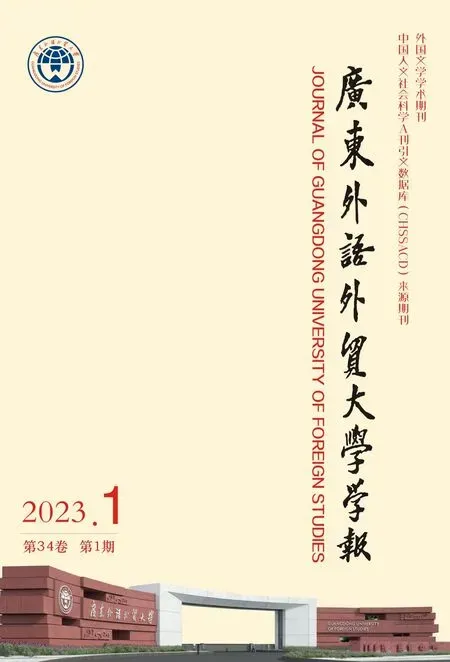布瓦洛形象论争之考辨
王夏
引 言
在中西诗学史上,法国17世纪著名的诗人、文学理论家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的形象经历了复杂的演变。他在世时,布瓦洛凭借《诗的艺术》(L’ArtPoétique,1674)成为“古典主义代言人”,他是“太阳王”(Louis XIV, 1638-1715)最器重的宫廷诗人,是有着狮子般性情的讽刺诗人和倔强的“崇古派”代表;在18世纪,布瓦洛是力求革新的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等启蒙思想家难以完全决裂的伟大的古典主义大师;在19世纪,布瓦洛是浪漫主义以“三一律”为由大刀阔斧批判的对象和文学演变史中新思潮反对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的替罪羊(Miller, 1942: 564);从20世纪至今,布瓦洛成为一个与现代和后现代文艺美学思潮格格不入的古典主义文论家。不同时代以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想象各自建构了布瓦洛形象,由此构成了一部面貌迥异的布瓦洛形象史,但这部形象史却最终都基于一个既定的事实——布瓦洛的“古典主义立法者”形象。
法国国内的论争远远不局限于此,与布瓦洛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作家、学术机构以及之后布瓦洛的文学研究者和传记作家都曾对其性格、人品等形象特征展开过详细的讨论。布瓦洛是一个怎样的人?严肃的老学究?卑鄙、阴暗的自私者?愤世嫉俗者?勇敢、正义的化身?真诚的人?自17世纪以来,鉴于他与国王的亲密关系以及他所参与的众多的文学活动和论战,布瓦洛始终是一个“敏感人物”,他的品行和人格也一直备受争议,被公认为“最受争议的17世纪法国作家”(Miller, 1942: 143)。一方面,厚今派的代表人物丰特奈尔(Fontenelle)说他是“阴险、伪善、邪恶的人”;法兰西学院在他逝世不久评价他为“卑鄙的思想者和愤世嫉俗者”;多努(Daunou)揭示他“铁石心肠”;拉·莫特·潘塔隆菲布(La Motte Pantalon-Phoebu)指责他“没有思想,是一个愚蠢的、古人的业余爱好者”(Miller, 1942: 106);有人以他最初拒绝在《诙谐决议》(ArrestBurlesque,1671)上署名说他“狡猾”;也有人猜测他把他哥哥的《论崇高》(TraitéduSublime,1674)译稿占为己有(Boileau-Despréaux, 1966: XXXVI),说他自私阴险……另一方面,在布瓦洛中学的文学老师阿尔伯特·拉方丹(Albert Lafontaine)神父眼里,布瓦洛是诚实、坦率、单纯的老实人;路易·拉辛(Louis Racine)每当提起他时,总是充满了亲切的回忆;查尔斯·奥古斯汀·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着力于他爱社交、有正气、 敢担当、“最活泼的正经人物”的肖像描写(布瓦洛,2010:20,30);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 1906: 6)称赞他是“一个真实的、纯粹的、从种族和心灵上来说都很纯净的资产阶级”,是法国人骨髓和灵魂的存在;乌尔达·于日乐·阿玛杜什(Ourda Hugel-Hamadouche, 2014: 177)把他作为“生活和写作的典范”,认为他具有坦率的性格和中庸的气质,并发现他对塑造和培养共和国“好公民”的价值和影响。
在国内,布瓦洛的“古典主义立法者”形象是学界的共识。在西方文论史和美学史的教材中,朱光潜、马新国、朱立元、曾繁仁、张法、高建平、刘旭光等学者将布瓦洛作为西方诗学史和美学史上“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加以简要介绍,布瓦洛形象研究的其它维度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虽然也有学者开始对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所体现的担当意识有所关注(刘伟,2015:31-34),其评介和引用只限于《诗的艺术》。由于布瓦洛的其它法文作品目前尚无完整的中文译本,对布瓦洛形象的全面认知和相关史实的考证付之阙如,这种研究的缺憾使人们对布瓦洛形象的争议和偏见处处皆在。“路易十四的奉承者”“古今之争中的保守派”等声音似乎构成了布瓦洛难以摆脱的是非纠缠。
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个饱受争议而又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愈来愈显得重要。鉴于此,本文将突破以往布瓦洛作为古典主义奠基人的形象认知,在熟稔把握布瓦洛法文文献的基础上,以文本分析与史实佐证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呈现布瓦洛形象的真实风貌。因而,我们更关注布瓦洛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个体形象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内涵,以期弥补国内布瓦洛形象认知的缺憾。
然而,我们又如何走进这位距今300多年的人物的心灵深处,把握他身上最真实和最本质的品质?诗歌的创作和理解离不开语境,需结合文化因素、社会背景和作家个人经历,始能更深入解读其本真(孙毅、邓巧玲,2022:34)。或许最有效可行的方法便是去除一切的偏见和立场,像平常人一样承认他的种种不完美,而只攫取他的文学生活中那些最真实的东西, 或许我们可以如圣伯夫所言,“带着极真切,极现实的情感来谈他”(布瓦洛,2010:12)。
真实与奉承
尽管布瓦洛崇尚文学的真实,反复吟唱着“没有比真更美了,只有真才是可爱”,但这位“巴那斯山的法官”却似乎离“真实”很远,他留给人们更深的是作为路易十四的宫廷诗人的形象。在《诗的艺术》《讽刺诗》(Satires)、《诗体书简》(Eptres)、《颂诗》(Odes) 等作品中,都有很多赞美路易十四英明、骁勇及其伟大时代的诗篇。许多个世纪过去了,“奉承者”布瓦洛的评价之声却一直存在。有人给出一种解释:如果说布瓦洛讨好国王,那是因为17世纪的国王代表法国,他通过讨好国王而讨好他的国家。推论:布瓦洛是一个好公民!(Hugel-Hamadouche,2014: 177)而当所谓的奉承对象是一个开明智慧、支持文艺事业的君王时,“奉承者”的含义就变得异常复杂。诚然,他与国王的依附关系对其人生存在影响,但是并不能成为评判布瓦洛真实与否的唯一依据。在布瓦洛的作品中,无论是讽刺诗,还是诗体书简与通信,这些文体对真实性的要求都很高。透过那些散布其间的、有关他的人生、轶事及其思想的描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布瓦洛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来自内心的真诚,是他在面对多重选择时体现出来的睿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布瓦洛清楚自己的才赋,在史诗、颂诗、戏剧和讽刺诗之间坚定地选择了讽刺诗。在《讽刺诗》中的“致国王”(Discours au Roy)一诗中,布瓦洛坦言,不公与轻率并非他的笔调(Boileau-Despréaux, 1985: 64),他不善于押韵,以致于诗歌有时有些轻浮。基于这种考量,布瓦洛(2010:69)很少专门做颂诗,而只是号召诗人“振发诗情”以歌颂国王的战绩,并告诫诗人“像这样的丰攻伟烈不容许平凡手笔”。他对国王说,“我只欣赏你。说出这种崇拜的乐趣使我学着在讽刺诗中赞美你”(Boileau-Despréaux, 1985: 200)。在讽刺诗中,布瓦洛(2010:94)既乐于“揭丑”,又不忘适时赞美国王,也就是他所谓的“一面用这支笔把邪恶涂成皂黑”,“另一面用这只笔歌圣德敬仰君王”。
对于戏剧创作,布瓦洛也认识到自己没有这种天赋,“法国的戏剧受卜拉顿的影响较深。而我,关于这一主题,我远远没有这种文笔”(Boileau-Despréaux, 1985: 199)。他不能像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莫里哀(Molière)和让·拉辛(Jean Racine)一样,通过丰饶的戏剧艺术化地塑造国王的英明形象,只能在讽刺诗、书简等文体中偶尔抒发对国王的崇拜之情。
在认清自己不擅长颂诗、史诗和戏剧之后,讽刺诗成为了诗人终其一生的选择。在“诗体书简十”(Éptre X)中,布瓦洛追忆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追随着兴趣的指引,我迈出了大胆的步伐。我唯一的天赋协助我作为佩赫斯(Perse)和贺拉斯(Horace) 勤奋的爱好者一路前行,走近芮尼 (Régnier)先生,我坐在了巴那斯山之巅”(Boileau-Despréaux, 1985: 212-213)。“讽刺诗九”(Satire IX) 副标题为“对自己才调说话”,这是布瓦洛模仿贺拉斯的“自我批评”。他自嘲“泼妇骂街”的刻峭,“愤世嫉俗”“好骂世”的“坏生性”以及想与贺拉斯齐名的狂妄企图,但真正让他把讽刺诗作为一生职志的原因在于说出“心里话”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见了平庸诗人被“捧为诗中王、文坛执政”就“心头冒火”,“见坏书就觉恶心”的强烈情感,是一种揭露愚昧,“使理性得蒙昭雪”的快意,更是一种“淘沙取金,不容许真中掺假”的果断和“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智慧与寄托(布瓦洛,2010:70)。
第二,布瓦洛意识到史官身份与追求真理之间的矛盾,选择了忠实于内心。1677年,布瓦洛因拉辛的《菲德尔》(Phèdre,1677 )受到牵连,国王任命布瓦洛与拉辛为史官,暂时退出文坛以躲避攻击。他们肩负路易十四的信任和重托,担负起用诗歌记录国王英雄事迹的伟大任务。但是“如何歌唱一个‘行动中’的英雄呢?尤其在他雇佣你和监视你的时候?诗歌如同灵感的自由一样要求表达的自由,拉辛和布瓦洛都深谙此道。在‘长期尝试’这项工作后,或许在他临死前,他才不得不承认这点。他们二人难道不会感受到:‘这项任务根本就与他们的天赋背道而驰’吗?”(Boileau & Racine,2001: 97)《友谊之信——1687-1698年间的通信》(Lettred’uneamitié——Correspondance1687-1698, 2001)中的这些话揭示了布瓦洛对于史官身份的困惑。他深知历史的真实难求,尤其当描写和记录的对象是国王。对于国王,布瓦洛满怀特殊的情感。他感激他对自己的庇护和赏识,同时欣赏他的英勇,特别是他对文艺事业的支持。但他深知做好一名“史官”的难度和“国王的史官”这一称呼背后的沉重和无奈,他清楚地认识到,如同诗歌的创作需要自由一样,历史的撰写需要绝对的真实。这一切使他感到力不从心。
应该说,布瓦洛对史官身份的困惑反映出他对历史家应该求真以及承担某种责任的觉悟。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出征和考察,在这项任务中所投入的热情远远少于拉辛,也甘愿承受年薪比拉辛减少的后果(Boileau & Racine,2001: 117)。“对布瓦洛而言,这段新的人生经历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只有从他临死前感人的懊悔中获知:他对这项工作感到‘非常气愤’,‘他的天赋只在于诗歌’”(Zuber & Cuénin, 1998: 267)。布瓦洛的隐退,恰恰是他崇尚自由的真实写照。
第三,布瓦洛在基督教统治的宗教氛围中,不加掩饰对冉森教派某些思想的好感,保留了相对自由的宗教思想。在宗派繁多的17世纪下半叶,“太阳王”加紧基督教的一统化,对加尔文教、冉森教、神秘主义等异端教派加强思想控制。冉森教徒由于自封为圣奥古斯丁弟子,被路易十四视为狂热的“危险分子”,冉森教因此成为“令人生畏”的教派(伏尔泰, 1982:565),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但这种严峻而可怖的思想局势似乎并未影响布瓦洛。《致外省人信札》(Provinciales,1656)出版时,他20岁。“他并不是唯一对它表露出彻底欣赏的人,但这种赞赏却决定了他作为论战者的职志。在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作品中,他看到了对危险的信仰和天赋谎言的抗议思想”(Zuber & Cuénin, 1998: 263)。布瓦洛欣赏帕斯卡尔——这位冉森教的杰出代表身上表现出来的论战气质。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奉者、怀疑主义者、不信教者构成他日常生活的同伴。冉森教的领袖阿尔诺(Arnauld)、出生于冉森教家庭的拉辛,都与作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布瓦洛从这个异教徒身上看到了一种思想的崇高,这是一种面对劫难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更是一种为宗教事业甘愿牺牲的伟大精神。在致主席夫人的“多样化诗歌与讽刺短诗七十”(Poésies Diverses et Epigrammes LXX)中,布瓦洛坦言:阿尔诺是“我在法国最尊敬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Boileau-Despréaux, 1966:273)。而对与冉森教永远纠缠不清的拉辛来说,布瓦洛怜惜他的真诚与才能,勇敢地保护受到攻击的他,支持他,并与他保持了持久而珍贵的友谊。在他看来,这些异端创始人身上所具有的笔战气魄以及论证的逻辑和语言都与宫廷中肤浅和诡辩盛行的风气截然不同(Magne, 1929:16)。对于后者,布瓦洛深恶痛绝,而对于前者,在当时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局势下,他并未以“异教徒”的理由排斥他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所敬仰的伟大思想家也是异教徒。“虽然朗吉努斯是异教徒,但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崇高。它在《荷马史诗》中同样存在”(Boileau-Despréaux, 1966:XIX)。这种崇高对于布瓦洛而言,正是诗歌必须拥有的东西。
然而,对冉森教派的这种好感和亲近却使布瓦洛的一生卷入了争论和攻击之中,并迫使他不停地为自己的信仰进行表态。在“诗体书简十二:关于上帝的爱”(Eptre XII:Sur l’amour de Dieu)中,布瓦洛坚决拥护奥古斯丁把上帝之爱变成所有虔诚的枢纽和归宿的观点。而在“讽刺诗十二:论模凌语”(Satire XII:Sur l’équivoque)中,他一再表明对上帝的虔诚,努力澄清他与冉森教的关系。但他的证明最终却不被国王看好,这首讽刺诗也多次遭禁,直到他死后才被公开出版。
“自由的真理是我唯一的追求”(Boileau-Despréaux, 1985:188)。正如诗人在致德吉列拉格(De Guilleragues)先生的“诗体书简五”(Eptre V)中写下的这句话,在所有人都在为国王“荣誉”讴歌的17世纪,布瓦洛却执着地追求他所热爱的真理和正义,在思想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在颂诗和讽刺诗之间,他坦言自己没有写颂诗的才能;在做史官期间,他深知“真实难求”,选择了“只忠实于诗歌”;在以异教徒为敌的国教统治下,他坚定地保留对冉森教派的好感。除此以外,“诗体书简五”中对自己前后期创作的总结,“致法兰西学院院士贝洛先生函”(M. Perrault,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中与贝洛的亲切交谈,《友谊之信》和《致布霍斯特的信》 (LettresàBrossette)中平常而真挚的情感,《诗体书简》中那个乐于在奥戴拉(Auteuil)生活、在那儿热情接待朋友、与园艺师亲切交谈的平实的老人,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位严肃的诗人真诚的心灵。无论是他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对安静和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向往,还是对冉森教派的好感与欣赏,无不体现出他的真实。这种真实也许带有“不迎合别人而牺牲自己利益”(Boileau & Racine, 2001: 86)的实用主义特征,但它却是特殊时期对自我的一种解放,是布瓦洛对人生的一种彻悟与热爱,更是一种王权至上的社会中“极其艰难的坦诚”(Boileau-Despréaux, 1966:XXVII)。
勇敢与怯懦
“要着手干他那一项事业是要有很多的勇气和胆量的”(布瓦洛,2010:19),圣伯夫在《布瓦洛评传》(NoticesurBoileau,1852)中的这句话是极为中肯的。作为讽刺诗人,没有勇气和胆量是万万不可想象的。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斥责他“保守”和“怯懦”,这些人通常是以“激情”“想像”和“情感”的所谓“现代性”视角,攻击他以理性为主,压制想像和情感的诗学观点。而在七星诗社出版的《布瓦洛作品全集》(Boileauuvrescomplètes, 1966)前言中,一段因《唱经台》(LeLutrin,1674)引起的推测也指向勇敢的布瓦洛的反面形象。同样,对布瓦洛在早年光顾“白十字”咖啡馆时与拉辛、菲雷蒂埃(Furetière)等人模仿《熙德》(LeCid,1636)的滑稽喜剧《脱帽的夏普兰》(Chapelaindéconffé,1665),七星诗社(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出版的作品全集给出这样的注释:布瓦洛不希望在作品上署名,也许是因为他畏惧万能的宫廷诗人夏普兰(Chapelain)(Boileau-Despréaux, 1966:1060)。这些不同的维度,似乎在无声地对抗着“勇敢的布瓦洛”这一结论。但当我们重读布瓦洛的作品,那些铿锵的文字向我们敞开的却是一个勇敢的心灵。至少从以下三点来看,布瓦洛是真正的勇者。
首先,他敢于挑战权威。1656年,位于荣誉之巅、担任皇室津贴的审核者和法兰西院士的夏普兰花了6年之久创作出的《贞德传》(LaPucelle,1656)雕琢浮夸,布瓦洛勇敢地站出来于1663-1664年间写了“多样化诗歌与讽刺短诗十五:反对夏普兰”(Poésies Diverses et Epigrammes XV:Contre Chapelain)指摘夏普兰的诗枯燥乏味,不忍卒读。随后,在致勒·瓦耶(Le vayer)神父的“讽刺诗四”(Satire IV)中,他嘲笑夏普兰的愚蠢(Boileau-Despréaux, 1985:84)。1665年,在“多样化诗歌与讽刺短诗十七:夏普兰的风格”(Poésies Diverses et Epigrammes XVII:Vers en stile de Chapelain)中,他讽刺夏普兰生硬沉重的诗歌风格;同年,他与拉辛、吉尔·布瓦洛(Gille Boileau)、菲雷蒂埃等人集体创作了《脱帽的夏普兰》,再次嘲讽和作弄夏普兰。夏普兰把与布瓦洛一起共同创作的人视为“新桥诗人”和“黑暗的称颂者”,并谴责布瓦洛的作品为“卑贱的滑稽”,从此与布瓦洛公开宣战。对于文学权威夏普兰的宣战,布瓦洛(2010:89-90)并未畏惧,这一点在他1668年发表的“讽刺诗九”和1674年《诗的艺术》中可以得到证实。
很显然,布瓦洛追溯“熙德之争”,目的是讽刺夏普兰代表学院写的《法兰西学士院关于〈熙德〉的感想》(Sentiment de l’Acdémie sur le Cid, 1638)。虽然布瓦洛并未参与这场文学纷争,他却满怀对高乃依艺术成就的肯定和对以夏普兰为首的文学审判的不满。接着笔锋一转,回到夏普兰身上,嘲讽他的《贞德传》附庸风雅。而在《诗的艺术》中,布瓦洛重申了“提高格调”的重要性,并提出“崇高”与“矫饰”、“诙谐”与“低级的滑稽”的重要差别,有力地回击了夏普兰有关“卑贱的滑稽”和“新桥诗人”一说。
除了夏普兰以外,布瓦洛对一些无知的贵族、伪善的宗教人士和雕琢派的博学之人都发起过攻击。由于莫里哀的作品揭露和讽刺了上流社会的阴暗面,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因此生前经常遭到一些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反对和迫害。布瓦洛敢于站出来,保护和支持莫里哀。对拉辛同样如此。在“菲尔德之争”中,面对冉森教派以爱情题材入诗为由对《菲德尔》的思想性的谴责和演出时来自布荣爵夫人(Duchesse de Blon)和尼维尔公爵(Dus de Nevers)的阻挠时,布瓦洛(2010:95)“坚强地站着,反抗这场风暴,并把他的正义的抗诉公诸社会”。在《诗的艺术》第三章,布瓦洛(2010:36-37)回溯了欧里庇德以爱情作为悲剧主题的历史,表达了与冉森教派的严酷教义相悖的立场。他并不反对悲剧描写爱情,但对描写手法和要求做了相应的补充和规定。1677年,他写下“诗体书简七:致拉辛”(Epitre VII: A Racine),回击贵族势力的阴谋,鼓励和支持拉辛。对来自法兰西学院的压力,他同样勇敢地展开挑战。1685年,法兰西学院以菲雷蒂埃取得自主决定《字典》(Dictionnaire)的编订权为由而排斥他,布瓦洛不畏法兰西学院的阻挠,于1688年菲雷蒂埃逝世后请求学院为其举行葬礼(Boileau-Despréaux, 1966:XXXVII-XXXVIII)。
其次,他敢于批评拙劣的作家。对布瓦洛而言,诗歌的体裁有主次之分,诗人也有优劣高下之分。《诗的艺术》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巴那斯多么崇高!精诗艺谈何容易!一个鲁莽的作家休妄想登峰造极”,诗坛的崇高性质决不容许拙劣、鲁莽和平凡的诗人和文匠滥竽充数,因此布瓦洛劝告诗人必须“久久地衡量自己的才华和实力”(布瓦洛,2010:3-4)。正是忠实于这一信仰,布瓦洛敢于说真话,批判那些不称职的平庸作家。其中有“骄傲的诗人”龙沙(Ronsard);有戴保德(Desportes)、白陀(Bertaut) 等“俗恶的滑稽家”;有不从容写作的斯居代利(Georges de Scudéry);有宫波(Gombauld)、梅纳(Maynard)、马尔维(Malleville)等平庸的商籁诗人;有专写文雅爱情著称的斯居代利小姐(Madeleine de Scudéry);有无病呻吟的色奈克(Sénèque);还有包野(Claude Boyer)、彭申(Pinchêne)、兰巴尔(Rampalle)等“无味的作家”。这诸多的作家都被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点名批评。如果没有超人的胆量和勇气,很难想象其批评能如此这般犀利和尖锐。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布瓦洛不留情面地批评诗坛的拙劣诗人,勇敢地捍卫诗坛的纯净和崇高。“这位讽刺诗人让拙劣的诗人从满意的天堂跌落,在他们的身上投下理性的光辉”(Reguig, 2016: 252)。他坚持讽刺诗创作,敢于讲真话,在讽刺诗这个“冒险而倒楣的行业”,正如他为自己所画的自画像一样,尽管遭人唾骂为“刻薄”和“愤世嫉俗”者,却乐于“揭发愚人的陷害,使理性得蒙昭雪”(布瓦洛,2010:90-92)。
再者,他敢于直面当下,揭露不良的文学风气。对于“诙谐”在17世纪中后期的跌落,布瓦洛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诗的艺术》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提到这种风气。“这风气有如疫疠,直传到全国郡县,由市民传到王侯,由书吏传到时贤。”诗坛上的“这股歪风”、“这种荒唐的放纵”指的就是“诙谐”风格的泛滥和滑坡(布瓦洛,2010:8)。布瓦洛争锋相对,在列举了诸多反面作家的粗俗滑稽之后,提出要学习马罗(Clément Marot)的“风雅的谐谑”以“提高格调”。在第三章篇尾,布瓦洛以对莫里哀喜剧的惋惜和期许再次发起对“新桥口味”的嘲讽,并进一步提出“高尚的诙谐”的喜剧观。与“诙谐”泛滥成灾相对的,还有盛极一时的矫饰之风。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多次以斯居代利的作品为例,揭露这种浮夸和雕琢之风的可笑。而在《传奇英雄的对话》(Dialoguedeshérosderoman,1713)序言中,布瓦洛更明确了对斯居代利小说的批判态度。
对于诗坛上的名利和虚荣,布瓦洛同样予以揭露和反对。“巴那斯山忘掉了它那初期的高贵。丑恶的牟利欲望熏昏了作者神思,粗劣的谄谀之辞玷污了一切文字;于是到处产生出千百无聊的著作,凭厉害决定褒贬,为金钱出卖讴歌。切莫让这种颓风成为你白圭之玷”(布瓦洛,2010:67)。在布瓦洛(2010:64)看来,诗坛的崇高本质不容许玷污,他决不允许“把神圣的艺术变成牟利勾当”的不良风气。正如1843年阿玛尔(Amar)出版社得出的结论:布瓦洛热爱高尚,对“灾难的时代”(Boileau-Despréaux, 1843: 10)以及“被玷污的秩序充满憎恨”(Hugel-Hamadouche, 2014: 167)。
在“多样化诗歌与讽刺短诗六十四:致尊敬的神父”(Poésies Diverses et Epgrammes LXIV:Aux Reverends Peres)中,布瓦洛反问自己,“重读朱韦纳尔(Juvénal)和贺拉斯,我尚不足以拿出讽刺诗人的勇气”(Boileau-Despréaux,1966:270)。就是这样,布瓦洛以贺拉斯等优秀的讽刺诗人为榜样,在不断的反思中变得更加勇敢。不管是谁,哪怕是最风行的作家、最受人景仰的院士、最显赫的贵族,或是最卑微亦或是最伟大诗人,只要他玷污了诗坛,他就会义不容辞地举起战斗的旗帜。就像他在致德·霍什神父(l’abbé des Roches)的“诗简二”(Epitre II)中的自白:“我们的诗歌是糟糕的,他们的就更值得看吗?我在这已经听到利格尼埃(Lignière)的怒吼。他召唤我投入战斗,无需写太长的文章”(Boileau-Despréaux,1985:174)。这就是战斗的布瓦洛所表现出来的果敢与胆识。
担当与利己
对布瓦洛而言,大多数人从他对文学事业的倾心投入中看到他作为知识分子要求介入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担当意识,但鉴于他和国王的亲密关系,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由专写讽刺诗的“暴躁的年青人”变为规矩、老实的理论家和诗人,是为了获得官方的认可,努力挤入掌控权利的上流社会,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自己,那这种声音也会将一切淹没,在历史上只留下丑闻和阴暗的字眼。
提到17世纪文学,布瓦洛的名字就无法避开,因为他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有着太多的牵连。诚如圣伯夫所说,没有这位文坛总管,莫里哀、拉封丹和拉辛的伟大就要大打折扣(布瓦洛,2010:32)。这就是“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存在的重要意义。“为什么立法”和“怎样立法”不仅仅有政治的维度,还有布瓦洛改革社会道德和守护文学理想的初心。这恰恰体现的是布瓦洛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改革是决心,也是一种担当。“我看你这样微弱,写作又这样不敏,居然想负起责任来改革世道人心,言词像泼妇骂街、高铁闹堂的刻峭,你那愤世嫉俗真叫我看了发笑”(布瓦洛,2010:79)。布瓦洛1667年在“讽刺诗九”(Satire IX)中写下的这段话,表面是在自我解嘲,却表明了他创作讽刺诗的初衷和进行文学革命的重要原因。因为对布瓦洛而言,文学是他实现改革“世道人心”的唯一途径。从他放弃神学和法学,决心选择文学开始,“用讽刺诗改良道德风尚”(Magne, 1929: 8)的这种愿望早在少年布瓦洛的心中悄悄埋下了种子。他对马莱伯(François de Malherbe)、拉康(Honorat de Bueil, seigneur de Racan)或受神灵启示的人满怀敬仰,学习他们的职业操守和尊严。投石党运动后,巴黎诗坛故弄风雅的诗歌风气盛行,真正的诗歌被淹没(Zuber & Cuénin, 1998: 265)。当他看到位于荣誉之巅的夏普兰创作出的《贞德传》不忍卒读、遭人耻笑时,布瓦洛的愤怒爆发了。这种愤怒源于对现实的抗议和作为作家强烈的尊严感和伟大的使命感。在“多样化诗歌与讽刺短诗五十六:关于他的肖像”(Poésies Diverses et Epigrammes LVI:Sur son portrait)中,布瓦洛为带“愤怒之情”的自己勾勒了一幅自画像:“别再寻找一个被描绘在画里的作家的名字,因为从他看着,并指着《贞德传》的表情上来看,谁不能认出这是B先生?”(Boileau-Despréaux,1966:266)讽刺的口吻将对夏普兰的愤怒之情和盘托出。如此种种,坚定了布瓦洛进行文学革命的决心。正如圣伯夫所言,布瓦洛(2010:18)所要做的,是像帕斯卡尔在散文界进行的改革一样,在诗歌领域也掀起一场革命。换言之,就是要把诗人引入正轨,提高其创作水平和品质,形成良好的文学风气。
在改革的道路上,他从以批判和讽刺见长的讽刺诗开始,结合笛卡尔理性哲学和朗吉努斯崇高论,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和制定规范;在理论上,他以《诗的艺术》为主要依据,从作家、创作过程、读者等层面做出严格规定,要求诗人以理性和像真性为原则,杜绝粗俗、浮华的不良创作;从社会实践上,他加入反对矫饰文学的文化圈,切身践行改革的主张。去除丑劣和粗俗,弘扬美好与崇高,主张文学与道德合一,建立规范、有序、均衡与和谐的文学秩序,这就是布瓦洛作为改革家的担当意识。
坚守是情怀,也是一种担当。对于文学,布瓦洛寄予它一种特殊而真挚的情感。文学是他的信仰,因为它代表崇高和纯净,是无知的人类寻求超越的精神归属的方式。在“诗体书简五”中,布瓦洛回忆起自己的文学之路,“谁会在这种可怖的职业中希望获得充实?谁相信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命运就应该屈服吗?”(Boileau-Despréaux,1985:188)“我却喜欢一种更高贵的职业。这位书记官的儿子、兄弟、叔叔、表哥、妹婿都前来劝我,给我很多有用的建议。我却远离宫廷,游荡诗坛”(Boileau-Despréaux,1985:66)。选择诗歌和讽刺诗,是因为他对文学寄予真诚的期许。布瓦洛宁愿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致力于文学事业,甚至是选择讽刺诗这一“最冒险、最可怖的职业”。
在致国王的一首讽刺诗中,他直言国王至高的权力,表明他作诗的意图是为了传达“善良、理智和箴言”(Boileau-Despréaux,1985:66)。当讽刺诗人被视为扰乱国家秩序的人时、当讽刺诗引发争议时,布瓦洛自问:“为了适应他们特殊的口味,是否应该放弃共同的意义?”(Boileau-Despréaux,1985:121)而所谓“共同的意义”就是文学所保护的“理性、存在和人类活动之光”(Pineau, 1990: 11),是正义和崇高的寄托。布瓦洛(2010:34)对文学的坚守,不但体现在他对文学的向往和追求,更体现在他“与文学谬误和伪善作斗争”的实际经历中。在“太太学堂之争”中,布瓦洛致信莫里哀,这一兄弟般的慷慨相助事实上表明了布瓦洛保护理性和真实的坚定立场。
1714年,作为“厚今派”喉舌的“文雅的信使”(Le Mercure galant)一改攻击的口吻在《批评的必要性或巴那斯山的大普雷沃》(De la nécessité de la critique ou le grand prévost du parnasse)的诗歌中,指出布瓦洛是“以情理反对矫揉造作、故作风雅和荒唐滑稽的文学风气的捍卫者”(Miller, 1942:127)。事实正是如此,为了保护良好的文学趣味,布瓦洛与粗俗的滑稽与浮夸的矫饰之风展开斗争;为了捍卫文学的经典性和崇高性,他加入了崇古派的阵营。尽管树敌无数,他始终是基础的价值魅力的忠诚的保护者(Pineau, 1990: 336), 精神上从不迷惑,他的价值观总是清楚而可靠(Pineau, 1990: 332), 慷慨、谦虚、有信仰,热衷于情理(Hugel-Hamadouche, 2014: 218),坚守着文学这一块阵地。这就是布瓦洛“凭着一时的兴趣、坚定的立场、愤怒与热情、卑鄙与慷慨,布瓦洛充分显示出‘可人’的形象”(Descotes,1986:389)。
结 语
如果说圣伯夫对布瓦洛“其人之重要性远胜于其文”(12)的断言是正确的话,以上对布瓦洛的个性、气质和精神世界的剖析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布瓦洛而言,诗歌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他自己的文字、秉性和生命融为一体,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和其内心与行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其诗学法则是它正直诚实的人品的写照”(Hugel-Hamadouche, 2014: 169),“他对文学的正直也印证了他思想的正直”(Boileau-Despréaux, 1843: 8),其人的精神与信仰,是他与文学相连的有效保障。
布瓦洛在西方学界始终是一位影响甚巨而又争议颇多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无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讽刺诗人、不良文学风气的批判者还是论战交锋之中的“崇古派”代表,他都一直对文学寄托颇深。他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对文学满怀期许,深深地热爱着它,为了崇高而纯净的文学家园而奋战、捍卫和坚守。虽然在整个世纪都在为国王“荣誉”而讴歌的局势下,布瓦洛难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运,但他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始终作为一位集真诚、勇敢与担当于一身,有着满身正气,为国家和民族效忠的诗人。凭着他对文学的自觉,“在专制国家的王权之下,既能捍卫文人的正直,又能保障臣民对君王的忠诚”(Lecoq,2001:135),这正是布瓦洛难能可贵的地方。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真实的诗人,一个勇敢的斗士,一个对文学真正有所担当的作家。这或许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布瓦洛不容忽视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