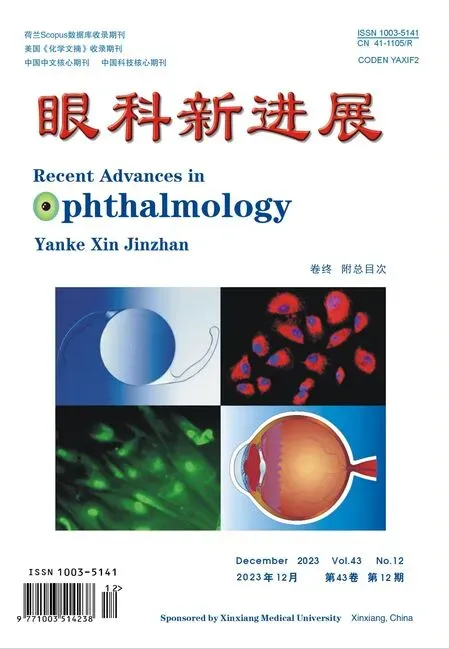小胶质细胞极化在视网膜退行性疾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张海燕 莫 亚
视网膜退行性疾病(RDD)是一类可以导致不可逆性眼盲的视网膜病变[1]。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 000万人因为该病而失明[2-3]。常见的RDD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RP)、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等。虽然这些疾病的潜在病因不同,但它们都是以感光细胞或神经节细胞丢失为共同病理特征,最终导致患者视力恶化,甚至失明[4-5]。研究发现,慢性炎症会加重RDD的病理改变[6-7]。视网膜组织中的小胶质细胞参与了这类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人们认为小胶质细胞活化是RDD发生的共同标志[8-9]。
小胶质细胞是视网膜组织中有别于神经元及其他胶质细胞的常驻免疫细胞,其本质是单核-巨噬细胞,广泛分布于视网膜中[10]。早期研究认为小胶质细胞的活化是导致RDD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11]。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小胶质细胞能够极化为M1/M2两种表型,并发挥不同的作用,精准调控小胶质细胞的极化可以减轻感光细胞和神经节细胞的死亡、控制炎症反应,从而保护患者视力[12-14]。本文对小胶质细胞极化在RDD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综述,旨在为这类疾病的治疗开辟新的途径和研究思路。
1 小胶质细胞的功能
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CNS)中固有的免疫细胞,作为CNS的第一道免疫防线,它主要发挥免疫监视、免疫防御以及修复的作用[15]。生理状态的小胶质细胞体形小且不规则,其发出的突起呈分支状,各分支间很少发生重叠。在生理状态下,这些分支活跃地进行着伸缩活动,并以一定频率与周围神经元突触接触,为大脑提供了一个高度动态和高效的监测系统,使小胶质细胞具有活跃的免疫监视功能[16]。该发现与早期定义的生理状态下小胶质细胞处于功能与活动的“静息状态”相反,具有重大意义。
当CNS发生创伤、炎症等病变时,小胶质细胞被激活,活化后的小胶质细胞胞体增大、表面分支状的突起回缩变短甚至消失,呈典型的阿米巴状,有学者将其称为反应性小胶质细胞[17-18]。反应性小胶质细胞代表巨噬细胞群,与组织损伤和神经炎症密切相关。据报道,组织发生损伤后,反应性小胶质细胞积聚在损伤部位,并吞噬受损细胞和碎片,从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19]。目前研究证实,小胶质细胞具有双重作用。在急性病变的早期阶段,小胶质细胞的活化主要发挥积极作用[20-21];但如果病理刺激持续存在,它将持续活化,并分泌炎症因子,产生毒性作用,加速神经元的死亡[22]。
从解剖和发育角度来看,视网膜是CNS的延伸,被称为“外周脑”[23]。视网膜组织中的小胶质细胞除了发挥免疫监视、免疫防御等作用外,它还可以调控视网膜发育[24-26]、调节发育性细胞凋亡、塑造神经元连接和调控原发性视网膜血管生长[27-28]。据报道,小胶质细胞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是诱导神经元凋亡的关键分子,可以促进感光细胞凋亡[29]。此外,小胶质细胞在视网膜发育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与其他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相互作用,在视网膜发育和成熟过程中修剪突触,调节突触发生[30]。如果耗竭视网膜中的小胶质细胞,可以导致突触变性,从而影响视网膜对光反应的功能[30]。这提示在视网膜发育过程中小胶质细胞功能发生缺陷会对视网膜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当发育完成后,视网膜中的小胶质细胞主要分布在外丛状层、外核层、内丛状层、神经节细胞层和神经纤维层[31];其中内、外丛状层中的小胶质细胞与突触相互作用,以维持突触结构和功能,这是视网膜对光电生理反应的基础[32-33]。
2 小胶质细胞的极化及表型
2.1 小胶质细胞M1/M2表型
小胶质细胞具有高度异质性和可塑性,它可以迅速响应周围微环境变化,反映为M1型(促炎型)和M2型(抗炎型)两种生物学效应截然相反的表型,这一过程被称为小胶质细胞的极化[34]。早期研究更多的将小胶质细胞简单地分为“静息”与“激活”两大类,认为激活的小胶质细胞会促进RDD的免疫反应以及加重炎症[3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小胶质细胞与所有巨噬细胞谱系的细胞一样,能够极化为多种表型,不能简单地分为“好”或“坏”[36]。目前研究已经证实,小胶质细胞可以被一定途径激活为功能状态和表面标志物迥异的两种表型,即M1型(经典激活型)与M2型(选择性激活型)[37]。
脂多糖、γ干扰素等促炎分子能诱导小胶质细胞极化为 M1 型。M1型小胶质细胞具有促炎特性,主要释放肿瘤坏死因子、环氧合酶2、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等促炎症细胞因子,导致炎症介质过量产生,当这些炎性介质积累到对神经元有害的水平时,它可以导致视网膜神经变性,所以M1型又被称为促炎型/神经毒性型小胶质细胞[36,38]。白细胞介素 4/10、转化生长因子 β 等抗炎递质介导小胶质细胞极化为 M2 型。M2型小胶质细胞具有抗炎特性,以抗炎细胞因子、神经营养因子分泌增加为特征,主要发挥抗炎与神经支持作用,有助于控制炎症、维持内环境稳态,促进损伤组织修复,故M2 型又称抗炎型/神经保护型小胶质细胞[38-39]。目前小胶质细胞M1/M2型分类方法更便于理解和研究,为较多学者所采用。此外,在小胶质细胞M1/M2型之外还存在其他多种表型。例如,在CNS中,与巨噬细胞类似,M2 型小胶质细胞又可细分为M2a、M2b、M2c 3种亚型,每种亚型都有各自独特的触发因子和生物学功能[40-41],而暗小胶质细胞是目前新发现的一类小胶质细胞[42]。
2.2 RDD中小胶质细胞极化表型的演变
有学者认为小胶质细胞M1/M2型只是它连续激活状态的两极,当面对体内复杂多变的微环境时,它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表现为极化表型的动态变化[43]。
RDD患者视网膜中的小胶质细胞能同时或先后表达M1和M2型标记物。在神经退行性病变初期,小胶质细胞可缓慢被激活为M2 型,修复受损组织,随着疾病持续进展,小胶质细胞会启动M1型极化相关基因的表达,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加重组织破坏[44-45]。在DR初期视网膜中小胶质细胞能同时表达M1/M2型标记物,但以M2型为主;至DR中、后期,则主要表达M1型小胶质细胞,释放促炎因子,导致视网膜神经变性[46]。与此相一致,有学者通过靶向DR视网膜中M1型小胶质细胞向M2型转变,结果促进了疾病的良性转归[47]。
小胶质细胞既可以表现为M1/M2型之间的状态,还可以相互转化。Pde6βrd1/rd1小鼠是研究RP的经典动物模型[48]。Zhou等[13]研究表明,表达CD86/CD206的小胶质细胞占比在Pde6βrd1/rd1小鼠视网膜中显著增加,而表达CD86/CD206的小胶质细胞是处于M1/M2型之间的状态[13]。此外,视网膜中小胶质细胞M1/M2型在特定条件下可互相转化,例如由脂多糖激活的M1型小胶质细胞可以被白细胞介素4诱导为M2型;反之亦然[49]。上述研究共同揭示了小胶质细胞在RDD中的复杂表型演变。因此,有学者提出以M1/M2型小胶质细胞的比率来表示小胶质细胞极化状态更为客观[39]。
3 靶向小胶质细胞极化干预RDD治疗策略的转变
近年来,以小胶质细胞极化为靶点干预RDD的治疗策略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既往研究主要是通过抑制或耗竭视网膜组织中的小胶质细胞来治疗RDD[9],由于不同表型的小胶质细胞在RDD中具有不同的作用,目前治疗策略已转变为抑制M1型小胶质细胞极化/促进M2型小胶质细胞极化,或诱导M1型转化为M2型,或增加M2型小胶质细胞数量,降低M1型小胶质细胞数量,即提高M2/M1型小胶质细胞的比率[38-39]。因此,有学者应用中药提取物和具有明确分子作用机制的现代药物对靶向小胶质细胞极化治疗RDD的策略进行了探索。
3.1 中药提取物靶向小胶质细胞极化干预RDD
积雪草酸是中药积雪草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其主要作用是抗炎、抗氧化,从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50]。Toll样受体(TLR)是人体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模式识别受体,与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结合后启动炎症信号通路[51]。Fang等[50]研究发现积雪草酸可以通过TLR4/MyD88/NF-κB p65信号通路介导小胶质细胞极化以减轻DR症状。与此相一致,李雷等[52]研究表明,氧化低密度脂蛋白会引起视网膜损伤,其机制与激活TLR4/MyD88信号通路靶向小胶质细胞极化为M1型有关。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EAU)的发病虽然不是以视网膜退行性病变为病理特征,但该模型诱导的病变部位主要位于葡萄膜和视网膜,是实验最常用的人类后葡萄膜炎模型[53]。Wang等[12]研究表明,中药淫羊藿的提取物淫羊藿苷可以促进EAU视网膜中M1型小胶质细胞向M2型极化,最终达到缓解EAU视网膜病变的目的。
3.2 其他
RP、ROP等是导致视网膜退行性病变的主要疾病,目前研究已经初步证实靶向小胶质细胞极化可以减缓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学者利用富含特异性促炎症消退介质的海洋油补充剂将小胶质细胞极化为M2型,结果改善了RP模型小鼠的视网膜病变[54]。Li等[38]通过构建早期ROP小鼠模型,发现小胶质细胞M1/M2型均参与ROP小鼠视网膜病变过程,而且随着炎症信号被激活,ROP小鼠视网膜主要表达M1型小胶质细胞,但当诱导小胶质细胞极化为M2型时炎症反应被抑制,并发挥抗炎作用。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关于小胶质细胞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首先,生理状态下“静息小胶质细胞”的观点受到挑战,生理状态下的小胶质细胞并非处于早期定义的功能与活动的“静息状态”,其可以表现出活跃的功能状态。其次,近年来,人们对于小胶质细胞的活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早期研究认为,小胶质细胞的活化是RDD发生的共同标志,新近研究表明不同刺激条件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可以极化为M1和M2两种生物学功能完全不同的表型;基于此,目前学者们提出以调控小胶质细胞极化为靶点干预治疗RDD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方式。由此,对于以小胶质细胞为靶点治疗RDD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从早期简单的抑制其活化或者完全耗竭小胶质细胞,转变为抑制M1型小胶质细胞极化/促进 M2型小胶质细胞极化。
虽然基础实验证实调控小胶质细胞极化表型可以作为治疗RDD的靶标。然而,目前对于小胶质细胞M1/M2 型极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外实验,在体内怎样实现小胶质细胞极化的精准调控,仍然需要不断探索。未来,随着对小胶质细胞极化表型精准调控机制的深入研究,相应的基础研究成果有望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