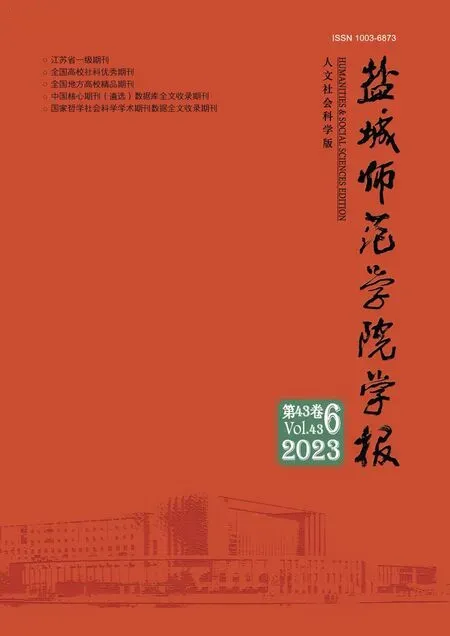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
——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马建高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1922年,当北洋政府教育部早已通令全国学校改用白话文教学,白话文刊物与新文学社团竞相涌现之际,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却办起了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文言杂志《学衡》月刊。身为哈佛大学留学生、东南大学教授,他们选择传统文化作为依归,主要是由其文化选择的理论决定的——即美国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学说。正如胡适“西乞救国术”之于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文化思想理路与之完全不同的学衡派也向西方取经,只不过取的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输入学理,再造文明”与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目的上异曲同工,都是在西方思想学说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然而因为年龄结构、求知经历、社会地位和知识背景相去不远,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往往在某一框架中运作、论争并提出西化或保守主义之主张。可以说,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论争过程中的差异处并不大于共同处,两派之间的认识,一半相同,一半不同。相同的是,双方都认为必须引进西学,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新生。差异处在于:一方面,双方引进的西学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西方思想和主义在中国之争;另一方面,一派主张把西方文化当作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另一派则主张用它来换置、创新文化的价值观。
刘禾认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译介西方学说,从翻译策略可以看到他们对西方思想的能动,而并非仅有“抵抗西方”一种模式。他们有时候受到语言能力所限,更多时候因为某种目的而极富创造性地“误译”(Intentional Mistranslation)原著,使某些西方观念产生混杂的、不中不西的新意义。“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一词,正是描述上述翻译、改写、挪用,又或其他能够产生新意义的创造过程[1]。考察这种“跨语际实践”的重点,不是从翻译技术层面讨论译文的优劣,而是要关注原著和译文之间不对等的部分,并由此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思想碰撞时的复杂思考、西方文本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产生的新意涵,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译介者的能动性(Agency)。本文通过梳理白璧德和学衡派相关理论文章,探索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过程,更准确地理解学衡派试图以西方文化思想为坐标矫正同属西方思想的实用主义的偏颇和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寻新意义和重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努力与坚持。
一、新人文主义的知识谱系与思想版图
新人文主义是一个内涵复杂、指涉多重的概念。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文学术语词典》中论述:“在上个世纪的1910--1933年间,由欧文·白璧德和保罗·埃尔默·莫尔领导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呼吁恢复以人文主义为主体的教育,恢复主要以古典文学为基础的有关道德准则、政治观念与文学标准的极其保守的思想。”[2]白璧德提出的新人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古典主义的延伸,对应着现代化造成的环境全面变迁现象,现代性以理性为主的价值观正在对古典传统进行全面清算,白璧德以“新人文主义”来建构现代性,进而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尤其是以培根(Francis Bacon)为代表的科学的人道主义(Scientific Humanitarianism)和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为代表的情感的人道主义(Sentimental Humanitarianism)传统展开清理和批判[3]。其目的,一方面是抗拒理性,另一方面则是重新诠释古典的价值。
关于白璧德的思想渊源,他的学生、历史学家张其昀有过比较系统的论述:“白璧德所津津乐道者,为希腊之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荷马与希腊悲剧诸作家,罗马之韦吉尔(Virgil 70--19B.C)与贺拉斯(Horace 65--8B.C),法国之巴斯加尔(Pascal 1623--1662)与圣伯甫(Saint·Beuve 1804--1869),德国之雷兴(Lessing 1729--1781)与哥德(Goethe 1749--1832),英国之约翰生(Johnson 1709--1784)柏克(Burke 1729--1797)与安诺德(Arnold 1822--1888),尤倾慕约翰生与圣伯甫之为人。”[4]虽然白璧德推崇许多哲学家与文学家,但大抵而言,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渊源除了远承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近宗文艺复兴人文学者约翰逊之外,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主要还是来自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评和社会学说,白璧德曾多次表示过他对阿诺德思想的推崇。白璧德强调,人若要成为一个有人性的人,就必须以“人性法则”来限制自然的自我之冲动和欲望泛滥。学衡派后起之秀,亦曾跟随梅光迪、吴宓步伐,研究白璧德思想学问,著名的古希腊文学研究者郭斌龢,简明概述白璧德理论渊源时即指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承续了古希腊罗马的精神传统与中国儒学传统思想,并将文艺复兴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坚守古希腊精神学者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知识谱系,成功地将这些古典思想文化遗产转化成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从而成为他批判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利器[5]。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主要源于对西方近代文化思想主流的痛切感受,以及对这些主流思想文化始作俑者的深恶痛绝。他既反对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对人的价值的贬低,又反对自卢梭开始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白璧德将人道主义界定为一种对普遍人性过于肯定的自信态度,这一界定侧重两个方面,一是“普遍人性”,二是“过于自信”。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开始对人自身的能力表现出某种自信,特别崇拜那些有天赋才能的人,不再相信中世纪神学所宣扬的人之谦恭和卑贱。但是这一对人性的推崇很快就变得有点过分,即把人的地位抬得过高,使人过于自信。而其与文艺复兴后期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推广人道主义最卖力的是卢梭。因为科学革命的成功已经彻底改变了中世纪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而科学家对自然界规律的探索,也大大增强了人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这种信心,后演变成现代社会的主要弊病之一。
白璧德认为人生有三性:神性、人性与兽性。神性属宗教,仅有少数人士可跻达;兽性则是卑劣,不该沉溺;唯有人性居中道,应为人类所关心。根据人类文明发展史,白璧德提出,培根的科学主义和卢梭的伤感主义乃是两种自然主义,使得人类朝征服自然、追求功利发展,同时扬弃传统规范。近代西方文明(也就是“现代性”)的败坏,世界大战的残酷、精神心灵的彷徨无依都和自然主义分不开。如何才能安置身心,获得立身行事的规范,回归秩序、保有理想的状态?这就要从传统的文化遗产中获得援引挹注,因为文化传统是一切时代的共通智慧的结合体。而要回到(到达)文化传统,人性中的克己、自制力量就很重要,因为唯有经由人类的主动努力,我们方能融汇到此一文化的传统中。此外,此一文化传统中,要留下最精粹遗产,文学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要有创造力,就要经由模仿文化传统中最精彩伟大作品,方可拔萃而出。白璧德肯定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另外由于他对佛教思想文化有相当的研究(比较宗教学),他在印度文化中发掘到一种与希腊罗马类似的文化理念。又由于与梅光迪、吴宓等中国学生接触往来,他也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发掘到相近的要素,白璧德所标举之人文理想,不设宗教,专尚人事,这与儒家思想极为近似,他认为孔子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人文主义学者的精神深相契合,甚至赞扬孔子之道优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可见他对儒家思想之钦崇。白璧德平素深以孔学没落为憾,认为儒家的人文传统乃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是谋求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6]。在白璧德的启迪下,学衡派诸子对自身的文化有了新的体悟,得到一种批判性的新认识,益发坚定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念与执着。这些体认在学衡诸子的文章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
对于文学,白璧德除了要有美学要素外,还强调要有道德含义,也就是道德与美学须臾不可分离,文学的教化作用不可忽却。因而,白璧德对卢梭浪漫主义的批判就不仅在放纵、泛滥、无所节制的思想及行事上而已,对其所呈现的文学艺术成品也大加挞伐,由卢梭自然主义延伸出来的文学上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也就无法在白璧德的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了。文学典范当然是古典的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关切的是普遍的人性,因而能展现永恒的价值,也才能成为我们模仿学习的理想典范[7]32。也因为文学被安置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基本上它就不是平民的文学,而是精英主义的精粹成果,具有永久性及普遍性。
“人文主义”一词代表着区别于自然界、以人类及其社会为核心的个人精神与自由思想,其含义随人类历史进程不断改变,特别是随着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认识的增加而变化。现代学者用人文主义一词阐述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精神世界,用它来追溯古典西方或东方文明。新人文主义强调中庸,判断价值不走极端,因此在对待文化遗产时,会采取谦恭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否定或一味肯定。对文化遗产,白璧德主张必须具有同情的态度,同时要有所选择。白璧德像阿诺德一样,认为文化由传统精华累积而成,因此不能从简单的进化论观点出发,用现在否定过去。换言之,他认为不可以用现代的各种进步,将以往的文化成就一笔勾销。这种对前人先贤的恭敬态度,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1)用“激进”或“保守”这样含义丰富的名词,比较困难,因为这些名词的意义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这里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对待文化的态度,而不是指政治上的守旧,虽然两者之间也有联系。详见马建高.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D].扬州大学,2017:39-45.。
白璧德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东西古典文化。学衡派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论为参照,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张,意即以古典主义中“理性”的批判精神对待传统,补偏救弊,突破清末以来“中体西用”的思想架构。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通过与西方以外的“他者”(the Other)的深入接触,开始质疑欧洲中心论,并重新思考西方的定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正是借鉴了古希腊罗马人文传统话语,同时经由与西方以外的“他者”的接触,发现了“东方”和中国。他挪用“东方经验”,特别是印度佛教和中国孔子思想中的伦理成分作为批判卢梭及其浪漫主义的话语资源。吴宓在向中国读者推介白璧德时认为,唯有从佛陀与耶稣的宗教教理和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文学说中,才能窥见和撷取历世积储的智慧与普通人类经验的精华[8]。
二、学衡派的“跨语际实践”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是通过学衡派的“跨语际实践”完成的。从理论上看,学衡派的文章多半是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并借此有针对性地反驳当时中国新思潮文艺创作和观念。他们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不仅维护了自己的文化、文学理念,且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引进与探索。
关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理论架构的影响,从吴宓日记可窥见一斑[9],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白璧德的尊崇及爱戴。白璧德对东方文化和孔子深感兴趣,当西方的传教士与汉学家们正将儒教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对佛和孔子的研究表明,就像对西方伟大导师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人类经验表面上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实际上仍可分为几大类。”“从佛教的结果来检验,佛教充其量只证明了基督教。若用同样的标准来检验儒教,则会发现儒教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也是一致的,而且总的来说与自希腊以来那些宣布了礼仪和标准法则的人也是一致的。若称孔子为东方的亚里士多德也显然是对的。”[7]12在白璧德看来,东西文化都不约而同地出现源远流长的传统:宗教与人文传统。前者在西方是基督教,在东方是佛教;后者在西方是古希腊的人文哲学,在东方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这种东西思想传统相互证明的思维方式,大大吸引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梅光迪、吴宓、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人,并促使他们在中国宣传与实践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吴宓等人以东南大学为根据地,借由《学衡》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传播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最佳场域。
作为白璧德的受业弟子及其学说的积极译介者,吴宓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其师学说的实质。吴宓综合中西宗教、哲学,一如其师把宇宙事物分为三界:上者为天界(Religious Level),以宗教为本,笃信天命;中者为人界(Humanistic Level),以道德为本,尤重中庸与忠恕;下者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不信天理人情,流于机械主义[10]。不同于白璧德试图用人文主义来代替宗教,吴宓认为宗教的境界最高,但他更重视道德,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境界,具有普遍性,故治世教人当以道德为主。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人性二元论”的基础上的,吴宓则在人性二元论的基础上对孔子教人修德之法作了新的阐释[11]。“克己”即以理制欲,是“实践凡百道德的第一步”[11],非只相关个人之私德,而实影响国家及后世。固举事立言,关系愈重,影响愈远者,则愈当慎之于始,不可因一时快意之故,轻于发动。即吾人做事目的虽正,而方法亦不可有瑕疵,这是针对近世急功近利的现象而言的。“复礼”之意为“就一己此时之身份地位,而为其所当为者是也”[11],换言之,即能随时随地尽自己义务,而无所缺憾。如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尊敬师长,敦睦邻里,悯恤贫弱,国有大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能克己复礼,则可去人性中本来之恶而存人性中本来之善,使人趋于完善。吴宓对“忠恕”两字的诠释为:“‘忠’者,知人类共有之优点而欲发达之于己身,纯恃克己之力。而‘恕’者,则知人类共有之弱点而能怜悯之于他人,全凭修养之功。”[11]两者相互为用,能行此道,国家才能太平富强。人文主义笃信中庸之道,认为“中庸”即知“一”与“多”之关系,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亚里士多德之学说也认为人应当不断地充实学识与经验,以随时调整自己之行事,使之适当有节制,所以吴宓认为“中庸”“实吾人立身行事,最简单、最明显、最实用、最安稳、最通达周备之规训也”[12]。吴宓坚信,孔子的这种中道的伦理观与亚里士多德、耶稣、释迦牟尼等的思想是相通的,不仅能行于中国,而且能施行于全世界。
刘伯明亦认为,执守中正的道德精神是共和政治实现的重要基础,中国改建共和仅历十年,德谟克拉西之形式已略具,然其精神却渺不可得,究其原因,正是缺乏这种道德精神,以至共和政治不能实现。“欲求真正共和之实现,必自恢复前所谓自由贡献之客观精神始,此项精神一日阙乏,则共和一日不能实现。”[13]刘伯明正是将白璧德等所倡导的道德精神观与儒家学说相结合,促使学衡派更有信心地以西学为参照系来重新认识、肯定孔子的精神与价值。
人性二元的道德理想,既是“一战”后出现的世界范围内反思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新思潮产物,也是中国古典文化“以理制欲”、追求儒学上“中庸”境界、以期成为“一多并存”的“君子儒”的精神内核。例如,儒家传统文化有一套“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注重内心的克制与外在的发挥,吴宓在提倡以“人文主义”为基点整合东西文化时,悄悄置换了其中部分内涵[14],这种“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实际就是在“一多并在”“多中有一”原理的指导下,由“多”而趋于“一”。因此,所谓“表里如一”“情智双融”“阴阳合济”亦即“执两用中”,一旦能达到“一”与“多”无碍的境地,不仅能观其全,还能观自在。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应清华学生会负责人吴文藻之邀请到清华对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作“人生观”的演讲时,力主划清科学与人生观的界限,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演讲发表后不久,即遭到丁文江的攻击从而引发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各方人马陆续加入“人生观”论战,前后历时约两年,最后论战文章结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文集作序,判科学派胜利,论战到此正式结束。学衡派成员虽未直接参与论战,然在第一时间,吴宓在《学衡》第16期(1923年4月)发表《我之人生观》,指出宇宙人生、事事物物皆有两方面,即“一”与“多”,能知两者之关系才是真知,且知“一”比“多”更为重要,更有价值。吴宓认为,凡论人事须于“一”“多”两类同时并重,如此才有内心之安定与和平。事实上,贯穿于这两者之中的是相同的理想主义精神。吴宓又说:“宇宙间事物,不可知者多,故生涯一幻象Illusion耳。”至于所信仰的理想、至理、绝对观念究竟是否存在,则“彼时既非吾之所能知,故亦不必辩定绝对观念究栖止于何处,但宜信其有,即已足矣”[12]。对社会上的思想混淆、不同主张者彼此间争论不休的情形,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标准未立之缘故,所以强调论事必须要有标准,如此不但对己可以立诚,对人也能不妄发言论,如此辩论才有意义,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五四新文化运动奏着启蒙与救亡的旋律,表现出“某种对自己民族文化、心理的追询和鞭挞”[15]。汤用彤1922年12月于《学衡》第12期发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他避开大变局时代中的中西文化思潮的众声喧哗,以及当时种种开新破旧与启蒙救亡的复杂变奏,直言:“时学之弊,曰浅,曰隘。”他引用希腊“神经衰弱症”(Greek Failure of Nerves)的季世诊断,“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16],似乎昭告了隔年开启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终究是一团漆黑与混乱,不免流于浅隘。该文是汤用彤评论当时新文化运动非常精简的文字,文中指陈当时学术的浅陋,谈论学问流于意气之争,在维新与守旧之间,“皆本诸成见”,而未能回归真理的讨论。汤用彤撰文的主旨其实在于跳出维新与守旧的简单框架,而期望于“精考事实,平情立言”的真理之讨论。此文也可以说预告即将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狭隘意气之争终将埋没真理之讨论。正当科玄论战“聚议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汤用彤在《学衡》上翻译发表E. Wallace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1923年5月、7月)、R. W. Livingston编辑的《希腊之宗教》(1923年12月)等文章。前者于《学衡》第17期首载时译者表示:“亚里士多德之书,必永为伦理及哲学之最好着手处。”[17]后者选译自该书中的第二篇,介绍西方文化的源头,可以说是《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中对研究文化真理的“探源”之论。
1936年,汤用彤在北大开始讲授“魏晋玄学”课程,当时学术界对魏晋时期哲学内容与形式还没有具体的轮廓,汤用彤以“魏晋玄学”来叙述此一时期的哲学特色,为汉魏学术思想变迁之轨迹定调,这一用法后为大多数哲学史家所采用。所谓“魏晋玄学”,广义而言,并不单就形上学或存有论而言,而是概指魏晋一代的哲学思想。“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这句话是在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首篇《读人物志》案头语中的。这句话现今看来似乎并无任何新颖独特之处,但在当时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新的一页。汤用彤梳理魏晋玄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定位“玄学”是为有别于汉代宇宙论的“玄学”:“弃物理之寻求,进而为本体之体会”的形上学[18]。这里的“玄学”或“本体论”(ontology),是相对于汉代“寓天道于物理”的宇宙论(cosmology)而言的,乃指狭义的形上学(theory of being),亦即处理普遍意义之存在(being-in-general)的“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而不是处理心理学、宇宙论、神学的“特殊形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在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我们其实看不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而上述的“弃物理之寻求,进而为本体之体会”“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流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等语、“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区分、“物理的寻求”与“本体的体会”的差别,这些可以说源于传统《老子》(以及《周易》注)诠释史中汉、魏注疏的不同,但又不得不令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中physics与metaphysics的区别。
如果进一步考察当时汤用彤授课用的魏晋玄学讲课提纲和学生的魏晋玄学听课笔记等材料,可以看到,汤用彤在授课时为了启发学生,确实有意以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作为参照的坐标:“汉学研究世界如何构成,世界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推源至太初、太始或太素,有元素焉。元素无名,实为本质。汉学为宇宙论,接近科学。汉人所谓元素,为‘有体’的,为一东西。唯在其表现之万有之后。王弼之说则为本体论。……王弼不问世界是what,or what is made of(什么,或由什么构成)。亚里士多德说种种科学皆讲‘什么’,being this or that(是这个或那个),而形上学讲being qua being(存在之为存在)。”[19]汤用彤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形上学》中physics与metaphysics的区分,从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推进了魏晋玄学的研究。
学衡派在对抗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文章,阐发对文化和文学的看法,时至今日,这些思想仍不乏借鉴之处。乐黛云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一文中,将学衡派置于世界文化的框架中。她指出,学衡派在面对新人文主义时并非简单地继承,梅光迪等人是有意识地选择新人文主义,故学衡派拥有超越新人文主义的可能性[20]。如《学衡》杂志在第3期刊载由胡先骕译述的白璧德1921年为中国留美学生作的“中西人文教育谈”讲演,借此突显其古典主义的文学立场。“惟其中缺乏自己的创造成分与具体的作品成果,因此在批判的力度上稍嫌薄弱。由于学衡派的文学主张并不系统,且未形成有个性的古典主义理论模式和规范,在与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对抗中,无法建构出体系完整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而这一文学使命,最后是在被称为‘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手中完成的。”[21]
三、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及理论意义
学衡派在批评新文化运动时所提出的观点,如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过度强调西方现代文化、赞扬引进浪漫主义文学与写实主义文学,对儒家克己复礼、中庸观念的排斥,对于文学的平民主义倾向等,处处皆有白璧德的影子。梁实秋亦曾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一文中提及白璧德对他的影响[22]。白璧德自己承认对中国所知无多,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多是通过译文或他人的诠释来展开的。他的弟子梅光迪对白璧德没能掌握中国语言深感遗憾地说:“若非如此,他就可以研究地道的中国文化,这样他也不至于被某些学者粉饰得像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埃及木乃伊;或者全凭他们自由地发挥想象,被随意地涂改。”[23]白璧德这种集中在儒家原典意义上的现代诠释的方式,显然与学衡派的思维理路相契合。五四时期存在着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和以《学衡》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两种围绕着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对立的命题。《学衡》人文话语的基石正是白璧德的人性二元论,亦即“人性既非纯善,又非纯恶,而兼具二者。故人性有善有恶,亦善亦恶,可善可恶”[12]。因此必须靠道德、理智和健全的人文传统来节制规范人性。相对于学衡派的人性观和文化观,《新青年》人道主义则偏向于强调个人天性的合理和社会文明制度的病态,他们在进化论的脉络上论证个人如何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摆脱出来,强调对西方自然科学态度的崇拜。对《新青年》群体来说,所谓人道主义,几乎等同于胡适积极向国人所推介的“易卜生主义”。
白璧德、穆尔(Paul E. More)等新人文主义者,试图以古希腊哲学、文学对抗近代以来日渐兴起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时代,他们的言说已非主流话语。至1929年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后,新人文主义在美国本土的影响更是日益缩小,唯其重视历史延续性与文化传统的态度,使他们的学说主张在保守势力始终不衰歇的中国得到过不小的反响。然而由于中美不同的现实历史走向与社会基础,吴宓等人对他们拳拳服膺的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接受与应用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吴宓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爱民的传统,主张修身与治事并举、道德与学术并进。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论核心人性二元论着实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屡次提及“人性二元为道德之基本”,然而,在道德实践方面,他却挪置了新人文主义的关键词,诸如选择、节制、规训、纪律等,朝向本土文化的纵深开掘,提出了完全符合中国语境的词语:克己复礼、行忠恕、守中庸,强调严以律己、宽以责人,继而阐释中国传统的当代意义。
学衡派将新人文主义以道德为本的标准推及文学批评上,吴芳吉在反驳胡适“八不主义”时即强调,“文以载道”的“道”虽指“孔孟之道”,但也可以是“道德之简称”。他认为:“文学自有独立之价值,不必以道德为本,此亦似是而非之言也。文以载道之意,原不限于道德,然即道德言之,又何可少?情感思想,并非神圣不易之物,不以道德维系其间,则其所表现于文学中者,皆无意识。”[24]他以园中之花来比喻文学作品,道德就像花下的泥土,游园的人虽意在赏花而非赏土,然而没有肥沃的土壤,是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来的。因此,“道德虽于文学不必昭示于外,而作品所寄,仍道德也”[24]。他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赋予“文以载道”新的意义。随着学衡派、梁实秋等人的传播,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中的古典倾向传入中国,并作用于中国现代文化及文学的建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批具有鲜明古典倾向的作家,如在文化观上反对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的学衡派、新月派作家。在人性观上,吴宓坚持“一多并存”、人性二元论的人生观,梁实秋主张普遍恒常的人性、健康与尊严的态度。在文学史观上,学衡派强调文化与文学的普遍性和永久性,认为,文化无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无中外之分,只有真伪可辨。在文学观上,吴宓、梁实秋、闻一多等人趋于古典主义,反对极端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
关于古典倾向文化观的学术史意义,一方面,古典倾向文化观促使学衡派以全世界的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吴宓认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各家各派虽面目不同,然其思想脉络、文学观点及风格形成则自有其渊源和影响,它们互相交织融合,发展中的中国新文学必须看到世界文学以往的发展过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才能避免走偏颇之途。早在1924年他就在《学衡》第28--30期分批将李查生(W. L. Richardson)和渥温(J. M. Owen)的《世界文学史》(LiteratureoftheWorld)译介到国内,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设立了一个立体的参照系。另一方面,学衡派具有新文化新文学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强调文化及文学的历史连续性与统一性。历史不是孤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浑然一体,是活生生的现实性的力量。新文化新文学阵营以捣毁传统文化经典和正统文学经典为目标,有步向民族虚无主义之境的危险。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选择时,虽表现出不同的现代化理路,但“反传统”是那个时代的最根本的特征。这种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25]的现代性思路,几乎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强势话语,引发了被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称之为“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寻找真理,对五四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反动[26]。这些关注古典文化的知识分子,试图借助西方思想来论证自己的立场,通过寻找中国与西方相同的思想以挽救民族自尊心。其中学衡派直接引进新人文主义观念并经过中国化的阐释与范式转换,来认同中国传统儒学的人文精神,正如刘禾所言,这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的主张虽与当时主流启蒙话语格格不入而难免处境尴尬,然其轨迹却不容遮蔽。自《新青年》创刊以来,新文化阵营始终在论争中证明自己,然而真正有力量的反对派一直没有出现,直到知识结构、话语模式旗鼓相当的学衡派于1920年代崭露头角,新文化阵营方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可惜来得太晚。学衡派的言论几乎是一场未实现且不对等的“参差对话”(Uneven Dialogue)。郑振铎说:“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27]尽管如此,学衡派用新人文主义的方法,将传统文化视作学习的对象,既要对之“同情”,又要加以“选择”。“同情”代表对文化传统的尊重,而“选择”则表明要取其精华,使其流传后世。学衡派在与新文化阵营的参差对话中,残存的话语与主导的、新兴的话语同时并存,彼此间相互融汇、冲撞、对话,呈现出多层次、多向度的局面,五四的精神正由于这种文化、教育、心理的多方需求,在不同趋向的各派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下缔造完成。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虽不主张盲目接受传统,但承认传统一如历史,人类应本于理性良知,加以批判抉择。尽管白璧德的学说也许陈义过高,但相较之下他提出了西方文化理性传统及其发挥制衡互动作用的独特方式。无论是白璧德还是学衡派,都同样认为“人文精神”可以作为开启“现代性”的新钥匙,但是对现代性却有着不同的想象与抱负。学衡派想要处理以及想要重建的框架在吴宓、梅光迪等人的诠释下,已然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有着区别,最终我们或许仍能说学衡派受新人文主义影响甚深,但同时也必须说学衡派不等于新人文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性”这个大框架中的一部分,它有着属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与魅力,而其真正的影响仍有赖于日后更多的研究来证明。毕竟学衡派诸君的看法,事实上牵涉中国儒家现代性尝试的一个里程碑。当然,此话题已经不是本篇论文所能容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