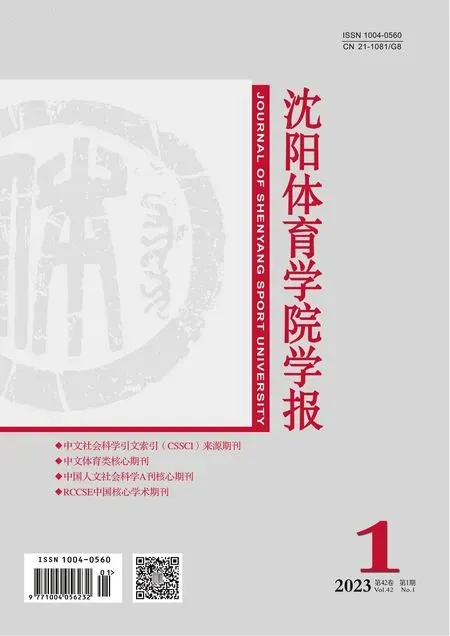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影响
刘 娜
(上海大学 体育学院,上海 200444)
敦促青少年积极从事户外体育活动,益于促进骨骼发育和功能性健康,降低超重/肥胖检出率[1-2]。 然而,近期各地方学校报告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结果显示:或因缺乏规律、适度的身体活动,超20%的12 ~18 岁青少年属于超重/肥胖人群[3]。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中强调,保证青少年在校体育活动的机会和条件[4]。 此外,教育部在相关文件中多次主张,学生在放学后要进行足量的体育运动,充分发挥家长、社区、地方政府对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作用,减轻过重课业负担[5-6]。 可见,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防控近视、避免超重/肥胖不应仅立足于在校期间,还应关注青少年非在校期间(放学后、假期、周末等)的身体活动情况。 多年来,学界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致因展开了多维、广域探讨,但此类研究多聚焦于在校期间的校园体育环境、个体心理特质等,而对非在校期间社区、家庭等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这一类问题的探究略显薄弱。 因此,考察社区、家庭等因素在改善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中的作用及联系,则成为构建青少年“家庭-社区”体育联动促进机制的必要前提和帮助青少年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环节,亦是学校、家庭、社区亟待共同解决的一项议题。
社会生态学理论认为,社区体育环境对个体身体活动具有显著的增值贡献[7]。 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包括青少年居住社区的体育设施条件、活动安全性及体育活动组织等,是社会生态健康行为模型中的远端层。 研究表明,社区体育环境因素为健康促进提供一种潜在资源,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仅次于学校和家庭,其体育娱乐设施、道路交通安全、体育氛围等益于调动青少年余暇社会活动的活跃度和参与积极性[8],并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产生促进功效[9]。 有学者认为,改善社区体育建成环境(交通设施、道路布局、体育娱乐设施等)是培养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前提,也是促进青少年课余户外活动、减少久坐时间、避免超重/肥胖、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10]。 可见,社区体育环境所营造的物质和条件保障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放学后、周末、假期等非在校期间的体育活动,是青少年保持规律身体活动、养成锻炼习惯的外部资源。 正如前人总结的:在适宜的社区体育环境中,居民(老人、儿童青少年)往往会有更多的适合自身特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中高强度身体活动)[11-12]。
另外,社会生态模型在解释青少年健康行为时发现,作为第二层级(人际层)核心元素,父母支持因素在社区体育环境与子女健康行为间具备中介效应[13]。 父母支持因素是父母鼓励子女行使自我决定权,并接受子女情绪、态度和反应的一种教养方式,既包括直接的行为示范或陪伴子女参加体育活动/游戏,还包括言语鼓励、暗示认可、倾听交流等无形的支持。 首先,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对父母支持因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一般来说,适宜的社区体育环境因素能促进父母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感知,提升父母对子女户外活动的支持水平,社区体育资源越充裕,父母越倾向于在周末或假期鼓励子女进行户外活动,以减少久坐行为[14];而且合理的社区体育资源还有助于父母身体力行地发挥榜样和示范功效,为子女行为的模仿和代际传递提供行为支持[15]。 正如情绪记忆系统理论所言:社会环境(社区体育环境)引发的愉悦、安全感等情绪感受会成为认知符号,指导并决定认知决策(父母支持)[16]。 其次,父母支持因素有助于激发子女参与体育锻炼的自主动机和决策能力,使青少年余暇时间的身体活动更主动、活跃。 有学者认为,父母支持因素诠释了亲代对子代的爱与理解,它能为子女创造一个独立成长、自由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激发子女锻炼自主意识和坚持性,使锻炼行为更规律、持久[17]。 那么,在放学后、假期、周末等非在校期间,社区体育环境因素能否通过提升父母支持因素而间接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尚需在实证中获得检验。
受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综合影响,青少年对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的感知及其行为方式往往会呈现性别差异,而且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的社会感知、人际关系敏感性等心理特质及其锻炼行为亦往往呈现学段差异[18]。 那么,对于青少年,在非在校期间,社区体育环境、父母支持及青少年身体活动是否也具有性别或学段差异? 基于此,构建研究假设模型(图1),从探查社区体育环境、父母支持和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在性别、学段方面的差异入手,探讨三者内在影响机制。 本文旨在厘清社区、家庭等因素在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中的定位和功效,亦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图1 研究假设模型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遵循分层整群抽样原则,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各抽取一个省份(吉林省、河北省、江苏省、河南省),在各省份按省会城市、一般城市、城镇乡村各选取1 所初中、1 所高中,每所初中、高中的各年级抽取2 个自然班级为调查单位。 调查共收集1 311 份问卷,遵循“反向题检验”“规则性填答”“应答率低于75%”等筛查原则,保留1 114 份问卷,再剔除5 份基本信息(性别、年级)缺失的问卷,共保留1 109 份有效数据,有效回收率为84.59%。 其中,年龄(14.98 ±1.640)岁;男579 人,女530 人;初中生563 人,高中生546 人。 经G-power 检测,本次测查所保留的分析样本满足问卷调查推荐样本量标准。另外,于2020年11月1日和11月10日对174 名被试者进行间隔10 天重测,最终配对样本量为159 份。
1.2 测量工具
1.2.1 社区体育环境量表(Community Sports Environment Scale)采用李佳薇等《青少年身体活动促进因素量表》中的《社区环境分量表》[19]。 共11 题,如“我们社区的公共体育健身器材或路径很适合我”。 各题项采用Likert 5 点法,从“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5)”,以总分评估被试感知到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的优劣情况。 本次测量得知:K-S非参数检验达显著水平(P(df=1109)<0.05);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累积贡献率66.448%,11 个题项全部进入预设,KMO=0.936,Bartlett 球形检验达显著水平(Chi-Square=10 469.567,df=55,P<0.001);验证性因子分析中,χ2/df(44)=3.372,GFI=0.918,NFI=0.967, IFI=0.971, NNFI=0.938, CFI=0.971,SRMR=0.042 9,RMSEA=0.067;量表Cronbach’s α=0.948,分半信度=0.919;间隔10 天重测稳定性系数为0.644(P<0.01,Spearman 秩相关性分析)。
1.2.2 父母支持量表(Parental Support Scale)采用Zimet 等《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家庭支持分量表》[20]。 量表共4 题,考虑到研究旨在评估被试在放学或休假期间(休息日、假期)感知到父母对其身体活动或体育锻炼活动的支持程度,故设定情境,并将题项中的“家人”改为“父母”,如“在放学后,或休假期间(休息日、假期),父母在身体活动或体育锻炼方面能够真正地支持我”。 各题项采用Likert 5点法,从“没未有过(1)”到“总是如此(5)”,以总分评估青少年感知到父母对其非在校期间从事身体活动的支持水平。 本次测量得知:K-S 非参数检验达显著水平(P(df=1109)<0.05);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累积贡献率72.059%,4 个题项全部进入预设,KMO=0.905,Bartlett 球形检验达显著水平(Chi-Square=2 220.283,df=6,P<0.001);验证性因子分析中,χ2/df(2)=2.608,GFI=0.973,NFI=0.973,IFI=0.974,NNFI=0.923,CFI=0.974,SRMR=0.030 1,RMSEA=0.061;量表Cronbach’s α=0.866,分半信度=0.834;间隔10 天重测稳定性系数为0.501(P<0.01,Spearman 秩相关性分析)。
1.2.3 国际身体活动量表-短表(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Short Form)采用Meeus等《国际身体活动量表-短表》[21]。 量表共7 题,选择前6 个题项询问被试不同强度的身体活动情况。考虑到研究旨在测评被试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且施测的过去7 天内无节假日,休息日可能参加课外辅导课程等,因此,本研究将放学后或休假期间统一表述为“非在校期间”。 设定情境为“最近7 天内的非在校期间”,如“最近7 天内的非在校期间,例如放学后或休假期间(休息日、假期),你有几天做了剧烈的身体活动,如提重物、大强度的有氧运动、快速骑车、激烈的体育活动等”。 量表旨在考察被试非在校期间各强度活动的周频率和每天累计时间,并赋以MET 值来核算,其中,高强度活动赋值8.0,中等强度活动赋值4.0,步行MET 赋值为3.3。 对数据进行清理、截断、异常值剔除及身体活动水平分组等,并以身体活动的等级分组(低、中、高)来评估被试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情况。 本次测量得知:K-S非参数检验达显著水平(P(df=1109)<0.05);间隔10天重测稳定性系数为0.583(P<0.01,Kappa 一致性检验)。
1.3 施测
施测前,统一对数据采集负责人进行规范化培训。 采用纸笔法,于2020年10月15日—28日,对各抽样单位进行问卷发放与回收工作。 施测时,以被试知情并同意参与调查为前提,保证班主任始终在场,由发收问卷的负责人口头宣读指导语、告知被试调查用途,并强调调查的匿名性、保密性、自愿性以及数据保存的方式。 问卷在填答10 min 后当场收回。 施测过程中还需获取被试年级、年龄、性别、所在城市等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有效数据导入SPSS 26.0 分析软件。 经相关潜变量计算处理等,利用K-S 非参数检验、探索性及验证性因子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重测信度检验等,考察数据的正态分布情况,以及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考察诸变量的性别和学段差异。 采用Spearman 秩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Bootstrap 法的Process(3.5 版)插件等,考察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利用Process 插件分析变量的间接效应时,具体设定如下:设定模型类型为4;X=社区体育环境,M=父母支持,Y=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Bootstrap Samples=5 000;取样方法为Bias Corrected,置信区间设为95%,分组条件为均值±1 个标准差(M±1SD)。 利用AMOS 分析软件,从直观、结构层面揭示诸变量的内在联系。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数据源于被试自陈式问卷调查,因此采用程序控制法和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考察施测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 1)程序控制法:指导语着重强调“调查只为科学研究使用”,反复强调施测的匿名性、自愿性、保密性,问卷现场填答完成后当场回收。2)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排除基本信息,对所有题项进行单因素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3个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第1 因子变异率为35.862%(未达到临界值40%),证实本研究施测的共同方法偏差可接受。
2.2 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与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群体差异分析
性别和学段的Mann-Whitney U 检验(表1 和表2)显示:1)对于青少年,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的性别差异皆不显著(P>0.05),而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性别差异显著(P<0.01),均值比较发现,男生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状况(1.94 ±0.854)优于女生(1.63 ±0.810),经测算,效应量为0.182;2)对于青少年,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的学段差异皆显著(P<0.01),效应量分别为0.185 和0.118,而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学段差异不显著(P>0.05),均值比较发现,初中生社区体育环境因素(44.29 ±9.967)及其父母支持因素(17.42 ±6.208)的水平皆显著高于高中生。

表1 性别的Mann-Whitney U 检验Table 1 Mann-Whitney U test of gender

表2 学段的Mann-Whitney U 检验Table 2 Mann-Whitney U test of learning phase
2.3 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影响效应分析
Spearman 相关系数统计结果(表3)表明:社区体育环境因素与父母支持因素(r=0.506)、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r=0.344)皆显著正相关(P<0.01),父母支持因素与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显著正相关(r=0.275,P<0.01)。
分别以性别、学段、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为自变量,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为因变量,采用强行进入法进行4 组回归分析(表4):性别(F(1,1107)=38.070,β=-0.182,P<0.001)、社区体育环境因素(F(1,1107)=136.461,β=0.331,P<0.001)、父母支持因素(F(1,1107)=84.314,β=0.266,P<0.001)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影响皆显著,并且分别解释了3.2%、10.9%、7.0%的变异,而学段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影响不显著(P>0.05)。

表3 Spearman 相关系数统计Table 3 Statistics of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4 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分别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回归分析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community sports environment and parental support on adolescents’ non-school period physical activities,individually
利用Bootstrap 法进一步考察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间接影响(表5)。 1) 方程1:学段(β=-0.650,95% CI=[-1.032,-0.268])、社区体育环境因素(β=0.151,95%CI=[0.133,0.168])对父母支持因素的影响皆显著(F(5,1103)=63.473,R2=0.223,P<0.001),但性别对父母支持因素的影响皆不显著(P>0.05)。 2)方程2:性别(β=-0.297,95%CI=[-0.389,-0.205])、社区体育环境因素(β=0.023,95% CI=[0.018,0.028])、父母支持因素(β=0.036,95%CI=[0.021,0.052])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影响皆显著(F(8,1100)=26.650,R2=0.162,P<0.001),但学段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影响皆不显著(P>0.05)。

表5 间接影响效应检验Table 5 Test of indirect effect
综上所述,在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影响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时,父母支持因素具备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效果量的计算公式:,其中,为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为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总体回归效应的变异率,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22]。 测算得知,中介效应量为0.250,即父母支持因素的中介效应量为25.0%。 基于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旨在从直观层面揭示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综合影响(图2)。

图2 中介效应模型Figure 2 Model of mediation effect
3 讨论
3.1 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与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群体差异
性别的Mann-Whitney U 检验证实:对于青少年,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的性别差异皆不显著,但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性别差异显著,其中,男生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状况优于女生。 1)众所周知,社区体育环境的建设与完善旨在丰富社区居民余暇活动、提升生活质量,其交通设施、道路布局、体育娱乐设施、社区体育组织等通常具有大众化、普适性特征[23],这亦使不同性别青少年报告相似水平的社区体育环境状况。 2)父母支持诠释了亲代对子代身体、心理、行为、情感等无性别偏见的爱与关怀,出于对子女全面健康、丰富业余生活、避免久坐或屏前时间增多等问题的考虑,父母通常会支持子女在非在校期间从事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也希望子女能利用闲暇时间加强体育锻炼[24],因此,不同性别青少年皆会感知到相似程度的父母支持因素。 3)此外,受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表达等往往存在性别差异,加之男生通常具有相对外向、活跃、好动的人格特质,因此,与在校期间类似,男生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往往比女生更积极、活跃,活动量也会相对较大。 正如特质论和现代人格心理学阐释的:人格特质具有指挥行为的能力,而人们所选择或表现的行为往往直接源于人格特质[25-26]。
学段的Mann-Whitney U 证实:对于青少年,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的学段差异皆显著,而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学段差异不显著,其中初中生报告的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及其父母支持因素的水平皆高于高中生。 1)本研究获取的社区体育环境因素数据,源于青少年对居住社区的体育娱乐设施、氛围、安全性等方面的感知与评估。 相较而言,处于环境感知萌芽期的初中生更关注体育活动的参与机会和时间保证,而对健身条件、建成环境等诉求相对较低,而高中生具有较高的自我意识,对自然环境和运动条件具有较高的诉求[27],亦相应提升了对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的评判标准。 因此,高中生对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的满意度和评估水平往往低于初中生。 2)初中生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和学习压力相对较小。 为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生活习惯、避免久坐少动、降低手机/电脑依赖性、培养活泼开朗性格,父母倾向于鼓励子女从事户外体育活动以度过闲暇;而囿于传统应试教育,高中生普遍存在较重的学业、升学压力,父母倾向于子女能够有更多机会和时间巩固学业知识,对子女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支持水平相对降低。 3)值得一提的是,与在校期间不同,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具有学段一致性特征[28]。 究其原因:不同学段青少年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量普遍较低,其居家身体活动、社区体育活动等皆处于非活跃状态[29];另外,在我国网民群体中,10 ~19 岁青少年占37.8%[30],这亦折射出屏前、静态行为已成为青少年非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形式,相应地,初中生和高中生往往表现出类似的身体活动特征。
3.2 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证实了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分别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利用Bootstrap法证实了在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影响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时,父母支持因素具备显著的中介效应。
首先,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正向影响显著(β=0.331),解释了10.9%的变异。 根据行为地理学和空间感知理论,外界环境因素会对主体行为产生作用,而主体从行为环境因素中获取的信息和映像能成为行为的决策依据,并影响主体行为[31-32]。 既有研究表明,社区体育环境因素是青少年开展社区体育的主要场所,也是促进青少年余暇体育参与的条件基础[33]。 本文聚焦于青少年放学后、休息/节假日等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证实了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具有重要的增益贡献。 一方面,充足、多样的社区体育娱乐设施可为青少年非在校期间从事身体活动提供物质保障,它有助于提升青少年户外身体活动、社区体育活动的可入性水平,这种工具性的支持元素是个体保持健康活动的外部助力。 另一方面,安全、适宜的道路布局和交通设施有助于降低青少年从事体育活动的难度和风险,提升美学性和正性体验,激发体育参与热情和自主能动性,使青少年在余暇时间(或非在校期间)里能积极主动地到社区从事身体活动,正如流畅理论所言:个体的认知和体验会成为认知线索而决定后续行为[34]。 此外,良好的社区体育氛围和组织管理有助于充实青少年的余暇生活,激发青少年非在校期间的运动意向,使青少年在闲暇时间里更倾向于到户外活动,避免久坐少动、手机成瘾,正如社会调适理论揭示的:人际氛围能够影响主体的健康行为[35]。
其次,父母支持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正向影响显著(β=0.266),解释了7.0%的变异。 换言之,与余暇体育锻炼、校园体育活动、在校身体活动类似,父母支持因素能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产生促进作用。 根据生态学模型理论和依恋理论相关观点:青少年的社会化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因素,尤其在童年或青少年初期,子女对父母的依恋、顺从会扩大父母支持因素的影响力,决定青少年认知与行为的发展[36-37]。 从数据结果来看:作为一种教养方式,父母支持因素诠释了合理的亲子沟通模式,它能激发子女体育活动的决策能力和投入状态,有助于青少年在非在校时期主动且充满活力地投入体育活动,形成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模式。 作为一种关爱传达,父母支持因素能保护子女应激情境下的情绪情感,有助于激发青少年的挑战欲和自主意识,并在居家情境下保持应有的活力和热情,避免惫懒状态,促进健康行为。 此外,父母的示范、陪伴等直接性支持因素还有助于增进家庭亲密度,提升家庭体育氛围,使非在校期间的青少年仍能保持积极、频繁的身体活动。 正如社会支持理论所言:重要人际的支持是缓解压力、调节情绪、促进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资源[38]。
最后,在社区体育环境因素影响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时,父母支持因素具备中介效应,其效应量为25.0%。 社区体育环境因素涵盖了青少年居住社区的体育设施、道路交通安全性及体育活动组织等。 1)充足、多样的体育设施条件可丰富居民体育休闲的选择,使父母身体力行的示范或陪伴子女从事户外活动成为可能,这种直接性的支持因素能为青少年提供模仿依据、参照模式,形成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39]。 2)交通、道路等设施安全性有助于提升父母对社区环境的可入性和安全感知,使父母愿意让子女从事安全的体育活动,避免久坐少动,进而使非在校期间的青少年能在父母的鼓励和认可(隐性支持)下形成积极的身体活动。 3)积极的社区体育氛围、频繁的社区体育活动有助于增进邻里互动与交流,提升父母对子女从事社区体育活动的支持度,从而促进青少年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水平。
4 结语
本文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实证研究,从诸变量的性别和学段差异入手,探讨了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对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综合影响。 结论:对于青少年,男生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状况好于女生,初中生社区体育环境满意度和父母支持水平皆高于高中生;在非在校期间,社区体育环境因素、父母支持因素是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的激励因素;社区体育环境因素既可以直接促进青少年在非在校期间积极从事身体活动,还可以通过提升父母支持因素而间接促进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
本文所得结论可为丰富青少年非在校期间的身体活动研究提供参考,但尚存些许不足之处:对诸变量的性别、学段差异分析发现,尽管身体活动的性别差异,以及社会体育环境、父母支持的学段差异皆达显著水平,但差异效果量较小,因此对此结论论断还需审慎;作为自陈式问卷调查,青少年非在校期间身体活动的自我评估可能受霍桑效应影响,在客观性评价方面或存不足;此外,本研究仅将青少年未在校的时期统一归纳为“非在校期间”,而未细化“放学后”“休息日”“节假日”各时段,或导致研究深度受限。 未来应采用加速度器等客观评定工具,并细化青少年不同时段的身体活动测评,使结论更具稳定性和可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