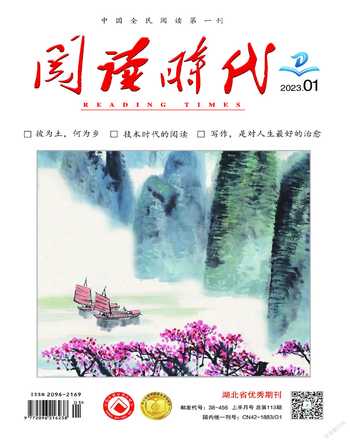为什么要阅读
〔法〕安妮·埃尔诺
几年前,我十几岁时就失去了联系的一位表弟来看望我住在镇上医院里的母亲,他借此机会顺道拜访了我的房子。在客厅入口处,他停了下来,目瞪口呆,眼睛盯着完全盖住后墙的书架。
“你都读完了吗?”他难以置信地问我,几乎吓坏了。
“是的”,我说,“差不多。”
他默默地摇了摇头,仿佛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努力的壮举。至于他,他14岁就离开学校,尽可能地工作。他的家人没有书,我只记得他看漫画书《泰山》的场景。
尽管越来越多的书进入了客厅,但从那以后,进入客厅的人没有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读过客厅中的大部分书,最重要的是,被书包围是我的天性。我甚至想知道,访问者、记者、评论家或学生是否一定认为,作为一名作家,我应该拥有更多的书。
我忐忑不安地回忆起无法掩盖的暴力
我经常会不安地回想起和表弟之间对话的场景。这幅场景下掩盖着另一残忍的场景。我那时15到18岁之间,责备父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他只看当地报纸《巴黎-诺曼底》。对于独生女的傲慢,他通常是平静和安抚,他严肃地回答道:“书对你来说很有益处,但对我来说,我不需要靠它们活着。”
这些话跨越时间,让我牢记在心,像一种痛苦和无法忍受的现实。我很明白我父亲的意思。我父亲对我抱有希望,他隐约知道书籍是很重要。它们构成了一个意义——“文化包袱”,用更世俗的一句话来说——也包括剧院、歌剧和冬季运动——一个优越的社交世界。
我明白这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我拒绝认为书籍的世界会永远对我最亲爱的人关闭。这些话表示并认可了他和我之间无法言说的分离。我继续我的学业,而父亲对此似乎只是一贯的置之不理。他只是在伤害我,就像我伤害他一样。阅读,在他和我之间,是一种相互的伤害。
当我唤起阅读的理由时,父亲的话不断地回到我的脑海,就像一个无法克服的个人矛盾。不,读书不是生活,但我一直与书一起生活。我惊奇地发现,阅读对我的意义和对他人微不足道甚至完全缺失之间的鸿沟。我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读书的人的位置上,即使在我生命中哀悼的黑暗时期。
自从我6岁学会阅读以来,我就被书中的文字所吸引。从字典到绿色图书馆(绿色图书馆是法国阿歇特出版社于1923年创作的儿童图书收藏,其特点是绿色封面,在 1955年到1980年之间达到了顶峰),我母亲也喜欢阅读,她经常给我推荐这些书。
那时书很贵,书从来没有够我用。我梦想在一家书店工作,我就可以拥有数百本书阅读。阅读的乐趣是不言而喻的,还有游戏的乐趣。书在我的游戏世界中发挥了作用,我常把自己想象成为书中的角色。我把自己想象成简·爱、奥利弗·特维斯、大卫·科波菲尔等等。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的话让我极度反感和痛苦,因为彼时阅读已为我开启了在广为接受的叙事之外新的可能,而那些被人们认同的所谓正确的叙事就存在于我所在的修道院学校,存在于我所在的工人阶级环境所认同的信念和对已有秩序的维护中。我困惑地寻找着,想知道是否有哪一本书推动了我,或者为我提供了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因为被禁止而变得更加令人向往:《无神论者》、《反抗者》等书的思想魔力,还有《绝对的探索》(巴尔扎克)、《通往自由的道路》(萨特)、《存在的困难》(让·科克托)等对生命的理解。
我在当代小说中寻找并发现了将我投射到未来的生活方式。因为在我存在的那一刻,阅读扮演着生命的预告片的角色(也许它一直存在,直到生命的晚期,就像与死亡的斗争一样)。

我在日记中写下引文,这感觉如同发掘有关自我的真相:至少有两个人分享的喜悦对生活困难的感觉。事后看来,我认为抄写句子好像是对我存在的肯定,沉浸在阅读中,每添加一个引文,都是对我父亲的话的抗议。如摘自《罪与罚》:“他以前曾有过无数次准备为了一个理想,一个希望,甚至为一个幻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在那个阶段,除了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外,我怎么能进入一个罪犯的内心世界呢?
在不知不觉中,我处于阅读所代表的矛盾的核心:它把我与人民、人民的语言分隔开来。阅读通过我认同的角色和我经验之外的其他世界将我与其他思想联系起来。
阅读分离并连接。阅读既是一种具体的分离:阅读意味着与所有语言交流的中断,与周围环境的分离。阅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分离:阅读就是被传送到一个新的宇宙,纯粹的想象。阅读就是暂时与自己分离,让一个虚构的存在,作家的“我”完全占据我们的内心空间,带我们走向他们的命运,激起我们的情感。接受一个声音可以闯入我们的意识并取代我们自己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早点睡觉。”也是接受被打扰、动摇并最终转化。
阅读让我们更接近他人,让我们置身于罪犯拉斯科尔尼科夫、阶级叛逃者马丁·伊登的头脑中,置身于达洛维夫人穿过伦敦的思绪之中。阅读开启了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敏感性。
同样,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模范童年》也让我明白了纳粹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是如何建立并繁荣起来的。阅读可以提高理解世界的能力,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法语中,lire(阅读)和lier(连接)包含相同的字母。
阅读是为了回归自我阅读是为了阅读自己
我意识到阅读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所有知识的源泉。像其他人一样,我不再查字典,而是上网。我在电视上看关于社会冲突和问题,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和纪录片。就像一本书一样,我从中获得了知识和逃避现实、快乐、情感。
但是为什么书是无可替代的呢?
首先,是因为书的易用性、可塑性。你可以翻阅一遍,从头开始阅读,也可以匆匆读完,或者放慢速度,停下来,抬起头思考一个句子,或者暂停几个星期,然后再继续。阅读不限定时间的长度,是最自由的文化行為。
其次,阅读一本书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通常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精确地进入。
最后,阅读无形地融入整个人的全部体验,所有的感官都被想象所调动。难以捉摸的是这本书的声音——在将小说改编成银幕时所缺少的——一种声音,其语气、色彩、温柔或暴力仍然存在于记忆中。
我在电影院看到的最令人不安的场景之一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华氏451度》电影中的最后一幕。鉴于所有书籍都被禁止和焚烧,躲在树林里的男人和女人来来去去,每个人都通过大声重复来记住一本书。
许多年前,在我的个人日记中,我写道:绝望,正如我所遇到的,是相信没有一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我所经历的。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弥撒后带我去了公共图书馆,它位于市政厅,只在周日上午开放。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公共图书馆,里面庄严而冷清。柜台后面一个人向我们询问想要的书名,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这个人为我选了梅里美的《哥伦布》,为我父亲选了莫泊桑的《哈森夫人的玫瑰王》。这是我看到他在餐桌上读的唯一一本书。
我大约20岁时开始写作。我把一本小说的手稿寄给了一位编辑,但编辑拒绝了。被拒绝了。我妈妈很失望,我爸爸没有,几乎松了一口气。他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的五年前就去世了。我想知道我写作的最终目标或驱动力,是否是让那些通常不阅读的人而阅读。
(源自“新阅读之全民阅读”头条号,有删节)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