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山判牍:晚清诗人笔端的法理与人情
文/宋伟哲
提起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往往五味杂陈。当时的清政府,从上到下腐朽无能,难觅“循吏”之踪影。不过,若以法律和文学而论,晚清名士樊增祥不可忽略。论文才,他派承晚唐,长于艳体,诗坛举足轻重;论吏能,他深明情理,善批判牍,备受法界推崇。在漫长的诗人与宦海生涯中,樊增祥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经典判牍,其所蕴含的法理与人情,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所在。
女装苦读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樊增祥的父亲名叫樊燮,官居湖南永州镇总兵。恩施县城内有条梓潼街,樊家宅第就坐落于此。院内有座读书楼,便是樊增祥与兄长樊增裪自幼读书的地方。鄂西群山小县中出了一位高级将领,樊家在当地自然名震一方。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身为将门虎子,樊家这对兄弟却天天穿着女装,整日在楼上苦读。在当时那个风气保守的年代,这番举动无疑是一种奇耻大辱,樊家人何苦如此呢?这一切,都要从樊燮与左宗棠的恩怨说起。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战火很快便从广西烧到了湖南境内。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力邀左宗棠入幕,帮助自己处理军政要务。后来的左宗棠名满天下,妇孺皆知,是晚清中兴名臣。可是在这个时期,他只是湖南巡抚帐下的一名师爷而已,并非朝廷命官。何以如此呢?原来左宗棠虽然聪颖过人,年纪轻轻便考取举人,可是在此后的科举道路上,他却屡试不第,未能考取进士,毕生引以为憾。左宗棠闭门苦读,钻研经国济世之道,名气也越来越大。直到湖南战局危机,他才在友人的多方劝说下,出山辅佐湖南巡抚。骆秉章凡事都要先询问左师爷的意见,对他言听计从。当时湖南军政,大抵由左宗棠一手擘画。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湖南官场的大小官员,更是无人不知左师爷威名,见了他也都毕恭毕敬,丝毫不敢怠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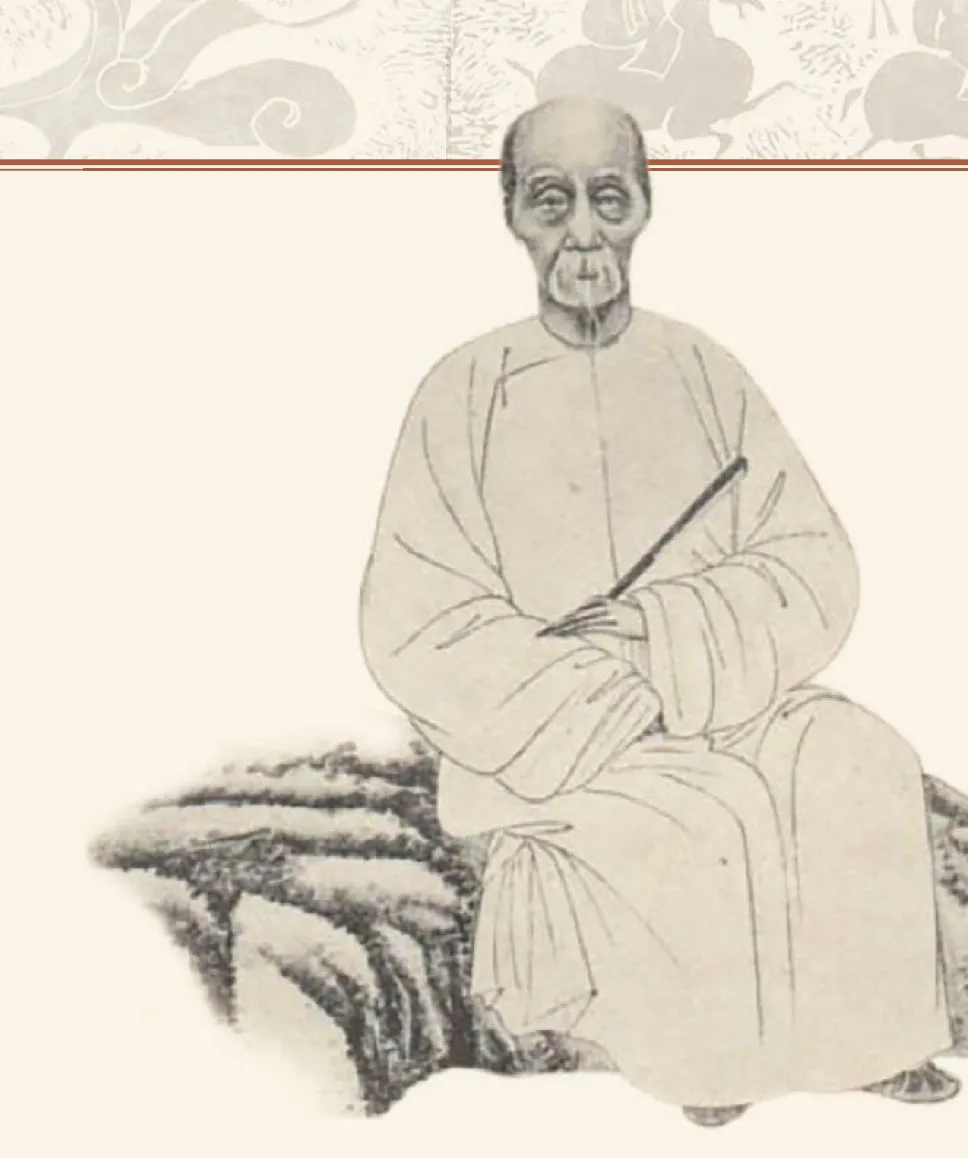
樊增祥
左宗棠性格孤傲,脾气火爆,再加上深受巡抚信任,手握重权,丝毫不把旁人放在眼里。春风得意的同时,自然也得罪了一大批人。一般人不敢与左宗棠计较,可是当他遇到永州总兵樊燮时,却惹来了杀身之祸。某日,樊燮赴长沙拜谒巡抚骆秉章,事毕便前往拜会大名鼎鼎的左师爷。樊燮拜见巡抚时,曾向骆秉章请安,而见左宗棠时,却并未行礼。毕竟樊燮身为总兵,是二品大员,左宗棠名气再大,终究只是一介布衣,双方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就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细节,却惹恼了权势熏天的左宗棠。他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樊燮怒声反驳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怒不可遏,抬脚就要踢樊燮,并大声辱骂道:“王八蛋,滚出去!”樊燮羞愤难堪,最终还是退了出去,双方就此结怨。不久,左宗棠借骆秉章之笔弹劾樊燮违法乱纪,樊燮也在湖广总督官文支持下,上表弹劾左宗棠为“劣幕”。此案因琐事引燃,背后当然也掺杂着当时湖广官场复杂的政治斗争,结局却是两败俱伤。咸丰帝览奏之后,樊燮被罢官免职,左宗棠也没捞到好果子。咸丰帝命令湖广总督官文严查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一消息对湖南官场可谓重磅炸弹,连曾国藩都在家书中感叹道,“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万幸在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大力营救下,左宗棠最终逃过一劫,并且很快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建功立业,成为晚清中兴名臣。
樊燮则没那么走运,他罢官之后便无缘东山再起,灰溜溜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恩施老家。他在梓潼街治屋居住,并特意盖了一座读书楼。书楼竣工那天,樊燮立下重誓,宴请父老见证,他说道,“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为激励后代雪耻,樊燮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做了一块写着“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的耻辱牌,置于祖宗牌位下方,朔望率二子礼拜。更震撼的是,樊燮要求两个儿子从此以后只许着女装,不准穿男服。他说:“考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汝等总要高过左宗棠。”在樊燮的激励下,两个儿子每日奋发苦读。长子樊增裪遗憾早逝,次子樊增祥则实现了父亲的愿望,先后考中秀才、举人,脱去了女儿衣装。光绪三年(1877),樊增祥终于高中进士,得以焚烧辱牌,为父亲雪耻,成就了一段求学佳话。
法官树鹄
樊增祥步入仕途后,被派往陕西渭南任知县,后逐渐成长为省级官员,担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樊增祥少年勤学,诗文功夫了得,一生留下数万首诗作,是晚清时期中晚唐诗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文学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之一,深受张之洞、李慈铭等名士器重。晚清吏治腐败,大小官员们整日吟诗作乐、歌舞宴饮,对卷牍案件漠不关心,导致政务荒芜,民冤难申。然而高产诗人樊增祥并没有因诗歌而耽误理政,反而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批阅案牍之中。即便后来升任省级高官,依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樊增祥文笔极佳,又精通情法律理,经他批阅的判牍,可谓对情理法的优秀诠释,能使官民信服。往往一经下发,“吏民传写殆遍”,甚至连省府的官报都以其判牍为资料。樊增祥平素留心保存这些案牍,友人又不断劝说他应当出版发行供学者参考。于是经他本人修订整理,这些卷帙浩繁的资料有幸出版,世称《樊山判牍》。
《樊山判牍》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广受好评。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遵循旧律而成的《樊山判牍》仍然供不应求,被认为是“审判必须”之书。民国四年(1915),法政学社再印此书,于序言中称赞道,“引经断狱,案无留牍,往往与文明法律互相发明……际司法独立改良裁判之时,法学人才亟待养成,倘能循兹途辙,实地研究,则谓此编为法官树之鹄焉可也。”(鹄,此处音“gǔ”,靶心之意,可以理解为榜样)这也不难理解,法律规范的形式虽有转向,但使用法律之官民却仍旧如故,传统法律文化理念依然在中国人心中代代相传。从这个角度审视《樊山判牍》,其价值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情理的作用不可忽视。法律规范不足时,情理可以补充法律。法律与情理冲突时,情理甚至可以替代法律。官员如果善于运用情理,而不是机械执法,则司法判决往往能够大快人心,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樊增祥处理韩城县关翠儿被杀一案颇为引人深思。韩城县四十九岁妇女孙氏夫故无子,与九岁女儿关翠儿相依为命。由于家中缺少男丁,孙氏便托媒人刘之安,招二十五岁的王心宽做上门女婿。不料王心宽人面兽心,进门刚四十天,就在某日夜里企图强奸丈母娘孙氏。孙氏哭骂不从,王心宽便用剃刀将其刺伤。翠儿哭喊,竟遭王心宽刺死。邻居们听到哭喊呼救声,立马赶到现场,王心宽便畏罪自杀了。面对这样一起悲剧案件,韩城知县丁锡奎依律作出裁决如下,“王心宽罪有应得,以死免议。房主邻人救阻不及,亦无庸议。剃刀库存,尸棺饬埋。”依法律而论,丁县令的裁判无可指摘,樊增祥也称赞“结得容易,办得干净”。
不过在樊增祥看来,这样的判决还称不上完美,导致这场悲剧的罪犯除了王心宽,还另有两人。其一是孙氏,她糊涂谬妄,引贼入门,只是已经受伤,姑且免去责罚。尽管如此,樊增祥还是表达了对孙氏的极度同情,叹息她既丧失幼女,又累及诉讼,还负担了大笔费用,可谓“不平极矣!”他试图运用情理为孙氏做点什么。樊增祥发现卷宗中提到了王心宽的叔叔王太和、舅舅史清善曾被司法机关传讯到案,却未透露王心宽父母的家产信息。于是他一方面下令详查凶手家庭信息,王心宽如有家产,应赔偿一半给孙氏;另一方面,樊增祥指出王心宽叔、舅的过失,对于自己晚辈娶九岁女子为妻,“为尊长者不能训阻,咎亦难辞”,让他们各出钱十串,赔偿给孙氏。除此之外,樊增祥认为最不可饶恕者,就是媒人刘之安。他愤然批道,“一男一女相差十六岁,欲求配合,至早须得五六年,乃竟罔为撮合,致酿此等淫凶冤酷之案。非将刘之安重责枷号,何以服人?”同时还判决刘之安出钱二十串赔付给孙氏。在批文的最后,樊增祥特别强调州府官员要迅速将此公文转至韩城县办理,并且要将办结情形“详悉复禀,勿延”。在《樊山判牍》中,情理与法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它是一座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宝库,值得不断挖掘和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