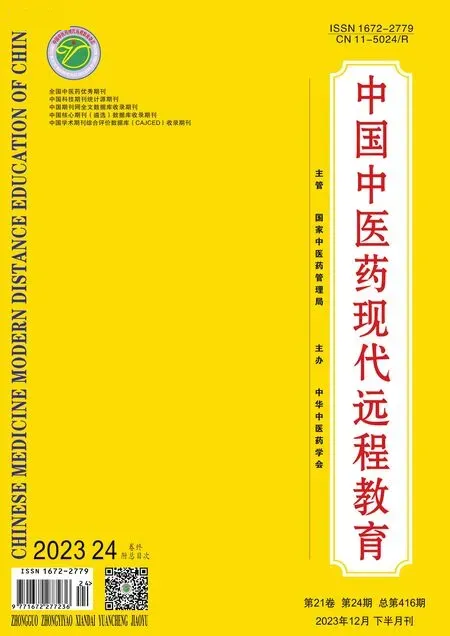升陷汤方证的临床应用 *
宋秀平 司廷林
(1.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硕士研究生2020级,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诊疗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1)
升陷汤出自《医学衷中参西录》,由生地黄、知母、柴胡、桔梗、升麻组成。张锡纯在书中写道:“治胸中大气下陷,气短不足以息。或努力呼吸,有似乎喘……诚难悉数。其脉象沉迟微弱,关前尤甚”[1]。张锡纯指出升陷汤中黄芪既补气又升气,且其质轻,中含氧气,与胸中大气有同气相求之妙用,因黄芪归脾、肺经,味甘,性微温,故配伍味苦性寒之知母,温寒升降并用,使气机得以调畅、宗气得以充养;方中柴胡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右上升;桔梗能载诸药之力上达胸中[1]。
临床应用升陷汤治疗呼吸、消化、循环、内分泌等各科疾病时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可见升陷汤所治病症较为广泛,凡是辨证符合升陷汤方证特点的疾病均可尝试运用升陷汤进行治疗,但张锡纯在书中所提到的有关升陷汤辨证的病症较为繁琐复杂,我们在临床应用时难以把握。司廷林教授从方证辨证的角度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升陷汤方证的临床应用特点,简单易于把握:(1)患者多喜长舒气,气短不足吸,深吸气则舒。(2)多数患者左脉按之较弱,寸脉尤甚。(3)患者舌质偏淡,没有明显的火热之象即可应用。(4)平素多操劳的女性患者多见,劳作时未发觉有气短等症状,反而静息时感气短症状加重。司廷林教授在临床实际运用升陷汤时,严格把握其方证特点治疗各科疾病,均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医案举隅
案1李某,男,72 岁,退休。初诊日期:2019 年9 月10 日。因“口干、多饮20 余年,加重伴双下肢浮肿半月余”就诊。既往糖尿病病史20余年,现长期口服二甲双胍降糖,血糖控制尚可。近半月出现下肢及足踝部浮肿,每于下午浮肿尤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化验尿常规示:尿蛋白(++),尿糖(+++)。患者平素时有胸闷、气短,偶有乏力、心悸,多饮,无口苦,无恶寒,纳食尚可,夜眠可,小便量尚可,泡沫尿,大便稀溏,舌质稍红、苔黄腻,脉沉,两寸脉偏弱。西医诊断:糖尿病肾病。中医诊断:消渴病肾病。中医辨证:脾肾亏虚、宗气下陷。治法:补肾健脾、升阳举陷。方用升陷汤加减:黄芪30 g,知母15 g,升麻9 g,柴胡12 g,桔梗12 g,桂枝12 g,葛根30 g,党参30 g,生石膏30 g,炒白芍30 g。共7 剂,水煎400 mL,早晚分服200 mL。降糖药未作调整。
二诊:患者胸闷、气短症状减轻,浮肿减轻,尿中泡沫减少,大便正常,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细。化验尿常规:尿蛋白(+-)。上方加巴戟天15 g,补骨脂15 g,菟丝子15 g,继服7剂,煎服法同前。
三诊:患者无乏力,无明显浮肿,纳可,夜眠可,尿中无明显泡沫。化验尿常规:尿蛋白(-)。继服上方7 剂,巩固疗效。嘱患者平时注意控制饮食,适当锻炼,增强体质,注意监测血糖,定期复查尿常规、肾功能、尿蛋白微量等各项生化指标。
按语: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全身各个脏腑所需的气血津液需肾精滋生,同时也需后天水谷精微以充养。肺从自然界吸入的清气和水谷之气合于胸中为宗气,若元气不足或水谷之气不足,无以充养胸中大气,均可出现宗气下陷的症状,故脾肾虚损会影响消渴病肾病病情的进展。若脾虚失运,可见大便稀溏。肾虚则不能司膀胱开阖,加之蒸腾气化失职,水湿内停,泛溢四肢,发为水肿;肾虚导致其固摄失职,血脉津液内的精微物质从尿液中流失,则可见蛋白尿、糖尿。因心悬于膈之上,若大气下陷,心将无所依附,故可呈现心悸、心慌等症状。以上诸多证候皆为脾肾亏虚日久、宗气下陷所致,佐以患者的舌苔脉象即可明确诊断。故治疗上选用升陷汤以补中举陷、升提气机。有医家指出葛根作为风药具有升散、善行特性,其升阳作用可使中气上达,既能够激荡气机,又能载药上行,可令水邪上行至肌表,由玄府而出[3]。故方中加用葛根既可升提气机,又可健脾止泻,以恢复脾的升清及运化转输功能。本证患者因宗气下陷日久,全身气机升降失常,痰浊、水湿、瘀血等毒素容易在体内停聚,郁积日久可化热,故见其舌质红、苔黄腻,方中用性凉之品知母、石膏以宣解郁热。二诊时患者诸症状减轻,考虑消渴病肾病患者久病必损及肾脏,此时不仅要升提宗气,同时应注重固本,可佐以补肾温阳之品以资先天助气化,故加用补骨脂、巴戟天、菟丝子温补肾阳。脾肾两脏正常生理功能得以恢复,全身气机升降正常,痰浊、水湿、瘀血等毒素在体内无以停聚,机体水肿则可消退;加之先天肾精充足,肾气能有效发挥其固摄作用,则精微物质无以流失,故尿蛋白明显减少。
案2白某,女,40岁,职工。初诊日期:2021年11月12日。因“月经淋漓不尽1月余”就诊,患者自诉近1月因情绪波动出现月经淋漓不尽,经色淡红质稀,平素有四肢沉重感,伴乏力、气短,休息时感上述症状加重,深吸气或提气则舒,面色苍白,小腹偶有下坠感,无下腹冷痛,无明显怕冷的表现,纳可,夜眠可,二便调,舌质淡胖、苔薄白,脉缓弱,寸脉尤甚。西医诊断:无排卵性异常子宫出血。中医诊断:崩漏。中医辨证:宗气下陷、血失统摄。治法:补气升提、固冲止血。方用升陷汤加减:黄芪45 g,知母15 g,升麻9 g,柴胡12 g,桔梗9 g,桂枝12 g,葛根30 g,茯苓30 g,甘草9 g,当归30 g,炒白芍15 g。共7剂,水煎400 mL,早晚分服200 mL。
二诊:病情好转,服药第2天月经淋漓停止,乏力减轻,无明显怕冷,无下腹冷痛,二便正常,舌质淡红、苔薄,寸脉浮余沉。上方黄芪改为30 g,加川芎30 g,熟地黄20 g。继服7剂,煎服法同前。
三诊:患者诸证好转,可守方继服,稳固疗效。嘱其保持心情愉悦舒畅,饮食上可适当补充营养物质,适量运动。
按语:《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肾气盛……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指出肾气充盛则月经可按时而来[4]。肾既能藏精血,又能发挥固摄作用,若肾虚则无法发挥封藏固摄气血的功能则可导致崩漏的发生;另外,脾既能统血,又能化生气血,血液的生成及其在体内的运行均依靠脾脏功能的正常发挥,一旦脾病则血液在脉道中的运行失去约束,或瘀积于内形成瘀血,或不循常道逸出脉外发为崩漏等症,故脾肾两脏与崩漏的发生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崩漏的病机是脾肾亏虚、瘀热互结,指出治疗时应注意补益脾肾,同时兼以活血祛瘀、疏肝清热,并自拟固冲汤以滋补脾肾、益气固冲,在临床实践中取得良好疗效[5]。司廷林教授指出属于虚证的崩漏在治疗时应以健脾补气、升提气机为主,同时再辅以补肾、疏肝、养血、化瘀等法。本证患者由于气虚失于固摄,血溢脉外,发为崩漏。患者的症状及舌苔脉象均为气虚的表现,气虚进一步可发展为气陷,可表现为深吸气则舒、小腹下坠感等,应急则治其标,以补气升提为主,予升陷汤加减,方中重用黄芪为君。张元素率先提出升麻具有升提作用,后李东垣在“补中益气汤”中对升麻升提阳气作用进行发挥[6],现在众多医家处方时也重视升麻的升提补气作用,治疗因中气不足所致的短气疲倦、崩漏、子宫下垂、脱肛等也取得良好效果。故方中加大升麻用量,以增强升提气机的力量。《傅青主女科》云:“妇人经来断续……是肝气之郁结乎”,指出崩漏的病因与肝气郁滞相关[7]。患者情志不舒,肝郁气滞也是崩漏发生的一大诱因,方中运用柴胡可起到调达气机、疏达肝气郁结的作用。考虑患者现已月经淋漓一月余,虽然是缓缓少量失血,但也必定存在血虚的情况,故方中加用当归既可补气血之亏虚,又可活血祛瘀;加用白芍既能濡养气血,又可柔肝舒达气机以调经止痛。复诊时患者寸脉浮,气虚症状减轻,表明胸中大气已复,故稍减黄芪用量,兼以养血补虚、培元固本为辅,加用熟地黄补血虚、滋补阴血;加用川芎行气活血,以保证全身气血津液的正常运行。川芎味辛可行气散血,当归味甘可补气血之虚,二者合用以补血活血、生新祛瘀,机体气血充足、气机升降调达,冲任二脉充盛,则崩漏自止。
案3李某,女,57岁,退休职工。初诊日期:2021年12月31日。因“阵发性胸闷10年余,加重伴乏力1周”就诊。患者既往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史10余年,5年前于当地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提示冠状动脉狭窄90%以上,予支架植入及对症治疗,现院外长期服用拜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银杏叶片等药物,病情相对稳定。1周前患者因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憋气、心悸症状加重,伴心前区刺痛,疼痛可放射至肩背部,每次持续约2 min,含服速效救心丸后症状可缓解,气短不足以吸、深吸气则舒,纳可,夜眠可,二便调,舌质淡胖大、舌边有齿痕、苔薄白,舌下静脉迂曲,脉沉弱,寸脉尤甚。西医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中医诊断:胸痹。中医辨证:宗气下陷。治法:补中益气。方用升陷汤加减:黄芪30 g,知母15 g,升麻9 g,柴胡12 g,桔梗9 g,桂枝15 g,葛根30 g,党参30 g,甘草9 g,泽泻15 g,丹参30 g。共7剂,水煎400 mL,早晚分服200 mL。
二诊:患者诉胸闷、气短症状减轻,自觉胃中冷,恶冷食,喜热饮,舌淡胖、舌边有齿痕,脉沉。上方加麸炒白术30 g,熟附片9 g,干姜6 g,继服7剂,煎服法同前。
三诊:患者诸证好转,未再出现明显胸闷、心悸、气短等表现,胃中冷明显改善,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继服上方7 剂以稳固疗效。嘱其减少重体力劳动,适度运动,定期复查。
按语:中医认为胸痹多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有学者认为,因宗气不足所致的胸痹治疗时应遵循“虚则补之”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健运中气法,临床运用四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治疗胸痹取得良好效果[8]。张锡纯受《灵枢·邪客》“五谷入于胃……宗气积于胸中”启发,指出宗气即大气,为诸气之纲领、周身血脉之纲领[1]。故宗气不足也可影响血脉的运行,血液运行不畅,心血不足,心肺失于濡养则可发为胸痹。司廷林教授认为在治疗因虚而致的胸痹时,应以补气升提为主、养血活血化瘀为辅。本案患者平素多劳累,劳伤心神,耗气伤阴,存在气血不足的情况,加之其本身脉管狭窄又处于支架植入术后状态,故其脉道通畅大不如前,不排除再次出现狭窄的情况,一旦血行不畅,则心血失于濡养,心肺气机有失调畅,气机升降失常从而导致宗气下陷,表现出胸闷、心悸、气短等症,患者的舌苔、脉象均为佐证,故治疗时应以补气升提为主,方选升陷汤进行加减。另外,本证患者因气虚日久,气虚无力推动血行而成瘀血,可见舌下静脉迂曲,故加用丹参以活血化瘀;因患者气虚血瘀日久,体内水液无法正常运化,容易酿生痰湿,故加用泽泻以利水渗湿。张锡纯首次明确提出了桂枝“升气”的观点,有学者[9]分析桂枝白芍组方配伍规律,指出桂枝既能发散,又可升提中焦营卫气机,此处加用桂枝既可温通经脉、濡养心脏,又可升举阳气以恢复胸中大气,从而改善胸闷气短等症状。二诊时患者上述症状减轻,因其诉胃中冷、恶冷食、喜热饮,考虑其合并有脾胃虚寒的情况,故又加用麸炒白术、熟附片、干姜,取理中丸之意,温补中焦脾胃以散虚寒。
案4王某,女,退休职工。初诊日期:2021 年9月31日。因“反复胸闷、气促20余年,加重伴憋喘1 d”就诊,患者既往有支气管哮喘病史20余年,平素间断雾化吸入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患者自述每于季节交替之际,容易感受外邪而致病情加重。近日感咳嗽、憋喘较之前加重,活动后憋喘尤甚,平静休息时尚不憋喘,呼吸急促、气短不足以吸、喉中哮鸣音明显,纳差,神疲乏力,自汗出,大便偏稀,舌边淡红、苔薄白,脉左寸沉细、右寸浮、关脉弦。听诊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哮鸣音、湿啰音。西医诊断:支气管哮喘。中医诊断:哮病。中医辨证:宗气下陷。治法:补气升提,兼以燥湿化痰。方用升陷汤加减:黄芪30 g,知母15 g,升麻9 g,柴胡12 g,桔梗9 g,桂枝15 g,葛根30 g,陈皮9 g,姜半夏12 g,厚朴12 g,苦杏仁12 g。共7剂,水煎400 mL,早晚分服200 mL。
二诊:患者憋喘、气短减轻,上方加党参30 g,麸炒白术30 g,茯苓30 g,甘草9 g。继服7剂,煎服法同前。
三诊:患者病情稳定,嘱其可继服上方,以巩固疗效。嘱其平时避免感受风寒,减少与花粉、粉尘等易诱发哮喘的病原接触,适当进行锻炼增强体质。
按语:中医认为哮病的发病机制在于“内有宿痰,触感而发”,肺从自然界吸入的清气和水谷之气共同构成宗气,即胸中大气。而肺主气司呼吸的功能由肺的宣发肃降来维持,因此肺脾两脏受损则会影响宗气的生成;反之,宗气不足、气机升降失常也可导致哮病等肺系疾病的病情进展。本案患者哮喘病史数十年,久病素体虚弱,必定会影响肺正常的生理功能,肺脾亏虚进一步发展必定会影响宗气的形成,从而导致大气下陷。本病因其体内留有伏痰,又感受外邪侵袭,伏痰与气交结于咽喉处,气机升降不利,则可出现呼吸困难、憋喘、气短等相关表现,故方中加用陈皮、姜半夏,取二陈汤燥湿化痰、理气和中之意,在补肺纳气固本的同时兼以化痰祛湿;加用厚朴疏利气机兼以化痰,加杏仁止咳平喘、化痰。因“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若脾脏虚损,水湿失于运化,聚湿生痰,停聚于机体各个部位则可表现为水饮、水肿,水饮痰湿又易受外邪引动,痰与气交阻进而影响气机升降,肺失宣降则发为哮喘[10]。中医认为治疗哮病应遵循“发时治标,平时治本”的原则,二诊时患者病情已平稳,治疗时应重视扶助正气,补虚固本,故方中加用党参、麸炒白术、茯苓、甘草,取四君子汤益气健脾之意,健脾化湿以杜绝生痰之源。脾气健旺,肺脏也受脾脏滋养,则肺中无痰可贮,体内痰湿祛除,规避外来邪气,其气喘自平。
2 小结
综上所述,方证辨证可以指导我们准确、迅速、有效地临床遣方用药,更好地防治疾病的发生和进展,从而达到异病同治的效果。我们在临床诊疗各科疾病的过程中,均可以方证辨证为指导,凡是符合升陷汤方证的疾病,皆可在升陷汤原方基础上加减化裁,为我们临床应用升陷汤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