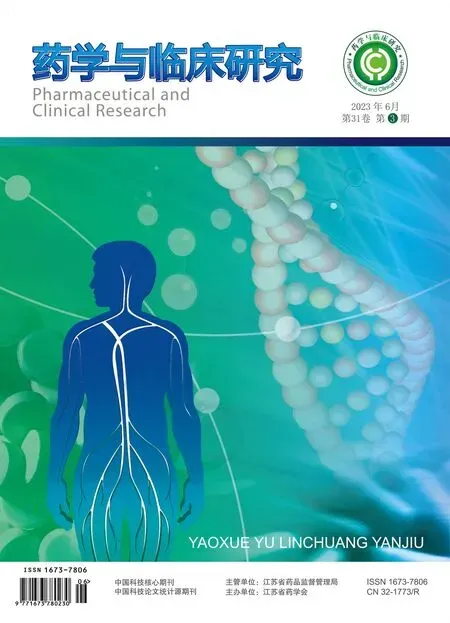肿瘤类器官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方艳芬,郭屾淼
1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 201203;2上海市洋泾中学,上海200122
随着肿瘤基础研究的深入、早诊早治理念的推广以及新诊疗手段的发现,特别是近三十年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研发,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获得极大提高。但是恶性肿瘤依然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问题,仍需通过基础研究的深入寻找开发更为有效的肿瘤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以及更精确地发现相应的受益人群。
肿瘤基础研究和抗肿瘤药物研发及相应应用方案的发现都需要准确、可靠且可重复的药效学模型予以支持。目前常用的模型主要是由人或动物的肿瘤组织构建的细胞株和利用这些细胞株构建的动物模型,但是由于长期在体外培养,肿瘤细胞株的基因、生物学行为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已不能真实反映临床肿瘤实际情况,导致由细胞株构建的模型筛选得到的有效化合物在临床试验中屡屡碰壁。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2000 年~2015 年2 万多个化合物的临床试验数据,结果表明成功率仅为3.4%[1],因此,贴近临床情况的肿瘤模型日益受到业界的关注和重视。直接利用病人来源的肿瘤样本构建从细胞到体内的不同层次模型,被称为病人来源肿瘤原代细胞株(patient-derived tumor cell,PDC)、病人来源肿瘤类器官模型(patient-derived organoids,PDO)和病人来源肿瘤异种动物模型(patient-derived xenograft,PDX)。这三类模型提供了更个性化、更符合人类肿瘤真实生物情况的实验模型,能更真实、通用地反映肿瘤生物学特征和药物的响应特征,有助于提高临床转化效率[2,3]。
类器官(organoids)是将多能干细胞或者成体干细胞/祖细胞在三维基质中培养,通过自组装形成与体内来源组织或器官高度相似的三维组织[4,5]。PDO是利用基质胶或者生物材料将癌症患者原代肿瘤组织在体外进行三维培养构建的培养物,是近十年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体外肿瘤研究模型。与以往只关注肿瘤细胞本身不同,PDO 立体地模拟体内肿瘤生长的微环境,从而更好地保持人肿瘤细胞生长的特征,有助于维持高度异质性,是新时代肿瘤研究领域的利器。本文将从PDO 研究进展、在肿瘤新药研发和基础研究中的应用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这几方面进行综述。
1 肿瘤类器官的研究进展
1.1 肿瘤类器官的构建现状
2009年,Sato T等[6]报道了利用小鼠肠道干细胞构建类器官的研究,由此开启了类器官研究的时代。利用干细胞构建类器官的实践为PDO 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不久之后,陆续有文献报道由鼠源肿瘤或者癌症患者来源的新鲜肿瘤组织构建而成的PDO。用于构建PDO 的肿瘤组织大部分来源于手术切除和活检取样,还有少量来自循环肿瘤细胞和胸、腹水积液。截止目前,十几种不同系统来源的肿瘤已成功构建PDO 模型,包括胰腺癌、结直肠癌、胃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膀胱癌、卵巢癌、肺癌、肝癌等[7]。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上皮样肿瘤,也有非上皮肿瘤PDO,包括胶质母细胞瘤和横纹肌样瘤[8,9]。不同类型的肿瘤组织,PDO 模型的构建成功率各不相同。肠癌、胰腺癌和卵巢癌的成功率较高,达到80%以上;而肝癌、前列腺癌的成功率则相对较低,仅约15%~30%[10-12]。相应地,目前已报道的结直肠癌、胰腺癌、胃癌PDO 例数累积均已达到几百例,而肝癌、前列腺癌PDO 例数仅累积几十例[11]。除了肿瘤类型,影响构建成功率的因素还包括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样本质量、样本分离到处理的间隔时间和保存条件等。
1.2 肿瘤类器官的优势
与细胞系构建的细胞和动物模型相比,PDC、PDO 和PDX 均采用临床肿瘤样本构建而成,重现且维持来源肿瘤组织的基因表达特征,具有贴近临床的先天优势。PDC 是用病人的新鲜肿瘤组织分离获得的肿瘤细胞,在体外培养体系中进行短期二维培养构建的模型,具有成本较低、培养方便、实验周期短、可进行高通量筛选的优势;但是PDC 构建成功率低、二维培养方式不能反映肿瘤真实生长的细胞特性、原代肿瘤基因特征在传代过程容易发生改变。PDX 是用病人的新鲜肿瘤组织直接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从而建立皮下或原位移植瘤模型,能很好保存原发肿瘤的组织形态特征、模拟人肿瘤的病理生理环境;但由于肿瘤组织中缺乏某些免疫细胞,因此在免疫缺陷小鼠上构建的类器官不适合评价一些免疫治疗药物,另外还存在成功率低、耗时长、成本高的问题[13]。
PDO 的生物学特性使其成为弥补PDC 和PDX不足的重要工具。由于采用三维培养,PDO 较好地保持肿瘤细胞与微环境基质的接触极性,高度呈现原代肿瘤组织的形态特征和基因组学特征,真实还原肿瘤异质性、药物敏感性等特性[14,15]。在合适的条件下,PDO 包含免疫细胞、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等成分,能立体地模拟人体内的肿瘤微环境,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半体内模型。与PDC 相比,PDO 可以更加准确地呈现临床肿瘤实际情况;与PDX 相比,PDO 形成时间短、传代时间短,有利于实验开展,适用于高通量筛选。
2 肿瘤类器官的应用
2.1 临床前药效评价和作用机制研究
目前,肿瘤类器官作为体外实验模型,广泛应用于新药研发的临床前研究,有助于提高新药临床试验成功率,降低新药研发成本和风险,因而已开始在临床前研究中得到较广泛的使用。Broutier L等[16]采用临床肝胆肿瘤病人的手术样本构建了8 例肝胆PDO,利用其中6 例模型评价了29 个抗肿瘤药物对肿瘤细胞增殖存活的影响,发现药物敏感性与基因突变之间的相关性,例如CTNNB1突变与porcupine 抑制剂LGK974 耐药、KRAS突变与EGFR 抑制剂AZD8931 耐药之间有关联。Hirt CK等[17]将自动化类器官培养、药物递送、细胞活力检测等技术进行集成,开发并利用全自动PDO 药物筛选平台对1172 个获得美国FDA 批准的临床药物(适应症包括癌症、炎症、心血管及中枢系统疾病等)进行抗肿瘤活性筛选。结果发现26 个药物对胰腺导管癌类器官具有潜在抗肿瘤活性,其中19 个是尚未获批用于胰腺癌治疗的化疗药物,5 个是用于治疗非肿瘤疾病(包括强心苷ouabain 和抗原虫药emetine 等)的药物。体内实验进一步证实,ouabain和emetine 对胰腺导管癌肿瘤生长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他们还通过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构建ARID1A错义突变的PDO,发现相较于野生型,ARID1A突变的胰腺导管癌对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达沙替尼和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基因Rad3 相关激酶(ataxia telangiectasia and Rad3-related,ATR)抑制剂VE-821 更为敏感。类似地,Lo YH 等[18]将PDO 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和CRISPR/Cas9 技术结合,在胃癌类器官模型中寻找基因组改变与药物敏感性之间的关联。在人正常胃组织类器官中敲除TP53和ARID1A,转录因子(forkhead box protein M1,FOXM1)及下游参与细胞增殖调控的基因显著上调,进而促进胃癌的发生。高通量药物筛选发现FOXM1 下游靶标BIRC5/Survivin 的抑制剂YM-155 能显著抑制TP53/ARID1A双敲除胃癌类器官的增殖存活。上述研究表明PDO 适用于高通量药物筛选,结合基因组学、转录组学技术,可建立基因表达/突变与药物敏感性之间的关联性,发现可能指征药物敏感性的生物标志物。此外,将PDO 技术与CRISPR/Cas9 基因敲除技术结合,可用于探索肿瘤耐药机制及药物合用克服策略,这些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提高抗肿瘤治疗效果[19]。
2.2 临床个性化用药方案制定
PDO 真实呈现原代肿瘤特性,且具有培养周期相对较短、操作方便等优势,有助于其用于临床癌症患者对于放化疗药物、分子靶向药物、抗肿瘤抗体等药物敏感性检测,预测患者对药物响应性的情况,具有辅助临床治疗决策的潜力。2018年,Science报道了一项转移性胃肠道肿瘤类器官用于药物敏感性测试的研究[20],该研究比对分析了21 位临床病人与其相应PDO 对一系列靶向及化疗药物敏感性差异,结果表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与患者实际疗效进行对比,PDO 预测良好(敏感性100%、特异性93%、阳性预测值88%以及阴性预测值100%)。2020年,Yao Y等[21]利用112 例局部晚期直肠癌活检组织构建了96 例直肠癌类器官,选取其中80 例检测其对放化疗的响应,结果表明直肠癌类器官对放化疗敏感性与病人临床响应高度一致(敏感性78%,特异性92%、准确性84%)。随后在胃癌、乳腺癌等肿瘤中,也发现PDO 与肿瘤患者对药物响应的一致性情况。Yan HHN等[22]利用34 位胃癌病人的肿瘤组织、癌旁组织和淋巴结转移灶构建了一个胃癌类器官库。其中有2 例发生肿瘤转移,在手术后进行了顺铂和5-FU 联合治疗,两者均有很好的响应。另1 例术前接受过化疗,术后对卡培他滨无响应。考察这3 例的PDO 相应化合物的敏感性,结果表明PDO 的药敏性与各患者的临床响应情况完全一致。Guillen KP等[23]利用内分泌治疗耐受、复发和转移的乳腺癌病人肿瘤样本构建了PDX 及PDO,且对这些样本进行了组织形态学、基因组和药物敏感性检测。结果表明,乳腺癌PDX 和PDO 均高度还原了其来源肿瘤的组织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特性,而且两者对抗肿瘤药物的响应一致。该研究中一位处于ⅡA 期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在经历术前化疗和手术治疗后1 年左右发生肝转移。研究者将构建的PDO 和PDX 进行体内外药敏检测,发现微管抑制剂艾瑞布林(erubulin)具有最佳治疗效果。根据这一结果,指导病人接受艾瑞布林治疗,用药后肝转移完全缓解,持续时间将近5 个月。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PDO 指导临床肿瘤患者用药的可能性,但所涉及的案例数较少,还需要更广泛的研究来评价PDO 在临床药物敏感性预测中的价值。另外还有研究表明,通过比较正常类器官和PDO 对药物的响应差异,发现选择性高的药物有助于降低临床患者的毒副反应。由此可见,通过PDO 进行药敏检测,发现最合适的药物治疗方案,将有助于提高肿瘤患者临床疗效,降低毒副作用、耐药风险和肿瘤复发几率,使患者最大程度受益。
2.3 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
2.3.1 肿瘤类器官作为肿瘤进展模型的应用 针对肿瘤患者疾病进展不同时期的PDO、原发和转移灶PDO,采用多组学技术分析基因表达、突变、表观遗传修饰等差异,有助于探索发现促进肿瘤进展和转移的新机制,为抗肿瘤新药研发提供新的分子靶标。Roe JS等[24]利用转基因KPC 小鼠胰腺导管癌的原发和转移肿瘤组织构建PDO,转录组学分析发现转移灶PDO 中转录因子(FOXA1)表达明显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FOXA1 诱导增强子重编程,从而使癌细胞具有转移性。Mo S等[25]利用转录组学、基因组学和单细胞测序技术比较了结直肠癌病人原发灶和肝转移灶PDO,发现转移灶肿瘤较好地保留了相应原发肿瘤的驱动基因突变特征,另外也产生一些新的突变图谱,这些突变是否驱动肿瘤发生转移有待进一步研究。
蛋白质组学对于肿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对用于检测的肿瘤样本量需求较大,因而限制其广泛应用。通过体外PDO 培养实现微量肿瘤组织的扩增,可为蛋白质组学检测提供足够的样本量。2015年,Boj SF等[26]利用iTRAQ 技术对小鼠正常胰腺导管类器官、胰腺上皮内肿瘤类器官、胰腺导管腺癌类器官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正常胰腺导管类器官和胰腺上皮内肿瘤类器官间存在710 个差异蛋白,正常胰腺导管类器官和胰腺导管腺癌类器官间存在1047 个差异蛋白。将这些数据与转录组学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正常胰腺导管类器官和胰腺上皮内肿瘤类器官、正常胰腺导管类器官和胰腺导管腺癌类器官间的差异表达在两种分析中均出现的概率分别是40%和70%左右,说明蛋白稳定性在胰腺癌演化进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Cristobal A等[27]利用Dimethyl 标记的蛋白质组学分析了临床病人来源的结直肠癌类器官和癌旁正常结直肠组织类器官的蛋白表达差异,共鉴定出5790 个蛋白,其中78个蛋白发生上调,227 个蛋白发生下调。与转录组学数据进行对比,这305 个差异表达蛋白中有22 个在两种分析中出现了一致的变化。类器官和蛋白质组学技术的结合可以获得蛋白层面的数据,为全面掌握肿瘤的生物学特征提供有力的研究手段。
2.3.2 肿瘤类器官在发现肿瘤抑制或驱动基因中的应用 利用正常类器官或者肿瘤类器官,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基因敲除、敲减或者过表达,可用于揭示相关基因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例如BAP1(BRCA1-associated protein 1),它是去泛素化酶家族成员之一,参与调控多种细胞生物学功能,包括基因组稳定性、DNA 双链断裂、细胞周期、凋亡等过程,但它在成人肝稳态和肝脏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并不清楚。Artegiani B等[28]利用CRISPR/Cas9技术在正常人肝导管类器官中敲除BAP1,发现BAP1 通过调控染色质可及性来控制细胞连接和细胞骨架相关基因表达,可影响细胞极性,使细胞丧失多种上皮特征,运动性增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使人肝导管类器官类器官携带TP53、PTEN、SMAD4和NF1 突变,分析敲除BAP1 对肝导管细胞恶化的影响,发现BAP1 敲除的肝导管类器官具有体内成瘤性,肿瘤组织形态学特征与临床胆管癌类似。该研究表明调节染色质可及性来控制上皮细胞是BAP1作为肿瘤抑制因子发挥功能的关键因素之一。
TGF-β 信号通路可抑制肠上皮细胞增殖,因此在肠道类器官培养条件中需要加入抑制剂抑制该信号通路提高构建效率,撤除抑制剂或者添加重组TGF-β 有效抑制结肠类器官生长[29]。利用这一特点,科学家们在肠道类器官中进行CRISPR/Cas9 基因敲除文库转染,撤除TGF-β 受体抑制剂或添加重组TGF-β 进行阳性筛选,寻找新的肿瘤抑癌基因(tumor suppressor gene,TSG)。Michels BE等[30]利用有APC-/-和KRASG12D突变的癌前结肠类器官筛选一个泛癌TSG gRNA库,发现一系列潜在的抑癌基因,包括在结肠癌中发生高频突变的基因(TGFBR2、SMAD4、PIK3R1、ZC3H13和FBXW7),及在结肠癌中并未见报道,但与其他肿瘤密切相关的基因(STK11、PBRM1和ZFP36L1)。Ringel T等[31]利用野生和APC敲除的人小肠类器官进行CRISPR/Cas9基因敲除文库筛选,发现一些与TGF-β 耐药性相关的基因,包括CNIH4、KEAP1、NBAS和SWI/SNF 亚单位(ARID1A和SMARCA4)等。进一步研究发现,ARID1A和SMARCA4介导的染色体重塑参与调控TGF-β 下游靶基因转录,进而抑制肿瘤生长。当ARID1A和SMARCA4发生突变,染色体重塑受到抑制,TGF-β 下游靶基因转录发生改变,肿瘤细胞发生恶性增殖。这些研究展现了PDO 结合基因编辑技术在研究发现新型肿瘤原癌或抑癌基因中的潜能。
2.3.3 肿瘤类器官在病原体相关肿瘤进展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对于肝癌、胃肠道肿瘤等涉及微生物感染的癌症类型,采用相关病毒或细菌感染正常类器官或者PDO,可研究微生物在肿瘤演化进程中的确切角色。比如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是肝癌最重要的致病风险之一,特别在中国,是肝癌发生的主要诱因。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实验模型,HBV 的致癌机制并不明确。De Crignis E等[32]利用HBV 感染由肝硬化病人的病理肝组织构建而成的肝脏类器官,转录组学分析发现这些类器官存在异常的早期癌症基因特征,为HBV 诱发的肝癌发生发展机制研究提供线索,也为治疗提供潜在的候选靶标。肠道菌群也被认为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如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E.coli)基因组包含一个50 Kb 杂合聚酮非核糖体肽合酶操纵子(pks),可产生小分子毒性物质colibactin,破坏细胞DNA。有研究将具有遗传毒性的pks+大肠杆菌注射入人肠道类器官内腔,在暴露五个月后对类器官细胞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其可诱导独特的突变特征。通过队列研究分析不同癌症类型的突变模式,发现这一突变特征在结肠癌中的频率更高[33]。可见,PDO 可为研究病原微生物在肿瘤发生及演化进程中的作用提供实验模型。
2.4 肿瘤新抗原的鉴定和发现
准确和快速鉴定肿瘤新抗原是肿瘤个性化免疫治疗的关键环节。基于质谱的免疫多肽组学通过免疫亲和力纯化和质谱测定,对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呈递的多肽样品进行鉴定和定量,可以在蛋白水平鉴定出真实存在的抗原肽,包括经翻译后修饰的肽和蛋白酶体作用产生的剪接肽等这些不能被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检测发现的免疫肽。但是免疫多肽组学需要大量的生物样本(>1 g),PDO 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肿瘤新抗原的发现和免疫治疗药物的开发。2019年,Newey A等[34]利用5 位结直肠癌患者的活检组织成功构建PDO,然后采用免疫多肽组学技术鉴定HLA-Ⅰ和HLA-Ⅱ呈递肽段。结果显示,每个PDO 的HLA-Ⅰ呈递肽段均数为9936,显著高于文献报道的在肿瘤细胞株上鉴定到的肽段数目,说明PDO 能更好地保持原代肿瘤样本的免疫源性。另外,这5 个PDO 的HLA-Ⅱ呈递肽段普遍较低,可能与PDO 中缺乏表达HLA-Ⅱ分子的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相关。2020年,Demmers LC等[35]利用一位结肠癌病人的肿瘤组织进行单细胞类器官培养,获得4 个结肠癌类器官亚克隆。免疫多肽组学分析发现,每个亚克隆均检测到大约7000 个HLA-Ⅰ类肽段,其中3%的肽段是结肠癌特异性的。结合蛋白质组学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肿瘤特异性肽段大部分来自DNA 损伤感知和修复蛋白。进一步分析发现,免疫多肽的序列在不同亚克隆中高度重复,但是其中15%~25%的多肽在不同亚克隆之间存在2 倍以上的数量差异。该研究说明即使在同一个体中,HLA-Ⅰ类肽的呈递也存在异质性,这种现象在肿瘤多肽疫苗研发过程需要加以重视。除了预测和识别潜在的肿瘤新生抗原,PDO 还可对这些潜在的肿瘤新生抗原进行鉴定,评估药物对抗原肽呈递的影响。Wang W等[36]利用多组学分析和预测了肝胆PDO 和匹配肿瘤组织的新抗原多肽库。将肝细胞癌PDO 与T 细胞进行共培养,通过细胞杀伤实验来鉴定可以刺激CD8 细胞产生抗肿瘤效应的多肽。Newey A等[34]利用结直肠癌PDO 分析了IFN-γ 和MEK 抑制剂曲美替尼(trametinib)对抗原肽呈递的影响。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基于PDO 的研究为个体化免疫治疗中新抗原多肽的临床前筛选提供了有效策略。
3 肿瘤类器官存在的问题
3.1 微环境成分丢失
PDO 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能模拟真实肿瘤微环境,但目前常用的基质胶包裹的沉浸培养下,PDO的主要成分是肿瘤上皮细胞,肿瘤微环境的其他细胞成分较少[37]。尽管Neal JT等[38]开发的气液界面培养(air-liquid interface culture,ALI)构建的PDO 包括了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和免疫细胞,但是这些成分在传代过程中会逐渐丢失[39]。为了解决肿瘤微环境成分缺失问题,将PDO 与肿瘤组织分离得到的CAFs 或者免疫细胞共培养,以期更真实地模拟肿瘤微环境[40]。另外,器官芯片概念也被引入共培养体系打造类器官芯片,实现PDO 与肿瘤微环境成分共培养[41]。
3.2 缺乏标准化
PDO 构建涉及多个环节,包括肿瘤组织样本取样、组织处理、三维培养等过程。但是这些环节尚无标准、统一的操作流程,不同实验室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各自的方法,实验技术的多样性可能导致PDO 不能真实、准确地重现来源肿瘤组织的生物学异质性。由于PDO 大多采用手术切除或者活检肿瘤组织,而组织处理方法往往又根据肿瘤组织不同而有差异,因此现阶段取样和组织处理标准的制定存在很大困难。相对来说,培养过程涉及的骨架材料、培养条件可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培养液中需要添加多种蛋白、生长因子促进PDO 生长,这些商品化的蛋白、因子价格昂贵,于是一些实验室采用在细胞中过表达的相应蛋白收集培养液进行替代。但这些条件性培养液不仅存在批间差异、实验室间差异,还有很多未知的成分可能影响PDO 培养,因此降低重组蛋白、因子的生产、使用成本,是实现培养条件标准化的关键环节之一。另外,目前三维培养最常用的骨架材料是从小鼠肉瘤(Engelbreth-Holm-Swarm,EHS)中提取的基底膜基质(Matrigel或者BME)或者动物来源的胶原基质,存在批次间差异、成分不明确、操控性差等问题。材料科学研究正致力于开发新型的生物材料,力图最大程度模拟体内肿瘤细胞与胞外基质的相互作用,重现肿瘤微环境[42]。
3.3 临床个性化应用问题
同种肿瘤不同病人、同一病人不同肿瘤灶构建的PDO 可能存在克隆选择,导致不能真实呈现原发肿瘤的特性,进而使得药物敏感性与临床实际存在偏差。尽管基于PDO 的高通量药物筛选可以建立基因-药物敏感性相关性,但是对于临床肿瘤患者个体而言,不同肿瘤灶的异质性存在药物响应差异,使得PDO 在临床治疗决策中的应用仍存在较大的挑战。此外,不同肿瘤类型PDO 构建成功率不同,成功率低的肿瘤较难支持药物敏感性检测,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改进[7]。
3.4 其他问题
PDO 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等待解决。肝癌、前列腺癌等肿瘤的PDO 构建成功率偏低,需要改进方法提高成功率[11,12];大部分构建成功的PDO主要来源于上皮样肿瘤,非上皮样肿瘤的PDO 构建有待开展;有些PDO 中混有正常组织来源的类器官,而且有些时候后者生长速度反而更快;目前常用的药物筛选或者根据细胞形态筛选PDO 并不适用于所有肿瘤,因此需要建立合适的PDO 筛选方法;另外,相较于二维细胞,PDO 培养周期较长、成本高昂,需要通过优化培养条件缩短培养周期、降低培养成本。
4 结论和展望
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本质和基本过程逐步被阐明,使得抗肿瘤药物的研究从传统的细胞毒类药物转向分子靶向、免疫调控抗肿瘤药物等,更注重于精准医疗、个性化治疗。相应地,抗肿瘤新药研发对药效评价模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贴近临床的体内外模型,被认为是缩短新药临床前到临床的研发周期、提高药物研发成功率的重要工具。作为一种新的肿瘤研究模型,PDO在过去十年间发展迅速,展现了诸多优势,在抗肿瘤新药研究领域和肿瘤基础研究中应用广泛。尽管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亟待改善和优化,但是目前已显示出PDO 对肿瘤基础研究、临床前和临床药物研发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相信在未来也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丁健院士对本综述选题的指导,感谢中国工程院未来少年科创营项目的支持。
- 药学与临床研究的其它文章
- 1例右侧颈内动脉瘤切除术后吞咽障碍患者的营养支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