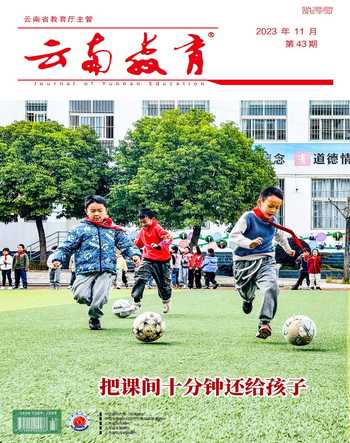被诺奖记录的疫苗进化史

經历了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为期三年的阻隔,我在2023年9月末又一次来到斯德哥尔摩,为即将公布的新一届诺贝尔奖进行现场报道的准备工作。按照惯例,诺贝尔奖总是在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公布,而首先被揭晓的则总是由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负责评选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校园里,与往年印象中树叶都已经开始发黄或变红不同,此时校园内的树木大多郁郁葱葱,保持着夏天的景象,这大约也算是全球变暖的一个明证。发布会定在10月2日11:30,在校园里一个名为“诺贝尔论坛”(Nobel Forum)的会场进行。我约了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进行医学研究的任晓远和我一起参加,帮我解读本届诺奖。还不到10点,会场里已经来了不少记者。
人们开始猜测今年可能的获奖者。有人猜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技术有可能获奖,原因是诺奖虽然对于医疗技术的进步不太敏感,但是此前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技术也曾经获得197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诊疗技术唯一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而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于医疗的贡献已经有目共睹。
有人根据“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拉斯克奖(Lasker Award)进行猜测。两位人工智能专家刚刚因为开发出了“AlphaFold”应用,完全改变了人类进行蛋白质研究的格局而获得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以此推测,或许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会破天荒地授予人工智能专家。
也有人谈到mRNA新冠疫苗获奖的可能,话题迅速转到去年就有很多匈牙利记者来到现场,因为参与开发mRNA新冠疫苗的重要科学家之一,卡塔林·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就出生在匈牙利索尔诺克。结果,尽管卡塔林与合作者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已经获得大大小小无数的科学奖项,但依然无缘2022年诺贝尔奖。当时看来,诺贝尔奖依然采取其一贯的策略,用时间来考验一项科学成果的真正价值。
发布会推迟了15分钟后在11:45开始。短暂的开场过后,本年度的获奖人被揭晓,正是“发现了核苷酸碱基修饰,从而开发出了有效的抗COVID-19 mRNA疫苗”的两位科学家,卡塔林与韦斯曼。现场爆发出一阵轻微的欢呼声。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mRNA疫苗迅速问世,让这两位科学家从默默无闻到几乎包揽世界上一切重要的科学奖项,进而被最重要的诺贝尔奖所承认和记录,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以科学发展的节奏来看,这一切快得出奇。
在发布会的提问环节,任晓远问道:“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mRNA疫苗如此之快,是不是也是对目前国际上反疫苗运动的一种回应?”奥勒·肯佩(Olle K?mpe)回答说:“对于反疫苗人士,我们不确定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对疫苗抱有犹豫态度的人,这个奖项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打消疑虑。我们已经从全球积累的大量的接种人群,证明了疫苗是非常有效和安全的。”
若是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0多年的历史来看,本年度的奖项不仅反应极快,授予一种抗病毒疫苗的发明人,其领域也相对冷门——追溯历史,只有1951年南非微生物学家马克斯·泰勒(Max Theiler)“由于关于黄热病的发现以及如何对抗它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以现代的观念看待疫苗,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预防性的药品和疗法。虽然目前也有关于能够预防重大病症——比如癌症疫苗——的研究,但从其历史上看,疫苗主要应对由病毒或细菌所引起的疾病。可以说,人类疫苗的发展,是从近乎本能到应用了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其间伴随着人类对于病毒认识的不断深入。在100多年来,其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也都被诺贝尔奖所记录。
发现“无限微小”的病毒
尽管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传染病现象及其危害,但是要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意识到“病毒”的存在。俄国科学家德米特里·伊凡诺夫斯基(Dmitri Ivanovsky)在1892年对烟草花叶病进行研究时发现,即便是通过细菌过滤器的过滤,一些健康的植物仍然可能被传染——这说明存在一种比细菌更小的传染性病原体。这种新发现最初也因此被称为“超过滤性病原体”(Ultrafiltrable Infectious Agent)。
到了1898年,荷兰微生物学家马丁努斯·拜耶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同样是在研究烟草花叶病时发明了“病毒”(virus)这一概念,并且证明了这种传染性病原体能够在植物中自我复制。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 TMV)也就成为第一种被人类发现,并且被详细研究的病毒——这是人类第一次确定某种疾病是由病毒引起。
第一个被发现的人类病毒则是黄热病毒(Yellow Fever Virus)。早在这种病毒被发现以前,黄热病已经危害人类长达数百年的时间。直到1900年之后人类才确定这种疾病是由一种病毒引起,并且可以通过蚊子传播。与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的细菌不同,相比之下病毒要小得多。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将其形容为一种“无限小的微生物”。
在人类发现病毒的存在之后,又过了50多年才能够首次给病毒以明确的定义。法国微生物学家安德列·利沃夫(André Lwoff)在1957年将病毒描述为,“具有感染性、可能具有致病性的核蛋白实体,它们只拥有一种类型的核酸,并且是从它们的遗传物质中复制出来的,它们不能生长和进行二分裂,并且没有利普曼系统(即利用酶催化产生能量的系统)”。利沃夫也因为“关于酶和病毒合成的遗传控制的发现”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Wendell Stanley)首次描述了烟草花叶病毒的纯化,并获得了该病毒蛋白质的结晶。因为这个成就,在经过了13次提名之后,斯坦利因为“制备出纯净的酶和病毒蛋白所做的贡献”终于获得1946年诺贝尔化学奖——这是第一个被授予病毒学研究的诺贝尔奖。斯坦利也被称为“病毒学之父”。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的病毒学研究中,一种可以感染细菌和古细菌的病毒——噬菌體(bacteriophage),开始被研究者用作复制基因的模型。这也让人们逐渐开始了解病毒和细胞发生相互作用的种种特点。但是人们对动物病毒颗粒的化学性质及其复制方式的理解依然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了细胞培养技术,病毒培养在此技术基础上得以实现突破,研究者们才有可能在实验室获得更多的动物病毒。
人类对于病毒概念的深入理解与对于遗传物质化学性质的理解紧密相连。时至1969年,三位美国生物化学家阿尔弗莱德·赫希(Alfred Hershey)、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因为“关于病毒的复制机制和遗传结构的发现”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于1952年通过研究发现,在噬菌体的繁殖过程中,核酸负责遗传连续性。这一发现为核酸是细胞的遗传物质提供了证据,也证明了噬菌体的遗传系统与高级生物的组织方式存在相似之处。一年之后的1953年,受到此研究的启发,沃森和克里克构建出了DNA双螺旋结构。
时至2020年,正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洛克菲勒大学的病毒学家查尔斯·赖斯(Charles Rice)因为“发现乙型肝炎病毒”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后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人类对于新冠病毒的研究,认为现在人类正处于一种重要的病毒学教育中。他对人类战胜新冠病毒的前景感到乐观:“这个领域从我读研究生的那些日子起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令人很放心的一件事情是,对于这次大流行病的全球反应,无论是学术、临床还是药物,进展的速度都很快。”“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测序一个病毒基因组。现在人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这项工作。人们在理解SARS-CoV-2和COVID-19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速度简直令人震惊。”
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除了人类对于病毒理解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整个科学界进行研究的模式发生了变化,更像是一个社区在协同工作。赖斯说道:“这真的在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使它更像是一个社区的努力,而不是多年前可能由少数几个实验室孤立地进行的研究。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年轻病毒学家们拥有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工具和能力,能够理解病毒生物学和宿主反应的情况。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不过,经过对病毒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对于一个问题始终没有确切的答案:病毒究竟是“活的”还是“死的”?曾经担任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的病毒学家埃尔林·诺尔比(Erling Norrby)在《诺贝尔奖与生命科学》(Nobel Prizes and Life Sciences)一书中写到,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到对生命的确切定义。我们通常认为生命是一个(自我维持的)可复制的化学系统。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一个生物实体,例如病毒,是否会参与达尔文式的演化?答案非常明显,病毒确实在进行着活跃的演化。
疫苗的演化之路
相比于人类对于病毒的研究,疫苗作为一种预防感染疾病的手段,在人类社会中已经有了至少数百年的应用。最晚到15世纪,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人群就已经开始有意让健康人去接触天花病毒,从而避免感染。
英国医师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免疫学的开创者。在1796年5月,他用从一个挤奶女工的牛痘疮中采集到的物质接种了当时只有8岁的詹姆斯·菲普斯。在接种后尽管菲普斯出现了局部反应,并有几天时间感觉不适,但随后便完全康复。到了1796年7月,詹纳又用从人类天花疮处采集的物质为菲普斯接种。而菲普斯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接种天花疫苗的人。随后詹纳利用拉丁语单词“牛”(vacca)创造了“疫苗”(vaccine)一词。
到了1872年,巴斯德制造出第一款由实验室生产的疫苗:用于鸡的禽霍乱疫苗。时至1885年,巴斯德为了拯救一名被疯狗咬伤的9岁男童,冒险使用了一种只经过动物试验验证的治疗方法:他直接将狂犬病毒注射到人体内,而且在整个13针的疗程中每一针注射的病毒剂量都要更大。接受这种疗法的病人约瑟夫·迈斯特( Joseph Meister)居然活了下来,并且在后来还成为巴斯德墓地的守墓人。
进入到20世纪之后,随着人类对于细菌和病毒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疫苗被研制出来。为了应对1918年首先在美国军队中流行开来的大流感,开发出一款流感疫苗成为美国军方的当务之急。美国陆军学院在1918年测试了超过200万剂的流感疫苗,但是效果并不明确。
时至1937年,泰勒与合作者在《实验医学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上发表论文,报告发展出一种“17D菌株的减毒病毒”(17D strain of attenuated virus)可以被用作活疫苗。这种疫苗最终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黄热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可以导致身体多个器官受损,并且出现严重出血。肝脏也会因为黄热病受到影响,最终导致黄疸。这种疾病的名字正是由其症状而来。数百年来,恐怖的黄热病都困扰着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它的传播方式一直是一个谜。人类对其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根据诺尔比的描述,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才开始逐渐理解黄热病的病因和传播方式。在1900年,由美国陆军医生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领导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人类志愿者证明了黄热病并不是通过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进行传播,而是存在一种蚊子载体——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它在疾病的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里德随后证明引发黄热病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细菌防护滤器。科学界最终才确认,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病毒。
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人类开始理解,黄热病毒的天然存储库是猴子,病毒通过生活在丛林之中的蚊子传播,偶尔也会由受感染的猴子传播给人类。但是如果受到感染的人进入到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黄热病毒则会通过蚊子开始人传人。
拥有热带医学和卫生学文凭的泰勒在1922年进入哈佛医学院进行研究。在研究者从猴子体内分离出了黄热病毒之后,泰勒成功地在老鼠大脑中进行了黄热病病毒的繁殖——这为进行黄热病研究提供了一种简单且相对低廉的方法。也正是凭着这项成就,泰勒在1930年进入了当时黄热病研究的中心——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在1935年到1937年间,泰勒与合作者们测试了具有各种属性的不同病毒菌株在不同种类的组织培养中经过数百次传播的结果,并且反复测试其对神经的活性,最终发现了一个既没有内脏效应也没有神经效应的病毒变种。泰勒与合作者们最终成功发明了名为“17D”的减毒活疫苗——这种疫苗不仅安全,而且能够提供长时间的免疫保护,对于预防和控制黄热病的暴发和传播都有重大意义。巴西在1938年首先对这款疫苗进行现场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诺尔比整理了诺贝尔奖的档案记录,从而梳理出泰勒最终获奖的过程:泰勒在1937年首次因为对黄热病的工作被提名,提名者是罗伯特·科赫传染病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 for Infectious Diseases)的微生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克莱内(Friedrich Kleine)。但当时诺贝尔委员会认为泰勒的工作没有足够的原创性。泰勒下一次被提名诺贝尔奖是在1948年,提名者是曾经与泰勒同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的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第三次被提名是在1950年,这一次的提名者是西班牙医生安东尼奥·纳瓦罗(Antonia Navarro)。此时泰勒的工作已经基本被诺贝尔委员会所认可。再等待一年之后,泰勒终于在1951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相比于其他的很多获奖者,泰勒在10多年间只获得三次提名便获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黄热病疫苗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积极效果。
疫苗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注重实效和安全性,而诺贝尔奖在评选过程中更看重“发现”和“原创性”。在整个20世纪,泰勒都是唯一一位因为疫苗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要再过72年,在又一场世界性瘟疫大流行之际,才有今年的两位科学家因为开发出mRNA疫苗而获得诺奖。因为其保密性,起码要再过50年,人们才能了解本年度诺奖的提名和讨论情况。相比于黄热病疫苗,mRNA疫苗的技术更先进,应用前景也更广阔,料想在评奖讨论过程中并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经过了对于病毒逾百年的研究,以及为了对抗病毒而开发出的种种疫苗和其他医疗手段,人类对于生命的定义在不断变化,对生命的理解也越来越广阔。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诺奖组委会(Nobel Assembly)成员伊利亚斯·阿尼尔(Elias Arnér)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达了他对于生命的看法。阿尼尔认为,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在“生”与“死”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生命体之中包含着非常非常多的化學反应。在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大量的化学反应。从这点来看,我们所说的生物其实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因为一切都在与周围的一切发生着相互作用。这也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有着宗教色彩的想法,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万物有灵”。这就是解释生命现象的一种哲学看法。当然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复杂性。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一个更大存在的一部分——这样的看法可能具有一定的冒犯性,不过在很多的哲学家眼中确实如此。
100多年以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所记载的远不止人类对于病毒和疫苗的研究,而是见证了人类在整个医疗科学领域的巨大进步。正如阿尼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从诺贝尔奖的历史中,我们能够发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社会的变化。不仅是科学界,而是整个社会对于医学、生物化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发展的关注,它们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与100多年前相比,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众多的新技术、更多的治疗手段,以及对于整个宇宙的深刻理解。没有科学进步,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正是科学的进步奠定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就像诺贝尔希望的那样,科学进步造福了整个人类社会。从现在之后的100年,我希望科学研究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人类社会也能够更加进步。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足够理智、正确地运用科学技术。”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苗 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