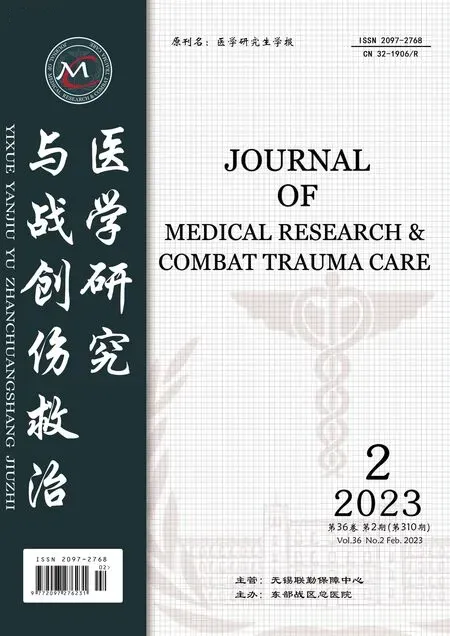IL-6在相关疾病中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张锦鹏,王颢典,任华建综述,任建安审校
0 引 言
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与炎症相关的多功能细胞因子[1],由多种类型的细胞产生,可以调节全身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如诱导分泌免疫球蛋白、激活T细胞、诱导分泌肝急性反应蛋白及刺激红细胞生成,此外,还可促进中性粒细胞分化、活化或骨细胞,促进角质细胞、肾小球细胞生长,诱导ACTH合成,结合HBV包膜蛋白等。
目前已知IL-6在手术、外伤、感染、应激反应等情况下产生迅速、半衰期短、敏感性高,此外,其作为重要的炎性因子,其表达失调可引起代谢性疾病、肝及肠道炎性疾病、脑部疾病、骨质疏松症及肿瘤等[2]。因此,其在临床疾病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近年IL-6在相关疾病中的作用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提供研究参考。
1 IL-6的概述
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科学家岸本忠三发现T细胞上清液可刺激B细胞产生抗体,称为B细胞刺激因子(B-cell stimulatory factor 2,BSF-2)。以及促进肝细胞急性时相蛋白质合成的称为肝细胞刺激因子(hepatocyte stimulatory factor,HSF)。1986年干扰素β2在成纤维细胞中被发现,并鉴定出与BSF-2、HSF[3]、杂交瘤-浆细胞瘤生长因子[4]为同一种物质,岸本实验室克隆出来其cDNA后[5],在1988年正式命名为IL-6。
人IL-6基因定位于第七号染色体上,IL-6是一种由184个氨基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21 000的糖蛋白,可由巨噬细胞、T细胞、B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肾小球系膜细胞及若干肿瘤细胞等多种细胞合成[6]。
IL-6相关受体可分为两种:膜连接受体(mIL-6R)及可溶性受体(sIL-6R)。IL-6R由一个IL-6结合受体分子(IL-6Rα链)和一个信号传感器gp130(IL-6R β链)组成,它在IL-6细胞因子家族中是共用的。IL-6/IL-6Rα链复合物与细胞膜上的gp130相互作用,引起细胞内信号转导,称之为经典途径[7]。然而,经典途径中需要细胞的表面同时表达IL-6Rα和gp130,所有细胞都表达gp130,但只有白细胞、肝细胞等少数细胞表面表达IL-6Rα链[8]。
IL-6Rα的可溶性形式sIL-6R由蛋白酶和金属蛋白酶结构域1·蛋白17(ADAM17)酶解产生,并广泛存在于血清中[9]。所有体细胞均有gp130表达,因而IL-6Rα链(-)gp130(+)细胞可通过血清中的sIL-6R接受IL-6刺激,参与细胞内信号转导。这种IL-6的作用模式通过细胞因子-可溶性受体复合物作用于靶细胞,被称为反式信号模式[10],此为IL-6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通过这一途径,IL-6可以在sIL-6R存在的情况下,刺激体内的任何细胞[11]。这种信号传递模式扩大了对IL-6有反应的细胞的范围,包括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等,这解释了IL-6作用于多种细胞和组织以发挥多效性功能的机制之一。事实上,这种模式在慢性炎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在表达IL-6α的细胞中IL-6活性通过经典途径介导,而在仅表达gp130的细胞中,通过反式信号模式介导。
近年来人们研究发现第3种IL-6信号通路,称之为IL-6的反式呈递作用,当抗原特异性树突细胞和T细胞相互作用时,树突细胞提供激活通路的信号,而后T细胞被激活,表现出对组织的高破坏性表型。
利用人类炎症疾病或炎症相关癌症的动物模型,研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相关癌症主要由IL-6反式信号模式驱动,而IL-6的抗炎与保护再生活性是由经典途径介导的[13]。
2 IL-6在代谢性疾病中的作用
IL-6家族细胞因子在代谢中至关重要,最初研究认为,IL-6会导致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抵抗。gp130信号通路的激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有害的,可导致代谢、肝和胃肠道疾病,如肥胖、慢性肝损伤。
然而,IL-6并不是单方面导致胰岛素抵抗,还有可能对于代谢有益。IL-6在运动过程中可从骨骼肌中释放,而胰岛素的作用在运动后立即增强[14],这就表明过度表达人类IL-6的小鼠则表现出胰岛素敏感性增加,并能抵御饮食诱导的肥胖和相关的全身炎症[15]。而IL-6-/-小鼠出现肥胖、肝炎症和胰岛素抵抗的验证性观察进一步证实了IL-6可能具有有益作用的观点。肥胖患者中脂肪组织释放的IL-6可导致肝胰岛素抵抗和炎症。然而,肌肉释放的IL-6增高了GLP-1的水平与活性,从而改善了小鼠和人类的β细胞功能和葡萄糖稳态[16]。
此外,脂肪细胞来源的IL-6在没有胰岛素耐受性主要变化的情况下促进脂肪组织巨噬细胞(adipose tissue macrophages,ATM)的积累,而髓系细胞来源和肌肉来源的IL-6抑制m1样巨噬细胞极化和ATM的积累,改善胰岛素耐受性,这些相反的作用与IL-6信号从经典模式(髓系细胞)到跨信号模式(脂肪细胞)的转换有关[17]。综上所述,IL-6产生的来源和信号转导模式决定了IL-6在代谢中的生理作用。
3 IL-6在肝疾病中的作用
在肝中,IL-6家族参与肝的稳态机制,包括病原体根除、肝再生、急性和慢性肝炎症以及肿瘤的起始和进展等过程。IL-6快速产生有助于宿主在感染和组织损伤期间的防御,但过度的gp130受体信号通路的合成和失调与疾病病理有关。
研究发现,IL-6基因敲除小鼠与野生型小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IL-6基因敲除小鼠在在肝切除术后,其肝不能再生,这与IL-6在参与肝再生中发挥着激活STAT3,限制炎症反应,触发肝细胞的增殖与再生的研究相符合[18]。
而长期暴露于IL-6可促进肝糖异生肝胰岛素抵抗[19]。肝胰岛素抵抗和脂质代谢受损的存在通常与高IL-6水平相一致,这支持了慢性IL-6信号传导发挥促炎作用的观点。一项在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小鼠模型中进行的研究表明,通过抗IL-6Rα阻断IL-6信号通路可增强脂肪变性,但可减少炎症的迹象[20],可以支持IL-6反式信号通路在炎症中的作用。
减少IL-6的治疗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病发生期间的肝脂质含量,这种现象的观察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概念[21]。IL-6家族细胞因子在急性和慢性肝病中调节炎症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在急性炎症模型中经常作为抗炎细胞因子,在慢性肝病中发挥促炎作用。
长期的IL-6细胞因子在慢性肝炎症中起着关键作用,其高表达会刺激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发展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IL-6、IL11、OSM、LIF和IL-27被认为是人类炎症与纤维化和癌症之间的关键调节因子。在实验模型和人类中,IL-6是IL-6家族中参与HCC发展的最典型的细胞因子。在晚期HCC患者中,血清IL-6水平的升高与不良预后、生存和复发相关[22]。
4 IL-6在肿瘤疾病中的作用
在癌症的发展过程中,目前认为只有5%~10%的癌症是由遗传基因缺陷引起的,其余90%~95%的癌症起源于与慢性炎症密切相关的环境和生活方式[23]。因此,与肿瘤的发生本质上由肿瘤前细胞触发的观点不同,环境因素,如感染、压力、肥胖、衰老和吸烟,每一种都可以诱发慢性炎症,可能是肿瘤发生的主要原因[24]。
研究发现,炎症因子IL-6与肺癌、结肠癌、肝癌等多种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23]。在肿瘤的生长过程中,尤其是实体瘤,其血管的形成与肿瘤关系密切,Nilsson等[26]报道IL-6在体外可趋化血管内皮细胞,在体内可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另有Dalwadi等[26]报道IL-6作为COX-2的执行者可促进血管的生成和肿瘤的生长。Naugler曾经研究过,通过应用雌激素控制IL-6的高表达来预防男性肝癌的发生[27]。
IL-6可通过刺激STAT3通路,成为许多癌细胞的重要生长因子,甚至在一些类型的癌症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胰腺癌的研究中发现,STAT3通路的大量激活导致肿瘤进展,是由肿瘤浸润骨髓细胞诱导的,它通过IL-6反式信号通路刺激肿瘤细胞。通过sgp130Fc蛋白选择性阻断该通路,可阻断胰腺上皮内瘤变向胰腺导管腺癌的进展[28],表明IL-6反式信号通路在胰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小鼠APC中min/+在结肠癌模型中,ADAM17基因缺失不仅产生sIL-6R,还产生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的可溶性配体,完全消除了肿瘤的发展[29]。此外,肿瘤的形成刺激了巨噬细胞上的ADAM17,导致EGFR配体的分裂,而后刺激EGFR。受到刺激的巨噬细胞会产生IL-6和sIL-6R,从而导致了肿瘤的生长。同样,通过sgp130Fc蛋白选择性阻断IL-6反式信号通路,可以阻断APCmin/+模型和另一种小鼠结肠癌模型中的肿瘤发展[30]。
5 IL-6在慢性炎性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自身免疫性疾病常伴有慢性炎症,又可称为一种自身炎症性反应,如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白塞氏病、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疾病、慢性肾炎等,其发病机制与细胞因子的失调有关[31]。
IL-6通过“反式传导信号”机制诱导STAT3磷酸化[32],STAT3诱导抗凋亡因子bcl-2和bcl-XL,抗凋亡因子阻止炎症细胞凋亡,促进T淋巴细增殖,刺激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导致慢性炎症的发生。炎症性肠病是一种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IL-6/STAT3信号通路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发展有关[33]。靶向阻断IL-6/STAT3信号通路,为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提供了新的思路。
IL-6基因敲除小鼠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症的动物模型中完全受到保护[34],表明IL-6在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自身免疫性疾病被认为是由免疫反应的失调引起的,然而,导致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和其他组织特异性疾病的真正致病性抗原尚未被确定[35]。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自身免疫性疾病并不总是需要对组织特异性抗原的破坏。相反,免疫系统对靶组织的过度激活可能是由非免疫靶组织中的局部启动子[36-37]。
6 IL-6在急性感染中的作用
IL-6是多能炎性细胞因子,能够刺激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增殖、分化并提高其功能,在感染与组织损伤时IL-6迅速生成,通过刺激造血与免疫来促进宿主抵抗感染。其在传递信息,激活与调节免疫细胞,介导T、B细胞,巨噬细胞和破骨细胞等的活化、增殖与分化及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根据2017《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解读专家共识》,认为IL-6在炎症及感染性疾病中,升高早于其他细胞因子,也早于CRP和PCT,可用来作为急性感染的早期诊断。IL-6也可用来评价感染严重程度,并判断预后,当IL-6>1000 ng/mL时提示预后不良。动态观察IL-6水平也有助于了解感染性疾病的进展和对治疗的反应
在稳态条件下,循环中的IL-6水平低至1~5 pg/mL,但在炎症状态下,这些水平可上升1000倍以上,在极端条件下导致脓毒症的IL-6水平在μg/mL范围内[38]。IL-6是由髓系细胞在toll样受体刺激下与细胞因子IL-1β和TNF-α共同产生的,它们通过一个前馈回路,导致炎症条件下IL-6产生的巨大扩增[39]。人体体内可能没有其他蛋白质的水平可以上升6个数量级。因此,IL-6是人体对感染、炎症和可能的癌症的反应的主要警报信号[40]。
细胞因子的浓度增加并引起各种炎症因子瀑布式释放,会引起组织细胞损伤。研究表明,肺炎初期感染侧IL-6和IL-10浓度明显高于非感染侧。细菌侵入下呼吸道后,其本身及分泌的内毒素激活肺组织局部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及上皮细胞,使之分泌IL-6以及“早期反应细胞因子”TNF-α和IL-1β,TNF-α和IL-1β,从而又进一步刺激上述细胞分泌IL-6以及其它促炎因子,从而使IL-6在局部组织的浓度增高,导致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IL-6的浓度增高。重症肺炎患者BALF中的IL-6、IL-10、TNF-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IL-6、IL-10、TNF-α在肺部感染中有重要意义。Zobel等[41]的研究提示:典型的细菌性感染可导致较高的IL-6和IL-10浓度,IL-6浓度可反映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且死亡组患者血液IL-10等细胞因子浓度显著高于存活组,并呈增高趋势。
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2019)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已成为一种大流行。其严重可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42]。ARDS是一种由肺炎、脓毒症和创伤性等机械损伤和感染引起的致命综合征[43],其也被认为是细胞因子风暴的结果[44]。快速进展的炎症伴随着大量的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的产生,这一观点支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的观点[45],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严重程度与炎症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相关,如IL-6、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TNFα[46]。
7 白细胞介素-6活性的治疗性靶向性研究
随着IL-6与各种疾病相关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已有约数百种相关药物进入临床。其药物作用原理主要依据IL-6与受体的结合方式。
7.1阻断IL-6R结合IL-6R达到阻断IL-6信号通路的药物有托珠单抗和sarilumab,此类药物竞争性结合IL-6及其受体相结合的表位,对IL-6通路中的经典途径和反式信号通路均有抑制效果[47]。
阻断细胞因子IL-6的生物活性被证明是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并在一项单药治疗试验中显示,阻断IL-6活性比阻断TNFα更有效[48]。通过中和性单克隆抗体托珠单抗阻断IL-6已在100多个国家被批准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31]。
此外,用IL-6R中和单克隆抗体托珠单抗阻断IL-6活性在治疗CAR-T细胞诱导的严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患者中也非常有效[49]。当癌症患者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时,遇到的细胞因子风暴[50],可以用抗体托珠单抗有效治疗。最近,人们已经认识到,许多患者在感染SARS-CoV-2(COVID19)病毒时也会经历类似的细胞因子风暴[51],这些患者也可以用托珠单抗来治疗[52]。
7.2阻断结合位点此类药物通过靶向阻断IL-6与IL-6R或IL-6-IL-6R复合物与gp130的结合位点达到阻断IL-6活性的目的。如单克隆抗体司妥昔单抗(siltuximab)已经被批准可用于治疗Castleman病[53],而对于其治疗其他疾病的临床试验仍在进行中。
7.3拮抗IL-6/sIL-6R复合物在sgp130Fc蛋白和中和单克隆抗体的帮助下,可以分别选择性地阻断IL-6反式信号传导或阻断所有IL-6信号传导。研究表明,使用特异性抑制IL-6/sIL-6复合物所介导的反式信号通路而保持原有的经典通路时,IL-6R在机体抵抗细菌[54]、脓毒症时肠道再生[55]、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中防止主动脉破裂[56]和骨折愈合[57]等方面,sgp130Fc蛋白按照GMP的调控规律进行表达和纯化。I期临床试验成功地在健康个体中进行,II期临床试验目前正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进行[58],这表明这些重要的过程在IL-6的整体活性受到阻滞时严重受损[59]。
还有诸多药物通过如阻断STAT、阻断Janus激酶、拮抗gp130等方式来抑制IL-6的生物学效应,仍有许多药物正在研究中,随着人们对药物安全性的重视以及不断深入的基础研究,未来有希望在治疗基础疾病的基础上研发从出具有更高安全性的IL-6信号通路选择性抑制剂。
8 结 语
在正常情况下,IL-6的水平非常低,但在病理状态下,其反应迅速,水平会增加数千倍。如今对IL-6浓度变化的监测已经广泛被应用于临床工作之中,可早期诊断疾病,动态监测IL-6浓度也能判断患者的预后与转归。
对于抗IL-6治疗,IL-6反式信号可以被sgp130Fc蛋白阻断而不影响经典信号,未来基于IL-6的治疗更可能使用IL-6反式信号的特异性阻断,而不是所有IL-6活性的阻断。在保持经典信号完整的同时阻断反式信号,被证明对经历COVID19或CAR-t细胞治疗的“细胞因子风暴”的患者有益[60]。同样,这种这种治疗方式能否更好地保留IL-6的抗炎活性,使得其在感染、代谢性疾病以及慢性炎症性疾病中更多得发挥其对身体好的作用;其是否可以抑制高水平的恶性肿瘤等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