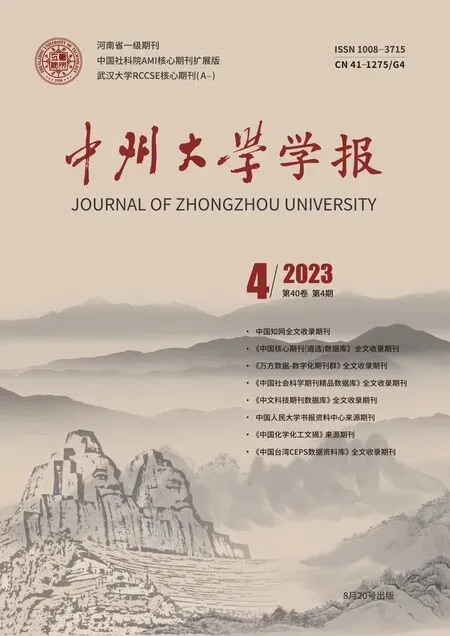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及其影响
李 优
(沈阳音乐学院 民族声乐系,辽宁 沈阳 110818)
在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演唱往往融为一体同步发展。这种情况从先秦时代“诗三百”即已开始。发展到唐诗宋词时代,文学与音乐融合发展的情况仍突出地存在。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唐代是古代诗这一文学体裁的高峰期,宋代是古代词这一文学体裁的鼎盛期,而唐宋时期也是音乐演唱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因此,无论从文学史还是从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史的角度看,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表现和形成原因,总结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相关的理论和规律,以便为当今音乐演唱汲取古典文学精华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唐诗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基于对诗歌体裁表达方式的考察,探讨唐诗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时至唐朝,文学领域的诗仍有很大一部分是要通过音乐演唱的方式实现表达和传播的[1]。显而易见,此时的诗通过音乐演唱予以表达是对此前诗歌表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先秦时代的“诗三百”,到汉魏六朝乐府诗和南北朝乐府诗都是配乐演唱的。但是与此同时,诗的表达也在另一条发展道路上谋求发展,即逐渐脱离音乐演唱向格律诗方向推进。这条发展道路起始也较早,从汉朝起,我国就产生了五言诗和七言古体诗,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又出现了“声律说”等关于诗格律方面的创新与改革,并因此逐渐形成了近体诗。近体诗在表达方式上与其前诗歌的最大区别是,诗不必通过演唱加以表达。律诗发展迅速,到了唐朝就成为当时文学的主要体裁,甚至唐朝诗人通过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题所创作的诗,也都不再通过演唱加以表达[2]。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等于说唐朝的诗已经完全与音乐演唱分道扬镳,事实上,仍有很大一部分采用音乐演唱的方式进行表达,尤其是唐诗中的很多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它们不仅大都可以配乐演唱,甚至其中很多作品是特意为音乐演唱而创作的。这种特意为演唱而写作的唐诗,即“唐人乐府”。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唐诗用于音乐演唱的那些名为《阳关曲》或《杨柳枝》的五言、七言绝句,其名称还大多作为词的调名而流传下来,刘禹锡的《杨柳枝》即是此种情况的典型例证。另外,学界许多学者为了证明唐朝时期还有很多诗是通过音乐演唱表达,他们更愿意举出唐代文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记载的“旗亭画壁”故事。这则故事很好地说明,在诗风日盛的唐朝开元年间,不分朝野无论官民,人们都喜欢吟诗唱诗,而当时很多名气颇大的诗人如王之涣、高适以及王昌龄所创作的诗,也大多是供人歌唱的歌词。易言之,唐诗有一部分是作为歌词创作并通过音乐演唱加以表达的。
唐诗与音乐的融合发展还体现在唐朝文人所创作的词。因为在唐朝人观念中,词是“诗余”。词作为一种新文体肇始于隋朝,起源于俗世民间,并逐渐形成模式,引得许多文人创作,便逐渐演化为诗歌中的一个种类或者一个分支。词因为是伴随着音乐的歌词,所以又有很多其他的别名,如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3]。词到唐朝以后逐渐走向定型化,许多文人也热衷创作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中唐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翃,据说他在怀念失散的小妾柳氏时曾写过一首《章台柳》,这首词的词牌原本叫《潇湘神》,然而韩翃依照这个词牌填写的《章台柳》感情深沉、意境婉丽,因此后人反倒将原来词牌《潇湘神》弃之不用,而把《章台柳》作为词牌名。尽管这是个故事,也能说明当时依照乐曲格式的词牌写词的风气已然在诗人中兴起。而且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其时张志和、韦应物和戴叔伦等诗人,在填写歌词方面都是佼佼者。尽管中唐以来文人按词的曲调进行词创作的文学活动比较普遍,但当时他们填词所使用的曲调,亦即后来的词牌数量,却极其有限。根据相关统计大概只有《一七令》《忆长安》《调笑》《三台》等十几个。唐朝文人的这种热衷填词的活动,造就了当时文学与音乐的融合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晚唐温庭筠这样卓有成效的词人[4]。温庭筠的词成就巨大,即便从现存的近70首词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出类拔萃。他填写过19种词牌曲调,而且其创作的词大都脍炙人口,广泛传唱,他在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方面成就不俗。
唐诗与音乐融合发展的成就,以及涌现出像张志和、温庭筠这样一些推动词与音乐融合发展并卓有成效的文人,这除了表明其时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外,也使得宋朝的词乘势而上,创造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繁荣期。
二、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
词发展到唐朝的中后期以后,势头劲健,到宋朝时便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达到发展顶峰的文学体裁。宋代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写词,叫做“填词”或“依声”。词的原形态实际是诗,从这个角度看,词其实是为了配合音乐而形成的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既然是诗的一个种类,创作词自然也要讲求意境、韵律和对仗词采等。但是词与诗更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通俗的大众文学艺术形式,而诗则是一种高雅的文人阶层的文学艺术形式。正因为这样的区别,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首先表现在把词这种文体,推广到社会的下层,并在那里得到广泛传唱。
由雅入俗,把高深典雅的作品转化成能够被大众接受的艺术,是很值得称颂的文化功绩。在宋朝,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文人需要把文学转化成文化商品以换取生活资源,宋词就成为当时许多像柳永一类文人的选择。如前所述,词出身低微,起于民间,再加上这一文体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时候,主要被当做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文学佐料,所以在传统的观念中词是“小道”,属于“艳科”,“诗庄词媚”烙印深深,尽管词在后来的发展中,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做出提升,又被辛弃疾等一些杰出作家提升到表达爱国情怀等同传统“诗言志”的高度,成为与诗歌地位完全等同的文学体裁,但是词与生俱来的低俗特征,以及可以被俗世大众接受的品质,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在宋代,柳永等词作家便把词普及向俗世大众,并在与音乐融合发展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柳永是宋代将词进行通俗化并传播到大众层面的最典型作家。他因为钟情追求华丽辞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抒发,写了许多缠绵婉约的爱情词而被宋仁宗所知,所以在参加科举考试时直接被皇帝取消了录取资格。这也使得他从此便把大部分人生流连在歌坊青楼之间,把给歌妓们写词唱词作为谋生的核心工作,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写出了很多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词。他不仅靠着给底层歌妓写词支撑自己的生活,还把词与音乐演唱融合予以通俗化努力,他的词普及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程度。他的词被广大的市民阶层所接纳,实现了世俗文学与音乐演唱的完美融合。
在宋代比柳永还早一点、创造婉约词并卓有成效的是晏殊。他的词也影响到自己的儿子晏几道,父子俩的词也大都在民间广泛传唱,做到了词与音乐演唱的高度融合。除此之外,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更是在“词别是一家”理论支持下,创作了一大批婉约词,其作品也广为传唱,使她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女词人。这样,自柳永以来到李清照的一批词人,所创作的那些既含有深刻意境,又带有深情厚谊的词,因为与音乐演唱完美融合,体现出高度艺术性,并为大众喜闻乐见。这对于当时文学与音乐演唱的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因为宋词艺术家的努力,雅致的词作品又能够进行通俗化的艺术处理,尤其是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遂被底层大众所接受。如柳永的《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等词句,不仅婉转绮丽,声情并茂,而且感情率真,语言质朴自然,意境雅致细腻,这样的辞章,配上悠扬婉转凄清悠长的曲调演唱,必定为广大的俗众所喜爱;与此相近,他那首《八声甘州》,语浅而情深,融写景、抒情为一体,通过描写羁旅行役之苦,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写尽了古代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感受,同时也仍能够与普通大众的思想情感产生共鸣,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在配乐演唱之后,成为千古绝唱。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写清秋时节的新婚小别,为排遣愁怀独上兰舟,西楼望月而恨雁来无书,然后用“花自飘零、水向东流”比喻无由消除的两地相思,呈现出婉约清新的格调、优美的意境和工致精巧的艺术性。尽管这首词出自上流社会知识女性,但其词却不加雕饰,明白如话,在配乐演唱之后,也能够为广大受众所接受。
宋词和音乐演唱关系更为密切,宋词是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更具典型意义的文学体裁。这一点在有宋一代婉约派的词上有充分的体现。柳永之后,有秦观、周邦彦等在词创作的作风和主题体裁等方面,继承了婉约派[5]。其中,周邦彦的词格律精严、风致醇雅。其规范化的格律表现与技巧的纯熟,使得时人无出其右。他不仅是当之无愧“词林正宗”,还成为集婉约派之大成的作家,同时他的词在与音乐演唱融合方面更臻于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并不止于婉约派词人,在豪放派词人那里,也有同样的表现。在宋代,因为苏轼的出现,打破了宋词领域婉约派一派独尊的格局,他以《东坡乐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窠臼,写出了一系列黄钟大吕瓦釜雷鸣般的词,开辟出词动人心魄的另一空间,拓展出宋词的另一流派“豪放派”[6]。该流派的词大多不再抒发离愁别恨儿女情长,也抛弃了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风格基调。尤其是在主题题材方面,凡怀古咏史、说理谈玄、议论时事均可入词。苏轼以及当时追随者对词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获得了许多词人的积极追随,如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苏门四学士为代表的响应者。这些人在此领域的创作成就,开辟出宋词的另一条战线。到了南宋,词风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李纲、张元干等写出了一大批爱国词,稍后则有辛弃疾,他以踔厉风发的积极心态,写了大量激情荡漾、气吞万里的爱国词。步其后尘的则有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辛派词人,而陆游作为一个同时代的爱国诗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宋词发展过程中,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一直若影随形且更为密切。词本来就是歌曲的一种,是合乐演唱的歌词,词被称为曲子词、乐府、乐章、琴趣等别名,也凸显着它跟音乐演唱的天然关系。这决定着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有着天然的基础和优势。
宋人作词,词必依照词牌填写,词牌就是词调,词牌名称决定着词的格式和演唱曲调。如《雨霖铃》和《水调歌头》,因为词牌不同,其演唱曲调自然也就不同。所有的词都是按照具体词牌规定的曲调进行演唱的。
三、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
唐诗宋词作为古代文人抒发感情的方式,其美感效果不仅在于表达自己的志向情怀,同时,还能引发别人的共鸣,诗词的用典对偶等修辞形式和韵脚平仄变化,也能使感情的表达变得更丰富细腻或动人心魄,在此基础上,诗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更因为音乐节奏和乐器的配合,以及演员演唱声调和技巧等艺术因素的参与,使得诗词作品动人心扉,其传播效果也更加突出。音乐演唱推助了诗词表达和传播方式,也正是由于音乐演唱的融入,古典文学中的唐诗宋词,不但在当时获得广泛传播并造成深刻影响,同时也得以流传后世,传唱不绝[7]。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方兴未艾。当代的音乐演唱也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今音乐演唱领域对于唐诗宋词的借鉴和萃取,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当下许多歌曲创作和音乐演唱特别注重借用和借鉴唐诗宋词的内容和意境,往往取材于唐诗宋词,或者将整首诗词纳入歌曲中,或者截取其中的名段佳句,或者在诗词的启发下加以创作。台湾的琼瑶和大陆的陈小奇就是采取这类歌曲创作形式的代表者。琼瑶的歌词创作惯于将唐诗宋词入歌,作为其歌词的核心内容,如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等。李清照那些描述少女情愁的词非常适合琼瑶塑造的古典型婉约淑女形象,歌词演唱所形成的氛围也有助于作品人物的情感表达;陈小奇是当下流行歌曲创作阵营中岭南一派的领军人物,也是颇有影响的歌手,他所创作并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廖百威演唱的《白云深处》和李进演唱的《巴山夜雨》,都是以唐诗作为核心内容和歌曲境界的,仅从歌曲的名称就可看出它们对唐诗思想意境的继承与创新。第一首歌词是以唐人张继《枫桥夜泊》为基础的拓展和创新,第二首则是对杜牧《山行》一诗的演绎和展开。陈小奇的贡献在于把唐诗的语句世情化、 感情化和烦琐化,而《巴山夜雨》的歌词则是摘取李商隐《夜雨寄北》第二句,然后予以化用,借助诗歌两地相思的意境来表达歌曲的主题。此外,陈小奇还曾创作了由吴涤清演唱的《烟花三月》《朝云暮雨》,以及由毛宁演唱的《大浪淘沙》,其中也明显有着对唐诗宋词思想境界的继承与创新,并以此表现当下人们的悲欢离合和人情冷暖,由此形成唐诗宋词进入流行歌曲的创作模式,形成作者独特的风格,为唐诗宋词融入当今流行歌曲创造了很好的样板。 其次,当今音乐演唱领域的歌词创作中盛行以唐诗宋词名句或诗词作为流行歌曲名称的热潮,比如内地校园歌手刘海波所演唱的《人面桃花》,就是从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相映红”中化出的歌曲名称;白雪的《声声慢》则是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采取的歌名;而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的歌名,则是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摘取,陈明演唱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演唱的《梦回唐朝》《月梦》等歌曲名也都基于唐诗宋词,尽管这些歌曲的名字不一定完全是唐诗宋词的原句,但其中的思想和境界情怀却毫无疑问源自唐诗宋词。最后,央视综合频道重点打造的大型音乐文化季播节目《经典咏流传》,进一步凸显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对今天音乐演唱领域的影响。该节目从2018年的第一季到2022年的第五季,历时四年,其中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每一季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并在央视文化综艺扎堆的情况下,同一档节目仍然能持续保持高热度。这也进一步说明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力。节目中谭咏麟演唱的《定风波》、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以及汪苏泷演唱的《少年狂》等歌曲,它们都体现了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总之,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不但在当时创造了文学结合音乐演唱艺术的辉煌,而且对今天流行歌曲创作和演唱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通过继承和创新,很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音乐演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