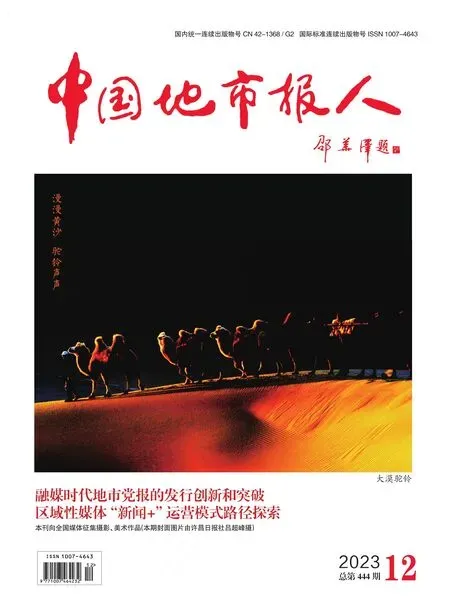纪录片中景观叙事与影像表达分析
——以《伊犁河》为例
杨 乐 游盛运
新疆广播电视台2019年制作的纪录片《伊犁河》,获得“第25届中国电视纪录片系列十佳作品”,该作品共分为六集,它以“共生”为主题,讲述了伊犁河两岸百姓生活发展和变化的故事。
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如何叙事,如何讲好关于人的故事,以及对现实非虚构化的表达,往往是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关键。《伊犁河》之所以能够赢得好评进入十佳作品,与它清晰的影像表达与流畅的叙事策略不无关系,它巧妙地将人物命运与一条河流连接起来,在中华文化中河流是一切的发源地,生活在美丽的伊犁河畔,各族群众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汇聚在一起,在伊犁河的哺育下繁衍生息。
一、自然景观参与叙事
自然景观包括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生物景观及天文景观。纪录片这种独特的艺术展现形式不仅可以通过自然景观优化叙事模式,也可以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出普罗大众的生存方式,原汁原味地体现出不同地区下不同民族的生活状态,赋予其独特的社会以及人文价值,积淀时代影像信息,彰显独特的艺术魅力。
新疆地区自然景观包罗万象,冰峰与火洲相望,沙漠与绿洲为邻,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在《伊犁河》《沙漠人家》《塔里木河》等一系列纪录片中均有体现,这些影片在展现新疆独特的自然风貌的同时也讲述了新疆故事,在塑造新疆形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景观的运用
自然景观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审美元素,陶渊明凭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现对世俗的看法,王勃手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千古绝唱,自然景观都直接参与了构建文学作品的审美空间,成为文学审美的意象之一。在影视作品中,故事的构建同样与景观无法分割,自然景观的呈现可以赋予故事一定的文化空间与历史意义,因此在影视作品中景观的出现不再仅仅是一个“背景”的出现,它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去贯穿整个叙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自然空间重要意义,景观也不再只是作为简单的画面出现,而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它是讲述者,更是推动故事发生的参与者。纪录片《伊犁河》将跨过雪山的雄鹰,草场上奔驰的骏马尽收其中,展现了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为新疆形象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空镜头推动叙事发展
记录生活,观照现实,是纪录片创作的初衷。在影片《伊犁河》中,为了使叙事更加流畅,每集影片伊始都会插入广阔的天空、广袤的草原山丘,以及奔流不息的伊犁河。在第一集《以梦为马》中,克德尔可西生活的昭苏草原,被誉为天马故乡,春天,克德尔可西一家开始向春牧场迁移,镜头切入奔腾的马匹、成群的羔羊,它们穿过河流,走过草原来到牧场,虽然辛苦却也是新的开始。同系列纪录片《沙漠人家》中导演在影片开头便用镜头俯瞰沙漠,崎岖不平的道路,稀稀疏疏的草木,几个镜头便将整部影片中的自然环境交代清楚,使得观众对于该地区的自然风貌一目了然,使观众迅速进入实景模式,交代时间和地点的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展开对故事情节的期待。
二、人文景观的构建
传统聚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地区独一无二的景观文化,比如陕北地区的窑洞、贵州的吊脚楼等,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均有所体现。新疆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人文特色,这在新疆系列纪录片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表达。纪录片《伊犁河》中,生活在昭苏草原的克德尔可西一家人世代沿河而居,牧马为生。当地人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养殖天马,这里也被誉为天马故乡。生活在伊犁河河谷周边的养蜂人培育着最香甜的蜂蜜,一路向西,巩乃斯河酿造着西域最烈的美酒,特克斯河与巩乃斯河的汇聚处隐藏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雪岭云杉,从人到自然,都汇聚在伊犁河周围,导演将宏大的自然景观与人类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相互穿插,地貌独特却能与人类和谐相处,相互哺育,展示了当地人民的智慧与独特的人文风貌。
(一)人物形象突出
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推动叙事发展的同时也可揭示人物心理,突出人物形象。在六集的《伊犁河》纪录片中呈现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在面对这些差异时,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该如何选择便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点。在《伊犁河》第一集中,草原上长大的哈萨克牧民努尔泰作为家族里唯一一个三文鱼养殖场渔民,家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但在片段的最后,家人吃到了努尔泰亲手养殖的三文鱼,父亲同意了这份工作。此时的画面切到了这片在山谷的包围下清澈的水域,鱼儿在水中翻滚,河流始终弯曲前行。纵使生活中有许多未知的阻碍如山谷夹击让你的人生道路变得狭窄,可心怀敬畏与坚定,你便有无数种可能。与努尔泰同样年龄的大学生古丽娜木兰,回乡创办服饰公司,将时尚与大自然融入服饰中,充斥着独特的民族元素。在导演的镜头中这个村镇简朴闭塞,没有一线城市的繁华,但却群山环绕,依水而生,从塞北到江南,古丽娜木兰将她所设计的服饰卖到杭州。在最后的镜头中古丽娜木兰穿着自己设计的裙子奔走在伊犁河边,这是人类生存的智慧,伟大的丝绸之路从伊犁河谷中穿行而过,哺育着这里的人们。大奔流不止,伊犁河畔周围的人们也永远向前。
(二)平民化视角
观众既是纪录片的接受者,也是影片审美价值的体验者,一部好的纪录片重点就在于能否抓住观众的心理诉求。《伊犁河》中导演针对不同的场景和叙事主体运用不同的拍摄技巧,在表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得画面也更具张力。
《伊犁河》中对于每一位人物故事的体现都是通过日常的生活场景去展现。将工作场景与个人生活相结合,既能展现人物在面对工作时的认真,也能展现私下个人情感的流露。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个人命运该如何选择,留在伊犁河畔还是去外面的世界,这些都成了影片表达的重点。在《伊犁河》第五集《大河之恋》中,哈萨克少年木拉格尔与牧民婶婶生活在大山中,在拍摄过程中家里的母羊在远处高坡上生下小羊,节目组使用第三视角,跟随着木拉格尔摇摇晃晃跑上山坡,木拉格尔见到小羊后抱紧它亲吻它。如此柔软的少年,与此对应的是木拉格尔需要步行三十公里,才能驱车到达学校。这位哈萨克少年身上既有童真也有坚韧,使观众看到一个少年身上不同的勇气。画面中的伊犁河从大山向外流出,这位哈萨克少年行走在上学的路上,追逐着属于自己的梦……这些画面的呈现更好地为观众传递情感,阐释主题,极大地提高了该影片的观赏价值。
(三)地域文化呈现
在叙事结构上,《伊犁河》充分发挥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表现方式,通过对生活在伊犁河畔不同的人物,去展现在经济以及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当代,不同人物命运的选择,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当地的地域文化。
《伊犁河》的故事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也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因此纪录片中故事的展现也应该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体现出立意。在第五集《大河之恋》中,出自年轻人赛杜拉之手的伊宁最富特色的小吃手工冰淇淋,现已是伊宁市的一张城市名片;出生在霍城草原的非专业舞者加娜提,在汇演时遇到了难题,她回到家乡寻找答案,以舞蹈为起点带出了关于家乡关于哈萨克民族对于唱歌跳舞的热情,他们时时刻刻无法离开歌舞,热情地对待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难题,这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对生活的热爱。伊犁河虽美却也充满着未知的暗流,大河的守护者李僵在伊宁市这片流域救起过许多人,伊犁河养育了他,他守护着伊犁河,无论欢乐与否,伊犁河必须不停地向前奔走,河流的使命是流淌,李僵的使命是做好这条大河的守护者。从系列纪录片《伊犁河》《沙漠人家》中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国产人文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上已逐渐脱离精英化和宏大的叙事模式,在叙事主体中层层递进,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增加情感共鸣与民族认同,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刻洞察,对历史对当下进行思考,构建出有大有小的社会景观,彰显了高度的人文情怀。
三、精雕细琢的解说词
人文纪录片的声音创作理念体现出个性化与叙事化的特征,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建构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人文纪录片愈发重视解说词、旁白以及配乐的使用,使得纪录片内容更具延展性,与画面交相呼应,给予观众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
在纪录片中,生动的解说词、形象的描绘,可以有效地弥补文化的抽象性,起到对场景的渲染铺垫作用,同时更快地将观众带入影片中。在纪录片《伊犁河》第五集《大河之恋》中说道:“水,此时保持着最原始的本真状态急流直下,在跌宕与前进中不断变化,成长、汇集,奔腾而出涌向更广阔的未来。暑假结束,十三岁的木拉格尔和很多牧民的孩子一样,将要去三十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乌拉斯台乡上学,血液里的基因让这个小小少年格外珍惜和大山相处的时间。”这些文字构建起了一个生动具体的意象空间,这位十三岁的少年如同这奔腾而出的河水,在这座大山里不断变化与成长,但最终他也会走出这里,迈向更广阔的未来。解说词将人物环境、生存状态以及人物感受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起到了画面无法替代的“联想”作用。
同时,文学性解说词通过富有音韵感的语言和诗情画意的文字,实现了人文意境的营造和对于文化美感的传播。近些年来,我国人文类纪录片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风味人间》等,其中《如果国宝会说话》经典引入语:“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语言年轻且生动,拉近了观众与国宝的距离。解说词愈发富有情感,它不再是独立于内容的简单客体,而是成为表达情感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在《伊犁河》第五集《大河之恋》中,结尾处说道:“无论你欢乐还是悲伤,它都必须不停向前奔走,河流的使命就是流淌,而李僵却是要做好这条大河上的守护者;少年木拉格尔从山里走出,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以后去读内高班,去踢球,像河流那样有多远就走多远。”人文纪录片更是如此,对于人的关怀以及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往往不是那种宏大叙事类的语言,而是通过细节化、情感化的语言来表达。叙事内容与解说词相辅相成,将小人物的命运与这条河流联结起来,他们不再只是简单的个体,而是千千万万个坚强的、乐观的生活在伊犁河畔的人们。从画面到解说词,将观众带入一个具有美好憧憬的想象空间,使作品内涵得以放大。
总之,在人文纪录片的创作中,解说词“通过文学性吸引大众的视线,饱含哲理、充满激情、触动人心;在愉悦观众的同时,也体现着创作者的文化品格和境界,抒发国人积极向上的情怀与文化追求,充满形象化、审美化、情感化和哲理化的文学性解说词,不仅使解说性语言摆脱了对画面的依附性,有了自身的独特魅力,更使得人文纪录片的人文性和艺术性大大增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人文类纪录片要想动人心魄、广泛流传,还需在解说词的文学性上不断加强审美追求。
结语:
文章通过对纪录片《伊犁河》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人文题材纪录片从自然景观、人物形象、地域文化等视角塑造乡村形象,乡村形象不仅是村民的生活空间,它更加包含着村民淳朴勤劳的精神象征,它鼓励着人们生生不息地向前奋斗。人文纪录片作为纪实影像中的一种,除了真实客观地记录,也在潜移默化中传达着人生哲理和人文内涵,为乡村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媒介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