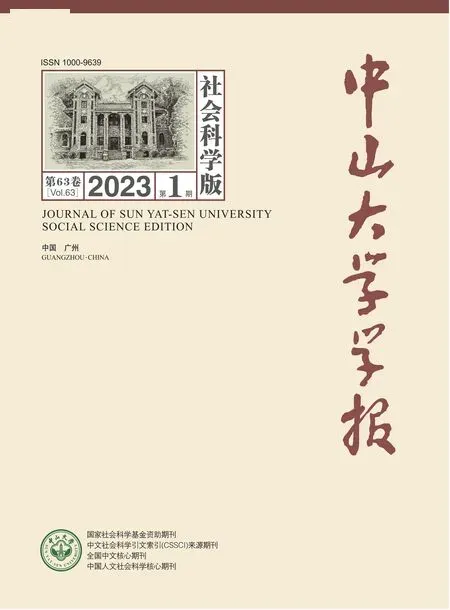富而好德,何必曰利 *
——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权衡关系
刘 乾,陈 林
一、引 言
《孟子·梁惠王上》曰:“何必曰利”。《史记·货殖列传》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而好兴德”。宋代“永嘉学派”提出“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对经济社会的“义利之辨”远远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着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国家治理、企业经营应该如何在经济利益与社会道德之间权衡,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代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一个主流领域——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正发轫于此。
作为营利性的社会经济组织,企业追逐物质利益最大化自古使然,因为只有企业盈利,它才具备生存的权利,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由此将其视为把投入转为产出的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单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功能不断贯穿于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等各个环节,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甚至超越国家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Berle &Means,1932)。企业所联结的不再仅是股东(Shareholder),而包括了消费者、员工、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他们或是为企业经营付出了代价,或是为企业分担了风险,因而企业需要作出补偿,即企业社会责任。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经理人支付股东的钱,被视为“企业宝贵资源的消耗”,即承担社会责任削弱了企业的经济目的,将使企业进入与其“正当目标”无关的努力领域,企业生存自此会因市场的竞争性而受到威胁。沿袭这一逻辑,绝大部分企业将社会责任视作一种经济负担,对“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承担多大程度的社会责任”总是“随波逐流”。为改变这种现状,最有效的切入口是找到企业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集部分,实现既造福于社会又有益于企业的“帕累托改进”式经济驱动。
也因此,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步从道德取向转变为绩效取向,分析水平亦从宏观社会层面转移到组织内部层面。大量研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李国平等,2014),但一直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据此部分研究关注到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权变问题。Brammer & Milling‐ton(2008)、Barnett & Salomon(2012)提出利益相关者影响力(Stakeholder Influence Capacity)理论,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U型关系,即CSR-CFP的关系取决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有效识别。然而,Cordeiro et al.(2021)发现在薄弱的制度环境下(如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这一U型关系并不适用于非家族等其他类型的企业,甚至会出现反转,即呈现倒U型关系(Guo & Lu,2021)。
不难看出,尽管非线性关系为CSR-CFP研究提供了整合视角,但仍旧存在争议:第一,在众多非线性关系的构造中没有触及潜在机制,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多数是简单地将传统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组织合法性理论(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Theory)等进行杂糅,通常使用模糊而笼统的论点,例如“任何东西都可能是有害的”(Haans et al.,2016),因此无法为二次关系提供一致性的理论依据;第二,国别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制度文化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因为制度条件能够改变企业从事某一行为的收益和损失,从而影响企业的动机和决策偏好,CSR-CFP关系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中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Cordeiro et al.,2021;Hirsch et al.,2022),因此在中国转轨经济环境下重新讨论非线性关系仍有一定意义;第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至今,已经是涉及消费者、员工、社会、社区、环境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概念,因此对其经济绩效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维度。
综上,本文试图跳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视角,即不再像传统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为一种反应性行为,而是将其视为企业能够主动实施的一种竞争战略,并依托产业组织理论与博弈论将其融入寡头竞争模型,为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及经济后果提供可行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辅以实证,利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基于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深入探讨企业的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双重协调的机理与路径,为学术界悬而未决的CSR-CFP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解释。
二、理论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诞生之初,是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显露后导致的环境污染、工人罢工、经济危机等问题愈演愈烈,相关学者借此提出企业为了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多数早期理论学者认为,无论企业是否可能或需要实施,基于“社会本位”,社会责任的履行具备必要性与强制性。然而,即便是早期的“规范性主义”企业社会责任,总有一个内在的前提,那就是企业若能通过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改善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从长期来看,可将这些努力看作是“开明的自利”。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因为担心企业对社会的不利影响(避免“消极因素”),但创造社会与企业协同价值(创造“积极因素”)与早期理论家和实践者的理念并不冲突。Lee(2008)观察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演变的趋势,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经济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研究被视为“新式CSR”的凸显特征,其本质是“行善以致富(Doing Well by Doing Good)”,内在的逻辑遵循以下机制:
第一,源于对社会契约的遵循。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不仅存在显性的经济契约,而且也存在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而该隐性契约的核心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尽管企业社会责任满足经理人的偏好可能构成道德风险,但企业社会责任同时能够满足投资者、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社区、政府的非经典偏好,使企业和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基于信任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关系契约),可以显著地降低契约成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降低经理人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柠檬”(即逆向选择)问题,从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角度,也能有利于监督经理人的自我服务(Self-Serving)行为。
第二,源于对社会压力的回应。企业社会责任的精髓就在于社会期望或市场压力等外在力量附加于企业的义务。食品与药品安全、员工福利、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的剧烈改变导致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环境与政府群体的外在压力下,如果企业要获取适于自己发展的健康环境,就必须在社会环境情景里对社会压力的剧情发展作出相应回应(沈洪涛,2005),确保其长期生存能力。它的价值在于将社会责任概念转化为一个管理概念,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是通过环境评估、利益相关方管理以及社会参与和公共政策管理去解决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实现对社会压力的有效回应,以维护其作为社会存在的“合法性”。
第三,源于对竞争优势的培育。社会责任将企业与某项社会事业或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实现消费者“自我实现”和“自我尊重”的诉求,以声誉和可信度塑造企业竞争力,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最终为企业培育不可完全模仿性、高成本壁垒与正当性的战略资源,进而助力企业发展。此时社会责任可被看作是企业在寻找与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相吻合的社会原因,然后以互利的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付诸实施,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在“新式CSR”基础上,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应运而生(Porter & Kramer,2006)。当企业确定经营地点与范畴后,社会责任行为和竞争优势将相互促进并形成良性循环。社会责任行为能够被用于影响企业的竞争环境,同时满足一些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这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换言之,企业在接受“经济目标”的同时适应“外部市场的美德”,实现协同价值创造(Synergistic Value Creation),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作一种“管理哲学与商业战略”,这就是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从企业经济(财务)角度为企业社会责任倡议提供了合理论据,有效回应了主流企业理论对社会责任的“口诛笔伐”。因此,社会责任之于不同企业并非存在一般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推动依赖于制定适当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旨在改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同时也改善社会福利。即正确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是追求经济和非经济目标之间的趋同。本文延续这一发展趋势,基于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开展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考察企业在“经济理性”下对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绩效。
三、理论分析
(一)基本模型
企业被赋予社会责任义务涉及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平衡与调整,不同企业实际履行的社会责任策略存在差异性。为了便于分析且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某一市场内存在两家企业,企业1为社会友好型企业(Socially-Concerned Firm),同时关注自身利润与社会责任,而企业2为利润最大化企业(Profit-Maximizing Firm),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二者生产异质性产品在市场上进行古诺(Cournot)竞争。市场反需求函数为Pi=a-qi-γq-i,企业的成本函数据此可得两家企业的利润函数:

当市场的力量回馈企业时,企业会主动地采取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消费者选择是企业社会责任最有力的拉动。因此尽管企业涉及员工、社区、环境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但消费者“责任消费”的趋势演变,即许多消费者愿意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产品支付额外费用,是促使现代企业竞相在社会、环境、道德、人权等诸多领域发展社会责任实务的根本动因。换言之,消费者是企业相对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由社会责任引致的市场竞争优势多是通过产品的最终消费得以实现。因此,本文参照Goering(2007)的经验做法,将社会友好型企业的支付函数设定为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的加权之和:

至此,我们可建立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在第一阶段,社会友好型企业决定最优的CSR实施策略(α);在第二阶段,各企业采用古诺策略进行非合作产量的竞争。在博弈过程中信息完全,模型求解采用逆向归纳法。
(二)产量竞争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企业1与企业2面临的最大化问题分别为maxq1V(q1,q2)和maxq2π2(q1,q2),由此联立求解相应的一阶条件,可得到两个企业的均衡产量:

将q1*与q2*代入企业利润函数,可得到两个企业的均衡利润水平:

为考察社会友好型企业不同的社会责任实施程度α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将式(4)中π1*相对于α求一阶偏导数,可得①其中=root[f(α),2],即为多项式f(α)的第二个根值。:

式(5)显示,企业社会责任程度是社会责任影响企业利润的权变条件。具体来说,如果社会友好型企业选择承担相对较低程度的社会责任(0<α≤或许不会损害企业利润,甚至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取决于产品差异化程度;而如果社会友好型企业选择承担相对较高程度的社会责任1),结果是企业利润的绝对下降。换言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存在一个上阈值如果不考虑产品差异化因素,这是企业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最优社会责任策略选择。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源于“经济理性”下社会友好型企业关于成本—收益的权衡。为了更加直观地探讨社会友好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对其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分析,设定a=10,γ=,可得图1(a,b,c)①除此之外,本文已多次连续赋值,所得图形结果基本相仿,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图1(a)描述了社会友好型企业的总收益曲线,其变化呈现凹型(Concove)或对数型(Logarithmic),这表明尽管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市场竞争途径作用于对手企业乃至于整个市场,甚至直接削弱了对手企业绩效(<0),但通过该类竞争优势获得的边际收益存在递减。图1(b)描述了社会友好型企业的总成本曲线,其变化呈现凸型(Convex)或指数型(Exponen‐tial),表明为了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友好型企业积极扩大自身的产出规模,边际成本递增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社会责任承担产生了迅速上升的成本。因此,在图1(a)与图1(b)的合力作用下,图1(c)最终形成了社会友好型企业的社会责任程度(α)与经济绩效(π1)之间的倒U型关系②Haans et al.(2016)将倒U型关系形成的潜在机制分为三类,本文的结果属于其描述的第二类。。

图1 α与收益、成本、利润的关系
从现实角度考虑,企业主动关注消费者利益、承担保护环境职责、实施慈善捐赠等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能够提高产品和服务营销的有效性(马龙龙,2011),吸引和留住更高素质的员工(陈宏辉等,2020),提供对政治与融资资源的优越获取(李孔岳和叶艳,2016),在负面事件期间缓解市场价值损失(朱焱和杨青,2021),从而使得该类企业在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主动地位,以形成竞争优势,但依托此类善因营销获取的竞争优势通常有限,正如Jung et al.(2017)研究的那样,捐赠规模与基于消费者的品牌权益存在曲线关系,较小的金额可能被消费者认为太低而效果不明显,但较高的金额,消费者亦有可能归因于不合理的高支出,从而产生怀疑。与此同时,从成本角度考虑,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资源,如治污投入、慈善投入、员工培训投入等,一旦企业从竞争优势中可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成本,那么就会损害经济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如果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企业的竞争战略,企业最优的社会责任策略是选择适当的社会责任实施程度,超越这一水平的社会责任投入不会对经济绩效有积极的贡献。即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三)企业选择
在博弈第一阶段,社会友好型企业需要选择最优的社会责任策略α。社会责任的实施不能忽略企业是理性主体的客观事实,基于“经济理性”视角,社会友好型企业面临的最大化问题是maxαπ1*(α,γ),结合一阶条件=0与二阶条件<0,可得到内点解α*=,即为该情景下社会友好型企业最优的社会责任实施程度。不难看出,该最优程度与产品差异化密切相关(如图2所示)。

图2 γ与α*的关系
图2表明,企业所能承担的最优社会责任程度与产品替代性呈现正相关关系,产品替代性越大,该最优程度越高。这意味着在产品差异化程度非常低的竞争市场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能促进企业利润的提升。产品异质性越大,社会责任越不容易形成竞争优势。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竞争优势的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有效识别。如果社会友好型企业与利润最大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基本不可替代,如位于不同的行业,那么前者承担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沉没成本,因为其对后者的产量、价格影响相对微弱,最终无法通过竞争优势作用于市场需求,社会责任在此情景下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竞争战略。简言之,如果社会责任不能产生有效的市场反馈与商业回报,也无从谈及其战略性。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性越强,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策略越容易形成竞争优势,最终所愿意实施的社会责任水平也相应较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市场竞争程度通过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报,进而影响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基于“经济理性”的战略性社会责任实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经济绩效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作为主导国民经济发展与保障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往往不是第一位,出于特殊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国有企业本身就被要求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国有企业所承载的使命存在很大共通之处,而且受政府干预明显。相对地,民营企业天生的逐利性诱使其在面对利益相关者压力时或仍会更多地遵循市场机制作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调整,即多数民营企业更倾向于把能否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作为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评判标准。因此,为了剔除国有企业目标多重性、行为利他性引发的偏误,本文将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
基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和讯网”定期公布了CSR评分,通过手动整理,本文获得了这一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企业经济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对以上数据库进行合并处理的基础上,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和异常值的样本;(2)考虑到金融和公共设施行业的特殊性,将这两个行业的样本数据也予以剔除;(3)为了减轻异常值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回归中所用的连续变量予以1%的水平缩尾处理。最终获得9493个初始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参照Barnett & Salomon(2012)等经验研究,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各个企业的经济绩效。由于企业经济绩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需要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引入其一阶滞后项Yit-1;CSRit为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如理论分析所述,不同程度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本文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变量的二次项CSRit2进行考察,以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Controlit为控制变量集合;μt、ϑj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变量与行业固定效应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择
企业绩效:本文以资产回报率(ROA)作为代理变量。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将比率变量作为因变量可能会夸大作用关系并混淆结果解释,原因在于自变量可以影响分母也可以影响分子,或者同时影响二者,从而使统计推断复杂化。因此本文补充企业净利润(NI)作为企业绩效的未标定的代理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可能对研究结果带来的潜在影响,本文对NI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企业社会责任(CSR):本文将“和讯网”发布的CSR评分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该评测体系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考察,各项分别设立二级和三级指标对社会责任进行全面评价,分数越高,表示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市场竞争程度(CP):本文采用CP=1-HHI作为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其中HHI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由企业i在行业j中所占市场份额的平方和进行计算。HHI数值越大,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垄断性越强。具体计算公式为HHIij=∑(Xij/∑Xj)2,其中Xij为行业j中企业i的营业收入,∑Xj为行业j全部企业的营业收入之和。
控制变量:本文分别从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进一步控制了其他潜在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上,将控制变量所包含的变量设定如下:企业规模(Size)、固定资产比例(FA),无形资产比例(IA)、存货比例(SR)、经济杠杆(FI)、成本率(CI)、流动比率(TD)。在行业层面上,本文重点选取了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水平(MI)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测度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测度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CSR平均值为23.536,尚未达到及格线,说明民营企业总体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较低;从行业层面看,MI平均值也仅为23.542,最大值为39.526,亦表明民营企业实际履行的社会责任程度并不高,这侧面反映出民营企业主要聚焦于获取利润。ROA平均值为0.045,说明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平均水平为4.5%,每单位资产创造的净利润水平较低。CP平均值为0.872,说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强,表明民营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相对激烈。其他企业特征变量均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基本符合现实情况,可作进一步研究。

表2 描述性统计
2.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方程(6)的计量模型,表3给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资产回报率(ROA)作用效应的检验结果。第(1)—(2)列为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第(3)—(4)列为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从一次项的回归结果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CSR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绩效提升的,这符合前文理论模型得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培育市场竞争优势的结论。由于本文选择的是民营上市公司样本,这一结果侧面印证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备战略性,只有在社会责任能转换为内在经济动因时,才更可能被实施。

表3 基准回归
进一步从二次项的回归结果看,CSR2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根据Haans et al.(2016)的研究,仅凭一个显著的二次项系数并不足以建立一个二次关系,还需验证转折点是否在数据取值的范围中间。依托第(2)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OLS与FE估计下二次曲线的转折点(CSR=-)分别为51.28、46.51,均在表2描述的CSR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以上结果验证了前文的猜想,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促进或抑制关系,而是取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申言之,尽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提升,但一旦企业承担过度的社会责任,是会“扭盈为亏”的,即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与假说1的预期一致。
3.内生性处理
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违背了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假设,同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也会引发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通常采用工具变量法(IV)或广义距法(GMM)对方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法虽然能够避免内生性问题,但容易引起模型遗漏其他变量而导致虚假回归问题;而差分GMM会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消掉,也容易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综合考虑,本文效仿杨灿明和詹新宇(2015)的经验做法,利用两步稳健型系统GMM方法对方程进行估计,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考虑到系统GMM估计量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采用Hansen检验与AR检验进行判断。前者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联合有效,如果不能拒绝则证明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恰当的;后者允许残差项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允许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表4第(1)列给出了利用系统GMM方法对方程(6)进行重新估计的结果。由于OLS估计通常严重高估滞后项的系数,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一般会低估滞后项的系数,所以对于GMM估计量是否有效可行,Bond(2002)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检验办法,即将GMM估计值分别与FE及OLS估计值比较。如果GMM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则GMM估计是可靠有效的。本文Yit-1的OLS、FE、系统GMM估计值分别为0.346、-0.019、0.108,系统GMM估计值确实处于其他两个估计值之间,证明系统GMM估计结果未因弱工具变量问题而出现严重偏误。此外,表4第(1)列报告了AR(2)检验的p值分别为0.913,表明不能拒绝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模型设定不存在偏差。Hansen统计量p值分别为0.292,表明系统GMM估计中没有证据拒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从这些假设检验结果发现,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的选择都不存在问题,本文系统GMM估计结果较为可靠。从具体结果看,CSR与CSR2的估计系数分别表现为显著正、显著负,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在此基础上,为避免企业绩效的测度方式不同影响实证结果,本文补充企业净利润(NI)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进行了系统GMM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AR检验与Hansen检验结果均显示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的选择不存在问题,同时CSR与CSR2的估计系数仅出现了绝对值上的改变,再次佐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4 内生性处理——系统GMM估计
4.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
在基准回归基础上,本文引入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二次项的交乘项进行考察。表5给出了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作用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AR(2)检验的p值分别为0.377、0.770,Hansen统计量p值分别为0.760、0.701,均显著大于0.1,表明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可靠有效的。从表5可以看出,第(1)列与第(2)列中CSR与CSR2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仅绝对值稍有改变,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CP*CSR2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二次曲线的转折点CSR=会右移,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由正转负的拐点变大。

表5 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
进一步解释,如果企业承担合理程度的社会责任,企业绩效可以获得提升,而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该种绩效提升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正正加强,即如果企业面临较强的产品市场竞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将会得到加强。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扩大由社会责任引致的盈利空间,进而增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程度的上阈值。换言之,在非常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内,社会责任才愈加可能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继而所能承受的最大社会责任程度也越高。这一结论符合假说2的预期。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更加倾向的社会责任行动范式是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投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决定出最适的社会责任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责任的企业价值增值作用,而非是传统理论与实践中注重的合规性或反应式CSR。
五、进一步讨论
综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如果社会责任可以视为企业主动实施的竞争战略,那么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权变问题。在现实经济中,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以捐赠等公益活动为主,而很少涉及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以及环境等(刘乾和陈林,2021)。这是因为在当前中国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多数企业偏向于实施公益慈善型社会责任,尽管同样消耗自身的资源,但服务于外部社会问题能够产生较强的可视性,更容易引起消费者关注。因此,不同制度环境衍生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属性具备差异,而这很可能引致不同的经济绩效表现(Cordeiro et al.,2021)。本文依据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已有研究中CSR-CFP之间关系不一致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机理解释,即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后,依据自身实际能力承担相应程度的社会责任,这样通过实施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最终实现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的统一。
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为社会责任理论的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即经理人的确可能存在利润与道德之间的权衡,从而偏离(或弱化)股东目标,转而培养一种“公司良知”。然而,以经济为导向的主流企业理论学者承认市场失灵可能无法确保有效定价或提供非私人物品,强调企业不能也不应该期望以对社会或环境负责的方式自愿行事。那么,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只能成为“败坏社会的信条”,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是否一定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本文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出于对社会契约的遵循,还是对社会压力的有效回应,作为内嵌于社会系统的重要组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与企业凝聚力的主要来源,是获取经济、政治激励(雷雪等,2022),维持社会存在合法性(李伟阳和肖红军,2011),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责任消费”的社会发展趋势下,社会责任已被企业视为获取不可替代市场资源的竞争手段,这将意味着企业采用社会责任并不是一味地增加资源耗费与企业成本。
解决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对立与统一的关键在于“适度原则”的合理应用。在中国,由企业多重目标导致预算软约束、激励不相容以及在经营中陷入“囚徒困境”的突出主体之一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从建立伊始就被赋予强大的社会责任,或者说由于国有企业既有一般功能又有特殊功能,兼具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成为其天然的属性(黄速建和余菁,200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同时仍要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政策负担,严重影响了经营效率和激励机制(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必须同时避开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这两个极端,其承担社会责任绝非重走“企业办社会”的旧路,而应是一种提升和重塑。
不难看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民营企业被赋予社会责任义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国有企业担负了弥补市场失灵、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等重要职能,与自身承载能力不协调的社会责任履行导致了很多国有企业经济利益受损,需要通过引入民营资本纯化经营目标,降低企业的社会性负担(陈林和唐杨柳,2014)。而根植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下,单一的利润目标导向与短期行为又可能会诱发污染环境、劳工血汗工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必要要求其加大自身行为的治理,强化社会责任。本质上,二者都涉及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平衡与调整。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实现可持续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将社会责任有效融入企业战略,既剥离“企业办社会”的政策性与社会性负担,又创造高水平的利益相关方价值、共享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率的“正和博弈”。
六、结论与展望
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既要致力于私有利润的创造,又需要承担社会、环境等公共利益服务,这势必要求企业应做到管理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之间的平衡。时至今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正朝着与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全面整合的方向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已由一个合规性问题演变为出于管理需要的战略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被赋予更多的实践意义。从战略层面厘清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之间的权衡关系及潜在机制,或可成为将社会责任落实到可操作性措施的引路之石。
通过相关理论梳理与分析,本文跳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视角,基于“经济理性”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经济绩效的权变作用,不仅回应了企业“是否需要CSR”,也为企业如何在“需要和可能的原则之上”履行CSR提供了可行性路径。第一,诚然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但企业不要一味地抗拒,只顾自己的利益,无视社会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取的。相反,当企业的市场战略处于劣势地位(如企业创新水平低)、市场战略相似(如产品同质)或市场战略无效时(如依靠产品质量无法获取出口优势),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或许可以获得不可替代的市场资源,从而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第二,要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长期投资,以建立利益相关者影响力,尽管履行社会责任初期可能无法获利,但是一旦建立了足够容量,就会发现它对提升经济绩效很有价值。第三,要意识到依靠社会责任培育竞争优势并不总是“一劳永逸”的,不能盲目过度扩大社会责任投入,企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外部市场环境有效评估社会责任的社会回馈效应,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作出权衡,以合理地、适当地、力所能及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最终以企业的利益促进社会利益的提高。
从理论起源看,企业社会责任虽缘起于西方,但并非“洋为中用”的外国产物。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所进行的“义利之辨”已涉及到“道德上的应当”与“物质利益”的权衡。“义利之辨”横贯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史,其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被摒弃,“义以生利,家国同构”的儒家积极伦理仍旧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的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允许企业从社会责任机会中受益,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双赢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承认,试图去获得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关系的一般性答案是徒劳的。正如Rowley & Berman(2000)所指出的,“只有我们当中最幼稚(或盲目希望)的人才会认为不良(良好)的社会行为将始终具有负面(正面)财务影响。”因此,相较于社会性与制度性的外部驱动,我们应将社会责任回归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内在战略驱动,强调社会责任之于企业并非存在一般性,研究如何战略性的选择和实施CSR行为,既是有效推动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良策,又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途径。
总之,企业社会责任既不是“规范性主义”所倡导的“高尚行为”,也非主流企业理论所宣称的“败坏社会的信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而须坚持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观点和对立统一规律,无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国有企业,还是根植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民营企业,都应基于“企业本位”权衡社会责任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进而准确判断最优的社会责任实施策略,最终实现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之间的趋同。“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让社会道德与经济利益相得益彰、齐头并进,才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之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