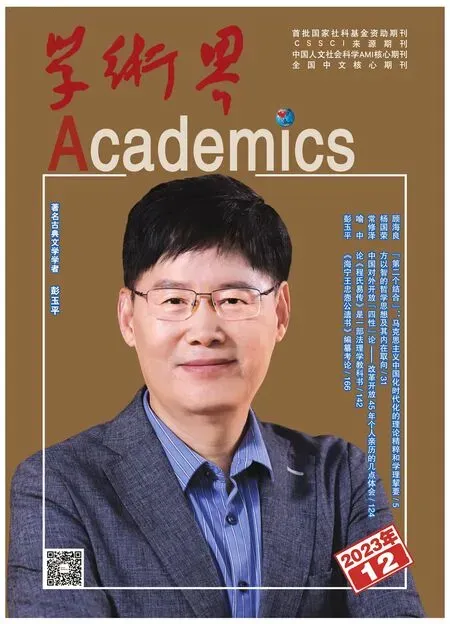论《程氏易传》是一部法理学教科书〔*〕
喻 中
(中国政法大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 北京 100088)
宋明理学作为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又称为宋明道学。冯友兰认为,“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所谓程氏兄弟,即兄长程颢(1032—1085)与兄弟程颐(1033—1107),二人分别被称为明道与伊川,“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中所谓程朱陆王之二派,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之二派。程伊川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1〕根据这样一条思想线索,程颐可以看作是程朱理学的主要开创者。由此看来,如果要理解宋明理学中的程朱一派的法理学,就不能避开程颐的法理学。
通往程颐法理学的路径有多种,其中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径,就是着眼于《程氏易传》。作为一部标志性的易学著作,《程氏易传》在今天通行的《二程集》中被称为《周易程氏传》,在学术史上亦称《伊川易传》《周易程传》《易程传》(下文根据不同的语境,或称《程氏易传》,或简称《易传》)。把《程氏易传》作为程颐法理学的主要载体,主要的理由在于:《程氏易传》是程颐的代表作,是程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程颐法理学的集中体现。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一方面,程颐本人对待《易传》的态度极为严肃,极为谨慎,对《易传》的价值深信不疑。可以找到多个方面的材料来支撑这个判断。譬如,据《河南程氏外书》,“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2〕(以下引自此书的文字,仅在引文后注明页码)《易传》虽然写成了,但程颐并不轻易示人,哪怕是他的学生,也不能随意翻阅。程颐还说,“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韩退之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然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第174—175页)这句话表明,程颐愿意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修改他的《易传》。他希望到七十岁的时候,能够把《易传》修改到他满意的程度。在《答张闳中书》中,程颐又说:“《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然亦不必直待身后,觉耄则传矣。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也,第患无受之者尔。”(第615页)这就是说,不仅完善《易传》很重要,找到能够传承《易传》的人,把《易传》传承下去,也是很重要的;试想,倘若没有合适的传承者,自己创作《易传》的辛苦,《易传》承载的儒家道统,岂不付之东流?此外,程颐还对自己一生的学思进行了总结:“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第314页)纵观程颐的生命历程,“六十以后”所著之书,就是这部《易传》。程颐为了这部书,几乎是以毕生的时间、精力来酝酿,成书之后又反复修改。由此可见,这部《易传》是程颐全部生命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念兹在兹的最主要的精神寄托。
另一方面,其他人也把《易传》看作是程颐最重要的代表作。根据朱熹所作的《伊川先生年谱》,公元1106年,亦即程颐去世的前一年,“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尹焞曰:‘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未能无失也。’”(第345页)几乎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自己实在无力再修改、再完善的情况下,程颐才把《易传》正式传授给弟子尹焞、张绎。这个细节表明,《易传》堪称程颐的“晚年定论”,是程颐主动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按照尹焞的看法,《程氏易传》比他人记录的程氏《语录》,能够更加精准地体现程颐的思想。而且,《语录》出自多人之手,反映了多个记录者对程颐思想的理解,众多的记录者分别写成的文字能否真实体现程颐的思想,可能还有一些疑问。相比之下,《易传》则是程颐自己写作、自己反复修改的完整著作,能够更加清晰、真实、准确地反映程颐的思想,完全可以解读为程颐为自己绘制的思想肖像。
更加重要的是,《易传》不仅是程颐的代表作,而且还是一部讲法理的教科书。作为一部法理学教科书,《易传》集中体现了程颐在中国法理学史上的贡献,集中体现了程颐自觉承担的法理使命。因而,要把握宋代的中国法理学,尤其是要把握程朱一派的法理学,就有必要认真对待《程氏易传》所承载的法理学。为了揭示程颐及其《易传》对中国法理学的贡献,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分述。
一、《程氏易传》是一部“讲理”的教科书
要阐明《程氏易传》是一部“讲法理”的教科书,是一部法理学教科书,首先应当阐明,《程氏易传》是一部“讲理”或“言理”的教科书。
(一)作为“讲理”之书的《程氏易传》
《朱子语类》有一节题为《程子易传》,记载了朱熹关于《程氏易传》的看法,“《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处。”朱熹还说:“程《易》不说《易》文义,只说道理处,极好看。”总之,“《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3〕朱熹的这几句话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点:其一,《易传》是一部“言理甚备”之书,简而言之,《易传》是一部“言理”或“讲理”之书,《易传》的主要特色与主要贡献就在于“言理”。如果我们要处理实际事务,那么,《易传》可以作为很好的依据,因为它提供了很好的道理,每一句、每一字都有用处。其二,如果从象数易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易传》则乏善可陈。因为,它不讲《易》之象数,甚至不大涉及《易》之文义。因而,在象数方面,《易传》没有“意味”。这就说明,《易传》虽然是讲《易》之书,但主要是在讲《易》之理,因而是一部“讲理”之书。
对于《程氏易传》的这个特点,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一书中有明确的阐述。针对程颐的经学,皮锡瑞认为:“其著《易传》,专言理,不言数。《答张闳中书》云:‘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故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纯正。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朱子作《本义》以补程《传》,谓程言理而未言数,乃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发明图书之义。”〔4〕皮锡瑞的这几句话,可以印证朱熹的观点:《程氏易传》乃是一部言理、说理、讲理之书。经过这样的辨析,可以看到:讲《易》之书,主要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易学谱系——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汉代是象数易学盛行的时代,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郑玄、虞翻等人,顾名思义,他们的旨趣在于《易》之象数,主要在于解释《易》之象与数,以之附会天象律历。
针对汉代的象数易学,魏晋时期的王弼提出了批评。王弼认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5〕
在王弼看来,象数易学之失,主要在于“存象忘意”,进而导致“义无所取”。因而,研究《周易》的正道,应当是忘其象而求其意,只有通过这种取向的易学,才能见《易》之义。义就是理,义与理合起来就是义理。追求义理的易学,就是义理易学,这就是王弼认同的易学。对于王弼所张扬、所发挥的这种义理易学,程颐在推崇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由此看来,在易学的谱系中,王弼与程颐可以视为义理易学的主要代表。而且,根据皮锡瑞之见,程颐对《易》之义理的阐释,已经超过了王弼。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甚至认为,在清初以前的易学史上,要论说理之精,应当首推程颐。换言之,关于《易》之义理,程颐是最好的阐述者,《程氏易传》是最好的易学著作。所谓“最好”,不仅仅体现在程颐其人其书“说理为最精”,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人其书的“纯正不杂”,因为其人其书排除了“老氏之旨”,这恰恰是王弼其人其书存在的问题,对此程颐已经批判地指出:“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第8页)程颐对“老、庄之意”的防范,让他的《易传》成为了一部相对纯粹的儒家著作。
在程朱之间,朱熹以“象数欠在”评论《程氏易传》,显然是寄寓了批评之意,由此可以表明,朱熹在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之间,对象数易学有更多的认同。针对《程氏易传》的“言理”偏好,朱熹的《周易本义》试图在象数易学方面有所创建,因而可以较多地归属于象数易学的谱系。可见,程朱虽是一派,但程朱对《易》的理解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程朱之间,如果着眼于捍卫儒家道统,如果立足于阐明纯粹的儒家义理,那么,较之于朱熹的《周易本义》,《程氏易传》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程氏易传》是一部“讲理”“讲义”“讲道”之书,而不是一部“讲象”“讲图”“讲数”之书。就像程颐自己所说:“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第671页)不能载道、不能讲理的经学著作,只能是无用的糟粕,因为它们无补于大道与天理。正是在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相互并立的格局下,可以发现,《程氏易传》的特质就在于“讲理”。
(二)作为教科书的《程氏易传》
如果说,《程氏易传》确实是一部“讲理”之书,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一部教科书?众所周知,教科书是教学用书,应当有明确的教学对象或教化对象,甚至还要有明显的教学目标。程颐写作这部书,试图教化的对象是什么?《易传》是为谁写作的教科书?全面查看《易传》写作的前因后果,可以发现:此书试图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君主,当然也可以包括以君主为代表的执政团队。换言之,《程氏易传》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作品,它是一部以君主及其执政团队作为教化对象的教科书。《程氏易传》所具有的这种教科书性质,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易传》的内容来看,程颐对《易》理的阐明,主要是以君主作为阅读对象的。对此下文还有进一步的论述。这里我们只看《程氏易传》正文的第一段。
在《易传》正文的开篇,程颐首先解释《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他说:“上古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重乾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乾。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故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第695页)这段话,以及整部《易传》,都是从“上古圣人”开始说起。“上古圣人”乃是《易传》的起点。这就提醒我们,“上古圣人”是程颐写作《易传》的一个基本参照、一个基本立场。
《易》既然出于“上古圣人”,那么,“上古圣人”作《易》,以成就三才之道,以穷尽天下之变,主要的意图,就在于启示“上古圣人”的后继者,亦即当下及未来的“圣人”,亦即后世的君主,教会他们懂得为君之道,教会他们成为像“上古圣人”那样的新一代圣人。可以推定,“上古圣人”不可能有闲功夫去写闲文、闲书,对天下及后世承担了神圣职责的上古圣人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不过,“上古圣人”虽然作了《易》,以之承载为君之道,但麻烦的是,后世君主未必能够理解“上古圣人”的智慧与苦心,未必能够深刻理解由《易》承载的为君之道、成圣之道。程颐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易传》,就在于把“上古圣人”创立的为君之道、成圣之道清清楚楚地阐发出来,以便于当下及未来的君主吸收、掌握,进而成为新时代的圣君。
按照程颐的解释,《乾》卦之“乾”,既代表了“万物之始”,同时也是天、阳、父、君的象征。在天、阳、父、君之间,君才是最终的落脚点。《乾》卦表征了广大的“四德”,意味着君主也应当承载同样广大的“四德”。这就是《易传》的基本立场、基本走向、基本旨趣:面向君主,进而教化君主。正是基于这样的预设,针对《乾》卦的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程颐写道:“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针对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程颐又写道:“三虽人位,已在下体之上,未离于下而尊显者也。舜之玄德升闻时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则虽处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将归之,其危惧可知。虽言圣人事,苟不设戒,则何以为教?作《易》之义也。”(第696页)
这样的一些解释与阐发,都是为了教化君主。譬如,根据九二爻辞,君主应当主动团结“大德之臣”,君主应当在“大德之臣”的协助下成就一番大业。当然,君主自己也应当成为“大德之君”,以泽被天下,最终成为众人仰望、万世仰望的圣君。再譬如,根据九三爻辞,一个潜在的君主,如果处在已有其德但尚无其位的关键时刻,那是比较危险的,这种潜在的君主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程颐的这些论述已经表明,他写作《易传》,预期的读者主要是“居天下之尊”的君主,旨在教化这样一些君主。可见,《易传》主要是一部以君主作为教化对象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从程颐一生的“行状”来看,教化君主堪称程颐自觉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易传》就是这种使命感驱使下的产物。
早在1050年,年仅18岁的程颐就写出了《上仁宗皇帝书》,此“上书”开篇就告诉仁宗皇帝:“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荛,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弃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接下来又说,“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圣人性之为圣人,贤者由之为贤者,尧、舜用之为尧、舜,仲尼述之为仲尼。其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第510页)如此年轻的程颐,就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尧舜之所以为尧舜的道理,就相信自己能够把“仁宗皇帝”教化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明之君。这篇“上书”表明,教化君主堪称程颐的初心,也是程颐自觉承担的使命。
有志者,事竟成。历史确实也给程颐提供了当面教化君主的机会。据《宋史》记载,随着程颐声誉日隆,“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哲宗初,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6〕在这几项职务中,最重要的就是“崇政殿说书”,因为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教化君主的职务,亦即真正的“帝王师”。正是在这个岗位上,程颐作为“侍讲”或“讲官”,对年幼的哲宗皇帝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教育,把自己教化君主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段经历,是程颐最为看重的自己一生的“高光时刻”。
在事隔多年之后所作的《再辞免表》中,程颐所追求的教化君主的理想依然显露无遗:“伏念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食以求志,不希闻达以乾时。皇帝陛下诏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讲说之职。臣窃思之,得以讲学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臣是以慨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余,夙夜毕精竭虑。”(第557页)在程颐看来,以“讲学侍人主”,是一个儒者立功、立言、立德的最高际遇。然而,颇为遗憾的是,这样的际遇并不常有,也并不长久。从程颐的晚年回过头去看,从1086年开始,他实际担任“侍讲”职务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准确地说,是“一年又八个月”,到了1087年,“八月二日,奉敕罢说书,差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先生知是责命,奔走就职”。〔7〕这一年,程颐54岁。此后,年复一年,他发现当面教化君主的机会已经不可能再次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一直迁延到1099年,66岁的程颐完成了自己的《易传》。
程颐的一生,有所拒绝,也有所接受。他在出与处之间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他虽然获得了多次机会去担任一些普通的官职,他都拒绝了。但是,他愿意承担“侍讲”之职。正是在失去了直接教化君主的“侍讲”职务之后,程颐精心构制了他的《易传》。在程颐的生命历程中,他的《易传》一书成为了他的“侍讲”一职的替代物。由此,我们可以揣摩程颐的心迹:如果实在没有直接教化君主的机会,那就为当世及后世的君主写一本教科书,通过这样一本教科书,不仅可以教化当世的君主,而且可以教化后世的历代君主。《程氏易传》,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写成的。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发现,《程氏易传》不仅是一本“讲理”之书,而且是一部“讲理”的教科书,更具体地说,是一部为君主讲儒家之理的教科书。
二、《程氏易传》是一部“讲法理”的教科书
上文表明,《程氏易传》是一部“讲理”的、旨在教化君主的教科书。通过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程氏易传》还是一部“讲法理”的教科书,是一部法理学教科书。为什么这样说?《程氏易传》讲了一套什么样的法理学?如何在《程氏易传》中发现程颐的法理学?
从一般意义上看,倘若以今律古,倘若打通古今,《程氏易传》作为经学著作,它关于《易》之理的解释与阐述,就相当于现代的法理学著作。要理解经学与法理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妨参考蒙文通在《论经学遗稿三篇》中的一个论断:“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8〕按照蒙文通的论断,在传统中国,经学就是最高的法典。不过,倘若要更加严格而精准地说,那么,以《诗》《书》《礼》《易》《春秋》为实体内容的经,才是最高的法典。经学作为经的理论阐述,旨在揭示的经之理,就相当于现代的法之理。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相当于现代的法理学。《易传》作为程颐写给君主的经学教科书,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其实是一部法理学教科书。
从《程氏易传》的内容来看,它已经建构了一个饱满的法理世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说《程氏易传》乃是一部法理学教科书。对于程颐通过《程氏易传》所表达的法理憧憬、所建构的法理世界,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把握。
(一)理·礼·法:规范的形态
规范是法理学不能回避的主题。《程氏易传》对规范的形态与类型多有揭示。在《易说·系辞》篇中,程颐认为:“圣人作《易》,以准则天地之道。《易》之义,天地之道也”。(第1028页)这就是说,《易》为天地提供了“准则”,这样的“准则”,具有强烈的规范意义。程颐对《易》的这种理解,恰好印证了蒙文通的上述判断:像《易》这样的经,就是“无上之法典”。根据《程氏易传》,在天地之间,具有规范意义、法典意义的准则,主要呈现为三种不同形态的规范,它们分别是理、礼、法。
先说理。在《程氏易传》建构的规范体系中,理是效力最高的规范,是其他规范的效力依据,具有最高的约束力。从法理层面上看,理就相当于自然法。程颐恰好也指出了理与自然的关系。譬如,针对《益》卦,他说:“盛衰损益如循环,损极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继损也。”(第912页)进一步说,“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第914页)这些论述表明,理有自然的性质。如果着眼于理的规范性,如果把理视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法,那么,“理自然”可以理解为“法自然”,“自然之理”可以理解为“自然之法”。作为规范的理,既是自然形成的理,也可以理解为自然形成的法。
自然之物也是天然之物。因而,自然形成的理,也可以理解为天然形成的理,亦即天理,“尽天理,斯谓之《易》。”(第1207页)这就是说,《易》既是“准则”,同时也是“天理”,《易》就是天理的完整表达;所谓“尽天理”,就是穷尽了天理的全部内容。在《程氏易传》中,甚至在宋明理学中,理与天理都可以相互替换。用“天”修饰“理”,一方面,可以说明理的自然属性或天然属性,天然的理,就是自然的理;另一方面,还可以说明理的神圣性,可以加强理的权威性,当我们宣称理是天理,有助于为理确立一个神圣的源头。
天理是上天昭示的法则,“天之法则谓天道也”。(第703页)因而,天理就是天道。天理、天道还具有“常”的性质,天理、天道就是常理、常道。不过,“常”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变。因为《易》的主旨就是变易,在这个意义上,《易》之理,其实就是变易之理。程颐刻意指出,“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第862页)
理就是道、天理、天道、常理、常道;理也是义、义理。这些终极性的概念,都可以解释理,都可以作为理的替代性概念,都可以表征最高的规范与准则。认识、揭示、表述这样的理,既是圣人特有的秉赋,同时也是圣人的天职或神圣职责。因为,“圣人视亿兆之心犹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文明则能烛理,故能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故能尽大同之道”。(第764页)既然只有圣人才能发现这样的理,那就意味着,只有圣人才是最高规范的表述者,其实就是最高的立法者。三代以后,孔子就是这样的圣人,就是这样的立法者。在孔子身后,只有那些能够传承孔子道统的人,才能够成为这样的立法者。后文的分析表明,程颐本人就有这样的法理担当。
次说礼。《程氏易传》既讲理,也讲礼。相对于理的自然法属性,礼作为各类主体普遍遵循的日常性规范,具有实在法的特征与属性。针对《履》卦,程颐认为:“夫物之聚,则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恶之分,是物畜然后有礼,履所以继畜也。履,礼也。礼,人之所履也。为卦,天上泽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为履。”(第749页)这里所说的“人之所履”,就是人所践履的礼,换言之,礼就是世人实际遵循的规范。针对《乾》卦,程颐说:“得会通之嘉,乃合于礼也。不合礼则非理,岂得为嘉?”(第699页)针对《归妹》卦,程颐又说:“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第979页)
这些论述表明,在礼与理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理之当”即“礼之本”。理是礼之根本,礼源于理,礼是理的表达与延伸。另一方面,不合礼则不合理,这就是说,礼与理是一致的,两者对人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准确地说,两者不能相互冲突,两者应当保持相同的指向。在某些方面,两者甚至具有相同的特征。譬如,理是变易的,礼也是变易的,正如程颐所言:“‘礼,孰为大?时为大’,亦须随时。当随则随,当治则治。当其时作其事,便是能随时。”(第171页)
再说法。从《易传》全书来看,程颐关注的规范,首先是理,其次是礼,最后是法。他也注意到了法的作用。他说:“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第1219页)这就是说,道为体,法为用。道与法,或理与法,具有体与用的关系。由此看来,在程颐建构的规范体系中,法作为“道之用”,亦即“理之用”或“体之用”,也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就法的功能来看,针对《噬嗑》卦,程颐说:“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第804页)根据这个论断,法具有预防或保障的功能,是一种后盾性质的规范。在通常情况下,法主要体现为刑。譬如,针对《蒙》卦,程颐写道:“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当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苟专用刑以为治,则蒙虽畏而终不能发,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第720页)因此,“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罚,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渐至于化也。或疑发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诛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第721页)这些论述,主要在于强调:“立法制刑”与“教化”都很重要。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立法”甚至还应当走在前面,通过“立法”,首先“去其昏蒙之桎梏”,接着再施以教化,那就可以成就理想的“治化”。因此,“立法制刑”乃是“圣人为治”的第一个环节。
当然,在“立法制刑”的实践过程中,还应当把握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慎刑”原则,要避免轻率地使用刑罚。具体的要求是,“君子观明照之象,则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于慎明,而止亦慎象。”(第990页)其二是“清刑”原则,“清刑”就是“清简”施刑,其实就是“轻刑”,主要在于体现仁厚之德。“在上者志存于德,则民安其上;在上者志在严刑,则民思仁厚者而归之。”(第1138页)恪守仁厚之德,“圣人以顺动,故经正而民兴于善,刑罚清简而万民服也”。(第779页)
(二)君·臣·民:主体的类型
《易传》既分述了规范的形态,同时也辨析了主体的类型。在法理上,这里所说的主体可以理解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根据现代的法学理论,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与其他组织。在程颐的法理世界中,法律关系的主体首先是君,然后是臣,在君臣之外,还有民。当然,在君、臣、民三类主体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在传统中国的法理学中,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强调平等的原则与观念,《程氏易传》所表达的法理学也不例外。
先看君。在《易传》中,程颐习惯于以“九五”之位代表君主之位。他说:“九五居人君之位,时之治乱,俗之美恶,系乎己而已。”(第801页)这就是说,治理天下,关键的因素是人君。人君既然占据了最高的地位,当然也应当具备最高的德性:“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众而君临之,当正其位,修其德。”“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过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归附者,盖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来之。”(第934页)君之德必须配得上君之位,人君如果失去了君之德,德不配位,也就失去了为君的资格。针对不同的卦,程颐阐述了君之德所包含的若干要素,譬如任贤、无逸、听取天下之议,等等。这些要素,既是对君之德的列举与解释,其实也是在为君主设定相应的义务。
譬如任贤,它的实际含义是:君主应当任贤。这是一个典型的义务性规范。针对《睽》卦,程颐说:“五虽阴柔之才,二辅以阳刚之道而深入之,则可往而有庆,复何过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兴盛王之治;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贤圣之辅,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第893页)君主如果偏于阴柔,那就应当依赖阳刚的贤臣。在历史上,像周成王、刘禅那样的君主,就要充分任用周公、孔明那样的贤人,并在他们的辅佐下造就中兴的局面。
再譬如无逸,它的实际含义是:君主应当无逸。针对《豫》卦,程颐认为,“六五以阴柔居君位,当豫之时,沈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耽豫而失之于人,危亡之道也。”(第782页)这里的“豫”就是“逸豫”或“逸乐”,倘若阴柔之君沉溺于逸豫,那就会滑入危亡之道。因此,“无逸”也是君主应当遵循的义务性规范。
同样,听取天下人的议论也是君主应当履行的一个义务。针对《履》卦,程颐写道:“古之圣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刚足以决,势足以专,然而未尝不尽天下之议,虽刍荛之微必取,乃其所以为圣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刚明,决行不顾,虽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刚明之才,苟专自任,犹为危道,况刚明不足者乎?”(第752页)这几句话,体现了程颐为君主设定的一项义务:要听取“天下之议”,不可“自任刚明”,不可刚腹自用,不可一意孤行。
再看臣。程颐以“为君之道”为君主设定了义务,同时也以“为臣之道”为大臣设定了义务。针对《坤》卦,他说:“为臣之道,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柔顺之道也。可贞谓可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从上之事,不敢当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终耳。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第709页)关于这样的“为臣之道”,程颐还针对《随》卦,给予了进一步的解释:“为臣之道,当使恩威一出于上,众心皆随于君。若人心从己,危疑之道也,故凶。”(第786页)这样的“为臣之道”主要在于强调,为臣者应当自觉维护君主的形象与权威,不要去抢君主的风头。
为臣者面对君主,既应当恪守“柔顺之道”,但也要坚持“自重之道”。为臣者要有自尊心,不可“降志辱身”。针对《比》卦,程颐说:“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至,然后出也。”(第740页)针对《蒙》卦,程颐又说:“贤者在下,岂可自进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第719页)程颐是这样说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根据朱熹的《伊川先生年谱》,程颐在履行“侍讲”之职的过程中,“容貌极庄。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重事,或侍立终日不懈,上虽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问先生曰:‘君之严,视潞公之恭,孰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第342页)这里的潞公,是指位高权重的文彦博(1006—1097)。依程颐之意,像潞公那样的权臣,在幼主面前,如果不够恭敬,可能会给人留下欺负幼主的印象;但是,像自己这样的没有权势、没有根基的一介布衣,则不必有潞公那样的顾虑,反而应当更多地保持自尊、自重。
还有民。在《程氏易传》中,民既是“人民”,也是“下民”。作为程颐法理世界中的主体之一,民的特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与王者(君主、君上)相对应,人民是人君“养育”的对象。针对《无妄》卦,程颐说:“天道生万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第824页)针对《泰》卦,程颐又说:“民之生,必赖君上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遂其生养,是左右之也。”(第754页)这就是说,人民之生,有赖于人君之养,这是着眼于政治上的尊卑,就君与民的关系作出的一个论断,在这样的关系中,人君作为“主民者”,应当“体天之道”,防止“民心既离”,否则,就将像《姤》卦所示:“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为上而下离,必有凶变。起者,将生之谓。民心既离,难将作矣。”(第927页)人君“养育”“教率”“辅翼”人民,自觉成为人民的主心骨,民心就会归向君主。
另一方面,下民与君子相对应,下民是君子教化的对象。针对《观》卦,程颐说:“小人,下民也,所见昏浅,不能识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谓之过咎,若君子而如是,则可鄙吝也。”(第799页)针对《履》卦,程颐又说:“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第750页)这是着眼于文化与心智上的高低,就君子与下民的关系作出的一个论断:君子与下民的关系主要是一个文化、心智上的高低关系。相对于民,如果说君主是政治上的担纲者,那么君子则是文化上的担纲者。根据程颐之见,在君子面前,下民没有见识,缺少智识,只能通过君子的教化,才能让下民的心志有所凝聚,有所锚定,不至于“泛若不系之舟”,这是在文化层面上实现天下大治的必要环节。
在君、臣、民三者之间,君虽然居天下之尊,但是,臣也很重要。只有把君臣关系调整好,才能造就良好的政治局面;因为,“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第925页)这就是说,仅仅有圣君,还是很不够的,圣君还需要贤臣与之配合,“贤才见用,则己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泽”,(第949页)因而,“君臣合力,刚柔相济,以拯天下之涣者也”。(第1003页)君臣之间的这种“合力”“相济”的结构,在宋代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宋代较之于其他朝代,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君臣“同治天下”。〔9〕这样的“同治”或“共治”在总体上提升了臣的地位。至于民,在“主民”的观念下,主要是在上者(君、臣)养育、教化的对象,总体上居于被动地位。
(三)辞·意·象:法律存在的方式
在程颐描绘的法理世界中,“理、礼、法”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规范,“君、臣、民”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主体。在此之外,程颐对中国传统的法理学还作出了更具个性化的贡献,那就是通过“辞、意、象”所展示的三个维度,揭示了法律存在的三种方式。当然,“辞、意、象”与《程氏易传》所依托的《周易》具有紧密的联系,归根到底,还是由《周易》派生出来的。
在经验层面上,可以看到,法既可以表现为言辞,譬如条文、语言;也可以表现为意义,包括法意、法理;还可以表现为符号,譬如法槌、法袍。因而,如果从法理层面上提问:法律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或者问:法律以什么方式存在?回答是:法律既以言辞的方式存在,又以意义的方式存在,还以符号的方式存在。法律存在的这三种方式,可以在《易传序》中找到依据:“《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第689页)程颐的这段话,主要阐明了辞、意、象三者之间的关系。
立足于法律的存在形式,分而述之,辞相当于法律的条文。在《程氏易传》中,辞主要是指《周易》中的卦辞、爻辞。一部《程氏易传》,就在于解释这些言辞。在程颐看来,无论是“吉凶消长之理”,还是“进退存亡之道”,都需要通过辞来承载;没有辞,理与道将无处挂搭。见于《周易》的古代圣人之道,虽然包含了辞、变、象、占四个方面,但是,相比之下,辞在其中占据了更加关键的地位,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辞’,谓于言求理者则存意于辞也。”(第1030页)辞不仅仅承载了道与理,还可以为“观象”提供指引,“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第615页)只有通过辞,才能理解象的含义。
意相当于法律的含义,亦即法所蕴含的理。程颐所理解的意,主要是理。就《周易》本身来看,意代表了一种通称。在王弼那里,意的实体内容是无,正如他的一个论断所言:“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10〕但是,在程颐这里,意的实体内容是理。理也是道,因此,辞之理,辞之道,都可以归于辞之意。程颐作《易传》,就是为了把《易》所蕴含的意(理、道)揭示出来,以之作为世人遵循的准则,以之规范君、臣、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就辞与意的关系而言,你看到了辞,但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辞之意(道、理)。《程氏易传》就是为了揭示辞背后的意(理、道)。当然,如果你不知辞,那么,辞蕴含的意(理、道),你也是不可能掌握的。因此,你不能避开辞,亦即不能避开《周易》中的卦辞、爻辞。如上所述,程颐特别强调,他的《易传》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辞,他希望通过“传辞”以“得意”。在“传辞”与“得意”之间,“传辞”是方法,“得意”是目标。由此看来,《程氏易传》与唐代出现的《唐律疏议》具有同工异曲之妙。所谓“同工”,是说两者都在于揭示辞背后的意(理、道)。所谓“异曲”,是说两者分别针对《周易》与《唐律》(亦即《永徽律》)。进一步看,《唐律疏议》解释的对象主要是刑律,《程氏易传》解释的对象是《周易》——它作为居于核心地位的经,实为传统中国“无上之法典”。换言之,《程氏易传》所揭示的《易》之意(理、道),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无上之法典”之意(理、道)。
象相当于法律的符号,它显现于外,具有“至著”的特征,可以视为法律的原型与本喻。上文提到的法槌、法袍,此外,还有像天平之类的符号,都可归属于法律之象。在《易传》中,程颐反复述及法律之象。譬如,针对《噬嗑》卦,程颐认为:“雷电,相须并见之物,亦有嗑象,电明而雷威。先王观雷电之象,法其明与威,以明其刑罚,饬其法令。”(第803—804页)“雷电之象”具有明与威的性质,恰好可以充当法律之象。又譬如,龙可以作为圣人或圣王之象,针对《乾》卦,程颐写道:“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初九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阳气方萌。圣人侧微,若龙之潜隐,未可自用,当晦养以俟时。”(第695—696页)不同的象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意(理、道)。从根本上说,“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第615页)通过不同的象,可以理解不同的意(理、道)。
在辞、意、象之间,程颐关于辞与意的论述较多,但也没有忽略象的价值与意义。源于《周易》、经过程颐重新阐述的辞、意、象,对于我们理解法律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从《程氏易传》的法理旨趣看程颐的法理担当
透过程颐的“年谱”或“行状”,可以发现,程颐对两件事情尤其重视。其一是《易传》的酝酿、写作、修改、完善。对此前文已有交待,这里不再重复。其二是担任“侍讲”之职。据《宋史》记载,程颐甫任“崇政殿说书”,就针对皇帝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显然,程颐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方案,把君主培养成为圣德完备的圣君。在实际履行“侍讲”职务的过程中,程颐可谓慎重其事,“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有一次,“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11〕还有一次,“讲罢,未退,皇帝忽起凭栏,戏折柳枝。先生进言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皇帝不悦。”〔12〕这些事例表明,程颐总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化君主,抓住一切机会教化君主,不惜小题大做,只希望按照古代圣王的标准来培养、塑造君主。就程颐的精神追求与生命寄托来看,教化君主最为重要。揣摸程颐的心迹,可以看到,如果能够把他面前的君主培养成为儒家道统中的圣王,那就是他能够作出的最大功绩。
至于创作《易传》,则是担任“侍讲”的继续与延伸。根据《程伊川年谱》,早在1056年,亦即在程颐24岁之时,他对《易》已有深刻的理解。其时,他与张载论《易》,就颇受张载的称赞,张载甚至承认,程颐“深明《易》道,我所弗及”。〔13〕然而,此时的程颐并不急于著书阐《易》,直至晚年,才把自己对《易》的理解著成《易传》。程颐关于轻与重、先与后的这些选择,可以解释为:如果能够以“侍讲”的身份直接教化君主、培养圣君,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就不妨后退一步,站在远远的地方,为不特定的君主写一部法理学教科书,借以告诉君主“应当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这既是程颐创作《易传》的旨趣,同时也反映了程颐的法理担当:以儒家法理教化君主。至于教化君主的具体方式,则可以有两种:其一,通过“侍讲”一职当面教化某个特定的君主;其二,通过《易传》一书隔空教化某些不特定的君主。
从中国法理学漫长的演进历程来看,《易传》其书的法理旨趣与程颐其人的法理担当,与程颐推崇的孔子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与可比性。孔子是最具代表性的儒家圣人,程颐也有这样的自我期许。据《宋史》:“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尝言:‘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14〕
见于正史中的这段文字表明,程颐的人生理想就是“至乎圣人”,更具体地说,就是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一代圣人孔子,虽有圣王之德,却没有圣王之位,所以只能做个素王。孔子作为有德无位的素王,最具标志性的成就当属《春秋》的编纂。《史记》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按照孔子的自我评价:“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5〕《春秋》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传统中国最高的法典,正如程颐在《春秋传》中所言:“夫子之道既不行于天下,于是因《鲁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第1086页)《河南程氏遗书》亦称:“上古之时,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第245页)这就是说,作《春秋》的孔子,其实是一个立法者,而且制定的是“百王不易之大法”。《春秋》既是“百王不易之大法”,其实也承载了“百王不易之法理”,亦即最高的法理。作《春秋》的孔子既是根本大法的制定者,也是最高法理的阐述者。
如果孔子通过《春秋》的创作,为“百王”规定了不容变更的根本大法与最高法理,那么,程颐则通过《易传》的创作,试图为后世的君主提供他们应当遵循的根本大法与最高法理。程颐试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下,以自己的《易传》呼应孔子的《春秋》,以自己的《易传》作为自己“学圣人”,“以圣人为师”,最终“至乎圣人”的标志与载体。在早期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程颐已经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写道:“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第577页)这就是说,圣人是可以学习的,圣人的境界、气象也是可以抵达的。倘若要进一步追问:“圣人如何学而至欤?”那么,程颐的选择显而易见:作《易传》。换言之,程颐试图通过创作《易传》,以实现“至乎圣人”的目标。程颐的这种选择,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蕴。
一方面,体现了程颐所追求的“以圣人为师”。程颐试图学习的圣人,主要就是孔子。如前所述,孔子很看重自己的《春秋》,但孔子也很看重《易》。《史记》已经载明:“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16〕由此看来,晚年的孔子希望通过数年的研习,对《易》形成透彻而全面的理解。孔子晚年是否实现了这样的愿望,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论。但是,孔子的愿望却在程颐那里变成了现实。对应于“孔子晚而喜《易》”,程颐则在自己的晚年著成了《易传》。按照程颐的自述:“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见于书者,皆未尽。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第374页)这句话表明,程颐著《易传》,有一个主要的动因就在于:“孔子赞《易》之后”,没有人“会读《易》”,没有人提供关于《易》的正解。因而,自己必须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职责。由此可见,程颐著《易传》,旨在直接回应“孔子赞《易》”。
另一方面,体现了程颐在“以圣人为师”这个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在此应当注意的是,五经出于圣人,但程颐对五经进行了差异化的处理。他说:“《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17〕这就是说,《春秋》与其他的经还不太一样:其他的经像法律,《春秋》像案例,更准确地说,《春秋》像是一部案例汇编。他还进一步补充指出:“夫子删《诗》,赞《易》,叙《书》,皆是载圣人之道,然未见圣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圣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圣人用处。”(第305页)这就是说,《春秋》主要承载“圣人之用”,《易》《诗》《书》主要承载“圣人之道”。“道”与“用”的关系,就是体与用的关系。这里暂不论《诗》与《书》,单就《春秋》与《易》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用”与“体”的关系。换言之,相对于《春秋》之“用”,《易》之“体”占据了一个更加基础性、本源性的地位。
关于《易》与《春秋》的关系,程颐既以“体与用”来解释,还以“理与法”来解释。在《春秋传序》中,程颐说:“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第1125页)这就是说,《春秋》提供了“法”,有助于“治”。可见,《春秋》的价值主要在于“法”与“治”。相比之下,《易》表征了更加根本的“道”与“理”,就像《易传序》开篇所指出的:“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第689页)这几句话表明,程颐创作《易传》,是希望在“道”与“理”的层面上,弘扬古代圣人开启的圣道与法理。显然,较之于《春秋》承载的“法”与“治”,《易》承载的“道”与“理”依然占据了一个更加基础性、更加本源性的地位。
由此看来,程颐著《易传》,旨在从根本上守护儒家道统与儒家法理,体现了程颐对圣人之道的固本强基与守正创新。
四、结 语
中国法理学史不能避开宋明理学中的法理学,宋明理学中的法理学不能避开“程朱一派”的法理学,“程朱一派”的法理学主要是程颐开创的,程颐的法理学集中体现在《程氏易传》一书中。上文的分析表明,《程氏易传》是一部“讲理”之书,从中国法理学史来看,则是一部“讲法理”的教科书。程颐通过《易传》分辨了三种不同的规范、三类不同的主体,在此基础上,程颐还以“辞、意、象”三个不同的维度,为理解法律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这些源于《周易》、见于《程氏易传》的法理论述,足以成为中国法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程颐借《易传》表达的法理旨趣,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智慧,同时还寄寓了他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在这里,且看程颐关于“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的一个比较:“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第187页)所谓“古之学者一”,是指古之学者所承载的古之道术纯正不杂。相比之下,“今之学者”则出现了三种弊端:有人喜好文章之学,有人喜好训诂之学,有人喜好佛老之学。这三个方向都是歧途,只有儒者之学才能够代表正道。这就是说,只有儒者之学所承载的儒家法理,才能够引领一种理想的文明秩序。根据程颐之意,如果要把儒者之学承载的儒家法理“坐实”,那就是他自己留给后世的《程氏易传》。由此看来,《程氏易传》体现了程颐当仁不让地捍卫儒家法理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