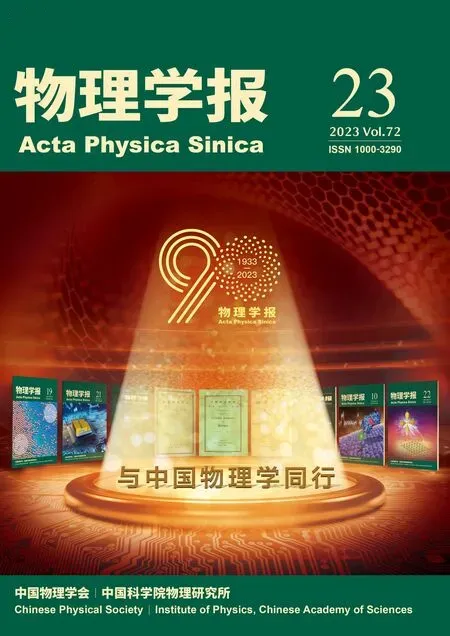关于《物理学报》1974年复刊的一些回忆
吴咏时
(犹他大学物理天文系,盐湖城 UT84112,美国)
《物理学报》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在物理学领域专业性最强的顶级中文学术刊物,向国内外展现、交流中国物理学界在物理学各前沿研究领域中的最新进展和成果.《物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自1933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90 个年头,一直受到国内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的欢迎和支持,以及国际上关心中国物理学发展的科学界友人的关注.回顾学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她的初期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是和当年老一代物理学家的艰辛付出及热忱的努力分不开的.
据《〈物理学报〉创刊70 周年大事记》所载[1],学报创刊至1937年已出版至第3 卷第1 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停顿两年,1939年又开始继续出版第3 卷第2 期.但在1940年第4 卷第1 期出版之后,受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再次停顿4年.除此之外,在1966—1976年共计10年的特殊年代里,学报也无奈停刊7年半,直到1974年1月方始复刊.当年我个人有幸被召集进入学报编委会,参与一些具体工作,略知某些内情.在此纪念学报创刊90 周年之际,回顾50年前的往事,深感学报在1974年的复刊,是学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下来之不易.回忆、记述学报的成功复刊,是一件对历史负责的事.当年的当事人物大都作古多年,忝列末位的我,记忆也变得日渐模糊,倘有不确或错误之处,尚待知情者指正.
学报在1966年夏季无奈停刊,可以一句话简单地说清.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犹如一场猝不及防的超级飓风: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不到三个月就出现全国大串联,正常的科研工作就完全无法进行,大学也完全停课.学报已出版到当年第9 期,但第7,8,9 期没有来得及发行就停刊了.
学报在1974年的复刊,就不是一句话可以简单地说清了.变化的最早信号,出现于1970年,中国乒乓球队获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相继访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并提出他们对国内物理学发展的看法和建言.二位先生在全国各地的学术报告,帮助中国的物理学界走出闭锁的状态,了解世界物理的前沿.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重磅文章.该文拨乱反正,针对贬低理论、忽视基础研究的“极左”思潮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并提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应有做法.广大科研工作者和高校教师深受启发,纷纷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排除干扰,坚定地开始恢复正常的科研和教学的秩序,尽力补救失去的时间,发奋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终于在1977年,迎来了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为标志的“中国科学的春天”.此乃后话.
在70年代前期科学界、教育界这一“拨乱反正”的浪潮中,中国科学院还有物理学界,都是当仁不让,甘当先锋.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创办《物理》杂志后,即积极酝酿、筹备学报复刊.1973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学报复刊,刊期为双月刊,并组建以王竹溪先生为主编的学报编辑委员会,主持筹办复刊的有关事宜.1973年8月,《物理》第2 卷第3 期刊登了《致读者》一文,宣布《物理学报》将于1974年1月复刊.
王竹溪先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他自1944年开始连续担任学报主编,德高望重,自然是复刊编委会主编的不二人选.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收到通知进入学报编委会,感到诚惶诚恐.一方面因为我是1965年夏才从北京大学(六年制)毕业,分配到物理研究所工作.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的科研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干扰,正常的评职程序也随之停摆.同时基本上再没有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科学院.所以直到 1973年,我的职称仍然是最低阶的实习研究员,一直是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人员.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被召集到学报编委会.另一方面,中国物理学会委托物理研究所管理学报的出版事宜,我在编委会内可以协助老一辈卓越的物理学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务性工作,也是一个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特别是主编王竹溪先生,我在北大念书时,就聆听过他教的热力学本科课程,也钻研过他的《热力学》《统计力学》以及《特殊函数论》(和郭敦仁合著)等专业名著.还有副主编朱洪元先生,我听过他关于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现象学分析的系列学术讲座,也钻研过他的名著《量子场论》.编委中这些老一代的物理学家(还包括戴元本先生),都是引导我入行科学研究的导师.他们都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我愿意协助他们做些事务性的工作,以节省他们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在一次私下的机会,我向王先生表达我资历浅薄,怕做不好工作的担心.他劝勉我一番,说他当年就是30 多岁就担任了学报的编委,这也是个磨练的机会.我也就决心尝试挑起这副担子.
那次见到王先生,离我本科上他的课时,已相隔12 个年头.他的身形较前更为瘦峭,但依然神采奕奕、精神瞿烁.同时,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的岁月和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的磨炼,所带来的沧桑和憔悴也依稀可见.我一方面为他挺过来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又钦佩他不计前嫌(“文化大革命”前期无端受到批判)、不顾疾病(据说是血吸虫病)为科研、为教学和为学报殚精竭虑的工作热情.直到1982年(他去世前一年),王竹溪先生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内,兢兢业业主持学报的出版工作.他是学报历史上大家特别敬重和特别怀念的一位主编.他过世后,中国物理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物理学报》编委会在学报发表《悼念》指出:“王竹溪教授在从事物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主持中国物理学报四十年.”“在主持学报工作中,他忠诚地贯彻办刊方针,坚持原则,处事秉公,奖掖后进,平易近人,为办好物理学报和在我国促进物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 从1973年参加学报复刊的筹备到1982年底离开学报编委会,我这10年的经历就是以上悼词的见证,它也表达了我现在深切怀念王竹溪先生的心声.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回顾1974年学报复刊后头五年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第一条,当然是复刊的时机选择恰当.当年在“极左”思潮横行的特殊时期要想办好学术刊物,是有风险的.学报复刊后坚定抵制“极左”思潮的干扰,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为后来科学界的改革开放开了风气之先.第二条,积极推动物理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1974年7月,授权美国物理学会委托杨振宁先生组织华人科学家翻译《物理学报》,以刊名“ChineseJournalof Physics”(ActaPhysicaSinica)英文版双月刊出版,全世界发行,出版了3年[1].1981年起又授权美国物理学会编译出版名为《中国物理》(Chinese Physics)的英文刊,选译《物理学报》等我国12 种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在该刊发表,并被SCI-CD(光盘版)收录,直到1992年底共出版12 卷[1].这些措施,有效地扩大了特殊年代里国内的前沿优秀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仅在我个人熟悉的一些领域里,比如于渌和郝柏林的《连续相变临界指数的骨架图展开》[2],石赫、许以超和郝柏林的《三维晶格统计模型的一种封闭的近似解》[3],陈金全、王凡和高美娟的《群表示论的物理方法 (I)—(V)》系列文章[4–8]等等,还有粒子理论层子模型[9],规范场拓扑对偶荷[10]等方面多篇文章,在当时学报发表后就有国际的可见度.第三条,在学报上公开发表科学界的争论文章.这一点我特别提出来,因为这是学报编委会于1974年9月召开会议(由副主编李荫远先生主持),专门讨论学报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决定的.我个人是支持在保持良好氛围的条件下进行公开的科学争论的.一个例子是在“经验交流”栏目里,学报在复刊后发表过两篇文章[11,12],对陆启铿、邹振隆和郭汉英[13]的《典型时空中的运动效应和宇观红移效应》一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我们现在也应该提倡在良好的氛围下进行公开的科学争论.
回望90年,学报从创办初期的艰难到复刊,再到今天的发展,来之不易;展望未来,预祝《物理学报》与时俱进,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