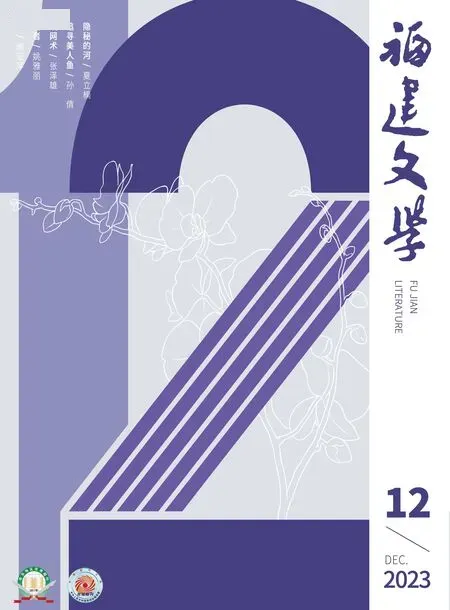走出与回归的尽头
万小英
1
“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2000多年前,《山海经》记下了两个从海里生长出来的地方。闽是福建,瓯是温州一带,它们原是一片浅海乱流,岛屿星罗棋布,先民在海沙江泥沉积形成的湿地上,经历沧海变桑田,又从桑田变城市的神奇变化。它们原本都是越王勾践的领地,只是后来被越王族子孙分出了闽越与瓯越。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天下划郡,它们同归为闽中郡。说起来,两地曾是一家人,所以,当我从福州来到温州的时候,自然生出亲切。
走在温州,尽管都是坚硬的实地,但每一步仿佛都能碾出水来,因为地名总是在提醒这里曾经是被统治。“海”“江”“溪”“汇”“塘”“屿”“河”“桥”等字眼在道路、街区、乡村的名字里随处可见,在高楼水泥间,固执地保留了远古的“化石”。
就像瓯海区娄桥街道河庄村,温州的一个普通村子,名字里有海,有河,有桥,表明河上之庄曾经是小桥流水人家。今天的它,已然变了模样。森马集团的大厂区,品牌林立的中国(瓯海)眼镜小镇,驾校的练车场,挤挤挨挨的民房楼栋……河庄有8000 外来人员,本村人口2000,但大部分在外面做生意。处于城市化边缘的河庄,虽称为村,其实田地、务农、野趣等农业模式与农村生态逐渐衰微。这并不是最令人惊讶的部分,让人最震惊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区区几年间。时代的翻天覆地,裹挟着人们往前奔,身在其中的人不免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觉:太快了!变化太快了!他们常常仰头望着繁华的高楼,低头脑海中浮现出这里曾经的模样——田地里,他们挥着锄头流着汗。
百年榕树静立村中。“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草木的无情,在于“依旧”,任世事沧桑变化,依然姿态不改站在原地。但也可以说,草木的深情,也在于“依旧”,一切皆变,唯我不移,成为守护的坐标。温州的市树是榕树,是的,和福州一样,只是它特指小叶榕。小叶榕在叶形上比之其他的榕树更为秀气一些,但一点也不要小瞧它的韧劲,台风暴雨过境,它总能繁茂如初。听到一个有趣的说法,以温州为界,往北就很难再见到小叶榕的身影。那么,小叶榕替温州绣了一道翡翠的边,或者用坚定的姿态为温州站了岗。河庄百龄以上榕树有三五棵,岁月沧桑,它们依然葱茏又从容,注视着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对个人而言十分重要的“走出”。河庄有户张姓人家,祖籍陕西凤翔府,后来迁贵州,最后来到这里,当时叫永嘉县吹台乡十六都河庄。到张锦这一代,家族有了起色。乾隆辛卯年(1771),张锦中了武举人,封朝议大夫。可能做得不错,他死去的父亲张兆享,还被追赠“中宁大夫”的官职。1776 年,张锦的一个孩子落地,就是张瑞溥。他在家里排行老大,为人洒脱开朗。
张瑞溥也走上了仕途。起初在“同知”里打转,在安徽、四川、重庆等各地当“同知”。同知就是知府的副职,是清朝正五品官员,负责分掌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事务。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张家走出了河庄,移居温州城中。
张瑞溥孔武有力,有智谋。嘉庆十九年(1814),他带领上百兵士,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剿灭乱匪的巢穴,竟然破贼四千余人。还有一个长期在官府挂号的积案被他破了。巨寇刘大靴纠合党羽数千人,横行当地,苦了百姓,多年都无法将他抓捕归案。张瑞溥上任后,艺高人胆大,趁刘大靴还乡扫墓之时,独自前往,用计将之擒获。他这般平叛乱、擒巨寇的壮举,连皇帝都知道了,特意召见了他,打量之下,对他的状貌称奇。我没有找到张瑞溥的画像,不知他的模样,不过连皇帝都称奇,应该是有过人之处吧。
道光初年,北京天坛要树杆木,那可不是一般的木头能行的,张瑞溥奉命到成都办理此事。他找了两年,终于得到了长13 丈的巨木。这么长的大木头运回去是个大问题,果然,走到北京通州时,堵住了水运。这个影响就大了,张瑞溥遭到御史弹劾。
道光四年(1824),皇帝召见,升他为湖南粮储道,掌督运漕粮。他起先还很有干劲,但是不久,因为与巡抚康绍镛不和,他萌生退隐之意:“吾官三十余年久,欲退矣。”做了30 多年的官,太久了。于是引疾归里,回到温州。
2
古人的退隐,往往意味着他要开始寻找自我,寻找人生最终的价值意义。张瑞溥从河庄走出,建功立业,算是比较成功,但如果只到这里为止,也就是古代官员普通的一生。说张瑞溥从河庄的“走出”十分重要,并不在于他所取得的仕途官职,而是在营营扰扰大半生后,他能够沉淀思索,找到安身立命的本心,将沉潜已久的梦想唤醒,去实现它,完善它。
张瑞溥在温州城建了一座“如园”,这是他袒露心中挚爱的园林,向中国山水诗鼻祖、东晋大诗人谢灵运致敬的方式。这份爱得到了时间的回应,如园如今成为温州的名胜之地。
谢灵运在永嘉(即温州一带)做过郡守,当时有些不得志,所以寄情于永嘉山水,没想到成为永嘉山水的发现者、传播者,不到一年时间,他游山玩水,写下了20 多首诗,瓯越之地开始走进中原文明的视野。谢灵运在积谷山麓开凿池塘,人称谢池,临池而建的木结构楼屋是其居所“池上楼”,《登池上楼》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的正是这里。北宋温州知州杨蟠规划三十六坊时,将这里划为“谢池坊”。
道光五年(1825),张瑞溥辞官还乡,在谢池旧址旁购地十多亩重建池上楼,还筑有怀谢楼、春草轩、鹤舫、十二梅花书屋、飞霞山馆等,取名“如园”。如园如园,如什么园呢?是如谢家之园,也是如张瑞溥心中之园吧。
园内亭台楼榭,曲径通幽,水流潺潺,暗香浮动。晚清封疆大吏、有“中国楹联学开山祖”之称的梁章钜,在这里留下一副楹联:“楼阁俯城隅,一角永嘉好山水;风流思太守,千秋康乐旧池塘。”永嘉山水与风流太守相得益彰。
今天,游人们在“池上楼”“春草池”“春草轩”盘桓,吟诵着“池塘生春草”诗句,满脑子大概都是谢公的风采,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想起张瑞溥这个真正的主人吧。他建园“以存谢公之旧”,就是将千年前的谢公留下,让他的身影与绪怀在这片土地萦绕,让名楼与名句有了具象的依托。这就是温州人对“知音”的报答与缱情。它所在的巷弄也渐渐成为一条名巷,集聚了“一代词宗”夏承焘、金融家周守良、瓯海医院首任院长杨玉生等名人。
张瑞溥并非只是将如园作为寄情、栖居之地,而是有精神意涵在内。他在如园监督儿子读书,数年不出门。后代在园中生息,出了不少才俊栋梁。
如园第二代主人张应庚,官至广东连平州知州,著有《寄沤吟草》;第三代主人张志瑛,官至湖北候补通判,署汉阳府通判;第四代主人的大房长子张之纲,成为中国近代著名金石学家;第五代张亦文是我国著名土木建筑专家、教授,20 世纪80 年代参与设计建造开封“清明上河园”主体工程,荣获国家重奖,著有《清明杂谈·从‘清明上河图’谈起》;第六代张珍怀,是张之纲之女,是当代著名女词人,著有《飞霞山民诗选》《清词研究》等。
张之纲,晚号谢村老民,童年在如园的池上楼度过。父亲赴汉阴府任职,他便随父去了湖北,从师皆一时名士。清光绪丙戌年(1886)秋,19 岁的张之纲因乡试返回家乡,登池上楼远眺,感慨而抒,其中有句:“挂冠还故林,谢公时迹在。筑楼聊登临,水心宅幽奥。高风振歧海,嘉会图山阴。”
张之纲对古文字感兴趣,也很好学。听说浙江瑞安藏书家孙衣言学识渊博,就去求问解悟,并与孙衣言之子孙怡让(后成为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古文字学家、近代教育家)成为莫逆之交。他们朝夕研论,激励共勉,探讨周秦以上古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纲中举人,开始仕途。辛亥革命后,在财政部任职。1930 年,决意隐退,辞官移家寓居上海,托迹于商贾间,在银行任职。当时他已年逾六旬,叹息道:“天地闭贤人,隐隐今其时与!”这是化用《易经》里的“天地闭,贤人隐”,意思是在乱世,贤人隐退匿迹正当时。
三十载宦途,让他感到岁月蹉跎,学无所成。在生命的最后旅程,该如何抉择,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退隐下来的张之纲如同他的先祖张瑞溥,在内心求索答案。他想起了少年时对古文字的痴迷、热爱。
“笺金功亦似镌金,冥索穷搜到惬心。”60多岁的张之纲开始钻研古文字,埋头著述。他在一本书中追忆:在宣南写稿的时候,暑雨连旬,老树荒庭,屋漏尽湿;那时候老妻还在世,昼夜忙着帮他转移书桌帷帐;对这些困难,他处之泰然。这样的笃志为学,让他接连写下《毛公鼎斠释》《契亭金文校释》《周书逸文征》《周书汇会解释注》《说文解字缘隙》等书,成为温州近代古文字考古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下启史学家刘节、夏鼐等人。
“一春镇与病为缘,欹枕听残漏滴圆”“墨致义公推卜繇,刀从纤劲察书形”,这是张之纲在上海写给好友刘景晨信中的诗句。那时候在病床上,靠在枕上,残夜将尽,他还在听着什么。听着什么呢?无人知道,可能是窗外的风声,可能是青铜器上遥远的凿字声,可能是故乡池上楼的梅花飘落声……
1939 年,时年73 岁的张之纲因病在上海去世。
3
人老归家,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张之纲没有再回到故乡河庄。但是,张瑞溥回来了。史料里有一段:“道光十一年(1831),张瑞溥卒于里第,年56 岁。墓在河庄。”对张瑞溥来说,有着池上楼的如园,是生命里最美的梦,而河庄,是最踏实的归宿。
不清楚张瑞溥暮年再次回到河庄,是怎样的状态,是否还能在村里走走,或者只能通过窗子看看外面的天空。我想,他一定是可以看到河庄榕树的,那庇护的枝臂,浓密的覆荫,仿佛将整个村子都包容起来了,让人感到无比的安心。
张瑞溥回来了,当年那个带着泥鳅干和灯芯草走的人回来了。河庄的人凡外出求学、经商、当兵等,必在行囊里装上泥鳅干。泥鳅干的做法特别,用稻谷壳和泥鳅一起翻炒,不易焦,又很香。在外若有水土不服,便吃它,也有将泥鳅干磨成粉末泡水喝。河庄原本水田多,在里面钻来钻去的泥鳅多,所以泥鳅干携带的其实就是故乡的水土。张瑞溥当年离开河庄的时候,肯定是要带泥鳅干的,那代表的是游子的故乡。
那时候的河庄,长着茂密的灯芯草,茎圆细而长直,芯能燃灯。灯芯草用处很多,用茎纺织,可作草席、枕席等;还可作中药泡凉茶,有利水渗湿、清心经热之用,小孩子发热受惊,可以喝。剥灯芯草是河庄祖辈留下来的传统手艺。张瑞溥离开河庄时,一定也会带上灯芯草,它是油灯里的光,是受惊时的药,是安枕的席——这多么像是在形容“故乡”的含义:故乡,就是我们的光,我们的药,我们的席枕啊!张瑞溥这次回来,大概也是躺在家乡灯芯草做的席枕上吧。
张瑞溥回来了,当年那个在法因禅寺顶礼拜佛的人回来了。从前禅寺四周环水,位于水中央的小岛。不远处是凤凰山,相传凤凰一边飞一边下蛋,蛋就化作一溜的岛屿或地块,禅寺所在之地就是其一。法因禅寺据说最早建于宋乾德年间,距今已有上千年,后来经过多次损毁重修。张瑞溥当年离开河庄,肯定曾到寺里烧香祈愿吧。禅寺以“法因”为名,大约源自佛经中一句“法因心起,还由心灭”,一切都是心。张瑞溥在故乡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是心起心灭。
今天的河庄,已经找不到张家的老宅,张瑞溥的墓在哪里,也无人知晓。只有三五座残垣断壁的门台,泄露一些往昔的生活气息,其中是否有一座是张家之宅呢?方形土门的瓦檐台顶上,野草繁茂,砖头上雕刻的花纹,如同没有发出去的历史的明信片。
河庄的桥与河,也模糊了,有时分不清哪是桥哪是路,哪是河哪是溪。法因禅寺也与陆地连成一片了,只有一面环水。泥田没有了,泥鳅也就没有了,泥鳅干不再是河庄临别时的缱绻。剥灯芯草的手艺也正在慢慢变成旧俗传说,河庄只有一户人家还在守着它。
我去潘秀媚大妈家的时候,她外出不在。热心的同村邱崇碎老伯在她回来后拍了视频给我:潘大妈样子素净,手里拿着一把干燥的淡黄色的灯芯草,笑意盈盈。这一下子就让我释怀,尽管很多东西如逝水流迁,已经不存了,但农妇温和的笑,仿佛很多东西回来了。
张瑞溥、张之纲,不,也包括张家,包括无数的我们,都是从家乡走出,在外漂泊、奋斗,很大程度都是在做好别人眼中的自己。张瑞溥是幸运的,在如园找到了自己,“复苏”了谢灵运的诗魂,而且,生命最后一刻叶落归根,回到故乡的怀抱,得了中国人心中的圆满。
更多走出去的人,还是如张之纲,魂梦无依,没能再回到地图上的故乡。不过,他们也在以一种方式找到归宿。张之纲60 多岁拾起少年梦想,钻进了古汉字里,那个时候,他就是回到了少年,回到了心灵起初的地方,那是心灵的家乡。
人的一生,不停地来来回回。为何而走,为何要回,回到哪里,有的人会思考,有的人不愿想。为什么我们总是对故乡充满着不可消解的情结?因为故乡就是我们最强韧又最脆弱的心灵——所以,故乡的尽头是走出,也是回归;心灵的尽头是走出,也是回归。
榕树的枝叶此刻在伸展,仿佛岁月的腰肢松了一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