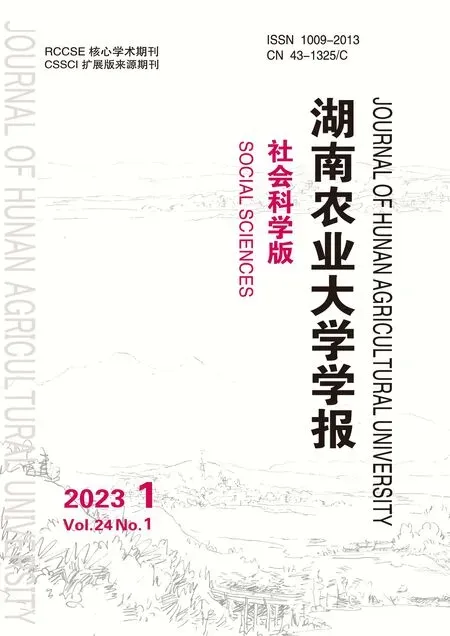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张连刚,史晓珂,彭志远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张连刚,史晓珂*,彭志远
(西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社会网络;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工资收入;身份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提升城镇化率,而且还要提高城乡融合的质量[1,2]。《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促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稳定提升的关键任务。《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条件,努力提高其城市融入水平。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国家统计局《2021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外出农民工总量为2.93亿人,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然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这就意味着农民工虽已搬入城镇,但他们却无法在城镇永久留居。此外,据2017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在符合落户的条件下,农民工愿意在流入地落户的比例仅为35%。城市定居意愿不仅是农民工迁入城市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问题,学界已经开展了较多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户籍制度。制度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受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的迁移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农民工离开所居住的村庄;第二个过程是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下来[3]。在此过程中,受户籍制度影响的农民工不能按预期顺利迁入城市,并获得城镇居民户口,于是造成户籍人口城镇化比例过低[4]。这也表明,目前中国仍需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实施以农民工落户为主要任务的新型城镇化建设[5]。第二,社会融入。首先,经济因素在农民工迁移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农民工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是其在迁入城市实现定居的物质基础。其次,已经迁入的农民工需要适应迁入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经历社会层面的融入[2]。同时,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过程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6]。最后,农民工在完成生存适应后,获得观念和身份的认同并实现在心理层面的融入,这成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7]。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个体要实现其市民化,必然要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完全适应迁入地[8,9]。
除了上述户籍制度和社会融入两个主要因素,社会网络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也倍受学界关注。一方面,农民工依靠原有“血缘”“地缘”关系,在流入城市后,结识由于“业缘”产生的人际关系网,并建构新的城市关系网络[10],同时凭借新的社会网络信息传递功能,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为自身就业和增收创造条件[11-13]。另一方面,农民工是“理性经济人”,社会网络不可避免被其视为一种工具性资产。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后,需要付出诸多心理、劳力以及时间成本去维护自身的社会网络,从而使其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达到最大效用。随着农民工参与新的社会组织,以及与组织成员产生互动,其自身的角色和城市身份也会不断进行更新。这不仅使农民工对自身身份认同有所提升,也使其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带来积极影响[14]。
鉴于此,笔者拟采用社会网络中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研究其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社会融入、创业等因素的影响[11,14-16],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社会网络这一无形资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着何种影响,本研究将从新的视角展开讨论;第二,本研究从农民工工资收入、身份认同两个层面,深入探究社会网络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社会网络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异质性,为提升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率和加快发展新型城镇化提供事实依据和启示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直接影响
农民工离开家乡流入城市,需要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构建的过程包括关系的“脱嵌”和“嵌入”[17]。“脱嵌”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进城后,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模式,甚至变得不再习惯农村生活。因此,农民工与农村的社会网络逐渐脱嵌。“嵌入”的过程表现为,随着流入城市时间的增加,农民工参与社会活动的频率以及与周边新结识的同伴交往频率也随之增加。由此,农民工的关系逐步嵌入城市并且形成新生关系网络。新生关系网络在农民工乡城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8],而农民工在迁入地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也成为影响农民工迁入和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19]。概括起来,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新生关系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农民工作为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新来者”,往往比当地居民更缺乏就业信息,并且农民工作为求职方与招工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20],这使得农民工对流入地的新生关系网络有着强烈的依赖[21]。因而,农民工可以通过已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朋友、同乡帮助找工作。能否找到稳定的工作,对农民工选择是否迁入城市至关重要[22]。拥有良好新生关系网络的农民工往往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与人交往频率会更高。这不仅能为农民工带来就业发展机会,也能增强其在城市的城市定居意愿[23]。
第二,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农民工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与他人的互动常常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24,25]。由于社会活动内部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农民工将会产生超越个体意识之外的集体意识。农民工参与社会活动增多,其集体意识也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具体表现在,农民工参与越多的社会组织活动,就会与迁入地居民的交往、互动越深入,越有助于其获得公共组织的认同感和社会支持[8,26]。而这种公共组织的认同感与社会支持促使组织成员之间进行价值交换,从而促进农民工与活动成员之间产生利益互惠行为。当农民工获得的身份更加多样化以及城市资源更加优质时,其城市定居意愿就会越高。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将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新生关系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H2:社会活动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间接影响
第一,社会网络通过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进而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弱关系理论”认为,社会网络是导致劳动力就业和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11,27]。一方面,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嵌于关系网络之中,社会网络可以为其提供就业信息、信任、人情等社会资源,帮助人们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28]。另一方面,农民工通过参与工会、社团、老乡会等社会组织,扩大其社交范围,认识更多的老乡、同事和朋友,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工作发展机会。与此同时,社会活动参与有助于增加农民工与迁入地居民交流的机会,增强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城市认同感[29]。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决策受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拥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更容易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他们自身的价值能够在城市中得到实现[22],从而其城市定居意愿得到提升。综上,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市场”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拓宽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增加其就业与发展的机会[30],从而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第二,社会网络通过提高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而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一个人身份决定于其在人际互动交往中所扮演的特定社会角色,个体在这一特定角色的要求下,逐渐形成自我观念和自我言行[31]。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的过程是由周围多重结构性力量与主体行动策略相互构建而成,也是农民工自我身份的整体感知、分类、建构及合法性认同的心理历程。新生关系网络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社会活动参与则有助于农民工从心理上摆脱群体偏见,并转变对自身身份的认同[32,33]。此外,身份认同是农民工在迁入城市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当农民工嵌入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在城市获得归属感时,其就会更加认可自己“本地人”身份,进而更加倾向于选择留居在迁入城市。因此,农民工通过与迁入地居民交流互动,形成的身份认同会为其城市定居意愿带来积极的影响。
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假设:
H3:社会网络能通过增加农民工工资收入进而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
H4:社会网络能通过提高农民工身份认同进而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该数据调查严格执行分层、多阶段、与规模呈比例的抽样方法。使用该数据的原因有两点:其一,CMDS数据样本量大且具有权威性。该数据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调查,是包括31个省级行政单位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型微观调查数据,数据总样本量为169 989个。其二,CMDS数据具备科学性及专业性。该数据的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5周岁以上、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县或其他县级行政单位户口的流动人口。结合研究需要和CMDS调查问卷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对象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特征: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龄在15~59周岁(其中男15~59周岁,女15~54周岁)、因务工或经商迁移的农业户籍人员。在剔除不符合研究需要并剔除数据缺失值之后,最终得到符合本研究需要的58 962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指的是农民工是否愿意在流入地定居,根据已有文献[2],本研究选择农民工转户意愿作为城市定居意愿的代理变量,将有意愿把户口迁入所在城市的农民工视为具有城市定居意愿的农民工。研究表明,具有强烈转户意愿的农民工,其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更加强烈[34]。将农民工转户意愿设定为二元变量,CMDS问卷中“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被访者可选择“不愿意”“愿意”“没想好”,将选择“愿意”的赋值为1,否则为0。从表1可以看出,有转户意愿的农民工相对较低,有意愿将农村户口转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占总体有效样本的34.5%。
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网络。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目前缺乏准确的衡量标准,本研究借鉴当前主流的做法,将社会网络分为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维度[35,36]。问卷中“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可以作为新生关系网络的衡量指标。本研究选取“是否参加工会/志愿者协会/同学会/老乡会/家乡商会”作为社会活动参与的代理变量,同时将农民工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一一相加,形成一个综合指标,即用农民工参与活动的数值衡量农民工的社会活动参与。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9,37]并结合2017 CMDS数据特点,设定如下三类控制变量:第一类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考虑到年龄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非线性影响,同时加入年龄平方变量。第二类为家庭因素,将“住房性质”“宅基地”“承包地”分别设定为虚拟变量。第三类为外部因素,考虑到不同地区(省级或地级)政策的差异,用虚拟变量形式控制地区效应,以降低估计偏误。
选取工资收入与身份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工资收入是农民工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较高的工资收入可以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在迁入地的生活水平。利用问卷中“您个人上月的工资收入”来反映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并对数据做缩尾处理。该数值越大,表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越好。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异方差问题,将工资收入做对数处理。鉴于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认同程度也可能影响其城市定居意愿,因此,对问卷中“我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以及“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四个问题,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得到一个综合指标,以此衡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该数值越大,表明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其身份的认同程度越高。
选取同乡流动经历与历史宗族力量为工具变量。首先,选择同乡流动经历作为新生关系网络的工具变量[38]。同乡的流动经历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地缘”关系、交往对象产生影响,同时,同一户籍城市其他人的流动经历可能会影响劳动者个体的流动决策,但并不直接影响本人的城市定居意愿。其次,选择历史宗族力量作为社会活动参与的工具变量[39]。历史宗族力量强的地区会经常组织寻亲、寻根等社会活动,这有利于农民工主动选择参与社会活动。而且这一工具变量属于历史变量,该特点决定了其比当期变量具有更强的外生性,不会存在反向因果问题,由此满足了外生性条件。综上,两者均满足与内生变量社会网络相关的条件,且满足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外生性条件。当然,两个工具变量是否有效,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变量的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设定
被解释变量“城市定居意愿”为二值虚拟变量,选择OLS估计模型可能导致异方差等问题。因此,本研究选择二元Probit模型来估计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非线性影响。模型表达式如下:


为了解决因为遗漏变量产生的偏差,本研究通过尽可能多地控制变量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地,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本研究尝试采用IV-probit模型进行分析。IV-probit模型的第一阶段回归方程(2)(3)如下,第二阶段的方程为在(1)式的基础上加入工具变量。

(3)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表2汇报的是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边际效应。其中,第(1)列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第(2)列纳入了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控制变量。结果可以看出,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第(3)列和第(4)列分别控制了省级区域效应和地级区域效应,新生关系网络以及社会活动参与的估计结果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为正。从各列结果可以看出,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2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准回归
注:表中汇报数值为边际效应而非系数;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第(4)列结果可知,农民工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每增加1个单位,其城市定居意愿将分别提升1.9%和1.8%。整体来看,准R值逐步提高,Wald检验值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社会网络不仅能够影响农民工的流动意愿,而且还能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在城市中,拥有较强社会网络的农民工,更易获得多元的身份和丰富的城市资源。具体而言,新生关系网络可以增加农民工与本地朋友的互动频率,促进其更快地适应迁入城市,社会活动参与可以扩大农民工的社交圈子,以便与当地居民进行价值交换,从而促进其更好地融入迁入地。由此,初步验证了H1和H2。
(二)稳健性检验
前述估计结果初步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检验其稳健性,通过控制稀有事件偏差、替换模型以及替换因变量等展开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于样本中有城市定居意愿的农民工比例偏低,直接使用二元Probit模型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因此,使用补对数-对数模型对其估计结果的偏差进行修正[40]。表3第(1)列显示,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将基准回归中的Probit模型替换为Logit模型,结果如第(2)列所示,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农民工从农村迁入城市再到市民化,其中实现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农民工具有城市定居意愿[41]。而且这个过程不仅是为农民工赋予与城市居民同等社会权利的过程,也是从社会排斥到社会接纳的过程[42]。因此,本研究利用二值变量留城意愿对原被解释变量(城市定居意愿)进行替换。利用“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两个问题,将回答愿意留居本地且打算留居10年以上时间的赋值为“1”,否则为“0”[43]。结果如第(3)列所示,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以上结果再次验证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带来的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H1、H2的结果具有稳健性。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构建新的关系网络以及在迁入地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从城市中获取资源并提高其城市适应性。因而,拥有较大社会网络的农民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入地的生活方式以及态度发生转变,进而产生强烈的城市定居意愿。

表3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稳健性检验
(三)内生性问题
农民工是否选择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是其自选择的结果,即社会网络可能并不满足随机抽样。因此,直接使用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选择性偏误。同时,社会网络可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反向因果的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越强烈,其越愿意去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源。为此,选择同乡流动经历、历史宗族力量分别作为新生关系网络以及社会活动参与的工具变量,采用IV-probit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其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内生性检验
注:括号中数字是稳健标准误
总体来看,Wald检验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分别为1066.473和1878.279,F检验值十分显著,这不仅表明模型整体拟合的效果较好,而且所选工具变量(同乡流动经历和历史宗族力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便于进一步展开分析。此外,外生性Wald检验值不为零,并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证明采用工具变量法纠正基准估计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是有效的。下文根据表4所示IV-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展开讨论。
第一阶段中,第(1)列的结果显示,同乡流动经历对农民工新生关系网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同乡流动经历能够给农民工新生关系网络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与前文的判断逻辑一致,同乡关系网络作为农民工在流入地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与当地居民相互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获取城市资源的主要来源。在同一户籍地的农民工,彼此间可以分享流动经历与生活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某种“流动文化”,这一现象使得同一户籍地流动人口的迁移经历具有相似性,以致加速形成“同伴效应”。第(3)列的结果显示,历史宗族力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宗族力量较强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实力雄厚的宗族会定期组织寻根访亲、文娱、旅游等社会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增强农民工的社会互动,累积社会网络,而且高质量的互动也会增进彼此间的情感以及凝聚力,从而为农民工的社会活动参与带来积极影响。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分别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第(2)列和第(4)列的结果显示,新生关系网络与社会活动参与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能够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如前文所述,新生关系网络范围越广、社会活动参与越丰富的农民工,其城市定居意愿就越高。故H1、H2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对于影响机制的分析,已有文献主要使用Baron 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44],而这一方法主要针对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况。由于被解释变量(城市定居意愿)为二值变量,为避免估计结果产生误差,本研究采用Karlson等提出的KHB分解方法[45]。该方法适用于被解释变量为离散变量的情形,目前已经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46,47]。表5展示的是基于KHB方法的估计结果。

表5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5第(1)列和第(3)列可知,工资收入产生的间接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这不仅表明新生关系网络会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间接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而且社会活动参与也能够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间接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同理,由表5第(2)列和第(4)列可知,身份认同的间接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这意味着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均会通过提高农民工身份认同进而间接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
通过计算第(1)列和第(3)列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得出,农民工工资收入发挥的间接效应占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14%和27.59%;同理,由第(2)列和第(4)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农民工身份认同发挥的间接效应占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60%和55.06%。综上可知,社会网络不仅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还会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和增加农民工身份认同,从而间接提升其城市定居意愿。H3、H4得到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得出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均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但这只是全样本层面的平均效应,并未考虑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带来的异质性影响。为了得到更为细致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将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分别与流动年限、性别、教育年限、宅基地以及流动范围做交互项,以此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分析
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新生关系网络×流动年限、社会活动参与×流动年限的交互项系数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表明其流动时间越长,社会网络的需求越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越强。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新生关系网络×性别、社会活动参与×性别的经验值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说明男性农民工随着社会网络拓宽,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烈。第(3)列的结果显示,新生关系网络×教育年限、社会活动参与×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正,表明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工社会网络越广泛,其城市定居意愿就越强烈。可能的解释是,首先,流动时间长的农民工,在迁入地的社会网络会随着流动时间逐渐扩大,与家乡的地缘血缘关系逐渐产生“断裂”,其在迁入地的城市定居意愿也就会越强烈。其次,女性在适应与融入城市过程中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也更需要来自家乡“强关系”的重视与帮扶。相比于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在流入地的适应性较好,同时男性较强的适应性也为其在城市定居提供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因而其城市定居意愿就会越强烈。最后,人力资本作为农民工从事非农工作的重要因素,其中教育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可以得知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其在迁入地的社会网络越丰富,城市定居意愿就会越强烈。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系统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果,可得到如下结论: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并在更换基准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后结果依旧稳健;运用KHB分解方法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间接影响发现,社会网络能够通过增加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农民工身份认同,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男性、教育年限越长、流动年限越长的农民工,社会网络范围越广,城市定居意愿就会越强烈。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重视农民工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建立完善的社区管理体系。政府应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以农民工实际需求为工作导向,建立和谐友好互助的社区管理体系。以此,更好地服务城市中的农民工,帮助农民工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为其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城乡带动作用,重视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鼓励不同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的农民工之间、迁入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以及农民工与其亲友之间进行互相交往,发挥社会互动机制中的同群效应、示范效应。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应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这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符合农民工的自身需求。第三,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标准,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增收机制。政府应出台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举措,保障农民工的用工环境以及最低工资水平。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鼓励企业通过培训职业技能等社会化服务,增大农民工的就业与发展机会,从而使其更好地在迁入地生活。第四,发挥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农民工在迁入地的身份认同。政府相关部门应维护农民工群体利益,减少户口歧视、身份歧视,并适当为农民工提供租房补贴、医疗补贴等社会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使农民工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成为迁入地的“新居民”。
[1] 尹志超,刘泰星,王晓全.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0(5):76-95.
[2] 刘金凤,魏后凯.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长期定居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22(1):34-52.
[3]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4):44-51.
[4] 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7):21-29.
[5] 刘小年.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现象分析——社会交换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8(1):75-86.
[6] 吴兴陆,亓名杰.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探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1):26-32.
[7] 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人口研究,2012,36(5):47-57.
[8] 何微微,胡小平.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J].农村经济,2017(8):122-127.
[9] 王春超,张呈磊.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J].社会学研究,2017,32(2):199-224.
[10] 徐美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4):53-63.
[11] 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 ——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J].管理世界,2013(9):55-68.
[12] 郭云南,姚洋.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管理世界,2013(3):69-81.
[13] 尹志超,刘泰星,严雨.劳动力流动能否缓解农户流动性约束——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7):65-83.
[14] 赵佩,黄德林.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以城市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5):36-43.
[15] WOOLCOCK M .The rise and routin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1988-2008[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0,13(1): 469-487.
[16] JACKSON M O .Network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behavior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4,28(4): 3-22.
[17] 风笑天.“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04(5):19-27.
[18] 胡必亮.“关系”与农村人口流动[J].农业经济问题,2004(11):36-42+80.
[19] LEE E J,KIM Y W.How social is twitter use?Affiliative tendency an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s predictor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4,39:296-305.
[20] 周先波,刘建广,郑馨.信息不完全、搜寻成本和均衡工资——对广东省外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程度的测度[J].经济学(季刊),2016,15(1):149-172.
[21] MUNSHI K.Strength in numbers networks as a solution to occupational trap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1,78(3): 1069-1101.
[22] 卓玛草,孔祥利.农民工收入与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关系强度与资源的因果效应分析[J].经济经纬,2016,33(6):48-53.
[23] KORINEK K ,JAMPAKPLAY A .Through thick and thin layers of social ties and urban settlement among Thai migrant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5,70(5):779-800.
[24] BREZA E,CHANDRASEKHAR A G.Social networks,reputation and commitment:Evidence from a savings monitors experiment[J].Econometrica,2019,87(1):175-216.
[25] 方航,陈前恒.社会互动效应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0(5):117-131.
[26] 李梦娜.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农民工反贫困治理研究[J].农村经济,2019(5):121-127.
[27]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28] LIN 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J]. Connections,1999,22(1): 28-51.
[29] 杨怡,王钊.社会资本、制度质量与农民收入——基于CHFS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21(8):115-127.
[30] GIULIETTI C,WAHBA J.Welfare migration: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migration[J].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489-504.
[31] HOGG M A ,MEEHAN C.FARQUHARSON J.The solace of radicalism:Self-uncertainty and group identification in the face of threat[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0,46(6):1061-1066.
[32] 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5(2):28-47.
[33] 李斌,张贵生.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分化逻辑[J].社会学研究,2019,34(3):146-169.
[34] 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长期定居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6):86-113.
[35] 聂伟,风笑天.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6):34-42.
[36] 张童朝,颜廷武,王镇.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与自雇佣妇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J].农业技术经济,2020(8):101-116.
[37] 祝仲坤,冷晨昕.自雇行为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状态——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20(5):109-129.
[38] 汪润泉,赵广川,刘玉萍.农民工跨城市流动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对农民工频繁流动的一个解释[J].农业技术经济,2021(7):131-144.
[39]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J].社会,2013,33(4):193-224.
[40] 钱龙,陈方丽,卢海阳,等.城市人“身份认同”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温州农户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9(8):40-52.
[41] 宁光杰,李瑞.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流动范围与市民化差异[J].中国人口科学,2016(4):37-47.
[42] 姚先国,宋文娟,钱雪亚,等.居住证制度与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J].经济学动态,2015(12):4-11.
[43] 吴伟光,李世勇.农村劳动力入城生活境况及留城意愿——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2(11):104-109.
[44] BARON R M ,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45] KARLSON K B ,HOLM A ,BREEN R.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s using logit and probit:A new method[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0,42(1):286-313.
[46] 王伟同,陈琳.隔代抚养与中老年人生活质量[J].经济学动态,2019(10):79-92.
[47] 祝仲坤.公共卫生服务如何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10):125-144.
How can social networks enhance migrant workers’ long-term settlement willingness
ZHANG Liangang, SHI Xiaoke*, PENG Zhiy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in 2017,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from the two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new generation farmers and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new relationship networkof new generation farmers and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As the link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the immigration area, social network can indirectly enhance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through wage income and identity. The heterogeneity test finds that the influence of new generation farmers’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is manifes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ence of mobility, education and gender, namely, thes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have an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It is advisable to establish a good 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ize the minimum wage of employees in the employing units, promote the supply of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ervices and play a leading role among different groups to enhance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social network; migrant workers; urban settlement willingness; wage income; identity
C912.82;F328
A
1009–2013(2023)01–0064–10
10.13331/j.cnki.jhau(ss).2023.01.008
2022-11-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163030)
张连刚(1976—),男,河南唐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合作社与乡村治理。*为通信作者。
责任编辑:曾凡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