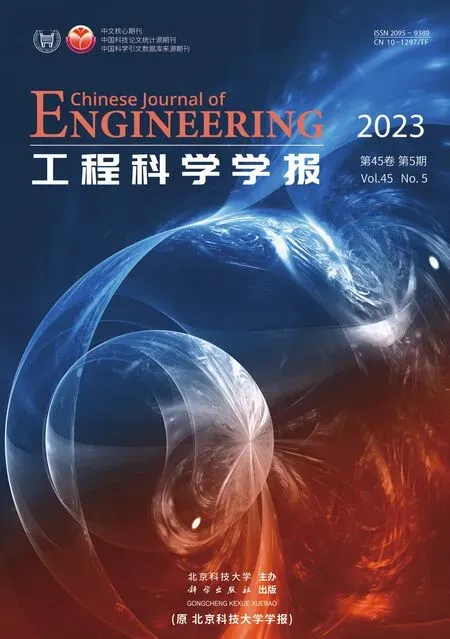机动车尾气和非尾气排放多环芳烃及其衍生物的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付家祺,王 婷,毛洪钧
天津市城市交通污染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1
机动车尾气排放是我国乃至全球的主要道路交通污染源之一,且随着全球机动车保有量不断高速增长,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贡献逐渐加大.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逐渐成熟和市场的不断推广,与机动车尾气排放相比,非尾气排放污染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多环芳烃(PAHs)是机动车尾气污染物中的一类具有较大毒性的有机化合物,具有致癌性、致畸性、致突变性和免疫毒性[1],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同时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而PAHs的衍生物硝基多环芳烃(NPAHs)和含氧多环芳烃(OPAHs),虽然污染水平比母体低1~3个数量级,但部分组分的毒性当量因子远高于PAHs[2].PAHs及其衍生物主要来自机动车发动机中燃料的热解,同时存在着表面生长和氧化的动态过程[3],因此发动机缸内燃烧条件的不同,可能会导致排放组分和浓度发生变化.但是,现有研究针对不同影响因素下PAHs及其衍生物的排放特征还相对较少.为此,本文主要从排放标准、测试工况、燃料种类、发动机类型、后处理技术、车型与行驶里程、机动车部件材料种类以及路面条件等方面系统探讨机动车尾气排放和非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的排放特征.
1 影响机动车尾气排放 PAHs及其衍生物的因素
1.1 车辆排放标准
目前国际上机动车排放标准以美国、日本、欧洲三大体系为主导.由于其完善的法律法规、健全的运行机制以及严格的排放标准,使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世界领先者.随着美国定义了2025年目标的长期愿景以及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出台,许多国家开始借鉴美国法规标准[4].我国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发展初期以欧洲体系为参考对象和依据,因此出台的国Ⅳ、国Ⅴ法规与欧洲排放标准类似;随后逐渐转向美国的排放法律法规,并在2020年实施的国Ⅵ标准限制严于欧Ⅵ排放标准.
表1显示了在不同排放标准下汽柴油车排放尾气的PAHs环数分布和排放因子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在排放因子数量级上的差异可能由不同工况、燃油以及车辆类型等复杂因素造成.

表1 不同排放标准下PAHs的环数分布及总PAHs排放因子[5,8,10]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AHs rings and emission factor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under different emission standards[5,8,10]
Zhao等[5]选取国Ⅰ至国Ⅴ排放标准的汽油车进行台架实验,结果表明汽油车尾气排放PAHs含量随排放标准的升高明显降低,最高和最低PAHs排放因子分别为国Ⅰ和国Ⅴ的1,206.87和 790.70 μg·km-1.其中苯并 [g, h, i]苝 (BghiP)、二苯并 [ah]蒽 (DahA)和苯并 [k]荧蒽 (BkF)为 PAHs排放总量贡献最大三种PAHs;对于NPAHs, 其排放因子变化与PAHs类似,国Ⅰ至国Ⅴ的PAHs排放因子分别为 28.74、27.29、20.42、17.55和16.68 μg·km-1.这是由于部分 NPAHs由母体 PAHs与NOx的二次反应生成.Zheng等[6]对汽油车PAHs排放因子研究结果显示国Ⅳ和国Ⅴ相对于国Ⅲ减少了49%~93%,并且总PAHs排放量相当均匀地分布在3~6环之间.
在欧洲排放标准汽油车尾气排放PAHs研究中,Lin等[7]发现,与欧Ⅲ和欧Ⅳ相比,车辆排放的2、4、6和7环的PAHs占比在欧Ⅴ和欧Ⅵ中减少,而欧Ⅴ汽油车中,3环和5环的PAHs呈上升趋势,总 PAHs中 2~3 环 (萘 (NAP)、苊烯 (ACY)、苊(ACE)、芴(FLU)、菲(PHE) 和蒽(ANT)贡献为 66.6%.这与Alves等[8]研究结果相似,PAHs排放量欧Ⅲ>欧Ⅳ>欧Ⅴ,欧Ⅴ车2~3环PAHs较Ⅳ稍高,4~6环PAHs均在检测限以下,且2~4环PAHs总是占主导地位.
不同排放标准下柴油车尾气排放PAHs含量变化与汽油车结果一致.Zerboni等[9]对欧Ⅲ和欧Ⅵ柴油车尾气颗粒PAHs含量进行测量,欧Ⅲ总PAHs(394 ng·mg-1)含量高于欧Ⅵ样品 (261 ng·mg-1),且二者含量最丰富PAHs为PHE.Chen等[10]通过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GC×GC-ToF-MS)测量国IV和国VI车辆的PAHs排放因子分别19.2 ±21.1 μg·km-1和 2.6 ± 1.3 μg·km-1,超过 90% 的 3 环和4环PAHs分布于气相.Cao等[11]进行车载实验,中型柴油车从国Ⅲ到国Ⅳ,排放标准的变化发现PAHs排放因子有明显的降低趋势,气相PAHs占总PAHs总量的56%~89%;NPAHs气相约占97%,气相 NPAHs中 4环 (1,3-硝基芘,1,3-NPYR)成分最为丰富,平均贡献约为84.9%.
因此,机动车排放标准对车辆尾气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量的降低起到重要作用,是排放控制要求最基本的底线.各国政府根据各国国情和民众意愿加强了排放控制标准.中国为在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做出表率,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日益严格,同时也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整改效果.
1.2 车辆行驶工况
在欧洲,新欧洲驾驶循环(NEDC)一直沿用至今,而美国则通过联邦测试程序75(FTP75)进行测试,自2000年以来,通过增加补充周期和加入低温循环,这组测功机测试周期确保了与现实驾驶更密切的关系,而NEDC实验室结果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在扩大,因此全球协调轻型车辆测试程序(WLTP)在2017年9月至2021年初之间逐步取代前者.但美国环保署在2010年表明不采用该程序,欧盟、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仍将WLTP作为基准.同时从2020年起,中国采用了WLTP进行乘用车型认证测试[4].WLTP对NEDC的基本变化包括:相对较长、更高的速度和更短暂的驾驶周期;略低的环境温度以及测试程序的一些变化[12].
Zheng等[6]在WLTC和NEDC两种循环下采集尾气排放颗粒物,WLTC下所测得3环PAHs排放量较NEDC略有下降(4%~9%),然而,4、5和6环物种的排放量均有所增加;同时在冷启动下WLTC的PAHs排放量分别是热启动的1.1~17倍;比较WLTC中速段和WLTC高速段时发现,高速驱动条件会导致更高的燃烧压力和温度,从而减少PAHs前驱体(如乙炔、乙烯)的产生,并有利于PAHs化合物向烟灰颗粒的生长趋势.Kostenidou等[13]研究发现,在Artemis欧洲驾驶循环的不同阶段中,热启动中的PAHs浓度略低于冷启动,PAHs排放主要在冷启动城市循环(ArtUrb)的最初几分钟和高速公路循环的加速期,2~4环PAHs均占主导地位.Alves等[8]之前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机动车在冷启动ArtUrb 和道路驾驶循环(ArtRoad)条件下PAHs排放量最高.在中国重型卡车/商用车试验循环(CHTC-HT)中,Chen等[10]在没有后处理装置的国IV型车辆冷启动条件下颗粒相PAHs排放更高;对于配备了柴油颗粒物过滤器(DPF)的国VI车辆,颗粒相PAHs从冷启动到热启动条件变化很小,无论冷启动和热启动条件如何,DPF都能有效地降低PAHs排放.Wang等[14]采用冷启动瞬态、热启动瞬态、怠速和稳态四个驱动周期对柴油车进行测试,稳态循环中平均总 PAHs排放因子为 0.0834 ± 0.146 mg·km-1,低于冷启动(0.180 ± 0.303 mg·km-1)和热启动 (0.239±0.310 mg·km-1)循环,所有驾驶周期中收集到的PAHs均以4环和5环为主(PYR、苯并[a]蒽(BaA)、CHR、苯并[k]荧蒽(BbF)、BkF和苯并[a]荧蒽(BaF)等).总的来说,低温启动下发动机燃烧效率降低,有利于不完全燃烧过程中PAHs前体的形成,使PAHs排放量增加.
对于机动车负荷对排放的影响,An等[15]通过台架实验发现,在2000 r·min-1条件下,随着发动机从低负荷(扭矩保持在60 N·m)到高负荷(扭矩保持在 120 N·m), PAHs排放量逐渐增加,气相中NAP(90 μg·m-3增 加 到 200 μg·m-3)、 PHE(3 μg·m-3增加到8.7 μg·m-3)、FLT(0.4 μg·m-3增加到0.8 μg·m-3)和 PYR(0.1 μg·m-3增加到 0.6 μg·m-3)浓度显著增加,颗粒相 4 环 PAHs中 BbF(0.55 μg·m-3增加到0.87 μg·m-3)和BghiP(0.45 μg·m-3增加到0.65 μg·m-3)质量浓度变化明显.同样,Arias等[16]在高负荷(2,400 min-1、90 N·m)下检测到柴油车尾气中总PAHs排放量较低负荷(1750 min-1、71 N·m)高,且PAHs以3和4环为主存在于气相,毒性较高的,DBalP和BaP存在于颗粒相.Li等[17]分别对柴油车发动机在20%、50%和80%负荷下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特征进行研究,PAHs总排放量在低负荷和高负荷下高,在中负荷下低(低中高分别在372~890、274~745 和 364~913 μg·kWh-1之间),NPAHs变化与PAHs类似,OPAHs排放量则随发动机负荷的增加呈升高趋势.这是由于在低负荷下,较低的发动机燃烧效率使燃料中PAHs燃烧不完全从而残留更多;过高负荷下,有利于PAHs前体的形成,导致PAHs排放量增加.Geldenhuys等[18]采用欧Ⅱ标准发动机,通过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TD-GC⊆GC-ToF-MS)分析发现,发动机在最大功率模式下PAHs浓度明显高于怠速模式(33.9 和 6.3 μg·m-3); 最大功率模式排放的 PAHs主要存在于颗粒相,而怠速模式主要产生气相PAHs,NAP是二者的PAHs优势组分.
在路况对排放的影响方面,在实际道路研究中,Cao等[11]通过车载实验对非公路和公路路线中柴油车尾气排放PAHs和NPAHs进行测量,柴油车在非公路道路上行驶时,更容易发生不完全燃烧,导致PAHs和NPAHs排放增多;反之在较高速度的驾驶条件下,由于排气温度的增加将导致化合物更好地氧化,从而PAHs排放更低.然而,中型柴油车的PAHs和NPAHs与轻型和重型柴油车呈现相反的结果,在公路上排放较高.Dhital等[19]沿台湾城市(UR)、郊区(SU)和高速公路(FW)三条路线,在正常驾驶行为和攻击性驾驶行为(快速加速车辆)下测量真实道路机动车尾气PAHs的排放量.总PAHs的排放以4环(57.83%~83.42%)和3环(7.07%~33.65%)PAHs为主;UR的平均总PAHs排放因子分别为SU和FW的1.5倍和2.4倍;AG驱动模式下总PAHs的排放因子和总PAHs的BaP等效毒性分别增加了128%和951%.
因此,不同运行工况下启动温度、驾驶模式和发动机负荷的变化将导致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是通过影响发动机的预热、稳定性和缸内温度及压力,从而降低发动机燃烧效率,造成燃料不完全燃烧,促进PAHs前体物的形成.
1.3 燃料种类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和更加严格的排放限值的出现,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各个国家未来的研究重点.欧盟指令2018/2001将2030年运输部门的强制性可再生能源提高到14%.排放污染物更低的可再生燃料替代化石燃料是一种可行的选择.生物燃料是指从植物油或动物脂肪通过酯交换过程与甲醇获得脂肪酸甲酯的混合物,由于部分生物燃料存在的堵塞问题以及难存储等问题,因此当前研究更关注生物燃料的混合,如生物醇.生物乙醇是目前较为常见的醇类燃料,但正丁醇具有较高的十六烷数、较高的热值、较低的挥发性、较高的闪点、更好的润滑性和于柴油的混溶性,使其在运输、储存和燃烧性质方面比乙醇更安全和高效,因此正丁醇作为混合成分的研究也成为了热点[20].
与柴油车相比,汽油车较重分子量PAHs对总PAHs的相对贡献增加,柴油车主要以低分子量PAHs为主,不同研究中柴油和汽油PAHs排放因子如图1所示.在Alves等[8]的研究中,柴油尾气颗粒中的 PAHs主要是NAP、PHE、PYR和 FLT,排放因子分别达 925、12.5、12.5 和 4.98 μg·km-1;汽油车尾气中主要的PAHs为NAP、PHE和ANT,最大排放量分别为 223、1.21 和 1.14 μg·km-1.Perrone等[21]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柴油车和汽油车中PYR对总PAHs的贡献最高,分别为60%和23%;汽油车中BghiP是另一种贡献较大的PAHs(18%),而其在柴油车的贡献较小(2%).

图1 不同燃料类型PAHs的环数分布及总PAHs排放因子[8,21]Fig.1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AHs rings and emission factor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under different fuel types[8,21]
在Wang等[22]进行的不同芳烃含量的汽油燃料PAHs排放研究中,汽油中较高的芳烃含量导致颗粒物和PAHs排放量更高, BaP等效毒性也更高.Huang等[23]结果表明,与ULSD相比,所含芳烃含量更小的瑞典柴油,PAHs排放量减少了45%~68%,NPAH的排放量减少了50%~58%.
McCaffffery等[24]将不同比例的乙醇燃料(E10、E51、E83)和异丁醇燃料(iBut55)与汽油混合发现,在气相PAHs中,醇类燃料的添加使得机动车PAHs排放量显著减少;在进气道喷射发动机(GDI)中,颗粒相PAHs排放量随乙醇含量增加而减少,E51和E83分别比纯汽油减少58%和69%.而芳香族含量和氧含量都比E51更低的iBut55燃料PAHs排放量减少了39%,说明PAHs排放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燃料中氧含量的增加,而不是芳烃含量的减少而引起的稀释效应.此外,缸内直喷发动机(PFI)的测量结果与GDI恰恰相反,随着乙醇和异丁醇共混物的增加,总颗粒相PAHs排放量逐渐增加.
从图2可以看出,在柴油与可再生燃料的混合研究中,结果不尽一致.Arias等[16]在清洁超低硫柴油(ULSD)中添加丁醇和生物柴油发现,二者的加入使芳香族化合物减少,但PAHs的总排放量增加,NAP、PHE+ANT 是主要气相 PAHs,PHE+ANT和PYR则是粒子相主要PAHs,表明燃烧过程中发生了低分子量烃类化合物的热解和热合成过程,生成的自由基结合形成乙炔,通过缩合产物形成芳香环.Yilmaz等[25]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较高正丁醇与生物柴油(BBu)混合比下PAHs排放量增加,BBu10、BBu20和BBu40分别为111~247、186~296 和 257~495 μg·kg-1.

图2 不同可再生燃料/柴油混合比PAHs的环数分布及总PAHs排放因子[16-17]Fig.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AHs rings and emission factor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with diesel, biodiesel and biodiesel/n-butanol blends[16-17]
Lim等[26]同样将ULSD与生物柴油混合,发现燃料中生物柴油含量的增加会减少颗粒相PAHs的排放,NAP是含量最高的PAHs,其次为FLU、PYR和FLT.这与Li等[17]研究一致.与柴油相比,使用B20、B50和B100的PAHs总排放量分别下降了28.2%、43.2%和60.4%,低分子量PAHs(PHE、PYR、ACE和FLU)是主要的PAHs组分;NPAHs排放量的减少与母体PAHs相一致;而较高的氧含量使B20和B50的OPAHs总排放量分别增加了24.3%和51.9%,在B100中过量的氧含量抑制了母体PAHs的形成,从而其OPAHs总排放量仅增加了8.9%.
1.4 车辆发动机类型
传统的汽油发动机通过将燃料和空气混合在进气系统中并引入气缸,后来演变成进气道喷射(PFI)发动机.随着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相关目标的提出,PFI发动机向增压、更高效、更小尺寸的汽油直喷(GDI)发动机转变.与PFI发动机相比,GDI发动机具有更高的压缩比和更低的充电温度,从而提供更高的燃油经济性.然而,由于燃料雾化时间和相关的燃料撞击时间缩短,大多数GDI发动机产生的颗粒物排放量远高于传统PFI发动机,同时也对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的排放特征带来相关影响[27-28].
Zhao等[5]对GDI和PFI发动机汽油车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含量测量,发现在不同行驶里程下,两种汽油车排放因子最大均为BghiP和DahA,且GDI排放因子均明显小于PFI汽油车PAHs排放因子,表明GDI汽油车可降低中、高分子量PAHs的排放;NPAHs排放也呈相似趋势,PFI汽油车 NPAHs的排放因子在 6.43~12.45 μg·km-1,GDI排放因子在 5.42~7.95 μg·km-1,均为 4 环 NPAHs对总量贡献最大.而McCaffffery等[24]观察到相反的结果,在使用E10汽油中,GDI的总气相PAHs排放量是PFI的5倍以上,以NAP为最主要PAHs; 颗粒相PAHs排放浓度GDI也比PFI表现出更高的浓度,这与烟尘颗粒物排放结果一致,印证了PAHs有助于促进烟尘颗粒物表面生长的观点.此外,两种车辆尾气中均含有OPAHs,其中贡献最大的是1,4-萘醌(1,4-NQ)和蒽醌(9, 10-ATQ).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验证.Kostenidou等[13]实验中GDI排放的PAHs质量浓度明显高于PFI,分别为1.66和 0.47 μg·m-3; Zheng 等[6]发 现 GDI车 辆 (4.8 ±1.4 μg·km-1)比 PFI车 辆 (1.6 ± 1.2 μg·km-1)PAHs排放高3倍,且PAHs增长趋势比颗粒物排放量更为显著.
图3对比了近年来文献中不同发动机的PACs排放因子.总的来说,GDI车辆排放的PAHs浓度一般远高于PFI车辆,且相比于气相PAHs,颗粒相PAHs浓度增加更为明显,说明GDI发动机较高的颗粒物排放量是导致PAHs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图3 PFI和GDI发动机的PACs的排放因子[6,13,24]Fig.3 PACs emission factor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from PFI and GDI vehicles[6,13,24]
1.5 机动车后处理技术
柴油颗粒捕集器(DPF)是目前公认的控制柴油废气颗粒排放最有效、相对成熟的装置.当废气通过DPF时,颗粒物首先被DPF捕集,然后被捕集的颗粒将被氧化并燃烧,以完成DPF的再生[29],而柴油氧化催化器(DOC)通常用于减少柴油发动机车辆的CO和碳氢(HC)排放,二者通常联用以提高污染物转化效率[30].同时,如前文所提到的,GDI发动机的颗粒物排放一直是一个显著的缺点.对此,许多国家已经对GDI车辆的颗粒物和颗粒数排放量实施了严格的规定,并且对颗粒物减排的研究也在积极地进行着,其中汽油颗粒捕集器(GPF)是减少颗粒排放的主要方法之一.GPF类似于在柴油车的DPF中收集和氧化颗粒物的方法,但它与DPF的规格和再生时间略有不同[31].
Lim等[26]对比了配备DPF与DOC的车辆,配备DFP的车辆的PAHs排放量的减少量比配备DOC的车辆高出85%以上,颗粒相PAHs的平均减少量在48.9%~79.7%.Huang等[23]在探究DPF捕集过程和再生过程中PAHs及其衍生物的排放中发现,虽然在DPF再生过程中排放量稍有增加,但PAHs和NPAHs的排放率仍然比没有配置DPF的排放低得多(83%~99%).
Yang等[32]发现随着GPF的应用,颗粒相PAHs排放量总体上都有大幅下降,两种GPF的平均排放量分别为97%和99%;气相PAHs的减少量普遍较低.NAP是气相和颗粒相中主要的PAHs.与母体PAHs相似,两种GPF的NPAHs总排放量分别减少了91%和77%,但一些NPAHs只在配置了GPF的车辆中检测到,这表明这些NPAHs通过选择性硝化反应在GPF系统中形成.Muñoz等[33]研究了两种涂有贵金属(GPF-2、GPF-3)和两种非涂层(GPF-1、GPF-4)的GPF对尾气排放的影响,四个GPF一定程度上都降低了PAHs的排放,但只有非涂层的GPF-1影响显著.对于BaP排放量,GPF-1和GPF-2和GPF-3分别降低了99%、99%和77%;然而,经GPF-4排放后,PAHs的排放量甚至更高,PYR增加9倍,FLT增加2倍,总PAHs排放量增加19倍,这可能是是GPF-4在低温条件下积累了半挥发性PAHs,并在高温条件下再次部分释放.同时在过滤颗粒数方面,GPF-1效率(96%~99.8%)是最好的,颗粒数排放降低2~3个数量级;GPF-3和GPF-4的过滤效率很差(60%~79%).
综上所述,机动车在配置DPF和GPF尾气后处理装置后能够大幅度降低PAHs及其衍生物的排放,且其降低效果通常与后处理装置的颗粒物过滤效率呈正相关.
1.6 机动车车型与行驶里程
机动车的内部因素如车型(PCs、LDVs、MDVs、HDVs)和行驶里程同样对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有着显著影响.
Perrone等[21]对私家车(PCs)和轻型车(LDVs)进行台架实验,以柴油为燃料的PCs的PAHs 排放因子与相同欧洲标准的LDVs相当,PCs和LDVs欧Ⅰ车辆PM10中PAHs含量分别为0.41和0.23 μg·mg-1.Cao 等[11]采用轻型、中型、重型柴油车(LDVs、MDVs和HDVs)进行测试,LDVs、MDVs和HDVs的颗粒相PAHs的排放因子分别为52,626.6304、 36, 214.18955 和 69, 908.82575 μg·km-1,其中MDVs与其他柴油车车型有较大差异.如图4所示,Wang等[14]也有类似发现,说明车辆尺寸对PAHs排放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4 不同车型的PAHs排放因子[11,14,21]Fig.4 PAHs emission factor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under different vehicle types[11,14,21]
Zhao等[5]探究车辆行驶里程影响因素时发现,行驶里程大于105km的汽油车总PAHs排放因子更大,并且4环PAHs对总PAHs的贡献增加了1.10~1.23倍,这是由于发动机内部积碳和车辆油耗随行驶里程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导致发动机的空气/燃料比下降,造成燃料的不完全燃烧;而不同行驶里程下NPAHs各环数的分布无明显差异.这对于行驶里程大于104km的汽油车同样适用,Lin等[7]研究结果显示,行驶里程大于104km的汽油车,总PAHs的排放因子随行驶里程增加而增大,2⊆105km后排放因子略微下降.
2 影响机动车非尾气排放 PAHs及衍生物的因素
随着机动车尾气控制技术的发展和排放标准的更加严格,交通尾气排放颗粒物已迅速下降.同时,电动汽车的逐步推广以及非尾气排放标准的缺失,使得机动车非尾气排放甚至超过了尾气排放.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30年,全球乘用车排放的非尾气排放PM2.5总量可能较2017年的基线增加53%[34-35].机动车非尾气排放颗粒物主要有4个方面:刹车磨损、轮胎磨损、道路扬尘再悬浮以及道路磨损.
2.1 刹车磨损
刹车磨损产生在刹车片与盘式制动器或鼓式制动器的摩擦减速过程中.刹车片和制动器分别由摩擦材料和灰口铸铁制成.刹车片按材料成分可分为:非石棉有机材料(NAO)、半金属材料(SM)和低金属材料(LM).NAO刹车片磨损率低和制动噪声低,但高温下制动性不好,通常作为轻型和小型车辆的刹车片材料.LM刹车片由有机化合物和少量金属成分的混合物制成,具有高摩擦力和良好的高温制动能力,但磨损率高,适合用于中型汽车、货车和卡车[35-36].
刹车磨损在机械摩擦过程中伴随着机械能转化为热能.机械磨损主要产生在300 ℃以下,刹车片和制动器的各种成分以粗颗粒的形式排放;而温度高于300 ℃后,一些热稳定性较低的成分通过热过程或化学过程以细颗粒和超细颗粒的形式释放[35].
Plachá等[37]采用LM制动片(含17%的碳质化合物)进行测功机实验,分别在测功机底部和采集管中收集颗粒物进行测量.环境空气中观察到的BaP的极限质量浓度为1 ng·m-3,PM10中BaP的质量浓度已多次超过环境空气的极限值,以ANT(8,130 ng·g-1)、PYE(7, 978 ng·g-1)、PHE、NAP、BghiP、茚并[g, h, i]芘(IncdP)为主.
对于不同制动循环下不同材料刹车片的PAHs排放差异,Alves等[38]研究结果表明,刹车片NAO1和NAO2显示出完全不同的PAHs排放模式:NAO1在最平稳的制动循环中没有检测到PAHs,但NAO2在相同的测试运行下中产生了最高的PAHs颗粒质量分数 (接近 140 μg·g-1),推测可能是由于虽然NAO1与NAO2刹车片属于同一类,但它们可能含有显著不同的有机材料,同理二者在不同制动循环下PAHs含量变化也不一致.此外,LM与NAO材料排放PAHs主要组分均为FLU,其次为PHE和ACE.
2.2 轮胎磨损
轮胎的成分主要是有机材料组成.然而,与制动系统类似,轮胎的具体组成在车辆类型和制造商之间差异很大,除橡胶本身外,还可以添加填料、强化剂、加工辅助剂、加速剂和缓凝剂、粘合剂和活化剂.欧盟指令2005/69/EC对含PAHs填充油在橡胶制造中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用低含量PAHs替代品替代.2010年1月1日以后生产的新轮胎或用于翻新的轮胎胎面不得含有任何PAHs浓度超过某些阈值的填充油[36].
轮胎磨损是由于车轮与路面之间的接触产生的剪切力和摩擦力从而使轮胎磨损颗粒排放或挥发.轮胎磨损颗粒的产生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驾驶方式、轮胎材料、路面状况以及环境温度、降水和湿度等[34].由于发生了热化学变化以及路面磨损颗粒的混合,轮胎磨损颗粒往往与原始轮胎材料所含PAHs组分不同.
2.2.1 轮胎类型
Alves等[39]测定两种夏季轮胎排放颗粒物PAHs含量,轮胎之间的PAHs含量在不同的制造商之间差异显著,主要的PAHs组分是NAP,同时存在于气相和颗粒相中,PM10中富含FLT、CHR、PYR和PHE.人工磨损轮胎碎屑中以CHR、PYR、BaP和BghiP为主.PM10中NAP、ACE、PHE、FLT和BkF含量是轮胎碎屑中含量的10倍以上.
Wu等[40]选择17种国内外品牌轮胎进行磨损并检测20种PAHs,同样发现PAHs含量在不同品牌下有显著差异,国外品牌轮胎PAHs含量略高于国内,而其主要贡献PAHs环数略低于国内品牌.总 PAHs含量在 12.13~433.64 μg·g-1之间变化,其中4环PAHs如PYR、CHR和FLT贡献最大,其次是3环和5环PAHs如PHE和BaP.
Sadiktsis等[41]分别对不同制造商的夏季轮胎和冬季轮胎颗粒进行提取,分析发现同一制造商的夏季轮胎PAHs含量总是低于镶钉和不镶钉的冬季轮胎.Nokian品牌的冬季轮胎的PAHs含量比夏季轮胎高出300%以上;Bridgestone品牌的镶钉冬季轮胎的PAHs含量比夏季轮胎高约27%.
2.2.2 行驶里程
Aatmeeyata等[42]探究了行驶里程对轮胎磨损颗粒排放PAHs浓度的影响,非尾气排放大颗粒物(直径大于40 μm)LPNE排放量中多环芳烃的浓度随累积公里运行呈线性增加.轮胎中只含有PHE、FLU、PYR和BghiP、ANT、BbF、BkF和BaP均低于检测限;PYR 的含量最高 (30 ± 4 mg·kg-1),其次是BghiP (17 ± 2 mg·kg-1),总PAHs为53.8 mg·kg-1.PHE和FLU的增长大于BghiP和PYR,由于轮胎排放PAHs的机制是通过挥发和产生轮胎磨损碎片,PHE和FLU的波动性高于BghiP和PYR,因此PHE和FLU同时通过这两种机制产生.
2.2.3 路面类型
Kreider等[43]分别收集道路扬尘(RP)、轮胎磨损颗粒(TWP)以及胎面颗粒(TP),TWP和TP之间PAHs的分布有所不同,TWP中PHE(1.66×10-6)、PYR(4.77×10-6)、BghiP(3.22×10-6)和 FLT(0.98×10-6)为主要PAHs组分,TP 以PHE(1.21×10-6)、ACE(1.24×10-6)、BaA(2.87×10-6)、BghiP(1.77×10-6)、CHR(2.95×10-6)和 FLT(1.62×10-6)为主.这是由于 TWP 是在由标准化的沥青质量分数为6.1%的沥青混凝土路面进行收集,沥青中所含PAHs可能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被释放出来.
2.3 路面磨损
路面通常由混凝土或沥青基铺成,后者主要由质量分数为95%矿物骨料和5%沥青组成.当轮胎与路面机械摩擦时产生路面磨损颗粒,路面沥青材料的转化也是形成原因之一.路面磨损颗粒通常与轮胎路面磨损颗粒内部混合排放,因此在现场或真实实验室条件下测量的轮胎磨损颗粒尺寸光谱可以很好地反映路面磨损.此外,直接磨损排放(轮胎、刹车或道路磨损)和再悬浮磨损排放很难区分,因此其对大气PM水平的相对贡献也不易区分[35].
2.4 道路扬尘再悬浮
道路扬尘通常由刹车磨损颗粒、轮胎磨损颗粒以及路面磨损颗粒混合组成,另外还可能源于周围环境中的粉尘如建筑工地、裸露土壤、大气沉积物和车辆带入的灰尘等.因此,道路扬尘再悬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道路扬尘负荷、路面纹理、交通条件以及气象、温度和湿度等环境条件因素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上因时间和空间而异[44].
Alves[45]等在葡萄牙5个主要道路采集大气颗粒物,在其他道路样品中,只检测到5种PAHs,总共不到 10 μg·g-1,而在马加尔海斯大道 (Fernão de Magalhães Avenue)采集的样品中观察到最高的PAHs含量 2,321 μg·g-1,在该道路上由于红绿灯和斑马线较多,机动车刹车非常频繁,导致内燃机效率低下,从而导致PAHs的排放增加;同时,其周围还分布较多餐饮区和居住区.这说明道路扬尘中PAHs的含量不仅取决于交通量,还取决于其流动性和周围环境中的其他燃烧源.
Demir等[46]收集道路扬尘并在高纯度氮气流下重新悬浮,对碳组分比值进行分析,确定道路扬尘样品的排放源.在元素碳(EC)各组分与道路扬尘中PAHs浓度的相关性分析后发现,EC1(r=0.64)、EC2(r= 0.81)和 EC3(r= 0.63)与 PAHs浓度存在很强的相关性,EC1~EC3可能来自于非尾气排放(车辆的机械部件、刹车磨损和轮胎磨损),其中,EC2对道路扬尘样品中的EC浓度有很大的贡献(分布在40%以上),道路扬尘样品中以刹车排放的非废气排放为主.
Kreider等[43]实验表明,非轮胎源在道路扬尘中占主要贡献.胎面颗粒和轮胎磨损颗粒分别占道路扬尘的5%和4%,道路扬尘中PAHs的含量显著高于胎面和轮胎磨损颗粒(p< 0.005).
因此,不同地区的道路扬尘组成成分和分布特征与当地天气环境、车队组成以及道路条件等因素紧密相关.应根据当地相关排放系数制定排放清单,以确定道路扬尘对大气污染的具体贡献.
3 结论
影响机动车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的相关因素可分为:
(1) 随着排放标准的严格,机动车尾气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量大大降低,排放标准在控制汽车污染物排放上具有强有力的执行力.汽油车以2环和3环PAHs为主,随排放标准严格3环PAHs占比略有增加;柴油车以5环和6环PAHs为主,5环PAHs贡献随排放标准的严格逐渐增大.
(2) 机动车在冷启动、瞬态启动、加速阶段、攻击性驾驶行为和高负荷下,由于发动机燃烧效率降低,有利于PAHs前体的形成,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量增大.应树立驾驶人员正确安全的开车习惯,从行车启动、油门以及车速控制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3) 柴油车通常以低分子量PAHs如NAP、PHE等为主,排放量远大于汽油车.汽油车高分子量PAHs的贡献较柴油车更大,其中BghiP可作为汽油车排放的标志物.可再生燃料的添加使PAHs和NPAHs排放减少主要源于燃料含氧组分的增加,同时这也使OPAHs排放量增加.然而对于丁醇混合燃料在PAHs的影响上没有达成共识,有研究发现正丁醇与生物柴油的混合可能会增加PAHs排放.
(4) 与PFI发动机相比,GDI发动机PAHs排放与其颗粒物排放呈类似的增加趋势.DPF、GPF等机动车尾气后处理装置能明显减少颗粒相PAHs的排放.
(5) 不同行驶里程和车型差异对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存在一定影响.车辆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量随行驶里程增加而增加;柴油PCs和LDVs在PAHs排放因子上无明显差异,与LDVs和HDVs相比,中型尺寸的柴油车PAHs排放因子略低.通过对机动车定期维护保养能有效减少车辆零件损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影响机动车非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的相关因素可分为:
(1) 刹车磨损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主要来自于刹车片有机组分的高温和高压反应.不同化学成分的刹车片排放刹车磨损颗粒成分存在一定差异,且不同刹车片在不同制动情况下PAHs浓度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
(2) 与刹车磨损类似,轮胎磨损颗粒受轮胎材料、车辆驾驶以及路面条件等影响,其排放PAHs通过挥发和轮胎磨损两个机制产生.轮胎磨损颗粒PAHs中PYE和PHE是贡献较大的化合物.
(3) 道路扬尘包括刹车磨损颗粒、轮胎磨损颗粒、路面磨损颗粒以及其他沉积在道路上的颗粒.交通状况、车队组成、道路条件、大气降水和道路清扫以及外部污染源存在导致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更新当地的排放系数制定排放清单成为必要.
(4) 相比于机动车尾气排放PAHs及其衍生物,非尾气排放研究较为缺乏,与尾气排放相比其对PAHs及其衍生物排放的贡献相对较小,其排放特征和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