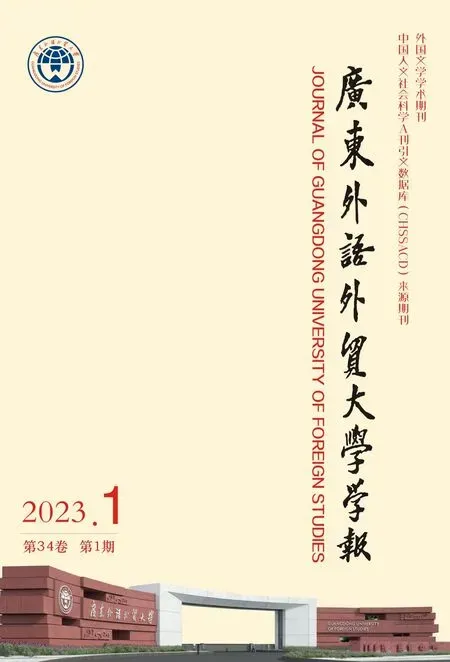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疯女人”
郭焕平 陈爱敏
引 言
迄今,中外有关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简·爱》(JaneEyre)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学界对伯莎·梅森(Bertha Mason)的关注不在少数,观点有二:一是简单地把伯莎·梅森看作是邪恶的“疯女人”,是女主人公简善和美的陪衬。二是基于女权主义批评视角,承认伯莎·梅森是疯子,但她是婚后被丈夫逼疯的,她的“疯”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反抗意识是女主人公简的隐蔽性人格(朱虹,1988:92;方平,1989:41)。然而,小说本身就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这已然为心理描写、揭示最真实的“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将伯莎·梅森的性格强加到简身上,颇为牵强。尽管两种观点存在差异,但具有共识性的是都认为伯莎·梅森确实疯了。本文尝试从全新的视角出发,运用理想化认知模型,力图阐明“疯子”并不疯。
认知诗学是21世纪初诞生的新型交叉学科,直接基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而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和新的研究范式,认知诗学不仅能够解释文本的意义是如何产生和获得的,而且能够对文本有新的发现,即发现新的原因、新的含义或新的形式特征和美学价值(熊木清,2012:448)。总之,认知诗学是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重新评估(Stockwell,2002:8;赵秀凤、赵晓囡,2016:17)。理想化认知模型是认知语言学范畴的核心概念,对文学阐释有着重要的作用。
理想化认知模型与小说解读
小说是叙事的,围绕事件展开,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问题。作品意义的产生不仅依赖于文本本身,也依赖于特定文化背景中对相关事物、人物、事件、场景等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即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Lakoff,1987: 68)。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往往是由若干个具有汇聚倾向的ICM组成(Evans,2006:271)。 ICM强调“特定的文化背景”,即理想化认知模型不是客观的,而是具有文化性和认知性,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甚至还经常互相矛盾,或与我们所拥有的某项知识相矛盾(王寅,2014:228)。例如,当语篇中提到“Tuesday”时,将激活我们认知中“TUESDAY”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如太阳的运行规律、一天有24小时、一星期包含7天、这7天是按顺序排列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该认知模型的主观性,显然,“7天是一个星期”并不是客观存在于自然世界中,而是人为设定的(王寅,2014:228)。另外,调查表明,西方文化背景的人认为“Tuesday”是一周的第三天,而汉语文化背景下的人却普遍认为“Tuesday”是一周的第二天(成军,2006:67)。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化认知模型ICM是意义产生的重要来源。ICM主要运用以下四种模型建构:
命题结构模型:命题结构指由具备诸种特性的诸成分以及表达这些成分的诸种关系组成的结构(Lakoff,1987:282-283)。命题结构属于认知型模型,而不是现实的诸种细节体现,所说的实体是心理实体,而不是真实的事物,是一种心理表征。命题结构具有客观性,即命题结构并不包含隐喻、转喻或心理意象等想象性(imaginative devices)的手段。例如,“简是孤女”就是命题性理想化认知模型,陈述的是客观事实,因为简父母双亡。
隐喻映射模型:即通过隐喻性思维建构的认知模型,借助始源域事物的特征来认知和理解目标域事物的特征,通常而言,始源域事物是具体的、熟悉的,而目标域事物是陌生的、抽象的,其认知基础是感知相似性或体验相关性。这一点在道德概念的建构上具有突出体现。研究表明,大部分道德概念是隐喻性建构的,例如用干净/肮脏程度来描述道德概念,在“肮脏—不道德”“干净—有道德”之间建立联系,其认知基础就是感知相似性,因为肮脏的事物和不道德事物都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感,由此产生了与此相关的多种语言表达,如“白璧无瑕”“政治污点”等;而当用光线的明暗程度表示道德概念时,则是基于体验相关性,因为光线的充足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了解,从而影响安全感,因此用“光明磊落”表示有道德,而用“阴暗”表示不道德。隐喻思维具有无意识性和普遍性,统计数据表明,至少70%的语言是隐喻的。
转喻映射模型:转喻是指在由ICM建构的同一个概念域中,某个成分与另一成分之间或某一成分与整体之间构成替代关系的心理表征。转喻通常包括四种主要类型:部分代整体(PART FOR WHOLE)、整体代部分(WHOLE FOR PART)、结果代原因(EFFECT FOR CAUSE)和原因代结果(CAUSE FOR EFFECT)等。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2009:46)指出,英雄史诗、散文、小说、电影等基本上是转喻的。卢卫中和刘玉华(2009:12)认为,小说叙事是围绕人物描写事件,由于篇章限制,尽管作者可以使用更多的、更为详细的描述来建构整个事件,但通常也只选择优势细节(privileged details)来建构叙事内容。文学作品中适当的“留白”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相反,事无巨细、密不透风的、冗长的叙事不仅会使作品庞大笨重,也会令读者厌烦。
意象图式模型:指人们在对世界的理解、体验和认识过程中不断概括而逐步形成的抽象的框架结构、空间体系和概念表征,储存于人们大脑中,构成用来处理新信息的图式性意象(Johnson,1987:73)。基本的意象图式主要包括:容器、路径、对称、上下、前后、部分-整体、中央-边缘等(Lakoff,1987:282-283)。隐喻思维与意象图式的建构密切相关。例如,“门外汉”“圈内人”等表达的认知基础是借助隐喻思维将某个领域看作一个与周围环境有分界线的容器,满足条件的是“圈内人”,反之,则是“门外汉”。文学作品也离不开意象图式,钱钟书的经典著作《围城》便是以容器图式点睛,对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阐释离不开理想化认知模型。本文拟以上述四种理想化认知模型为基础,对《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进行观照,以期对该人物产生全新的认知。
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伯莎·梅森
伯莎·梅森是被禁闭的“疯女人”,她直接露面的机会少之又少,总体来说,她是一个失声的人物,她的疯子形象是由她丈夫罗彻斯特的一面之词建构出来的。从理想化认知模型看,这一固有形象就会完全颠覆。
(一)命题结构模型视域下的正常人
罗彻斯特和伯莎·梅森是法定意义上的夫妻,结婚14年,罗彻斯特将妻子当作疯子秘密关押在庄园的阁楼里10年,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罗彻斯特试图将下列理想化认知模型汇聚为“伯莎·梅森是疯子”这一命题的理想化认知模型:
① 我既看不到谦逊,也看不到仁慈;既看不到坦率,也看不到雅致……(345)
② 伯莎·梅森凶蛮无理、平庸、粗俗、淫荡……(345)
③ 伯莎·梅森智力低得像侏儒(345)
④ 伯莎·梅森心理庸俗、猥琐、狭窄(345-346)
⑤ (伯莎·梅森是)我所见过的最粗野、最下流、最堕落的生命……(346)
⑥ 伯莎·梅森身体的结实程度抵得上她脑子的贫弱……(346)
⑦ 这疯女人又狡猾又恶毒(349)
⑧ 伯莎·梅森是疯子的女儿(345)
为了巩固“伯莎·梅森是疯子”这一命题,罗彻斯特辅之以情景烘托,月圆之夜,伯莎·梅森的吼叫似“狼嚎”一般,着意营造一种惊悚的恐怖氛围,因为西方文化长久以来认为月圆与疯癫有直接关联(牟童,2019:8)。然而,上述ICM的汇聚倾向是“令人讨厌的正常人-ICM”,而不是“疯子”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疯子-ICM),因为疯子的典型特征是心智失常、精神错乱。显然,“讨厌”与“心智失常”不是相同的概念,两个命题模型不能等同视之。所有描述如“粗野”“下流”“堕落”“脑子贫弱”“狡猾”“恶毒”等激活的都是“令人讨厌的正常人-ICM”,而不是“疯子(心智失常的人)-ICM”。换言之,苛求一个精神病患者优雅、善良、智慧是荒谬的!另外,罗彻斯特指出,妻子的母亲也是精神病患者,试图以此推理妻子成为“疯子”的必然性。然而,根据“精神病-ICM”可知,精神病的确具有遗传性,但并不意味着必然的遗传性。妻子的母亲患有精神病,不过是使罗彻斯特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以此为契机大做文章,为污名化伯莎·梅森找个借口罢了。上述分析可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伯莎·梅森符合令人“讨厌”的人的性格特征,具体而言,就是令其丈夫讨厌,但与“疯子”属性相差甚远。
罗彻斯特的主要身份是伯莎·梅森的丈夫,“HUSBAND”的命题结构模型激活了如“婚姻”“男性”“责任”“道德权威”等ICM,这些ICM集合构成了HUSBAND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假设妻子确实是罹患精神疾病,成了“疯子”,罗彻斯特作为丈夫的反应也与正常人大相径庭。首先,他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对妻子刻骨的愤怒、仇恨。“愤怒-ICM”是对“本可以如此,却偏不如此”事件或人物的态度;“仇恨-ICM”是针对严重伤害自己身心的敌手的态度。预设(presupposition)是语义学范畴的重要概念,指发话人在生成言语过程中的预有信念、语用策略和交际意图,预设可以“揭示语句的内涵”(张德禄,1993:53)。由此可知,罗彻斯特的“预有信念”就是妻子是正常人,且具有高智商,因此难以对付。另外,根据“疾病-ICM”,生病不是人能够主观控制的,哪怕夫妻之间曾经矛盾重重,一方一旦患病,另一方正常的态度应该是悲悯、无奈、疲惫、绝望等等复杂情绪。如果妻子罹患精神疾病,丈夫何来的愤怒与仇恨且历经10年不能化解?由此推断可知,罗彻斯特内心很清楚,伯莎·梅森是难以对付的正常人。因夫妻关系不和,他索性将妻子当作疯子秘密囚禁,确实抹杀了妻子的存在,也有效地隐瞒了他已婚人士的身份,但也使夫妻关系彻底恶化,成为死对头。只要伯莎·梅森活着,他的生命就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罗彻斯特本人也将桑菲尔德庄园比作是“亚干的帐篷”“蛮横的墓穴”“魔鬼的狭小的石头地狱”(340),均与死亡有关。另外,将妻子当作疯子关押,罗彻斯特本人也承受着巨大的良心谴责和痛苦煎熬,伯莎·梅森被囚禁的10年,便是拷问罗彻斯特良知的10年,一旦触及,他马上变得暴躁、狂怒。可以设想,假如伯莎·梅森真的精神失常,罗彻斯特会重重的舒一口气,而不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综上所述可知,“伯莎·梅森是疯子”这一命题是不成立的,罗彻斯特所有的描述都在建构一个“令人讨厌的正常人”,一个死对头,而不是“疯子”。显然,“令人讨厌的正常人-ICM”≠“疯子-ICM”,“伯莎·梅森是疯子”违背了命题结构的客观性原则。“伯莎·梅森是疯子”只是借用“疯子”的相关特征来理解“令人讨厌的正常人”,其建构原则应该是隐喻映射。
(二)隐喻映射模型视域下的正常人
詈骂语是在愤怒、敌意、鄙视、仇恨等消极情绪支配下对人或事物进行的极具主观色彩的、侮辱性的、攻击性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客观性极低。几乎所有的詈骂语都是隐喻性的(桂永霞,2014:29),例如,“狗屎”“神经病”“垃圾”“畜牲”,本质上是取相关事物的讨厌特征来描述和理解认知对象。“伯莎·梅森是疯子”属于隐喻性描述,而非对客观事实的直接描述。
伯莎·梅森是富商之女,携带3万英镑的嫁资和庄园嫁给了罗彻斯特。婚后,夫妻冲突不断,关系日渐恶化。当丈夫“足够富有”,夫妻迁居英国后,她被当作疯子关押起来。囚禁的10年中,伯莎·梅森曾3次走出密室,这为还原真实的梅森提供了一些关键信息。第一次,她溜进了丈夫的房间,要烧死他。需要注意的是,她目标很明确,就是丈夫,而不是其他人,因为偌大的桑菲尔德庄园还住着其他不少人。第二次,在丈夫要和另一个女人举办婚礼前的一天深夜,伯莎·梅森溜进了这个女人的房间,想必是要看看丈夫将迎娶的女人是何方神圣,但没有表现出任何要伤害人的迹象。显然,这绝不是罗彻斯特口中那个见人就咬、见人就杀、吸血鬼一样的疯子(320),否则伯莎·梅森当晚可以轻易置简于死地,因为简不仅瘦小,而且因惊吓过度已经晕了过去。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伯莎·梅森见到丈夫时,却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婚礼当天,罗彻斯特被当众揭发重婚,婚礼被迫取消,罗彻斯特愤怒地率众离开教堂回家,前往“野兽窝”见识“疯子”妻子,在一大群人中,伯莎·梅森扑向丈夫,和他扭打起来,由于体力上根本不是丈夫的对手,迅速被制服。可见,伯莎·梅森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罗彻斯特本人。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伯莎·梅森被层层禁闭,却能够获悉丈夫重婚,深夜溜出来看了丈夫的未婚妻后,又悄无声息地返回阁楼,这足以说明,伯莎·梅森和看护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和妥协,否则,她根本不可能做到。第三次,伯莎·梅森逃了出来,放火焚烧庄园,步入火海,身亡。种种迹象表明,伯莎·梅森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疯子能够完成的,她不仅神志清醒,而且思维缜密、恩怨分明。
综上所述,可知“伯莎·梅森是疯子”是隐喻性詈骂语,罗彻斯特甚至将妻子婚前的爱慕异化为“勾引”,詈骂语的主观性可见一斑。隐喻性詈骂语的认知基础是心理相似性,即厌恶心理,罗彻斯特是出于主观上强烈的憎恶心理,将妻子喻为疯子,并将伯莎·梅森仅仅针对他本人的报复行为泛化为普遍的攻击性,将其妖魔化,可谓用心良苦!
(三)转喻映射模型视域下失败婚姻中的被迫害者
事件转喻理论认为,从事件组成看,一个典型的事件包括四个要素:“事前(BEFORE)”指动机、潜在性和能力等可以导致事态场景发生;“事中(CORE)”指现存/真实事态场景;“事效(RESULT/EFFECT)”即紧跟事态场景的必然后果;“事后(AFTER)”指事态场景的可能后果,其中的每个要素都有可能与整个事件形成转喻关系(Lakoff,1999:447)。以此为基础,下文将从四个方面分析罗彻斯特与伯莎·梅森婚姻的成败机制。
事前(BEFORE)。婚姻主体双方的动机是什么?罗彻斯特陈述的全部是他人的动机,而非自己所愿:罗彻斯特的父亲为了确保财产的完整性,将财产继承权全部给了长子;为了保证小儿子罗彻斯特的生存,安排他去向富商的女儿求婚,因为有3万英镑的嫁资。罗彻斯特一再懊悔,说他当时刚大学毕业,不谙世事,受伯莎·梅森勾引、情敌们的刺激、众人的怂恿,他落入了众人联手设计的圈套,糊里糊涂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对于妻子的巨额嫁资,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父亲没有提到她的钱财”(345)。罗彻斯特着力凸显他人的动机、隐去了自己的动机,即用他人动机代替了全部动机,是典型的“部分—整体ICM”转喻性叙事。罗彻斯特一再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她”(345),那么,他既不爱女方,又不图她的钱,难道他是白痴或者任人摆布的玩偶吗?横向联系可知,巨额嫁资毫无疑问是罗彻斯特择偶的关键动机。由于篇章限制,小说必须选择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来揭示特定群体、特定阶层,从而展示宏观的、立体的社会。小说开篇即描写了“我”与表兄的冲突,“我”是穷苦的孤女,10岁,因父母双亡,从小寄身于富人(舅妈)篱下,被嫌弃欺凌;表兄14岁,富人家庭的孩子,小孩打架,成年人调解,由此引出了多方观点,借以揭示当时金钱社会的本质特征。没有钱就没有尊严,没有钱就活该被践踏,类似的事件在小说中比比皆是,甚至慈善机构也不例外。正如徐葆耕(2014:177)指出,金钱和权力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家殚精竭虑所探索的社会表层之下最隐蔽因而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简·爱》通过“我”的所见所闻,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社会各个阶层,如富人、穷人、慈善机构人员、伯爵夫人、歌女、舞女等,根据“个体-范畴”“子事件-复杂事件”之间的转喻关系,揭示了金钱社会这一显著特征。罗彻斯特“大学毕业”,激活了如“一定的年龄”“成熟的认知能力”和“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等ICM,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罗彻斯特岂能不明白不名一文的生活将是怎样的残酷?另外,当时已婚妇女无权掌管财产,罗彻斯特生于斯长于斯,对这一婚俗必然有所耳闻。纵向联系可知,罗彻斯特不仅对金钱敏感,而且具有强大的操控能力。当父兄亡故,他又继承了大笔财产而足够富有,他一气呵成,采取种种举措,迅速迁回英国,脱离妻子娘家的影响,找医生确诊妻子精神病、囚禁妻子,然后,放浪形骸游走于各类女人之中,这与罗彻斯特自我描述的那个不谙世事的纯洁青年判若两人!时过境迁,面对自己追求的女人,罗彻斯特在讲述婚姻的来龙去脉时,隐去图谋妻财的不光彩动机,不过是要洗白自己,彰显品格之高洁,维护高贵绅士的美好形象,同时也博取恋人的同情。那么,伯莎·梅森的择偶动机是什么呢?根据罗彻斯特的描述“她千方百计讨好我,拼命显示她的美貌和才情来讨我的喜欢……她又来勾引我”(345)可知,伯莎·梅森的择偶动机应该是爱情。因为,对于一个养尊处优、被异性众星捧月、将携带巨额嫁资出嫁的美女,能使她屈尊的似乎也只能是爱情了。概言之,这桩失败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一个因钱而来,一个为情而去。
事中(CORE)。罗彻斯特和妻子4年的婚姻生活过程,关系是如何恶化的?婚后,罗彻斯特住进了作为妻子嫁妆的湿漉漉的花园,并在此庄园生活了4年之久。然而,罗彻斯特对这段生活的描述基本是空白的,只是一再围绕妻子是多么讨厌这一主题打转。
事效(RESULT/EFFECT)。4年的婚姻生活培养了罗彻斯特对妻子及其家人刻骨的仇恨,妻子是个疯子、妻子的弟弟是个白痴,厌恶妻子所有的亲属(347)。4年将尽时,罗彻斯特的生活迎来了转机,父兄亡故,他继承了全部财产,“我够富有的了”,不迟不早,“当时医生已经诊断出,我的妻子疯了”(346)。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陈香兰和申丹(2009:1)认为,语篇内普遍存在“伏笔”和“应笔”之间的转喻关系,在此则体现为金钱与话语权之间的因果转喻关系。《维莱特》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著作,其中也包含有精神病案例,作者感叹精神疾病是一个 “复杂得无法检验,抽象得一般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勃朗特,1996:344)。由此可知,伯莎·梅森被诊断为疯子完全有可能是金钱运作的结果。另外,看护人也是按疯子来描述伯莎·梅森的,那么,看护人的话是否值得参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罗彻斯特说他“出了很多钱”“一年200磅”从疯人院雇来一个“忠实可靠的”“好看护”(349)。从文中可知,简做家庭教师一年的收入是30磅,足以说明罗彻斯特确实是“出了很多钱”,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在此依然存在金钱与话语权之间的因果转喻关系。总之,伯莎·梅森之所以被丈夫当作疯子囚禁,金钱起到关键作用。伯莎·梅森就是这样步步为营被迫害,在金钱编织的社会网络中,她没有出路,她注定万劫不复。
事后(AFTER)。伯莎·梅森逃出来,放火烧毁庄园,葬身火海。罗彻斯特在救火中双目失明、财产尽失,但也不再被婚姻束缚,为男女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创造了条件。
总之,罗彻斯特关于婚姻的叙述,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表现出典型的转喻性叙事,详略皆服务于叙述者的目的意图,把自己塑造成无辜受害的高贵绅士,同时将妻子污名化、妖魔化为具有普遍攻击性的“疯子”,顺理成章,也使后续对妻子的迫害成为绅士对恶女人的正当管教。事实上,污名化和妖魔化女性一直以来都是男权社会迫害女性的重要途径,始于心智上的否定,继而否定其所有行为,最终将对女性的迫害正当化、合理化。借助转喻性理想化认知模型可知,罗彻斯特绝非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而是思想偏激、自命清高、不思悔改的浪荡子;伯莎·梅森是金钱社会失败婚姻中的被迫害者,丈夫娶她,完全是为了那笔巨额嫁资。丈夫有钱后,因夫妻严重不睦,伯莎·梅森被贴上“疯子”标签,永久囚禁。总之,罗彻斯特和伯莎·梅森的婚姻可谓成也金钱、败也金钱。
(四)意象图式模型视域下的被迫害者
意象图式来自身体体验,特定的词汇可以唤起意象图式(汪少华,2005:43)。其中,容器图式是最基本、最常见的图式,这是因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一点一点地感知所使用的器皿、自己的身体、居住的房屋、乘坐的交通工具等等,逐渐形成了对容器常规性的认知结构。建筑与容器存在密切的联系,桑菲尔德庄园以及阁楼都激活了“容器”图式。首先,桑菲尔德庄园是个隐秘的“容器”。“我”长途跋涉去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在距桑菲尔德庄园仅六英里的一个旅馆,向人们打听该庄园的位置,然而,无人知晓,足以说明庄园地处偏僻。到了庄园后,“我”发现“坍塌了的篱笆”,“高大的老荆棘树”把庄园与外界隔开,不远处的小山以“一种归隐遁世的气氛包围了桑菲尔德”(109)。可以看出,容器图式隐含在对桑菲尔德庄园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桑菲尔德庄园拒绝世人靠近它、了解它。同时,“thornfield”一词的字面义是“荆棘地”,具身认知使人本能地将该词与磨难、棘手、麻烦等联系起来,预示着桑菲尔德庄园是一个不祥的容器。庄园的阁楼则更为鲜明地激活了“容器”图式,罗切斯特先生先后打开两道门,第一道是“低矮的黑门”,进去后,墙壁被帷幔遮蔽,打开帷幔,出现了第二道门,里边囚禁着“疯女人”,没有窗户,暗无天日,天花板下的链子挂着一盏灯(331)。这样的密室隐藏至深,关押其中,不仅插翅难逃,而且也绝无可能向外界传递任何信息。毫无疑问,这样的秘密囚禁是成功的,甚至庄园上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里边关着一个“疯女人”。综上所述可知,桑菲尔德庄园及阁楼构成一个层层加固的密闭“容器”,伯莎·梅森在此被残忍迫害,“我”目睹了她被两臂反绑起来,又被捆在一把椅子上。平常当她“发病”时,看护人在疯人院工作的儿子也会来帮忙(340)——至于如何“帮忙”,书中没有交代,但也可想而知。10年折磨,伯莎·梅森变成非人非兽、不人不鬼的怪物,身上穿的不知道是床单还是裹尸布,头发灰白、两眼充血、脸又黑又肿、皱纹纵横。总之,当伯莎·梅森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并被当作疯子虐待10年后,从外表看来,她确实越来越像疯子——反过来讲,在这样遭遇中,谁还能指望她心存美好、衣着得体、谈吐优雅?罗彻斯特因果倒置,不过是要将迫害妻子的行为正当化、合理化。这也反映了金钱社会一个可悲的现象:在夫妻关系极端恶化的婚姻中,丈夫“足够富有”很有可能让妻子变成“疯子”。
结 语
根据理想化认知模型理论,本文从命题结构模型、隐喻映射模型、转喻映射模型和意象图式模型四个视角对伯莎·梅森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重释,经过分析发现,“伯莎·梅森是疯子”是隐喻性理想化认知模型,是认知主体罗彻斯特出于强烈的憎恶心理而将妻子污名化为疯子;转喻映射模型则揭示了这桩婚姻成败的内在机制,而庄园、阁楼、荆棘地等意象,则昭示着这些场所是心智正常的女主人公被迫害的真正的牢笼。从理想化认知模型来看,伯莎·梅森自始至终都没有疯,是一个头脑清晰、思维活跃的正常人。她是男权社会的绊脚石、金钱社会的牺牲品,是代表着男权利益的罗彻斯特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人物。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理想化认知模型为我们研究文学经典打开了另一扇新奇的窗户。
注释:
① 凡引自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内容,均出自:夏洛蒂·勃朗特. 2015. 简·爱[M]. 宋兆霖,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引用时只出现页码,不另做注。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的其它文章
- 哈罗德·品特《申请者》中的荒诞性:认知文体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