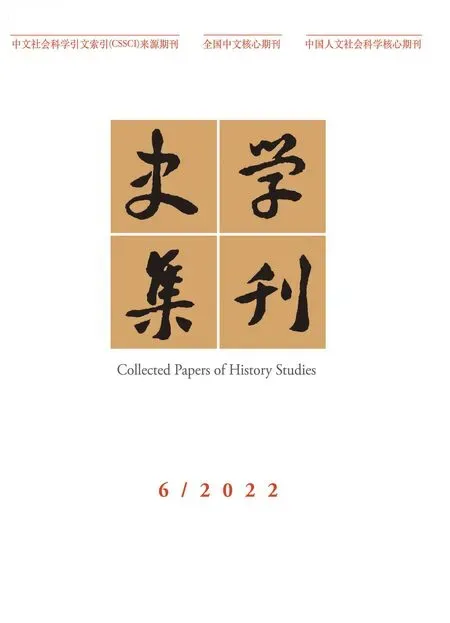论皇侃经学思想的主体与本质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从两汉至南北朝,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汉儒的训诂章句之学、魏晋的经义之学和南北朝的义疏之学。(1)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0页。南朝儒家经典的义疏当属皇侃的《论语义疏》最为典型。研究者多从佛、玄、道思想与皇侃经学思想关系的角度加以论述,甚至有学者认为,皇侃注经已经玄学化了。(2)张文修:《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朱汉民:《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宋力:《浅析〈论语义疏〉玄学化的注经特色》,《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徐望驾:《佛教文化与皇侃〈论语义疏〉》,《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徐望驾:《皇侃〈论语义疏〉道教语词刍议》,《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徐望驾:《皇侃〈论语义疏〉中的佛源词》,《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年第4期;柏宇航:《论佛教对皇侃〈论语义疏〉的影响》,《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这些论述毫无疑问地反映出皇侃经学思想某一方面的特色,但不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皇侃经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本文欲就此问题献芹以就正于方家。
一、《论语义疏》的儒家主体特征
《北史》评价南北朝双方各自的学术特点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北史》卷八一《儒林列传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09页。清人皮锡瑞这样评价南朝经学的“约简”:“说经贵约简,不贵深芜,自是定论;但所谓约简者,必如汉人之持大体,玩经文,口授微言,笃守师说,乃为至约而至精也。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余技。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4)(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6页。诚然,南朝经学与两汉时相比显示出极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毕竟不是本质上的,皮锡瑞所用“说经”二字,表明这种差异只是注经方法上的。
应该说,南朝与两汉的经学有异有同,南朝经学家注经时加入了佛教玄学,这在两汉时是没有的,这是方法上的“异”,但是,南朝的经学并没有因此变成玄学或佛经,它还是儒家经典,这是本质上的“同”。然而不少论者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方法之异上,而忽视了本质之同。或许是因为本质之同太浅显了,人们认为没有研究和强调的必要。正是由于人们常常对一般常识性的东西熟视无睹,因而放弃了对常识背后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例如南朝学者“儒玄双修”,在文献记载中俯拾皆是,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很少有人进一步问,谁在儒玄双修?双修的主体是儒者还是玄学家?这个问题对于认识南朝经学尤其是皇侃经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皇侃不是玄学家。他注《论语》与何晏、王弼有本质不同。何晏、王弼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他们的“贵无论”奠定了魏晋玄学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他们注《论语》是站在玄学立场上,试图借儒家经典阐发其玄学思想。而皇侃注《论语》,是力图保持完整的儒家体系。他说:“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自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7页。皇侃所说何《集》即何晏《论语集解》。这部著作以儒家正宗《鲁论》为基础,经过西汉张禹兼讲《齐论》,发展成为世所贵的《张侯论》。何晏又将东汉马融、郑玄、苞咸、周氏,曹魏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七种儒家解说集于一书。尽管作为玄学家的何晏作《集解》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5页。加进一些玄学,但总体上没有影响儒家体系的完整。这是皇侃义疏《论语》先通何《集》的一个重要原因。皇侃始终是一个经学家,《梁书》把皇侃列入《儒林列传》:
侃少好学,师事贺玚,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解职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于夏首,时年五十八。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7)《梁书》卷四八《儒林·皇侃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0-681页。
皇侃一生始终从事儒学讲诵,吸取佛道概念和一些思想纳入《论语集解义疏》,却不破坏儒家体系的完整,不改变《论语》的儒家性质,这个事实与其说是“儒玄双修”,毋宁说是皇侃对儒家立场的坚持和吸收其他学说的养分对儒家思想加以丰富和提高。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与何晏《论语集解》相比有两个显著变化:
一是玄学思想数量增大。《论语集解义疏》中的玄学家,何晏、王弼、郭象自不待言,除此之外,还有缪播。缪播字宣则,晋怀帝时任给事黄门侍郎、侍中、中书令,后被司马越所杀。缪播所注《论语》在《论语集解义疏》中保存了17条:
1.释“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人之极也,能审好恶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恶。若未免好恶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2.释“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学末尚名者多,顾其实者寡。回则崇本弃末,赐也未能忘名。存名则美着于物,精本则名损于当时,故发问以要赐对,以示优劣也。所以抑赐而进回也。
3.释“子见南子”:应物而不择者,道也;兼济而不辞者,圣也。灵公无道,众庶困穷,钟救于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钟不可以不应,应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见之。涅而不缁,则处污不辱,无可无不可,故兼济而不辞。以道观之,未有可猜也。
4.释“子路不悦”:贤者守节,怪之宜也。或以亦发孔子之答,以晓众也。
5.释“夫子矢之曰”:言体圣而不为圣者之事,天其厌塞此道耶。
6.释“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圣教轨物,各应其求,随长短以抑引,随志分以诱导,使归于会通,合乎道中。以故刚勇者屈以优柔,俭弱者励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为累,常恐有失其分,觅功衒长,故因题目于回,举三军以致问,将以仰叩道训,陶染情性,故夫子应以笃诲以示厥中也。
7.释“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夫投竿测深,安知江海之有悬也?何者?俱不究其极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为夫子,武叔贤子贡于仲尼,斯非其类耶?颜回尽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渊亦唯孔子也。
8.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死生者,所禀之性分;富贵者,所遇之通塞。人能命养之以福,不能令所禀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贾,不能遭时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为言自然之势运,不为主人之贵贱也。
9.释“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居理足,本无危亡。然贤而图变,变则理穷,穷则任分,所以有杀身之义,故比干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10.释“子曰:有教无类”:世咸知斯言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谅深。生生之类,同禀一极,虽下愚不移,然化所迁者,其万倍也。生而闻道,长而见教,处之以仁道,养之以德,与道终始,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论之也。
11.释“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则失之有渐。大者难倾,小者易灭。近本罪轻,弥远罪重。轻故祸迟,重则败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
12.释“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宰小邑,能使民得其可弦歌以乐也。
13.释“割鸡焉用牛刀”:惜不得导千乘之国,如牛刀割鸡,不尽其才也。
14.释“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夫博学之言,亦可进退也。夫子闻乡党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闻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为戏也;其知之者,以为贤圣之谦意也。
15.释“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玉帛,礼之用,非礼之本。钟鼓者,乐之器,非乐之主。假玉帛以达礼,礼达则玉帛可忘。借钟鼓以显乐,乐显则钟鼓可遗。以礼假玉帛于求礼,非深乎礼者也。以乐托钟鼓于求乐,非通乎乐者也。苟能礼正,则无持于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畅和,则无借于钟鼓,而移风易俗也。
16.释“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尔时礼坏乐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惧其往,以为圣人无微旨以戒将来,故假时人之谓,启愤于夫子,义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何?答曰:时人失礼,人失礼而予谓为然,是不仁矣。言不仁于万物。又仁者施与之名,非奉上之称,若予安稻锦,废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
17.释“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则文”:君子过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务在改行,故无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后能之理著,得失既辨,故过可复改也。小人之过生于情伪,故不能不饰,饰则弥张,乃是谓过也。(8)参见(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83、106、148、149、160、271、302、398、415、426、446、447、458、468、469、500-501页。
在上述17条中,第一、第七、第十条中的“极”,第二、第九、第十一、第十五条中的“名”“实”“本”“末”,第三、第五、第六、第八、第十、第十四、第十六条中的“道”“理”“无可无不可”,第六、第八、第九条中的“分”“性”,都是玄学概念或命题。缪播《晋书》中有传,本传中丝毫反映不出他与玄学关系的信息,然而通过《义疏》可看到这个貌似与玄学无关的人却是个玄学家。
二是容纳了佛道思想。东晋南朝玄学乃西晋之余绪,一方面玄学家不少,佼佼者不多;另一方面又与佛教相融合。东晋张凭、殷仲堪,南朝刘宋颜延之、释慧琳,萧齐沈马粦士、顾欢,萧梁太史叔明均属此类。张凭、殷仲堪已有专文论述,(9)王云飞:《张凭〈论语〉注研究》,《船山学刊》,2012年第1期;王云飞:《殷仲堪〈论语〉注研究》,《唐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颜延之和释慧琳曾是政治同僚,释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均为诋呵佛教之论。“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余言”,被宋文帝赞作“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10)(梁)僧佑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卷一一《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之论,足见其佛教立场。颜延之释《论语》“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说:“射许有争,故可以观无争也。”他释“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说:“秉小居薄,众之所与;执多处丰,物之所去也。”他释“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说:“谮润不行,虽由于明,明见之深,乃出于体远。体远不对于情伪,故功归于明见。斥言其功故曰‘明’,极言其本故曰‘远’也。”(11)参见(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54、95、304页。争与不争、失与得、明与远,这些命题具有鲜明的佛学色彩。
顾欢是道家,然而却说“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道则佛也,佛则道也”,(12)《南齐书》卷五四《顾欢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31-932页。实则把佛纳入道之体系。他在释《论语》“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说:“此明非求非与,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内充,则是非自镜也。”顾欢所说的“明”借用的是佛教概念,即“智慧”,用“明”形容五德内充。顾欢释“未知生焉知死”说:“夫从生可以善死,尽人可以应神,虽幽显路殊,而诚恒一。苟未能此,问之无益,何处问彼耶?”这种解释也有佛教轮回的意味。他释“回也其庶乎?屡空”说:“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每虚以称贤。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于无欲。虚而未尽,非‘屡’如何。”太史叔明也发挥说:“颜子上贤,体具而敬则精也,故无进退之事,就义上以立‘屡’名。按其遗仁义,忘礼乐,隳支体,黜聪明,坐忘大通,此亡有之义也。忘有顿尽,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验之,圣人忘忘,大贤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复为未尽。一未一空,故‘屡’名生也焉。”(13)参见(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15、274、279-280页。顾欢所说的圣人“无欲于无欲”“全空”,太史叔明所说的“圣人忘忘”,也颇有“本来无一物”的禅味。
上述两个变化,能否说明皇侃的经学思想玄学化或佛道化了呢?当然不能。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对汉末以来诸家对《论语》的注疏做了如下统计:
何晏所集七家,并何为八;江熙所集十三家,并江为十四;皇《疏》所引二十八家,并皇为二十九。通为五十一家。(14)吴承仕著,秦青点校:《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2页。
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魏晋至南朝梁,对《论语》的注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何晏《集解》,第二个阶段是江熙《集解》,第三个阶段是皇侃《义疏》。这三个发展阶段反映出这个时期经学发展的两个问题:
第一,儒家思想始终占主体地位。何晏《集解》八家,除何晏之外,马融、郑玄、苞咸、周氏、陈群、王肃、周生烈几乎都是儒家。皇侃《义疏》的儒家主体性前已论述,此不再赘。此只论江熙《集解》的儒学主体性。
江熙《集解》十四家最具儒家特色的是江熙和范宁,(15)关于江煕与皇侃的思想联系,可参见高侨均:「江煕『集解論語』と皇侃『論語義疏』——魏晉六朝における『論語』解釋」、『六朝學術學會報』第9集、2008年、101-129頁。关于范宁的思想,参见[日]吉川忠夫著,王启发译:《六朝精神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114页。玄学色彩最鲜明的是郭象和缪播。江熙字太和,东晋时人,官至兖州别驾。他注《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保存在《义疏》中的《论语注》102条,从内容看很少有玄道佛思想痕迹,当为儒家解经。范宁也是东晋时人,官至豫章太守,在郡大设庠序,取郡四姓子弟,课读《五经》。他曾著论痛斥何晏、王弼玄学说:“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16)《晋书》卷七五《范汪附范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4-1985页。范宁注《论语》有54条,亦为儒家解经无疑。郭象解经15条,缪播解经17条。二人加起来还抵不上范宁一人所注。如果把江熙、范宁二人所注与玄学家所注做一比较,更可以彰显其儒家特色。然而江熙、范宁、郭象、缪播注释同一条《论语》的数量有限,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王弼的注释也加进来。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郭象注道:孔子“伤器存而道废,得有声而无时”,由此引申出器与道的问题。而江熙注道:“和璧与瓦砾齐贯,卞子所以惆怅;虞《韶》与郑卫比响,仲尼所以永叹。弥时忘味,何远情之深也!”范宁注道:“夫《韶》乃大虞尽善之乐,齐,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陈,舜之后也。乐在陈,陈敬仲窃以奔齐,故得僭之也。”(17)参见(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163页。江熙之解侧重解释孔子的感情所在,范宁之解则在说明齐国之所以有韶乐的原因。《论语·子罕》说:“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王弼注道:“譬犹和乐出乎八音,然八音非其名也”,涉及名与实的关系。而江熙注道:“言其弥贯六流,不可以一艺取名焉,故曰‘大’也”,(18)参见(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206页。意在说明“大哉”的意思。《论语·阳货》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王弼注道:“孔子机发后应,事形乃视,择地以处身,资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乱人之邦。圣人通远虑微,应变神化,浊乱不能污其洁,凶恶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难不藏身,绝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系而不食,舍此适彼,相去何若也”,言及圣人通远虑微,应变神化,避难不藏身,绝物不以形之特质。江熙注道:“夫子岂实之公山弗盻乎?故欲往之意耶。泛尔无系,以观门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见形而不及道,故闻乘桴而喜,闻之公山而不悦,升堂而未入室,安测圣人之趣哉?”(19)参见(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52-453页。虽涉及形与道之抽象,但侧重点在于阐述孔子志向和子路之愚昧。综上所述,同样的注,江熙、范宁与玄学家显然不同,前者说经,后者说理;前者具体,后者抽象;前者实,后者虚。可见江熙、范宁之注儒家色彩是鲜明的。
第二,儒家思想体系的成熟。比较注释《论语》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儒家思想主体有一种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趋势。魏晋时期玄学大盛,但何晏集解《论语》,除个别地方做玄学发挥之外,所集绝大部分都是儒家学者所注。何晏之所以如此,当然想借儒家《论语》宣扬自己的思想,但如果玄学理论发挥或集入过多,恐怕不会得到当时经学界的接受和认可,反而对宣扬自己主张不利。这也反映了当时在玄学思想冲击下,儒家相对封闭以自我保护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说是因自身体系不成熟而缺乏包容和自信的表现。魏晋时期,何晏用玄学利刃在儒家相对封闭的经学本体上撬开了一个口子,然而到了江熙《集解》,更多玄学思想被加进来,到了皇《疏》又主动引进了佛道思想,而这种引进又是在儒家体系不变的基础上进行,与其说是儒家的玄学化或佛道化,毋宁说是儒家主体由于成熟而更加开放包容的表现。因为只有主体的成熟,才会在吸收引进不同思想的同时而不被改变本质。
二、皇侃经学思想的儒家特性
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勿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20)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内篇·齐物论》,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3页。尽管论而不议,也足以说明儒家圣人对六合之内人和事的关照。况且,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学者对六合之内的事理且论且议且阐发。可以说,关照现实,服务现实是儒家思想的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潮中,玄学所关照的是形而上的幽深与玄远,佛教所关照的是冥冥中的彼岸世界,因此,关照现实是儒家思想区别于上述二者的鲜明特性。(21)关于皇侃经学思想的儒家性质及与现实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如陈金木:《皇侃之经学》,“国立”编译馆1995版。日本学者今井裕一发表了系列研究皇侃的论文,如「聖·賢の境界:皇侃『論語義疏』における顔回」、『國學雜誌』第117辑、2016年、97-113頁;「至徳の証明:皇侃『論語義疏』における泰伯」、『國學院中國學會報』第61辑、2015年、34-44頁;「皇侃の『命』について」、『國學院中國學會報』第54辑、2008年、44-58頁。日本学者猪股宣泰也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如「『論語義疏』に見える皇侃の學問観·人間観と教化論」、『集刊東洋學』第88集、2002年、42-61頁;「『論語義疏』に見える皇侃の思想」、『集刊東洋學』第80集、1998年、1-19頁。
东晋之后,朝代更替、政权禅代一个接着一个,臣子变为天子,天子又被迫“禅位”给自己的臣子。在这种循环往复中,所谓“忠”的观念被消磨得全无踪影。不仅禅代者不忠,就是一些无篡位之心或无篡位之力的臣僚,看着自己所赖以取得俸禄的朝廷更主易姓,也安之若素,不肯以身殉忠,更甚者还为“禅代”推波助澜。以刘宋为例,萧道成辅政,权势渐重,在刘宋政权岌岌可危之际,尚书令王僧虔和左仆射王延之却持“中立无所去就”态度。(22)《南齐书》卷三二《王延之传》,第585页。褚渊、王俭等均为刘宋之臣,却成为南齐萧道成的佐命元勋。在一次宴会上,萧道成对他们说:“卿等并宋时公卿,亦当不言我应得天子。”褚渊当即答道:“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识龙颜。”(23)《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第429页。宋时公卿甘作萧齐臣子,并以未早识龙颜为愧,可见他们对刘宋王朝存亡处之淡然的态度。
对皇位的篡夺使“忠”的观念遭到进一步破坏,而“忠”的观念崩坏,又使对帝位的篡夺之风愈演愈烈,从外族他姓发展到皇室内部。南朝宋、齐两代,宗室内部互相残杀尤为酷烈,被杀者中,上辈有叔祖,同辈有兄弟,晚辈有侄孙。阅宗室诸王列传,这些被杀之人,有的是企图篡位,有的是被牵进了帝位争夺的旋涡,有的是被视为对皇位的威胁。总之,他们的死,大多与帝位之争有直接或间接关系。“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24)《魏书》卷九七《岛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2页。在这种父子兄弟残杀中,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在皇室中也只剩下一些支离的碎片了。
魏晋以来在政治斗争中臣下所表现的不忠,宋、齐时期皇室所表现的不孝,对梁武帝的影响极深。他自己就是趁着齐末宗室大杀戮所造成的政权虚弱取而代之的,因此,他对不忠不孝所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感。他即位的当年四月便下诏说:“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终之运,当符命之重,取监前古,懔若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杀胜残,解网更张,置之仁寿。”(25)《梁书》卷二《武帝纪中》,第36页。这里的“取监前古,懔若驭朽”,绝非即位时的套话,而是反映了他对不忠不孝给政权稳固造成冲击的忧心。所以,南朝萧梁建立以后,梁武帝一直致力利用种种手段重新培育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皇侃的日诵《孝经》二十遍当与这种社会背景有关。
作为儒家学者,皇侃对儒家忠孝道德重建的关心和参与,不仅仅表现是在日诵《孝经》二十遍,更重要的表现是在《论语义疏》中对忠孝观念的阐发。
皇侃关于“孝”本质的论述,表述了移孝入忠、忠孝合一的观念。这个观念在《论语义疏》中多有涉及。《论语·为政》:“临民之以庄,则民敬;孝慈,则忠。”皇侃注释:“言君居上临下,若自能严整,则下民皆为敬其上也。”“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则民皆尽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曰:‘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则民亦孝慈。孝于其亲,乃能忠于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2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39页。皇侃在“江熙曰”前用了一个“故”字,既表示了他对江熙注解的赞同,又表示了他与江熙解释之间相通的逻辑关系。这种相通的逻辑关系可以从皇侃注释孔子的另一段话中看出来。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奚其为为政?”皇侃对此注释说:“言人子在闺门,当极孝于父母,而极友于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为政也。”“此是孔子正答于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则邦国自然得正。亦又何用为官位乃是为政乎?”(2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0页。人如果在家孝悌做得特别好,从政后自然就正直忠诚,用不着把他放到官的位置上后再要求他正直和忠诚。这与江熙所说“孝于其亲,乃能忠于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是一个意思。皇侃在注释“举善而教不能则民劝”时说:“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则举而禄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则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则民竞为劝慕之行也。”(28)(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39页。这里的“善”显然是指忠孝行为,阐释了皇侃任用忠孝之人,培养忠孝之人,从而使忠孝蔚为风气的主张。《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皇侃注释说:“人子之礼,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忠,移事兄悌以事于长则从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孝以事父,悌以事兄,还入闺门,宜尽其礼也。先言朝廷、后云闺门者,勖已仕者也,犹‘仕而优则学’也”。(2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223页。在南朝梁积极推进儒家忠孝道德时,上述这些关于忠孝的阐发,显然是一种理论和舆论上的助推。
礼仪制度在南朝梁得到极大的发展。梁武帝即位后,十分重视礼对治理国家的作用。“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505),梁武帝又下诏置五经学馆,一时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梁武帝还“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燕语,劳之以束帛”。由于他的提倡和推动,梁朝的儒学水平大大高于东晋和宋齐,出现了“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的局面。(30)《梁书》卷四八《儒林列传·序》,第661-662页。同时,南朝梁又是礼制建设的关键时期。尚书仆射徐勉曾这样叙述梁朝以前五礼制度建设的情况:
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咨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敛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31)《梁书》卷二五《徐勉传》,第380-381页。
为此,梁武帝专门下诏说:“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32)《梁书》卷二五《徐勉传》,第381页。于是梁朝建立后,制定五礼制度的工作有序展开,最后完成了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的五礼大典。
了解了上述社会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皇侃撰写《礼记讲疏》,并将《礼记讲疏》上奏给朝廷的行为,这是出于一个儒家学者对现实的强烈关照。这种关照同样表现在《论语义疏》中。《论语义疏》中关于礼的注释,大多围绕礼与治国关系的主题。
关于礼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皇侃注释说:“夫礼所贵,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不因于玉帛而不达,故行礼必用玉帛耳。当乎周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叹之云也。故重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明礼之所云不玉帛也。”(33)(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57页。礼的根本作用在于安上治民,而玉帛只是礼的形式,只重视形式而忽视其本质内容,就会使礼变成一个空壳。《论语·卫灵公》:“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皇侃注释说:“虽智及、仁守、莅庄,而动静必须礼以将之,若动静不用礼,则为未尽善也。”(34)(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12页。治国当然靠智、仁、庄,然而没有礼,智会有摇摆之失,仁会有松弛之失,庄会有严厉之失,所以要达到安上治民的目的,礼是最根本的要素。
礼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皇侃注释说:“为,犹治也。言人君能用礼让以治国,则于国事不难,故云‘何有’,言其易也。”“若昏闇之君,不为用礼让以治国,则如治国之礼何?”(3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89-90页。如果用礼治国,治理国家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臣之从君,如草从风。故君能使臣得礼,则臣事君必尽忠也;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3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69页。昏君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就是因为丢掉了礼。
治理社会风气也是治理国家的内容之一。《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皇侃对此注释说:“人君行化,必礼乐相须。用乐和民心,以礼检民迹。迹检心和,故风化乃美。故云‘礼之用,和为贵’。和即乐也。变乐言和,见乐功也。乐既言和,则礼宜云敬。但乐用在内为隐,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为美’者,先王谓圣人为天子者也,斯,此也。言圣天子之化行,礼亦以此用和为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礼而不用和,则于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礼须乐,此明行乐须礼也。人若知礼用和,而每事从和,不复用礼为节者,则于事亦不得行也。”(37)此段文字,中华书局校点本分句解释,不便整体引用,故此处征引《丛书集成新编》本《论语集解义疏》。参见(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丛书集成新编》第17册,新丰文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00页。社会风气包括人心和人的行为。这两个方面需要礼乐合力治理,乐和民心,礼检民迹,行礼须乐,行乐须礼,皇侃此论,强调了礼对治理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
人是治理国家的主体,治国者的素质高低,与其礼的修养有密切关系。《论语·尧曰》:“不知礼,无以立也。”皇侃注释说:“礼主恭俭庄敬,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礼者,无以得立其身于世也。故《礼运》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诗》云‘人而无礼,不死何俟’,是也。”(38)(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524-525页。人而无礼不得立身和生存,同样治国之人无礼,国便不能立,亦不能存。所以皇侃说:“得制礼乐者,必须德位兼并,德为圣人、尊为天子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礼乐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无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则礼乐不行;若有位无德,虽为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则礼乐不行,故必须并兼者也。”(3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153页。
上述皇侃《论语义疏》中关于“忠”“孝”“礼”等问题的阐释,植根于六合之内的孔子之论,针对当时振兴儒家道德和完成礼制建设的社会现实而议论发挥。它既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源之水,也不是没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谈,而是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具有鲜明的儒家特性。
三、《论语义疏》对儒家思想的理论提升
义疏之学兴起于南朝。清人皮锡瑞说:“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40)(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186页。蒙文通先生说:“及今文章句沦亡,义疏遂猾起于齐梁之际。”(41)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南朝义疏之学的兴起,当与佛教盛行有关。《维摩经略疏垂裕记》:“疏者疏也,决也,疏通经文,决择佛旨故曰疏也。”(42)(宋)智圆:《维摩经略疏垂裕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15页。《摩诃止观》卷七下:“第九安忍者,能忍成道,事不动亦不退,是心名萨埵。始观阴界至识次位八法,障转慧开,或未入品,或入初品。神智爽利,若锋刃飞霜,触物斯断。初心聪睿有逾于此,本不听学,能解经论。览他义疏,洞识宗途。”(43)(隋)智:《摩诃止观》,《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第99页上栏、中栏。可见“义疏”一词是由佛教经典而来。
皇侃是儒家学者,主张儒经独尊。他解释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说:“此章禁人杂学诸子百家之书也。攻,治也。古人谓学为治,故书史载人专经学问者,皆云治其书、治其经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故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为害之深也。”他还对何晏注“云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说:“云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者,善道,即五经正典也。有统,统本也。谓皆以善道为本也。殊途谓诗书礼乐为教之途不同也,同归谓虽所明各异而同归于善道也。云异端不同归者也者,诸子百家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归也。”(44)此段文字,中华书局校点本分句解释,不便整体引用,故此处征引《丛书集成新编》本《论语集解义疏》。参见(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丛书集成新编》第17册,第502页。这反映了皇侃对儒家经典的根本态度。然而皇侃并不一概排斥异端,《论语义疏》中出现许多佛教和玄学的词语和概念。如果细加分析可以发现,皇侃不是简单地使用这些概念,而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创造。佛教义疏是“疏通经文,决择佛旨”,是“览他义疏,洞识宗途”,那么,《论语义疏》应该是疏通儒家经文,决择儒家之旨,洞识儒家宗途。《论语义疏》对名物制度训诂忽而略之,对儒家思想的本旨发而弘之,这是对佛玄思想方法的运用和借鉴。用义疏的方法发掘儒经中的义理,是皇侃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义理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总结规律。皇侃《义疏》对规律的总结表现为对学习的认识。孔子说:“学而时习之。”皇侃则紧紧抓住“时”字发挥。他说,学有三时:人中、年中、日中。所谓人中,即学习要在适当的年龄,年纪太小则学不懂(幼则迷昏),太大了学不进去(长则扞格)。所谓年中,即一年当中选择合适的季节学习相应的知识(学随时气,则受业易入)。他还引用《王制》“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一语,并解释说:“春夏是阳,阳体轻清,诗乐是声,声亦轻清,轻清时学轻清之业,则为易入也。秋冬是阴,阴体重浊,书礼是事,事亦重浊,重浊时学重浊之业,亦易入也。”(4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2页。查《礼记·王制》无此语,不知此《王制》出自何书。或从《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一语而来。所谓日中,即将所学日日修习,不要有一日之废。皇侃把“时”分为三个方面:生理之时,四季之时,日月之时。在人生最好的年龄,在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并加以持之以恒的坚持。选择、安排、坚持与学习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触及学习的规律问题。
其二,揭示本质。皇侃《义疏》对事物本质的揭示表现在对“孝”的深层思考。《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皇侃解释“好犯上”为怀有谏诤之心,释“鲜”为“少”。怀有谏诤之心的孝悌之人之所以“少”,是“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谏”,即肯定一部分人即使怀有“犯上”谏诤之心,也是孝悌之人。这就否定了孝悌者必以无违为心,以恭从为性,没有犯颜谏诤之心。皇侃引用其师贺玚的话说:“今按师说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顺;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愿君亲之败。’故孝与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乱。”(4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5-6页。孝与不孝,不是看其表面上是否恭顺,因为表面的恭顺,有的是出于对长辈的尊敬,也有的是出于“愿君亲之败”的邪恶目的。孝与不孝,要看恭顺背后的动机,这就深入到了对“孝”的深层次探讨。
揭示本质还表现在对人性的探讨。《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马融注道:“所因,谓三纲五常也。”人类十世乃至百世的历史之所以可知,是因为三纲五常世世相因而不改变。皇侃则进一步把五常归为人性:“五常,谓仁、义、礼、智、信也。就五行而论,则木为仁,火为礼,金为义,水为信,土为智。人禀此五常而生,则备有仁、义、礼、智、信之性也。人有博爱之德谓之仁,有严断之德为义,有明辨尊卑敬让之德为礼,有言不虚妄之德为信,有照了之德为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恒,不可暂舍,故谓五常也。”(4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2页。这种认识,是对曹魏刘劭理论的继承。(48)刘劭《人物志》:“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参见(魏)刘劭著,梁满仓译注:《人物志·九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页。人性之常不变是就其质而言,就量而言是有变化的。皇侃疏《里仁》说:“里者,邻里也。仁者,仁义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为染着,遇善则升,逢恶则坠,故居处宜慎,必择仁者之里也。”(4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81页。怎样认识人性?皇侃认为,金木水火土或者说仁义礼智信包含在天地之气当中,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就天然赋有五常之性。性与情是不同的两种东西,性是与生俱来的,“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皇侃还提出“性无善恶”的命题,那么,仁义礼智信五常不是“善”么?皇侃认为,五常不但不可以名之为“恶”,也不能称之为“善”。这个论断是符合辩证法的。试想,如果认为有“善”五常,就不能否认有“恶”五常。既然人性禀五常之气,那么只有浓薄之分,不应有善恶之别。(50)(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45页。
其三,抽象概念。《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皇侃注释说:“此章美颜渊之德也。回者,颜渊名也。愚者,不达之称也。自形器以上,名之为无,圣人所体也;自形器以还,名之为有,贤人所体也。今孔子终日所言,即入于形器,故颜子闻而即解,无所咨问。故不起发我道,故言‘终日不违’也。一往观回终日默识不问,殊似于愚鲁,故云‘如愚’也。”(51)(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31页。在皇侃看来,孔子思想是形而上的,一旦表现为语言,就落入具体的“有”。而领会圣人之无,只有通过他的语言。而颜回是能够领会圣人形器以上之“无”的。《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皇侃注道:“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禀以生者也。天道,谓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52)(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110页。文章表现为“言”,是具体的、可见的,而文章之“旨”是深而远的,不可直接得到的。
在有些地方,皇侃又把儒家形而上的抽象归为“道”或“理”。《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皇侃注释说:“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学者加功于此书也。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数五十,是穷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既学得其理则极照精微,故身无过失也。云‘无大过’者,小事易见,大事难明,故学照大理则得一,不复大过,则小者故不失之。”(53)(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167页。《论语·卫灵公》“予一以贯之”,皇侃注释说:“贯,犹穿也。既答曰‘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学而识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识者,我以一善之理贯穿万事,而万事自然可识,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贯之也。”他注释何晏“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一以知也”说:“元,犹始也。会,犹终也。元者善之长,故云‘善有元’也。事各有所终,故曰‘事有会’也。事虽殊涂,而其要会皆同,有所归也。致,极也,人虑乃百,其元极则同起一善也。是善长举元,则众善自举,所以不须多学,而自能识之也。”(54)(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394页。《易》中有“理”,一善之理贯穿万事,这是皇侃对“理”的抽象。关于“道”,皇侃在注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时说:“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于可通,不通于不可通。若人才大,则道随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则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5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09页。《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皇侃注释说:“谋,犹图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谋道也。自古皆有死,不食亦死,死而后已,而道不可遗,故‘谋道不谋食’也。馁,饿也。唯知耕而不学,是无知之人也。虽有谷,必他人所夺,而不得自食,是饿在于其中也。虽不耕而学,则昭识斯明,为四方所重。纵不为乱君之所禄,则门人亦共贡赡,故云‘禄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曰‘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二三子之手’是也。学道必禄在其中,所以忧己无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禄在其中,故不忧贫也。”(5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410-411页。在皇侃看来,道和理一样,是可以贯通万物并使人安身立命于上的东西。皇侃甚至认为,“道”和“理”是同一个东西。他在注释何晏“凡人任情喜怒违理”时说:“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无偏,故违理也。”他又在注释何晏“颜渊任道,怒不过分”时说:“过犹失也。颜子与道同行舍,不自任己,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岂逃形?应可怒者皆得其实,故无失分也。”他注释何晏“怒当其理,不移易也”时说:“照之故当理,当理而怒之,不移易也。”(5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126-127页。凡人任情,所以违理;颜渊任道,所以当理,可见“道”和“理”是一个概念。
其四,辩证思维。皇侃在《论语义疏》中,提出了一些辩证范畴。例如“无知”与“有知”的关系。《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皇侃注释说:“知,谓有私意于其间之知也。圣人体道为度,无有用意之知,故先问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无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无意也。”“虽复鄙夫,而又虚空来问于我,我亦无隐,不以用知处之,故即为其发事终始,竭尽我诚也。即是无必也”。他解释何晏“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尽也。今我诚尽也”说:“知意,谓故用知为知也。圣人忘知,故无知知意也。若用知者,则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尽也。我以不知知,故于言诚无不尽也。”(58)(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214页。皇侃在这里揭示了怀有无知之心,才能广纳知识,最后达到无所不知的辩证关系。再如“同”与“异”的关系。《论语·宪问》载,一个担草筐的人讥笑孔子不肯随世而变,孔子因此感慨,让不了解自己的人不讥笑自己是很难的事。皇侃对此注释说:“贤圣相与,必有以也。夫相与于无相与,乃相与之至。相为于无相为,乃相为之远。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同自然之异也。”(5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集解义疏》,第385页。意思是,圣贤之间的交好,是以相知为前提条件的,这是因为他们“同”。然而这不是最高境界的交好。交好于无交好才是交好之至;互助与无互助才会互助得长远。因为这是通过各修其本而达到的沟通,是同自然之异。“异中之同”高于“同中之同”,其中的道理是很深刻的。
总结规律、揭示本质、抽象概念、辩证思维这些具有浓厚理论思维的义理内容在魏晋以前的经学里是罕见的。直到魏晋时期,王肃始对经学进行义理方面的阐发,而皇侃则把王肃经学这一特点进一步发扬光大。北宋陈祥道说:“孔子之世,师道既明,异端未起,由辨议无间而作,故圣人之答问言理而足矣。”“然而孟子之世,许子之言盈天下,孟子思欲拒诐说,放淫辞,不得已而有辨焉。难疑问答,不直则道不见,故其为言尤详于《论语》”。(60)(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96册第64页。孔子时代用问答形式承载儒理,孟子时代则用直辨形式表达儒理,之所以如此变化,是因为时代发生了“许子(许行)之言盈天下”的变化。同样,魏晋以前,思想界儒家独大,没有什么学派对儒家的地位构成冲击和威胁。而魏晋时期,玄学由兴转盛,东晋南朝,佛教又异军突起,玄学对事物本源的抽象思辨,佛教对生命去从的超世阐释,都极大地吸引着当时的士人群体。在这种形势下,经学如果固守名物制度的训诂,剖章析句,但诵师言,势必在玄佛二家形而上的理论优势面前相形见绌,从而失去吸引士人群体和知识精英的魅力。因此,大力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使经学具有形而上的理论形态,是经学能够和玄佛并立争荣的需要和前提。魏晋时代王肃对义理的阐发是播下思想的种子,皇侃时已经开花结果,使经学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有了显著的提升。他们所坚持的儒学体系,是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吸收玄学和佛教思想的坚实本体;他们所阐述的儒家义理,是隋唐以后产生的理学和心学的思想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