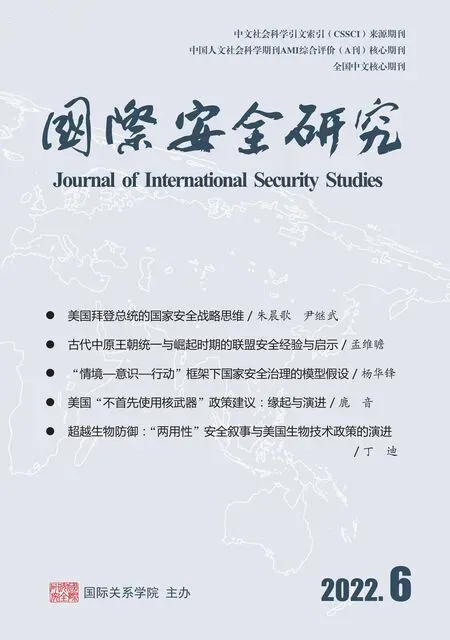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建议:缘起与演进*
鹿 音
【内容提要】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指有核国将核武器的作用严格限定在核威慑上,公开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仅用作核报复(核反击)。从冷战开始至今,美国国内一直在从理论上探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支持者与反对者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角度提出各自的理由。美国政府内部也一直都有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建议,但美国却始终未能正式采纳并宣布这一政策。阻碍美国政府采纳这一政策建议的因素长期存在,包括思维方式的桎梏、政治工具的局限性、核作战战略准备的内在矛盾和盟国持续施加的压力等。鉴于目前的安全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不大可能正式宣布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尽管如此,由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表达出大国避免核战争、保持战略稳定的意愿,同时有利于回应广大无核国的安全诉求,避免误判和危机,增进战略互信,维持全球和平与战略稳定,维护人类社会共同福祉,该政策建议仍会继续影响美国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决策进程。
核武器是战略威慑武器,也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类社会唯一一次使用核武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的轰炸。此次使用显示了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造成了重大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心理冲击。在此后的77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有核国家首先使用过核武器,“核禁忌”逐步形成并影响到决策者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①“核禁忌”是指将不使用核武器作为一种禁止性的规范,从而使得决策者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而无法作出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参见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 页;Nina Tannenwald,The Nuclear Tabo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65-366。但关于核武器能不能使用,怎样使用的政策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以下简称“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核心内容为公开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②Frank Blackaby, Jozef Goldblat and Sverre Lodgaard, eds., No First Use,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1984, p.v.“不首先使用”政策既是有核国公开宣示的核武器使用政策,也是对核武器战略作用最本质的认识,即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威慑,只有在受到核攻击时,核武器才能用于报复性打击。③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August 18, 2020,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07-31-Democratic-Party-Platform-For-Distribution.pdf.目前,在联合国承认的五个法定有核国家中,④法定有核国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即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只有中国公开宣布并长期坚持无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1 页。苏联一度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但其核武器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于1993年放弃了这一政策。⑥孙向丽:《苏联/俄罗斯核战略研究》,载张沱生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 页。没有法定核国家身份的印度也宣称自己奉行“不首先使用”政策,但其政策内容有重大附加条件,即在印度或印度军队受到生、化武器攻击的情况下,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所以,印度宣称的“不首先使用”远非严格意义上的“不首先使用”政策。⑦Kumar Sundaram and M.V.Ramana, “India and the Policy of No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Vol.1, No.1, 2018.
美国是最早拥有核武器且一直保持超级核大国地位的国家,其学界和政界对“不首先使用”政策的讨论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却始终未能成为政府正式宣布的政策。本文将梳理美国国内对这一政策建议的讨论与推进过程,分析其受阻的原因及未来影响,从而为深入理解“不首先使用”政策提供一种思路。
一 美国国内关于“不首先使用”政策的理论探讨
美国国内关于“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讨论,总体上有两种表述、三种含义。一种表述是完全意义上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即公开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认为核武器的主要作用是战略威慑,只有在受到核攻击时,核武器才能作为反击力量进行报复性使用。另一种表述称为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政策(SP),包括三种含义:第一,美国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威慑,只有在美国及其盟国受到核攻击时报复性使用。这一含义基本等同于完全意义的“不首先使用”政策。①Ankit Panda and Vipin Narang, “Sole Purpose Is Not First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Declaratory Policy,” February 22, 2021, https://cis.mit.edu/publications/analysis-opinion/2021/solepurpose-not-no-first-use-nuclear-weapons-and-declaratory.第二,将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威慑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攻击作为政策目标,即美国只会考虑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一含义在奥巴马政府2010年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出现过,也是首次出现在美国官方报告中。②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pril 2010, p.ix,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这一类似含义最新出现在2022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情况简报:2022年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中:“美国核武器的基本作用(fundamental role)是威慑对美国、美国盟友伙伴的核攻击。美国只会考虑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生死攸关的利益。”③“Fact Sheet: 202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and Missile Defense Review,” March 29, 2022,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9/2002965339/-1/-1/1/FACT-SHEET-2022-NUCLEAR-POSTU RE-REVIEW-AND-MISSILE-DEFENSE-REVIEW.PDF.以上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说法为核武器的首先使用留下余地,可谓模糊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第三,美国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威慑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重大战略进攻,包括核进攻。这一含义基本不属于“不首先使用”政策,因为它赋予美国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比较大的余地。④Ankit Panda and Vipin Narang, “Sole Purpose Is Not First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Declaratory Policy,” February 22, 2021, https://cis.mit.edu/publications/analysis-opinion/2021/solepurpose-not-no-first-use-nuclear-weapons-and-declaratory.
本文所讨论的美国“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是指完全意义上的、无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也包括“唯一目的”政策表述中的第一种含义。据此定义,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和争议内容,可将美国国内关于“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争论分为支持派与反对派。
(一)早期观点概述
冷战期间最早的支持派代表人物是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起草的美国核政策建议文件长达79 页,其核心内容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可能服务于理性目的,除了遏阻战事的爆发;在和平时期将美国核武库中武器的数量和当量严格限制在后来被称为“最低核威慑”的水平,并在战争爆发情况下采取一种“不首先使用”的战略。凯南认为,这份文件“就其含义而言,是我在政府内曾写过的所有文件中最重要的之一——如果不是其中最最重要的”。①George F.Kennan, Memoirs 1925-1950, New York: Pantheon, 1983, p.472.同时,凯南也承认,这样一种立场将要求美国与盟国仔细磋商,并且大大提高常规军力水平。②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 83 页。在冷战背景下,凯南的建议毫无悬念地遭到美国国会和军方的强烈反对。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文件(NSC-68)。接替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保罗·尼采(Paul H.Nitze)针对“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写道:“在当前我们常规武器方面相对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这样的声明会被苏联解读为,美国承认了自己有着巨大弱点,同时让我们的盟友认为,这是我们打算抛弃盟友的明确表示。此外,这样的声明是否会引起克里姆林宫的足够重视,从而成为决定其是否对美国发起攻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值得怀疑的。可以预料,克里姆林宫会更加看重关于现实的能力,而不是我们发出了一个打算如何运用这种能力的声明。”③参见1950年4月14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 号文件(NSC-68):“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28, No.3, 1975, p.34。
1961年,莫顿·H.霍尔珀林(Morton H.Halperin)④莫顿·H.霍尔珀林从20 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多次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重要部门任职,被称为美国核战略和军备控制的创始人之一。发表了一篇学界认为非常重要的论文——《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其中再次提出美国应该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主张,认为美国应与苏联签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正式条约。霍尔珀林指出,更有可能被实施的威胁,比更有力量但不太可信的威胁更有威慑力,后者可能被视为虚张声势。威胁使用核武器似乎很有可能降低威慑造成的威胁程度,而威胁使用常规武器进行干预(这也是被认为更可信的干预)则更有可能阻止公开侵略。①Morton H.Halperin, “A Proposal for a Ban on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1961),”https://stars.library.ucf.edu/prism/554/.
在苏联1982年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后,美国国内关于“不首先使用”政策的讨论出现了一个高潮。乔治·凯南和肯尼迪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以及尼克松政府国务院负责原子能事务的特别助理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等四位前美国政府高官,于同年在美国知名学术期刊《外交事务》上联合署名撰文《核武器与大西洋联盟》,该文核心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最初是在美国拥有压倒性核优势时确立的,但这种优势早已不复存在,也无法重新获得。现在已经到了研究新政策的时候,即除非侵略者首先使用核武器,否则美国不会使用核武器。
二是苏联与美国及其联盟一样,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这使人们对核战争的危险更加关注,因为双方核武器系统的大量存在,使得任何一方为首先使用这些武器制定合理的计划,都比以往更加困难。
三是从来没有人成功地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相信任何程度核武器的使用,可以可靠地预期到使用的有限性,即使是最克制的战场使用也会对平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破坏。
四是如果有这样一种政策,认为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都会有效,那么人们肯定会严重怀疑该项政策是否明智。因此,考虑“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可能性、要求、困难和优势似乎是恰逢其时。②McGeorge Bundy, George F.Kennan, Robert S.McNamara and Gerard Smith, “Nuclear Weapons and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Vol.60, No.4, 1982.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发的一系列学界讨论,在美国国内甚至是更大范围内提高了对“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关注度。③相关讨论参见Stanley Kober, David C.Jones, Earl C.Ravenal, Carl N.Anderson and Donald L.Hafner, “The Debate over No First Use,” Foreign Affairs, Vol.60, No.5, 1982; Frank Blackaby,Jozef Goldblat and Sverre Lodgaard, eds., No First Use,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1984。直至今日,仍有评论认为,在所有关于“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分析中,《核武器与大西洋联盟》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①Thomas Graham Jr.,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Why Biden Should Declare a Policy of No First Use,” September 29, 2021, https://www.justsecurity.org/78375/the-role-of-nuclear-weaponswhy-biden-should-declare-a-policy-of-no-first-use/.
为回应《核武器与大西洋联盟》一文的观点,1982年,美国四名学者联名撰写了《核武器与和平的维护:对美国前政要建议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回应》一文,整体上反对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虽然该文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国内学者的观点,却突出反映了美国盟友的反对意见。该文的核心观点包括:
一是核武器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不仅带来诅咒,还带来了它的“孪生兄弟”,即对释放这种力量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基础是对自我毁灭的恐惧。如果没有核武器的战争预防作用,欧洲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结合使得东西方之间的战争至今无法进行,也无法取胜。这种预防战争的战略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即必须表现出进行核战争的意愿,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战争。
二是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肯定会使目前的战争预防战略失去决定性意义。人们不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将因此而处于能够在欧洲发动战争的优势地位,它将不必再担心核武器会对其本国领土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可信地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将再次使战争变得更有可能。
三是拟议中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将破坏欧洲各国特别是联邦德国对欧美联盟作为一个风险共同体的信心,并将危及联盟的战略统一和西欧的安全。核武器的存在,为联盟30年来在防止战争和维护自由方面的成功作出了基本贡献。减少对早期使用核武器的依赖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将有悖于欧洲和整个联盟的安全利益。
四是四位美国政府前高官提出,“不首先使用”政策需要更强大的常规力量,联盟也有能力在预算范围内完成这样的任务。但他们大大低估了西方国家通过增加军备建立常规力量平衡的政治和财政困难,其成本将大大超过目前的国防预算。②Karl Kaiser, Georg Leber, Alois Mertes and Franz-Josef Schulze,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A Response to an American Proposal for Renouncing the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Foreign Affairs, Vol.60, No.5, 198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1984年出版的《不首先使用》论文集收录了以上两篇文章。论文集编者认为它们在探讨“不首先使用”政策方面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①Frank Blackaby, Jozef Goldblat and Sverre Lodgaard, eds., No First Use,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1984, p.v.
(二)逐步形成体系的观点综述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关于“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讨论并没有停止,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一度出现政策辩论的高峰,比如20 世纪90年代中晚期,以及21 世纪奥巴马总统竞选及执政期间,拜登总统竞选及执政期间等。支持派与反对派在政策讨论过程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认知体系。
如果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出发论证“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合理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倾向于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权力和利益,认可物质能力的核心作用。现实主义观点更为看重“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力量基础。支持派认为,与常规力量弱小的国家宣示“不首先使用”政策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不同,常规力量强大的国家更少依赖核武器,其“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反而更值得相信。因此,现在常规力量全球第一的美国应当考虑不用核武器应对常规进攻,而只用核武器威慑核进攻。②Ankit Panda, “‘No First Use’ and Nuclear Weapon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17,2018,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no-first-use-and-nuclear-weapons.同时,支持派认为,真正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将要求核力量保持与“确保摧毁”态势相一致,这一态势避免以打击军事力量为目标。“不首先使用”承诺在作战力量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可使核武库规模更小且威胁更少。③Nina Tannenwald, “It’s Time for a U.S.No-First-Use Nuclear Policy,”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2, No.3, 2019.
第二类倾向于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国内和国际规则制度可以决定国家行为,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可以转换为国内和国际规则。根据这一理论,支持派认为,即使“不首先使用”的承诺是不可执行的,也并非没有意义。为了更有意义,必须将“不首先使用”的承诺纳入国内机制,即军事作战能力的结构。④Ronald Mitchell, “Regime Design Matters: Intentional Oil Pollution and Treaty Compli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3, 1994.“不首先使用”政策声明将有利于美国防止其他国家或恐怖组织使用核武器和防止进一步的核扩散,这样的声明不会降低美国威慑力量的可信度,而是可能增加非核反应的可信度。⑤Scott D.Sagan, “The Case for No First Use,” Survival, Vol.51, No.3, 2009.在国际层面,自由主义者强调防止核战争的规则和制度的价值。“不首先使用”无论如何已成为事实上的规范,因此应公开、多国一起宣布。①Nina Tannenwald, “It’s Time for a U.S.No-First-Use Nuclear Policy,”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2, No.3, 2019.由于几乎没有可以想象到的情况需要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美国几乎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②Gregory Kulacki, “China Is Willing to Negotiate on Nuclear Arms, But Not on Trump’s Terms,” March 30, 2020,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20/03/china-willing-negotiate-nucleararms-not-trumps-terms/164204/。类似的讨论还可以参见Nina Tannenwald, “It’s Time for a U.S.No-First-Use Nuclear Policy,”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2, No.3, 2019。同时,“不首先使用”政策可降低意外核升级的风险,减少对手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误判,降低核战争风险。③Steve Fetter and Jon Wolfsthal, “No First Use and Credible Deterrence,”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Vol.1, No.1, 2018.还有观点认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不首先使用”最重要的好处在于增强危机稳定性。一个可信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将有助于减少对手对美国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恐惧,从而减少在严重危机中意外、无意或故意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④Michael S.Gerson, “No First Use: The Next Step for US Nuclear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2, 2010.
第三类倾向于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对国家行为及利益的建构作用。支持派重视“不首先使用”政策对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作用,认可“核禁忌”作为禁止性规范对决策的影响,认为宣示性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是强化核克制规范和七十多年不使用核武器传统的重要途径。⑤Nina Tannenwald, The Nuclear Tabo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p.365-366.而“首先使用的选择会鼓励其他国家效仿,比如印度”。⑥Scott D.Sagan, “The Case for No First Use,” Survival, Vol.51, No.3, 2009.“不首先使用”政策也是一种外交互动工具,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是负责任的核大国,并将持有相似观念的国家团结起来,尤其是可以吸引并团结美国的盟国。在“不首先使用”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撤回慑止对盟友的核威胁或攻击的“核保护伞”。⑦John P.Holdren, “The Overwhelming Case for No First Us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76, No.1, 2020.在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同时,通过增加国际外交支持,可提升美国的道德和外交领导地位,发出摆脱冷战思维的信号。⑧Brad Roberts, “Debating Nuclear No-First-Use, Again,” Survival, Vol.61, No.3, 2019.
而反对派的意见多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实力与国家利益的现实价值,不太认可偏重理想主义的理论框架。反对派的观点包括:第一,力量与威胁论。力量决定派始终认为,“不首先使用”政策是“空头支票”,“我们的对手永远更相信自己的预警系统,而不是我们的宣言”。①Seth Moulton,“We Must Eliminate Nuclear Weapons, but a ‘No First Use’ Policy Is Not the Answer,” November 29, 2021, https://www.msn.com/en-us/news/politics/we-must-eliminate-nuclearweapons-but-a-no-first-use-policy-is-not-the-answer/ar-AARgN0u.虽然就全球而言,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常规军事优势,但是在欧洲或亚太,由于该地区常规力量平衡已经向有利于中俄的方向转变,俄罗斯或中国可能占据局部性常规军事优势;②Brad Roberts, “Debating Nuclear No-First-Use, Again,” Survival, Vol.61, No.3, 2019.而且,“不首先使用”政策将降低对常规军事攻击的威慑力,毕竟核攻击是唯一无法用非核手段击败的对抗性威胁。③Amy F.Woolf, “U.S.Nuclear Weapons Policy: Considering ‘No First Use’,” March 29, 2022,https://sgp.fas.org/crs/nuke/IN10553.pdf.“不首先使用”付出的代价太高,以至于对手可能在没有核报复的压力下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一切非核攻击,包括生化攻击。④Morton H.Halperin, Bruno Tertrais, Keith B.Payne, K.Subrahmanyam and Scott D.Sagan,“Forum: The Case for No First Use: An Exchange,” Survival, Vol.51, No.5, 2009.
第二,降低威慑信誉论。“不首先使用”政策会降低威慑的可信度,如果对手不担心美国的核报复,可能会大胆采取常规军事行动,损害美国或盟友的利益。⑤Michael Rühle, “The Problem with Sole Purpose and No First Use,” June 23, 2021,https://nipp.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IS-493.pdf.在美国的威慑因多种原因已经减弱的时候,再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将严重破坏美国的威慑力。采纳这一政策不会为不扩散和裁军努力增加有意义的领导作用,反而会对美国国会内两党在核政策上所剩不多的合作产生消极影响。⑥Brad Roberts, “Debating Nuclear No-First-Use, Again,” Survival, Vol.61, No.3, 2019.“不首先使用”政策将吓倒美国的盟友,鼓励美国的对手并破坏声称要推进的不扩散目标。⑦“Biden Ready to Change US Nuclear Weapons Policy,” November 3, 2021, https://www.rt.com/usa/539286-us-nuclear-weapons-doctrine-revision/.美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不会改变中国和俄罗斯的核政策,因为中俄绝对不会相信美国的“不首先使用”承诺。⑧Franklin C.Miller, “Outsid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and Posture,”Prepared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March 6, 2019,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CHRG-116hhrg36235/pdf/CHRG-116hhrg36235.pdf.
第三,弱化盟友关系论。美国继续将数十个国家置于其核保护伞之下,包括数个国家也非常坚决地要求美国作好为它们使用核武器的准备,这一政策如果改变,盟国会对美国的威慑力失去信心; 如果盟友对美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失去信心,将削弱联盟关系,①Franklin C.Miller, “Sole Purpose: A Policy Without a Purpose,” Real Clear Defense,September 19, 2020, https://www.realcleardefense.com/articles/2020/09/19/sole_purpose_a_policy_without_a_purpose_577999.html.同时刺激它们自行制造核武器,导致核扩散;②U.S.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Apr/01/2002108036/-1/-1/1/U.S.-NUCLEAR-WEAPONS-CLAIMS-AND-RESPONSES.PDF.一些盟友可能会将“不首先使用”政策更广泛地视为美国放弃对盟友历史性承诺的标志。③George Perkovich and Pranay Vaddi, “Proportionate Deterrence: A Model Nuclear Posture Review,”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Perkovich_Vaddi_NPR_full1.pdf.
二 美国“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发端与推进
在美国国内对“不首先使用”政策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将其升级为国家政策的尝试也在同步进行中。学术理论与政策实践本身是相互促进、相互验证的关系。本章重点考察“不首先使用”作为政策建议在美国政府的起源与演进过程,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加深对“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屡屡受阻的理解。“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建议曾在核时代的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无论是在主张降低核武器作用、倾向于支持“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民主党执政期间,还是在重视核武器作用、反对“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共和党执政期间,都曾出现关于这一政策建议的讨论,以及推动其上升为国家政策的具体行动。由于党派利益和理念的不同,民主党总统采纳这一建议的主观意志相对更强些,而美国国内关于“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建议最早也出现在民主党总统执政时期。
(一)冷战时期“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出现
如前文所述,20 世纪40年代末,美国“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建议最早出现在凯南起草的政策建议文件中。当时,苏联刚成功试爆了原子弹,美国各界反应强烈,激辩是否要靠制造威力更大的氢弹或“超级”炸弹来回应苏联的原子弹。凯南认为,战争毕竟被设想为实现某种目的的一个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可能达到塑造敌手的政治目的,而是同敌手一起毁灭。所以凯南不支持用氢弹应对苏联,并提醒美国政府,不要犯首先使用或计划首先使用这些武器的错误,误以为它们可以最终服务于某种积极的国家目的。④“Kennan Memorandum: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January 20, 1950,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 Volume 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39.
然而,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苏联会进一步发展威力更大的核武器,美国应该加快发展自己的大威力核武器,并做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战争设计。1952年春,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文件指出:“如果威慑失败,与苏联的战略核战争发生,美国必须获胜,并能够迫使苏联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寻求尽早终止敌对行动。”①参见“Defense Department Guidance 1984-88,” 转引自 Frank Blackaby, Jozef Goldblat and Sverre Lodgaard, eds., No First Use,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1984, p.126.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颁布了第一份明确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 号文件(NSC162/2)概述了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即“在发生敌对行动时,美国认为核武器与其他弹药一样可用”。②“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NSC162/2 ),” October 30, 1953,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ume 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593.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宣称,美国将以大规模的核报复来回击苏联阵营对其任何规模的侵犯。同时,鉴于在冷战之初的欧洲,苏联不仅拥有了核武器,而且其常规军力远远超过北约,1957年,北约军事委员会第14 号文件(MC- 14/2)的核战略附件明确规定:“除非北约立即使用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否则北约无力阻止(苏联)迅速占领欧洲,因此,我们必须准备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不论苏联是否使用核武器,北约都将以立即使用核能力为依托。”③David S.Yost, “NATO and the Anticipatory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Affair, Vol.83, No.1,2007.因此,凯南关于“不首先使用”政策及其他核政策的设想最终只能停留在建议文件中。
1962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在冷战两大军事集团高度对峙的背景下,此危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于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有核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机事件。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决策层几乎一致认为苏联很可能要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为此,美国应当对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以避免自己陷入被动,这一政策选项一直放在肯尼迪的办公桌上。后来的历史证明,美国即使处于巨大力量优势与强大安全风险压力下,依然不敢对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而面对危机升级,苏联更不敢冒险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④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4-115、119、130 页。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所揭示的事实是,尽管美国当时在核武器方面对苏联拥有17∶1 的优势,也不能对比较弱势的苏联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双方都不得不防范局势失控的风险。①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69 页。古巴导弹危机是核危机管控的经典案例,其管控的目标是防止危机升级为核战争。在危机期间,美苏领导人都面临着是否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如何防止核武器被对手首先使用的巨大压力。肯尼迪总统在详细了解了如何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对手的作战计划后认为,站在世界两端的两个人,要是能下定决心毁灭整个文明,那简直是疯了。他总结道:“核武器‘只有威慑功能’。”②迈克尔·多布斯:《午夜将至——核战边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陶泽慧、赵进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279 页。经过古巴导弹危机,“不首先使用”的理念在现实场景中得到检验。
古巴导弹危机后,为管控美苏核危机及军备竞赛,同时占领国际核不扩散道义制高点,美苏两国开始进行以危机管控为重点的实质性核军控谈判,主要目的还是避免大国间再次出现有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况。同时,美苏在保持自己有核国的地位优势、防止出现更多有核国家的问题上产生了共同利益,而防止更多有核国出现也是国际核不扩散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美苏两国共同提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并推动各自集团国家签署该条约。
广大无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不结盟运动国家也通过签约承诺自己不发展核武器,同时希望得到有核国家不对无核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但是,美苏两国既想通过这一签约过程彰显全球核不扩散进程“领头羊”的形象,又不想给予无核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最后,作为无核换安全的条件之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美国、苏联和英国的倡议,通过了第255(1968)号决议,承认安理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向核武器侵略行为的受害国或这种侵略威胁的对象提供援助”。③Resolution 255(1968),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1433rd meeting, June 19, 1968,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90759?ln=en.显然,这样的承诺与无核国家希望得到的安全保证,还有很大差距。
1982年,苏联在裁军问题特别联大上正式宣布:“苏联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即刻生效。”④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rmament Affairs, The 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Yearbook:Volume 07: 1982, December 1983, https://www.un.org/disarmament/publications/yearbook/volume-7-1982/.苏联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在当时的安全环境下,是巨大的政策进步,这使同样作为超级核大国的美国面临的道义压力明显增加。为应对苏联的政策调整,同时也为了回应广大无核国的反核诉求,在苏联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后,美国国内也开始密集讨论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一直坚持美国应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并为自己的主张不被政府采纳而苦闷的乔治·凯南,这一时期也开始再次积极重申其主张:“大部分军备建设应严格控制在美国本土防御,满足北约和盟国日本最低防务需求的范围之内。……工作的重点是在国家军备中普遍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以及战略导弹。与此同时,美国要秉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只保持最基本的核威慑力量……”①乔治·凯南著,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凯南日记》,曹明玉译,董旻杰译校,中信集团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 页。正是在凯南的积极推动下,才有了1982年四位前高官在《外交事务》上的署名文章。
冷战时期,在两个超级核大国及其领导的两大集团长期敌对的背景下,美国“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发端于对核战争和苏联的双重恐惧。美国既无法摆脱对毁灭性核战争的恐惧,又时刻担心在军力上会被苏联超过。随着美苏陷入核军备竞赛,核力量的“超杀”能力及核危机的真实出现,使双方领导层和广大民众对核战争产生更深切的恐惧,“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建议具备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二)冷战后“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曲折推进
冷战结束后,随着主要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也随之消失;同时,美国常规军力不断增强,逐渐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全球最强。但冷战后几届美国政府对于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兴趣却大不相同。概括而言,“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有所推进,而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则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严重倒退。
1993年,克林顿政府首任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下令评估美国核政策时曾声明,“任何首先使用都不能构成新的不扩散政策的基础”。②Steve Fetter and Jon Wolfsthal, “No First Use and Credible Deterrence,”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Vol.1, No.1, 2018.然而,阿斯平1994年退休后才正式出台的美国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在重申进一步核裁军并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中作用的同时,完全不提及“不首先使用”政策。③“1994 Nuclear Posture Review,” December 31, 2001 , http://nautilus.org/projects/nuclearstrategy/1994-nuclear-posture-review/.1995年,为说服无核武器国家同意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再次承诺其“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①这也是重申美国有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参见安理会第984(1995)号决议, 1995年4月11日,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76507?ln=en。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宣布核力量的唯一作用是“威慑核攻击,或威慑以核攻击胁迫美国或其盟友”,美国“不再威胁要用核武器应对常规、化学或生物攻击”。这一观点与1994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阐述的观点恰恰相反,②John P.Holdren, “The Overwhelming Case for No First Us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76, No.1, 2020.但却符合“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1999年秋,卸任不久的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J.Perry)撰文提议,美国应弱化核武器在北约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其核心思想也是“不首先使用”政策的近似表述“唯一目的”政策。③William J.Perry, “Desert Storm and Deterrence,”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4, 1991.
21 世纪初,小布什政府任内的核政策与核态势评估基本处于保守状态。2001年12月,美国宣布退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反导条约》,对全球核态势及安全稳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作为某种平衡,2002年2月,美国国务院又重申了其关于有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的长期官方立场。④Harold A Feiveson and Ernst Jan Hogendoorn, “No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10, No.2, 2003.但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仍是小布什政府的政策重点。这一政策也充分体现在美国200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该报告提出,核武器在美国及其盟国友邦的防御能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可提供可信的军事选择,以应对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在内的广泛威胁。⑤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Excerpts), January 8, 2002, http://lasg.org/documents/NPR/NPR_2002.htm.
奥巴马总统上任前,四位美国前政要在《华尔街日报》上共同撰文,倡导“无核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为奥巴马上台后推动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舆论铺垫。⑥这四位美国政要是指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P.Shultz)、前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J.Perry)、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及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Sam Nunn)。2007年,四人共同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署名文章为《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2008年,他们再次发表共同署名文章《迈向无核世界》,由此掀起“无核世界”倡议运动。2009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接受并倡导“无核世界”,⑦“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Prague as Delivered,” April 5,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prague-delivered.而“不首先使用”政策是迈向“无核世界”的第一步,也符合奥巴马政府减少核武器作用及实现核不扩散政策的目标。“无核世界”能得到官方认可,学界受到极大鼓励,支持“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学者与前政要们继续推动奥巴马政府采纳该政策。①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讨论包括:Scott D.Sagan, “The Case for No First Use,” Survival, Vol.51,No.3, 2009; Morton H.Halperin, Bruno Tertrais, Keith B.Payne, K.Subrahmanyam and Scott D.Sagan, “Forum: The Case for No First Use: An Exchange,” Survival, Vol.51, No.5, 2009; Joshua Pollack, “Reducing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30, 2009,https://thebulletin.org/2009/10/reducing-the-role-of-nuclear-weapons/; William J.Perry, Brent Scowcroft and Charles D.Ferguso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62: U.S.Nuclear Weapons Poli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wps/cfr/0017112/f_0017112_14636.pdf。然而,由于对该政策的支持与反对意见仍然尖锐对立,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出台的2010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不得不推迟发布,且最终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政策改变,继续体现出有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内容,只是将条件限制为“极端情况”。这是奥巴马总统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的第一次尝试,但没有成功。即便如此,2010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也几乎是最大程度限制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和场景,并将“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威慑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攻击”作为美国核政策的未来目标。②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pril 2010,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这也是美国领导人在核政策选择上最接近于“不首先使用”政策的一次。
2016年夏,奥巴马再次展开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协调与努力,打算公开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大量支持美国政府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学术与政论文章。③关于奥巴马任内对“不首先使用”政策的争论,可参见员欣依:《关于奥巴马政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争论》,《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第130页。美国学界支持“不首先使用”政策的代表性文章参见 Bruce Blair, “How Obama Could Revolutionize Nuclear Weapons Strategy Before He Goes,” Politico, June 22, 2016,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6/barack-obama-nuclear-weapons-213981/; Ramesh Thakur, “Why Obama Should Declare a No-First-Use Policy for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9, 2016, http://thebulletin.org/why-obama-shoulddeclare-no-first-use-policy-nuclear-weapons9789; Kingston Reif and Daryl G.Kimball, “Rethink Oldthink on No First Use,” August 29, 2016, https://thebulletin.org/2016/08/rethink-oldthink- on-no-first-use/。然而,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盟国反复游说,反对美国改变核武器的使用原则。同时,面对当时与俄罗斯的矛盾和朝鲜半岛不断升级的核紧张局势,美国政府担心“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可能被视为软弱,于是软化了态度,最终这一政策宣示未能在奥巴马任内获得成功。④Nina Tannenwald, “The Vanishing Nuclear Taboo? How Disarmament Fell Apart,”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6, 2018.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对“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推动,有其个人及党派的理想主义与政治意愿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其政府对威胁判断的调整与美国整体军事实力的增强。奥巴马第一任期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与其他核力量,特别是俄罗斯、中国的关系是确保战略稳定。①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pril 2010,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NPR/2010_Nuclear_Posture_Review_Report.pdf.同时,美国常规军力在冷战后获得长足发展,加之美国政府对核武器本质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削减冗余核武器数量就成为大势所趋。
奥巴马政府任内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努力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出现了严重倒退。一是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整体上提高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明确表示将针对常规进攻使用核武器;二是退出《中导条约》《伊核协议》和《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军控条约或协议,威胁全球战略稳定;三是研发量产战术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即便如此,在特朗普任内,2017年以后美国国内再次出现推动政府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呼声,并陆续有议员向美国国会提出议案,建议制定“不首先使用”政策,但未获成功。②Joe Gould, “Warren, Smith Introduce Bill to Bar US from Using Nuclear Weapons First,”January 30, 2019,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19/01/30/warren-smith-introduce-bill-tobar-us-from-using-nuclear-weapons-first/.2019年3月,美国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卡内基国际核政策大会上发言指出,美国要制定“不首先使用”政策,前提是将威慑作为拥有核武器的目的,而不是去考虑如何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政策就是对核武器能够遏止对手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的认可。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Keynote with Representative Adam Smith,”March 12, 2019, https://s3.amazonaws.com/ceipfiles/pdf/NPC19-RepAdamSmith.pdf.
(三)当前“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新动向
早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拜登就一直支持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在拜登竞选总统时期,就已开始展现对于“不首先使用”政策选项的积极态度。无论是民主党竞选纲领还是拜登的个人言论,均表现出对这一政策的持续支持。2019年6月4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拜登公开确认对“不首先使用”政策和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承诺。④Thomas Graham Jr.,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Why Biden Should Declare a Policy of No First Use,” September 29, 2021, https://www.justsecurity.org/78375/the-role-of-nuclear-weaponswhy-biden-should-declare-a-policy-of-no-first-use/.2020年3月,拜登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我认为,美国核武库的唯一目的应该是威慑,并在必要时报复核攻击。作为总统,我将与美国军方和盟友协商,努力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①Joseph R.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S.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这些表述在2020年的《民主党竞选党纲》中全部得以重申。②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August 18, 2020,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07-31-Democratic-Party-Platform-For-Distribution.pdf.这一不断重复和强调的政策内容,正是“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核心。美国学界提出,随着拜登政府准备进行核态势评估,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③Thomas Graham Jr.,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Why Biden Should Declare a Policy of No First Use,” September 29, 2021, https://www.justsecurity.org/78375/the-role-of-nuclear-weaponswhy-biden-should-declare-a-policy-of-no-first-use/.
2021年7月,拜登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启动新的核态势评估,其结果将包含在《国防战略报告》中,于2022年初完成。④美国国防部称,由于俄乌局势的影响,该报告的发布将推迟。参见Jim Garamone, “Austin Says Current Operations Give Hints of New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OD News, February 18,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940956/austin-says-current-operationsgive-hints-of-new-national-defense-strategy/。这也是冷战后美国政府首次不单独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而将其打包于《国防战略报告》中。围绕在新的核态势评估结果中是否应该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美国学界和政界再次掀起讨论热潮,来自支持者的联名呼吁在这一轮讨论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在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工作正式启动前,倡导“不首先使用”政策的美国学者和前政要们就已经行动起来。在2021年5月底举行的“‘不首先使用’全球运动”大会上,他们起草了致拜登总统和普京总统的公开信,呼吁两位领导人宣布共同承诺美俄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将此作为完成联合国彻底销毁核武器目标的关键一步。这封公开信得到了1 200 多名政治、军事和宗教领袖以及立法者、学者、科学家和其他民间社会代表的支持。公开信在美俄峰会召开前的2021年6月16日发表,旨在希望两国总统能在会面时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达成一致并宣布共同承诺。⑤“Presidents Biden and Putin Urged to Consider Nuclear No-First-Use Policy at Upcoming Geneva Summit,” June 10, 2021, https://nofirstuse.global/2021/06/10/presidents-biden-and-putinurged-to-consider-nuclear-no-first-use-policy-at-upcoming-geneva-summit/.
在核态势评估工作开始当月,美国国会核武器和军备控制工作组的四位联合主席共同起草了一封给拜登总统的信,并得到 18 位立法者的支持。信中强烈呼吁美国应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并引用拜登总统自己的话说:“鉴于我们的非核能力和当今威胁的性质,很难想象存在合理情景,让美国有必要或有理由首先使用核武器。”①“US Congress Members: Nuclear Posture Review Should Affirm a Policy of No-First-Use,”July 26, 2021, https://nofirstuse.global/2021/07/26/us-congress-members-nuclear-posture-reviewshould-affirm-a-policy-of-no-first-use/.
考虑到日本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对美国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持反对态度的主要盟国之一,2021年8月9日,在日本长崎遭受核袭击的第76 周年纪念日,包括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在内的5 个美国学术组织,包括佩里、霍尔珀林在内的21 名美国核武器政策专家,共同致信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和日本主要政党领导人,呼吁日本不要反对美国政府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并声明这样的政策不会刺激日本获得核武器。②“United States Experts Call on Japan Not to Oppose a US No-First-Use Policy,” August 10,2021, https://nofirstuse.global/2021/08/10/united-states-experts-call-on-japan-not-to-oppose-a-us-no-firstuse-policy/#respond.
2021年12月16日,包括21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88 名美国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在内的近700 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公开信的方式,呼吁拜登总统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修改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力并减少部署的核武器数量等。③“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Letter to President Biden on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December 15, 2021, https://ucs-documents.s3.amazonaws.com/global-security/letter-POTUS-NPR-dated-12-15-21.pdf.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外界对于拜登政府可能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保持了一定期待。但2022年2月危机爆发后,安全环境与威胁判断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相关政策的调整。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全文尚未出台,但根据2022年3月底公布的“情况简报”,美国仍然强调致力于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只会考虑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并重新建立其在军备控制方面的领导地位。④“Fact Sheet: 202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and Missile Defense Review,” March 29, 2022,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9/2002965339/-1/-1/1/FACT-SHEET-2022-NUCLEAR-POSTU RE-REVIEW-AND-MISSILE-DEFENSE-REVIEW.PDF.其政策措辞与奥巴马政府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的表述几乎一致,但去掉了将“唯一目的”作为政策目标的说法。这体现出拜登总统本人及其党派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也兼顾了当前的安全环境。“不首先使用”政策并没有出现在这份“情况简报”中,拜登政府推动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努力无果而终。然而,考虑到乌克兰危机的持久影响,这一政策表达应该是未来至少五年内美国政府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不大可能宣布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
三 美国“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主要阻力
从冷战开始至今,围绕“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辩论及其形成的舆论氛围,体现出该政策建议的生命力,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正式采纳这一政策建议,这也反映出美国决策层中支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力量依然强大。“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主要阻力至少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思维层面:寻求绝对优势与意识形态偏见的桎梏
寻求绝对优势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偏见,使“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难以对决策层产生决定性影响。自美国开始实施全球扩张以来,其追求并保持军事与安全领域绝对优势的思维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这也直接影响了美国对“不首先使用”政策的选择。“美国人千差万别,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可替代却是团结美国国民的国家共识。”①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5.pdf.这一点基本上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执政的共性,其区别只在于实现的途径与方法。无论核力量比对手强大多少,美国始终认为主要对手的核力量是严重威胁。冷战时期这一威胁来自苏联,即使是在美苏核力量差距悬殊时亦是如此。在美国的核武器处于绝对优势的20 世纪50年代初期,例如1951年,美国拥有428枚核武器,而苏联只有25 枚,但美国却认为苏联会对美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并将其作为首要威胁进行研究。②Robert S.Norris and Hans M.Kristensen, “Global Nuclear Inventories, 1945-2000,”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2010, p.81,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epub/10.2968/066004008.1955年,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研究出台的“应对突然袭击的威胁”报告认为,美国战略力量的脆弱性会诱使苏联发动突然袭击。③“Report by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the Threat of Surprise Attack,”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57, Vol.19,Washingti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2.这种恐惧也和二战后美国国防开支大幅下降,常规军事力量发展不足直接相关。常规武器不占优势的美国,无论如何不可能轻易放弃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其追求绝对优势的思想更加膨胀。冷战后,除俄罗斯外,美国将其主要核威胁一度指向朝鲜、伊朗等国家;而在当前,美国认为威胁来自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中国与美国的核武库差距明显且中国一直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美俄之间的核军控条约仍然有效,且多年来有核国实际上遵守了“核禁忌”,但美国寻求绝对优势的思维惯性难以改变。这种对绝对军事优势的执着追求表现为夸大军事安全威胁,追求军力全面占优。而“不首先使用”政策主张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使核武库戒备状态、核武器数量及现代化投入等各方面向下调整,这是美国长期保持绝对优势的思维方式难以接受的。
此外,由于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其决策层很难接受“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尽管冷战时期苏联宣布了“不首先使用”政策,但美国对此却一直持怀疑态度。美国研究核问题的资深学者认为,冷战时期苏联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其目的是试图在“不首先使用”的承诺上进行欺诈,因为苏联当时在欧洲部署了大量的常规军事力量,其“不首先使用”政策宣示只是宣传工具,苏联企图以此离间美国与欧洲盟国。“苏联欺诈论”加上美苏多年对于“不在欧洲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争论,形成了不愉快的历史记忆,最终导致美国安全文化对“不首先使用”这一术语根深蒂固的排斥。①顾克冈、杰弗里·刘易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美核对话的困境与出路》,《外交评论》2012年第5 期。
(二)政治层面:政策沦为美化形象政治工具的局限性
“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一定程度上沦为超级核大国美化自身形象的政治工具。冷战期间,美苏政治博弈的一个主要舞台就是核军备控制。无论是从力量上还是在形象上,限制对方、美化自己都是两个超级核大国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本质是在核政策上限制核武器的使用,有利于核大国占领道义制高点,成为全球核不扩散的“领头羊”,更易达成核大国推动的核不扩散政治目标。在此目标上,美苏具有共同利益,需要团结一致。两个超级核大国在推动各自集团国家放弃发展自己核武器的同时,需要给这些国家可信的安全保障。有核国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这种安全保障的内容之一,这也是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代表性成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的背景。为了避免有核国发生核大战殃及广大无核国,有核国之间互相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是实质性降低全球核威胁的可靠保障。所以,“不首先使用”政策比较突出地满足了广大无核国的安全需求,当然,宣布这一政策的国家同时展示了更好的政治形象。这样的道义制高点,美国当然不会轻易让与苏联。这也是为什么当苏联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后,美国国内很快形成了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高潮。政策建议产生的宣传效果虽然积极,而一旦要真正限制自己,给予无核国安全承诺时,美国又表现得犹豫不决。其对无核国有限的安全保障附加了若干条件,至于向有核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对美国而言利益权衡就更为复杂。达到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政治目的、展示了好的政治形象后,美国对调整自己的“不首先使用”政策自然不再积极。
冷战后,在国际安全环境缓和的大背景下,主要对手的消失使美国各界对核战争的担忧明显降低。同时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放弃了苏联曾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对“不首先使用”政策的信誉产生了负面影响。冷战后美国推动采纳“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建议,当然也有政治形象上的考虑,既要继续保持其全球核不扩散“领头羊”的地位,又想在大国核军控谈判中造势。在乌克兰危机增加外界对于大国核战争担忧的背景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无忧虑地表示:“核冲突的前景曾经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又成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①Jessica Chasmar, “Nuclear War ‘within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UN Secretary General Warns,” Fox News, March 14, 2022, https://www.foxnews.com/world/nuclear-war-realm-possibilityun-secretary-general.面对这样的安全态势,拜登政府的“情况简报:2022年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但也没有激化安全矛盾,而是回归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近似表述。相对而言,这一立场有利于拜登政府的国际形象,为其下一步在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大国博弈中增加了政治筹码。
(三)军事层面:“核作战”战略计划与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
军事战略准备与政策选择的内在矛盾比较明确地体现在“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推进过程中。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武器,但这并不妨碍美国需要打赢一场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先发制人进行核打击不仅成为美国早期关于核战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美国军事与安全战略的宏观概念中,而且体现在具备实际操作意义的“核作战”(war-fighting)战略中。无论各届政府如何进行核政策选择,美国军方都始终需要做好“战场制胜”的军事准备。②“核作战”或“战场制胜”(war-fighting)战略,属于西方核战略领域的一个流派,是指将核武器用于并力图打赢各级别核战争的战略理论与能力,包括战场作战与控制升级的能力。也有中国学者建议将war-fighting 译为“打核战”或“核战”。参见孙向丽:《核时代的战略选择——中国核战略问题研究》,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9年版,第71 页;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70 页。
美国的“核作战”战略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它以打赢核战争为目标,并且不放弃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打法。这一战略的实施以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关于核战争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为代表,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选择也保留在SIOP 中。①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 页。该计划整合了战略轰炸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海基潜射弹道导弹(SLBM)的“三位一体”核能力,为美国总统提供了一系列的目标选择,并明确了发射程序和已经设定的核武器打击目标。②“Operation Plans,”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oplan.htm.“统一作战行动计划”从1961年持续至2003年,每年更新一次,直到2003年2月并入“作战计划8044”(OPLAN 8044)。OPLAN 8044 计划仍是整个“作战计划”中高度保密的独立部分,不像其他作战计划由战区制定,而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制定。自2012年7月起,美国的核战争计划调整为“作战计划8010-12”(OPLAN 8010-12),即关于战略威慑和武力运用的计划。③“Operation Plans,”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oplan.htm.美国在战场使用核武器并获取胜利的“核作战”计划从冷战延续至今。
尽管政策选择与战争计划有所区别,且前者在总体上决定后者,但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准备也会影响政策选择的过程。“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建议与先发制人打赢核战的军事准备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这也是“不首先使用”难以获得美国官方特别是军方认可的实际障碍。
(四)同盟层面:“延伸威慑”政策与盟友压力的持久障碍
“延伸威慑”政策与来自盟友的压力是美国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面临的持久障碍。维护“延伸威慑”的可靠与可信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基石(联盟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把为西欧和东亚盟国提供安全保护、阻止对手采取军事行动的威慑,称为延伸威慑。④姚云竹:《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10 页。延伸威慑可以用核武器实施,也可以用常规武器实施,具体的实施方式存在一定的政策模糊性。以核武器实施延伸威慑就是俗称的“核保护伞”政策。长期以来,美国承诺用自己的核武器保护盟国的安全,保留为盟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选项,而盟国不必自己发展核武器,这一延伸核威慑战略一直是美国对于盟国的安全承诺,也是美国控制盟友的有效手段。多年的承诺传统形成了来自盟友要求“核保护伞”的压力,美国也始终想在盟友中维持“核垄断”,这使其很难放弃对盟国的“核保护伞”政策。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可能极大地限制美国的“核保护伞”政策,至少意味着美国对盟友的延伸核威慑只表现在盟友遭受核打击后美国对敌国进行核报复,而不能先发制人对敌国进行核打击,或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敌国形成压力,迫使敌国放弃对美国盟国的常规打击。
长期以来,即使是在美国采取“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情况下,盟友对关键时刻美国是否会信守延伸核威慑承诺一直有所怀疑,反复让其重申承诺;如果美国再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那么其延伸核威慑的承诺在盟国眼中就更不可信,因为盟友会担心,自己在遭到敌国核打击后,美国恐怕也不太敢为了盟友而对敌国进行核报复。这将侵蚀联盟的基础。相反,如果美国不放弃在极端情况下威胁对敌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比如敌国以常规军事力量严重侵犯美国盟国领土安全等极端情况,那么这种“首先使用”的威胁可能吓阻敌国的常规军事入侵,这是盟国希望美国不要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更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敌国占据常规军事优势,或者盟友认为自己受到敌国越来越严峻的常规军事威胁时,盟友对美国可能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担心就会加剧。所以,美国政府要想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延伸威慑”与来自盟友的压力会持久存在。
四 美国“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未来可能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断修订其核政策,也曾多次表示要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正处于调整与振荡的关键阶段,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仍未减弱,在某些地区、某些个案中还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核升级就是典型案例。①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于2月27日将军队的核威慑力量转入特殊戒备状态(on special alert),参见“Press Review: Why Putin Put Nuke Forces on High Alert and Liberation of Donbass Continues,” February 28, 2022, https://tass.com/pressreview/1412885。然而,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宣布提高核武器戒备状态后,在行动上依然保持了克制;美国也采取了降级反应,避免激化局势,如拜登政府第一时间回应,不会相应提高美国核武器戒备状态;②2022年2月28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没有看到有理由改变我们的戒备级别,而且我们看到升级的言辞有明显的重大危险。”参见“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2/28/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jen-psaki-february-28-2022/。美国宣布推迟其“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等。①“US Cancels ICBM Test amid Ukraine Conflict,” Air Force Technology, April 4, 2022,https://www.airforce-technology.com/news/us-cancels-icbm-test/.这些都再次证明了大国对核武器使用的谨慎态度。可见,“不首先使用”的理念以及不断推动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公开呼吁还是迂回表达,都已在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国内反对“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势力更为强大,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正确”,也使得政府层面推动采纳这一政策建议的努力一再失败。未来,无论美国政府是否采纳“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其依然会发挥有限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一)“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将继续为美国的政治形象加分
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退约风波后,美俄首脑终于在2021年6月召开了日内瓦峰会,会后发布了一份关于战略稳定的《美俄总统联合声明》。该声明重申了“里根—戈尔巴乔夫声明”,②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A nuclear war cannot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早在1985年,美苏日内瓦裁军谈判时该声明就得到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认可。并表示要继续推动军备控制,包括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的安排,以及下一步两国共同开展综合性的双边战略稳定对话。③The White House, “U.S.-Russia Presidential Joint Statement on Strategic Stability,” June 16,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6/u-s-russia-presidentialjoint-statement-on-strategic-stability/.为落实两国首脑峰会的成果,美俄日内瓦战略稳定对话已经进行了三轮,但未能形成具体成果,而且因乌克兰危机的出现,对话气氛恶化,后续乏力。要想打破美俄军控对话与后续谈判的僵局,拜登政府必须拿出更积极的核政策,即使难以出台完全意义上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但对这一政策的支持与推动本身,也有利于美国政府继续打造全球军控与不扩散“领头羊”的形象。在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屡次出现俄罗斯要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舆论风向,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而美国整体上保持了克制姿态,没有公开威胁要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加强了危机管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界对于大国打破“核禁忌”,人类陷入核毁灭的焦虑与恐惧。这一实践既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对“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实际坚持,又成功抬高了美国的政治形象。
(二)“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有利于平衡美国军费支出
美国核力量过剩已是老问题。虽然冷战后美俄进一步削减核武器,但两个超级核大国的核弹头总量仍达万枚以上,占全球核武器总量的比例超过90%。④2021年,美国的核弹头总量为5 550 枚,俄罗斯的总量为6 255 枚。参见SIPRI Year Book 2021, https://www.sipri.org/yearbook/2021。对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均为全球之首的美国来说,维持如此巨大的核武库既消耗资源,又有损其全球核不扩散领导者的形象,继续削减核武库是必然趋势。有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军种之间关于战略武器的竞争有时并非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是为争夺更大的国防预算份额,这种努力最后退化为一场争夺美元的竞争。①Darius Watson, “Rethinking the U.S.Nuclear Triad,”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1, No.4,2017.根据相关分析,在所有围绕核力量的支出中,部署和维护核武库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制造核武器本身。制造核武器的成本只占7%左右,而部署、指控体系及核武器的全套维护与安全处理成本占据了剩余的近93%。②Stephen Schwartz, ed., Atomic Audit: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Press, 1998, pp.12-33.美国核力量基础设施普遍老旧,核武库需要全面更新换代。对拜登政府和后续的美国政府而言,是保留现有核武库规模还是削减后再现代化,已经是紧迫的选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每两年进行一次维护及升级核武库10年支出的成本评估。根据其2021年的最新报告,如果保持现有核武库规模,从2021年到2030年,这一支出成本将达到6 340 亿美元,比2019年的评估高出28%,呈明显上升趋势。③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Projected Costs of U.S.Nuclear Forces, 2019 to 2028,”January 2019,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19-01/54914-NuclearForces.pdf.“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无论是否得到采纳,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政府限制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实质性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从而为削减更多的冗余核武器铺平道路。
(三)“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仍会影响美国与盟国的关系
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面临的持久障碍是来自盟友的压力。2021年年初,拜登政府就“不首先使用”政策征求盟国意见时,不但遭到了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反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北约国家也表现出压倒性负面反应。④Demetri Sevastopulo, “Allies Lobby Biden to Prevent Shift to ‘No First Use’ of Nuclear Arms,” October 30, 2021, https://www.cnas.org/press/in-the-news/allies-lobby-biden-to-prevent-shiftto-no-first-use-of-nuclear-arms.无论奥巴马总统还是拜登总统,在表达支持“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同时,都特别强调要与盟国协商。拜登政府更以联盟优先为政策选择,强调“将重振和更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认为联盟是美国“强大的力量源泉和独特的美国优势”。⑤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在当前背景下,美国大国战略竞争的总体战略导向及国际安全环境的突变因素等,会使盟友对美国“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持更加强烈的反对态度。同时,“核保护伞”作为威慑手段必须进行公开政策承诺,否则难以达成威慑效果。如果美国需要加强与联盟的安全承诺,公开表达继续坚持“核保护伞”政策就成为必要选择。在美国整体实力相对下降、更加倚重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背景下,盟友对美国联盟战略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也在上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必将重新评估俄罗斯对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进一步凝聚盟国的力量。在考虑“不首先使用”政策时,如何回应盟友对延伸核威慑的诉求,既公开规避“核保护伞”的政策承诺,又使其盟友相信延伸核威慑的承诺通过常规武器一样可以兑现,这不仅是拜登政府的难题,也将是未来持续影响美国与盟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结 语
回顾核大国博弈的历史,由于首先使用核武器风险巨大,几乎没有大国会这么做,即使是在最接近于人类核毁灭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两国也都没有优先选择向对方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内提出并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但每个阶段的政策阻力都大于政策的推动力。
从冷战至今,美国政府一直在放大安全威胁,保持“核作战”战略,从而无法在核政策上真正有所突破。在其实力相对下降并更加重视盟友和伙伴的背景下,美国也会更加注重回应盟国对“延伸威慑”的诉求,而乌克兰危机可能增强美国盟友对“核保护伞”的需要。拜登政府推进“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努力可谓“生不逢时”。然而,美国国内坚持推动“不首先使用”政策建议的力量并没有退缩,依然在寻找机遇推动其走向政策层面。同时,广大无核武器国家的愿望也值得重视,2021年1月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便是无核国家团结起来采取的实际行动。国际反核运动对核武器国家并非没有压力,美国作为超级核大国理应率先垂范,在政策上及时调整改进。
乌克兰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将成为拜登政府及未来美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危机中,俄罗斯提升核武器戒备级别并跟进了战略武器领域的实际动作,这再次引发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核大国有可能打破“核禁忌”,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大国矛盾的积累导致国际安全环境恶化,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危机突变。当危机再度激化时,俄罗斯还会不会保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实际状态?同时,大国关系不稳定,容易出现彼此误解误判,美国长期让相当一部分核武器处于“一触即发”的高戒备状态,本就不利于危机稳定性。当误解升级时,美国有把握管控好自己的核武器,使其不在危机中被首先使用吗?可见,在乌克兰危机及后危机时代,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仍在增加。
同时应看到,即便乌克兰危机会对国际安全形势造成长远的、不确定的影响,不能打核战争的国际共识也依然存在。2022年新年伊始,在中国的成功推动下,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以五核国的身份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理念,可见核大国对于避免核战对抗有高度共识。①《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人民网,2022年1月4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2/0104/c1011-32323573.html。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避免大国对抗上更应负主要责任。“不首先使用”政策表达出大国避免核战争、保持战略稳定的意愿,同时有利于回应广大无核国安全诉求,避免误判和危机,增进战略互信,维持全球和平与战略稳定,维护人类社会共同福祉。此外,“不首先使用”政策还有助于推动减少冗余核武器数量。因此,即使是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下,该政策也仍然值得核大国,特别是美国认真考虑。中国已经坚持无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政策近六十年,也将继续为美国及所有核国家做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