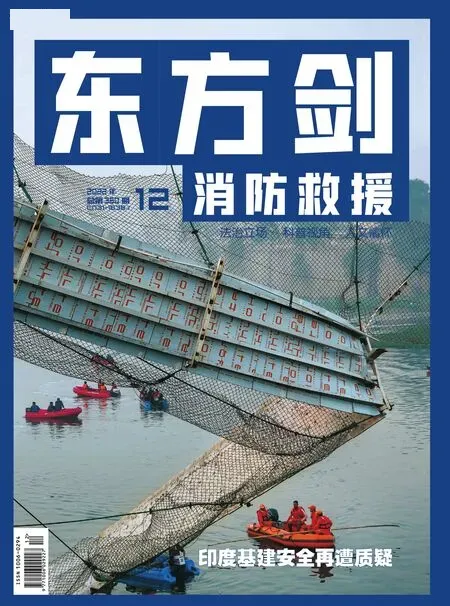但使城郭如逝在
2015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住国际饭店的两位来沪与会的新加坡友人,离沪前约我叙旧。我说就在国际饭店旁边黄河路凤阳路口的港式餐厅仔码头见面。那家餐厅的生意一直很好。他俩的兴致也很好,买好了大光明电影院的夜场票,说是难得来,在老电影院里感受一下老上海。那个时候的大光明电影院已修旧如旧,恢复了1933年的原样。菜点还没上齐,外面警笛声起。距此不远的新世界商厦失火,引起商场内的顾客及路人一片恐慌。所幸消防队几乎近在咫尺,很快控制了火势,也无人员伤亡。事后得悉,火因是户外广告灯箱电源瓦数高而自燃。新世界商厦位于南京路商圈中心,着火时浓烟滚滚,显见明火,当然成了一大新闻。
我在《丝弦吴侬梦里影》一文中提到的新昌路救火会,建于1909年,正式启用的时候,是第七维多利亚蒸汽救火车队进驻,由20 名义勇队员和30 名苦力组成救火队。救火车也是中国火险公司的财产。抗战胜利后,上海市警察局消防处设其为新闸消防区队。1949年后,市公安局消防处设其为北京西路消防队。1983年起编入武警序列,隶属市消防总队第五大队,现为黄浦区北京消防救援站。今年6月始,疫情之下的上海日渐如常的同时,“二级以下”旧里的居民动迁工作加快了进程。周围的石库门老宅里巷现已人去楼空。原本安扎于鳞次栉比的商住楼栋和喧杂市肆之间的“火焰蓝”,乃是这座城市发展变迁史上已然不变的见证吧。
1998年的元旦之夜,我是同多位好朋友在花衣街116 号度过的。当时因为书多,老房子实在搁不下,全搬去新居又远,一下子要我付之论斤称重,自然不舍;工作室租在了距离老房子不远的花衣街,遂采取一边选用工具书、文献、收藏的版本置于工作室留存,一边处理掉了大部分看过的闲书杂书。工作室所在之地,是一间旧式大宅院的二层前楼,梁枋和椽子的木雕及寿字花纹清晰可辨,整个建筑的风格也是中西杂糅,正屋回廊尤其漂亮。这座四进五开间的大宅院里当时住着十几户人家。平时我要么白天过去写一会稿子,要么就在那里晤友、谈事、慢酌。2000年黄浦与南市两区合并之前,我离开了花衣街。
直到十年前,偶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时评,作者呼吁不要将老城厢内的一处一百五十多年的老宅拆除,我才知道自己也曾客居两年的这座深宅大院的主人,是晚清沙船巨商沈义生。这座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的院落,之所以一改坐北朝南的传统,坐西朝东,就为把当年黄浦江尽收眼底,沙船当然面向大海。已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沈宅老建筑,最终得以“保护”的仅仅是其中一个庭心。
前年,一条谓之“外滩枫径”的时尚夜市,人气爆棚。集市就设在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建筑群之间。我不明白的是,它的入口处就是枫泾路,人头簇拥,也不是什么红枫秋叶落满径的氛围,仍旧名之为“外滩枫径”。其实这一片历史上船舶如蚁、舳舻连接、帆樯栉比、洋货山积、万商云集。明末清初的上海,已是全国有名的县城及通商要埠,自海上而来的闽、浙、粤、鲁等地的商货,千帆满载,由吴淞江驶入,停泊在黄浦江上,一派繁华。最初枫泾路叫福建街,可想而知,也是源于水路抵沪的福建商船之多。因为上海另有一条福建路,故在1940年代初改福建街为枫泾路。与枫泾路垂直相交的阳朔路,当初经营洋货的行号皆集聚于此,曾名洋行街。这一上海滩最闹猛的市肆,早就无迹可寻了。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从老西门到老西门》的长文,我自己用“沪语讲述”的形式同时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音频,阅读量持续上升。“二级以下旧里”的顺利动迁,对几十年来生活在逼仄空间里翘首盼望改善居住条件的绝大部分老城厢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福音。当年迁徙沪渎的新移民,在这片人烟稠密的城郭之中,留下太多已然稍纵即逝的屐痕。而今,与其说老城厢是重振健全,不如说是亟待一次真正的爬梳剔抉。任何个人的生存价值,无疑在于延续一份真实的鲜活;任何一座城市的价值,更在其仍有否鲜活于其中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退休后仍潜心于老城厢历史风貌保护研究的建筑师徐大玮告诉过我,西仓桥街的一处绞圈房院落,起码也有百年历史了。我不是建筑学家,我只在意闹市深处的这么多年来俨然蒙着神秘面纱的民居之中曾经或正在发生的人事。西仓桥街,得名于储粮仓,因仓址在城西俗称西仓,当年有跨中心河上的西仓桥。那天,我过仪凤弄、走梦花街、沿静修路,也就十几分钟,便见到了西仓桥街几处年代久远的典型的石库门老宅。我忽然想到了距此不远的大兴街。大兴街最早是上海南火车站旁边逐渐形成的一片专门卖假货次货的贸易市场,因为乘火车的人赶辰光要紧,买了不靠谱的东西也来不及找去交涉。上海人有句切口叫“开大兴”,意思是指一个人说大话、不靠谱、弄虚作假,出典即从大兴街而来。我不难想到,清廷废除海禁后,小东门内有了江海关署,嘉庆年间的上海,已然“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到了道光前期,城东南隅已是“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了”。西仓桥街这片里巷一带,也是与“十里洋场”交相辉映的“红灯区”。我更是在想,一座城市的正面良好功能是什么?首先是人脉乃至社会网络的维系包括个体的自塑。
鉴于保护老宅主人的个人隐私,我不著一字。作别西仓桥街当天,我只更新了自己的“微言”。照录于兹:
算好了足够个辰光,提早半个钟头到了老西门,虽然晓得搿一片区域已开始了动拆迁进程,但我相信里巷深深必定还有小辰光个早饭等我去寻味。果然,勒勒某个转角有一爿馄饨店,叫了一碗小馄饨,8 块洋钿14 只,只只饱满,肉馅汁鲜,我打包票讲,乔家栅、大富贵肯定侪做勿到了。笃悠悠吃好早饭,呒没两步路,就是今朝约我来采访个搿幢独门独户个老建筑了。有关部门个同志特意请来了房子个主人,聊了两个钟头,信息量足够我落笔成文。
观音帽,漂亮个仪门,保存完好个门当,每一块花纹各异个木雕图案浪向,能清晰辨认出刻画的故事;清澈个“太平”古井,好像勒搭我讲,侬早一个号头来,可能吃得着浸了半日个西瓜……脚下是清代个石板,让我一记头就想起,从四通八达个此地,转几个弯,就是洋行街,千帆竞发个黄浦江,万商云集个上海城,同我所在个搿个院落,也就两百年。
我勒“阿平面馆”吃了一碗葱油拌面加辣肉丁,又再一趟像煞乡下人刚到上海一样,坐到哈根达斯,背对着永安公司地标,拍勒搿张照片,想表达啥呢?两百年辰光邪气快,有几个人会得关心搿爿哈根达斯个前身是海仑个咖吧。
(《振华微言~虎步龙骧》)
“星罗江火”专栏,行文至此,九篇了。一年来,每一篇完稿的时候,但使城郭如逝在,这七个字,总会激活我心底沉沉的忆念。新一年里,字里行间,我愿意尽最大努力,与热爱这座城市的你,一起“行走”,分享梧桐背后的“丝竹”,那毕竟是久久萦绕不去的“琤琮”。
(本文图片来自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