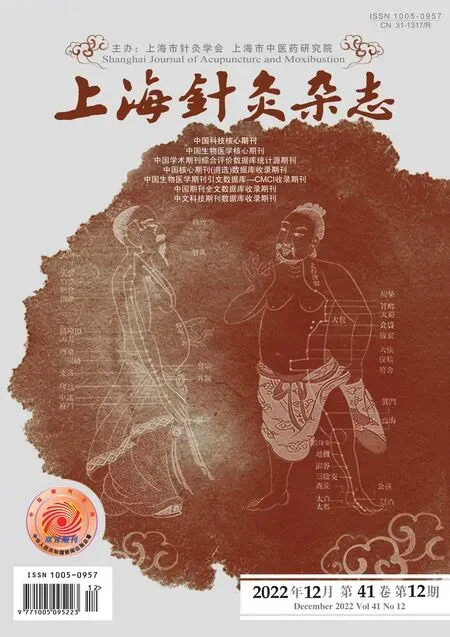针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的应用
李仪丙,彭茂菡,吴帮启,王旭慧
(1.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300193;2.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1617;3.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以发热、干咳和乏力为主要症状[1]。截至2021年6月9日,中国累计确诊病例115 22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6 285例,死亡病例4 636例[2]。多数患者在住院治疗后可通过自身免疫功能修复炎性损伤、消灭病毒而痊愈,少数患者病情进展快,无法控制,最终死亡[3]。多个研究[4-6]表明抗病毒药物对于新冠肺炎患者预后改善不明显。本次疫情中医药疗效显著,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达91.5%[4-7]。新冠肺炎属于中医学“疫病”范畴。针刺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以往抗疫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将疫情爆发以来针刺在新冠疫情中的临床应用报道如下,为抗击疫情提供参考。
1 新冠肺炎临床治疗期的针刺干预
针刺治疗疫病最早见于《素问·刺法论》,其记载“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明清时期,《针灸大成》《针灸逢源》中总结了历代医家治疗疫病的针刺经验。民国时期,针刺曾用于治疗霍乱且疗效显著[8]。
1.1 缩短病程,减少住院天数
针刺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时,即时效应和累计效应明显,研究[9]显示接受针刺治疗的患者病程和住院天数明显短于未接受针刺治疗的患者,提示针灸能缩短新冠肺炎患者病程,减少住院天数。
尹鑫等[10]针药联合治疗17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针刺太溪等穴,根据患者症状虚实采取提插补泻法,补法留针2 min,泻法不留针,每日针刺1次,治疗期间仅3例患者由重型转为危重型,其余患者均按诊疗标准出院,平均住院时间15 d,所有患者症状改善有效率为82.4%,CT感染灶较前吸收患者占比41.2%。段云珊等[11]中西医结合治疗60例新冠肺炎患者,在西医治疗与中药汤剂治疗基础上,根据患者症状不同选取后溪、太溪、太渊、内关、神门、天突、阳陵泉、三阴交、中脘、天枢、气海等穴位针刺治疗,治疗期间死亡3例,其余57例患者均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12]出院标准出院。龚亚斌等[13]采用针药结合治疗33例新冠肺炎患者,针刺列缺、合谷、内关、曲池、足三里和太冲,留针30 min,隔日治疗1次,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平均住院天数 9.24 d,胸闷、乏力、心慌等症状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
1.2 控制感染,改善肺部症状
针灸作为炎性疾病的治疗手段之一,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炎性疾病的临床指南中[14]。针灸治疗新冠肺炎,不仅能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情况,促进胸腔积液吸收,还能极大地改善发热、呼吸急促和胸闷等肺系临床症状。
侍鑫杰等[15]使用管针联合中药汤剂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33例普通型、9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针刺合谷、内关、曲池、列缺、足三里和太冲穴,行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30 min,每日针刺一侧肢体穴位,次日取对侧穴位,经治疗后所有患者的胸闷、胸痛、乏力和心慌等症状均得到明显缓解,达到治愈标准出院,且治疗过程中无任何不良反应,亦无职业暴露。
龚亚斌等[16]针药结合治疗2例新冠肺炎卧床患者,针刺足三里、三阴交、太冲、合谷、列缺、内关和曲池穴,留针30 min,每日针刺1次,12 d为1个疗程,2个针刺疗程间隔3 d,1例以发热和双下肢无力起病的普通型患者在针刺治疗3 d后发热症状消失,针刺7 d后,患者可以站立行走,3次核酸检测阴性,胸部 CT提示肺炎较前吸收。另外1例以胸闷、呼吸急促,血氧饱和度低为主要症状的重型患者,针刺2周后,上述症状明显缓解,血氧恢复正常,胸部 CT显示肺部炎症及胸腔积液较前明显好转。
陶兰亭等[17]报道1例武汉市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接受奥司他韦等药物治疗胸闷、呼吸急促等症状仍未缓解后,予针刺联合中药、莫西沙星治疗,针刺太溪、曲泽、大陵等穴,施以提插捻转强刺激手法,至患者有酸胀、麻木、疼痛,四肢或全身放射感,不留针,患者在改变治疗方案第 3天后,自觉劳累后呼吸短促症状较前改善,在治疗第10天后,患者自觉完全康复,胸闷等不适症状消失,查胸部 CT示病情较前明显吸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试验阴性。
刘力红等[18]针药并用治疗 1例新冠肺炎患者,取穴右侧内关透外关、太渊透阳溪匀速进针,不予特殊行针和补泻手法,留针45 min,每日1次。在初次针灸治疗后患者胸闷、胁痛症状较前好转,针刺7个疗程后,胸闷、胁痛症状基本消除,次日出院。以上均体现了针刺在治疗时即刻效应明显。
1.3 控制脓毒症休克,改善意识状态
脓毒症休克是重症新冠肺炎的常见并发症,现代医学主要通过糖皮质激素来缓解症状,但激素不良反应明显,甚至会降低新冠病毒的清除速度[19]。一项纳入811例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针灸联合常规治疗能显著降低脓毒症患者炎性反应,降低死亡率[20]。
YEH B等[21]报道1例73岁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在3次核酸检测阴性后第3天突然出现心动过缓、脓毒性休克合并缺血性卒中,在入院后第 5天开始对患者进行针刺治疗,针刺承筋、下巨虚和梁丘穴,留针30 min,每周针刺3次,在第1次针灸治疗后,患者出现不自主睁眼,并逐渐恢复意识,针刺 2周后,患者停用呼吸机及抗生素,胸部CT显示双肺磨玻璃影和实变逐渐消退。
1.4 改善合并症,迅速缓解痛苦
由于针灸防治疾病的有效性和广泛性,在面对新冠肺炎患者诸多合并症时,针灸能迅速改善相关症状,缓解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史锁芳等[22]报道在江夏方舱医院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时,2例2次以上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在采用太极六气针法结合三因司天方治疗后核酸 2次转阴,有患者出现便血、咳嗽、头晕、胃痛、颈椎痛、关节疼痛等症状时使用太极六气针法在初次针刺后症状迅速缓解。
2 新冠肺炎医学观察期的针刺干预
《素问·刺法论》中记载“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及“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认为自身正气充足,阴阳平衡,可免除疫气侵扰。现代研究[23-24]也证明针刺能调节血清免疫水平。针刺干预新冠肺炎密切接触的人员,有助于其提升正气,调节免疫力,避免疫气侵袭。
钟国就等[25]采用薄氏腹针结合胸腺肽对100余例新冠肺炎密切接触人员预防性治疗,针刺中脘、气海、下脘、关元等穴,每日1次,治疗7 d后,所有患者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可能与针刺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相关[26]。
3 新冠肺炎相关心理障碍的针刺干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郁”之概念,认为情志致郁,“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流而不行”。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快,传染力强,预后不详,故部分患者因郁而病或因病而郁[27]。一项Mete分析表明针刺能有效减低患者抑郁程度,改善相关症状[28]。
ZHAO F等[29]使用针刺百会、内关穴联合中医情志疗法治疗 30例新冠疫情下老年酒精依赖性抑郁症患者,发现针刺组能明显降低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缓解疼痛,提升生活质量,且与对照组(仅使用中医情志疗法)相比均具有显著性差异。NORONHA L K等[30]在巴西使用针刺治疗340例新冠肺炎所致的心理疾患,其中 66%的患者并发疼痛障碍,经治疗后患者的症状均得到改善。李卫林等[31]使用十三鬼穴、灵龟八法、调脏腑三联针刺法治疗新冠肺炎疫情期心理应激障碍患者8例,隔日治疗1次,针刺7次为1个疗程,治疗2个疗程后判定疗效,治疗后有效率为 87.5%,所有患者均停用安眠药。针刺具有多重效应,不仅能舒缓情绪,改善心理障碍,还能减轻其合并的疼痛障碍。
4 针刺治疗新冠肺炎的可能作用机制
一项基于生物信息学的研究[32]揭示了针灸治疗新冠肺炎的多靶点机制,针刺后产生的两种活性化合物和180个蛋白质靶点,提示针刺治疗新冠肺炎可能与抑制炎症应激、提高免疫力和调节神经系统功能有关,包括激活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钙信号通路、癌症通路、病毒致癌、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会激发机体产生天然免疫与适应性免疫,适度的天然免疫与炎症反应会产生抗病毒效果并激发适应性免疫抵御病毒感染[33],但过度的天然免疫与炎症反应会导致免疫过激、炎症因子风暴及微血栓形成,引起急性呼吸衰竭、脓毒症休克及多器官衰竭[34]。已有研究[24,35]证明针灸可以调节免疫系统,促进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以及NK细胞活性。针刺时穴位中的大量肥大细胞会聚集脱颗粒,激活神经-内分泌-免疫反应[36-37]。罗伟等[38]研究发现针刺肺俞穴能明显降低病毒性肺炎大鼠的炎症因子水平,从而降低免疫病理损害。针刺亦能激活中枢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调节炎性反应,与体液抗炎通路相比,神经抗炎通路调节炎性因子更快速、直接、且特异性更强[39],这可能是针刺即时效应明显的因素之一。
5 针刺治疗的安全防护措施
针刺作为一种侵入性的有创操作,研究[40]发现针刺可能将皮肤表面菌群带入体内,但细菌大多数为非致病菌,数量也远低最小感染量。而针刺诱发感染主要与疾病类型、器具消毒灭菌处置、操作误刺、锐器处置不当、操作人员手卫生、医疗废物处置和针灸环境等相关因素有关[41-42]。尽管针刺的感染率极低[43],但考虑新冠肺炎传染性较强,在针刺操作过程中应避免医源性交叉感染。
医务人员在接触每个患者前后应严格执行手卫生或手消毒[44],针刺部位皮肤需采用碘伏或乙醇棉球消毒,每次2遍,以患者腧穴为中心,由内向外消毒,消毒面积大于5 cm2。医者其他部位被患者体液分泌物、排泄物或者血液污染时,必须对污染部位进行消毒处理[45]。进针时避免手直接接触针身,针刺过程中保证一针一穴一棉球。患者治疗完毕,使用棉球将针孔压紧,避免出血引起患者间交叉感染。使用后的废弃针灸针置入利器盒中,三分之二满,封盒,避免锐器伤[44]。病房内定时进行空气消毒[46]。
目前临床医师在针刺时多使用努劲单手进针法(以右利手为例),即用右手拇、食指持针,露出针尖0.5~1寸,中指指尖紧靠穴位,针刺时拇、食指快速向下努劲,使针尖迅速穿透皮肤。此法操作简便,但在针刺过程中手接触针体的部位也进入了患者体内。在新冠病毒肆虐之际,此针刺法可能会增加交叉感染风险。因此针刺在应用于新冠肺炎时,针刺方法亦应符合无菌原则。经查阅文献,推荐以下几种无菌针刺法供临床使用。第一,飞针单手进针法。用右手拇、食、中三指捏紧针体,根据穴位针刺深度露出针身适当长度,针尖对准穴位,悬腕,使针尖距穴位皮肤1~2 cm处,运用腕臂力量突然发力,将针尖迅速刺透穴位皮肤,并使针体刺入筋肉之中,随即松手,整个过程各指尖不与皮肤接触[47],操作过程中需注意穴位针刺深度要小于手指捏紧针体位置与针尖的距离,避免手指接触针体的位置进入皮肤内部。第二,弹指速刺进针法。右手拇、食二指夹持针身,针尖朝向穴位并保持与皮肤2~3分的距离,沉肩、垂肘、悬腕,保持针体垂直于皮肤,屈曲持针的拇指指间关节及食指的远端指间关节,之后迅速发力弹指使拇指指间关节和食指的远端指间关节伸直,使针迅速弹出垂直刺入皮下,此过程中始终保持针身夹持在二指之间[48],操作过程中也需注意穴位针刺深度不可大于手指夹持针体位置与针尖的距离。以上两种针刺方法均符合严格的无菌原则,但对各手指间的协调配合和关节的力量控制要求较高,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须多加练习才可运用自如。除了传统的进针方法外,亦可结合现代技术,通过运用针灸进针器达到无菌进针的目的。目前国内的针灸进针器主要包括管针进针器、毫针夹持进针器、机械弹刺进针器和高速自动进针器[49]。管针进针器的操作为用长短适宜的毫针置入管内,针尾略露出 0.4~0.5 cm,将针管以进针角度放置于穴位上,左手压紧针管,右手食指指腹对准在针管上端的针柄,快速打击或弹压,将针尖刺入穴位皮下,然后退出针管,将针刺入穴内。毫针夹持进针器需右手持夹持进针器,夹持部夹取适宜长度的毫针,使针尖外露约1 cm,对准消毒好的穴位,手腕用力带动夹持进针器将针尖快速刺入皮下,随后退除夹针器,将针刺入穴位。机械弹刺进针器操作时将毫针放入进针器内,左手压紧进针器保持直立,右手按压进针器轴柄,并迅速放开,毫针便会受到进针器内部弹簧的弹力快速刺入皮下,随后提起进针器,将针刺入穴位。高速自动进针器的进针原理与机械弹刺进针器相同,但其针盒内可容纳多只毫针,能连续针刺多个穴位,仅需针孔对准穴位即可,操作更为便捷。使用进针器进针能保证医者始终不接触针身,符合无菌操作的要求,能有效地避免交叉感染。
6 讨论与展望
新冠肺炎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在2020年2月中国针灸学会发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第一版)》[50],指出艾灸在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轻型、普通型及恢复期患者的使用方法,旨在提升患者免疫力,改善症状,调节情绪,但该指南中并未提出针刺在新冠肺炎中的具体应用方案。2020年3月中国针灸学会迅速发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第二版)》[51],该指南较上一版更为全面,增加了不同针刺疗法在新冠病毒肺炎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和恢复期3个阶段的应用,并将在针刺处方、针刺手法、留针时间标准化。两版新冠肺炎针灸干预意见的发表给一线针灸医师在治疗新冠肺炎时提供相关参考及循证证据。
中医药在本次疫情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多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52-53]均将中药作为常规治疗方案。研究表明藿香正气方、连花清瘟胶囊在治疗新冠肺炎时亦能调节免疫应答,消除相关炎性因子[54-55]。相比中药治疗,针刺在治疗新冠肺炎过程中仍有独特的优势,针刺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并发症如关节痛、颈椎病、头晕等起效速度较中药更快,这可能与针刺能激活迷走神经中枢效应、外周胆碱能效应和交感-肾上腺效应有关[56],故针刺即时效应明显,并持续累计效应。一项关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程和住院天数的回顾性研究显示[9]接受针刺治疗的患者病程明显比未接受针刺治疗的患者短,住院天数也短于未接受针刺治疗的患者,但该项研究纳入样本量少,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由于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迫切需要有效的新冠肺炎治疗策略。针灸可能是新冠肺炎的另一种治疗选择。临床上可以鼓励患者主动进行穴位按摩、穴位敷贴、耳穴等进行新冠肺炎的防治,医生可以通过微信或视频等借助互联网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具体操作的指导。此外,可对针刺防治新冠肺炎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总结针灸的选穴规律及特点。
临床试验应该为客观评估新冠肺炎治疗和预防的潜在疗法提供高质量的数据。针刺因其独特优势治疗新冠肺炎各个阶段疗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现有文献较少、样本量不足和多为个案报道)。针刺治疗新冠肺炎的基础研究匮乏。目前关于针刺治疗新冠肺炎的研究多为中西并用、针药结合的综合疗法,导致针刺治疗新冠肺炎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不同医家针刺治疗新冠肺炎过程中针刺手法、留针时间不甚相同。今后仍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为针刺治疗新冠肺炎提供高级别的循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