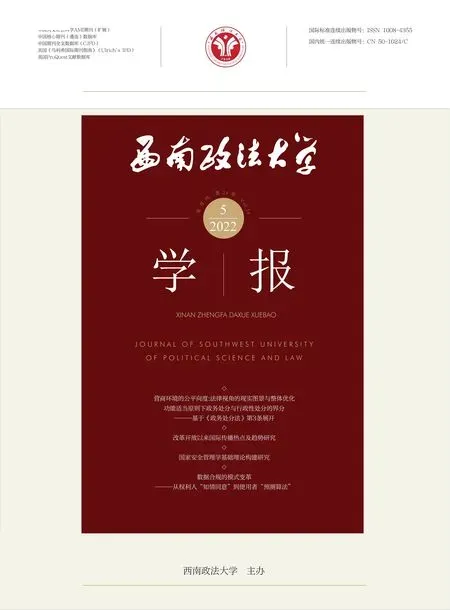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生态安全及其法治完善
陈 亮,杨 攀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引言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①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求是》2019年第3期,第5页。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成为衡量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与指标。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囊括了生态安全在内的“11种安全”,标志着生态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高度;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修订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对生态安全进行了间接阐释,奠定了生态安全制度安排的基石与制度运作的基点,生态安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性不断彰显。在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从行政式治理向法治化治理转型的趋势下,①李文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页。完善生态安全法治保障体系,是维护生态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践行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中国生态安全法治研究积累了诸多有益成果。如对生态安全融入法律规范的价值性阐释,②马波:《生态安全法治保障论》,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5期,第72-79页。以及对生态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建设的系统性研究,③张震、张义云:《生态文明入宪视域下生态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建构论》,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2期,第1-12页。还有对生态安全立法及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的探讨。④王树义:《生态安全及其立法问题探讨》,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123-129页。但总体而言,生态安全法治的建构依然任重道远。既有研究对生态安全法治的探讨或是从还原论出发的规范性愿景构想,或是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从生态危机的现实推论出生态安全的肯定性意蕴,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对生态安全与外部领域交互作用的忽视,在制度安排上可能存在管中窥豹的隐忧。从制度内部来看,制度建构离不开对客观事实的准确把握,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生态安全的内涵及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待更全面地梳理;从制度外部来看,传统安全威胁犹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凸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区分又相互交织的国际社会形势,⑤[英]拉里·埃利奥特、丹·阿特金森:《不安全的时代》,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34-37页。有必要从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整体视角对生态安全的法治方案进行检视和补充。
一、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生态安全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
1.生态问题的安全化动因
作为安全内涵拓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安全化是理解非传统安全的一把钥匙。⑥王江丽:《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36页。“人和生物圈中其他生命的同一性,决定了人与其他生物一样,必然受到生态平衡运动的限制。”⑦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这就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漫长历史演进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但人类对安全概念的不确定认知导致传统社会未能把生态安全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具象化地进行表达。⑧王贵松:《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2期,第22页。因此,尽管在历史上曾有诸多因资源争夺而引起的战争、因资源枯竭而消失的文明,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时期中,生态问题并未被作为一种安全问题来对待。生态问题从非安全问题步入安全领域,成为一种非传统安全的过程,即生态问题的安全化,其安全化动因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的重叠交织。工业革命后,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和程度飞速发展,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生态问题不仅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损害,更日益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⑨2019年《柳叶刀》(Lancet)发布的基于2017年数据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环境颗粒物污染是导致死亡和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数)的四大危险因素之一;早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基于2012年数据的报告也曾指出,全球23%的死亡和22%的DALs由环境因素导致,中国可归因于环境的疾病负担居全球最严重行列。伴随着生态环境支撑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功能被普遍揭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发生了内在同构,“生态安全”从传统生态学的生态系统安全问题,演化为涉及健康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行动也越来越多地被赋予维护人类生命安全的内在意蕴。二是安全领域与安全观念的积极拓张。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使国家的生存环境和生存需要发生改变,军事行动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原有比重地位降低,而来自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不稳定因素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突起。随着社会发展呈现从物质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向,公众安全需要空前提高。鉴于自然资源、环境和人口要素与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紧密关联,生态系统退化和生态服务丧失可能直接引起贫困化、“生态难民”等社会动荡现象,现代生态问题已经具备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必要性。
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正常状态被破坏,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生态功能维持的需求问题,这种需求衍生了以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态状态为核心的特殊的生态利益诉求,①张璐:《环境法与生态化民法典的协同》,载《现代法学》2021年3月第2期,第172-173页。并促使政治议程与科技议程发生改变。政治议程属于政府和政府间层面,由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组成,最终决定如何对待生态问题:科技议程在政治中心之外,由科研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目的在于提出生态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政治议程与科技议程形成生态问题安全化的两股主要推动力,经由二者及其之间的交叉互动,生态问题实现了从非公共问题到公共问题、从公共问题到政治问题再到安全问题的发展。②王江丽:《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4期,第38页。
2.生态安全的内涵
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和全球安全的威胁最早是被作为“环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在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早期一般认为,环境问题如森林退化、荒漠化、环境污染等,其核心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干扰因素导致的资源数量、质量下降从而造成资源短缺,资源环境的功能稳定或变化特征是相应评价研究的主要关注内容。③Swart R, Security Ris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96, p.187-192.20世纪末,随着对完整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视,国际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资源稀缺性上升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相关问题,推动环境安全向生态安全的内涵拓展。④Pirages D,Cousins K. From Resource Scarcity to Ecological Security:Exploring New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p.134-138.相较于传统的环境安全,新兴研究明显赋予了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人类生计相联系的含义。⑤应凌霄、孔令桥等:《生态安全及其评价方法研究进展》,载《生态学报》2022年第5期,第1681页。研究者指出,生态安全的基础是关注生态系统维持稳定和恢复适应的能力,⑥McDonald M,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Towards Ecologic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Theory, 2018, p.153-180.生态系统自身及其对人类资源的供给、与社会经济福祉相关的一系列调节和文化功能的状况及变化特征,共同组成了对生态安全及更广泛人类福祉的重要反映。⑦Villa F, Voigt B, Erickson J D. New Perspective on Ecosystem Service Science as Instruments to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ie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 2014, p.152-158.
在我国,对生态安全的界定可以划分为两个向度:一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视角的生态安全,侧重于生态环境能否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如将生态安全定义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①肖笃宁:《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载《应用生态学报》2002年第3期,第354页。或者地球上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一系列环境要素综合表现的安全性表示。②余谋昌:《论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29页。这种生态安全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普遍性反思,其与国家安全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认识就形成了第二个向度,即作为国家安全的生态安全。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将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定义为“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原国家环保总局首任局长曲格平从自然生态价值和经济社会稳定的交织影响出发,认为生态安全一方面旨在防止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公众不满,影响社会稳定。③唐先武:《关注中国的生态安全科技日报》,载《人民日报》2002年3月15日,第4版。在学术领域,尽管目前对生态安全尚未达成统一的概念,但通过文献梳理来看,一般认为国家生态安全是指一国具有支撑国家生存发展的较为完整、不受威胁的生态系统,以及应对内外重大生态问题的能力,具有下述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和稳定性,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平衡,生态系统要素合理和生态系统功能健全;二是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即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功能及其整体是否能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三是国家应对生态问题能力,包括预防、容纳、控制和化解生态危机与生态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意蕴
从系统论观点和方法出发,④系统论认为,系统不等于要素的机械相加或简单堆积,而是具有由组成要素的动态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的整体特性,即整体涌现性或称复杂性。认识对象本身的整体涌现性或复杂性原则上是认识主体无法约化的,无法通过分析、分解、还原的方法揭示系统本质,而应当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对待,付出更多的认识代价。参见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500页。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子系统,其与国家安全大系统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文化等若干子系统之间具有包含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等特征的内在逻辑关联。因此生态安全的解释不能独立于其他安全,而必须置之于国家安全的系统视角下予以考察。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为什么要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怎样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重大课题的系统回答,其凝练归纳的总体属性也规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别于其他国家安全理论的哲学气质,使其成为一种扎根系统思维、具备实践品质、契合当代实际的国家安全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对内指向一个系统整体,对外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要让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成为现实,就需要把握国家安全的总体属性。⑤冯未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2页。
一是国家安全具有整体性。整体性意味着一个国家任何领域的安全问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一个领域的安全不代表另一个领域的安全,不同领域之间的安全风险具有相互传递、相互转换、相互交织的特征。虽然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都有各自的结构、功能及发展规律,但在“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结构下,⑥马世骏:《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载《生态学报》1984年第1期,第1页。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受到其它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制约。作为一个环境、人口、经济、政治大国,中国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利益关系极为复杂。在此背景下,对生态安全的思考不能缺乏语境或陷入国际潮流追逐,而必须立足于国家安全整体全面统筹,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二是国家安全具有动态性。动态性是指国家安全的风险来源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过去被认为是主要威胁的因素可能发生变化,曾经被认为安全的领域也可能不再安全,安全的外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态安全呈现不同样态,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影响生态安全的因素也在变化,甚至原先维护生态安全的条件也可能变成生态安全的潜在威胁。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生态安全的潜在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生态安全的发生机制愈发复杂。动态性要求突出风险预防原则,运用全方位、全时空、全流程视角来认识生态安全工作,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维护生态安全,实施防范化解的全流程治理。
三是国家安全具有开放性。国家安全既有“内忧”也有“外患”,而在全球化时代,封闭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既是不现实的,也将极大地增加国家的发展成本和发展风险。生态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内部的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源自境外的外来物种入侵、污染跨境转移尤其是国际贸易中的污染转移,也是危害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从开放性出发,生态安全维护不能采取闭手段,诉诸于绝对的风险“隔离墙”,而必须立足于开放环境,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将安全维护战略建构保持开放性的大前提之下。
四是国家安全具有相对性。相对性是指国家安全状态是相对于一定时期或一定程度而言的,不存在完全没有危险和内外威胁的安全状态。生态安全的多尺度特征决定了生态安全风险具有多维度性,社会发展始终处于相对的生态安全风险之中,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安全状态。因此,生态安全维护必须立足于国家实际情况来考虑安全边界设置和安全资源投入,而不能盲目追求“零风险”而使得治理活动顾此失彼。同时,要采取动态的、合理的生态安全治理策略,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建立起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的生态安全标准、评价指标,而不能固守单一的安全观念而导致治理活动僵化。
五是国家安全具有共同性。共同性是指全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实现需要各国携手合作而非独善其身。别国面临的不安全威胁可能成为本国安全的风险来源,因此“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来谋求自身安全”。①冯未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2页。从整体上来看,全球面临着共同的生态安全风险,如气候变暖、病毒肆虐、物种多样性锐减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超出单个国家或局部地区之能,需要各国的积极参与和共同治理;从区域来看,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状况等因素差异,区域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各有不同,但不同区域的生态安全风险具有相互传递性,局部生态问题也可能发展为整体性的生态安全风险。因而生态安全治理需要各国摒弃零和博弈、结盟理念等旧观念,秉持可持续的安全观、全球安全观。
(三)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内在关联
首先,生态安全与其他安全构成具有内在相互关联性的国家安全系统整体。生态安全是其他国家安全的载体和基础。一方面,生态安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是社会安全的基石,是国土安全的屏障,是资源安全的重要保障,还是国际安全的重要内容。①陆军:《强化国家生态安全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载《环境保护》2019年第8期,第10页。“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保障生态安全对于其他国家安全的维护具有基础性意义;另一方面,生态安全的实现有赖于统筹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损害的恢复倚靠经济与科技的支持,生态环境风险的预防有赖于行政机制的高效运行,而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一切生态安全实现条件的可持续性更是扎根于稳定的政治局面与和平的环境。因此,维持总体国家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生态安全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其次,生态安全的实践以防范化解生态风险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威胁为基本目标。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外延积极拓展的产物,其源于新的时代背景下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风险的新来源,这种背景渊源赋予生态安全制度体系以回应国家安全新挑战的制度基因与初衷。生态风险对国家安全的挑战突出表现在生态承载力、资源环境瓶颈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其发生具有长期潜伏性、损害爆发性以及影响中华民族实现永续发展的严重性,因此生态安全实践须立足于事前预防,以防范化解生态风险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路径和主要形式。
再次,生态安全的获得与表达须在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的宏观叙事下展开。国家安全的相对性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用以生态安全维护的资源是有限的,生态安全的维护应当在增进总体国家安全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因此,生态安全的思考并不止步于生态系统平衡或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价值,而是要与国家总体安全紧密结合。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例,如何阻止部分国际势力将大背景下的生态退化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投资联系起来,以此抹黑中国国际形象、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如何恢复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如何防止打着“环境保护”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精神运动死灰复燃?如何克服自然退化导致的一些文化纯化、自然圣境化的原教旨主义风潮?上述问题都需要落实到生态安全的策略设计中。
最后,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超越单个国家安全指向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模式包括了整个世界,而风的流动不需要护照”。②[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在生态安全领域,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从长期来看是趋于一致的而非此消彼长的。全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拥有不同背景的群体能够达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共识。③龙潇:《中华法系的文化安全智慧——以价值观为中心的考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165页。尤其是在发展鸿沟日益加深,军事冲突尚未消弭,冷战思维与强权政治阴魂不散,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和传染病持续性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威胁世界和平的情况下,生态安全是最能够凝聚各国共识与促进各国合作的议题,具有引领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深远价值。
二、我国生态安全法治的实践与现状
坚持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法治优势,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领域和重要内容。①马方:《系统构建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载《理论探索》2022年第1期,第12页。进入新时代,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形势,“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②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加强法治建设,通过良法善治来解决生态安全危机是我国生态安全维护的重要方略。
(一)我国生态安全法治的实践历程
马克思指出:“一切原理都有其世纪,”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内在地构成中国生态安全建设的话语前提和现实依托,中国维护生态安全的法治实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发展阶段性和议题针对性。
1.生态安全意识的萌芽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防止外部势力侵略、确保新生政权稳定、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该时期生态安全工作也是以政治工作为中心开始萌芽。在生产发展层面,环境资源对生产发展的支撑作用和约束条件率先受到重视,环境资源被纳入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资料范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的现实状况,党的第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与此同时,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水土流失、土壤盐碱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对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和对国家发展造成损失,国务院领导实施了一系列植树造林、保持水土、兴修水利工作。④1955年,我国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单独的章节作出林业建设的任务和具体部署,强调林业的发展和保护。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指出绿化问题并规划森林覆盖面积。其后,分别出台《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和《森林保护条例》等。“一五”计划时期国家亟需完善水利设施和加强水系治理,出台《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总体而言,该时期无论是立法或政策都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安全的概念,生态安全主要是作为一种朦胧的资源保护意识与自然灾害防治意识,在加强政治建设中心工作下获得“被动式”保护。究其原因,一是该时期其他社会问题都让位于巩固新生政权、解决人民温饱的主要矛盾,二是由于该时期工业化刚起步,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较小。但是党和国家在生产发展和社会治理层面已经体现出生态安全意识,为后续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2.生态环境法治的快速发展期
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资源瓶颈日益突显,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不仅为国际上构建绿色壁垒制造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提供可乘之机,为了保障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从政治建设中心下的“被动式”保护转向“促进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主动治理。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走上法治轨道,其后各种环境资源单行法陆续出台。⑤该时期出台的环境资源单行法主要包括《森林法(试行)》《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同时《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也对环境资源保护事务作出相关规定。199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将“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总体来看,该时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重要程度在国家工作中不断提升,藉由高频率的环境立法与环境政策制定活动,我国初步构筑起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基本覆盖了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的主要内容。
3.生态安全法治的全面完善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到“和谐共生”,蕴含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超越了作为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保障的“功用”层面,而上升到与人类命运、社会存续息息相关的安全层面。2014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①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生态安全正式进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国家安全法》第7条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并强调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完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立法”;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 年)》提出“更加注重法治思维”;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完善生态安全法治也成为我国进入新时期的紧迫任务。
(二)我国生态安全法治的基本现状
1.立法层面:不断完善生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涵括“国内立法—国际条约”两大板块、“环境资源立法—国家安全立法”两大领域、“宪法—中央立法—区域立法—地方立法”四个层次的法律规范体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安全规范体系,缔结或参与了一系列公约和议定书,②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缔结或参与的公约和议定书中,与生态安全紧密关联的包括:1989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90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6年《核安全公约》、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2000年《生物安全议定书》、2004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6年《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2009年《哥本哈根协定》等。其内容涉及气候治理、危险废物治理、核安全、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管理、生物安全等多个生态安全领域。2015年《国家安全法》规定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2018年宪法修正案第32条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从根本法的层面明确了生态安全的宪法渊源。除了制定和修订《环境法》以及环境资源单行法外,还针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安全问题进行特别立法,如《核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与此同时,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施行与生态安全空间格局体系的展开,我国颁布了首部以流域空间为治理对象的《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草案)》《国家公园法(草案)》也相继进入审议阶段。
2.制度层面:稳步构建生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6页。是党和国家对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整体部署。既有生态安全政策实践主要是在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生态安全空间格局构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并以“三线一单”制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空间精细化管控,推进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现代化。上述部署与安排初步勾勒出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目标,以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屏障构筑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作了总体部署和全面安排,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68页。规定了包括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环境监管制度、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经济政策、市场化机制、生态保护补偿体系、政绩考核体系、责任追究体系等全方位、多项目的制度安排。
3.实施层面:持续推进生态安全法律实施体系
为了保障生态安全法律规范制度的良好运行,法律和政策规定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生态安全法律实施机制。一是生态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机制,旨在为生态安全法律规范制度的实施提供信息基础。《“十三五”规划纲要》第47章第2节规定构建完善的国家生态安全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对于可能存在着的生态风险问题进行评估,完善突发生态环境安全事件信息报告和公开制度;《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安全监测制度、生态环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生态环境红线制度;二是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机制,旨在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责任内容和责任实现方式。基于侵害对象差异性和公私益诉讼分野的原理,我国建立了包括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司法救济体系。三是生态环境监管机制,旨在强化责任意识,形成刚性约束,督促党政领导干部担负起生态安全法治建设的政治责任,包括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
三、当前我国生态安全法治的问题审视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法治事业快速发展,为生态安全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总体国家观的提出以及国家生态安全形势的日趋严峻化,我国生态安全法治亦迎来了新问题、新考验。
(一)既有环境资源法治对生态安全维护的支撑不足
1.环境资源法律体系对生态安全整体价值表达不足
生态安全包含“生态”与“安全”两个互相依存的核心要素,当前环境资源法律体系体现了对“生态”的表达,但“安全”的要素价值尚未获得应有重视。“生态安全”具有不同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价值:一方面,二者具有不同目标。生态安全法治所追求的不止是优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关系、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系统,更强调生态环境系统支撑国家生存发展的功能持续稳定,以及国家妥善处理好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生态承载力不足、外来生物入侵等内外重大生态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生态安全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同调整向度。既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在社会关系调整上遵循损害原则,以利益或负外部性为调整对象,其基本思路是损害填补和外部成本内部化,主要指向事后救济;但对生态安全而言,“安全这个问题所对应的是风险和危险”。①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安全观研究》,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6页。从这种意义来说,生态安全真正应对的是“尚未发生的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判断未来状态和未雨绸缪,主要指向事前预防。既有法律体系亟需整合“生态”与“安全”的价值,并在生态安全法治建构中凸显安全的目标追求,
2.环境资源法治实践无法回应生态安全的治理需要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资源立法主要采取“要素立法+功能立法”的模式,其基本逻辑是将生态环境拆分为单一的环境要素(如水、大气、土壤、森林等),再根据单一环境要素的不同使用价值分别立法,从而把生态环境拆解为环境要素集合,把要素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约化为简单的线性关系,实现对生态资源环境的综合管理。这种以单线纵向思维方式控制调整对象的专一性,将环境要素不断细分与区别,力求从要素部分来认识环境整体的立法模式是还原论思维的理性呈现。②陈廷辉、林贺权:《从还原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 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模式的转变》,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6月第3期,第20页。虽然简化了对复杂客观对象的认识,便于建立法学范畴、认识法律运行规律,但由于其将作为整体的客观对象分割化、离散化,无法照应生态安全的整体特性,在实践运转中容易造致法律体系防范生态安全风险功能不足。此外,生态安全的空间地域差异和多尺度特征,对生态安全治理提出灵活性、精准性、科学性和全面性要求,既有的要素立法不能体现各要素空间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功能属性和管控要求,致使法律体系实施生态安全治理的效能不足。
(二)国家安全法治中的生态安全治理机制薄弱
1.国家安全法律规范体系中对生态安全的规定较少
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宪法》《国家安全法》《刑法》《反分裂国家法》《国家情报法》《反间谍法》《国防法》《戒严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立法的重点领域和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法律规范存在效力低、内容少、约束力低的问题。③马方:《系统构建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载《理论探索》2022年第1期,第14-15页。当前,生态安全主要是作为政治概念存在于党的文件中,尚未在法律规范中得以明确。尽管有学者提出宪法生态文明条款及相关条款的整体诠释可以作为生态安全的法理支撑,并且结合《国家安全法》第3条“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各领域国家安全”的明示规定,以及第30条包括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生态保护红线、生态风险”等因素,可以认为其构成了对生态安全内容的初步诠释,④张震、张义云:《生态文明入宪视域下生态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建构论》,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2期,第1-5页。但上述内容尚不足以支撑系统化的生态安全法治保障体系,也很难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因此,生态安全规范价值的实现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其法理和规范基础。
2.传统安全维护体制与手段不适应生态安全的维护需求
既有国家安全法律实施体系是围绕传统国家安全维护来建立的,因而长久以来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运作模式都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以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实施主体,以国家间的外交谈判和军事斗争为主要方式。然而,非传统安全具有迥异于传统安全的特征,面对生态安全,传统安全维护的体制与手段陷入牵牛下井的困境。当前,生态安全工作的实际运转大部分是由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农业部门、水利部门等共同承担,但这些部门的工作并不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目标下开展的,相关部门也尚未形成维护该领域国家安全的工作机制,“由于法律实施主体不明确,利益各方缺乏国家安全意识,高屋建瓴的法律规定无法全面实施”,①马方:《系统构建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载《理论探索》2022年第1期,第16页。在实践中还存在无法及时识别生态安全风险、应对生态安全危机效能低下的弊端。
3.生态安全的刑事机能不足以充分回应生态犯罪治理需要
近年来,我国生态犯罪的阈值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但作为新兴犯罪领域的生态安全犯罪具有刑事柔性化现象。②张霞:《生态安全犯罪的实证研究及问题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第189页。一方面,受制于我国刑法“厉而不严”的结构性矛盾,③刑法“厉而不严”的结构性问题,在立法层面上表现为刑事法网不严密,包括整体刑事法网不严密和个罪法网即罪状不严密,二者的共同点是当入罪而不入罪或未能入罪,从而放纵诸多具有可罚性的行为;在刑罚设立上表现为罪刑不相适应,刑罚过于严苛。参见储槐植:《再说刑事一体化》,载《法学》2004年第3期,第77页。生态安全犯罪法治的架构缺乏体系性定位,一些生态安全犯罪行为无法列入刑事领域加以评价,④如对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按单个资源种类进行保护的方式,不设概括性罪名,且在立法上采取的是最狭义的环境概念,远远小于《环境保护法》等行政法规涵盖的需保护的环境要素。这种对保护对象选择的偏失,与其说是出于对行为危害性的客观考量,毋宁说是立法早期人们对自然资源生态价值认识不足导致的。存在因保护对象狭窄造成整体法网疏漏的隐患。另一方面,当前生态环境资源犯罪以自然人为主要规制对象,且在罪量认定上单一依赖数量评价,可能导致对落入法网的犯罪人苛以过重处罚。因而总体来看,当下刑法在刑事理念、罪名体系、刑罚适用等方面尚不能充分回应生态安全犯罪的新问题,生态安全犯罪的治理仍略显捉襟见肘。
(三)生态安全法治的理论基础需要夯实
1.生态安全事件与一般生态环境事件的区分有待澄清
生态安全在性质上区别于一般生态环境事件,归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从形式来看,危害生态安全的行为与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行为具有相似的表征,因此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法治框架,首先存在一个如何区分生态安全与一般生态环境资源事件,尤其是生态安全与既有的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问题。当前在生态资源环境领域,定罪多以违法数量或程度为标准,存在“违法”与“犯罪”界限不清的问题,一方面行为人易产生侥幸心理难以形成生态资源环境保护的自觉,另一方面实践中部分生态资源类案刑罚适用结果与民众的朴素正义观偏差过大,有违刑法人权保障之目的;而如果仿照其他类型犯罪的构成,以严重后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则与生态资源保护预防优先理念相悖。此外,对于违反《国家安全法》中生态安全条款行为的制裁,也离不开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多种责任适用,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法》与《刑法》《环境保护法》《民法》等其他法律在生态安全领域的适用规则与适用逻辑。
2.生态安全党内法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有待完善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取得的各种成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内容丰富的佐证资源。①耿密:《强化党内法规研究历史维度的三重逻辑》,载《党史党建研究》2020年第4期,第45页。生态安全直接体现于执政党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安全法治进程的推进与执政党的主张具有密切关联。党内法规政策向国家法律转化是生态安全法发展与完善的重要路径。在内容上,由于党内法规和法律规范分属政治与法律两个系统,二者在内在价值、外在形式、实现机制和稳定性上都有区别,必须基于两个系统自有功能对特定目标的可实现性来谨慎选择法律化的内容,避免损及政策的灵活性价值与法律的稳定性价值,导致二者价值共赢策略的失败。在形式上,“法言法语”具有专业性、平实性,“党言党语”具有丰富性、形象性,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有待妥善处理,否则可能引起理论上的困惑、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和法律运作中的误导。
3.生态安全法治实施的效能有待提升
生态安全法治的提出具有高度的时代性、前瞻性与创新性,然而受制于起步时间短、实践经验较少等因素,生态安全法治的理论与制度还在探索与完善之中,尚非“良法”,也未达成“善治”。作为国家安全的生态安全面对的法治实施困境,不仅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中广为诟病的国家安全的秘密性与法治化、公开化的矛盾,还受制于环境问题“决策于未知”特点的困扰,面临着现代风险行政中广为人知的议程设置的随意性、最后十分之一、②[美]布雷耶:《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宋华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6页。规制活动本身带来的替代性风险、潜在收益丧失甚至系统性风险等现实困惑,③Frank B. Cross,Paradoxical Peril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53 Washington & Lee Law Review,1996,p. 851.无不制约着生态安全的制度效能。在生态安全法治的塑造与完善阶段,如何规避与控制这些可预见的实施难题,是我国当前生态安全法治面临的重要挑战。
(四)当前我国生态安全法治的问题省思
源起于经典科学的还原论认为万事万物均可经由“分割—还原”的路径来认识与把握,通过被分割的局部可以解释整体,通过低层次现象可以解释高层次现象,这种思想锻造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视域。我国治理体制的基本结构亦是延循了这种还原逻辑:根据社会事务的性质建立起林立的管制结构,法律规范内容重点是指定主管机关、界定规范对象、厘清管制目的、选择合适的管制工具以达成管制目的、运用执行手段以推动管制目的落实。④叶俊荣:《环境立法的两种模式:政策性立法与管制性立法》,载《清华法治论衡》2013年第3期,第8页。这种治理结构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体现,能够对不同性质的事务实现专门化、针对性的管理,但随着部门分工的固化,诞生于部门交叉领域的新兴事务很容易成为没人要管的“管制孤儿”。与此同时,新兴社会事务和管制需求的不断增加,管制事项、管制结构和管制法律日趋庞杂化,由此可能引起法律适用、组织分工和实际实施上的障碍,如何统合林立的管制便成为现代法治发展的一大难题。
生态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议题,诞生于生态环境资源与国家安全的交叉领域。“新兴性”与“交叉性”,使生态安全法治不可避免要面临“管制孤儿”与“管制统合”的困境,这种困境正是当前我国生态安全法治问题的根源所在。尽管作为社会事务的生态安全与生态环境资源治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作为一种国家安全的生态安全,其核心价值与治理目标与生态环境资源治理是有明显差异的。因此,生态安全法治需要有意识地跳出生态环境资源治理的语境,在传统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生态安全法治独特的价值导向、法律规范和制度基础。
四、完善我国生态安全法治的建议
良好的生态法治秩序能够促进法律功能的发挥,能够将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理念内化于系统的法治秩序之内,并能够系统地发挥于生态安全问题治理的实践之中。①马波:《生态安全法治保障论》,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5期,第73页。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生态安全以空前的重要地位与特定的时代价值,面对生态安全法治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有必要从多个层面对生态安全法治进行完善。
(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安全观为价值指引
从哲学上看,价值是反映认识和实践活动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事物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对象性、双向性、生成性、互益性关系之契合度的一个范畴。②方世南:《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价值意蕴》,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34页。马克思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社会制度的后果,③叶海涛:《“自然”概念与马克思生态理论的逻辑结构》,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36页。主张从制度层面找寻解决自然异化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途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生态安全观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通过进一步阐明生态安全与其他社会领域安全的辩证关系,实现生态安全与国家生存发展、人类共同体安全的紧密结合:一是生态安全以人民安全为核心。人民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是生态安全的始基与价值之源,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认识和实践上不能将生态安全与人民生命安全、健康安全切割开来;二是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有机统一。“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只有生态安全了,才能保障生态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供给能力,稳固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三是生态安全对政治安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态环境危机会引发公众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信任危机,进而造成政治危机。因此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应对,而是要将其上升到关系政治安全的高度加以认识。四是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在国别问题已经演变为“类危机”的情况下,没有国家可以在生态安全危机中独善其身。因此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共进,共谋全球化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人类文明的安全。从生态安全观出发,维护生态安全的价值指向保障人民基本权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降低资源环境对生存发展需求的刚性约束以及应对生态环境危机及其引发的次生危机,上述内容共同构成我国生态安全法治体系建构的价值指引。
(二)夯实生态安全法律规范和制度基础
依法治国,立法先行。从《宪法》和《国家安全法》的有关法律条文出发,亟需进一步明确生态安全维护的法律规范和基础制度,为生态安全法治体系建构提供更坚实的规范依据和制度工具。其一,在生态环境资源法治领域,尽快落实《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的诸项法律法规、标准制定和制度安排。及时对现行环境资源管理规范中与生态安全价值不匹配的条文进行“废、改、释”,减少部门分割、要素治理带来的管制冲突,协调生态环境法律施行。其二,在《国家安全法》第四章“国家安全制度”中,针对生态安全维护的特殊性,有必要在具有通用性质的国家安全制度中寻找生态安全维护所需要的具体国家生态安全制度,并以单行法规、规章的形式予以确定下来。其三,在刑法领域推进轻罪立法,扩张生态资源犯罪圈、密织生态安全犯罪法网,在犯罪构成上强调刑法的提前介入,并根据“轻轻重重”理念对现有生态资源类犯罪的刑罚进行调整,优化刑罚结构,推动生态安全刑事规制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结构转向。上述法律规范和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法律化、法规化、规章化的关系,以平衡法律稳定性和避免立法过大过粗造致条文虚化,影响制度实效。
(三)明确生态安全法治的实施主体及责任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良好的实施是生态安全法治的完整表达。在《国家安全法》第11条所规定的诸多实施主体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生态安全法治的具体实施主体及其责任范畴。系统的层次性原理要求尊重组成部分的规律,从发挥整体功能的角度出发来优化系统层次。对此,可以通过细化生态安全法治实践,在三个层面、多个主体之间建立起生态安全法治实施体系:一是在领导层面,由各级党委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领导、统筹与协调生态安全法治建设的具体职责;二是在横向实施层面,成立由党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农业部门、水利部门等多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领导小组,围绕生态安全信息获取与评估、生态安全法规政策实施、生态安全维护事务分工、各部门治理目标等,在实现整体治理效果最大化的基础上进行统筹协调;三是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垂直部门之间,按照部门的治理任务和执行能力,对生态安全维护的权责进行合理配置。对于横向协作机制,应避免滥用问责手段造成“人人有责无人担责”的情况,而以调整、建立和生态安全维护目标一致的利益激励机制为完善方向;对于垂直部门之间的纵向协作机制,应推动监测、研究、执法力量等行政资源向基层压实,以应对生态安全维护的治理需要。
(四)回应生态安全法治的特殊需求
其一,优化生态安全司法审判。生态安全是生态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交叉,既具有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专业性特征,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司法审判提出了重大考验。生态安全司法审判应当从两个方面予以优化:首先强化生态安全审判的专业性,通过引入专业人员参与司法审判、完善专家证据规则、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等程序措施来应对生态安全问题提出的复杂性挑战,以增进裁判结果实质正义的达成;其次是进一步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从关注个案公益损害的修复,到更注重抓溯源、治根本,抓前端、治末病,更加充分地发挥司法制度效能。其二,作为一种实现成本高昂的法律,生态安全执法既不能追求全域覆盖,也不能搞面面俱到,而是需要提升执法效能,使法律实施效果最大化。具体而言,生态安全执法应当以“三线一单”为重点监管内容,通过探索和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跨区域执法等执法方式,来应对生态安全问题所具有的跨区域特征、提高执法效率,加强对与民生领域紧密相关的生态安全事件的执法,防范生态安全危机向政治安全危机的转化。
五、结语
生态安全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一个具有前瞻性、实践性特征的理论命题,其不再囿于“不发展”的问题范畴,而是矢志于回答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以及发展后带来的成果保障与地位维护问题。生态安全法治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生态安全的法治化治理实现生态安全维护,其不仅是对政策实践成果的法律化,更是从国家安全视角出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再认识,以及对既有法律理念、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重塑。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生态安全无疑将获得更加深厚的诠释基础与理解视域。本文从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出发,仅初步探讨了既有生态安全法治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方向,并没有作出因应的、全面的回答,也未对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完善进行具体详实的阐释。生态安全法治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存在的诸多重大疑难问题,还有待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