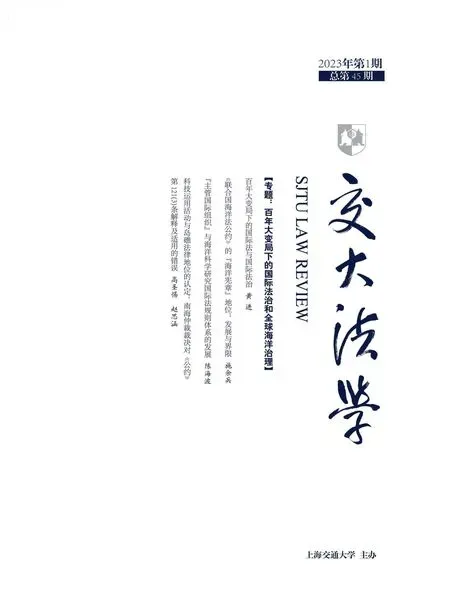“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陈海波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海洋依然是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之一。对海洋的科学了解是人类各类相关活动的根本。海洋科学在地球系统科学的探索、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各类海洋资源、海上运输安全、国家海洋权益保护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研究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也能推动其他学科和相关技术发展。(1)参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编: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海洋科学》,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联合国大会决议回顾历史,明确提出,“海洋科学通过持续开展研究和评估监测结果增进知识,并把这些知识用于管理工作和决策,对消除贫困,加强粮食保障,养护世界海洋环境和资源,帮助了解、预测和应对自然事件以及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开发至关重要”。(2)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海洋和海洋法”议程项目2021年12月9日大会决议(A/RES/76/72),2021年12月20日,第4页。海洋科学研究以及海洋技术的发展与转让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但在现实中,各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并不均衡,(3)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世界海洋科学现状》,2017年;《2020年全球海洋科学报告——海洋科学能力摸底调查》(执行摘要),2020年。直接影响了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或1982年《公约》)针对海洋科学研究的多个方面做出较全面规定,是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主要载体。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以促进海洋科学研究为主旨,并力争实现各方利益平衡,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海洋科学技术能力建设与利益共享,推动多层面国际合作,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公约》将“主管国际组织”纳入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多角度展现主管国际组织在推动海洋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多重功能和重要作用,是《公约》的重要创新与突破,也是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突出特点。
《公约》通过并生效至今,需要对这一特殊体系安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国际社会日益倚重“主管国际组织”进行、组织、主持、推动海洋科学研究与相关活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呈现多元发展之势。这一多元发展趋势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论文选取 “海洋科学研究”概念的澄清、《公约》相关规定的适用,以及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这三个视角,就多元发展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此,中国应如何应对,促使中国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中能够趋利避害,也是论文的重要着眼点。
如无特指,文中“主管国际组织”一词包括《公约》第247条规定的“国际组织”。在一般性表述时,“海洋科学研究”这一表述是《公约》第13部分“海洋科学研究”与第14部分“海洋技术的发展与转让”相关事项的统称。
一、 “主管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一) “主管国际组织”角色定位的缘起
1. 海洋科学研究与国际组织初期发展阶段
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和海洋科学研究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4)近现代意义上的海洋科学研究肇始于英国海军巡航舰“挑战者”号(HMS Challenger)自1872年末至1876年初持续三年半时间的跨洋科学考察。其考察对象主要包括水体和海底,考察成果丰硕,所取得的研究发现奠定了现代海洋学的基础。See Catherine Danleyal, Diving to New Depths: How Green Energy Markets Can Push Mining Companies into the Deep Sea, and Why Nations Must Balance Mineral Exploitation with Marine Conservation, 44 William and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 219, 219-265(2019).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国家间联系不断增强,使一些专门的、技术性的事务突破国家边界,促使在国家间建立主要以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协作为职能的机构,即“国际行政联盟”(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Unions)。参见梁西: 《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 节选集》,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68—69页。早期的相关国际组织包括在1874年成立的邮政总联盟[General Postal Union, 1878年改名为“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在1873年成立 (转下页)海洋科学研究所体现的从跨国性向全球性发展,从侧重考察向侧重观测发展,从个体性向合作性和公用性发展,以及进行多尺度系统的跨尺度研究,科学和技术协同发展等特点和发展趋势,(5)(接上页)的国际气象组织[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IMO,1950年转型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在1902年成立的国际海洋开发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ICES)等。(6)见前注〔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书,第12—19页。呼唤更多专门性、技术性国际组织的建立。这些国际组织的运行也进一步推动了(海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及应用的发展。(7)较为典型的是,世界气象组织(WMO)前身国际气象组织(IMO)在1878年正式成立后,即先后发起第一次国际极地年(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IPY)活动(1882—1883)和第二次国际极地年活动(1932—1933),并与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前身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ce Unions, ICSU, 1931年成立)共同发起并组织了第三次国际极地年即国际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IGY)活动(1957—1958)。之后,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发起和联合发起了多项“国际年”或“十年”活动(International Years and Decades)。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成功举行激发了更多国际合作科研活动的启动与实施,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和联合发起的国际水文十年计划(International Hydrological Decade)(1965—1975)、国际海洋考察十年计划(International Decade of Ocean Exploration)(1971—1980)等。2017年,第7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了“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海洋十年”)(2021—2030)实施计划,指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 IOC/UNESCO)负责协调实施。See E. I. Sarukhanian & J. M. Walker, The 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IMO) 1879-1950, http://ane4bf-datap1.s3-eu-west-1.amazonaws.com/wmocms/s3fs-public/The_International_Meteorological_Organization_IMO_1879-1950.pdf. 载世界气象组织发展史介绍网页https://public.wmo.int/en/about-us/who-we-are/history-IMO, 另见国际科学理事会发展史介绍网页https://council.science/about-us/a-brief-history/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史介绍网页https://www.unesco.org/zh/75th-anniversary, The Science we need for the ocean we want: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Ocea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2030), IOC/BRO/2020/4, IOC/UNESCO (202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5198, 以及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海洋和海洋法”议程项目2017年12月6日大会决议(A/RES/72/73),2018年1月4日,第292—295段。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一部公约对“海洋科学研究”和国际组织角色定位做出明确规定。
2. 成立国际法委员会至1958年多部海洋法公约获得通过阶段
在联合国框架内担负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之责的国际法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即将公海制度和领海制度列为编纂主题,开展工作。(8)参见国际法委员会: 《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281页。
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完成了海洋法条款(共73条)的最后报告。(9)参见国际法委员会: 《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2卷,第253—301页。这73条海洋法条款没有明确规定海洋科学研究,特别是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角色与作用。但是,在起草过程中,以及对海洋法条款第68条进行评注时,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两点意见: (1) 不排除将来建立国际机构的可能性,由该国际机构负责科学研究,提供指导和协助,以期为了普遍利益(general interest)促进对海底区域(submarine areas)进行最有效的利用;(2) 有可能在现有国际组织的框架内设立这样的机构。(10)参见国际法委员会: 《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2卷,第215页;国际法委员会: 《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2卷,第298页。
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5条第8款开创性地采用了“适当机构”(qualified institutions)这一措辞,规定“倘有适当机构提出请求……作纯粹科学性之研究者,沿海国通常不得拒予同意……”(11)参见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6卷: 第四委员会(大陆架),A/CONF.13/42。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四委员会通过的案文采用“request is submitted by a qualified institution”措辞。这一措辞被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5条第8款采纳。这一措辞以及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两点意见为1982年《公约》将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主体扩展为“所有国家”和“各主管国际组织”开辟了空间。《大陆架公约》第5条第8款体现了“沿海国同意”“加入”“参与”“发表”等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的相关要素,也为1982年《公约》确立较全面具体的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奠定了基础。(12)See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DOALOS):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 Revised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2010, para.2.
同时通过的1958年《公海公约》第25条首次明确提到主管国际组织。从防止海水受放射性物质或其他有害物质污染的角度,《公海公约》要求各国均应参照主管国际组织所订定的标准和规章,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并要求各国均应与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采取措施防止海水或其上空遭受污染。
3. 成立特委会至1982年《公约》获得通过阶段
在科学研究方面,除大陆架制度中有少量规定外,实际上相当于没有法律规定。(13)参见《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报告》,大会正式纪录: 第27届会议补编第21号(A/8721),联合国1972年,第243段。为此,联合国大会先后于1968年和1970年决定设立和扩大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筹备第三次海洋法会议。(14)参见联合国大会第23届会议第2467 A(XXIII)号决议(1968年),以及联合国大会第25届会议第2750 B(XXV)号决议(1970年)和第2750 C(XXIII)号决议(1970年)。特委会将与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相关的法律原则与标准、问题清单、条款草案等确定为重点议题之一。
在特委会专题研拟的基础上,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自1973年至1982年共举行了十一届,最终通过了《公约》。其中,明确提及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的条款包括第238—239、243—244、246—249、251—254、256—257、262—263、265—266、268—273、275—276、278条等,(15)See “Competent o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Law of the Sea Bulletin No.31, United Nations, 1996, p.89-95.较为具体、全面地规定了“主管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中的多重角色和突出作用,是《公约》的重要创新和突破,也是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突出特点。主管国际组织所担当的角色主要体现为海洋科学研究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导者,详见下文。
(二) 参与者: 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
《公约》是首次确认主管国际组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多边条约。《公约》第13部分通过多项条款规定“主管国际组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以及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时的相关事项。其中,第238条和第247条是核心条款。
第238条将“各主管国际组织”(compet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与“所有国家”相并列,故此可以认为第238条所规定的“各主管国际组织”范围较为广泛。所有具有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职能的国际组织均可成为第238条规定的“各主管国际组织”,有权进行海洋科学研究。(16)参见[美] 迈伦·H. 诺德奎斯特(Mron H. Nordquist):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4卷),吕文正、毛彬译,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420—428页。
第247条使用“国际组织”(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措辞。在《公约》谈判过程中,有观点认为第247条中的“国际组织”一词应与第238条“各主管国际组织”含义相同。(17)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502页。可以看出,这两种用语互为解释、相互替代,至少表明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主管国际组织”的范围具有可变性,可以为更多国际组织参与推动海洋科学研究预留空间。主管国际组织/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可以充分展现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实现利益共享、数据交流,具有主权国家在一国领海或管辖海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时所不具备的优势,利于利益调和、成果共享。
(三) 推动者: 促进海洋科学研究和相关国际合作
《公约》基于海洋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全球、区域、分区域、双边及各国单边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对“主管国际组织”提出了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的开展以及进行相关国际合作的“要求”。(18)参见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附件六《关于发展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基层结构的决议》。
鉴于国际组织往往代表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利益,具有推进海洋科学研究更广泛参与的特点,《公约》第239、242、243、244条等许多条款明确规定(各国和)“主管国际组织”应当按照公约规定,促进和便利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行;促进为和平目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通过缔结双边和多边协定以创造有利条件,进行海洋环境中的海洋科学研究;通过适当途径公布和传播海洋科学研究相关情报和所取得的知识,促进知识转让,加强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自主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能力。《公约》第14部分还为此明确了基本目标,确定了实现措施,并围绕各国与主管国际组织(和管理局)的合作与职能安排以及各国双边、区域、多边国际合作,海洋科学和技术国家中心与区域性中心的设立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19)参见《公约》第266、268、269、271、272、273、275、276条等。这些规定为更多国际组织多样化参与推动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规则基础。
(四) 引导者: 促进制定海洋科学研究一般准则和方针
《公约》第251条要求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以协助各国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第271条要求各国直接在双边基础上或者通过主管国际组织促进制定海洋技术转让方面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主管国际组织”应当是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准则和方针的积极推动者。
第251条的正式文本不直接规定由主管国际组织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而是通过主管国际组织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以协助各国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在措辞上,“一般准则和方针”的范围可以较为广泛,无需考虑研究计划与勘探和开发生物、非生物资源是否直接相关,也不再局限于进行基础性研究与非基础性研究的判断。(20)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535—536页。可以认为,具有相应职能范围的国际组织均可成为第251条规定的“主管国际组织”。
第271条侧重海洋技术转让方面方针、准则和标准的制定。相关案文的起草谈判时间与第251条的时间基本同步。谈判方对于主管国际组织角色和作用方面的主张也基本相似,同样未对“主管国际组织”作任何限定。可见,其同样希望主管国际组织发挥引领的作用,在相关事项上提出建议、指南甚至做出示范,统一各国的规定,形成可以普遍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
上述主要角色中,“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显性”角色,使“主管国际组织”身处海洋科学研究实践的最前沿,直接引领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引导者”虽是“隐性”角色,却为“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实践与规则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定力与动力支持。详见下文。
二、 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趋势及其体系支撑
《公约》通过并生效至今,海洋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场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的相关实践更加丰富,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从其内在原因和体系依据看,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体现了制度安排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 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表现
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主要体现在组织机构、组织合作与组织行为、研究项目、研究内容等方面。
1. 组织机构与组织形式多元化
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以下简称“海法司(DOALOS)”]曾经制作了主管国际组织的清单。(21)See “Competent o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Law of the Sea Bulletin No.31, United Nations, 1996, p.89-95.不难发现,如果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IOC)[以下简称“海委会(IOC)”]理解为《公约》通过并生效当时最为直接的“主管国际组织”,(22)《公约》附件八第2条规定,在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由海委会(IOC)或者该委员会授予此项职务的适当附属机构“编制并保持”专家名单。近40年来,除海委会(IOC)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科学理事会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SCOR)[以下简称“海科委(SCOR)”]、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海洋物理学协会、海洋能源系统执行联盟(OES)、全球环境基金会(GEF)、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大洋中脊协会(InterRidge)、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及其他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3)参见高峰、王辉主编: 《国际组织与主要国家海洋科技战略》,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这些国际组织中,既有政府间组织,也有非政府间组织;既有全球性组织,也有区域性组织。尽管类型不同,这些国际组织均将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列入组织职责范围,且具有相应的专业资格和组织能力,符合《公约》英文文本“competent”一词的通常含义,可以被认定为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
相关国际组织还采用“对话”“论坛”“会议”等形式,通过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咨询机制”,组建“长期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进行“长期可持续的会议交流”,将相关国家、(24)联合国大会决议促请各国……“与主管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依照《公约》继续努力通过加强本国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增进对海洋和深海,特别是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范围和脆弱性的了解和认识”。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291段。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各类主体等组织在一起,形成共同参与、相互激励的海洋科学研究联盟。(25)见前注〔22〕,高峰、王辉书,第155页。
2. 国际合作与组织行为多元化
国际合作是解决各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不平衡问题的有效方法,(26)See P. Bernal & A. Simcock, Chapter 30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L. Inniss and A. Simcock, The First Global Integrated Marine Assessment: World Ocean Assessment I, United Nations, 2016, p.7.是主管国际组织回应全球或地区关切,进行、组织、主持、推动海洋科学研究的优势所在。主管国际组织通过合作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联合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例如海委会(IOC)与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共同签署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备忘录,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科学选址、计划制定、项目执行等阶段以及组织运营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推动这项关乎各国和全人类发展的海洋科学研究。(27)Se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on the Co-Sponsorship of the GOOS Steering Committee, 1998.
二是联合发布海洋科学研究战略计划。例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世界大洋环流试验(WOCE)、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试验(TOGA)、国际海洋钻探计划(IODP)等,吸引全球范围的科学家参与其中,带动全球范围的大合作,更大范围地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发展与海洋科学技术进步。(28)见前注〔22〕,高峰、王辉书,前言及第1—3页。大型国际研究计划在具体实施中,往往需要多个相关国际组织紧密合作。(29)见前注〔22〕,高峰、王辉书,第23—28页。
三是联合发布海洋科学研究报告。围绕具体领域,汇聚领域专家,对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判断、预测,提出解决方案或相关建议,为政府层面、国际组织层面甚至全球领域的海洋治理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例如由海委会(IOC)、国际海事组织(IM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发布的《海洋与海岸可持续发展蓝图》(A Blueprint for Ocean and Coastal Sustainability)为里约会议20周年峰会(Rio+20)讨论海洋问题提供了参考。(30)见前注〔22〕,高峰、王辉书,第29页。
四是联合建设海洋科学研究基础设施。较为典型的是由海委会(IOC)、世界气象组织(WMO)、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局(JAMSTEC)、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等联合制定的Argo(Array for Real-time Geostrophic Oceanography)国际计划,召集30 多个国家和组织合作建设Argo 全球海洋观测网,实时、持续监测和认知全球海洋状态,形成各类海洋数据。(31)See IOC: Resolution XX-6: the Argo Project, the 20th Executive Council, June 1999; IOC: Resolution EC-XLI.4: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olution XX-6 of the IOC Assembly Regarding the Deployment of Profiling Floats in the High Sea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rgo Programme, the 41th Executive Council, IOC, 2008.
五是联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建设。例如在联合国框架内,持续强调“必须加强主管国际组织的能力,以在全球、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各级,通过与各国政府的合作方案,协助发展在海洋科学以及可持续管理海洋和海洋资源方面的国家能力”。(32)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3页。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搭建的平台进行国家最佳实践方面的交流,是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建设的新兴路径。(33)Se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irection of IODE in the Next Decade, European Commission (Feb.25,2022), https://emodnet.ec.europa.eu/en/recommendations-direction-iode-next-decade.
3. 研究项目与研究内容多元化
海洋科学研究涉及全球、区域、分区域、双边和各国单边对海洋的认知保护利用,也是在海洋经济、海洋治理、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宏微观决策和采取行动措施的重要基础。由主管国际组织进行、主持、推进、促进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在项目内容、参与主体、参与方式等方面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在联合国框架内,对于海洋和深海的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系统、人为威胁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海洋酸化等的研究均为当下及未来的重要研究项目。(34)研究项目详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3—7页,第14—22、291—307段。相关区域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也有相似特点。(35)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74段。See also Yoshinobu Takei,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Arctic, in Erik J. Molenaar, Alex G. Oude Elferink & Donald R. Rothwell eds.,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Polar Regions: Interactions between Global and Regional Regime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p.362-363; Zhang Chao,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the Promotion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in Keyuan Zou & Anastasia Telesetsky eds.,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New Marine Technologi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Brill Nijhoff, 2021, p.197-202; see also Charlotte Salpin, Vita Onwuasoanya, Marie Bourrel & Alison Swaddl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95 Marine Policy 363, 363-371 (2018).
(二) 海洋科学研究“公共性”与国际组织“功能主义”呼唤多元发展
海洋科学研究的“公共性”与国际组织的“功能性”同频共振、遥相呼应,是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重要原因。
海洋科学研究涉及重要的公共利益,其成果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体现人类集体利益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弥合和相互促进。但是,各国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管理海洋数据和信息的软硬件能力并不均衡。(3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年全球海洋科学报告——海洋科学能力摸底调查》(执行摘要),2020年。因此,进行国际联合行动是克服这些不足的重要方法。以往重大国际海洋科学研究方案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均表明,利用当今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海洋探索的重大努力仍然是人类最有价值的集体努力之一。(37)See Bernal & Simcock, supra note 〔25〕, at 1.
例如,1957—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IGY)活动催生出的非政府组织海科委(SCOR)和政府间组织海委会(IOC)自成立开始,就将发展海洋科学研究与服务,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实施海洋科学研究联合行动,促进能力建设等作为成立目标和重要职能。还有一些国际组织,例如国际海事组织(IMO),即使未将海洋科学研究列为基本职能,也会基于职能履行的需要,将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工作列入主要工作范围,体现国际组织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优势,实现《公约》对人类集体利益与各国国家利益进行弥合和促进的主旨。
实践表明,海洋科学研究“公共性”与国际组织“功能性” “遥相呼应”效果明显,各类研究活动、研究计划、相关决策安排和具体措施层出不穷。(38)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3—7页,第14—22、291—307段。
(三) 《公约》的推定同意制为多元发展预留空间
为了实现沿海国与研究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公约》要求在沿海国领海内、专属经济区内或者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时,需要获得沿海国的同意并满足相关条件。(39)《公约》起草过程中,谈判方对于《公约》第246条“同意”要求是否适当的观点不相一致。国家海洋科学研究能力的实际情况对于是否应当采用沿海国同意制度以及同意制度的具体内容会产生较明显影响。See Clive R. Symmons & Piers R. R. Gardiner,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Offshore Areas: Ireland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7 Marine Policy 291, 291-301(1983).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470页。可以说,取得沿海国同意是对海洋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约束。
与此同时,《公约》又体现出对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的特殊关切。(40)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499页。《公约》第247条专门规定“推定同意”制,降低“沿海国同意”要求的门槛。(41)《公约》第247条只适用于由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第247条规定:“沿海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或同该组织订有双边协定,而在该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该组织有意直接或在其主持下进行一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如果该沿海国在该组织决定进行计划时已核准详细计划,或愿意参加该计划,并在该组织将计划通知该沿海国后四个月内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则应视为已准许依照同意的说明书进行该计划。”根据该条规定,沿海国与进行或主持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之间可以存在两种关系: 一是沿海国为该国际组织的成员;二是沿海国与该国际组织订有双边协定。只要属于其中一种国际法关系,在该国际组织决定进行该海洋科学研究计划时,如果沿海国已经依据国际组织内部程序及要求对海洋科学研究的详细计划进行了核准,或者沿海国愿意参加该计划,并且沿海国没有在收到研究计划通知后的四个月内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即应视为沿海国已经“同意”该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已经准许该国际组织依照所同意的计划说明书进行或主持该海洋科学研究计划。
从国际组织宪政角度看,《公约》第247条将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转换为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利益协同,体现前述“遥相呼应”“同频共振”的效果。
如果海洋科学研究项目或者能力建设项目与沿海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发展目标相协调,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该项海洋科学研究工作将可以成为沿海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补充,从而在沿海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组织宗旨与功能实现之间形成相互呼应、互为成就的良性循环。可见,推定同意制可以避免以国际组织为主导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受到不当延误,有利于在沿海国和国际组织为之“服务”的国际社会之间形成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利益平衡,在保障海洋科学研究的进行,促进国际合作,推进海洋科学研究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时代发展的前瞻性。
(四) 《公约》条款与缔约文件为多元发展提供支撑
尽管《公约》的核心条款第238条没有明确规定“主管国际组织”具体所指,第247条也没有界定“国际组织”的范围,但是仍然可以结合《公约》其他条款、公约谈判情况以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来整体理解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的范围界限。
1. 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不具有唯一性
《公约》中文文本使用的“主管”一词,与英文文本使用的“competent”相对应。依通常的中文表述,“主管”为主要负责的意思,易使“主管国际组织”被误读为具有特定性、排他性甚至唯一性的国际组织。如果依据通常的英文表述,“competent”更侧重该国际组织是否具备履行某种职能的能力,是否具有法律承认的资格,与通常的中文表述有所不同。(42)参见[美] 拉扎尔·伊曼纽尔: 《拉丁法律词典》,魏玉娃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1页。从《公约》条款的整体规定和适用实践看,宜采用英文文本中“competent”一词的通常含义,强调相关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相关事项之间的实质联系。《公约》第238、239、242、247条等使用的表述(如compet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43)使用此类措辞的还有: 《公约》第61、197—202、204—205、207—208、210、212—214、216—217、222、238、243—244、246、248—249、251—252、254、256—257、262—263、266、268—269、271—273、275—276、278、319条等,以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附件六《关于发展各国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服务基层结构的决议》。《公约》第163条使用“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competence”,也不具有唯一性。均为一般性措辞,不特指进行或者获准进行具体研究项目的某一主管国际组织(44)使用相同措辞的有: 涉及海道通行的第22、41、53条;涉及人工岛屿、设施、结构的第60条;涉及船源污染的第211条;涉及船旗国、港口国、沿海国执行的第217、218、220条;涉及便利措施的第223条;涉及具体海洋科学研究项目的第246条第5款、第252条(b)项、第253条第1款(b)项、第265条等。。《公约》第278条规定也可以印证“不具有唯一性”的解读。第278条促请《公约》第13部分和第14部分所提及的那些主管国际组织积极合作,有效履行相关职务和责任。可见,具有海洋科学研究相关活动资格的国际组织均可视为属于第278条规定的范围。(45)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712页。某一国际组织是否为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应依实际情况来确定。实践中,会有多种国际组织基于实际情况成为进行海洋科学研究、主持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促进和推进海洋科学研究等的主管国际组织,客观呈现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态势。
2. 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不局限于全球性国际组织
尽管《公约》第13部分和第14部分没有明确规定“主管国际组织”是否包括区域性国际组织,我们仍可立足于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发展和转让的特点与实践需求来加以确定。区域国家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的发展与转让方面,有更趋一致的共同利益、共同关切与共同需求。通过区域性组织协调各国行动可以为合作奠定良好基础,进行积极实践,满足迫切需求。因此,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技术发展与转让的“主管国际组织”不应局限于全球性国际组织,也应当包括具有这方面职能的区域组织甚至分区域组织。从《公约》第278条规定出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有观点认为,对于某一全球性或区域性政府间组织而言,只要其组织文件或相关文件显示海洋科学研究属于该政府间组织的职责范围,该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或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即属于《公约》第247条规定的“国际组织”。(46)See The background of Article 247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in UNESCO, Procedu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47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 2007, p.9.这一解读和实践需求为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47)例如,北极理事会2017年主持通过了《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协定》(Agreement on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rctic Scientific Cooperation),目的在于拓宽对相关北极区域的科学认知。协定还确认许多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框架对于北极地区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与贡献。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框架包括许多区域性组织。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345段。
3. 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应否为政府间组织需要具体确定
《公约》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条款只使用(主管)国际组织这一表述并未规定是否限定为政府间组织。有观点认为,“主管国际组织”至少应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的“主管国际组织”应为海委会(IOC)。但是也有不同主张,认为《公约》第13部分规定的“主管国际组织”可以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特别关注海洋科学并且能够参与研究计划的非政府组织也可能属于《公约》第238条的范围。(48)See George K. Walker ed., Definitions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erms Not Defined by the 1982 Conven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2, p.137-140;另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415—416、428页。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如海科委(SCOR)往往与政府组织[如海委会(IOC)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支持相关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49)例如海科委(SCOR)和海委会(IOC)于2008年共同设立并运行的数据公开工作坊(SCOR/IODE Workshop on Data Publishing)。See UNESCO: SCOR/IODE/MBLWHOI Library Workshop on Data Publication, IOC Workshop Report No.230, 2010.又如由海委会(IO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气象组织(WMO)和海科委(SCOR)共同建立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Se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on the Co-Sponsorship of the GOOS Steering Committee, 1998.发挥各自特长,因而可以共同成为某项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主管国际组织”。
综上,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有其现实需要、内在原因和制度支撑。相较于《公约》通过并生效之时,当下的海洋科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特点。未来,多元发展仍将是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三、 多元发展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影响
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在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产生了一定影响,突出体现在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厘清《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制定一般准则与方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的发展等方面。
(一) 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

1. 问题肇始: 《公约》谈判过程中的争论
《公约》谈判起草之初,谈判方对于“海洋科学研究”是否包括应用性研究有较明显的意见分歧。(54)See Walker, supra note 〔47〕, at 241-244;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421—426页。之后,谈判方从重点讨论“海洋科学研究”的定义逐渐转变为讨论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主体、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权利范围及限制条件等方面,不再关注“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这直接导致第238条的最终文本没有界定“海洋科学研究”,也没有明确回答“海洋科学研究”与应用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是否涉及资源研究等问题。
另一个突出争议是“海洋科学研究”是否包括水文测量(军事测量)的问题。尽管有关“测量”/“测量活动”和“研究”/“海洋科学研究”的“几项提案全部提及了军舰的问题”,(55)[斐济] 南丹(S. N. Nandan)、[以] 罗森(S. Rosenne)编: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2卷),吕文正、毛彬译,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但是,《公约》既没有对“测量”“测量活动”进行界定,也没有明确回答“海洋科学研究”与“测量”是包含关系还是平行关系,“军事测量”是否为“测量”的一种,“军事测量”是否属于“海洋科学研究”范畴等问题。
2. 问题持续: 《公约》通过并生效后的相关争论
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引发了持续争论。美国学者J. 阿什利·罗奇(J. Ashley Roach)(56)参见J. Ashley Roach: 《对科学研究的界定: 海洋数据搜集》,载傅崐成等编译: 《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 1977—2007》,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5—1727页;see also J. Ashley Roac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Fourth Edition), Brill Nijhoff, 2021, p.486-540.和劳尔(皮特)·佩德罗佐[Raul (Pete) Pedrozo]、(57)See Raul (Pete) Pedrozo, Responding to Ms. Zhang’s Talking Points on the EEZ, 10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7, 207-223 (2011). See also Raul (Pete) Pedrozo, Preserving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Right to Conduc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hin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 9-29 (2010).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默斯利(Christopher Whomersley)、(58)See Christopher Whomersley,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Covered by Part XIII of UNCLOS?, in Zou & Telesetsky, supra note 〔34〕.澳大利亚学者山姆·贝特曼(Sam Bateman)(59)See Sam Bateman, A Response to Pedrozo: The Wider Utility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10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77, 177-186 (2011).日本学者田中嘉文(Yoshifumi Tanaka)也有相似观点。See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442-444.和中国学者张海
文(60)参见张海文: 《沿海国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与军事测量的冲突问题》,载前注〔55〕,傅崐成等书,第1611—1612页。See also Zhang Haiwen, Is It Safeguard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Maritim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 Comments on Raul (Pete) Pedroz’s Article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1, 31-37 (2010).的主张较具代表性,显现出三种思路。一是以《公约》相关条款及其文字表述为依据,将没有出现在《公约》第13部分的活动或者已被第13部分排除的活动排除在“海洋科学研究”范围之外,例如J. 阿什利·罗奇在其2007年论文中的论证思路和劳尔(皮特)·佩德罗佐的论述;二是以《公约》相关条款及其文字表述为依据,将没有出现在《公约》第13部分的活动或者已被第13部分排除的活动排除在《公约》第13部分的适用范围之外,例如J. 阿什利·罗奇在其 2021年新书中的论述,克里斯托弗·沃默斯利的论述,以及山姆·贝特曼的部分论述;三是以研究或测量对象、使用工具和技术、操作方法及成果运用等为依据,对海洋科学研究、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水文测量、军事测量等进行实质探究,据以确定《公约》相关用语的确切含义和内在联系,例如山姆·贝特曼的部分论述和张海文的论述。前两种思路更多是为相关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测量行为无需事先通知沿海国并取得沿海国同意寻找合法性依据;而第三种思路则更加关注《公约》解释与适用的时代性和发展性。
3. 问题澄清: 多元发展为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提供实证基础
“海洋科学研究”是实践性概念,需要立足国际社会的实践发展来进行理解和应用。有学者担心“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演化解释可能需要通过缔结相关协定或者着眼于国家实践等方式,经过较长时间方得实现。(61)See Hua Zhang, Redefin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UNCLOS: Could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Play Any Role? in Zou & Telesetsky, supra note 〔34〕, at 61.阿尔多·奇尔科普(Aldo Chircop)认为,海洋法和海洋科学方面的国际组织在继续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未完成的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62)参见Aldo Chircop: 《海洋知识技术的进步: 对MSR机制的意义》,载前注〔55〕,傅崐成等书,第1740页。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在海洋科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法工具、研究范围、组织实施等方面,为明确“海洋科学研究”的含义,协调《公约》相关规定的解释与适用提供实证基础。
(1) 海洋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从实践看,海洋科学研究对象包括海洋环境全域,如海洋环境整体、海洋环境内部各构成要素与各种过程、海洋资源,以及海洋环境与其他相关系统之间的联系,(63)当前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 海洋和水道的深度测量和海底测绘; 海洋、深海及其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范围与脆弱性;人为威胁叠加作用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印度洋及其与全球海洋和大气的内在联系;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潜在来源;海洋观测方案和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对监测和预报气候变化、气候多变性、地球系统预测、建立和管理海啸预警系统等方面的作用等。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291、293、295、297—298、300—302段。还包括围绕海洋、海岸、海洋生物等对相关事件、环境及生态系统偶发或持续变化等的应激反应与影响后果进行的研究。(64)当前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 研究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海洋酸化的影响,污染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后果,考虑安全、预防、应急和缓解等方面的方法,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并分享最佳做法,建立和运行区域性和国家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方面的研究,研发并传播增强型海啸信息产品;确定应对自然灾害的减灾备灾措施方面的研究;对海洋和海岸所面临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及其国际合作与协调,在了解和有效应对海洋面临的前所未有压力方面加强科学与政策衔接等。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200、245、302—305、307段。海洋科学研究从注重具体研究项目向更注重对相关系统的研究转变,并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开展彼此相互联系的各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公约》第243条规定中的“海洋环境”一词应作全面、立体、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理解。
(2) 海洋科学研究的研究内容。鉴于“海洋环境”具有立体多元、动态演变、内在联系紧密、外向辐射广阔等特点,许多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既是基础性研究,也是应用性研究,难以做严格区分。以海洋测量为例,目前仍有很大比例的海洋和水道尚未得到直接测量,而在各海洋空间进行的每一项人类活动均需依赖测深学知识,以保障该人类活动安全、维持可持续发展和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因此,联合国大会决议持续强调海道测量和海图制作对于海上航行和生命的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包括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和全球航运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65)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4—5页,第297—298段。在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框架下,有12个全球海洋观测网、12个以生物领域为重点的观测网、15个海观系统区域联盟和为该系统做出积极贡献的84个国家。参见海委会(IOC)就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二十二届会议“海洋观测”专题向秘书长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报告提交的文件。可见,随着海洋科学研究实践的发展,已经难以严格区分“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和“应用性”海洋科学研究,更不应以“是否具有应用性”作为某一观测研究活动是否属于《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的判断依据。
(3) 海洋科学研究的方法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方法、技术与工具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除现场进行海洋科学测量和研究外,还可以通过布设大型水上、水面、水下观测装置和设备,使用各种传感器、探测器和自动水下航行器等方式进行远程测量与观测,(66)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世界海洋科学现状》,2017年。通过建模等方式进行模拟、评价与预测,实现科学突破,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等。客观上,“有效的海洋科学并不仅仅包括一系列一次性项目。需采取持久的努力,监测和了解海洋环境高度动态的发展,并将这种知识应用到预测和管理决策中”。(67)参见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42(a)海洋和海洋法: 关于联合国依照大会第54/33号决议为便利大会每年审查海洋事务的发展情况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A/56/121),2001年6月22日,第5段。在同一次研究行动中,可以同时调用多种研究设备,从多个研究角度对海洋环境进行观测与研究。例如海委会(IOC)2018年第51届执委会会议准许Argo全球浮标系统增加测量六个参数,由此可以进一步提高海洋环境观测与研究的效能。(68)增加测量的六个参数是: 氧气、pH值、硝酸盐、叶绿素、反向散射和辐照度。为此,Argo浮标需要增加相应感应装置。参见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Evolving Capabilities of the Argo Profiling Float Network, IOC/EC- LI/2 Annex 9, 2018.使用船只进行观测与测量也是如此,可以应用多种仪器设备进行立体、全面、系统而又具体深入的观测与测量。(69)国际海道测量组织(IHO)《海道测量词典》对“海道测量”(Hydrographic surveys)一词的界定是: 以水体数据的测定为主要目标的测量。海道测量可包括以下一类或几类数据的测定: 水深、海底形状和底质、流向和流速、潮高和潮时、水位和用于测量和航行目标的地物、固定物标的位置。详见国际海道测量局在线海道测量词典http://www.iho-ohi.net/S32/index.php。
(4) 海洋科学研究的研究范围。鉴于海洋环境的高度动态性,测量/水文测量是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实现海洋科学研究目标的重要路径。因此,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必然应当包括以高度动态化的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水文测量。(70)如果船舶以本船在本航次的航行安全为目的,使用测深仪和雷达等手段进行海图定位,这一行为属于本航次航行附带发生的活动,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航行船舶仍应以正常合理的航行作为主要目的与表现。如果航速过慢,不断停留,甚至在某一特定区域徘徊往返,均不是正常合理的航行,其所进行的水文探测等活动均应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范畴。
(5) 海洋科学研究的组织实施。基于海洋科学研究的特点,长期、大型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和项目日渐增多,海洋科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科学研究相互交叉、密切联系的程度日益增强。因此由相关国际组织主持和组织多个国家或者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人员合作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不在少数,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实践中,组织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合作的既有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有区域性国际组织;既有政府间组织,也有专业性非政府组织,如海科委(SCOR)等。(71)一些专业性非政府间组织在海洋科学研究项目的确定、评估与具体实施等方面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南极海洋科学研究方面更为突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23条明确规定发展合作工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和海科委(SCOR)。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和海科委(SCOR)还获得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观察员”资格,在南极海洋科学研究领域持续发挥专业咨询、研究方案设计与评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参见王怡然: 《非政府组织参与南极国际治理的地位与作用》,载《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3期,第79—93页。
综上,可以将《公约》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理解为: 以实现增进对海洋及相关系统的认知,获得并有效处理海洋信息与数据,实现促进人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等目的,由《公约》缔约方、非缔约国家进行,或者由主管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以海洋环境及其进程、海洋环境内部及与外界联系等为研究对象,使用一次性或长期性、定期或持续性研究工具,通过学科内或者跨学科、特定地理区域内或者跨区域、实时信息处理或数字建模等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科学研究活动。(72)挪威代表团向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2次会议提交的提案《海洋科学及海洋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包括能力建设(挪威代表团提出)》, 以及一些区域性组织的组织文件或区域国家相关协定等对于“海洋科学研究”概念也有相似的理解。参见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2次会议《海洋科学及海洋技术的开发和转让,包括能力建设(挪威代表团提出)》(A/AC.259/4,2001年)。
(二) 厘清《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
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对《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公约》第13部分与第14部分的适用关系;二是《公约》第247条规定的适用方法;三是《公约》第13部分其他规定与《公约》其他部分有关条款的适用关系。
1. 《公约》第13部分与第14部分的整体适用关系
《公约》第13部分主要规定了沿海国同意制度,赋予沿海国绝对同意权、斟酌决定权、兜底性决定权等。《公约》第14部分主要规定了促进海洋技术发展、技术转让和提供技术援助。从适用关系上看,第13部分与第14部分是应当相互平行、各自独立适用,还是互为基础、需整体适用,《公约》对此未作明确规定。

为此,需要形成第13部分和第14部分互为基础、整体适用的清晰认识。国际社会及区域国家强调并积极推动多边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利益攸关方积极开展国际海洋科学合作,(75)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3页,第307—308段。促进《公约》第14部分的有效执行,在增加科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海洋科学研究能力,转让海洋技术,促进国际法律和政策的制定,(76)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海洋科学报告——世界海洋科学现状》,2017年。另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决议再次申明“必须通过能力建设和转让海洋技术等途径开展合作,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沿海国,既能执行《公约》,又能从海洋的可持续开发中获益,并能充分参加处理海洋和海洋法问题的全球与区域论坛和进程”, 见前注〔2〕,大会决议(A/RES/76/72),第3页。使沿海国家获益,继而增强沿海国对在其领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认可甚至期待,消除沿海国在依据《公约》第13部分决定是否同意该海洋科学研究计划时的顾虑,避免迟延。简言之,借助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海洋科学合作,明确两部分的整体适用关系,特别要使之成为《公约》第14部分与第13部分整体适用的重要连结纽带,共同实现第14部分和第13部分的缔约宗旨。
2. 第247条规定的适用方法
《公约》第247条对主管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设立了推定同意制度,是《公约》第13部分的核心条款之一。如何适用《公约》第13部分的第247条规定,也体现了沿海国和研究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如前所述,有学者主张将应用性科学研究、水文测量等排除在“海洋科学研究”范畴之外。他们似乎认为只要不被认定为“海洋科学研究”,就不需要受沿海国同意制度的约束,也不需要受到《公约》第13部分其他规定的约束。
但是,这一逻辑推理不适用于由主管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首先,主管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不同。《公约》对于主权国家作为沿海国、内陆国、船旗国等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当然适用于主管国际组织。《公约》明确规定主管国际组织有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这一权利不需要“并入”“航行自由”。其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的实施离不开国际组织成员方的共同意愿和积极支持。最后,由国际组织进行或主持的海洋科学研究往往关乎全人类福祉,可以较好地兼顾沿海国成员方的利益需求。可见,国际组织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限定“海洋科学研究”的范围与种类,绕过沿海国成员方的意愿而执意开展研究。
因此,在适用《公约》第247条规定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既照顾作为沿海国的国际组织成员的利益,又避免因沿海成员方延迟同意甚至拒绝同意,影响整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的顺利实施。对此,海委会(IOC)从一般适用和特别适用两个层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良好效果。海委会(IOC)制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47条适用程序》(Procedu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47 of the UNCLOS by the IOC of UNESCO, 2007)(以下简称《IOC第247条适用程序》),将海洋科学研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来看待,对《公约》第247条规定进行更为清晰明确、更便于操作的解读,使海委会(IOC)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得以在尽快完成第247条各项程序要求后付诸实施,避免误解和不必要的迟延。(77)详见《IOC第247条适用程序》引言和附件四。此外,还明确规定海洋数据收集系统(Ocean Data Acquisition Systems, ODAS)仍应受《公约》调整。(78)海委会(IOC)还明确了海洋数据收集系统(Ocean Data Acquisition Systems, ODAS)的性质和处理方法,认为海洋数据收集系统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方式,所使用的浮标大都属于研究全球海洋现象的国际科学方案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公约》未作具体规定,仍应使海洋数据收集系统受到《公约》的相应调整。详见《IOC第247条适用程序》附件一“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第71—74段。
针对具体的Argo项目,海委会(IOC)先后通过成员国大会第XX-6号决议(1999年)(79)《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大会第XX-6号决议(Argo项目)》(IOC Assembly Resolution XX-6: The Argo Project)。和执委会第EC-XLI.4号决议(2008年)(80)See IOC Resolution EC-XLI.4,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olution XX-6 of the IOC Assembly Regarding the Deployment of Profiling Floats in the High Sea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rgo Programme, 2008.,对Argo研究项目的相关法律事项做出具体规定,强调Argo项目应当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须在符合《公约》的场景和以符合《公约》的方式加以实施,并且不得损及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管辖权。(81)这两项决议对Argo项目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规定,包括: 通过适当渠道,将可能漂入沿海国管辖水域的Argo浮标的所有布放情况事先通知相关沿海国,指明布放的确切位置,要求海委会(IOC)执委会告诉成员国Argo浮标的漂浮位置和如何获取浮标数据,设立Argo信息中心以便利上述事项的顺利实施。《IOC第247条适用程序》作为国际组织内部操作规则,其具体内容和实际运用为《公约》第247条规定的具体适用奠定了重要的实证基础, 坚守了《公约》第247条规定的国际法效力和公约适用的权威性。这两项决议虽然在文字表述上没有提及《公约》第247条规定,但是具体内容基本遵循《公约》第247条规定,结合Argo项目特点灵活处理沿海国同意与项目研究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对《公约》第247条规定内容的具体化和高效化。该决议在实践操作中取得了非常积极的实施效果。(82)例如德国评价该项目操作规则在处理沿海国主权问题上确立了非常有效的原则和程序规则,效果非常好。See IOC/ABE-LOS REVIEW: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IOC Advisory Body of Experts on Law of the Sea (IOC/ABE-LOS), by Working-group on the Review of the IOC Advisory Body of Experts on the Law of the Sea, IOC/INF-1293, Dec. 2011. 海委会(IOC)2018年第51届执委会会议准许Argo全球浮标系统增加测量六个参数,使Argo浮标系统的优势得到最充分发挥。参见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Evolving Capabilities of the Argo Profiling Float Network, IOC/EC-LI/2 Annex 9, 2018.
3. 《公约》第13部分其他规定的适用方法
《公约》第13部分除确立沿海国同意制度外,还通过大量条款明确了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基础、原则、权利与义务、责任承担及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内容。海洋科学研究主体、对象、内容、方法、工具等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围绕“海洋科学研究”范围引起的众多争论,(83)例如《公约》第13部分应否以及如何规制使用海上浮标、水下设施的活动,相关机构和学者对此有不同观点。See Katharina Bork, Johannes Karstensen, Martin Visbeck & Andreas Zimmerman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Floats and Gliders — In Quest of a New Regime? 39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298, 298-328 (2008); see also Tobias Hofmann & Alexander Proelss, The Operation of Glider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46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67,167-187 (2015); Chuxiao Yu, Operational Oceanography as A Distinct Activity from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under UNCLOS? — An Analysis of WMO Resolution 45 (Cg-18), 143 Marine Policy 105131 (2022).均使如何适用《公约》第13部分规定成为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中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部分学者主张将测量、应用性研究等排除在“海洋科学研究”范围之外,目的是排除《公约》第13部分沿海国同意制度对该测量活动、应用性研究活动的约束。然而,这一主张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不论研究目的有何不同,这些测量活动、应用性研究活动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海洋科学研究”并无明显差异,研究行为对海洋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风险亦无不同。因此,如果像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将测量、应用性研究排除在“海洋科学研究”范围之外,还会产生《公约》第13部分其他规定也被排除适用的结果,进而使此类活动不受任何约束,相关主体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关争端缺乏解决路径,进而使研究方与沿海国之间出现严重的利益失衡,使海洋环境面临不受约束的损害风险等。这一结果显然会架空《公约》第13部分的具体规则,背离《公约》宗旨,置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利益于风险之中,也不利于《公约》“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等目标的实现。(84)详见《公约》序言。
因此,有必要考虑对《公约》第13部分和《公约》其他部分的规定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并赋予《公约》第13部分一般性、基本性规定以优先适用的地位,使每一项以海洋环境为对象的研究活动都有法可依,每一项研究活动均受到必要、基本的约束。
对《公约》相关条款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是有条约解释依据的。从文字表述看,《公约》起草者的意图是将《公约》第13部分与《公约》其他部分相关规定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公约》第13部分中,除第3节第246、248、249、252、253和254条相互之间进行交叉援引外,许多条款直接使用“本公约”这样的措辞,(85)使用“本公约”措辞的《公约》第13部分主要条款有: 第238、239、240、242、244、246、254、257、258、260、263条等。相关表述为“按照”本公约,“符合”本公约,“不影响”本公约,“在”本公约“限制下”,“依”本公约,“遵守”本公约等。第246、256和263条等条款还指向了第5部分“专属经济区”(如第60条)、第6部分“大陆架”(如第77条和第80条)、第11部分“区域”、第12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如第235条)。与此相对应,《公约》其他部分的相关条款也指向或提及“海洋科学研究”或“研究”。(86)具体包括: 《公约》第2部分(如第19条和第21条)、第3部分(如第40条)、第4部分(如第54条)、第5部分(如第56条)、第7部分(如第87条)、第9部分(如第123条)、第11部分(如第143条)、第12部分(如第200条)等。其中,第143条更是明确规定“区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应当按照第13部分进行。
可见,《公约》第13部分的规定与《公约》其他部分的相关规定具有整体理解和适用的制度基础。在适用时,一方面,应当将第13部分所规定的“海洋科学研究”作为一般性、基础性概念,尽量涵盖所有以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应当将第13部分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相关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多数条款作为一般性、基础性规定,适用于所有海洋科学研究活动。(87)《公约》第13部分具有一般性、基础性特征的条款贯穿各节,主要包括: 第一节“一般规定”各条款,第二节“国际合作”各条款,第三节“海洋科学研究的进行和促进”中除沿海国“同意”判定依据外的其他条款,包括第246条第3款对于海洋科学研究“专为和平目的”“谋全人类利益”的要求、第5款沿海国享有斟酌决定权的触发条件、第8款中不应“有不当的干扰”的要求、第249条对于海洋科学研究应当遵守相关条件的要求、第250条通知研究计划的要求、第251条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的要求、第253条暂停或停止具体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触发条件和操作要求、第254条邻近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享有的权利、第255条“便利海洋科学研究和协助研究船的措施”等,以及第四节“海洋环境中科学研究设施或装备”各条款,第五节“责任”各条款,第六节有关争端解决和临时措施的相关规定等。同时,在对《公约》第13部分与《公约》其他部分相关规定进行整体理解与适用及交叉指引的基础上,《公约》第13部分的一般性、基础性规定依然适用于以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但是未被定性为“海洋科学研究”的研究活动。(88)海法司(DOALOS)的爱丽丝·希库布伦迪(Alice Hicuburundi)女士在其发言中提出了相似的想法。她指出,对于海洋数据收集行为的性质及法律适用问题尚无一致意见,大家目前一致的想法是只对Argo项目的实践操作制定操作指南。此外,《公约》规定,特别是第13部分确立的适用于海洋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可以为如何界定这些研究活动的实践操作提供指引。《公约》第13部分第1节、第2节可以比照适用于应用性海洋学研究,第4节、第5节和第6节也可以提供指引。See Annex 8 Operational Activities and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under UNCLOS, of Final Report (Rev. 2), Technical Workshop: Enhancing Ocean Observations and Research, and the Free Exchange of Data, to Foster Service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Ocean-Safe), A Contribution to the Planning Phase (2019-2020)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Ocea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2030), 2019.
(三) 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公约》除在海洋科学研究的基础、原则、权利与义务、责任承担及争端解决等方面确立诸多具体规则外,还通过第251条(89)《公约》第251条“一般准则和方针”规定:“各国应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一般准则和方针的制定,以协助各国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和第271条(90)《公约》第271条“方针、准则和标准”规定:“各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在双边基础上或在国际组织或其他机构的范围内,并在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的情况下,促进制定海洋技术转让方面的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特别“要求”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一般准则、方针(和标准)的制定,以协助各国确定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影响,以及为海洋技术转让奠定良好基础。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趋势下,制定准则、方针的行为具有什么特点,对《公约》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的发展有何影响,值得观察和思考。
首先,主管国际组织不负有制定“准则、方针”的强制性义务。从文字表述看,《公约》第251条未直接规定由主管国际组织“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而是要求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设法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第271条规定了两条路径,一是由各国直接在双边基础上促进制定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二是各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或其他机构的范围内,促进制定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可见,《公约》第251条和第271条更像是“政策声明”,(91)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675—676页。未对主管国际组织设定强制性义务。
其次,主管国际组织是制定“准则、方针”的积极推动者。从第251条和第271条规定看,《公约》意图制定较具普遍性的准则、方针。显然,个别国家的国家实践还不足以成为广为接受的一般准则、方针。通过较具代表性的主管国际组织来确立相关准则、方针,可以满足《公约》的上述要求。《公约》谈判方希望主管国际组织在相关准则、方针的制定上发挥积极作用。与此相对应,希望各国积极配合,充分参与由主管国际组织围绕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议题组织的讨论和决策,使其所制定的准则和方针彰显公约宗旨、平衡各方利益和体现广泛意志,从而实现《公约》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的重要目标。
再次,主管国际组织通过“一般准则和方针”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第251条和第271条均使用了较为宽泛的措辞“一般准则和方针”/“一般接受的方针、准则和标准”,也没有特指哪个国际组织是主管国际组织。因此,应当采用通常理解,具有相应职能的国际组织均可成为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的主管国际组织。(92)有观点认为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在执行第251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见前注〔15〕,诺德奎斯特书,第536页。随着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多元化,主管国际组织的范围会日益扩大,继而使相关准则、方针、标准的制定更加多样化。从实践看,相关国际组织已经制定或促进制定了许多“准则和方针”。例如,海委会(IOC)先后制定了四项主要准则和方针;(93)包括: (1) IOC: Resolution XX-6: the Argo Project, the 20th Executive Council, 1999; (2) IOC Criteria and Guidelines on the Transfer of Marine Technology, 2005; (3) Procedu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47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 2007; (4) IOC: Resolution EC-XLI.4: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olution XX-6 of the IOC Assembly Regarding the Deployment of Profiling Floats in the High Sea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rgo Programme, 2008.海法司(DOALOS)2010年制定通过了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 Revised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OSPAR Commission)于2008年制定通过了OSPAR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Marine Research in the Deep Seas and High Seas of the OSPAR Maritime Area等。虽然在性质上,这些准则与方针具有软法性质,不能产生修订《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则的法律效力,但是它们可以成为解释与适用海洋科学研究相关国际法规则的重要论据和实践,使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内容更加具体,规则适用更具有针对性。因此,客观地看,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可以产生丰富、拓展规则体系相关内容,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发展的实际效果,(94)有学者认为,主管国际组织在通过软法来弥补海洋科学研究法律和政策的不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Aldo Chircop: 《海洋知识技术的进步: 对MSR机制的意义》,载前注〔55〕,傅崐成等书,第1740页。甚至可能促进和推动相关国际法规则在条约法层面的变革。(95)在笔者看来,较有可能形成突破的是海洋观测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Ocean Observing Data Collection)的规则体系。海洋观测数据收集与处理是联合国非正式协商工作2022年主题。
四、 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风险及中国方案
国际社会倚重国际组织多方位介入,使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特点日趋明显,在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碎片化风险也日益凸显。
(一) 国际法碎片化与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
国际法的范围因多种原因而急剧扩展。国际法的人本化现象直接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法的新分支,(96)有关国际法人本化发展趋势的研究,参见曾令良: 《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89—103页。多边条约活动的数量成倍增长,同时产生了各种程度不同的治理机制。(97)See Finalized by Mr. Martti Koskenniemi,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ocument A/CN.4/L.682 and Add.1, 2006, p.10.这种扩展使国际社会在活动和结构等方面产生了专门化和相对自主的领域,(98)Se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58th Session, General Assembly Official Records 61 Sessions Supplement No.10 (A/61/10), 2006, para.242, p.403.使国际法体系充满了法律一体化程度各不相同的全球性、区域性甚至双边性的体系、小体系和微体系。(99)See Gerhard Hafner, Risks Ensuing from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its fifty-second session,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55th Session, Supplement No.10, 2000, p.143.这被称为国际法碎片化(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现象。(100)“国际法的碎片化”一词直译自英语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联合国大会及国际法委员会相关文件的中文版本中使用“国际法不成体系”这一译法,参见国际法委员会第52届会议所审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文版本《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第58届会议所审议的研究组报告中文版本《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 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工作报告中文版本第12章“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 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等。古祖雪教授提出,将英语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译为“国际法不成体系”,似有否认国际法是一个法律体系之嫌,因此采用其英语直译“国际法的碎片化”。参见古祖雪: 《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5页。本文采用直译。
国际法的碎片化是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有其积极的方面,(101)伴随这一现象出现了各种专门的和相对自足的规则或规则体系、法律机构和法律实践。See Koskenniemi, supra note 〔96〕, at 10.但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例如担忧专门体系与其他体系及整个国际法体系之间会不会出现规则解释与适用上的矛盾、实施方面的冲突等。(102)See Gerhard Hafner, Pros and Cons Ensuing from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25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49, 856-858(2004). See also Malcolm N. Shaw QC,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8-49.国际法碎片化还会直接导致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使机制规则模糊,规范效应降低,产生权力政治博弈与非正式治理等。(103)参见王明国: 《机制碎片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第11—13页。以区域贸易规则及治理机制对多边贸易规则及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例,呈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区域性规则及治理机制使多边规则的适用效力和多边机制的治理效果受到影响,削弱多边规则及治理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利于多边体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104)著名学者约斯特·鲍威林(Joost Pauwelyn)以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关系为视角,对国际公法规则冲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比] 约斯特·鲍威林: 《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周丽瑛、马静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有关区域贸易协定整体上与WTO规则相符性问题,参见徐崇利: 《“政治性国际贸易争端”的裁判解决》,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4—115页;陈海波: 《世贸组织协议在欧盟法中的法律地位——欧共体法院在区域一体化抗拒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1卷),2004年第4期,第141—164页;陈海波: 《WTO对RTAs的法律约束》,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二) 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碎片化的主要表现
海洋法规则体系和海洋治理方面呈现出的碎片化,是国际法碎片化与全球治理碎片化的突出体现。(105)学者认为,《公约》自身存在严重的局限性,特别是《公约》的分区主义立法进路与海洋统一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公约》的功能主义管理路径与整合性治理之间的矛盾等,国际性、区域性海洋组织的分散性与国际立法的不成体系性,以及缔约国的履约意愿与合规性问题等,是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的主要根源。参见郑志华、宋小艺: 《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的挑战与因应之道》,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年第1期,第175—178页。
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趋势下,主管国际组织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功能不一,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与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参与主体各异。各主体对相关规则与要求的解释和适用不相一致,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不尽相同,难以实现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与保护海洋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利益冲突难以协调,由此带来的规则体系碎片化和海洋治理碎片化问题将日渐突出,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
1. 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的碎片化
如上所述,《公约》没有界定“海洋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对于海洋科学研究行为的基本权利、义务、责任承担等的基本要求不明确,第13部分、第14部分以及相关具体规定的适用关系不清晰。在多元发展趋势下,不同国际组织的组织文件或相关条约的规定不相一致,相关国家的主张与实践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通过主管国际组织制定的“一般准则和方针”也可能存在差异,从而会导致具体研究行为的法律规则适用不明确、不一致,甚至存在规则适用冲突或规制真空的情形。(106)在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中,国际法院通过审查,发现案涉《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Whaling)未对“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进行界定。但是,由于《公约》并未界定(海洋)“科学研究”,针对诉讼方有关“科学研究”定义的控辩,国际法院未能参考《公约》的规定。这实为规制真空的一种体现。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4, p.226.
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碎片化会产生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例如,所援引的具体规则不相一致,易使当事国或国际组织无所适从;相关规则适用或决策决定未能代表多数国家的意志,影响规制效力,使具体规则或决策决定失去法律确信和权威性,不利于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及相关国际合作的顺利开展。(107)在海委会(IOC)的问卷调查中,参与调查的成员国所占比例不高,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有不少明确表示对相关事项毫不知情,或者对相关规则素有疑问,甚至对海委会(IOC)相关机构解决《公约》法律问题的能力和效果不予信任。See IOC/ABE-LOS REVIEW: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IOC Advisory Body of Experts on Law of the Sea (IOC/ABE-LOS), by Working-group on the review of the IOC Advisory Body of Experts on the Law of the Sea, IOC/INF-1293, Dec.2011.同一国家如果身处《公约》规则体系和围绕某一主管国际组织所构建的另一规则体系之中,在这两个规则体系均须遵守但是规范内容相互矛盾甚至排斥的情况下,该国将因遵守其中一个规则体系的规范要求,而不得不“挑战”另一规则体系的规范要求,为此承担国家责任甚至引发国际争端。
2. 海洋科学研究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下,同一国际组织可以同时进行或主持多个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同一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来组织或承担。大型海洋科学研究项目可能会嵌套若干小型海洋科学研究项目,组织、承担的国际组织相互交织。海洋科学研究主管国际组织可以是全球性组织或区域组织,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各类国际组织在进行、主持、促进海洋科学研究时,或者在协调国际合作、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时,将遵循各自的组织文件和议事决策机制安排,组织行为、决策过程与结果可能呈现差异性,对海洋科学研究项目以及相关国际合作和准则方针制定等将产生不确定性和潜在冲突的风险。
如果该主管国际组织自身设有争端解决机制,还可能产生相同的争端方将彼此之间的争端交由不同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解决的情形。这种情况下,不同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判断标准、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争端解决的结果等均可能有所不同,同样产生治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甚至潜在矛盾。(108)例如在(国际法院)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国际海洋法法庭)剑鱼案(智利诉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剑鱼案(欧共体诉智利)中,争端方就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See ICJ,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https://www.icj-cij.org/en/case/148; ITLOS, Case Concern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Swordfish Stocks in the South-Eastern Pacific Ocean (Chile/European Union), https://www.itlos.org/en/main/cases/list-of-cases/case-no-7/;WTO DS193: Chile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Transit and Importing of Swordfish,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193_e.htm.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 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发展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和相关学者均提出,可以通过条约解释的方法来维护国际法体系的整体性。(109)See Koskenniemi, supra note 〔96〕;参见冯寿波: 《论条约解释对国际法体系的维护——以VCLT第31.3条(c)项为例》,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32—42页。这是一种“事后”方法,即对已经制定甚至生效的条约进行适当解释来维护整体性。因此,还应寻求“预先”方法。国际法不能脱离和改变其“国家间”属性。(110)见前注〔95〕,曾令良文,第103页。国际法碎片化和治理机制碎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需要通过“国家间”协议、认可与合作来予以一定程度的避免和消除。国际社会应当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相关机制的设计、建构时期,以及主管国际组织处理海洋科学研究相关事项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避免潜在矛盾,减少不协调的方面,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和冲突的激烈程度。
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作为海洋科学研究积极参与者,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不断提升海洋科学研究能力和海洋技术水平,实现了几乎从零起步到跟跑、并跑,再到某些方面领跑的跨越式发展。(111)参见陈连增、雷波: 《中国海洋科学技术发展70年》,载《海洋学报》2019年第10期,第3页。中国积累了丰富经验,海洋治理能力有极大提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参与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500多项国际公约,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议程设置权全面提升。(112)参见王毅: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华章》,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3日,第07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继续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海洋科学研究发展情况,(113)中国学者通过对标世界发达国家,提出当前中国海洋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海洋物质能量循环、跨圈层流固耦合、海洋生命过程、健康海洋、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快速变化的极地系统等方面。参见吴立新等: 《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载《地学前缘》2022年第5期。不断提升中国海洋科学研究能力与发展水平。同时继续发挥优势,结合自身最佳实践,在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情势下趋利避害,为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可以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 积极支持、参与“海洋十年”行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海洋十年”行动目标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且突出了人类迅速行动全面认识海洋、可持续利用海洋、有效保护海洋的紧迫性,是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和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指引。

3. 坚持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整体适用原则,积极推动海委会(IOC)和海法司(DOALOS)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公约》强调整体性,这原本是对碎片化风险的一种预防。但是,如果《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相互割裂,未能整体适用,依然会产生碎片化风险,与《公约》的初衷相背离。因此,需要提炼并整体适用一般性规则。对于特殊情形,则可以针对具体研究项目,在主管国际组织层面消除分歧,形成共识,进而得以有效实施。需要推动海委会(IOC)和海法司(DOALOS)共同促进制定既体现国际法精神与基本规范,又贴合海洋科学研究实践的一般准则和方针。(120)这一适用方法与海委会(IOC)《IOC第247条适用程序》的操作方针相似。《IOC第247条适用程序》第7—10条列出征询和获得沿海国同意或默示同意的具体情形。第11条强调该程序规则应当以符合《公约》规定的程度和方式进行解释,相关条款不得损及各国依据国际海洋法,特别是依据《公约》所享有的权利、管辖权和所承担的义务。将海委会(IOC)和海法司(DOALOS)作为起主导作用的少数机构,还可以避免“准则和方针”制定方过多,这些“准则和方针”相互之间发生重叠或真空等情形,不利于彰显“准则和方针”的权威性和广泛接受性。(121)联合国系统内设立了机构间协调机制,使海委会(IOC)具有更广泛的权力,以避免在系统内各机构间发生类似的重叠或真空等情形。See ICSPRO Agreement, UNESCO IOC/INF-785, p.17-18.其他主管国际组织促进制定相关准则和方针,可以通过最佳实践方面的交流,确定其是否可以吸收为海委会(IOC)和海法司(DOALOS)层面的“一般准则和方针”,有助于该准则和方针在联合国框架内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和实践。这一操作方法,还可以真正发挥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作用,通过具体实践来更科学地解释和适用《公约》规定,推动人类更好地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
4. 积极推进能力建设,在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方面大有作为。我国海洋科学研究发展尚不均衡,面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需要全面推进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工作: (1) 以项目为支撑,开展广泛深入的海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投入多层次科研力量,并特别注重吸收年轻研究人员和跨学科研究人员参与研究;(2) 以培训为重要补充,对外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国际合作义务,对内为自我提升奠定人才基础,因此要特别关注跨区域的专业培训;(3) 注重研究成果转化,需要有专业机构和人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应用与跟踪;(4) 设立对外代表国家的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为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以及执行《公约》相关规定奠定必要基础;(5) 积极参加解释、适用、修改《公约》相关规定,以及主管国际组织促进制定“一般准则和方针”的活动,并注重国际国内立法研究成果的转化。
中国科学家明确提出,海洋科学是战略科学,海洋科学实力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发达的海洋科技是创新型国家的标志。(122)见前注〔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书。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的重要方面,要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123)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8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10月15日致2019年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贺信;2018年6月12日至14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2021年11月22日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2022年4月10日至13日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的内容。现在正值联合国“海洋十年”,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在专为和平目的和全人类利益理念的《公约》践行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方向和脉络,加快推进海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在推动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为全人类利益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构筑重要规则基础方面,做出中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