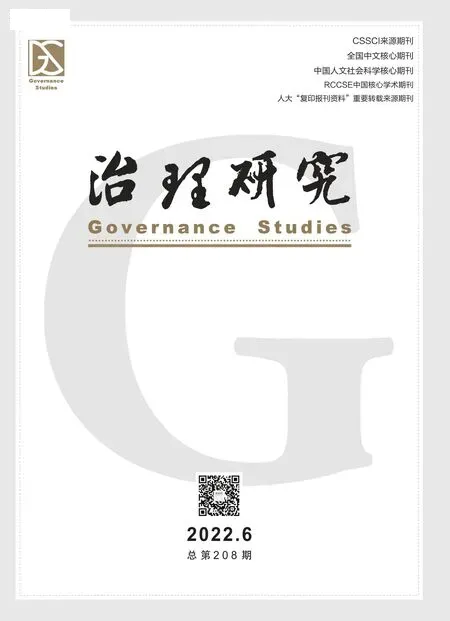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表达
□ 包大为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并非是法国哲学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对政治伦理的又一种拒斥,而是当代法国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及其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公共反思。二战之前,这种公共反思的历史主义特征明显,黑格尔主义与青年马克思哲学交替介入了文本与现实的伦理批判。二战之后,作为科学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不仅使得阿尔都塞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对作为丑闻之展现的“政治哲学”(1)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的批判,更使得资本主义治理技艺成为了理解社会征候的关键。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及其规训一方面在表象层面借由自由主义话语“化整为零”,另一方面则在事实层面成为超结构的压抑性力量(2)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这种力量不仅成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新社会的首要阻碍,更促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从近代至今伴随始终的历史主义和政治哲学的特质。
一、历史主义:黑格尔“幽灵”之下
在当代法国哲学中,似乎不会再有人怀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法语经验的形成历史中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重要作用了。一方面,辩证法的介入提供了结构主义之外的思想和方法资源,使得试图超越文化之既有确定性的激进思潮得到安置;另一方面,辩证法又成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反思革命正反经验的新视角,提供了在意识形态压制下突破社会结构的思想动力。但是,在近似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法国激进左翼思潮的叙事中,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特征是模糊的。因为读者大多会强调激进左翼与解构主义的内在勾连,将其视为与19世纪断裂的未竟事业——不断地撕裂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意义系统、指向必然未知的革命远方。但是,这种以拒斥和解构展露出强烈的否定性表征的政治哲学或“元政治学”,事实上有着极为深刻的辩证法的前提。被阿兰·巴迪欧称之为“事件”的东西,尽管被一些读者简单地断言为革命本身,事实上也是主体以自身为中介反思价值的重要条件。在斯宾诺莎所表述的作为现代价值基点的“自我持存”之外,主体需要以黑格尔式的进路,在否定性之中克服自我,才能够去展望类似黑格尔现象学之起点的自由。(3)Alain Badiou, Quel communisme: Entretien avec Peter Engelmann, Paris: Bayard, 2015, p.23.

这种理论特质体现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极为“出众”的激进性,即对历史现状的单纯否定,以及对替代方案的大胆建构。这种激进性显然极易演变成列宁所说的“左翼幼稚性”,即由于对历史客观性的忽视而导致的理论的极端和实践的冒进。事实上,早期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和茹尔·盖得的经济决定论就无法得到马克思本人的认同,以至于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7)马克思所说的“ce qu'il y a de certain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被恩格斯多次在信件中提及,其中包括1882年11月写给伯恩施坦、1890年8月写给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9月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586、590页。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甚至认为马克思所批判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mysticisme panthéiste logique)在现代的最后回声并非来自于唯心主义,而是来自盖得所提出的“人正在成为上帝”的口号。(8)Jacques D’Hondt, De Hegel à Marx,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p.178.由于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机械论传统,19世纪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混淆为泛神论,另一方面又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了起来。马克思所构想的历史科学或是被定义为社会结构进行整体替换的整治方案,或是被理解为某种历史极致背后绝对理性般的狡计。因此,这种具有机械性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寻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身份,但却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而黑格尔哲学,成为了让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否定之否定地思考政治的关键因素,以至于梅洛庞蒂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意志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内的19世纪所有伟大的哲学理论都起源于黑格尔。(9)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trans. by Hubert Dreyfus and Patricia Allen Dreyfu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63.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法国的学院派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对黑格尔兴趣索然。(10)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最初郑重地将黑格尔引入当代法国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群体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反传统学者。其中安德烈·布雷东在1920年代的著作中对黑格尔哲学的大量引用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更吸引了艺术界和善于为建构新社会而冒险的法国民众的关注。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布雷东认为黑格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在“道德领域”产生于自为意志与自在的普遍意志之间的矛盾,而这恰好能够支持超现实主义。(11)André Breton, Manifestoes of Surrealism, Trans by Richard Seaver, Helen Lan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p.138.
事实上,真正将黑格尔哲学系统引入法国哲学界,并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辩证地、历史地思考政治的学者,则是亚历山大·科耶夫和让·伊波利特。他们对《精神现象学》和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研究,最终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复兴,乃至60年代结构主义兴起的知识资源。(12)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科耶夫对主奴辩证法的重释,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得以在经济还原论之外展望另一种关于阶级斗争历史的解读路径,并且产生出一种基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义。但是,科耶夫和曾经主持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亚历山大·科瓦雷所引入的黑格尔哲学,却始终带着浓重的早期海德格尔色彩。另外,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暗含的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意图,无法被并不熟稔19世纪德国思想历程的法国读者所辨识。桑希尔曾总结过这两种意图在政治领域的相似性,浪漫主义如同历史主义,基于对启蒙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试图挑战理性化的权利-自然主义和宪法主义,同时力求阐明法律和国家背后充满生机的、融合的和文化的源头。(13)Chris Thornhill, Germ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Metaphysics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42.而科耶夫所描绘的普遍的法权人格,既是对《精神现象学》的发展,也十分接近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在德国的最终形式,即谢林的启示哲学与人格主义(personalism)。(14)Chris Thornhill, Germ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Metaphysics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58.
真正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的是让·瓦尔,尤其是伊波利特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甚至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源头也须追溯到伊波利特对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的关注。尤其因为伊波利特试图纠正实证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对黑格尔的误解。法国马克思主义最初所表现出的激进是两个方面的,或是在实证主义影响下拒斥辩证法,或是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倾向于空想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伊波利特则告诫人们必须重视《精神现象学》,因为正是这一文本将具体事件(événements concrets)或特殊性(singuliers)与普遍理念(idées universelles)融合起来。当时,一些人倾向于指责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玩弄语词游戏(logomachie),让具体的历史委身于逻辑;也有一些人指责黑格尔以历史事件来污染理念。但是这两种指责都忽略了黑格尔划时代的创新性,即统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努力。(15)Jean Hyppolite, études sur Marx et Hegel, Paris: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65, pp.46-47.另一方面,伊波利特试图通过对黑格尔中前期哲学的着重解读,让人们看到黑格尔哲学或辩证法所蕴含的革命性。伊波利特认为黑格尔用天才般的辩证法去洞察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时代,并由此把握了这个世界终极的矛盾形式——那些酝酿着危机的风暴。(16)Jean Hyppolite, études sur Marx et Hegel, Paris: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65, p.86.他同时肯定了青年马克思所揭示的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悖论,即黑格尔“演绎”立法权的法哲学是为了调和无组织的群众(la masse inorganisée)和国家权力,而马克思很清楚看到在法国大革命语境下这种国家哲学与普鲁士政治现状的矛盾,因此德国领先其他国家的“理念革命”,必须被无产阶级扬弃自身的实践承接过去,而不是仅仅在哲学家的大脑中发酵。(17)Jean Hyppolite, études sur Marx et Hegel, Paris: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65, p.136.
伊波利特解读黑格尔哲学所选取文本和视角,使得他融合黑格尔国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遭到了质疑。从1940年代开始作为社会主义同情者(sympathisant)的伊波利特在战后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新黑格尔主义的首要目标。首先开火的是青年阿尔都塞,他在1950年发表了《回到黑格尔:对学院派修正主义的最后评价》,在该论文中,阿尔都塞之所以将伊波利特称为试图削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骗子”(mystificateur),是因为他虚构了“黑格尔的真实历史本质”。(18)Louis Althusser, Le Retour à Hegel. Dernier mot du Révisionnisme Universitaire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t. I, Paris: Stock- IMEC, 1997, p.259.与其相反,让·瓦尔则在黑格尔的哲学家形象背后看到的是一位神学家。(19)Jean Wahl , 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p.1.他试图从更具有宗教意味的角度具体阐述苦恼意识,这推动了天主教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哲学的形成。瓦尔并没有冒险以黑格尔的概念替换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而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国哲学界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接受程度——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成为一种方法之前,是一种将意识从意见转变为概念的一种体验。瓦尔认为人类为了实现普遍性,经历了18世纪以来试图完成无尽欲求的生产革命和克服自我对立(异化)的政治革命,但是直至今日仍然相去甚远。因为只有当所有对立面都被克服,普遍性被真正实现的时候,苦难意识及其痛苦才能被终结。(20)Jean Wahl , 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p.52.瓦尔转述的黑格尔历史主义最终引起的是自由主义者的共鸣,并且在上世纪末对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提出巨大的挑战。其代表人物就是马塞尔·高歇,他认为黑格尔通过历史性将人类经验带回了绝对的轨道,在人类通向未来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应该被理解为启示的不同阶段。处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中的我们之所以处在历史的结尾(la fin de l'histoire)(21)Marcel Gauchet, La Religion dans la Democratie: Parcours de la Laicite, Paris: Gallimard, 2001, p.25.——抑或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终结”,是因为抽象权利已经实现了自我意识,为承认而展开的殊死战斗已经结束。
最终,尽管侧重点和意图各不相同,科耶夫、让·瓦尔与伊波利特等学者掀起的法国新黑格尔主义思潮毋庸置疑催生了辩证法的新传统,进而影响了此后一个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乃至成为法国激进左翼和毛主义政治思潮的新起点。他们一方面反思过去政治经验中显现的阶级异化的症候,即局限于本阶级利益的极端革命热情(22)Jean Hyppolite, études sur Marx et Hegel, Paris: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65, p.115.;另一方面认识到消灭哲学和克服异化的历史任务需要“最后的工具”——无产阶级。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以黑格尔为中介成为一种新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治哲学,曾经以社会结构否定历史、以经济机制否定主体意识、以科学断言哲学终结的方法也就开始式微了。
二、历史科学:青年马克思的“遗产”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政治和理论斗争中能够凭借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他们需要面对巴黎公社失败和第二国际分裂所带来的内外挑战。除了资产阶级政府,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工联主义交织成不可回避的舆论障碍。另一方面,在理论中可以作为论据的马克思文本的译介又颇为滞后。当埃米尔·波蒂热利(Emile Bottigelli)在1968年重新译介了《巴黎手稿》,阿尔都塞不由地感叹,莫利托版本的“漏洞百出、谬误丛生”的节译本,总算有了更好的替代版本。在此反映出从1930年代直至196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缺乏可靠文本的窘境,以至于根据莫斯科版本的MEGA编排翻译的《巴黎手稿》全本的出版成为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2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5页。但是,除了文本困境,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的讨论,主要还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理论外部的伦理学勾联,二是理论内部的断裂(即两个马克思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仍然遭受着唯心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对政治哲学的纠缠。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围绕《巴黎手稿》和青年马克思的两个论战。波斯特所勾勒出的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征也许能够反映出这两个论战的历史语境。在战时十分清晰的“敌我界限”,到了战后却愈发模糊,越来越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也开始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因为这一标签不仅能够赢得人民的支持,更能通过战时的反抗斗争“积累”急需的合法性。一时间出现了人本主义的、伦理学的乃至天主教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都十分倚重于《巴黎手稿》和异化概念,而法国共产党迟钝且教条的回击却着重宣传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异化哲学。真正“严肃地对待和批判异化概念的神奇魔力”的哲学家是路易·阿尔都塞。(24)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至今为止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仍然从多个方面受益于阿尔都塞对战后浮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和伦理学特征的三个维度的批判。
首先,对作为伦理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这种在阿兰·巴迪欧那里仍在不断发展和弥散的批判,追溯到阿尔都塞那里则更为集中和明确——保卫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将“躲在”异化概念和青年马克思肖像背后的政治哲学予以暴露和批驳。这种伦理化的倾向或是表现为将黑格尔的历史的内在主义(L'immanentisme historique)植入马克思主义(25)Jacques D’Hondt, De Hegel à Marx,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p.162.,试图调和资本主义现实与启蒙理想;或是认为异化及其苦恼意识的最终扬弃只能通过返回主体意识——只有让尤利西斯讴歌奥德修斯,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26)Jean Wahl , 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p.15.总之,在战后法国政治哲学总体上亲近马克思主义的乐观局势下,隐含着将革命、历史必然性和阶级斗争等核心概念抽离的理论危机。因此,在阿尔都塞肯定波蒂热利重译《巴黎手稿》的词句中,他总结了1930-1960之间“攻击和保卫马克思”的特点和不足。《巴黎手稿》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法国各种马克思主义之间“战斗的论据、争执的口实和防守的堡垒”。这本著作最初由社会民主党人(兰茨胡特和迈耶尔)捧场,接着又受到唯灵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家的捧场。但是,这些《巴黎手稿》“追捧者”的理论却是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点“格格不入的”——他们声称人们在这本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通过“伦理学、人本学(二者是一回事)”,乃至从宗教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2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6页。而最初的“追捧者”兰茨胡特和迈耶尔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资本论》是一种伦理学的理论,在《资本论》里保持沉默的哲学只是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里才大声说话”(28)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页。。而针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中愈发得以自明的人道主义的、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官方理论家们,却“恐惧和急躁”地作出了不恰当的回应——全盘地肯定马克思,并接过论敌的论点去为《资本论》辩护,从而“过分地抬高了手稿的理论地位”(29)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6页。。
其次,肯定青年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裂变,支持以科学扬弃哲学的理论革命。在今人看来,对《巴黎手稿》、异化概念和人道主义的辩论也许只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但是在阿尔都塞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辩论的结果“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30)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6页。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上,饶勒斯(Jean Jaures)通过死亡证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道德联盟的无效性,其实践的限度在其早期理论意图中就已经颇为明确了,那就是在路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那里寻找社会主义的根源,并且把财产权让位于人权作为政治斗争的最终目标。(31)Madeleine Rebérioux, Jaurès, La Parole et l’acte, Paris: Gallimard, 1994, p.52.在战后法国,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又开始陷入了饶勒斯式的困境,既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东方政治经验,又无法抛却具有道德外观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主义不可能成为欧洲的革命理论,为了说明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必须在文本和概念中发掘出适合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哲学。(32)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张金鹏、陈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随着《巴黎手稿》引起了对青年马克思的重新理解,如何看待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法国知识界的辩论主题。而在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国家哲学愿景中人们会十分容易地将一些辩证结构全盘移植到马克思对政治和革命的理解中,甚至很难拒绝认同马克思主义所引向的是一种弥赛亚主义的伦理愿景。阿尔都塞认为这些被黑格尔主义波及的粗心读者实际上没有分清青年黑格尔派的革命要素和马克思所发展出来的新的辩证结构之间的区别。青年黑格尔派发展了黑格尔两方面的革命要素,一是“历史是自由和理性的实现的观念”;二是将历史视为一个辩证的过程,因此历史没有终结并且还有希望的观念。国家应该变成自由的国家,历史应该产生出还不存在的自由。但是马克思从这两点发展出来的革命理论则呈现出三个环节:(1)全面接受这种黑格尔自由左派的观念;(2)这种自由理论被一种乌托邦的和道德的革命理论即异化的理论所取代;(3)最后的形式,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革命观。(33)路易·阿尔都塞:《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1955-1972年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巴黎手稿》、异化概念、政治伦理或者人道主义完全无法满足马克思的抱负,即完成对历史哲学的拒绝,并且,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奠定基础。
最后,批判对青年马克思政治意图和理论意图的混淆,并由此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划定界限。在1960年代,对青年马克思与《巴黎手稿》的历史属性的判断,几乎成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个标准。法国共产党与斯大林主义的支持者始终坚持《巴黎手稿》与马克思晚期政治经济批判的一致性,而政治伦理学家与黑格尔主义者又试图将晚年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视为背离哲学的罪状。在阿尔都塞看来,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搞混淆了”。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巴黎手稿》是《资本论》的先声,是一部“灵感奔放时的神来之笔,往往比完成了的作品更加宏伟”。同时正如波蒂热利所言,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著作说明他已经投入了拥护无产阶级的事业。(34)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9-151页。但是从消极的角度而言,《巴黎手稿》体现了“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他为了完成与哲学的决裂,“让哲学去碰运气,去碰最后一次运气”——他赋予了哲学对它的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这个失败最重要的方面体现为他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政治经济学接受了下来,而对其展开的系统批判和改造则是1845年之后的工作。(35)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0页。
因此,1940年代以来关于青年马克思与《巴黎手稿》的争论,最终使得人们逐渐理解青年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一种看似悖论式的共存状态,即“一个人可以是共产主义者,而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36)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1页。马克思主义用以说明历史科学的理论,虽然在1844年之前并没有被确立,但是却深刻地说明了1844年之前马克思所参与的——甚至更早之前的共产主义运动。那种“把各种观念随意地联结起来,或者对各种术语作简单的比较,而对文章本身却缺少历史的分析”(3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页。的做法,到了1960年代之后已经连同教条化的斯大林主义被人们辨识和离弃。而《巴黎手稿》与异化概念所蕴含的研究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方法,则与法国实证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在结构主义的思潮中涌现出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成果。例如康吉莱姆通过以科学形式理性地把握了对象,体现了理性主义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可能性。(38)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惊讶或不安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列宁在半个世纪之前,早就在那些谁都说得出来的著作中指出了这一点”。参见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李春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286页。康吉莱姆及其深受辩证唯物主义熏陶的科学主义研究,为当下法国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唯物主义的火种,使得马克思“扬弃哲学”的方法论在当下法国政治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39)福柯认为,离开康吉莱姆就无法更好地理解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无法更好地理解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所进行的一系列讨论。而阿兰·巴迪欧从侧面印证了福柯的这一评价,他坦陈正是康吉莱姆教会他如何用哲学来理解科学。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论》,蓝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同时,虽然吸收了拉康主义术语和结构主义方法,阿尔都塞还是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开辟出一种政治科学或历史科学的可能,即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突破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在精神上的整体性。尽管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未必承认这种现代政治理论的表征整体性(la totalité expressive)是终止于政治的历史运动,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却处处印证了类黑格尔主义的逻格斯与存在、世界及其知识之间的宗教性的共谋关系(la complicité)。而阿尔都塞对此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结构主义的拷问:如果这种共谋关系破裂了,话语的新观念将何以可能?(40)Louis Althusser, Lire Le Capit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4, p.9.这一问题也正是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国家政治批判的最终限度,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得不走向更具科学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革命政治。
三、革命与治理的话语:未竟的矛盾
今天,何种因素决定着法国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或许在后阿尔都塞的语境下变得极为模糊。一方面,原先来自东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41)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法国哲学的影响,请参见包大为:《当代法国激进左翼哲学中的毛泽东思想》,《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的理论奥援逐渐退却,另一方面解构主义开始成为人们直面现代社会的新姿态。但是,对于法国学者而言,有一个历史条件却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而正是这一结构的意义在哲学乃至艺术中的不断延异,最终迫使哲学直面自由主义治理术及其话语。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承接了20世纪未竟的批判,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危机色彩和意识形态斗争性。今天仍然“马克思主义地”思考政治哲学的学者,在经历了20世纪斗争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两点。首先,20世纪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而这个世纪已经随着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建立而终结了,“无拘无束的市场和漫无边际的民主的结合最后使得这个世纪的意义变得平淡无奇”(44)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其次,过去的斗争证明了哲学在抗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中的虚弱无力,尤其是身处知识权力分工机制一个环节的“哲学家们”,难以勃发出超越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批判,亦即“受束缚和奴役的哲学家,他们的身心受到职业机制及其低劣境遇的摧残……哲学不再拥有一个使之能够以独立方式存在的地方”(45)雅克·朗西埃:《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蒋海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3页。。从历史分期来看,塑造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危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三是当代政治哲学和资本主义治理话语的媾和形成了新的挑战。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被“生成-世界”两个维度所困扰着。一方面苏联的“领袖的马克思主义”,提醒着激进“左翼”人士注意到所处“社会”的落后——在这个社会中,政治应该解体,并主动填补到这个社会中去。另一方面则是“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未完结之处,努力用政治学和美学来补充它,直到这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转向对其自身的不可能性的无休止的分析上来。(50)雅克·朗西埃:《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蒋海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6-327页。这两个维度的张力使得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一个多世纪已然失败的政治实践及其理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政治科学源源不断地提供治理话语的精准性与经验性基础。这使得事实上承认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作为历史前提的政治哲学日趋犬儒化,哲学家们如同康德那样,在对作为历史表象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无限崇拜的同时,却贬低大革命中的激进分子。(51)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论》,蓝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这种内在分裂使得政治的真实程序——阶级统治与阶级反抗、阶级的治理与共同体的治理,都被伦理原则所遮蔽。
从历史主义到历史科学,从理论批判到治理术批判,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在为着一个更为真实与自由的政治而求索。在当代法国,由于代议制民主的“数字和统计”的游戏构成了人们唯一可以想象政治的途径,民主政治因为含混的民主概念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话语基础。朗西埃回溯民主制度的最初设计,指出人民的投票只是一种统治者所需要的虚伪的赞同。(52)雅克·朗西埃:《对民主之恨》,李磊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巴迪欧则指出,代议制民主并不能确保公正的有效性,甚至会适得其反,民主本身也身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历史性危机之中,实现正义的希望在于扬弃资本主义的“真正的民主主体”(le sujet démocratique véritable),走向“共产主义主体”(un sujet communiste)。(53)Marcel Gauchet, Alain Badiou, Que Faire, Paris: Philo Editions, 2014, p.151.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哲学视野并非是一个合理化的阶级的治理秩序,而是世界(le monde)本身。(54)Giorgio Agamben, Introductory Note on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Democracy in What State?Translated by William McCuai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p.7.在治理话语中,资产阶级维持着合法性的象征。但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民主与规训、爱与暴力、市场自由与极端贫困却始终共存着,世界始终被铁丝网、围墙和武器所分隔。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无意于重复20世纪的革命政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资本主义治理术已经成为了生产他者的机制。当越来越多的身份(族群、种族、性别)成为他者再生产的标签,当身份政治的虚假斗争代言了政治斗争本身,政治哲学就必须回到前革命的原点,通过他者的反抗和理论的回击,重构作为革命主体的自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阶级。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认为这种属于未来的革命政治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部分实践,亦即作为现代解放政治的“第一循环”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循环涉及了列宁和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独特的政治序列,例如在毛泽东名义下的政治序列凸显的两个根本标尺:群众(masse)和党(parti)。(55)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论》,蓝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当然,这一循环也许已然落幕——“党、大众、阶级的绝对性似乎已经消耗殆尽”(56)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但是在巴迪欧和朗西埃看来,20世纪未竟的政治哲学主题仍然值得坚持,因为战争和剥削所构成的世界结构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没有改变,而有待激发的革命主体及其政治实践仍然在等待着资本主义治理危机所给予的契机。□
——重读阿尔都塞的《论青年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