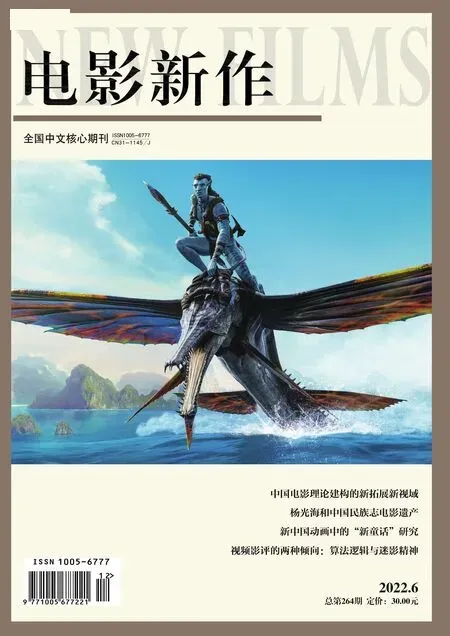缺席与在场:隐身人恐怖电影中的隐显辩证
林少雄 朱尊莹
一、隐与显:隐身人与电影相反相成
关于“隐身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隐”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隐,蔽也”。隐可以是动作,有隐蔽、遮蔽之意,隐蔽是主体的主动藏匿,遮蔽是外物的遮挡使主体不显露;隐也可以是一种状态,如长期的隐遁、隐逸。在英文中,多以the invisible man指隐身人。invisible的核心词义为无法看见的、看不见的,第一个次要词义为视力外的、看不清的,第二个次要词义比喻人不被注意的、不受重视的1,本文取英文中的核心词义及第一个次要词义,即视觉上的不可见,而非在社会意义上被无视。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品的相关影片中,以hollow man指隐身人,用hollow代替invisible,一是规避侵权问题,因为威尔斯的《隐形人》小说改编的版权为环球影片公司所有;其次hollow有窟窿、洞,无意义的、空洞的之意,引申为不真诚的、虚伪的2,与电影中的隐身人形象——空洞的身体、虚伪的人格极为符合。the hollow man,the invisible man的相同点是身体在视觉上不可见,它们在中文中常被译为“隐形人”或“透明人”。由于电影中这一角色身体透明不可见,但若借助衣服、沙尘、水等外物,仍会暴露形体与踪迹,因此笔者认为“隐身人”一词更适合,本文将以“隐身人”统称这类角色。由于隐身人在隐身后不仅隐藏了生理上的物质身体,也隐藏了他的社会身份,不再受道德伦理、法律秩序的制约,因此本文所用的“身体”(soma)概念借用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定义:“活生生的、感觉灵敏的、动态的人类身体,它存在于物质空间中,也存在于社会空间中,还存在于它自身感知、行动和反思的空间中”3,而非未经教化、修养的材料“肉体”(body)。
隐身人首先是存在的。对于所隐对象来说,隐身人可以是已知的,可以是未知的,但不会因为隐身而失去其存在性;其次,隐身是对视觉官能失效的行为或状态,而不针对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甚至第六感等感觉官能;隐与显互为辩证,隐的悖反是显,但隐的目的也是显,主体无法离开他者的承认而存在,双方相互敌对又相互依赖,隐身人总会显现痕迹使他者觉察,否则如同消失不见,因此隐身人是可知的而非不可知的。同时,隐身人在电影的背景设定、情节逻辑中是原则上可以存在的人,而不是某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现象;隐身人也区别于变身人,虽然两者同为改变自己真正的外形以迷惑他人,但变身仍然是可见的,不属于隐身。总之,隐身人,是存在的、可知的、身体在视觉上不可见的人物。电影,则是光影的艺术,视听的盛宴。隐身人电影,便是以可见的艺术形式塑造不可见人物形象的一种独有类型。
隐身人是既缺席又在场的视觉形象,电影则是表现隐身人的独特形式。“时间的运动借助空间环境显现了它的形象的魅力;而空间造型,则透过时间的运动,故事情节的展开,赋予它更为丰富的表现力”4,电影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特性,使它获得了创造新的艺术形象的可能性。隐身人无法呈现于雕塑、建筑等空间艺术。相比于绘画、行为艺术,电影中的隐身人被赋予了动态行为及其生命力。相比于小说,电影中的隐身人获得了视觉和空间的具象造型。
隐身人是一个“反电影”的独特银幕形象,同时又遵循了电影的规律。“荒诞而又真实,明知是一种荒诞而又把它当作无与伦比的真实——这就是电影的全部秘密所在”5,隐身人既不能实现巴赞所说的“木乃伊”情节,也不符合克拉考尔所说的“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虽然这一无法被凝视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观众窥视行为的失败,却激发了观众的窥视欲,极大拓展了观众的期望阈。
电影史上隐身人形象的不断涌现,说明了这一形象经久不衰的吸引力。然而隐身人出现在银幕上,却需要至少两方面的准备:其一,电影观念的准备;其二,电影技术的支持。在电影史上,爱迪生最早发明了电影,但发明家的身份决定了他将“电影之父”的桂冠拱手相让;卢米埃尔兄弟因深得电影商业化、产业化三昧而获得了“电影之父”的美誉;而梅里爱则因为深悟电影以技术来创造艺术的本质特征而名留青史。在此三人中,梅里爱对电影艺术的感悟与体认最为深刻。于是我们看到,当卢米埃尔兄弟还在执着于胶片的纪实功能及其对物质世界的影像再现时,梅里爱早已开始思考电影的技术与艺术属性,其具体表现便是因偶然的机器故障所导致的对“停机再拍”的观念思考及其虚构或叙事类电影的开宗立祖。或者可以说,无论隐身人形象的出现,还是虚构叙事类电影的开拓,都与“停机再拍”技术的自觉运用密不可分。所以电影隐身人形象,几乎在电影诞生之初时激情燃烧的岁月便已出现。
1896年,梅里爱自觉运用“停机再拍”的技术手段拍摄了《贵妇人的失踪》。影片中一位坐在椅子上的贵妇人突然不见了。这虽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隐身人”的概念,但却为此后一系列隐身人电影的兴盛提供了观念与技术的借鉴。1909年,法国导演塞冈多·德·乔蒙拍摄的《会隐身的贼》,以停机再拍、叠化展现技术,通过人类的隐身幻觉再现,最早在电影中表达了人类的隐身渴望,可以看作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隐身人电影。从此以后,隐身人电影绵延不绝,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资料记载的隐身人影片有七十多部。
隐身人形象在银幕上的出现,反映了观众隐身的欲望及超越银幕影像的渴望心理,以及潜意识中统治与操控现实世界的恒久动力。电影创作者精妙控制剧本的叙事、镜头的运动,巧妙布置灯光、布景、道具、人物造型等,在众多B级片和少量大制作影片中呈现了或恐怖或暴力或搞笑或情色的隐身故事,在银幕上塑造了一批虽不可见但又无处不在、如影随形的隐身人。可见,电影中的显身与隐身互为表里、相反相成。
作为独特的银幕形象,隐身人一直被电影研究所忽略,因此这一课题成为学术上的“隐身人”。隐身人电影多带有一定的科幻元素,同时与恐怖、情色、喜剧等类型糅合。但需要明确的是,隐身人电影本身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叙事模式,也没有发展成一个电影类型。
科幻与恐怖是隐身人电影中最常见的元素,隐身人也多以透明恶魔的形象出现。究其原因,一是小说的影响,欧洲的两位“科幻小说之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与儒勒·凡尔纳分别创作了《隐形人》(1897)和《隐身新娘》(1910),《隐形人》重在探讨科学家与社会的问题,即能力超越时代的个人如何与时代相处的问题,隐身人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后加强了恐怖感;《隐身新娘》则是科学家利用隐身进行情爱争夺的通俗小说,两种类型呈现了后世电影在这一题材上科幻、恐怖的端倪。二是恐怖题材本身的吸引力,恐惧如同烙印在基因中的经验,对大众有着强大吸引力,“为了避免伤害,我们将自己暴露在最黑暗深层的恐惧之中,特意地刺激我们的原始脑,我们似乎无法分辨出电影和真实世界的不同……观赏这类影像会让人思考真正置身其中时要如何应付,测量自己恐惧阀的欲望使好莱坞赚进了大把钞票”。6恐怖片能够激起观众的生理反应,使观众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对恐惧自虐式的渴望驱使观众不断走入电影院。最重要的原因是隐身人题材与恐怖元素的耦合,隐身人不可见,因此难以被观众同情、认同,不可见的人成为恶魔比成为英雄更容易。同时,在恐怖题材中,隐身人更具独特性,因不可见而难以认知,因未知而恐怖。比较而言,在超级英雄片中,如《神奇四侠》系列影片,隐身人能够控制身体的隐显,在必要的时刻发挥隐身技能,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显身,在有利于观众代入并认同于角色的同时也削弱了角色的独特性;在喜剧片中,如《两傻大战隐形人》(1951),观众站在上帝视角,已经知道隐身人的存在,叙事清晰但没有激发观众的具身体验或带来强烈的悬念感;而恐怖片中的手法更为高明——以不可见、难以认知的恶魔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强化恐怖感,充分利用视听语言创造一个若有若无、不可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恐怖隐身人,比较典型的影片有《隐形人》(1933)、《透明人》(2000)和《隐形人》(2020)。
二、隐之显:缺席凸显在场
隐身人并没有因为不可见而削减重要性,反而因神秘不可捉摸而无处不在、如影随形。隐身人电影中,缺席与在场并非非此即彼,身体的缺席反而会凸显在场感,这消解、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在场/缺席”的一分为二的对立关系和等级关系。
(一)不可见的恶魔:恐怖感强化
相比于已知,未知更加恐怖,不可见、难以认知的恶魔会带给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更易于强化其恐怖感。有大量恐怖片制作经验的雷·沃纳尔执导的《隐形人》(2020)是隐身人题材中最恐怖的一部。作为仅有7000万美元投资的低成本影片,《隐形人》没有大量依赖视觉特效,而是充分利用隐身人不可见的特性,以一些模棱两可的段落——不知道隐身人是否正在偷窥、威胁,让观众紧张、恐惧。
影片多暗示隐身人的在场,同时又不明确告知观众,以不确定的危险调动观众潜意识中不安的情绪。厨房段落中有一个较长的固定静态镜头,西西莉亚走出镜头后摄影机依然对着这一无人的场景拍摄了很久,在观众的观影经验中,长久注视的留白画面一定会出现不同寻常的事物,但什么也没出现会令观众更加不安。摄影机如安德里安一般展现出强烈的控制欲,控制观众的注意力,强迫观众注视这一空间。类似的不确定性反复出现,不断为观众营造悬念和紧张感。在安德里安凭借隐身杀死西西莉亚的姐姐并嫁祸西西莉亚后,西西莉亚深陷牢狱,此时观众与西西莉亚已经明确隐身人的存在,但不知隐身人是否在场。在审问场景中,画面右侧的角落空无一物,非常干净,让观众产生隐身人作为幕后真凶正在那里倾听旁观的感觉,但又无法确定。因不可见而来的不确定性,引发观众对于恐怖的想象与猜测,引导观众自行脑补恐怖画面。因此,人物的缺席处理比人物在场的威慑性更强大,悬念感更强烈,给观众造成的心理压力也更为强烈,缺席以此凸显在场,让影片充满了心理恐怖效果。
在被废弃的素材中,可以看到一些明确表示隐身人存在的事件,西西莉亚在去找工作面试之前,放在桌子上的手机被未露脸的人拿走,之后西西莉亚四处寻找手机,将放着作品集和履历表的包随手放下,包随后被人拿走,在情节逻辑上解释了为什么面试时西西莉亚掏出来的是简报。在成片中,这一段被删减,西西莉亚信心满满地面试,面试官也甚为满意,打开包却是简报,既加快了叙事节奏,有足够强的反转,也使观众怀疑西西莉亚的精神状态。事实证明,主创们的选择是明智的,不给观众明确答案,这一悬念紧紧地抓住了观众,使观众一直高度集中注意力,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以免错过隐身人在场的线索,紧绷的观影心态强化了影片的恐怖感。
隐身人的身体在视觉上不可见,但不是消失,人过留名、燕过留痕,导演多借助外物显露隐身人的在场,如影片中常用灰尘、水、蒸汽等布景或道具描摹其局部的轮廓。因此,这些本不产生意义的日常细节,因显露了隐身人在场的痕迹,成为恐怖、危险的隐喻,原本极其寻常之物获得了诡异的氛围。这些不自然的细节是非自然化的、无意义的斑痕,它使既定的含义动摇,为意义的阐释提供了入口,产生缝合点的效果。7最典型的是《隐形人》(2020)中西西莉亚听到不明声源后起身查看的段落,此时西西莉亚和观众都还未确定隐身人是否在场,在西西莉亚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团因寒冷而凝结的白色蒸气,这一日常的细节带有了惊悚的意味,成为隐身人在场的标志。《隐形人》(1933)中雪地上的脚印、雨天里诡异的身影、漂浮的帽子,《透明人》(2000)中独自旋转的椅子、血水里的脚印等道具或布景暗示了隐身人的在场,它们令观众发现了某种不宜的细节,最日常的物件产生了令人恐惧的意味,以至于一切事物都可疑了。但若隐身失去其神秘性,“一旦引起恐惧的全在之音所属的身体忽然现形,那种恐惧便什么也不是了”8,这些不宜的细节也成了隐身人的致命弱点,不论是格里芬,还是塞巴斯蒂安、安德里安,一旦隐身的秘密被揭露,便成为众人围攻的对象,最终成为一具流血的血肉之躯,失去了令人恐惧的力量,这便是“鬼魅般的‘不可见’存在只剩下普通的形体存在之后的命运”。9
总之,在电影创作者的精心设计下,很少显身的隐身人却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尤其在《隐形人》(2020)中,导演雷·沃纳尔证实在大部分镜头中,隐身人是存在的,但观众永远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些镜头中,以至于在部分场景中隐身人并不在场,但观众依然认为他在场,达到了让观众自己吓唬自己的目的。
(二)隐形的身体:本我显现
在恐怖题材的影片中,隐身人大多具有双重身份:当其显身时,是现实中某一科学领域的领头人;当其隐身时,是凌驾于法律、道德之上的强者和加害者。隐身人并非一出场便是恶魔,而是在隐身之后逐渐放纵自我。隐身对人物的好恶起到了关键性的转折作用。可见“隐身”行为本身,不仅激发着观众的观看欲望,也是诱惑着“隐身人”的动因。
隐身人因不可见而可逃避惩罚,便逐渐肆无忌惮地作恶,尽情享受快乐原则,不断释放压抑本能,终成为邪恶的负面角色。肉体的隐形使邪恶的无意识显形,弗洛伊德认为显露出来的意识只是冰山一角,是处于心理结构的外表,能被觉察到的心理活动。此外还有潜意识与前意识,潜意识是受压抑的、难以认识的心理活动,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前意识是潜意识与意识的中介。本我是未知的,潜意识的,有大量被压抑的内容,由快乐原则主导;自我是本我中通过前意识知觉被外部世界直接影响改变的一部分,会把外界影响施加给本我,同时也常实现本我的愿望,由现实原则主导;作为本我分化的一部分,自我中存在着分化阶段,弗洛伊德称为超我,其对自我的支配以良心或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出现。10
隐身人隐身后一开始会做无伤大雅的恶作剧,《隐形人》(1933)中格里芬捉弄无知的小镇居民,《透明人》(2000)中巴斯蒂安以空洞的身体吓唬孩子,虽然暴露了他们本我中恶劣的一面,但并不让人难以接受,随着隐身潜力的不断开掘,隐身人逐渐沉迷于不受限制的权力,其行为愈加不受控制。《透明人》(2000)的开场,还未隐身的塞巴斯蒂安偷窥女邻居脱衣服,当女邻居拉上窗帘后,他自骂了一句“该死”后继续工作,此时他的自我占上风,把法律道德的约束施加给本我,遵循了现实原则;当他隐身后,再次偷窥女邻居洗澡,此时他自问“谁会知道呢?”之后便利用隐身进入女邻居房间并施行强暴,此时他的本我占据上风,完全由快乐原则支配,潜意识不再受压抑并付诸行动;之后他大开杀戒,谋杀了长官、同事。正如塞巴斯蒂安所言:“当你在镜子里看不到自己的时候,你能为所欲为。”隐身是人从自我回归到本我的关键,与潜意识、本我、欲望紧密相连。同时,人物利用隐身,隐身也控制了他们。几位科学家为了能在社会生存,将自己裹得如木乃伊,或者裸身在冷风中。隐身人无法正常工作,只能以偷窃为生,或控制他人为自己牟利,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隐身人只有在死亡之时才能恢复容颜,因此,不是人物驾驭了隐身能力,而是人物被隐身挟持、异化,走向邪恶的深渊。
虽然人物的身份、阶层,隐身的原因、目的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隐身后人物沉迷于隐形状态,本我的快乐原则占据主导,隐身人利用不可见逃避道德法律的约束,疯狂地追求权力,其行为从无害的恶作剧变成有计划的破坏,甚至谋杀,身体隐形使得本我显现,呈现了人性的幽深、复杂及其无奈。
三、显之隐:视听艺术中的不可见之法
电影是极度依赖视觉表现力的艺术,是“显”的艺术;隐身人则是视觉上不可见的人,是“隐”的形象。电影中的隐身人,是需要观众看见的不可见之人,这一悖论反而成就了隐身人的独特性。电影创作者充分利用声音、画面,依靠特效技术的支撑,展现了一个个神秘的隐身人。
(一)凭声音在场:不可见却无所不在的隐身人
由于隐身人在视觉上不可见的特性,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的声音属性及其作用更为突显。詹姆斯·惠尔在为《隐形人》(1933)选角时,曾称不在乎演员的长相,但声音必须好听、迷人;保罗·范霍文执导《透明人》(2000)时将多个扬声器放在片场的不同位置,使演员凯文·贝肯的声音出现在各个位置,以激起演员的真实反应。
声音是隐身人在场的重要证据,但声源模糊与声音多义带来了恐怖想象。米歇尔·希翁认为在“纯听”(acousmatique)的情况下,因难以确认声音的来源,声音可以带来“叙事模糊”的效果。声音的模糊性带来了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比画面更具想象的空间。《隐形人》(2020)中,西西莉亚在家中听到了细微的声响并四处寻找,观众和西西莉亚并不确定声音究竟是安德里安还是动物发出的,这种不确定性使观众和受害者处于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之中:不知道隐身人是否正在身边监视自己,因此杯弓蛇影、疑神疑鬼。可见,声源的不确定性强化了暗箭难防、无处可逃的挫败感和恐怖感。
声音成为发现隐身人踪迹的重要线索,因此影片中会有诸多凝神细听的情节,无声胜有声的时刻。《隐形人》(2020)是将寂静无声运用得淋漓尽致的影片,当呈现晃动的主观视角的摄影机登堂入室并肆无忌惮地观察时,突然而来的寂静无声让观众感到恐惧。“在电影作品中,有声的艺术处理是影片真实还原现实世界的手段,而无声的声音处理却常常被电影创作者用来表现人物的主观感受,暗示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突出传达故事中的重要的信息。”11无声强化了西西莉亚的主观感受和知觉状态。克制的声音设计表现了人物内心的恐惧,塑造了一位饱受折磨的女性形象;同时声音意味着生命的存在、人的生息,无声在心理上给人一种负面的压抑之感,因为隐身人的陷害,西西莉亚被周围人误会,寂静显现了她孤立无援、无处求助的状况。
当空间变得寂静无声,施虐狂隐身人的细微动作造成的声响显得强烈而刺耳,“在‘寂静’的音调和节奏中我们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更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记住这种听觉上的反差”12,镜头与极为细腻的听觉效果结合在一起,不知何处而来的细微声响和西西莉亚紧张的喘息声、细小动作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西西莉亚的注意力、呼吸以及观众的神经都被这声音的无形之手操控,寂静之中的不明声源营造了极强的恐怖氛围和悬念感。正如巴拉兹所言,“静甚至会使事物脱落它们的假面,仿佛瞪大了眼睛死瞪着你。如果在一部有声片里,某一物象周围的各种噪音突然完全消失,镜头也随即换成它的特写,这一物象的面相便会激发某种新的意义,引起某种新的紧张,对事件的进展产生承前启后的作用。”13这一段落,便暗示了隐身人登堂入室、完全侵入西西莉亚的新生活,承担了重要的戏剧作用。
(二)以画面暗示:留白创造恐怖想象
电影艺术形式的微妙之处必须经由创作者与观众的共振才能捕捉,隐身人影像更是如此,由于不可见的特殊性,导演为了充分调动观众的观影感受力,往往以有悖于观众观影经验的视听语言暗示视觉上缺席的人的在场。
不平衡构图便是隐身人恐怖电影中常用的手法。“在均衡构图里视觉比重对称或均匀地分布于画面中,以传达整齐性、一致性或先决性。与此相反,非均衡构图经常与追逐、局促或紧张联系在一起。”14画面中的留白呈现了隐身人可能出现、存在的区域。在警局的审问段落中,西西莉亚和警官面对面隔桌而坐,一般电影中会以正反打镜头表现对话,拍摄西西莉亚时,是警官的过肩镜头,但比标准的过肩镜头更向两个人的轴线以外偏离,警察在画面中占据的空间很小,其作用和地位被弱化,反而西西莉亚周围有大量的留白空间,这一镜头仿佛是其他人的视角,另有其人占据主动位置,审视着西西莉亚;在西西莉亚的视线中,本应处于画面中心的警官成为一团黑影,被挤到画面的边缘,视觉中心成为相对明亮的空白空间,使观众怀疑此处是否有隐身人在窥视、偷听。虽然影片没有说明,但不平衡构图使这一场景成为隐身人的主场。

图2.电影《隐形人》剧照
精心构思的场面调度也发挥了强大的叙事功能,水平摇镜头的巧妙运用使隐身人的存在感非常强烈却又无法确定。在一般情况下,镜头摇射到一个特定的人物或物品,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力,暗示被摇射的对象承担重要的戏剧性叙事功能,或有重要的事情将会发生。隐身人电影中的很多平移镜头颠覆了观众的预期,摄影机摇移后什么也没有,只有空旷的空间,创造了强烈的悬念。在西西莉亚整理衣服的段落中,一般情况下,摄影机会一直拍摄人物或者直接切转镜头,但影片中,西西莉亚继续叠放衣服之时,摄影机平移,最终对准门口停了下来,观众会期待有人出现在此处,但什么都没有出现。类似的摄影机运动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引导观众产生空间中有他者的感觉。
摄影机常以隐身人的视角出现,带来强烈的恐怖感。在《隐形人》(2020)第27分钟左右,黑夜中,从满是落叶的地面的俯拍镜头,摇移到警察住所外,模拟了一个人走路的视角,之后镜头侵入内部空间,通过室内的驻足、观察后,最终“找”到了西西莉亚,镜头仿佛是第一次进入他人领域的他者,登堂入室,悠闲地、信心满满地观察着、寻找着,当镜头凝视女主时,原本用电脑的女主有所警觉,也开始凝视镜头,但反打镜头中,观众和女主什么也没看见,黑洞洞的门吸引着注意力。凝视的不对等制造了恐怖效果,也成了监控社会中摄像头无处不在的隐喻。
摄影机也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运动,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角色。电影开场,西西莉亚在别墅逃跑时,摄影机没有紧紧地在后面跟拍,而是隔着室内的建筑物冷静地侧面跟拍;当西西莉亚停下来穿衣服时,摄影机游离于女主自行运动,摇射过别墅内的空间,对准了一个尽头是黑暗的走廊,给观众一种黑暗中会有人走出来的暗示;镜头又摇射回正在穿衣服的女主;在惊悚、低沉的音效中,凝视着女主,之后先于女主来到楼梯、车库,安静地、冷漠地俯视着或旁观着惊慌失措的女主,这一段落中摄影机被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角色来运用,独自运动,寻找目标,甚至先于西西莉亚到达某个逃跑点。摄影机如同猫抓老鼠一样看着女主,如隐身人残忍地、傲慢地玩弄西西莉亚与观众,给观众带来被掌控的焦虑与恐惧感。
(三)借特效显形:精确技术触发感性体验
隐身人电影致力于建构一个真实生活场景与虚拟特效相融合的幻象,于“显”的艺术中塑造“隐”的形象,电影特效的支持必不可少。可以说隐身人见证了电影技术发展史。从1933年的《隐形人》到2000年的《透明人》再到2020年的《隐形人》,创作者不断探索,尝试超越前辈,以求隐身人形象更“真实”的视觉效果。
1933年詹姆斯·威尔导演的《隐形人》将当时的电影特效推向了极限。影片采用了由弗兰克·威廉姆斯发明的合成技巧。为了呈现人物透明的效果,饰演格里芬的演员克劳德·雷恩斯身着黑色天鹅绒服后裹满绷带,他揭开绷带的动作在一个黑色背景前被均匀照亮,镜头被不断地拷贝到高对比度的底片中,直到背景以及黑色的剪影从底片中去除掉,接着再采用接触式印刷将背景冲洗到带有剪影遮罩的胶片上,隐身人与正常的镜头结合,这些复杂的镜头最终巧妙呈现了绷带下的身体的透明效果,即格里芬在众人面前解开绷带恐吓小镇居民。15电影特效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好奇心,使《隐形人》成为1933年环球影片公司最赚钱的影片。之后的多部隐身人电影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并更加精细巧妙,如《隐形人的归来》(1942)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特效奖,在评论界对恐怖电影持有偏见的当时算是一个奇迹,也说明了影片在特效上的成功。
数字特效的运用为隐身人的展现带来了新的表现力,合成依然采用类似的技巧:将前景元素加入背景内,只不过古老的活动遮罩胶片系统如今已基本被绿幕和通过计算机进行roto遮罩处理所替代。16《透明人》(2000)和《隐形人》(2020)中部分段落运用实拍画面与实拍画面抠像合成,实景画面与计算机生成画面合成,蓝幕或绿幕拍摄与计算机生成图像合成。
《透明人》(2000)创作之时,特效人员如同上帝,以演员凯文·贝肯为模型,在电脑上创造了解剖学上真实的电子凯文。创作者从医学、解剖学的角度复原当皮肤被掀开时,会发生什么,力图以精确的、科学的手法获得真实的效果,以影响观众的感性体验。在另一方面,真实会向美学让渡,在真正的解剖中,皮肤下面有大量油脂,但电影建模减少了油脂,扩展了肌肉,目的是让它看起来更真实,更像皮肤的外表面,真实与虚假,形成了有趣的悖反。
《透明人》(2000)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提名。影片中隐身人和隐身大猩猩隐显转换的段落常被作为特效范例,这一段落将视觉引入不可见的身体的内部,颠覆了古典的身体意象中亘古不变的完美无缺。隐形的过程如同人体的迅速腐烂:皮肤消失,血淋淋的血肉组织赤裸裸呈现出来,血肉消失,内脏消失。光滑精巧且封闭完整的古典人体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撕裂的、怪诞的血肉,最后只剩下骨架,最终化为乌有。隐身人的转变过程中,同事处于观众视角,其反应带有一定的好奇,但更多的是恐惧与厌恶。正如茱莉亚·克丽斯蒂娃所说,当意识到了自身的物质性时,察觉自身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在尘世的脆弱,我们的反应是厌恶。一般来说,身体的内部可视化过程,是死亡或走向死亡的过程。但影片中隐身人迈向死亡之时,内部的身体从内到外再次可视,最终容颜呈现,肌肤覆盖了黑暗的、血腥的内核:一个完美的皮囊的呈现标志着死亡的到来。隐身人生时为了融入社会,将自己裹成木乃伊,在迈向死亡的生命中与死神共舞,死时反而显露了俊美的、年轻的容颜,呈现了隐与显、生与死的辩证主题。
不同于隐身药水,《隐形人》(2020)中隐身的方法被设置为隐身衣,隐身衣损伤失效时会出现隐身人隐显转换的画面。在拍摄前期,片方制作了黑色和绿色的隐身外套装备,根据不同的情节场合,特效演员穿着不同的隐身衣。在阁楼泼油漆段落使用了绿色隐身衣,西西莉亚从阁楼探出头,觉察到梯子上的不对劲,将一桶油漆泼下,伴随着令人不适的音效声,隐身人赫然显现。这一段落由固定在西西莉亚肩上的摄影机多次拍摄后合成,一次拍摄没有人的空镜头;一次拍摄西西莉亚倒油漆,隐身人穿着隐身衣的绿幕外套,以及只倒油漆的镜头。后期将以上视频合成,形成油漆泼在人形轮廓上,危险猛然显现的惊吓效果。
得益于数字控制拍摄技术的支持,《隐形人》(2020)成功制造出不可见的敌人的恐怖感。厨房打斗戏是一个看起来一镜到底的长镜头,保留了时空的完整性和动作的完成性,更具有真实感和恐怖效果,但同时也有制作上的难度。数字控制拍摄意味着机器人摄影机被设定了一组特定的动作,将以特定的速度,按照特定的轨迹进行拍摄,因此,西西莉亚拿刀叉的时刻、刀叉指向的方向、被抓着脖子抬起、被按到墙上的动作等场面调度被精准计算。西西莉亚被隐身人扔到餐桌对面的段落,机器人摄像机被设定以完全相同的运动和时间重复拍摄,一是演员伊丽莎白·莫斯被扔出去的动作;再是以特技演员替代伊丽莎白·莫斯,特技演员被绑在威亚上支撑着,穿着绿色紧身衣的特效演员以隐身人带来的力量将她扔到桌子对面,然后再拍伊丽莎白·莫斯被扔下后的反应。镜头以一种冷酷的、手术般精确的方式对这个场景进行追拍,最后按照特技编排预先编程,将女演员的镜头无缝衔接到特技替身的镜头上,并把威亚和绿幕擦除,加工成看起来是一镜到底的长镜头。
总之,得益于精心设计的视听语言,不断发展的特效技术的支持,导演以科学的、技术的、理性的影像精确地控制观众感性的、个人的体验,并使得恐怖片中的隐身人显得越来越神秘而恐怖、魔幻又真实。
电影的本质属性在于将客观事物转化为影像形式在银幕上呈现,从而极大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与观影期待,而隐身人却在电影中被隐去了身体,让观众观影时在视觉层面难以看见,从而深深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与想象力。以电影本质的“可见”来呈现银幕影像的“不可见”,以观众观看的“不可见”来阐释电影艺术的“可见”,电影对视觉表现力的依赖与隐身人对银幕属性的消解与重构,说明了二者的相悖相合、相辅相成。几乎伴随着电影史涌现的“隐身人”系列,又说明它遵循了电影的艺术规律。视觉上的“缺席”强化与突显了艺术上的“在场”,电影创作者则通过精心设计的视听语言,在“显”的艺术中塑造“隐”的形象。电影与隐身人构成了隐与显、缺席与在场的辩证图景,而观众身处影院,暂时疏离了社会与同类,在黑暗中目光炯炯有神,紧紧盯视与辨识着银幕上的“隐身人”,成为社会中的“隐身人”。
【注释】
1参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编译.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101.
2同1,1005.
3[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4王心语.影视导演基础[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11.
5徐葆耕.电影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
6美国纪录片《恐惧实验室》的解说词,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了恐怖片的吸引力。
7齐泽克在讨论希区柯克的电影时,将赋予了影片恐怖意味的隐喻式的日常细节称为“希区柯克式斑点”,隐身人电影中亦有诸多类似的斑点。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51.
8吴琼.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1.
9同8.
10参见[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谈自我意识[M].石磊编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30.
11冯果.电影中的无声艺术[J].当代电影,2004(04):123-126.
12谯慧琼.触及无声——“静默”在有声电影中的运用[J].声屏世界,2021(02):72-73.
13[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219.
14[美]默卡多.电影人之眼:活用电影构图[M].黄裕成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8.
15参见[美]Jeff Foster.影视绿幕技术完全手册:拍摄、抠像与合成:第二版[M].邵佳阳,兰渊琴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20.
16同1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