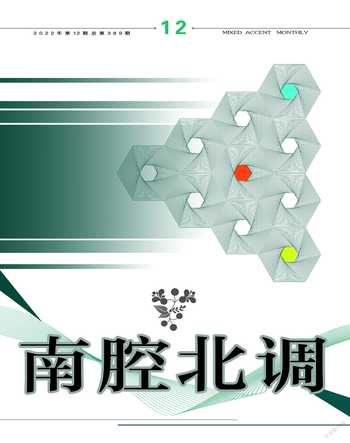陈众议:回归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会长陈众议对拉美文学的研究颇为深入,尤其撰写过很多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很多作品的评论。为了以特殊的方式致敬大师,陈众议也出版了一部融合悬疑、魔幻、荒诞等多种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是我闻》。
陈众议既是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同时在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领域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此次跨界创作的小说,他蕴积十余载,抨击封建迷信蛊惑人心的积弊,用一种新颖的表达,在营造出极强艺术感染力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的独特认知和敏锐反应。
一、你要看,而且要看见。陈众议说,在《如是我闻》中,他努力一层层发掘魔幻如迷信、玄奥背后的真实。
舒晋瑜:您愿意如何概括《如是我闻》?魔幻现实主义?神秘的文化现象比较多,您的文学创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多?
陈众议:我的文学创作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的,除非有意模仿某个作家或某些流派。《如是我闻》首先是一部反迷信小说,最初的动因来自一腔愤懑。十年前我太太受人蛊惑,轻信“大仙”“大师”,最后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而当时那些人都用难以稽查的网络和手机信息与她联系,他们钻了虚拟空间的空子。这也是我缘何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呼吁网络和手机实名制的直接原因。导致各种迷信沉渣泛起固然原因众多,但人们信仰的阙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心理落差和心理压力等都是客观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主观因素。我太太身体不好,刚四十出头就提前退休了。像我太太这样的人最易被蛊惑。
小说有魔幻因素,因为生活忽然变得魔幻起来。就像莫言读了拉美当代小说,尤其是马尔克斯的作品,认为这不就是高密东北乡吗?不过我的小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关键在于如何一层层发掘魔幻如迷信、玄奥背后的真实。
舒晋瑜:小说透露出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忧思:我国从事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仁何止千万,却始终未能阻止邪教和迷信的泛而滥之。您希望通过写作传达什么?作品完成了,能帮助您、帮助读者获得一些启发吧?
陈众议:我特别希望人们回归理性。文明浩荡,怎么能让这些滋生于数千年前莽荒时期的神神鬼鬼、巫不巫傩不傩的东西再度复活呢?遗憾的是邪教尚未被肃清,不少人包括青少年依然跌入八字算命、风水运势的陷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想从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巧妙地、润物无声地将它们解剖、打倒。当然,我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总得有人先吃螃蟹。
舒晋瑜:我想《如是我闻》大概是一部学院派的小说,知识点很多,对当下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教育、技术等皆有关注,并且在写作中不断提出思考和反省。您觉得知识分子的写作有何特点?
陈众议:学者的毛病之一是好为人师,但我已经尽量克制了。问题是大量的迷信故事让我不得不对其背后的故事和产生的土壤有所还原和开掘。这就免不了会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等有效武器。虽然我尽可能不动声色,但难免还是会露出马脚。这是两难的选择。
舒晋瑜:小说中“我”看到女孩关小露有一番辩白,用“由甲感官挪移至乙感官的纯粹游移,具体说来是将过去生活中某种重要情感由甲目的物向乙目的物迁移的过程”解释“这是移情却并非别恋”,形容关小露是“理所当然的目的物”。这既是“心理学概念,也是量子纠缠,更是人之常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可以获取到知识点,但对于多数读者来说,有没有掉书袋的嫌疑?您这么用心写作,也可能被读者一晃而过,会不会有些失落?
陈众议:一定会有很多类似的细节被忽略。不过问题不大,我坚信段子是一时的精神自慰,而迷信是一生的精神迷醉。只要这一个目的达到了,那么也算是开卷有益了。
舒晋瑜:您是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期间曾多次提交有关教育的建议和提案,这一身份对于创作是不是也有很多帮助?有心的读者会发现教育在小说中有所体现。
陈众议:开始构思这部小说,适逢校外培训如火如荼。它的问题已为世人所公认。校内放羊,校外厮杀,不仅使亿万孩子及其父母身心俱疲,关键是国家教育体系和意识形态被严重破坏。我这一代,包括我孩子这一代,基本没有择校的概念,大家都是就近上学,公平竞争。之所以造成“双减”前的乱象,我认为原因很复杂,除了资本侵入,有没有优质教育资源权力寻租?总之,问题很复杂,但受害最甚的无疑是孩子。因此我从2015年起开始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不减负,不切切实实地减负,谁敢要孩子,别说二胎三胎了!念兹于兹,此乃真正国之大者!
小说中有个人物叫夏琴,她命途多舛,与主人公“我”的关系十分暧昧。她便是从事校外培訓的,我借她之口道出了一些奥秘。
舒晋瑜:笑话和段子在《如是我闻》中比比皆是。是人物塑造、情节构造所需,还是叙事节奏的需要,或提振阅读的兴趣?您如何看待幽默(段子)在小说中的作用?生活中您很幽默吗?
陈众议:其实我在生活中过于正经,也过于矜持,而且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属于比较乏味的那种。但与人为善是我的本性,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期间,从副所长到所长20多年,我基本充当了“和善家长”的角色。
至于作品中的大量段子,我用来与迷信对位,就像我前面说的,“段子是一时的精神自慰,迷信是一生的精神麻醉”。段子是极端世俗化的表征,而迷信只有在极端世俗的土壤中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失去了崇高和理想,等待的就只能是金钱至上和醉生梦死。
舒晋瑜:小说中石头讲的笑话都是从《笑林》或者百度、知乎、抖音之类的网站上捡来的;老白在精神病院纵火后逃逸,电台、报纸、微信公众号到处悬赏通缉;师尊不仅有通灵术,而且对现代通信技术也运用自如,他写微博,还是最早的网红;“我”无从断定朝露姐妹是克隆还是整容或者人工智能加基因工程的产物——您的创作受到新媒体的影响比较多?
陈众议:是的。虚拟空间已经全方位浸润现实生活。在《如是我闻》的姐妹篇《冥合天人》中,批判迷信和邪教依然是主题,但虚拟空间的描写有大幅度提升。像剧本杀、元宇宙等从一开始便有被带偏的危险,而克隆术及其相关的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也完全有可能被资本和邪教利用,因此我斗胆提前敲几下警钟,说科幻也好,谓杞人忧天也罢。
舒晋瑜: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媒体)的挑战?
陈众议:新媒体不是法外之地,但新媒体也确实易受资本和各种不法利益入侵。我们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严格管理,恐怕还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毕竟在虚虚实实、似是而非的海量信息面前,谁都有被淹没的危险。反过来说,别有用心的人也可能乘虚而入。
二、谈读书,陈众议始终有一个观点:任何时代伟大的文学都是凤毛麟角。
舒晋瑜:小说中为了多少给朝露一点提醒,“我准备将枕边的《儒林外史》送给她”,能否谈谈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有什么阅读习惯吗?
陈众议:枕边书会经常更新。学者最自由,但也最辛苦,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五加二、白加黑,也没有一篇文章、一部著作不是一次重新开始,否则会被当作自我“抄袭”。但阅读中总有一些是“常客”。我的“常客”中有《老子》《庄子》,也有唐诗宋词和《红楼梦》、元曲和《本草纲目》。后者这些年有点被束之高阁,原因是网络太方便了,图文并茂,而且还可能有视频作参照。
我读书向来挑剔,因此买得多,读得进去的少。主要习惯大概有两个,一是工作需要,刚性,没什么可说的,必须读;二是真正入目入心的,就像看到心仪的人、碰到会心的事,只消翻两页就知道这书是为我写的。随着阅历的增加、年龄的增长,这样的书越来越少,有点可遇而不可求了。可能是越来越珍惜时间,觉得时间最宝贵、不容浪费,或者是老了!觉得“学焉未能,老之已至”!可心里还有一大堆事想做,岂不既犯难又犯愁?
舒晋瑜:《如是我闻》中“我”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不同领域的书皆有涉猎,谈谈您本人的读书情况吧,留学期间,读得最多的书是什么?您最喜欢的文学类型有哪些?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
陈众议:留学期间读得最多的自然是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在西方文学中又以西班牙语文学为甚,同时兼修西方历史和哲学,后来又扩展到心理学和社会学。要说最喜欢的文学类型倒是有过几次变化,开始是近代文学,尤其是19世纪西方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而后是拉美当代文学,再而后是西班牙古典文学。对于题材和风格就没有那么挑剔了,但大抵比较喜欢空灵一些的,比如古今玄幻或魔幻小说。
至于不为人知的趣味,大概是委婉地问我对西方女孩的认知吧?虽然骨子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或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区别还是有的。比如五服之外我们大概率不会喜欢西方女孩,但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尤其是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好莱坞梦工厂的影响日渐扩大,别说现在,就是我们的上两代也已经与西方审美渐渐趋同了,如今更甚。但夏日炎炎,且不说体味不同,即使稍有不慎触碰到了胳膊,你也会发现她们固然金发碧眼,但具有几近肤色、不易觉察却颇为扎人的汗毛,还有不同的体味。悄悄地告诉你,我还是更喜欢细腻温婉的中国女孩。
舒晋瑜:很开心分享秘密,谢谢您的坦率!在《说不尽的经典》(作家出版社)中,您对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均有精辟地剖析,而且很多作家不止一篇。您经常重读作品?重读哪些?
陈众议:我读书向来挑剔,这可能是比较的结果。但矛盾的是文学艺术可以自立逻辑,它是文艺赖以永恒的不二法门。几年前有人对《高玉宝》提出批评,认为它逻辑有问题,半夜鸡叫,谁会相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自成逻辑的,因为雇农们没有钟表,鸡鸣便意味着天要亮了,何况背后有周扒皮这个混世魔王。因此,从文学作品本身的逻辑来看,“半夜鸡叫”的可信性是成立的。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这归咎于“艰深乍觉诗如谶,消散方知道是虚”。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能让我重读甚至不断重读的书往往有几个特征:一是让我不忍立刻读完的,它们就像孙猴子吃人参果,是需要慢慢地品尝的,而且乐于慢慢地品尝,以至于生怕它们被吃相难看的猪八戒囫囵吞了;二是可以入梦的,它们会一直萦绕在我的无意识中,无论是人物还是情景,非空非色,却能随时撩拨方寸神机;三是经得起理智判断的,譬如我会将不同的文艺作品或其他书籍分门别类。言情的肯定以《红楼梦》为最;言志的肯定以唐诗宋词为先;载道的如诸子、古来演义和红色经典就难分伯仲了。当然,言情和言志在很多人眼里是同一回事,但在我看来还是有区别的。我反倒觉得古来争论不休的载道和言志是可以杂糅的。谁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许多名著不是既载道又言志的呢?也许只有《红楼梦》是反道统的。
上面提到的基本都是我经常重读的作品,除了《高玉宝》《西游记》《水滸传》,因为它们入眼即化,无须重读。
舒晋瑜:您有一个观点:任何时代伟大的文学都是凤毛麟角,少数作品幸免于难的原因,要归功于学院派(哪怕是广义学院派)的发现和守护,才完成和持续其经典化过程。可否简单概括一下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否所有经典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或必然性?
陈众议:是的。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的。首先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创造经典的,也不是所有时代的经典都能流芳百世。这可以有两大指向,一为纵,二为横。从纵向看,不少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并不一帆风顺,《红楼梦》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它的命运可想而知。也许被“诲淫诲盗”之类的唾沫永远埋入历史尘埃也未可知啊!结果是书生或谓学院派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点点地将它从烟尘中抢救出来,并一步步将它推为“四大名著”之首,以至于毛泽东当年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时,还不忘加上“半部《红楼梦》”。其中就有一定的偶然性。所谓沧海桑田,世风日新,很多中外名著都是在数十乃至数百年之后才被重新发现的,有的甚至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譬如《堂吉诃德》,将它定于一尊的是在塞万提斯去世两百余年后的德国浪漫派。当然,文学作品的内在肌理是决定因素。这是基本的辩证法。
诚然,从横向看,当下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资本的作用将大为增强,这几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对当代经典的形成机制颇为悲观。好在最终由时间老人说了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是未来史;一切文学亦然。
三、学外语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强健母语和母体文学文化的拿来。
舒晋瑜:创作、评论、学术研究……您多方兼顾,皆颇有成就。可否先谈谈您的小说创作,如长篇小说《玻璃之死》《风醉月迷》及很多短篇小说,在小说创作中您有怎样的体会?和写评论比,状态有何不同?
陈众议:作为外国文学学者,我是叛逆者。我始终认为学外语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强健母语和母体文学文化的拿来。借用许渊冲先生关于三民主义的译法——“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我们何尝不应该是of the Chinese, by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归根结底,我们的工作终究是为了强健中文母语和中华文化的拿来及中外互鉴的送去!背离了这个初衷,一切也就无从谈起,至少是舍本求末。因此,我间或从事文学创作便是为了贴心地拥抱中文,同时紧密与母体文学文化的血脉联系。
至于《玻璃之死》,那是一部抽屉小说,始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遍地书香的时代。后来一不小心拿出来示人,心里充满了遗憾,于是又追加了《风醉月迷》。虽然后者起笔于90年代,但明显较前者成熟稳重一些,虽然标题有点花哨。那些短篇小说是随机写下的,有朋友看到就拿去发表了。当时不像现在,既不论家门,也无所谓名利,毕竟主业是外国文学,总觉得写小说是离经叛道,有时甚至不得不化名发表。
这多少受了老先生们的影响。虽然我所在的单位有一大批“双枪将”,如冯至、钱钟书(后被借调至文学所)、杨绛、卞之琳、李健吾、袁可嘉等,但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大抵是在青年时期,后来基本都潜心问学了。何况,时移世易,分工越来越细。创作和研究有点儿不相杂厕,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不过我还算是比较执拗的,一直坚持了下来,因此抽屉或电脑储存了不少残编断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如是我闻》的初稿其实是七八年前草就的,另一部刚刚删减削剔好的《冥合天人》算是前者的姐妹篇,同样起手于七八年前。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以此接续对母语的亲切感和亲密感。
当然,从事研究与投入创作的心态确实不太一样。研究要尽可能既有我又有他(她),创作却是非常自我的一个活计。行当所行,止当所止,海阔天空,全凭个人兴趣。
四、作为评论家的陈众议,每年保持二三十部国内原创长篇小说的阅读量,其他中短篇小说和诗歌难以计数。
舒晋瑜:您的评论文章鞭辟入里,即便是批评,也是善意的。比如在莫言获诺奖后您写的评论文章中,就有一篇《莫言的五根软肋》。莫言看到过这篇文章吗?您会和作家交流观点吗?
陈众议:在我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30余万外国语言文学从业人员,相当于解放战争渡江战役粟裕麾下的主力队伍——我可能是同中国作家圈保持往来的极少数之一。我每年保持二三十部国内原创长篇小说的阅读量。其他中短篇小说和诗歌难以计数。由此,我会应约写一些关于国内作家的评论。
做文学批评难免吹毛求疵。因此,当莫言摘取诺奖桂冠以后,我除了替他高兴,第一件事便是写一篇自以为中肯的批评。我列数了莫言的五个过人之处,同时又认为这些过人之处或许恰恰也是他的“软肋”,譬如狂放的想象力、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不拘小节甚或蝌蚪效应等。我这不仅仅是为了批评的批评,而是想说明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评判文学的标准,遑论唯一。
舒晋瑜:早在2002年您就写过《文学理论到了该清理的时候》,20年过去了,您对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何评价?对于批评的重建您有何建议?
陈众议:我认为这方面的清算还不够彻底。至少对西方现当代理论的盲从依然存在,批评的武器远未转向武器的批判。而文学批评实践也尚未摆脱阿谀和恶搞现象。如何有礼有節、进退中绳尚需同道努力,“四个自信”和“三大体系”建设任重道远。我的建议之一是重温李健吾对巴金、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
舒晋瑜:对于拉美文学您的研究颇为深入,您如何评价魔幻现实主义对您、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
陈众议:拉美现当代文学的确是一座富矿。当然,在“冷战”时期对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文学的推崇和推介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原因。拉美文学左右逢源,加之后发的优势,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对我本人的影响毋庸置疑,我曾借用“集体无意识”概而括之。
我想,受拉美文学影响最甚的莫过于“寻根派”和“先锋派”作家,前者得益于马尔克斯(这是国人对他的简称,在此随俗,譬如有人告诉你达·芬奇应该叫列奥纳多),后者受惠于博尔赫斯。这是千真万确的。但究其原因,也许前者基于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和一代人对前现代的反叛冲动,后者则更加取法同现实生活的间离效果。这只是一概而论,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何况每个作家也在不断地发生窑变。
舒晋瑜: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您写过很多作品,比如《〈百年孤独〉何以畅销》《二十年后谈孤独》,2022年5月是《百年孤独》出版55周年,您有什么要表达的吗?
陈众议:《百年孤独》在20世纪80年代被中国作家奉为“圣经”,但在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抽样调查中,却成了“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而且位列外国文学作品榜首,就像《红楼梦》位居“死活读不下去”的中国文学作品之首一样。马尔克斯尚在世,他若听到这个消息,又当作何感想?我觉得他会高兴。毕竟他的作品可以同我国的第一名著对位并列了,哈哈!话又说回来,以范晔译本《百年孤独》的销量看,读它的人依然不少。它和《红楼梦》一样,是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阅读的。我对儿童和青少年朋友的忠告是多读文学作品,倘使你连文学经典都不肯多读,那么也就错过了许多“美梦”和“艳遇”、“深潜”和“飞翔”的机会喽。
舒晋瑜:您的译著多吗?能否谈谈当下文学翻译有哪些新的问题?
陈众议:我年轻时译过一些文学作品,但主要是零敲碎打,譬如博尔赫斯、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等人的作品,同时还翻译过一些古今诗歌。如果说文学是遗憾的艺术,那么翻译尤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活计。首先是阅读趣味的变化,其次是研究领域的发现,再次是语言习惯的移易,这些都可能决定译本的命运和不断被重译的必然,加上错译在所难免,因此不可能没有遗憾。马尔克斯就曾表示《百年孤独》中有二十几个错漏,有些已被研究界零星发现,我自己也发现过一两个。可惜其他“马脚”被他永远地带走了。自然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趣和使命,我的遗憾是后来退却了:当有人约我翻译马尔克斯时,我婉言谢绝了。
现在翻译有网络的帮助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因为有了网络和翻译软件,问题越来越多。但守望和专注于译德的青年人依然不在少数。寄希望于他们吧!
舒晋瑜:您曾著有《帕慕克在十字路口》,您和帕慕克有过深入交流?能否谈谈对他的印象?
陈众议:我担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期间先后邀请过七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是其中一位。他是很有个性的作家,率真而不失睿智,这不仅体现于他的作品,同样表现在他的为人。很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觉得他太任性,而我却喜欢他的这种性情。做事直来直去,讲话有一说一。除了在北京几天,我还带他去了我的老家绍兴。他很喜欢那里的风景和黄酒,结果有一次喝多了。我老家有一句箴言:“绍兴老酒后反堂”,意思是它后劲儿足。酒香又不冲,不知不觉几杯下去便可能被醉倒。同去的许金龙先生也不免多喝几杯,结果连皮夹子都丢了。
五、阅读就是蜘蛛织网的感觉:从一点开始,不断延伸,往返穿梭,这也是一般西方高等教育的取法:凡事都讲个学术史视野。
舒晋瑜:记得您好像提到自己最早的阅读是“听书”,那么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否谈谈童年“阅读”对您的影响?
陈众议:我上学比较早,当时未满5岁,在这之前一直在街头和茶馆酒店门前听人说书。此外,江南夏天闷热,于是家家户户都摊一张凉席、搬几把竹椅在街头消夏,街边总有清渠。太热了,孩子们就会跳到水里凉快一会儿,顺便摸鱼捉蟹玩儿。但凡有人讲故事,就会竖着耳朵倾听,也就顾不得玩水了。听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其次是《北宋杨家将》《说岳全传》,再次是《聊斋志异》《徐文长传奇》。后者属于少儿不宜,一般情况下大人会有所避讳,尽管我等偶尔侧耳听说一二也是有的。我开始阅读大概是在7岁那年,因为可以磕磕绊绊连猜带蒙地看书了,就开始大撒把,只要是文学作品,便逮着什么看什么。一直到“文革”和知青年代,阅读便成了习惯。
过去以为“三岁看大”“七岁见老”是一种迷信,如今却被科学证明是有道理的。就阅读习惯而言,我称之为童年的味蕾。由于读得最多的是演义类作品,从隋唐演义到明演义,其中当然还有《杨家将》《岳飞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等。外国文学最先入目的是《基督山伯爵》《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之类。同时苏联和国内的红色经典也一股脑儿地入目入心了。因此,“义”字早于儒释道进入我们那一代孩子的心志。这个“义”既是古来我国文化四要素之一的侠义,也包含了现代红色经典的正义凛然。
舒晋瑜:作为政协委员,您一向关注教育,不知您是否关注当下孩子们的阅读?可否在阅读方面提一些建议?
陈众议:目下孩子们的阅读情况令人担忧。究其原因,一是手机剥夺了孩子们阅读的兴趣,从小沉溺于游戏的不在少数;二是课业的压力过大,我曾多年就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本挺进基础教育、中小学校举手投降的结果。“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孩子们如果不能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很难想象他们走上社会后还有时间和兴趣沾染书香。
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从小学开始规定阅读纲目,而且必须同语文、思政和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同课业考核结合起来,甚至同中考和高考这两大杠杆结合起来。非如此,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
说到阅读,我不免想起两位前辈来。首先是钱钟书先生,围绕其一生的最大公案之一,便是他1949年缘何谢绝民国要员之约,坚定地留在大陆。关于这桩公案,当然也是私案,坊间曾有过许多揣测。最终杨绛先生在晚年用最简单也最温婉的方式了却这桩公私案:她说,“为了中文”。原来事情居然这么简单!其次,我的故友柏杨先生毕生致力于探究国民性,尤其是国民性的美与丑。他不像辜鸿铭先生那么乐观,用一个“gentle(温良)”简单概括国人的心性;但也不像钱玄同先生那么悲观,后者几乎偏激到了否定一切、横扫一切传统的地步。柏杨在鞭笞丑陋的中国人和褒奖美丽的中国人的同时,编修了《中国人史纲》,并雄辩地论证了国人何以对外平和、对内严苛的根本原因:几千年一亩三分地,以乡土为本的小农经济。他甚至认为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稳定性之所在。而我曾斗胆替他的这个稳定性附加了另一个关键因素:中文。如果没有中文,我们的文化也许早就被辽化、金化、蒙化、满化,甚至完全西化(或拉丁化)了。而守护中文、强健中文的最好方法无疑是文学,其中阅读与书写尤为重要。还是那句话,如果连文学名著都读不进去,那還能指望什么?好,不说文学家,看看钱学森、苏步青、杨政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一干科学家吧,居然也都个个饱读诗书、文采飞扬!
舒晋瑜:您在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师从于哪些名家,他们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在阅读方面,会给您具体的指导吗?
陈众议:我于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但半年后就被选拔为“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了。因此,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国外完成的。要说受谁的影响最大,那肯定是时任校长的苏步青。他既是著名的数学家,又是诗人。而且选派留学生的动议还是他率先提出来的。
由于外语水平太差,我的洋插队比土插队还苦,尤其是开始一两年,那真个儿是两眼一抹黑,两耳成摆设。但我曾经的口头禅是:“活都不怕,还怕那个苦吗?”(另一个版本是:“活都不怕,还怕那个死吗?”)因为成分不好,当兵报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尔后只能硬着头皮读洋文,但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成为作家甚至学者型作家,这可以无限伸展理想的翅膀,也可以尽情潜入别人的生活,无论古人今人、文臣武将。
为此,阅读就是蜘蛛织网的感觉:从一点开始,不断延伸,往返穿梭,这也是一般西方高等教育的取法:凡事都讲个学术史视野。这样由点及面,纵横捭阖,庶乎既见树木也见森林便成了一种阅读习惯。
舒晋瑜: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您想见到谁?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
陈众议:这我得想想。也许是巴尔加斯·略萨吧!他一生风流倜傥,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唯一的遗憾可能是竞选总统未果。我曾于2011年6月邀请过他,他来了。当时他还是新科诺奖得主,可谓意气风发。我当时最想知道的是他70年代中后期缘何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拳脚相向,以至于分道扬镳,连文风都为之一变,写起了艳情小说。可出于礼貌,最终我还是没好意思张口。我想现在旧事重提应该没什么忌讳了吧?2011年以后,老马和老略似乎渐渐言归于好了,何况人家马尔克斯已经去了天堂。与其谣言满天飞,倒不如说开了来个痛快。谣言之一是马尔克斯看上了略萨(这是国人对他的简称,我也一并随俗)的前妻加舅姨胡莉娅,又说马尔克斯钟情于略萨的第二任妻子加表妹帕特里西娅,总之都是桃色的。问题是他老人家80多岁了,如今又因为菲律宾名媛闹得满城风雨。呵呵,真想问问他如何打理文学与生活。
舒晋瑜: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陈众议:我可能会带三本最实用的:为了自救的《本草纲目》、为了生存的《鲁滨逊漂流记》和为了跟自己说话的《现代汉语词典》,当然我会把汉语两个字改成中文。
舒晋瑜: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陈众议:我会邀请马尔克斯,在他有生之年,我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同时我把略萨也请上。我还会邀请亚历山大大帝,他像个任性的孩子,笃爱听故事。但我最想邀请的是萨福,她是古希腊诗人,据说才貌双全,还男女通吃。俗话说,“三女一男是三娘教子”,那么三男一女呢?
舒晋瑜: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成谁?
陈众议:我想成为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或者图尼埃笔下的礼拜五,反正要去无人岛了。
作者单位:《中华读书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