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常思君
——追忆“文学圣徒”高贤均
北京/李 昕
陶渊明曾作《挽歌》,诗中有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说的是人去世了,会逐渐被友人淡忘,本是常情常理。但是,老友高贤均去世至今已整整20年,我对他的怀念却有增无减,他的音容笑貌常在目前,以至我几次在梦中与他对话。
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高贤均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们一同入职,一同成熟和成长。他担任当代文学第一编辑室主任时,我是第二编辑室主任。他当总编辑助理时,我是社长助理。在人们眼中,他和我是陈早春社长兼总编辑的左膀右臂,是社里培养的两个接班人,是“天生一对”,无法拆分。人们习惯地将我俩绑在一起,议论起来,基本是有高就有李,有李就有高。本来,我们应该是终生的“搭档”,但后来我被调往香港工作,他留在社里担任了“人文社”副总编辑。
记得那是2002年8月18日,我在香港接到“人文社”一位同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高贤均刚刚走了。他已罹患肺癌两年,这消息并不突然,但我内心仍然深受打击和震撼,悲痛至极。那位同事知我与高贤均相知甚深,便问我,社里委托他起草高贤均的生平,在遗体告别时使用,“你看最终应该怎样评价他?”
我想,高贤均走时很年轻(55岁),从事编辑工作只有20年,这样的编辑在老一代编辑心目中还只是年轻人。但是他论成就论贡献,却早已超过了许多老一代人。我觉得对他必须高度评价,所以说:“你一定要写上,高贤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一代卓有成就的出版家和编辑家。”这句话后来成了官方定论,登在报纸上,令我欣慰。然而不久以后,我听到陈忠实将高贤均评价为“文学圣徒”,感到这是文学家从另一个角度做出的点睛之论,可以和我的说法互补。
1982年,入职“人文社”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四个男生,高贤均、夏锦乾(后任《学术月刊》总编辑)、张国星(后任《文学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和我,曾被同在朝内大街166号大院里上班的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称为“四大金刚”。但在这四个人中,高贤均是最出众的。我们一同被送到校对科从学习图书校对开始进入编辑角色,从最初接触校样那一刻我们就发现,高贤均对于编辑工作简直就像有特异功能一样。那时校对科实行评分制,逐月为每一位校对的“消灭错误率”(即查出排字或版式错误的百分比)打分,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和夏锦乾马马虎虎可以打上80分,张国星则是把心思用在给作者挑毛病上,校对只满足于60~70分的成绩。只有高贤均,校样到他手里,好像错误会自动往出跳一样,几乎每次得分都在95分以上,令我们刮目相看。我那时就觉得,文化界喜欢把善于治学的人叫做“读书的种子”,其实当编辑也有天生的种子,高贤均就是一个“编辑的种子”。
高贤均特别适合当文学编辑,也是因为懂创作。他在大学时期就发表过剧本和小说,而且阅读涉猎极其广泛。中外文学作品,凡是在国内有一点影响的,他几乎没有没读过的。这对他判断文稿帮助极大。所以他审稿后给作者提修改意见,常令作者心服口服。这种能力使他在编辑部短短几年就有很高威信。至于创作,他写得的确不多,因为太忙,一年要看两三千万字书稿,平均一天七八万字,实在顾不上写。但他的中篇小说《七个大学生》在丁玲、牛汉主编的《中国》杂志发表以后,与我同在一个编辑室上班的文学评论家杨桂欣赞不绝口。他对我说:“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高贤均背后的文学积累。在你们‘四大金刚’里面,数高贤均最有才能。”我说:“我们四个人的才能不是各有侧重吗?怎么能一概而论?”杨桂欣说:“你没发现吗?高贤均特别善于钻研,他现在是搞当代文学创作,没有进入其他领域,如果他搞别的,也一定成功。比如,他如果和你一样搞文艺理论,恐怕就会比你强。”
杨桂欣这样说,我是服气的,相信他看人很准。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发现高贤均身手不凡。他1978年考进北京大学时是四川省的文科状元,当时他已经背过两本词典,即英汉词典、俄汉词典,上大学没上过一天外语课。他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中学时代已经读完《鲁迅全集》。他的学识积累比我们都要早上很多年,他的文化修养着实让我们佩服。我的直觉,他有条件成为一个很棒的作家或学者。
我很早就知道高贤均有一个作家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忽然有一天他说要写长篇小说,腹稿都打好了。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他的时间和才华都用在编辑上了,“为人作嫁”,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后来他做过自我分析,说如果把编辑工作丢在一边,自己埋头写作,他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但不会是很优秀的(这当然是自谦之语),但如果专心做编辑,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编辑。他的结论是:“与其当三流作家,不如当一流编辑。”这后来就成了他给自己人生道路的定位。他很享受编辑工作,曾说:“我给作者提提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提高作品质量,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凡是与高贤均合作过的作者,对他的文学修养和编辑能力不仅认可,而且佩服。远的不说,就拿我本人作例子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些东西,曾经想尝试各种创作。我不怕丢丑,写了作品,总是第一个拿给高贤均看。我曾参考自己大学同学的一段经历,写了中篇小说《望尽天涯路》,描述一个既自卑又自负的青年人的心理悲剧。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时候完全不知该如何落笔。高贤均看后,说情节很好,但是太平铺直叙了。他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要把结构打碎,把单线变为复线,把单向度时空变为交错时空;二是告诉我,整部作品中,缺少几个“弯”,就是可以调动读者情绪的转折性细节。“文似看山不喜平”,有几个小小的转折性细节,使读者有出乎意外的感觉,就不平了。我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一遍,后来作品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竟然还引起《新华文摘》重视,给予全文转载。
后来我又写了一个短篇名叫《七色光》,作品是写一个经济拮据的青年知识分子家庭,买不起彩色电视机,而当时北京电视台天天播放的儿童节目名叫《七色光》,内容很好看,但这青年家五六岁的儿子不愿看自己家的黑白电视,天天往邻居家跑看彩电,由此引起父亲和儿子之间心理上的对抗。高贤均看了以后,认为故事的立意没有问题,但是表达平庸。他对我说:“你和我是一样的人,咱们的心理都太正常了,这样是写不出好小说的。你要把自己变成作品中的人物,他的性格中应该有一些怪异的因素,你就要把自己变得‘怪’一点,要发一些奇想才行。”他说,他自己写小说,也常常需要“克服”自己心理过于“正常”的毛病。对此我极受启发。后来这篇小说修改后,被台湾作家郭枫看重,发表在台湾的《新地》杂志上。
至于高贤均在编辑出版中发现好作品和帮助作者修改书稿的故事,那就实在太多了。他是一个永远可以给我信心的人。我刚开始担任编辑室主任的时候,他曾经是编辑室副主任,遇到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凡是拿不准的,我一定会问他。记得有过很多次,我和他一起同作者交流,只要有他在,我就以他的意见为主,因为他的意见总是更加专业,且更加系统。他曾经支持过很多别人并不看好的作品在“人文社”出版,这正是显示他的眼光和水准的地方。例如麦天枢广受赞誉的获奖长篇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最初由我交给一位曾经创作过报告文学的老编辑审读,没想到他提出完全否定的意见,主张退稿。这时我向高贤均求援,请他帮忙判断。结果高贤均却大声叫好,认定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令此稿起死回生。后来我特地做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为其作序并热情推荐,实话说,我的底气,一半来自高贤均。另一个例子是云南青年作家邓贤的获奖作品《大国之魂》,内容新颖、史料丰富,但因为作者没有写作经验,书稿结构很不成型,题材也稍微敏感。接手书稿的《当代》杂志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要用,有人要退,最后一直弄到社领导分出两种意见。后来是社长找到高贤均和我,我们都写了肯定性的意见,同意这本书做一些修改后出版。我清楚记得高贤均当时读到邓贤作品时满脸兴奋的神态。他对于邓贤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描述抗战时期滇缅战场的情景是极为赞赏的,认为此书是填补当代文学空白的力作,并预言此书会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出版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这部后来好评如潮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投稿和出版之路却极其曲折。1994年完稿以后,阿来四处投稿,却经历了多家出版社数次退稿。客气的答复是给作者寄一封退稿信,那不客气的,就是书稿石沉大海。退稿的原因,想必是出版社对这位无名作者没有信心,不看好市场。直到四年后的1998年,“人文社”编辑脚印拿到了书稿,事情才有了转机。脚印喜欢这部作品,但是她需要得到领导的首肯,于是把稿子转给时任副总编辑的高贤均。高贤均当时正在患病休养中,但他很快看完稿子,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对脚印说:“我是真喜欢这部作品!我等了很多年,咱们四川终于等来了一个会写小说的作家!(高贤均和脚印都是四川人)这本书咱们出版,你一定要好好编。”于是一锤定音。《尘埃落定》以急件安排出版,除了获奖以外,还成了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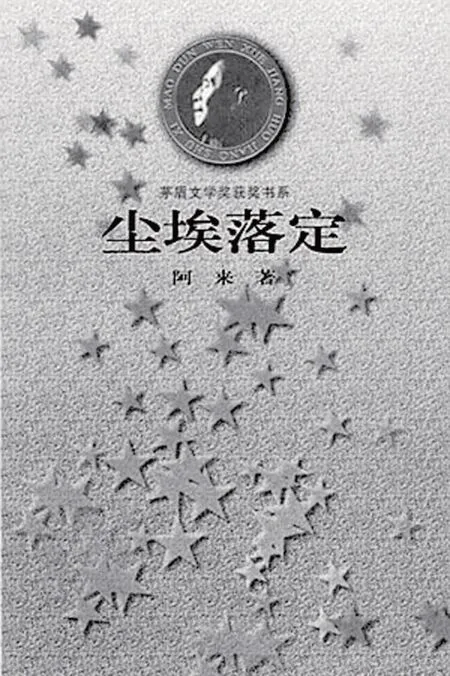

“人文社”是出好书的地方,但是好书要有人识,有人编,有人拍板。好书的背后,总有人默默奉献。高贤均是这家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出版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堪称幕后英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学优秀作品的编辑出版,从《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活动变人形》《纪实和虚构》《南渡记》,到《白鹿原》《尘埃落定》《历史的天空》《日出东方》《狂欢的季节》,以及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等等,都与高贤均有关。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会懂得,这一串书单的分量有多重,它意味着什么。有人对我说,高贤均就是在深夜审读《哈利·波特》校样的时候,吐出第一口血,从而被确诊为肺癌的。原本作为副总编,他根本不必去理会什么校样,但是他的责任心驱使他亲力亲为。在上述所有图书中,高贤均有时是责编,有时是审稿人,有时参与出版策划,有时是决策人。总之他作为幕后推手,时时显示出独具的眼光、魄力和胆识,以及丰富的编辑经验。
我以为,高贤均能够有这样夺目的业绩,不仅基于他的文艺修养,而且基于他对出版事业的挚爱,和他对编辑工作的一种燃烧的激情。
他去世后,大家怀念他,有很多同事和作者写了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我把那本杂志找来看,发现大家想起高贤均总会回忆起同一个场景:大家都记得他每天中午端着盒饭这个屋聊一会儿,那个屋聊一会儿,聊的都是看稿子的事。他这个人,日复一日地看稿子还总是那么兴奋,一有新发现马上跟别人分享。我至今都记得他给我讲的两个细节。
有一次高贤均看了阿城的《树王》,跑来告诉我说,阿城写树的细节是自己过去没有观察到的。作品描写的是巨大的树,写风从左边刮过来,树叶就从左边开始抖动,然后到中间,再渐渐波及到右边,树的抖动不是呼啦一下展开,而是有层次、有波浪的。高贤均说,阿诚的观察多么细,他原来没注意过,看了阿城的文章后才有意识地去看,果真如此。还有一次,高贤均读了《白鹿原》书稿,很兴奋地跟我说,你快去看看“黑娃吃糖”是怎么写的。作品中黑娃是个苦孩子,长到十几岁从没有吃过糖,当有人给他一块冰糖时,他不知是什么东西,以为是石子。当他把冰糖放进嘴里,他愣住了,从来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神奇的滋味,从眼珠到整个身体顿时就不会动了。这里,作品对黑娃表情的描写简直是一绝,写他竟然浑身颤抖,继而哇哇大哭。吓得别人以为他的喉咙被卡了,慌忙掐住他的腮帮,要帮他把糖向外抠,其实他那只是幸福的表现,他被那甜甜的味道震撼了。高贤均说,这个细节写得太精彩了,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陈忠实的功力。
那时,每天中午我们和高贤均一起吃饭,总是听他讲这些。我觉得他真是激情满满,沉迷于书稿,沉迷于文学作品,全情投入,入戏很深。
关于高贤均以激情编书的故事,有两个很好的事例,我曾多次在高校和各大出版集团开设的编辑学课程中当作案例。
一是关于《白鹿原》,我要说说高贤均在这本书出版中的作用。《白鹿原》书稿,是“人文社”副总编何启治早早约定的。他从上世纪70年代前期陈忠实刚刚写过一两个中短篇开始,就发现了这位作者的创作潜能,建议作者写长篇。但陈忠实直到20年后才完成这部巨作。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天,陈忠实通知何启治,可以交稿了。正好此时,高贤均和《当代》编辑洪清波要到成都出差,何启治就说,请你们顺路去一趟西安,陈忠实有稿子,你们先看看。于是高、洪二人去西安见陈忠实。
我看到当时情景的有关记录是这样:陈忠实拿出的书稿是手稿(那时没有方便的打印条件),40万字的书稿很厚,他把稿子包了又包,裹了又裹,里面是牛皮纸,外面是塑料袋,打成一包,很郑重地交给高贤均和洪清波。然后他说:“我这是把多来年的心血托付给你们了。”高贤均当时要打开,陈忠实慌乱地说:“你不要打开,你不离开这里不能看。”我猜想,其实陈忠实是心里害怕,担心用六年时间写出的成果不被承认(作者在这种时候很紧张,像接受考试一样,压力山大,这是正常心态)。要知道,陈忠实在家里六年闷头创作《白鹿原》,除了这本书稿以外,其他创作很少。他在此之前没有写过长篇,中短篇也没有太大的反响,所以他老婆不断讥笑他,说他还不如开养鸡场,养鸡还可以指望吃几个鸡蛋,而他这些年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陈忠实曾经跟老婆说,这部作品不成功他就开养鸡场。他是把这辈子命运的宝,都押在这本书上了。
高贤均和洪清波拿到稿子后马上坐上去成都的火车,一上火车就开始看稿。高贤均和洪清波一起轮着读,到了成都又利用会议间隙读,还没回北京,两人都把稿子读完了,工作如此神速,显示了编辑的激情和敬业。回到北京后,高贤均第一时间写了一封信给陈忠实,说这是一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注定要留下一笔的书,是他看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最有分量的一本。陈忠实后来回忆说,高贤均拿到稿子只十天就给他来信,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快递,一封信就要走几天,而高贤均又要开会又要赶路,居然有这么高的效率!陈忠实也没想到高贤均的评价这么高。收到信后他欣喜若狂,猛地翻身从沙发上跳起来。他对老婆说:“我不用开养鸡场了!”后来高贤均和洪清波做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白鹿原》获得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评价——茅盾文学奖。
另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就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的出版。这部书稿在到达“人文社”之前,也曾被两家出版社退稿。作者徐贵祥写了一篇文章回忆此事,说他曾经想把这稿子一把火烧了,从此不写了。结果就在心里很矛盾的时候,他见到了“人文社”《当代》杂志的编辑,提到了这部稿子,那位编辑说愿意拿回去看看。过了几天,徐贵祥打电话问编辑:“你觉得怎么样?”编辑说:“说不好,我一个人看怕判断不准,转给小说组编辑也看看吧。”于是稿子就被转给“人文社”小说组另外一个编辑。这位编辑看完后,作者去电问:“你觉得怎么样?”那位编辑也说:“拿不准,还是给领导看看吧。”这样稿子才到了高贤均手里。高贤均在一周后直接给徐贵祥打电话说:“请你来,我要跟你面谈。”
“人文社”副总编直接找他面谈,把徐贵祥吓了一跳,因为当时他还是没什么名气的作家。后来作者在回忆文章里描写了他到高贤均办公室后的情景:
高贤均高度评价这部书稿,他当着几个编辑和作者,“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双手舞动着讲了一个多小时”。这让他感觉到自己幸运地遇到知音了。关于稿子里涉及的国共关系的敏感话题,就是前面说到有些人拿不准,有些出版社因此而退稿的那些内容,高贤均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可以说是秘授机宜。作者说,其实高贤均提的都是些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四两拨千斤,操作起来一点不困难,作者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最后高贤均做了总结,对作者说:“你就照这个方法改,改完以后我给你做两个预测:第一,这本书可以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第二,这本书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很有竞争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测全都正确,这本书出版后一共获得四个大奖:“解放军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试想一下,两个出版社退稿,本社也有一些编辑拿不准的书稿,到高贤均手里变成这样,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吗?
“人民文学奖”评奖的时候高贤均已是肺癌晚期,距他去世只有两三个月,但他作为评委,坚持从医院赶来开会,上台讲了20分钟话,介绍《历史的天空》。后来作者提到这件事非常感动,他说一想起高贤均就流眼泪,还说对高贤均他无以报答。“人文社”的编辑就跟他说,你要想报答高贤均,今后有好稿子就都交给“人文社”吧。作者就承诺说:“好。”我以为,这纯粹是高贤均以自己对文学事业和对作者的一片赤诚换来的。说他是“文学圣徒”,信然。
2012年8月18日,高贤均去世10周年时,作者们来到他的墓前。墓碑的题词是作家阿来所拟:在人间编好书;去天堂听妙音。特别要说明,高贤均是一位古典音乐超级爱好者。
高贤均去世20年了。“不思量,自难忘”。我今天在这里追忆他,因为我感到他的名字是值得出版界同仁永远铭记的。他身上的那种执着、勤奋、充满激情的敬业精神,理应得到后来者的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