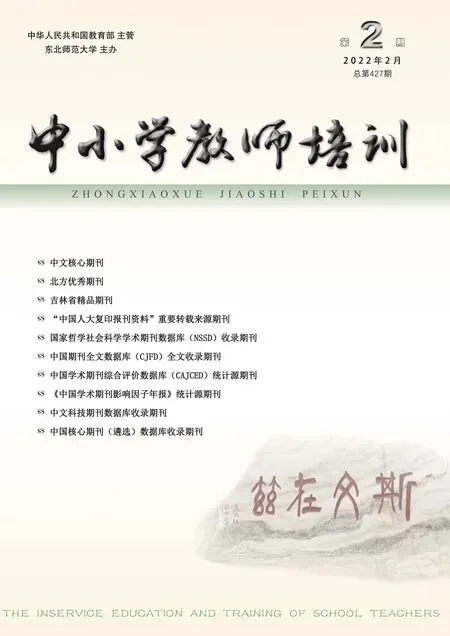读写共生:内涵、特征和实施路径
仇定荣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 江苏 常州 213131)
阅读与写作,乃语文教学的两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叶圣陶先生说得甚是明确:“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之。”[1]“国文课的目的,说起来很多,可是最重要的只有两个,就是阅读和写作的学习。”[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表述得更具体,必须“重视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口语交际教学之间的联系,善于将读与写、说与写有机结合,相互促进”[3]。由温儒敏教授担任主编的部编初中语文教材,深入贯彻新课标精神,不仅秉承了读写结合的教材建设理念,还在助学系统、“活动·探究”单元、综合性学习、名著导读、写作等五大板块中充分落实。因此,我们不仅要夯实阅读和写作这两项最基本的语文能力,还要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让阅读和写作从“结合”上升为“共生”,从“单向联系”跨入“相互促进”,彰显阅读和写作“双剑合璧,威力剧增”的共存共促、共生共长的综合效应和高品质教学智慧。
一、读写共生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读写共生,伴随着共生理论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在语文教学之中。其最早的提出者为全国语文名师黄厚江先生,是其实现“本色语文”教学主张的一种主要机制。
“共生”,原本指的是在生物学上不是同一种属的生物却能够通过彼此借助自身的特性在环境中共同存活、共相发展的一种生物学现象;同时,这些生物在与其他生物或者外部生存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形成密切共融的联系,也可以叫作共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共生的本质是协商、合作与融合,强调的是相互之间的依存和促进关系,最终达到共生互惠的状态。概括地说,就是“互促共进,共生共长”的意思。
读写共生,是指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通过阅读和写作之间的不断往复和交融,在信息的输入、输出过程中,实现言意共生、促进言语生命成长的融合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强化读和写的深度融合,更突出在此基础上的共生共长。透过这一基本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读写共生的核心是关注阅读与写作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生互惠,最终达到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协同提高的理想境界。其主要特征为:
(一)相互促进性
共生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事物之所以发展、生物个体或群体之所以成功的“奥秘”。阅读和写作作为语文教学的核心,所要表达的内容和建构的样式是相同的,仅仅是侧重点有所差异:阅读强调的是吸收,写作突出的是倾吐。从其本质上看,阅读是写作的起点和基础;写作是阅读的升华和创新,两者和谐相生,互促互进,共同承担着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任。
(二)实践创生性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4]无论是基于阅读的读写共生,还是基于写作的读写共生,都是基于语文实践基础上的创生过程。这是因为,学生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写”,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生活化情境,不仅需要紧扣文本内容生发开来,创作一段文字、一个片段乃至成文之作,还要调动习得的写作方法,自如地运用于作文之中;同样,学生在写作时,必然会阅读并借鉴文本中的内容和技法,努力把作文写好写美。如此看来,读写共生的过程,就是通过构建动态的创生性教学过程,达成“读”与“写”之后的实践性创生过程[5]。
(三)整体推进性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是学生在读和写两种能力培养上的相互交融。这是因为,学生在建构自己的文本意义时一般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参考、借鉴其所阅读过的文本,运用阅读这些文本所获得的经验,建构自己所需表达的结构图式和言语图式,如谋篇布局、语言表达、手法运用、立意选定等;同时,学生在写作时必然会把阅读之习得内化到自己的作文之中,或写作内容的渗透,或作文框架的建构,或写作方法的借鉴,或语言文字的迁移……所以,阅读和写作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为同一个学习系统,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相互作用,整体推进。
(四)相互体验性
读写共生目标的达成过程,不仅是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更是一种体验提升的过程。一方面,学生将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某种写作知识和写作技法,在特定目的和特别情境的指引下,通过特定的写作要求和创作行为,建构了新的认知结构和言语图式;另一方面,学生在写作实践时,不仅紧扣本单元主题,再度阅读文本,吸纳着单元课文的谋篇布局之法和写作知识,而且将独特的生活感悟与阅读之所得进行友好的“碰撞”和“融合”,从而创作出形神兼备的作品……这样的过程,充溢着读写共生的美好体验,彰显着读写能力的同步提升。
(五)纷繁复杂性
物质世界中不同事物的共生现象,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读写共生教学,依然如此:不论是指向于“读”的读写共生,还是指向于“写”的读写共生,抑或基于专题的读写共生……也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就要求我们精心策划,用心设计,有序推进,才能收获共生的双赢效果。
二、读写结合与读写共生的比较
从一般意义上看,“读写结合”与“读写共生”似乎是相同的,两者并没有什么多少差别,仅仅是将“结合”替换为“共生”。其实不然,若能站在研究角度考量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真正的区别恰巧就是“结合”和“共生”这两个词语的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
读写结合,就是将阅读或写作当作一种工具,为特定阶段的写作或阅读服务,即借助对方来促进写作或帮助阅读,一旦完成任务,就束之高阁,弃之不顾。
【案例1】 教学《中国石拱桥》一文时,有这样一个环节:仔细观察图片“扬州五亭桥”,并依据“五亭桥状如莲花,于黄昏时,格外美丽”这一简明材料,为下面的片段续写一段文字:五亭桥是由五个亭子构成的联拱石桥。登桥远望,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若于岸上望去,可见________。
这个教学片段,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读写结合”,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想象进行写作,更好地理解举例子的说明方法(既要紧扣说明对象的特征,又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茅以升先生就说过“中国最古老的桥是赵州桥,最壮美的桥是卢沟桥,最具艺术美的桥就是扬州的五亭桥”),而没有让阅读反哺写作,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
读写共生,强调的是双向互动,共生共赢,不仅把阅读或写作当作一种提升自我的方法手段,而且力求能够服务好对方,促进其提高,强调反哺和馈赠。因此,“共生”是双向的互帮互助,是共享硕果,是彼此主动“介入”。
【案例2】 教学《穿井得一人》一文时,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活动:请你仿照前两则寓言《赫尔墨斯和雕像者》《蚊子和狮子》的结尾,用“这故事适用于那些________的人”的句式,补写本文包含的道理。
这个教学环节,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读写共生”。这是因为,一是选点精准,用仿写的形式提炼主题,实现了“读写结合”;二是互促双赢,这里的“写”,让主题概括得简明凝练,强化了“读”;同时,这里的“读”,既要深度阅读原文《穿井得一人》,还要浏览《赫尔墨斯和雕像者》《蚊子和狮子》,并揣摩结尾的内容和形式特点,这就自然促进了“写”。于是,“共生”特质得到了充分彰显。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传统意义上的读写结合,其内涵还比较模糊,只是指向于“合作”,但没有明确具体路径。事实上,在认知科学理论看来,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结合”,而是彼此“介入”的关系。在英语语境中,读和写是“合作和介入”的关系,“connection”(结合)这个词极少使用,而多用“integration”(介入)一词。因为“介入”比“结合”更能体现读写之间的互促共进、共生共长的融合关系[6]。
如此看来,读写结合,仅仅是在阅读或写作之中偶然的一次“单线联系”,是属于“一次性交易”;读写共生并非如此,阅读和写作是双向的互动交流,彼此平等的合作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阅读和写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读有效地促进“写”,写更好地促进“读”;读写和谐相生,彼此介入,共同提升着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读写共生的实施路径
读写共生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强调了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共生关系,在阅读教学中融入“写”的积极因子,在写作教学中发挥“读”的引导效应,使读与写相互作用,和谐双赢。然而,由于统编语文教材编写采用“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双线组织单元的结构形式,在日常的阅读和写作教学过程中,还是以分开的居多,因此,读写共生的真正落实,一般说来,还必须依据不同的课型采取不同的实施路径。
(一)基于“阅读”的“读写共生”:立足阅读,以写促读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依据文本特点和教学需求,适时穿插一些适量适度的、与此时此景的文本阅读密切关联的写作实践环节,使之既促进深度阅读又锤炼写作能力。这种立足于阅读的读写共生教学,阅读教学无疑是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教学行为,承担着一堂阅读课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写作则是渗透于阅读之中,起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双重功效。
换句话说,就是在教学文本的重点处、难点处、关键处,抑或学生阅读的忽略处、易错处、疑惑处,精心设计并自然得体地配以适量的写作实践活动,让写作不仅肩负起“促进阅读”的认知功能,还具有“表情达意”的交际功能,进而达成阅读与写作相互交融、和合双赢的共生效果。前面列举的《穿井得一人》这一教学案例,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促读”型“读写共生”教学策略。
(二)基于“写作”的“读写共生”:为了写作,以读促写
在写作教学过程中,依据作文题目(话题)、训练目标,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与写作密切相关的典型语句、示范片段或同类文本进行阅读鉴赏,使之既能提高写作水平又能拓宽阅读渠道、分享阅读的甘甜。这种立足于写作的读写共生教学,写作是“主角”,它通过教师的精要指导和学生的当堂练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篇主题鲜明、结构完整、语句流畅的完整片段或命题作文。阅读只是配角,在作文指导和写作实践中引入的这些阅读材料:一是让学生拓宽写作范围,明晰写作思路,借鉴写作方法;二是扩大阅读面,让类文阅读、群文阅读的路径更为宽广,从而自如地达成读写共生教学目标。
通俗地说,基于写作的共生教学,就是阅读为写作服务,重在通过精要阅读,为写作提供语言积累、素材资源和写作技法、文本样式等素材,同时又为阅读本身打开了一扇明艳的窗。此时,阅读是作文的“路基和桥梁”,写作才是真正的成功“到达彼岸”。
【案例3】 部编教材八上第四单元的写作训练是“语言要连贯”,并附有写作指导。为此,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了五次前后勾连的读写共生活动。(1)阅读《语言要连贯》写作指导短文,用3个四字短语概括。(2)阅读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说说文章是如何体现这三个要求的?(3)以《答谢中书书:语言连贯的标杆》为题,依据“知识短文”的三个要求,以6人组为单位,分工完成“主题鲜明紧扣美、顺序合理分层美、衔接过渡连缀美”三个话题中的某一个写作任务(不少于100字)。(4)仿照示例(略),将“高峰入云……四时俱备”这6句话改写为不少于150字的片段(写作要求同(3))。(5)以6人组为单位,将各自的习作组合成一篇完整的鉴赏性作文(开头和结尾已经在“当堂训练”中提供),教师点评、出示下水文并加以总结。
这是一堂比较典型的基于写作的读写共生指导课。活动一:阅读《知识短文》,为了把握“语言要连贯”的三个基本要求,即“话题统一、顺序合理,衔接过渡自然”,这既是为了写作而明确目标,又培养了学生提取信息的概括写作能力。活动二:阅读《答谢中书书》,一是为了借助例文印证“语言要连贯”的三点写作要求,二是架起了阅读和写作之间的桥梁。这两处的读写共生是基于“读”,但宗旨是为了“写”。活动三和活动四:依然要阅读相关材料(或文本,或示例),但理解基础上的写作才是根本。此时的读写共生,还有“读”的因子,不过已较为隐蔽,真正呈现出来的是“写”出来的作品。活动五:组合完成习作,依然需要阅读,方能挑选精品组合成一篇精美的赏析作文;而教师的下水文和小结则将“读写共生”推向巅峰,学生之读写和教师之读写完全融为一体,共生共长。
(三)基于“任务”的“读写共生”:专题读写,多元融合
这是指借助“阅读”和“写作”的共同配合,多元合作,一起来完成某一任务的读写共生教学策略。此时的阅读和写作,已不再是看上去似乎简单的“以读促写”和“以写促读”,而是有着深度融合的“携手共进”,它们随时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综合参与意义的建构和任务的完成,逐步实现从读写结合到读写共生的跨越[7]。统编教材在八、九年级安排的新闻、演讲、诗歌、戏剧等四次“活动·探究”单元,就是“任务型”读写共生的“风向标”。此时的共生,整合了多方面的元素——既有阅读共生,也有写作共生;既有资源共生,也有情景共生;既有思想共生,也有精神共生。
【案例4】 部编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活动·探究”单元,包括新闻阅读、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三项任务。就单元编排形式看,读写共生理念已“暴露无遗”。我们不妨看一个《新闻写作》的教学设计,主要包括5个任务:(1)观看2004年雅典奥运会郭晶晶三米跳板的决赛视频,并拟写一个标题。(2)阅读《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两则消息的标题,把握标题的基本要求和情感倾向,并完善拟写的标题。(3)阅读郭晶晶三米跳板决赛的有关补充资料,并深度阅读《消息二则》,为该消息撰写导语和主体。(4)阅读“倒金字塔结构”的相关知识,并修改习作;展示下水文,完善其习作。(5)阅读通讯《“飞天”凌空——跳水姑娘吕伟夺魁记》,而后改写为一则消息(包括写作、师生互评、教师下水文展示)。
这是一则典型的“任务型”专题读写教学案例,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读写共生。从阅读层面看,单篇阅读,适时兼顾群文阅读;课内阅读,更倾向于课外阅读;有文本内容和主题理解,更有方法和技巧指导……这些,不只是为阅读而阅读,更是为了写作而阅读。从写作层面看,有一句话写作,有片段训练,更有成文创作;有学生习作,更有教师之作……这些,是为了写作,但同样深化了阅读。简而言之,这种高度综合的读写共生课堂,让“消息阅读、消息写作、消息采访”三大任务得到了圆满完成。
读写共生,乃阅读与写作交互融合的至善境界,其要义在于打通读写之间的关隘,以读引写,以写促读,强调读与写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因此,语文教师要依据部编语文教材,善于发现两者的“共生点”,构建有效的训练体系,为读写共生铺就厚实的路基,以期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