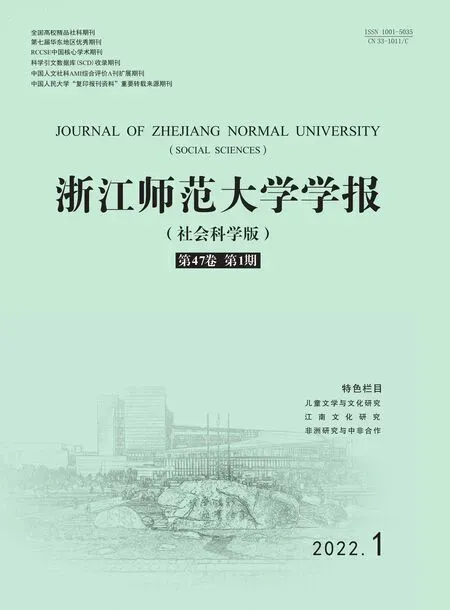“一段心灵朝圣的旅程”
——彼得·马修森《雪豹》中的佛禅思想
徐向英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序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思索的一个永恒话题,但西方的主流文化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环境污染这一外部严峻现实的困扰,西方的主流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开始有了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也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环境保护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方的佛禅思想以其固有的对人与自然的深刻认识,恰逢其时跨洋越海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对这场环境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识之士冲破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向曾经被主流文化认为是原始、落后、边缘的东方思想学习古老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把东方思想的万物一体观和联系观吸纳到自己的创作思想中,反思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态。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1927—2014)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马修森是美国当代作家,也是一名佛禅信徒。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自然文学写作,他都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是少数几个被美国国家图书奖数度垂青的作家之一。1966年、1973年他先后入选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79年、2008年先后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以虚构类作品和非虚构类作品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接触佛禅,直到2014年去世,马修森对东方佛禅的热爱体现在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文学创作,佛禅都对马修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要深入理解马修森的世界,佛禅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国外,马修森与东方思想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Rebecca Raglon(1994)①通过小说《海龟岛》(FarTortuga,1975)分析了马修森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发展与佛禅的关系。Mark Christopher(2001)②认为马修森的疏离感和孤独感源自于他遵循的西方男性准则,所以他的救赎之路在佛禅。他分析了12世纪中国禅宗的《十牛图》在《雪豹》(TheSnowLeopard,1978)中的体现,并指出佛禅与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和感情的相通性。Intaek Oh(2005)③指出马修森环境主义的非二元论核心思想先是由他的禅宗实践所塑造,后来又在印第安人地球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启发。作者认为,禅宗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土著印第安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两者都以其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万物一体的观点。国内,通过知网查阅发现,目前除了徐向英(2017)④从东方视角分析中国水墨画的留白手法对马修森小说《海龟岛》的叙事方法和叙事主题等产生的影响外,鲜有其他相关研究。综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佛禅对马修森创作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马修森是个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30多部作品,其研究空间还很大,有待进一步发掘。本文以作家最直接阐述佛禅经历和体验并为其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的自然文学《雪豹》为具体文本分析对象,并辅之以作家1969年至1982年间写作的禅修日记《九条龙河:1969—1982的禅修日志》(1985),从佛禅的角度,分析作品中蕴含的宇宙一体观和不修之修的顿悟修行方式,呈现作家对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思考以及他对西方生存状态的反思,以此呼吁人们学习古老东方的文明。
一、“我随着大地的起伏而吐纳”
1973年秋天,马修森接受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的邀请,陪同他穿越尼泊尔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到达青藏高原的多尔波地区,协助他研究生活在雪山上的喜马拉雅蓝羊和以猎杀蓝羊为生的雪豹。这便是自然文学《雪豹》的创作缘起。不过,对于已经接触佛禅多年的马修森而言,他此行的目的绝不仅仅止于此。从世界各地物种的灭绝到雨林的萎缩,从各种土著传统文化的消失到人类的大屠杀,马修森的一生似乎都在与暴力、失去和死亡作斗争。这次的旅行也不例外。1972年冬天,他的第二任妻子黛博拉·拉芙(Deborah Love)因癌症去世。马修森带着失去妻子的悲痛踏上了这段旅程。他希望借助这次机会能够参观位于青藏高原上的水晶寺,拜见那里的大师,学习东方佛禅对生命、死亡和无常的理解,以减轻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悲痛和内疚。所以,《雪豹》与其说是他和夏勒两人研究蓝羊和雪豹的考察之旅,倒不如说更是马修森的一场心灵之旅。正如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所说,这场千里迢迢的旅程是“一场真正的朝圣,一段心灵朝圣的旅程”。[5]3《雪豹》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在雪山中与当地向导、挑夫、冰雪、巨石、卷云、鸟兽为伍的旅程中所领悟到的种种内心体验以及由此而发的他对东西方文明和生存状况的思考。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但其主流思想是二元观,崇尚个人主义。二元观是一种两极思维,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理性与感性、人类与自然等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在这种两极对立思维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片面化的世界,非美即丑、非善即恶、非黑即白,“如此这般形成的画面是一幅可怕的画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本真的原初的自然之中,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工的、文化的自然中”。[6]75显然,这种试图以二元模式理解并建构世界的对立思维就如同盲人摸象,蒙蔽了人的双眼,使人深陷在“自我、个体存在和梦想的幻觉中”,[5]63这些幻觉限制了人们洞察个体与宇宙同为一体的能力,阻碍了人类看清事实的真相,所以“只能有限地写照生命”。[5]61与二元观思维密切相关的是位于“美国民族神话核心”[7]144地位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主体,以利益为中心,崇拜物质主义,鼓励自由追逐财富上的成功以满足各种欲望。这种对自我个性的彰显、对成功的执念和对物质的欲望,使得人们生活的地方,用马修森的话说,就像“荆棘和杂木”,充斥着“理念、恐惧、防卫、偏见和压抑”。[5]38这种由二元观和个人主义所建构的自我一旦形成,衍生出各种沉重如“盔甲”般的观点、成见、思想和诸如“过去、现在和未来”等抽象概念时,人们就失去“对事物本身的直接、自发的体验”,[8]8“简单的、自由的存在”[8]6就被剥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感和紧随其后的人自身的恐惧感和孤独感也就形成,“人把自己封闭起来,最后只能隔着黑牢的狭缝看万物”。[5]35
马修森承认自己继承了西方的主流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塑造了他的性格,导致了他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在的欲望、恐惧、空虚、孤单和失落,“在每一次呼吸的底部都有一个空荡荡的地方,充满了需要填满的渴望”。[8]7为了填满这个空荡的地方,寻求精神寄托,他多年来不停地流浪,投身到一场又一场的追寻中。在《雪豹》中,他回忆了自己1945年在海军舰艇上遇到太平洋风暴的一个小插曲:“浪花一再冲过甲板,最后水、空气和钢铁融成一片……一切思想和情绪都化为乌有,自我意识完全消失。”[5]36在那一瞬间,马修森忘掉了自我这个个体,强烈地体会到一种与大地融为一体的幸福感,“我听到的心跳就是世界的心跳,我随着大地的起伏而吐纳”。[5]36这种幸福感让他的心久久无法平息,从此开启了重新寻找这种体验的一系列旅程。从20世纪60年代起,像那个年代离经叛道的“垮掉一代”年轻人一样,马修森开始大量尝试迷幻药,到世界各地寻求原始部落的智慧,但始终都达不到与大地起伏吐纳的体验,也无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直到他遇到东方的佛禅,才让他的生活“焕然一新”。[8]7
佛教禅宗(简称佛禅)是佛教体系的一支,在进入中国后受中国道家哲学的影响,融汇了中国的文化,视野非常宽阔,形成了独立的思想体系。不同于二元建构世界的对立两极思维,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佛禅认为“虽然宇宙由对立的一对对组成:光明与黑暗、男人与女人、声音与静寂、好与坏,但所有这些对立都是相互的,因为它们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9]3换言之,这些对立只是相对而言,不过是表面现象,形式或形状不一样而已。一旦超越这个表象,就会发现万物皆为同一本源,其内在的本质是一致的,“虽然宇宙万物有不同的名字和形状——太阳、月亮、高山、流水、人类等等,但其都是由同一物质构成”。[9]3显然,佛禅对宇宙的感知是一体的,其否定二元对立,以超越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回归万物的和谐统一。在具体修行方法上,佛禅不像西方宗教有经典、教义和救世主;相反,佛禅不向外觅求,而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10]243是一种“不以文字或字母为基础的在经文以外的特殊传播,它直接指向人类自己的心灵,让他看到自己的真实本性”。[8]6具体言之,佛禅认为,要真正达到顿见本性,把握本体,依靠语言、概念是不可能的,只有凭借直觉的体验和内心的瞬间觉醒,即,“如桶底之脱”般的“顿悟”,[10]250才能感悟自然中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的美好和圆满,从而泯灭主客二分的两极对立,洞彻世界一体的真如实性。
在马修森看来,“宇宙本身就是圣经,宗教正是每一刻对上苍的领悟”,[5]28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救世主”。[5]38在两个多月一步一个脚印的漫长旅途中,在远离现代化,与宇宙中之溪流、白雪、星辰、苍穹、雪峰、瀑布、野兽和飞鸟朝夕为伴的日子里,马修森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由,深深地体验到个体与整体融合在一起的和谐境界。这里位于尼泊尔西北部,靠近中国的西藏,地处偏远,没有无线电,现代化交通工具几乎难以到达,几个月听不到一声马达声。因为轻装旅行,马修森可以免于事物的羁绊而自由轻松,“多了一样物,就多了一样灵魂的负担”;[5]125因为不受信件、电话干扰,不必应付他人的需求,他可以“自动自发回应万事万物,没有防备心或自我意识的屏障”。[5]113一路上,马修森只管尽情地领略雪山的美丽,用心去体验雪山的神秘。充满在空气中的蝉叫声,清脆、细腻、响亮,“使蜘蛛网在阳光下微微颤动。我听了这种宛如从全世界同时发出的天籁,一时目瞪口呆”。[5]113喜马拉雅弯角粗毛羊,很安静的一种动物,但在“天空下……却给整座山带来了生机”;[5]75发情的蓝羊薄暮时分在雪山上上演了一出出“狂野的落日场面”。[5]239被誉为现代环保之父的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开枪射死野狼的那一刻,从野狼快要熄灭的绿光中获得了生态的启蒙,领会到鹿、野狼和山三者之间紧密相连的一体关系,开始“像山一样思考”,[11]167“客观聆听狼的嗥叫”;[11]168马修森在与雪山为伍中获得了心灵的觉悟,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觉得孤单,相反,他感觉到的是物我同一的圆满境界:“水晶寺就在正下方,群山和天空环绕,羊群吃草,我咀嚼面包,喜滋滋与羊群打成一片。”[5]238因为身体不适应高山环境,他患上了高山病、雪盲和干燥病,但这种浑然忘我的美妙让一切伤痛和不愉快都消失了。多年前在海军舰艇上的体验终于回来了,他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泪盈满眶,内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宁静和澄明,“求生和怕死的本能使我们感受不到身、心、自然合而为一的无言净境是多么幸福”。[5]35
对利奥波德来说,生态的启蒙改变了他对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看法,完成了从猎人角色到资源保护主义者角色的转变;像利奥波德一样,马修森在心灵的启蒙中打破了自己与宇宙世界的隔绝,领悟到与宇宙无区别的一体感带来的内在快乐。但马修森比利奥波德又更进一步,他获得了对生命的更深刻认识。他发现,一旦人超越了自我界限,意识到宇宙万物的无本质区别而达到心中无疆界时,收获的不仅仅是内在的喜悦,更能实现对生命更高层次的感悟。生命既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刻也穿越于无限的循环中——思想、情感甚至由此延伸到出生和死亡。置身在天空、雪花、艳阳中,马修森的身心恢复到与所有宇宙万物和谐一体的状态,他刹那间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如桶底之脱”[10]250般领悟到宇宙万物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个中深意,“在呼吸、阳光、风、水流的律动里,在不分过去和未来的山水风光里,在这一刻,在所有时刻,‘无常’和‘永恒’、‘死’和‘生’浑然一体”。[5]130这一瞬间的直觉感受让马修森深刻感知到人与过去、现在、未来的宇宙生命同为一体。而一旦获此感悟,马修森发现,人可以超越自我和他者、主体与客体、生命与死亡的两极对立,不再去“伤害别的生命”,不再有“生老病死的恐惧”,[5]1因为死亡本身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最终的意义就是跟死亡和平共存”。[5]89
二、“希望不在别的任何时空,就在此时此刻”
虽然佛教有很多宗派,但“顿悟之说,却是佛禅所特有的思想”,[12]3是“禅宗的精髓”[8]5所在。马修森与喜马拉雅雪山融为一体的亲身经历充分验证了禅宗的顿悟思想。而要顿悟宇宙万物同为一体,佛禅认为:“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不修之修。”[10]247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礼拜、祈祷,佛禅告诉人们修行的途径就在于当下日常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细节之中,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3]69也即,把直接经验世界的佛禅实践融入到此时此刻行住坐卧、挑柴送水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在“自然地做事,自然地生活”[10]247中,体认、顿悟与所有存在相互依存的境界,从而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实现所有生命的和谐统一。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如马修森所言,既不是去“思考永恒的问题”,[5]87也不是“知识启蒙”;[5]248既不是向生活投降,也不是遁世隐居,更不是厌恶生活。相反,是不要“让生活因对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白日梦而破碎”,[8]7是能够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应对当下,即便“在非凡时期也能专心致志,一心把握此时此刻,除了此刻什么都不想”,[8]104因为“希望不在别的任何时空,就在此时此刻”。[8]109
马修森在这次艰险的长途跋涉中对此深有感触。尽管雪山美丽得让人陶醉至极,曾几度令他莫名感动、泪流满面,但同时雪山也粗暴、狂野、凶残,到处都是死亡的陷阱和威胁:冰壁、绝壁、悬岩、急流随处可见,寒风、暴风、暴雪、雪崩随时可能来临。因为担心见不到雪豹、遇不上大师,因为牵挂刚失去母亲不久独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幼儿,也因为害怕在悬崖边上失足,马修森感到周边的整个环境都叫人恐慌不安,“空气中有一种能,一种漫无章法的威胁”,[5]221脚下的步伐也因此变得迟钝、笨重。他笨手笨脚,步步如履薄冰。可让他惊讶的是,当他放开其他一切,不再去想水晶寺中的大师,不再去想雪豹,不再去想家中的幼儿,心无旁骛,一心一境,充分相信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脚底下的碎片、紫萁、马粪等细小的东西上时,他发现自己从这些细小事物中得到了莫大的满足,“我真想到水晶寺,真想看雪豹,但若看不到也没有关系的。现下有鸟儿”。[5]90随着心境发生变化的是他的脚步开始变得轻快而敏捷,那个曾让他恐惧不堪的深渊在回程时“压迫感消除了……每一步路的动作、感觉和声音都使我充满活力”,[5]221空气中那股曾让他心神不宁的“能”现在正“贯穿全身,使我的身体与阳光合二为一……消融在山林吐纳的矿物气息中”。[5]230
佛禅倡导不修之修,全心全意专注于此时此刻的细节,从眼前的细节中获得领悟,获得对万物一体的存在本质的洞察。马修森在雪山的经历正体现了禅宗所提倡的不修之修。在这一次艰苦、危险的跋涉路程中,马修森体会到了专注此时此刻此地的奥秘,领悟到“时时刻刻担心未来,却也分分秒秒剥夺了现在”[5]287的哲理,满足了一次只做一件事的幸福,获得了不修之修的圆满结果,“我渴望看到雪豹……如果不现身……不看也甘心……千里迢迢来,我以为自己一定会失望,但我并没有那种感觉”。[5]240
在此次行程中,马修森不仅亲身体悟到不修之修的禅理,一路上他也自觉不自觉地观察当地人的生存方式。他发现这里的人们过着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人们的日子艰难,但却有一个“奇迹”,总是满面笑容,“盲女笑容可掬……绅士蔼然含笑……老太婆也是笑眯眯的”。[5]4沿路乞讨的女孩,虽然跛腿,但眼眸清澈,“笑眯眯极清爽的”[5]14向路人道早安。一路陪伴马修森同行的人,除了夏勒外,还有他们雇佣的当地夏尔巴厨师、挑夫、向导。这些人热情地过着当下的生活,“随时接纳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5]168厨师蒲泽林,一副“充满敬畏的面孔像小孩似的”,[5]168途中休息时常盘腿而坐,怡然自得地哼歌。行走到尼泊尔东部时,他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他含泪“公开把信念给扎营处的所有夏尔巴村民听”。[5]168想到西方人遇到这事一定会“悄悄溜出去、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狠踢石头”[5]168时,马修森和夏勒对他们这种坦然接受生活磨难的宽容态度既惊讶又佩服。他们如此不压抑生命的真性情和毫不设防的人生态度,“即使在纯朴未开化的民族间也不多见”。[5]27马修森认为,这些单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这种人生态度与他们信仰的宗教密不可分。佛教相信因果关系、众生相依,强调宇宙间所有的生命互为因缘、相互依存,“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连串的因果造成的”。[10]233包括花草虫鱼鸟兽在内的一切众生,彼此之间都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因果的依存关系中,犹如“一束芦苇,相依而立”。正是相信生命之间这份紧密相连的相互依存感才让夏尔巴村民可以毫不设防,自由自在地活在现下。
夏尔巴人挑夫土克丹给马修森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尤其深刻。虽然他有骂人、酗酒和惹麻烦的坏名声,但马修森注意到他身上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土克丹拥抱一切生命,对万物充满爱心,并且一视同仁:“所有的动物和行人都是土克丹的朋友……他自然而然,到哪儿都随遇而安。”[5]302途中休息时他会随缘地跟路边人搭讪谈笑,“柔软低沉的嗓音像南风一般和煦,弥漫四周”。[5]302行程途中因为迟到,他被生气的夏勒痛骂了一顿,但他没有生气、没有反击,只顾着慢慢放下肩上的重担后,“用观察万物的恬静目光望着夏勒……感谢神明让他抵达山口”。[5]91马修森因为不听他的判断而走了弯路,向他承认自己的愚蠢,可他发现西方的这一套对土克丹毫无意义,因为“他根本没有抱怨,又怎么谈原谅不原谅呢”?[5]306一路上马修森情绪容易波动,常常怀疑人生,缺乏安全感,抱怨挑夫们的不守规矩,生气甚至粗暴,但土克丹却从不沮丧、疲倦,“我没见过他无精打采或露出倦容;我最近脾气不好,他也没有对我板过脸或失礼过”。[5]302土克丹一双带有“野性又智慧的眼睛,散发出内在的宁静”,[5]47似乎带有藏人所谓的“‘疯行者’的智慧:无拘无束”。[5]81这让很多人在他面前不自在,与他保持距离,但马修森发现自己不知何故,总感觉他们之间有某种关联,彼此之间有一线相牵,“我经常感觉到他的目光,仿佛他是来守护我……目光坦然、平静、和蔼,不带任何批判”。[5]48
旅程在加德满都结束,马修森告别了土克丹。看着车窗外正含笑目送自己离去的土克丹,马修森突然意识到,自己带着明确的目的去了水晶寺,满心希望见到大师向他学习,但事实上,他所寻找的老师一直都陪伴在他的整个旅程,以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时时刻刻向他展示佛禅的生活智慧:“土克丹活在眼前,不依恋任何东西,每天过得单单纯纯,这些方面他一再教导了我,他正是我希望找的良师。”[5]317马修森为自己在行程最后一刻的又一觉悟深感欣慰,“走完一趟远比希望或想象中更美丽更奇特的旅程”。[5]317土克丹不受约束的简单和内心的自由深深地印刻在马修森的灵魂里,成为他日后的精神导师。他的目光犹如一面镜子,时常映照出马修森自己内心里的“空虚、贪婪、嗔怒和愚妄”。[5]4815年后的1989年马修森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对他念念不忘:“这个‘邪恶’的土克丹,被人怀疑是小偷和醉汉,满嘴脏话,但在整个旅程中他都是我的老师。”[14]23
当然,马修森没有把这里人们生活中的困难浪漫化。他看到了小孩的营养不良,看到了无数人勉强生活的艰难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一路上,从来就不缺痛苦和死亡,它们总是与雪山的原始美丽相伴而行。但在马修森眼中,令人眼花缭乱的雪峰,清澈干净的空气,晶莹剔透的雪花,唱安魂曲的鸟儿,村民们傍晚的呢喃,柴火旁的谈笑,路人的满面笑容,这些都是“日常的奇迹”。[5]230比起那些由所谓的进步所制造产生的城市贫民窟和印第安保留地里的悲惨,马修森更喜欢这里的生存方式。这里,人们几乎一贫如洗,吃的是粗糙无味的食物,住的是破旧不堪的棚屋,但他们没有浪费生命,全心全意把此刻当作人生最后的时光,一心一意把眼前一分一秒的生活过充实。
结 语
在雪山的自然山水中,马修森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形象地感受到东方万物一体的和谐观,顿悟宇宙万物密不可分的道理,意识到生命最终的意义就是跟死亡和平共存,并深深地体验到这种领悟给自己带来的内在满足与快乐。在高山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马修森顿悟了不修之修的生活智慧,活在当下,不要因懊悔过去或寄望来生而破坏了眼前认真生活的良机,浪费了此刻的生命。当然,马修森也意识到对于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感知模式的西方人来讲通过不修之修来领悟宇宙一体的哲理并不容易做到,而且稍纵即逝,难以持久维持。这一次的旅行不可能让他彻底远离黛博拉的死带给他的悲伤,更不可能让他远离过去而获得持久的超脱和平静。一路上,他时而经历着顿悟的片刻,领悟到禅理,轻松快乐,时而又被拉回到欲望中,在抓放之间他被置于知性与本性的分裂之中。他很清楚自己一旦从雪山回到美国,西方的二元感知模式会阻碍他对东方一体经验的理解。他也清楚自己既无法逃离美国,也无法摆脱他的成长经历,但他渴望超越自己。这趟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长途跋涉改变了他,不仅给了他力量,让他经历了一种像蛇蜕皮一样的成长,也为他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从他的禅修日记《九条龙河》(1985)中可以看到,回到美国之后,马修森沿着这条启蒙之路继续他的最终朝圣,禅修成为他日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1978年《雪豹》问世后为他赢得1979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成为他最成功的畅销书,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1981年他正式成为佛禅弟子,1990年成为佛禅老师,一直到2014年去世。从二元建构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以禅宗的生活方式来看待人生,是马修森一生的努力。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生存状态的不同,以此反观和重审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二元思想,呼吁人们学习东方古老的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和活在当下的人生观,这正是《雪豹》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