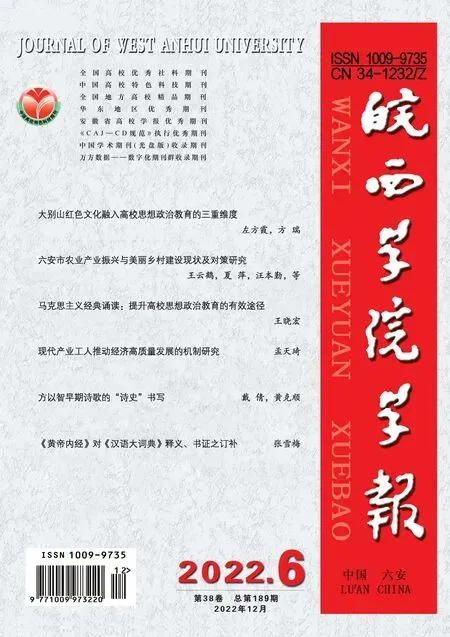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为灾害的时空变化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路曙光,吴 立,张广胜
(1.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皖西学院 环境与旅游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灾害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严重全球性问题之一。灾害是指一系列超过社会自身资源的应对能力,并造成人员、财富、环境损失,使社会功能遭到严重破坏的事件,灾是造成损害的现象或原因,害是它的结果[1](P250)。根据灾害发生的诱导因素,通常把灾害分成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学者们在历史时期灾害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3],但是这些成果多集中于自然灾害的研究领域,而人为灾害的相关研究较少。
目前,对于我国历史时期人为灾害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灾种,如龚胜生等就战争与瘟疫的关系进行了研究[4],发现我国自先秦至清代的两千多年里,兵疫之年达224个,发生兵疫的频率为8.05%,波及539个县,且兵疫的发生频率呈现出时间上波动上升、空间上从内地向边疆扩散、分裂时期扩散而统一时期收缩的特征。程杨等根据疫病相关的史料[5],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疫灾进行了研究,发现明清时期的疫病发生频繁,疫病的发生频率和影响范围在1840年以后呈现出明显升高的趋势。虎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6-7],以及贵州、广西、我国西部等边疆地区[8-10],对于我国内陆地区兽灾的研究略显不足。在火灾的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们主要借鉴了欧美国家在森林火灾方面的经验,利用树轮火疤准确确定火灾发生的年代,从而研究过去和现在火灾发生的规律[11]。这些火灾多为自然火,而非人为因素引起的人为火灾。饥荒作为粮食安全危机的主要表现,我国学者在饥荒灾害的分布特点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12-15],认为气候变化背景下当前及未来全球粮食安全均面临极大风险。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大量的史料留存至今,为今天研究历史上的灾害提供了宝贵资料。明清距今较近,历史文献记载的丰富程度更高,为灾害研究提供了更加详尽和可靠的历史数据来源与文献参考。
徽州地区是中国传统村落保存最完整、数量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其境内的西递、宏村古民居村落于2000年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8 年徽州地区又被列为全国首个跨行政区的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6]。徽州古村落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而这些文化遗址又很容易被火灾等灾害所破坏。古为今用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研究徽州地区灾害发生的规律对我国文化传承及文化遗产地环境监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人为灾害的历史文献资料纯文字描述进行定量化处理,分析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饥荒灾害的成因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一、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概况
本文所指的“徽州”是明清时期的徽州一府六县(图1),即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和婺源县,大致位于117°11′—118°56′E,29°01′—30°18′N之间。六县政区在历史时期保持了长期稳定,其空间范围大致等同于今天皖南和赣北同名的六县空间范围。根据徽州地区的历史沿革,除去后来划归徽州地区的太平县(今黄山区),古徽州地区大致包括现今安徽省黄山市的徽州区、屯溪区、黟县、歙县、休宁县、祁门县,宣城市的绩溪县和江西省上饶市的婺源县[16]。考虑到历史文献资料和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以六县为单位进行灾害统计,其中屯溪区归入休宁县、徽州区归入歙县,其他各县保持不变。

图1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地理位置
徽州地处我国亚热带北缘地区,是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气候条件复杂。本区的地形以中低山地和丘陵为主,四周为高山所环绕,中部为河谷平原或盆地。特殊的地形结构与气候使得该地区地理条件较为复杂,灾害频繁发生。
(二)材料与方法
各种灾害的数据主要来自徽州地区的地方志和地名志,包括《徽州府志》《休宁县志》《绩溪县志》《祁门县志》《歙县志》《婺源县志》《重修婺源县志》《黟县志》《黟县四志》《沙溪集略》[17-35],从相关资料中提取人为灾害数据,整理并校对灾害记录,以求灾害的统计结果更加完整、合理与可信。在此基础之上,以“年”为时间单位,“县”为空间单位对人为灾害进行定量化统计处理,以便更好地探讨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为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本文在进行人为灾害数据统计时,把兽灾列为人为灾害,这是根据兽灾产生的原因来划分的。从相关记载来看,兽灾是指野兽(尤其是虎)侵入人类活动场所,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的事件。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威胁到了野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即人类活动导致兽灾的发生,所以把兽灾列为人为灾害。本文统计的火灾均为人为因素引起的人为火,而非自然火。饥荒灾害是天灾还是人祸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水旱灾害等自然灾害是导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但是一个地区粮食短缺并不一定会发生饥荒灾害,如果当地粮食储备充足,或者政府或社会组织及时从外地输入粮食,缓解粮食危机,当地就不会发生饥荒灾害。反之,如果当地政府干预力度不够,粮食入不敷出,可能引起当地物价波动,人口死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基于饥荒灾害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认为是人类活动的因素导致了饥荒灾害,即饥荒灾害是人为灾害。下文也将重点探讨饥荒灾害与当地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饥荒灾害发生后,政府往往会通过减少当地赋税或拨发赈灾款等方法以缓解灾情。所以,本文在饥荒灾害的统计中,除历史文献中有“饥”的记载之外,把当年没有粮食收入、政府免征或减征当年赋税、物价突然上涨、政府进行赈灾等相关史料都列为饥荒灾害,如“无麦”“免征未课钞”“发米银赈之”“春,米价腾贵,斗米五钱”等。在季节划分上,历史文献中的春、夏、秋、冬分别为农历的一至三月、四至六月、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连续季节的灾害不是指灾害持续发生数月,而是代表灾害的时间跨度,包括二连季、三连季和四连季,如“春夏”不一定指灾害持续发生六个月,而是代表灾害跨度春季和夏季。
二、结果分析
(一)人为灾害的发生频次
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人为灾害进行统计分析(图2),可以看出,徽州在公元1368—1911年的544年间共发生人为灾害376次,平均1.4年发生一次,主要包括饥荒、火灾、兽灾和瘟疫4种灾害。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饥荒的发生频次最高,共有281次,占主要人为灾害总数的75%,平均1.9年发生一次;火灾仅次于饥荒,共发生51次,占灾害总数的14%,平均10.7年发生一次;兽灾共发生32次,占灾害总数的8%,平均17年发生一次;瘟疫的记载最少,共有12次,占人为灾害总数的3%,平均45.3年发生一次。总体来看,徽州地区的饥荒灾害是其他人为灾害总和的3倍,是徽州地区主要的人为灾害类型。

图2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各种人为灾害发生频次比例
(二)人为灾害的年际变化特征
以10年为时间单位,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人为灾害年际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图3),可以看出:首先,从变化趋势上看,各种灾害的发生频次随时间呈现出波浪式的变化特征。除了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瘟疫和兽灾变化不明显外,各种灾害的变化特征基本一致,其中饥荒灾害的变化趋势最接近灾害平均值。其次,朝代更迭期间的灾害发生频次较低。然而研究表明,灾害是导致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36],例如,明朝末年旱灾频发,尤其是重大的旱灾引发饥荒灾害,导致民众大量死亡,而明政府在此时却放弃了对社会救助的义务,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加之满洲势力的迅速崛起,加速了明朝的灭亡[37]。很明显,朝代更迭期间灾害的发生频次并非如图3中表现的那样少,而是战争和政治混乱导致历史资料记载失修的缘故。这种由于战乱等因素导致史料缺失的情况在元末也同样存在[12]。再次,就明清两朝而言,明朝(公元1368—1644年)的人为灾害发生频次整体上略高于清朝(公元1644—1911年)。清朝的人为灾害整体上低于明朝,说明清朝在社会治安管理和救灾赈灾能力等方面更加完善,其中火灾发生频次的降低表明人们的防火意识得以提高。最后,人为灾害的变化特征与中国整体上“明清自然灾害群发期”基本一致。

图3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各种人为灾害发生频次年际变化
(三)人为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各县的灾害发生频次上看(表1,图4),婺源灾害最为严重,共发生人为灾害89次;绩溪仅次于婺源,发生灾害74次,其次是歙县,发生灾害65次,祁门和黟县的灾害发生频次相同,都发生灾害51次,休宁发生的灾害最少,仅有46次。

表1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为灾害发生频次的空间分布统计(次)

图4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为灾害发生频次空间分布
从灾害类型的空间分布上看,饥荒是徽州最为严重的灾害类型,主要分布在婺源(64次)和绩溪(60次),其次是黟县(47次)和歙县(46次),休宁(33次)和祁门(31次)的饥荒灾害最少,这与徽州地区的粮食运输方式有关,徽州主要依靠饶河水系和新安江水系购入粮食,而祁门和休宁水运便利,能有效缓解粮食问题,所以饥荒发生的频次较低;火灾主要分布在歙县(15次)、祁门(14次)、婺源(12次),占火灾总数的60.7%,明代的火灾多发生在公共场所,如税务局公文庙、养济院等,清代多为商业店铺,这反映了明代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清代徽商的繁荣;徽州各县瘟疫的发生频次相差不大,婺源4次、歙县3次、绩溪3次、休宁1次、黟县1次、祁门没有瘟疫记载,虽然记载很可能有缺失,但是各地瘟疫的发生频次比较均衡,所以数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徽州的兽灾除两次没有明确的野兽类型记载外,其余的兽灾均为虎患,主要分布在婺源(9次)、绩溪(8次)、休宁(7次)、祁门(6次),而歙县和黟县都只有1次兽灾记载。
三、饥荒灾害产生的原因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饥荒灾害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发生频次最高的灾种,而火灾、瘟疫、兽灾发生频次较少,说明饥荒是对徽州地区影响最为严重的灾害。鉴于此,该部分将对饥荒灾害的产生原因和社会响应机理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饥荒灾害产生的原因
徽州地区的自然灾害和土地利用类型是当地粮食短缺的重要原因。自然灾害通过毁坏农作物,使徽州的农业收入减少,造成粮食短缺,容易引起饥荒灾害。统计结果显示,与旱灾相关的饥荒记载有76处,水灾35处,而其他灾害记载的饥荒较少,这表明造成徽州粮食短缺的自然灾害主要为水旱灾害。此外,徽州地区饥荒的产生也与土地利用类型有关。徽州素有“七分山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俗语,该区的地形类型大多是山地和丘陵,适宜林木的生长,而耕地面积相对较小,所以当地以山林经济为主,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小且产量不高[38]。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约为人均4亩,而徽州的人均耕地从明朝万历年间的2.2亩,到道光时期仅有人均1.5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9-40]。不仅人均耕地面积少,而且徽州地区的土地也非常贫瘠,农作物亩产量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例如,“歙山多田少,产米常供不给求,……。米面不常食,商铺有定律,月四餐、六餐而已”;“祁居僻壤,山多田少,农夫终岁勤动,仅敷三月之粮,其余仰给于江西”;“婺为山麓之区,土瘠而硗,犁仅一尺,计一岁所入仅供四月之粮”;“(黟县)以麦食佐米食,仅足三月之粮,其余贩运于江西”;“绩邑山多田少。道咸之间,产米合小麦仅敷民食十分之六,杂粮俱作正餐”[41](P222-282)。徽州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粮食产量不足,难以自给,当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影响到农作物生长时,极易导致饥荒灾害的发生。相比较而言,休宁不仅“芦苞、山芋,其收成较籼糯为易,以补民食之不足”,而且“(婺源)岭以北取足于休宁”[41](P234-246),说明休宁的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能供应周边地区,所以休宁地区的饥荒灾害发生频次较少。
前文已述及,人类活动是引起饥荒灾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在社会经济更为繁荣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加之徽商的迅速崛起,社会经济在饥荒灾害发生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所以,导致徽州饥荒的直接原因多为粮食输入受阻。徽州地区粮食取足于湖广和江浙地区[40]。徽州地区四面环山,陆路交通不便,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运输主要依靠水上交通,如新安江、阊江及其支流等水系[42]。徽州地区水运受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水贼猖獗所致,如“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婺源大旱,祁门为浮寇阻水道,斗米一金,民多饿死,黟亦大饥”[17](P512)。水贼阻碍水路运输,粮食难以及时运输到徽州,从而引发饥荒。另一方面,当地的水运政策阻碍水运,如“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黟县)无麦,赴赣运粮,又被祁阻,声名前案,始通行”[34](P17)。当地政府的政策导致水上通行受阻而影响粮食运输,虽然最后得以通过,但是延误了粮食运输的日程,可能会引发饥荒乃至灾情加重。
(二)饥荒灾害的社会响应机理
自然灾害尤其是严重的水旱灾害作为一种媒介,将气候变化的负向影响传递到人类社会,以加大原有的社会风险和矛盾[43]。徽州水旱灾害频仍,加上当地的农业种植条件差,使得农业子系统更加脆弱,容易造成粮食短缺。若当地粮食储量充足,则可以顺利消除粮食危机,否则需要从外地输入;粮食及时输入,徽州地区的粮食市场可以维持稳定,不会发生饥荒灾害;反之,当粮食输入受阻或输入粮食不足,区域内粮食供不应求,往往会导致饥荒灾害的发生。饥荒灾害发生后对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产生影响,而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饥荒灾害,从而进入恶性循环(图5)。

图5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饥荒灾害响应机理图
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粮食收入是国民的经济命脉,也是稳定社会的物质基础。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通过影响徽州地区的农业系统,使得当地的农作物减产,威胁地方粮食安全,若当地政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饥荒灾害。粮食短缺以及饥荒灾害的发生还会引起粮价上涨,例如,“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六月,旱,大饥,斗米银八钱”[33](P32)。
饥荒发生后,中央、地方政府会对饥荒灾害进行救助。相关史料中有近90处“赈饥”“赈济”“赈谷”的记载,史料还记载了多处免粮、免米的记载,如“特旨蠲免钱粮”“奉旨免漕项尾欠”“灾伤,知府周正奏免粮米”等。此外,当地的乡绅富户在饥荒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大饥疫,道祲相望。(邑庠)同叔父震佶倡捐为粥食,饿者全活数千人”[26](P361)。可见,当饥荒灾害发生后,徽州地区的救济工作是由多方面完成的,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免除赋税、拨发赈饥粮款,当地政府组织赈饥工作,乡绅富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王朝末年政府无暇顾及灾民时民众组织的救济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饥荒发生后,若当地政府救助得当,饥荒就会消除,社会稳定。反之,若饥荒灾害没有得到很好的救助,则会引发其他灾害,加深社会民生与生态问题。首先,饥荒会引起疫灾。如果饥荒没有得到及时救助,就会产生大量的人口死亡,而死亡人口处理不当时就会引起瘟疫,如“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六邑饥,斗米一钱八分,又大疫,僵死载道”[17](P511)。其次,饥荒灾害可能引起兽灾,如“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休宁饥,多虎”[17](P510)。饥荒灾害发生后,人们的食物极度匮乏,甚至“采薇掘葛,以聊其生”[44](P18)。然而,人们的这种行为威胁到了野兽的生存,如“(歙县)州源及英坑,地连淳安、昌化,深山、穷谷且数百里,居民至冬月以掘蕨烧炭为生,有虎白昼食人,伤男妇二百余人”[26](P358)。人们对植被的破坏影响了植食性动物的食物来源,导致植食性动物大量减少,破坏了自然界的食物链,虎等肉食性动物的食物供应受到影响,为了生存,它们走出栖息地来到人类活动场所,威胁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政府救助不当还会引起社会民生与生态环境问题。例如,“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春,因饶河遏,籴米贵腾至三两一石,民采苎叶竹米及掘石脂粉为食”[13](P514)。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时代,人们往往采食植被,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社会民生的安定,引发社会动荡,也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使得原本生产能力不高的土壤更加贫瘠,而且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更易引发自然灾害,进一步加重灾情,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四、结论
通过对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徽州地区人为灾害文献史料的统计与量化分析,本区人为灾害的发生具有明显的时空地域分异特征:
第一,徽州地区的人为灾害随时间呈波浪式的变化特征,灾害的变化特征与中国整体上“明清自然灾害群发期”相对应,其中饥荒灾害的变化趋势最接近灾害总频次的平均值。
第二,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人为灾害发生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婺源、绩溪、歙县、黟县、祁门、休宁,饥荒主要分布在婺源和绩溪,火灾主要分布在歙县、祁门和婺源,兽灾主要分布在婺源、绩溪、休宁和祁门,瘟疫主要分布在婺源、歙县和绩溪。
第三,徽州地区的自然灾害和土地利用类型容易导致粮食短缺,而引发饥荒灾害的直接原因是粮食运输受阻,包括水贼猖獗和政府政策等。
第四,饥荒灾害的产生与徽州地区的农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以及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如果政府能及时赈灾,则会解决饥荒,社会稳定。反之,如果政府救助的能力不足或者放弃施救,不仅当地社会经济体系受到影响,还会破坏生态环境,威胁社会民生,甚至引发民众暴乱,造成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