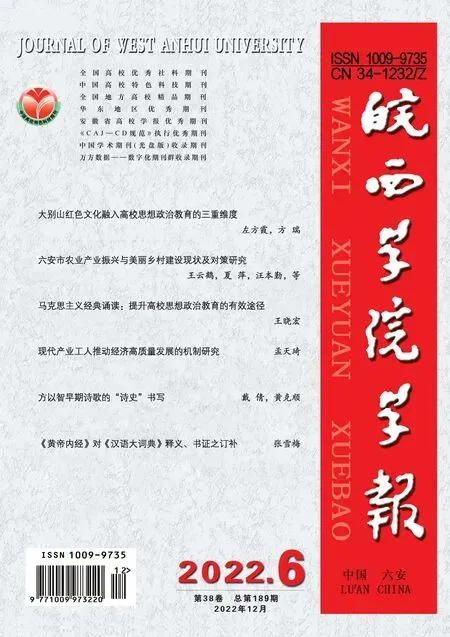繁简字理论问题探析
丁 明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汉字形体的“繁”与“简”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基本状态。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汉字的繁简现象。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初有隶书,已趣(趋)约易”。相比于大篆,小篆已经颇为“省改”,而为求“约易”,隶书在小篆基础上更加简洁。许慎以两次汉字形体的更迭,揭示了汉字发展过程中的“繁”与“简”。中国古代学者虽然很早对汉字的繁简现象有所察觉,但却始终未能将其准确命名并上升至理论的高度。直至近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深入,变更书写繁琐的汉字成了汉字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俗体字”“手头字”“破体字”“简笔字”“简俗字”等称呼逐渐成了简易汉字的代名词,人们对繁简字的概念也有了较为初步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开展汉字简化运动,相继颁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总表》等一系列法定字表,简化字在中国内地得到了有效地推广和使用。至此,繁简字的概念逐渐清晰、明朗,人们对汉字繁简现象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新中国成立至今,繁简字的研究在方法上不断进步创新,在内容上也逐渐丰富多样,呈现出了系统化、立体化、多样化的总体特点。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现有繁简字的研究成果多数集中在汉字整理与规范的方面,在繁简字的本体理论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和不足。此外,当下对于繁简字理论的研究大多数散见在各个材料之中,还未见有专门阐述繁简字本体理论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的繁简字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生成途径、消长机制以及判定方式三方面对繁简字展开讨论,希望能为繁简字搭建起相对科学、全面的理论框架,为之后的相关研究作铺垫。
一、繁简字的生成途径
繁简字,顾名思义,是一对“繁字”和“简字”的简称。如果单纯从繁简字产生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在汉字系统中生成的繁简字,而另一种是经人为规定后产生的繁简字。下面我们便从这两个角度简要论述繁简字的生成途径。
(一)汉字系统中生成的繁简字
汉字之所以会有繁与简的分别,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汉字系统中“简易律”和“区别律”的影响。所谓简易律,是指人们在日常书写汉字时,为了方便使用、提高效率从而简省汉字形体的现象;所谓区别律,是指人们在日常识读汉字时,为了方便辨认和识记进而增繁汉字形体的现象。正如王宁所言:“就书写而言,人们终是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识而言,人们又希望符号丰满易识。”[1](P56)简易律可以促成汉字形体的简化,既方便了人们的日常书写,也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而简化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破坏汉字结构的表意特征,提高了识别的难度。反之,区别律使汉字形体不断繁化,增强了汉字间的区别特征,提高了汉字的辨识度。但繁化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增加汉字的书写难度,降低了使用效率。因此,汉字系统在简化与繁化两种形体演变的规律中不断调节,以确保汉字能够正常的使用,发挥其记录语言的基本职能。而汉字繁化与简化的最终结果,便是形体出现了“繁”与“简”的分别。我们以“从”和“鸟”为例。


(二)人为规定下生成的繁简字
与汉字系统中生成的繁简字不同,人为规定的繁简字是以汉字简省为主要目的的正字运动的产物,其主要以国家的政治力量为基础,以国家颁布的法定文件为主要手段。因此,这种繁简字具有强制力和公信力。此种途径下产生的繁简字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由于是正字运动的产物,因此繁字与简字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呈现出一种替代关系。其次,这部分繁简字在原有的汉字系统中往往呈现出“非繁简关系”,而经过人为的整理和修订后,两个字才建立起繁简关系。综合以上两个特点,只有1935年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等一系列法定字表中的部分繁简字才符合这些标准,属于由人为规定生成的繁简字。我们以“捨—舍”为例。
捨—舍。舍,《说文·亼部》:“舍,市居曰舍。”形体为房屋之形,本义即供人居住的房屋,使用中常假借用来表示“放弃、放下”。《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后分化出“捨”,用来专门表示“放弃”这一义项。《说文·手部》:“捨,释也。从手舍声。”据此,“捨”应该是“舍”在“放弃”这一义项上的后造本字,二者应属分化关系。汉字简化时,《简化字总表》(1986年版)将“捨”列为繁体字,简化为“舍”。
以上我们从两个方面说明了繁简字的生成途径。这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汉字系统中生成的繁简字是汉字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和产物,是使用汉字的全体成员共同推动下产生的。因此,其具有约定俗成性。而人为规定产生的繁简字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推行并使用的,推行后由社会全体成员遵照标准执行。因此,其具有人为性和可操作性。
二、繁简字的消长机制
繁简字的产生与汉字的简化、繁化密切相关。简化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繁化在汉字形体演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汉字形体正是在这两种演变规律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但不论是简化还是繁化,受汉字自身属性的影响,它们都势必会在一定的阈值内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汉字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制约和平衡形体过繁或过简的机制和规律。探求繁简字的消长,就是探求这种制约和平衡的客观规律。
(一)汉字的本质属性制约汉字过度简化

此外,与表意文字不同的是,表音文字主要通过字符的形体来连接声音,再连接意义。因此,字符的数量不必过多,利用字符间的组合和拼读便可以实现彼此间的相互区别,并完成记录语言的基本职能。而以汉语为代表的表意文字首先是通过字符的形体来连接意义,然后再连接声音,字符的形体与语言中词的意义直接发生关联。而词汇是语言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往往表现得纷繁复杂。因此,汉语系统需要极其庞大的字符数量才可以记载语词的意义,而且字与字之间也必然要有一定的区分度才可以指称数量庞大的汉语词汇。这就导致了汉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部构造也较为复杂。

(二)汉字的职能属性制约汉字过度繁化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其之所以被创制出来,是为了弥补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足。因此,实用性的职能属性决定了汉字不可能为了表意的丰富而一味地繁化,而是会在一定的区间内通过简省自身的成分来满足使用者的基本需求。由此,汉字的使用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便可制约汉字形体的过度繁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使用者的主观因素。人们在使用一些形体过于繁琐的汉字时,主观的求简心理、使用者的文化水平以及使用者无意间的疏漏等,都会导致汉字形体的“损耗”。一些过于繁难、不便于记忆和书写且对汉字整体表意不起到必要作用的部分便会被逐渐地省略掉,而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部分则会被保留下来。因此,使用者的主观因素是制约汉字过度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汉字初创时期不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促使着汉字的使用频率不断提高。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新事物的产生,汉语语义的细密化程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词语不断出现,而这些新产生的词语,又急需一批汉字来承载其意义,因此汉字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正如王宁所言:“汉字的增多是因为汉语词汇不断增多”[2](P39)。汉字高频率的使用以及极其庞大的数量都促使着其形体不可以过度繁难,这主要是由于使用者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一旦使用者的记忆达到饱和状态,汉字便会失去其使用价值。因此,生产力和社会的客观因素也是制约汉字形体过度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以上两个方面外,我们也要格外注意政治权力对制约汉字形体过度繁化方面发挥的作用。王宁指出:“每一个汉字字符的创造与改变,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个人使用、社会通行和权威规范。”[1](P58)权威规范中除专家学者发挥的作用外,便是国家行政命令的指挥和调节。国家通过政治权力调节汉字形体过繁最好的例子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的一系列汉字简化政策,这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国家政治权力的干预也是制约汉字形体过繁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简化与繁化是繁简字生成、发展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动力。因此,从本质上讲,繁简字的消长问题,也就是简化与繁化这两种形体变化规律的制约和平衡问题。汉字的本质属性和职能属性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种形体演变规律的过度发展,使它们都能在一定的区间内合理地发挥作用,由此保证了汉字系统内部的动态平衡。
三、繁简字的判定方式
在以往一些研究中,学者们常常习惯于利用笔画的多少来判定繁简字,有的学者在笔画的基础上还会进一步引入异体字的概念进行指称。从这两方面来看,前者是从繁简字的外部形式出发,而后者则是深入到了繁简字的内部功用,可以说二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繁简字的判定提供一些参考,但如果细致考证我们会发现这两种判定方式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利用笔画的多寡来判定繁简字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是最直观也是最直接的判定方式,但如果仅仅只依靠这一条判定标准未免有些单薄。因为在汉字系统中,存在笔画多寡区别的一组汉字随处可见,如“封”与“寸”,但我们却很难说它们之间存在繁简关系。其次,如果在笔画的基础上结合异体字的概念,似乎可以从内部功用上使繁简字的判定更加具象。但异体字含义本身也存在着部分异体字和狭义异体字的争论,如果仅从异体字的角度去判定,我们也无法了解究竟是哪种定义下的异体字,这样便使判定的结果更加不确定。此外,繁简字与异体字虽然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着相似之处,但本质上二者仍是两个独立的字际关系。因此,引入异体字概念来判定繁简字的方法模糊了字际关系间的界限,是不值得提倡的。其实,不论是繁字还是简字,它们的本质都是汉字,只有从汉字的本体属性出发才能从根本上使繁简字的判定更加全面、科学。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利用“汉字学三个平面理论”来解决繁简字的判定问题。
王宁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一书中将汉字的全面属性分为构形属性、书写属性和字用属性,并指出应该“通过各种属性来认识事物,并比较事物之间的异同,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2](P143)。李运富也指出必须从“外形、结构和职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汉字的属性”,他将这种汉字属性的分析方法概括为“汉字学三个平面理论”[3](P3-17)。三个属性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又共同组成汉字的本体属性。汉字学的三个平面理论是从汉字本体出发分析汉字属性的基本方法,是对汉字全面的考察和科学的划分。因此,利用“汉字学三个平面理论”,可以对繁简字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从而确立起科学的判定标准。下面我们便分别从书写属性、构形属性以及职用属性三个角度入手,对繁简字的判定方法作简要的论述和探讨。
(一)书写属性
书写属性着眼于汉字的外部形态,主要探讨的是汉字书写的基本性质以及书写属性与其他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笔画是汉字书写属性视域下的基本构成单位,而判定一组汉字是否具有繁简关系最为直接的方式便是利用其笔画的多寡。一般来说,繁体字的笔画比较多,而简体字或简化字的笔画比较少。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笔画来判定繁简字有一定的作用条件,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两个概念:字体和字形。字体和字形都是汉字书写属性下研究的重点内容,目前学界对于字体和字形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所谓字体是就“某一群体字的总风格”而言的,而字形则是就“某一群体字内部个体字的特征”而言的[4]。就繁简字的判定而言,汉字繁简的差异应该表现在字形上,即某汉字系统或群体内个体汉字的外部特征。也就是说,繁简字的判定应该归入字形的视域下进行分析,而不应该作用于字体系统。不同的字体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催生出的风格各异的汉字书写形态,字体不同往往也意味着汉字的产生时代、地域、用途、书写工具、书写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比如早期的甲骨文多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写而成,而后代的楷书多用毛笔在纸上书写而成,书写的工具与载体不同所呈现的字体形态也势必会有一些差异。因此,比较不同字体系统中的汉字是否存在繁简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刘琼竹指出:“繁体、简体、异体、正体等概念,实际上属于‘字形的变体’。”[5]孙建伟也指出:“字形包含本体属性和关系属性”,而“关系属性主要指繁简、正异、正俗、正讹等字际关系。”[4]两位前辈虽然在表述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他们都将繁简字归入至字形的视域下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是十分合理的。综上,只有在同一汉字系统内,比较汉字个体字符间的形体差异才可判定两个字是否具有繁简关系。
(二)构形属性
构形属性着眼于汉字的内部结构,探讨的是汉字构形的基本性质及构形属性与其他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繁简字的判定而言,构形属性上的判定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一是构件的数量。王宁在其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将构件这一概念引入至繁简字的定义,其指出:“(繁简字)在构造或书写上存在构件或笔画的数量差别。”[6](P96)因此,繁简字不仅仅在笔画数量上存在多寡的分别,在构形属性中,构件的数量也存在着多少的区分。构件的数量可以相当直观地反映出一组字中孰繁孰简。一般情况下,繁体字的构件数量比较多,简体字或简化字的构件数量相对较少。
二是构件的结构。构件结构有复杂和简单的分别,这是由汉字笔画间的不同组合决定的。笔画是汉字书写的最小构成单位,它们通过彼此组合、交接和搭配构成构件。一旦笔画组合为构件,这些笔画或笔画组便进入到汉字的构形系统中,成为构形的基础元素。笔画间的搭配和组合越复杂,构件的结构也会越复杂;反之,笔画间的搭配组合越简单,构件的结构也就会越简单。因此,从构件结构的角度去判定繁简字是建立在汉字书写属性基础之上的。一般来说,繁体字的笔画较多,构件结构也比较复杂;而简体字或简化字的笔画较少,构件结构也相对简单。
(三)职用属性
汉字的职用属性着眼于汉字的使用职能,探讨的是汉字的职用以及职用属性与其他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记录汉语便是汉字的基本职用。汉字记录语言主要体现在音和义上,即汉字的记音职能和表义职能。能够构成繁简关系的两个字记录的一定是语言中的同一个词或语素。因此,一般来说,能构成繁简关系的两个字的音义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但在繁简字中,还有一种是由人为规定产生的繁简字,我们在上文也有所提及。这部分繁简字的繁字与简字在原有的汉字系统中可能记录的并不是同一个词,它们记音和表义的职能也仅仅表现为部分相同。但好在这部分繁简字往往只存在于国家的法定文件和字表之中,我们在判定时只需要参考相关的文件即可,不必将其他因素考虑进来增加判定的难度。
综上,三种方法是从汉字三个不同的属性出发提出来的,书写属性和构形属性的判定方法都是针对繁简字的形态特征提出的,而职用属性的判定方法则是针对繁简字的内部功用提出的,将三者结合起来便是完整的繁简字判定原则。
四、结语
繁简字是汉字字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繁简字的研究也是当下汉字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本文以繁简字为核心,在学界现有观点的基础上,讨论了繁简字的生成途径、消长机制以及判定方式等相关理论问题。从繁简字的生成途径入手,可了解繁简字的产生原因。从繁简字的消长机制入手,可了解繁简字发展的内部制约机制和平衡规律。从繁简字的判定方式入手,可以制定一套汉字学三个平面理论视域下的繁简字判定原则,进而使繁简字的畛域关系更加清晰明朗,与诸字际关系的边界模糊问题得到有效和科学地解决。因此,繁简字理论问题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不仅可以为繁简字搭建起一套科学的理论框架,对于其他字际关系的理论问题建构也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识记“己”“已”“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