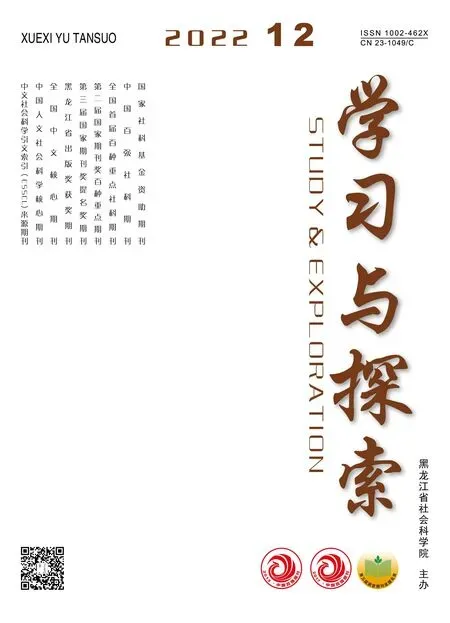洛特曼和雅各布森:路径与交集
[爱沙尼亚]伊戈尔·皮里希科夫
(1.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美国 洛杉矶;2.塔林大学,爱沙尼亚 塔林)
黄 玫 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 俄语学院,北京 100089)
一、“浪漫主义学者”雅各布森
罗曼·雅各布森于1982年7月18日辞世的消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反响,而在这位学者的故乡俄罗斯(当时是苏联)却悄无声息,尽管雅各布森的名字及其著作在苏联从未被禁。雅各布森唯一的俄语讣告发布于侨民的《新杂志》[1]。但在爱沙尼亚(当时还是苏联的一部分),情况则有所不同。爱沙尼亚语文学的重要期刊《语言与文学》(KeeljaKirjandus)委托塔尔图大学的尤里·洛特曼教授撰写一篇纪念雅各布森的文章。洛特曼生前仅以爱沙尼亚语发表的这篇纪念文章在作者去世后于1995年以俄语发表,2003年被收录于洛特曼论文选集中。讣告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无论雅各布森被20世纪中叶多舛的命运抛向何处,他周围总会出现一个学术小组,这个学术小组很快就变成具有世界意义的研究中心。这使得雅各布森的学术传记与本世纪的人文科学史密不可分[2]77。
此言不虚。雅各布森考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后,1914年底,他便与同系的几名学生(其中包括博加兑廖夫、布斯拉耶夫和雅科夫列夫)一起成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联合创始人,该小组于1915年2月16日(俄历3月1日)正式成立。雅各布森当选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主席,直到1920年他离开俄罗斯之前长期担任这一职务。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雅各布森来这里听沙赫马托夫的讲座),勃里克、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和雅库宾斯基在雅各布森在场的情况下,决定再成立一个诗学研究会。1919年10月2日,这个研究会被命名为“奥波亚兹”(诗语研究会)。雅各布森是这两个学会的积极参与者,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后来成为文学学中的形式论学派(俄国形式主义)。
1926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Pražsklingvistikkroužek,PLK)在杰出的捷克语言学家威廉·马泰休斯的公寓里成立,主席为马泰休斯,副主席是雅各布森。据雅各布森所言,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是按照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组织模式”建立的,“顺便也吸纳了其学术规划和成就”[3]。该小组成员制定了一个以结构语言学方法研究斯拉夫各族语言、文学和民俗的十分宽泛的纲领。1929年,雅各布森首次将从心理学家那里借用的术语结构主义作为语言和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加以运用。1939年春,在德国军队侵入捷克共和国并使其成为“德国保护国”之前不久,作为犹太人的雅各布森被迫辞去布尔诺大学教授职务,并辞去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副主席一职。对雅各布森来说,“无家可归,被迫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流浪的岁月已经到来”[4]。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挪威和瑞典)工作两年后,雅各布森获得前往美国的许可,1941年6月4日抵达纽约。1942—1946年,他在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ELHE)任教。这是一所法国侨民“流亡大学”,在学校里工作的,是纳粹入侵后因担心受迫害而离开法国和比利时的人文学者,包括那些担心因犹太血统而受到迫害的人,如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洛特曼称列维-斯特劳斯与雅各布森这两位科学家在纽约的会面是“历史性的”[5]不无道理,正是他们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美结构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雅各布森讲授课程的直接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开始使用描述语言结构的方法来描述社会结构(如亲属关系系统)。他发表在纽约语言学小组杂志《世界》(Word)1945年第1期的奠基之作《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L’analysisStructuralenlinguistiqueetenhumanology)中援引了雅各布森的几篇文章,列维-斯特劳斯视这几篇文章为方法论的范例。纽约语言学小组(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1943年10月开始工作,雅各布森与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其他教授一起成为其创始人。他担任该小组的副主席,直到1949年离开纽约前往哈佛。这是雅各布森创立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语言学小组。也是在这些年里,雅各布森逐渐成为美国斯拉夫学主要重建者之一。
洛特曼特别强调指出,“雅各布森学术笔法的一个特征,是他对跨学科的兴趣”[2]76。雅各布森学术思想的嬗变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即形式论时期(1915—1922),重点是语言学诗学;功能结构主义时期(1923—1939),重点放在将索绪尔符号学重新阐释为普通美学;神经语言学时期(1940—1956),重点研究语音和失语症问题;最后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期(1957—1982),重点是符号学——通过符号系统进行交际的普适科学。雅各布森晚年追求的目标雄心勃勃:制定针对文学作品和非语言艺术的共同方法,泛而言之,是寻找所有类型文化活动的语言和心理共性;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将语言和文化作为人类交际手段来研究。雅各布森本人在其作品选集每一卷末的“后记”(Retrospects)中,都对自己的学术道路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章在他去世后被译成法语,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书名为《语言中的生活:一个学者的自画像》,之前曾被收入学术回忆录《与克里斯蒂娜·波莫斯卡的对话》。
在洛特曼看来,究竟是什么帮助雅各布森实现了这些各不相同的学科组织计划和研究纲要?这就是:他“终其一生都是学术界的浪漫主义者”[2]75。这种学术“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努力将动态发展引入语言结构的概念本身”,而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雅各布森语言思想的特点”[2]76。在这方面,洛特曼将雅各布森与尤里·蒂尼亚诺夫(雅各布森曾与其合作著文)和扬·穆卡若夫斯基(雅各布森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战友),还有米哈伊尔·巴赫金等学者相提并论并视他们为自己的老师和前辈。
二、“浪漫主义学者”洛特曼
著名比较研究力作《开放的结构:雅各布森—巴赫金—洛特曼—加斯帕罗夫》的作者娜塔莉娅·阿夫托诺莫娃指出,在阅读洛特曼关于雅各布森的纪念文章时会产生一种印象,即在雅各布森身上,洛特曼似乎看到,或者说强调了他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换言之,她认为雅各布森学术研究中的浪漫主义特征也是洛特曼自己的特征,“洛特曼这样称呼雅各布森,但这个定义也适用于他本人”[6]。
还有一个与“学术浪漫主义”相关的特征,使我们能够比较和整合雅各布森和洛特曼的学术道路——他们都有一种部分天生、部分出于被迫的能力,即在新的学术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自己的思想(当然,很少有人的学术生涯能与雅各布森之字形的跨文化轨迹相提并论)。洛特曼于1939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在那里他开始在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课堂上学习民俗学,并且听了格里高利·古科夫斯基的18世纪俄罗斯文学课程。1940年,洛特曼应征入伍,在整个战争期间担任炮兵信号员,最终在柏林获得两枚战斗勋章和六枚奖章。1946年,他重返学业,听了维克多·日尔蒙斯基、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鲍里斯·艾亨鲍姆和其他战前即为杰出语文学家的学者们的课,并在古科夫斯基的学生尼古拉·莫多夫钦科的指导下撰写了毕业论文。洛特曼大学毕业时,正是反犹太主义运动的高潮,才华横溢的洛特曼无法继续攻读研究生,或者在列宁格勒找到工作,他不得不离开列宁格勒,来到塔尔图。塔尔图是爱沙尼亚和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重要大学城。一段时间后,洛特曼成为塔尔图大学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建立了符号学教研室。
1962年,莫斯科语言学家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和弗拉基米尔·托波罗夫组织了一场关于符号系统的结构研讨会,通常认为这是苏联符号学历史的开端。这次研讨会的确非同寻常,甚至引起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相当激烈的反应。符号学在莫斯科这座大都市受到排挤,符号学研究中心转移到爱沙尼亚。
1964年,洛特曼推出《结构诗学讲义》,该书甫一面世,立即被视为新结构主义文学学的宣言。其出发点是,语言元素,包括与之同理的艺术结构的元素,并非是由其自身的实体属性所确定的,而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其相应和对立)及其在总的系统中的功能所确定的。这本书是塔尔图“符号系统研究”系列丛书的开山之作,伊万诺夫是丛书编委之一,他与洛特曼是在一年前相识的。从1964年开始,伊万诺夫、托波罗夫和莫斯科其他符号学家成为在基亚埃里库的塔尔图大学体育基地举办的派生模拟系统暑期学校的固定参与者。就这样,在1964—1965年,一个团体成立了,这就是莫斯科—塔尔图或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通常认为,这个学派的塔尔图分部由洛特曼领导,莫斯科分部由伊万诺夫和托波罗夫领导。
十年后,伊万诺夫发表了《学术行为之符号系统》。在这篇文章中,他发展了雅各布森式半官方的学术共同体类型学,而将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组织结构提升到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为协调中心的布拉格学派的层次,进而又提升到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层次,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组织机制方面的典范。雅各布森也堪称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之父,卡列维·库尔和叶卡捷琳娜·维利梅佐娃对该学派成员的访谈证实了这一点[7]。雅各布森和他在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同事彼得·博加兑廖夫,都参加了以派生模拟系统为主题的塔尔图暑期学校。在《符号系统研究》第七辑这一纪念博加兑廖夫的特刊上,洛特曼回忆道:
彼得·格里戈利耶维奇·博加兑廖夫身上反映出符号学研究的生动历史:他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一员,也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他以自己的合作积极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符号学研究的勃兴。1962年,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符号系统的结构研究学术研讨会,后来又成为塔尔图符号学交流的积极参与者。……第二期暑期学校(1966年)的参与者们还记得那个在壁炉旁度过的夜晚,博加特兑夫和雅各布森分享了他们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回忆,以及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布拉格进行符号学钻研的最初时光[8]。
1963—1971年,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对人文学科中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定量方法的讨论,这成为整合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外部原因。伊萨克·列夫津、尤里·洛特曼、亚历山大·若尔科夫斯基、尤里·谢格洛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和符号学运动的其他参与者加入了由结构主义反对者首先发起的论战。这场争论以洛特曼的论文《文学学应是一门科学》(文章标题是由该杂志编辑部加上的,但它正确反映了文章的主旨)而告终。洛特曼将严格的科学性与官方教条主义和伪科学印象主义相对立,他指出,“新型的文学学家”是“必须同时具备独立获得的广泛经验材料和精确科学训练出的演绎思维能力的研究者”;“理想情况下”,他应该“集文学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9]。在这一论点中很容易发现来自雅各布森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
还在雅各布森生前,翁贝托·埃柯就称雅各布森为当代“符号反应”的“主要催化剂”[10]。雅各布森对符号学的推广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开辟了道路。洛特曼从文学文本的结构—符号学分析起步。然而,符号学视界为他将艺术符号系统与非艺术和准艺术符号系统进行比较提供了可能,例如,将日常行为审美化或意识形态化。由此,洛特曼转向将所有的文化现象原则上都作为“文本”来阐释:文学文本可与戏剧文本、绘画文本、非艺术文本、匿名引用的材料、该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一系列事实和行为方式(行为文本)等相比较。
文化符号学主张将意识形态、审美和日常生活现象置于其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之中进行研究。这种统一体就是作为“非遗传性集体记忆”的文化[11],即用于生成、存储和传递整个人类或其特定群体的“非遗传信息之集成”的符号系统[12]。但人类文化并不是最大的符号学机制。为了表示总体性符号化空间,类似于地球化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所提出的生物圈和智力圈概念,洛特曼提出符号圈概念,从而为文化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概念平台。这个系列的文章被组合在一起收录于《思维世界的内部》一书中,在作者去世后出版——作者生前此书已被译成英语出版,书名为《思想的世界》(UniverseoftheMind),副标题为“文化符号学理论”(ASemioticTheoryofCulture)。
三、中世纪史专家雅各布森和洛特曼
雅各布森影响了洛特曼在多个领域的探索。首先,雅各布森是俄罗斯中世纪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重要研究者。雅各布森与他在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同事——拜占庭研究专家亨利·格雷戈耶和历史学家马克·谢夫特尔共同编撰的文集《十二世纪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LagesteduprinceIgor’, épopéerussedudouzièmesiècle)成为20世纪中期斯拉夫学中最重要的学术事件。雅各布森撰写的一篇长达125页的论文《论“远征记”的真实性》收录其中。这篇论文专门探讨俄罗斯中世纪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伊戈尔远征记》的真实性问题。这是由法国斯拉夫学者安德烈·马松(André Mazon)发起的争论。马松认为,这部作品是18世纪的伪作。雅各布森详细分析并驳斥了马松的所有论点,他依据历史语言学材料以及几十个与其文本中“晦涩难懂之处”类似的古俄语作品,证明了该作品语言和诗学的古风。在同一本书中,雅各布森发文对《伊戈尔远征记》文本进行了批判性重构,其中提出了新的分词法,并将古俄语文本翻译成现代俄语。这一工作在系列研究中得到了继续,这一系列论文与1948年发表的文章构成了雅各布森著作选集第四卷的重要部分。
今天,谈到洛特曼,我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中世纪史专家。俄罗斯古代文化的杰出专家、塔尔图大学毕业生玛丽娅·普柳汉诺娃回忆道:“洛特曼在塔尔图的整个前半生几乎一直在教授古俄罗斯文学课。1970—1971那个学年……好像是最后一季。”[13]在中世纪史专家洛特曼的诸多兴趣中,《伊戈尔远征记》占据中心位置。在庆祝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0周年(1960年10月24—25日)的学术会议上,洛特曼做了题为《〈伊戈尔远征记〉研究的当代问题》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洛特曼有两部关于“远征记”的最著名的论著面世。其中之一是60页的专著式长文《〈伊戈尔远征记〉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的文学传统》,这篇长文探讨的与其说是这一古代俄罗斯文学的古文献在现代文学中的接受,不如说是这一文献文本的真实性问题。在关于故事起源的长期争论中,洛特曼和雅各布森一样,支持文本的真实性,并且以文化学视角的反驳来补充雅各布森在与马松论战中语言学视角的反驳,证明故事的美学和意识形态与18世纪的趣味大相径庭。洛特曼驳斥了“怀疑论者”的一个论点,即《伊戈尔远征记》是对他们所假想的创作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政治现实的一个加长版寓言。18世纪到19世纪之交文学家们对“远征记”的接受成为研究材料,证明了在“远征记”中捕捉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文学趣味之痕迹的说法毫无根据。因此,洛特曼的文学学论据是对雅各布森语言学论据的重要补充。21世纪初,雅各布森的结论得到了杰出的莫斯科语言学家、塔尔图学派成员——安德烈·扎利兹尼亚克的证实和补充,他彻底证实了《伊戈尔远征记》语言的真实性,并得出结论:认为它是伪作的概率几乎为零。
另一篇文章是洛特曼对《伊戈尔远征记》和基辅时期其他文本中“荣誉(честь)和荣耀(слава)”两个词的分析[14],该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建构于雅各布森对古俄语文本重建的基础之上,尤其是雅各布森对《伊戈尔远征记》最后一个句子提出的猜想:“荣耀归于大公,而[荣誉]归于随从”(“Glorytotheprinces, and [honour] totheretinue”)。现存唯一的古俄语文本是:“荣耀归于大公和随从。阿门。”(字面意思是:“Glory to the princes and the retinue. Amen.”)如果没有雅各布森式的重建,洛特曼的最终结论就不那么令人信服:在古俄语文本中,“荣誉”是物质的,“意味着物质奖励(或礼物)”,而“荣耀”具有非实物性,它“意味着缺乏物质标志”,因而对中世纪意识来说比“荣誉”更有价值。相反,在18世纪文化中,“荣誉”是“贵族阶层的主要道德之一”,被视为在“荣耀”之上[15]。这是反驳《伊戈尔远征记》是伪作的又一间接论据,这不是从语言形式,而是从意识形态内容来说的,洛特曼认为,意识形态内容与其语言体现不可分割。
四、普希金专家雅各布森和洛特曼
毋庸置疑,洛特曼是俄罗斯最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杰出研究者,洛特曼谙熟普希金专家雅各布森的论著。雅各布森论普希金雕像的象征意义这篇开创性文章于1937年在捷克出版,后被译成法语,然后又译成英语,因而广为人知。《普希金象征体系中的雕像》(SochavsymbolicePuškinově)一文后来被作者易名为《普希金诗学神话中的雕像》(TheStatueinPuškin’sPoeticMythology),这个标题更广为人知。这篇文章是基于雅各布森1937年2月8日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报告《普希金的象征体系》(KPuškinověsymbolice)完成的。这篇文章还与这位研究者的另一部著作有关,即1936—1938年由雅各布森和阿尔弗雷德·博姆(Alfred Boehm)编辑、布尔诺大学俄罗斯学研讨会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出版的四卷本《普希金作品选》。雅各布森《论普希金的抒情诗》《论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论普希金笔下民间诗歌的回响》作为四卷本文选各卷的后记发表。1975年,普希金研究系列经作者的修正和补充以英译本单行本出版。
关于雕像的文章旨在确定普希金“丰富象征体系”中“不变的成分或常数”,即一位作者或其特定的一组文本所特有的语义“不变体”[16]。雅各布森将“诗学的神话”定义为这些不变成分的一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诗学的神话”被认为是民间神话的个性化的类似物,正如“诗歌方言学”和“诗歌词源学”手法在诗歌语言中可类比为方言差异和实用语言中的民间词源学的现象。因此,在研究诗语和诗的语义时,雅各布森采用的是与普通语言学、方言学和民族学相同的那些方法。
雅各布森以“诗学的神话”的概念补充了他在其第一本书《俄罗斯新诗》中引入的两个概念。他认为,“实用”语言也可以借助“诗的”语言被描述的那些方法而得到描述。正如语言学家观察当代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功能,然后才将这一知识推及此前时代的那些语言一样,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的考察应该从自己的那些同时代人开始,而不是像学院派的文学学那样从经典作家开始:“普希金的诗,作为诗歌事实,现在可要比马雅可夫斯基或赫列勃尼科夫更不易懂、更令人费解。”[17]从这个视角出发,诗语的多样性便被视为“诗歌方言学”,类似于实用语言的方言学。雅各布森那篇论著的原名《走近赫列勃尼科夫(诗歌方言学初探)》正来源于此。赫列勃尼科夫诗歌的主要手法及其诗歌方言学(用当代术语来说:个人习语[идиолект])的基础是基于“诗歌词源学”而创造新词,“诗歌词源学”就“相当于”实用语言中的“民间词源学”。
洛特曼在雅各布森对“诗人的个人神话”的描述中加入了文化维度。洛特曼的著作《在诗语的滋养中: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收入其《晚期普希金现实主义的类型学特征》一文,而在《思想的世界》(《思维世界的内部》)一书中,在一篇题为《象征——“情节的基因”》的文章中,洛特曼援引了雅各布森关于“诗人完整的个人神话学”的说法,提出了个人的象征与传统的象征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在空间上假定性地呈现为水平和垂直的共时性象征和历时性象征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或那一个诗人的象征“电码”并不总是具有个性:他可以从时代的、文化思潮的、社交圈子的大量储存中汲取自己的象征。象征与文化记忆相关,一系列象征形象垂直地渗透于整个人类历史或其大部分区域。艺术家的个性不仅体现于对偶然的象征(即对非象征物的象征性解读)的创造,而且体现于对有时是相当古老的象征性形象的凸显。可是,最具有意义的是诗人在那些奠基性的形象—象征之间建立的关系系统。象征的意义领域总是具有多义性。只有通过形成相互关联的品格,诗人们才能创造出诗的世界,这才是这位艺术家的独特之处[18]。
洛特曼感兴趣的并不是象征的起源,而是象征在作者的“世界图景”结构中的位置;世界图景也是语义结构,它是由艺术文本结构演绎出来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洛特曼就放弃了苏联文学学对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传统划分,而将文本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文本结构是文本所有元素与文本整体之间关系的被复杂地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创造文本的意义。这一视界后来得到不断拓宽、发展和完善,但其方法论基础没有改变。这使得洛特曼确实也有资格将其早期的两篇研究普希金的论文——《〈上尉的女儿〉的思想结构》《〈叶甫盖尼·奥涅金〉艺术建构的独创性》与上文提到的文章一起辑入《在诗语的滋养中: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一书。
五、雅各布森和洛特曼论“语法的诗”与二元对立
20世纪50年代中期,雅各布森投入很多精力研究语法的理论问题。继探讨移位(语言的标记元素)和动词范畴(1957)以及俄语格的结构(1958)的著作之后,他提出了语法范畴对于诗学的意义问题。语法范畴是任何语言表述的基础,但在诗歌中,特别是在篇幅较短的抒情诗中,语法范畴还会发挥“布局作用”。华沙诗学大会论文集《诗学》(Poetics.Poetyka.Поэтика,1961)堪称战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里程碑,这本文集中收录了雅各布森的论文《语法的诗和诗的语法》,题目本身就标示了分析诗歌文本的一种新视界。雅各布森通过研究声音层面和语法层面在诗文本中的作用及其与作品语义的关联,展示了“没有形象的诗”如何成为可能——普希金的诗《我曾爱过您……》成为例证。在同一篇文章中,普希金的另一首诗——《我的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得到来自“语法的诗”这一视角的分析。
雅各布森在这个路向上完成的下一篇论文,便是与列维-斯特劳斯合著的文章《夏尔·波德莱尔的〈猫〉》。随后,他对好几十篇分属不同语言和文学传统的诗歌杰作进行了语法分析,“总共涵盖了过去十三个世纪的世界诗歌”[4]88。所有这些论文都收录于《选集》第三卷。对波德莱尔《猫》的分析最为著名,博得学界足足用了350页的一大卷《波德莱尔的〈猫〉:方法的冲突》来讨论,雅各布森为这一卷讨论集写了一篇后记。不过,对于洛特曼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其他成员们来说,第一篇即“普希金的”的那篇至关重要。
洛特曼认为,雅各布森“论诗歌文本中语法形式的艺术意义”这一命题非常“令人信服”,它开辟了通向“艺术中文本的形式元素语义化的其他例证”的路径[19]26。“正如雅各布森所指出的那样,语法范畴在诗歌中会表达相对而相关的意义。正是那些语法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出诗性的世界视象的模型,主—客体关系的结构。”[19]202洛特曼指出,雅各布森的研究不仅对话语文本的诗学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普通符号学意义重大,因为他(雅各布森)“清楚地展示了”对语法范畴艺术功能的考察在一定层面上相当于空间艺术形式中几何结构的游戏。
洛特曼认为蒂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是以结构—功能视界研究文学的首创者,扬·穆卡若夫斯基和布拉格学派的其他代表则延续了他们的工作。结构诸要素之间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功能上彼此区别开来。不论是语言的结构还是文学的结构,其任何因素都具有区分语义的功能。由此可知,就其物质的组成而言同一个元素“依据我们将其纳入其中的对立系统的不同而会获得不同的含义”[9]。洛特曼紧随雅各布森,以二分法(二元对立)——而不是,例如三分法(一如在皮尔斯符号学中那样)——的形式来思考这些差异。根据这种观点,任何一个多项式对立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组二元对立,况且还是存与缺之对立(“A vs. -A”这一类),而不是彼此均等的对立(例如“A vs. B”这一类)。
雅各布森毫不含糊地声称,“二元对立是必要的;没有二元对立,语言的结构就会失去”[20]。语言单位,如音素,是由二元对立系统而连接在一起——这是1942年那些讲座的最新版本,正是这些讲座使得列维-斯特劳斯“转向”结构主义。雅各布森和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依发明了一种用于语音的二元对立分析法,之后,雅各布森又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包括语义层在内的文本的不同层面的分析。在其文学结构主义宣言(《文学学应是一门科学》)中,洛特曼将二元对立的方法称为“构建不同的结构模型的有效手段”,并将“特鲁别茨科依—雅各布森视界”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达尔文的“对立原理”和索绪尔的“同质与异质的语言学机制”这些基础性的认知进行比较。在其早期的《结构诗学讲义》中,在1967年那篇文章中,洛特曼甚至试图仿照特鲁别茨科依所提出的“初始音素”概念引入“初始义素”概念。尽管在洛特曼诗学的后期版本中这一思想受到的关注较少,洛特曼的《诗文本分析》一书里,无论在其理论编,还是在其实践编,雅各布森之二元对立的分析是一直被征引、被应用的。
由于结构是一个关系系统,而文本是对这些关系的物质实现,所以艺术文本的分析基础应当是对构成文本的那些二元对立的分析。因此,对于《叶甫盖尼·奥涅金》布局至关重要的,是其“章节是根据成对的对立这一系统而构建的:奥涅金—彼得堡上流社会;奥涅金—作者;奥涅金—连斯基;奥涅金—地主们;奥涅金—塔吉娅娜”,等等。不仅如此,“塔吉娅娜也有一个不亚于奥涅金的对立群:塔吉娅娜—奥尔加;塔吉娅娜—拉林一家;塔吉娅娜—女友们;塔吉娅娜—保姆;塔吉娅娜—奥涅金”,等等[21]。文本的其他层面也是通过类似的“并置—对立”(洛特曼造的新词)而被组织起来的。这种视界使得洛特曼能够解释,为什么长篇小说里对所有提出的问题给出不同的、往往是相互排斥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反映出彼此并置—对立的人物(包括叙述者本身)观点的多样性,反映出对同一事物不同观点的碰撞而产生的那些矛盾之立体的同时并存。“在这样的文本建构背后,隐藏了生活原则上不可被文学完全容纳这一观念”,而开放式结尾则象征着“现实具有不可穷竭的可能性和无限的变体”[22]。
六、“负手法”“零符号”“消极特征”(洛特曼、雅各布森、蒂尼亚诺夫)
在洛特曼看来,文本并不具有自主自律性,而是一个更复杂系统的组成元素:艺术作品“由文本(文本内关系构成的系统)和文本外关系”组成[23],即文本与文本外现实的关系,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还有与文学规范和传统的关系,那些规范与传统在培育读者期待。因此,对于文本的结构具有意义的,不仅是文本中实有的,还有文本中没有的。研究者“是正确的,当他强调手法并不是事实,而是事实对其所折射出的背景的关系,手法的缺席可能比手法的在场更有效”[24]。不知道一个文本中有意味地缺失什么,便无法理解该文本。洛特曼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负手法”。
文本的同一个物质元素在进入整体的不同结构之中,必然会获得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含义。这在使用一些否定手法,“负手法”的情形中,尤其明显地被表现出来。……结构分析的出发点是,艺术手法——不是文本的物质元素,而是一种关系[25]51。
韵脚的缺失,在古希腊古罗马诗歌(那里还不曾有韵脚)或自由诗(那里已经没有韵脚)文化中,不是在艺术上有意义的元素,但普希金的《我再次造访问……》(1835)中韵脚的缺失,在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诗学传统——这一传统只允许无韵诗在严格地确定的体裁范围内出现——背景下的这一缺失,就会打破读者期待,而以其故意而为的散文化让人印象深刻。与负手法类似,洛特曼称之为“负韵脚”。
一方面,负手法这一思想受到现代分子物理学中“孔洞”概念的提示,作者直接援引了这个概念:孔洞“这是——物质在意味着它之在场的那个结构位置上的缺失”[25]59。“孔洞”一如那些物质的元素一样,也是结构的元素。这样的观点,同索绪尔的语言学与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中有关“零”符号(“零音”“零词素”,等等)的观点,丝毫也不相悖。另一方面,洛特曼发展了“失望的期待” (frustrated expectation) 这一心理学概念,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与诗学》中曾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诗的形式元素,而非内容元素。最后,洛特曼这一概念的另一个来源——蒂尼亚诺夫关于“被销蚀的手法”“消极特征”之有效性的命题:
将文学定义为一种动态的言语构造这一界定本身并没有提出裸露手法的需求。有些时代,被裸露的手法也像所有其他手法一样,是自动实现的——那时,被裸露的手法自然会引发被销蚀的手法与之辩证对立的需求。这一被销蚀的手法在这种情境下会比被裸露的手法更具活力,因为它会取代已成寻常而平凡的构造原则同材料之间的对应对比,进而使它得到强调。一旦被裸露的形式之“积极的特征”被自动化,被销蚀的形式之“消极的特征”就可能被赋予强大能量[26]。
洛特曼的创新,完全契合而大力发扬了蒂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的精神:“负手法”的前提不是“缺席”,而是“负存在”;它不是被动的“零”,而是主动的“负”。
七、洛特曼对雅各布森交际图示的修正
洛特曼不仅是雅各布森的追随者,他同时对雅各布森的一些最重要假设提出了修正。雅各布森在其著作《语言学与诗学》中确定了交际行为的六个“构成要素”,即信息发出者、接收者、代码、信息、语境和接触。洛特曼关注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所使用的语法/代码之间的差异。雅各布森本人曾强调这一差异。洛特曼的朋友和合著者鲍里斯·乌斯宾斯基意识到雅各布森在这本纪念文集中的文章对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要意义,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其他成员也采纳了这一观点。在《艺术文本的结构》一书中,洛特曼认为“雅各布森和其他学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即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实际上使用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代码:一种是对信息进行编码,另一种是对信息进行解码”[27],然后他再次引用上文提到的乌斯宾斯基的文章,强调“在语言学文学中,雅各布森关于区分语法综合规则(说话人的语法)和分析语法(听话人的语法)的观点已得到认可”[28]。《论文化系统的两种交际模型》(1973)一文收录于《思想的世界》中,标题为《自我交际:作为听话者的“我”与“他人”》。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差异被理解为自我交际的条件:尽管说话人和听话人是同一个人,但他们彼此不完全等同,他们的语言也不同。因此,自我交际成为任何符号系统内在多语性的基本例证。
接下来,洛特曼对雅各布森的交际图示进行了根本性修正。首先,有别于代码,语言有历史:“语言不仅包含代码,还包含代码的历史”[23]48。蒂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在文章与著作里曾经论及的任何共时现象的内在历时性,语言的异质性与代码的同质性相对应的观点都是源于此。洛特曼在其晚年著作中有一本书又回到了这种想法。
抽象的交际模型不仅意味着使用相同的代码,而且还意味着传递者和接受者具有一样的记忆容量。事实上,用术语“代码”替换“语言”完全不像看起来那么安全。……语言——这是代码加上它的历史。对交际的这样一种理解隐含着一些根基性的结论[29]。
再继续说,除了一般的“宏观历史”外,语言还拥有个体的历史——准确地说——众多个体的历史: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全民族语言之独特的变体(个人习语)。这样,交际行为就变成翻译行为——从说话者的语言(习语)到听话者的语言(习语)的翻译行为。结果便是交际诸要素在模型上的统一被失去。洛特曼对雅各布森图示正是作出了这样的“修订”:
人们交流的基础是交际行为,它被看作为符号性的交流结构中一些等价符号彼此之间的交换……。所有这些不同的交际类型在罗曼·雅各布森的著名图示中均得到概括:

这样,交际过程的本质便呈现为:一些信息作为编码—解码的结果从发送方传输到接收方。在这种情形下,这一行为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后者接收到与前者发送的是相同的信息(或者,根据某些公认的规则,与之完全等同的信息)。对等值性的违反被视为交际链功能发挥中的缺陷。……不难发现,这种交际图示的功能设置,能解释这一或那一社群集体中已然现成的信息之循环机制,但不仅无法解释,而且会直接排除“发出者—接收者”链条中新信息产生的可能性。
米哈伊尔·洛特曼——尤里·洛特曼之子,也是他的思想的一位优秀的阐释者,对这一修订的另一些结果作出了这样一番表述:
根据罗曼·雅各布森的理论,信息发出者会考虑到语境,而借助语言来形成信息,一旦接触具备,他会将信息传递给接收者。在尤里·洛特曼看来,交际行为通常并不是现成信息的传递:不仅仅是在文本之前和文本之外都不可能有语言——对于雅各布森之所有其他的交际要素,这一点都是公正的。语境——这是共文本(со-текст,кон-текст),它不可能在文本之前存在;语境对文本的依赖程度,一如文本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交际行为乃翻译行为,乃转换行为:文本在转换语言,在转换接收者,在发信者和收信者之间建立联系,也在转换发信者自身。况且,文本还在自我转换,而不再与自身相同[30]。
但是,如果任何交际行为乃翻译行为,就会产生一个悖论:一方面,意义只有在翻译过程中才会被发现,甚或得以成形;另一方面,任何翻译都会转换原文(从发信者的角度)的意义而产生新的意义。无论如何,意义不再等同于它本身,而是在赋义和重新赋义的过程(符号化过程)中得以不断转换。可是,如果根据雅各布森在其经典性著作《论翻译的语言学层面》中所提出的观点,符号系统具有完全的“相互可译性”(mutualtranslatability)特征,那么,在洛特曼看来,这一可译性乃是不完全的:
如果说,雅各布森将“不可译性”解释为通过一定的程序即可以消除的交际障碍,那么,洛特曼则在不可译性(更准确地说,难译性)这一现象中看到了一种文化创新机制,这一机制使人类交流变得艰难,而最终则会使这一交流更富有蕴涵[31]。
对于任何交际行为而言都具有根本性的多语性,正是由此而生[32];最终,这也是文化多语性的缘起之处。
八、后记
“洛特曼与雅各布森”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远非这一篇文章可以穷尽。雅各布森和洛特曼的“系统”和“结构”概念的阐释(以及相应术语的使用)没有得到考察。这个问题值得单写一篇文章,我计划以纪念洛特曼诞辰100周年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为动机撰写此文。洛特曼和雅各布森同欧美符号学奠基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关系,对他们思想的发展和(重新)阐释问题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局部的问题也值得讨论。
我将引用已发表的洛特曼和雅各布森这两人对于彼此的评论,作为这篇概述的结束。他们总是相互支持和尊重,这一点非常重要。1973年,雅各布森在法文版《诗学问题》后记中将洛特曼列为诗歌语法的创建者之一,这些创建者对语言分析和文学分析同样擅长。同年,雅各布森在提到洛特曼对“荣誉”和“荣耀”的分析时称之为“精当的阐释”[33]。十年后,雅各布森在洛特曼生日纪念文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洛特曼“极具远见卓识”[34]。
洛特曼对雅各布森的首次书面评鉴发表于1971年,并不是用俄语,而是用爱沙尼亚语发表的。这是《爱沙尼亚苏联百科全书》(ENE)第三卷中的辞条:
俄罗斯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雅各布森是现代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杰出理论家,是音韵学理论和语言共性理论的开拓者。雅各布森还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诸多诗学问题[35]。
“杰出”这一评价值得注意,须知在托波罗夫为用俄语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KLE)撰写的类似辞条中,根本不允许有评价性定义。
洛特曼在雅各布森的讣告中表达了他对雅各布森个性和学术才华的无比景仰,本文以引用这一讣告的结尾而开篇,现在我要引用它的开头来为自己的阐释圈上句号:
1982年7月18日……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各布森在86岁生日前几个月辞世了,他是世界最著名的语言学家、斯拉夫学者、其研究兴趣如百科全书般广博的人文学者。雅各布森的学术遗产浩如烟海:截至1971年,这位学者已面世著作的书目有828条(其中不乏数百页的专著)。……但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这几百本书籍和文章中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研讨会上的每一篇报告,每一次采访都是一个学术事件,引起强烈反响,摧毁学术成见并且开辟完全出乎意料的全新学术前景。他从来不是追随者。甚至不追随自己。
今天,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洛特曼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