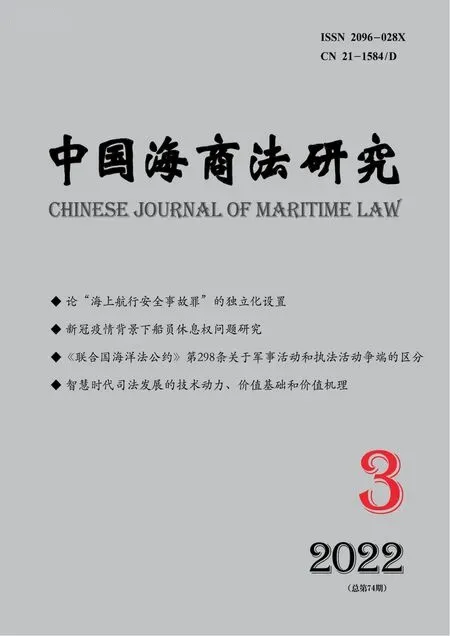“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划区管理工具法律问题研究
任鹏举,马明飞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各海洋大国对国际海底区域(简称“区域”)矿产资源的勘探逐步深入,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简称国际海底局)的既定路线,随着《“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简称《开发规章草案》)的出台,对包括深海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以及富钴结壳等在内的深海海底资源的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已不再遥远。与此同时,大量的水下文化遗产沉睡在广袤的深海海底,它们也是各国海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业化开发“区域”矿产资源的过程中,这些水下文化遗产将会被发现,如何在作业区域内开展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将会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出现。在国际海底局划定的大西洋盆地奥格兰德海峡和中大西洋海脊北部的勘探区内,已发现大量的水下文化遗产,因这一区域曾是历史上罪恶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线的必经之处(1)参见David Eltis, David Richardson,et al:Atlas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访问网址:https://www.slavevoyages.org/voyage/maps#introductory-。。在这一航线上,约有180万非洲黑奴丧生,约1 000艘参与奴隶贸易的船只失事,就此形成了独具奴隶贸易时代特色的水下遗址。[1]保护这些数量庞大的水下文化遗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相关区域远离陆地,且其中沉船、遗骸数量众多,根据《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简称《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第5款的规定,对这些水下遗址实行就地保护,规划相应的水下遗址保护区应作为首选。但由于“区域”非任一主权国家的管辖范围,且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在“区域”内设置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面临着法律和现实障碍。基于此,必须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划区管理工具因需要被管理之客体的不同而存在多种表现形式(2)例如对特定物种、相关栖息地、具有栖息地特征的区域进行保护和管理,从而限制人类活动对区域内相关客体的不良影响。参见Julian Roberts,Aldo Chircop,Sian Prior:Area-Based Management on the High Seas:Possible Application of the IMO’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 Concept,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010年第4期,第484页;转引自邢望望:《界定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第152页。,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来看,划区管理工具就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管理人类活动,从而减少对“区域”内水下文化遗产造成的不良影响,以达成保护之目的。目前,在多边层面,同“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相关的国际组织主要有两个,分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海底局,且这两大国际组织各自均有划区管理工具可适用于“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在区域层面,欧盟1992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框架下的划区管理工具也可在保护“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区管理工具因其适用范围的问题目前难以全面发挥功效,国际海底局也因其暂无保护“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直接职权而不得不依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组织也暂未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纳入其保护客体的范围之中。因此,实现各国际组织在就地保护“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上的互动势在必行。笔者将在系统分析现有“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基础上,探讨在多边层面实现各划区管理工具间协调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具体路径。
二、现有“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述评
为了更好地保护“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防止“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对水下文化遗产造成不利影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海底局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组织在国际法的授权下行使着相应职权,以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组织为代表的区域国际组织也在积极发挥作用。不同的国际组织获得授权的方式不同,权限也各有侧重,具体到划区管理工具的应用上更是差异明显。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发展
作为专司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来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和《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均有所体现。
1.《世界遗产公约》中的《世界遗产名录》
为共同保护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出台了《世界遗产公约》,而后依据该公约第8条的规定,在1976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该公约的实施。这一委员会通过对缔约国境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选取、认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进行管理和保护。这一划区管理工具运行至今,已选定1 154项世界遗产(3)参见UNESCO:World Heritage List,访问网址:http://whc.unesco.org/en/list/?&。。《世界遗产公约》也已有194个缔约国(4)参见UNESCO:States Parties Ratification Status,访问网址:http://whc.unesco.org/en/statesparties。,影响范围广,为保护对人类共同发展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遗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划区管理工具在运行初期尚未给予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过多关注。1980年至2001年,仅有43处海洋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进《世界遗产名录》,且水下文化遗产寥寥,其中有代表性的仅有两处,分别为印度的默哈伯利布勒姆古迹群和墨西哥的奇琴伊察古城。在这一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然为应对海洋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考验专门开展了针对性的保护项目,但保护对象仅限于自然遗产。
随着《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在2001年的问世,国际社会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逐渐深刻,上述偏重于保护海洋自然遗产的格局逐渐被打破,《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也与《世界遗产公约》实现了兼容。一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水下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现有世界遗产或海洋遗产的一部分可以是水下文化遗产。美国夏威夷的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和阿尔卑斯地区史前湖岸木桩建筑是《水下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水下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5)参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世界遗产中的水下文化遗产》,访问网址:http://www.uch-china.com/content.thtml?cid=297。。近年来,随着深海海域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的逐步深入,海洋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成为了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法律和治理领域新的热点。事实上,早在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委员会就意识到了代表性的世界遗产保护网络不能缺少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的保护。[2]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题为《公海世界遗产:一个时代的到来》的报告,报告中认为《世界遗产公约》没有任何地方指明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公海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应被排除在该公约的保护范围之外。[3]此外,该报告还详细地论证了公海区域内存在符合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标准的公海世界遗产,并举出了五个潜在公海世界遗产保护区的例子(6)这五个区域分别是:失落之城热液区(The Lost City Hydrothermal Field)、哥斯达黎加热穹窿(The Costa Rica Thermal Dome)、大白鲨咖啡厅(The White Shark Cafe)、马尾藻海(The Sargasso Sea)、亚特兰蒂斯浅滩(The Atlantis Bank)。。基于此,《世界遗产公约》中的划区管理工具或可为保护“区域”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线水下遗址提供协助。
2.《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及其附件
随着人类深海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水下活动空间大大拓展,这使得多年未受干扰的水下文化遗产暴露于人类的活动范围内。人类也对沉没于海底的水下文化遗产开展了各种活动,水下文化遗产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包括不断增多的建筑施工活动、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为了商业目的而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的打捞。[4]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这一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世界遗产公约》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出台了《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以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值得关注的是,该公约将就地保护列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原则。[5]为贯彻这一原则,水下文化遗产的勘测、发掘和保护都必须采用特殊的科学方法、恰当的技术和设备,而这些内容都体现在了《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附件《关于开发水下文化遗产之活动的规章》(简称《规章》)之中。作为水下文化遗产之勘探、发掘与保护的技术性规程,《规章》所涉及的包括项目设计、文物保护计划及遗址管理计划等诸多管理手段已有明显的划区管理工具的特征。除此之外,就“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第11条、第12条还专门规定了报告通知制度和协调国制度。但遗憾的是,“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尚未有成功实践。
但仍值得关注的是,对“泰坦尼克”号沉船的保护或可为“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7)1985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位置被确定在加拿大的外大陆架海域。为防止其被商业性开发或破坏,美国国会于次年出台了《“泰坦尼克”号海事纪念法案》(R.M.S. Titanic Maritime Memorial Act of 1986)来专门规范针对该沉船进行的研究、发掘及打捞活动,同时也有防止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包括法国、英国及加拿大)对“泰坦尼克”号进行打捞的意图,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纠纷:从1993年至2006年,关于“泰坦尼克”号沉船的诉讼一直不断。直至2004年,为共同解决各国间对“泰坦尼克”号沉船的争端,同时防止无序打捞对该沉船遗址造成的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四国最终达成了合作保护协议——《关于“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协议》(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Shipwrecked Vessel RMS Titanic)。。“泰坦尼克”号沉没在加拿大的外大陆架海域而不是“区域”,如果“泰坦尼克”号位于“区域”内,《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关于“区域”内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得到更全面的探索。[6]即便如此,《关于“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协议》中仍纳入了《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就地保护原则。虽然合作保护协议中并未明确要设立类似于划区管理工具的水下遗址保护区,但协议及其附件提及的保护项目及诸多管理手段同《规章》如出一辙,设置“泰坦尼克”号沉船遗址保护区或不失为一个最优解。综上,该案仍可为就地保护“区域”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线水下遗址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国际海底局划区管理工具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
在广袤的深海海底蕴藏着包括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在内的丰富的战略金属资源,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的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其潜在环境影响的关注。为规范“区域”探矿行为体的行为,保护深海环境,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成立的管理“区域”活动的国际海底局陆续出台了三部勘探规章,要求承包者、担保国等利益相关方同国际海底局合作,制定并实施方案,监测和评价深海采矿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并可运用影响参照区和保全参照区等划区管理工具进行监测和评估(8)根据国际海底局三部勘探规章的规定,影响参照区是指反映“区域”环境特性,用作评估“区域”内活动对海洋环境影响的区域。保全参照区是指不应进行采矿以确保海底的生物群具有代表性和保持稳定,以便评估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的任何变化的区域。。除了上述划区管理工具之外,国际海底局理事会还在2012年审议通过了有关克拉里昂-克利伯顿(The Clarion-Clipperton Zone)断裂带特别环境利益区的决定(9)克拉里昂-克利伯顿勘探区位于东中太平洋,在夏威夷岛之南和东南,贮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核,目前已有八个承包者获得面积共约52万平方公里的勘探许可。,形成了9个特别环境利益区也即环境特受关注区,旨在对克拉里昂-克利伯顿勘探区内的海洋环境进行动态监管和有效保护。有消息指出,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将会是“区域”内第一个被商业开发的地区。[7]154为此,国际海底局理事会还进一步拟订了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环境管理计划,并列入建立特别环境利益区域代表性网络的规定,以确保有效地保护相关区域的海洋环境(10)参见Decision of the Council Relating to 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Clarion-Clipperton Zone(ISBA/18/C/22)。。可以说,国际社会对深海环境保护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平衡“区域”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了国际海底局的重要任务。[8]但是,在这一时期,上述划区管理工具均旨在加强“区域”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在目标之列。
随着“区域”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进程的推进,为规范国际行为体在开发过程中的行为,明确相关权利和义务,国际海底局自2013年起开始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规章制订的准备工作,并明确了监管思路。[9]在多次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国际海底局于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间陆续发布了四版草案,在其中,影响参照区和保全参照区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风险预防原则一起被国际海底局多次强调。值得关注的是,在草案中不仅有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条款(11)例如2019年3月版《开发规章草案》第35条。,且草案附件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也要求承包者在环境影响报告中列出“已知存在于潜在影响区内的任何具有考古和历史意义的遗址”,这表明国际海底局已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划区管理工具的考量因素中。这或可为将国际海底局划区管理工具运用到大西洋盆地奥格兰德海峡和中大西洋海脊北部勘探区内进行奴隶贸易航线水下遗址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三)区域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潜在互动
在区域层面,区域海洋组织依据区域海域协定而设立管理工具适用于区域内专门划定的海洋区域,这是目前国家管辖外海域划区管理工具实践的主要形式。截至目前,在南大洋、地中海和东北大西洋,已有数个公海保护区成功设立。[10]其中,南大洋公海保护区是最早设立的,旨在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在其设立依据1980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生效之后,在海洋保护区的非官方正式表达中,将“保护历史和文化遗址”纳入了海洋保护区设立的目的(12)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目的是为海洋物种、生物多样性、栖息地、觅食和哺育场所提供保护,并在某些情况下保护历史和文化遗址。参见CCAMLR: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访问网址:https://www.ccamlr.org/en/organisation/achievements-and-challenges#MPA。。而在其后的地中海派拉格斯公海保护区的设立过程中,在其设立依据1995年《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的文本中,明确将“在科研、审美、文化或教育层面有着特殊意义的地址”纳入了特别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之中(13)参见《地中海特别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议定书》第8条第2款。。除此之外,在区域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北大西洋公海保护区。东北大西洋公海保护区是在《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体系下建立起来的。[11]119截至目前,《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的缔约方包含东北大西洋沿岸的15个国家以及欧盟(14)缔约方如下: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英国、卢森堡、瑞士、欧盟。,适用的海域中超过50%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该公约的主要目标是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预防和消除污染,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洋区域免受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并在切实可行时恢复受到损害的海域(15)参见《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第2条。。为实现这一目标,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组织于2003年引入了《关于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建议》《关于识别和选取〈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下海洋保护区的指南》《关于管理〈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下海洋保护区的指南》这三个文件,为该公约项下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和管理奠定了法律基础。截至目前,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组织已设立7个公海保护区,总面积超过46万平方公里(16)参见OSPAR:Key Figures of the MPA OSPAR Network,访问网址:https://mpa.ospar.org/home-ospar/key-figures。。可以说,这些成功的实践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相关条款和指南所具有的可操作性。虽然这一公约暂未将水下文化遗产明确列为其保护客体,但是鉴于水下文化遗产同海洋环境及生态存在密切联系,在《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划区管理工具下实现海洋环境保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互动仍有一定空间。此外,鉴于公海和“区域”在地缘上的结合性(17)在地理空间上,“区域”的上覆水域即为公海,二者在地缘上的结合性决定了“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区域海洋组织划定的公海保护区的相关管理与保护措施之外。,区域海洋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在“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作用也应予以重视。
(四)国际组织“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简评
由上观之,现有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从不同的出发点为就地保护“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既可以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将“区域”内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水下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加以保护,又可通过《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附件《规章》中的保护计划及遗址管理计划实现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而国际海底局借助其设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也为在“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就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依据和空间;区域海洋组织现有的公海保护区的成功实践更是为“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积累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总体来讲,上述划区管理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均可在“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初期为就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提供思路和方向,但在实践阶段,上述划区管理工具在适用上的困境会进一步凸显,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国际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适用的困境
(一)《世界遗产公约》暂无法适用于“区域”
通过对《世界遗产公约》的文本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这一公约虽然并未在任何地方指明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区域”水下文化遗产应被排除在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但是却在多处强调了对缔约国本土境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18)参见《世界遗产公约》第3条至第6条、第11条、第13条、第19条。。除此之外,在该公约划区管理工具运行的实践中,即在选取、认定符合公约规定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管理和保护的过程中,均为一个或几个缔约国将位于本国或多国领土内的遗产向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尚未有申报“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先例。因此,从目前的国际法的解释和实践来看,《世界遗产公约》划区管理工具暂无法适用于“区域”。
(二)《水下文化遗产公约》适用范围有限
上文已提及,《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及其附件《规章》为实现“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作了诸多有着明显划区管理工具特征的安排,但仅限于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截至目前,《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仅有69个缔约国,[12]仅约占《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数量的三分之一,因而适用范围十分有限。进一步说,目前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大国寥寥。以前文提及的奥格兰德海峡和中大西洋海脊北部勘探区为例,国际海底局已分别同承包者签署了一份锰结壳勘探合同和三份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19)参见ISA:Exploration Contracts,访问网址:https://www.isa.org.jm/index.php/exploration-contracts。,涉及法国、俄罗斯、巴西、波兰等四个担保国,其中仅有法国和波兰加入了《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因此,如何将《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划区管理工具适用于“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仍待观察。
(三)国际海底局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权能较弱
国际海底局的职责在于规范承包者、担保国等利益攸关者在“区域”内进行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活动,同时防止这些活动给“区域”带来潜在环境影响,保护和养护“区域”的自然资源。而具体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国际海底局的三部勘探规章及《开发规章草案》仅规定了承包者的发现通知义务、国际海底局秘书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的转交义务以及暂停开发义务三个程序性事项,暂未涉及实质性的保护措施(20)在国际海底局颁布的三部勘探规章中,以《“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为例,其第8条规定,在“区域”内发现任何实际或可能的考古或历史文物,探矿者应立即将此事及发现的地点以书面方式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这些资料转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国际海底局正在修订的《开发规章草案》中,以2019年3月版《开发规章草案》为例,其第35条规定,承包者应立即将在合同区内发现的任何具有考古或历史意义的人类遗骸或任何类似性质的文物或遗址及其地点,包括所采取的保全和保护措施以书面形式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应将此类信息转交给担保国、遗骸来源国(如已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及任何其他主管国际组织。在合同区内发现任何此类人类遗骸、文物或遗址后,为避免扰动该人类遗骸、文物或遗址,不得在合理范围内继续勘探或开发,直至理事会在考虑遗骸来源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及任何其他主管国际组织的意见后,决定可继续勘探或开发。。从文本上看,在后续进行水下文化遗产实质性保护时,国际海底局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见。进一步说,《开发规章草案》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虽已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划区管理工具的考量因素中,但综合整个制度来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仍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附带性事项,在未来“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仍未可知。
(四)区域海洋组织同多边国际组织存在潜在的冲突
区域海洋组织划区管理工具的主要目标在于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虽然已有部分区域海洋协定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了保护目标,但由于区域海洋组织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权限和措施仍然存在模糊之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时至今日仍无区域海洋组织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划区保护的成功实践。此外,由于目前已有的部分区域层面的公海保护区的海床、底土同“区域”在地缘上存在重合,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海底局等多边机制下,“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之管辖已完全碎片化,区域机制同多边机制存在部分重叠,因而二者在划区保护“区域”水下文化遗产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此类冲突将使“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识别、选取和保护变得更加复杂。
四、未来“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完善和协调的方向
随着“区域”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进程的加快,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国际组织划区管理工具进行协调以实现“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这一契机,依托现有平台,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相关划区管理工具的完善和协调。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方式有二:一是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区管理工具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区域”;二是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担保国责任的范畴以提高国际海底局划区管理工具的效能。但上述设想在短时间内恐难实现,基于此,为回应现实需求,国际海底局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探索路径先行达成专项谅解备忘录,在多边机制的框架内就“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水下文化遗产的合作保护及划区管理工具的协调达成合意。最后,在上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完善和协调的过程中,应加强同区域海洋组织的互动,密切关注目前正在进行的公海保护区谈判,注重其同公海保护区的耦合。
(一)逐步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区管理工具的适用范围
如前所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有的框架下,无论是《世界遗产公约》还是《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均无法将各自的划区管理工具适用于“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就前者而言,《世界遗产公约》虽缔约国数量众多,但目前的国际法实践和解释暂不支持这一公约适用于“区域”;而后者虽将“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中,但囿于缔约国数量有限,且大部分“区域”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大国均未加入该公约,致使现阶段该公约划区管理工具的功效也无法充分发挥。而相比较而言,前者面临的障碍更加复杂。事实上,为将“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的保护对象范围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通过渐进式改变或正式的政策改变,扩张地解释《世界遗产公约》从而将其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二是在《世界遗产公约》之外对其进行修正,类似于1994年《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与《海洋法公约》的关系;三是通过缔约国之间的国际谈判制定《世界遗产公约》项下的任择议定书,但其只对那些批准任择议定书的国家具有约束力。[13]通过上述任一路径均可使《世界遗产公约》划区管理工具适用于“区域”,笔者对上述三种路径均表示认同。但现实却仍存在诸多变数,目前缔约国对世界遗产专家组的意见和决策存在较多的质疑,国际社会对世界遗产委员会过度政治化的批判也是不绝如缕。[14]有鉴于此,无论作出何种路径选择,实现《世界遗产公约》划区管理工具在“区域”的适用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将《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划区管理工具适用于“区域”,最根本的路径是鼓励各国特别是“区域”矿产开发大国加入该公约,以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但如前文所述,目前已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大国较少,具体到奥格兰德海峡和中大西洋海脊北部勘探区涉及到的担保国中仅有法国和波兰加入了这一公约。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各海洋大国选择暂不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与本国承担的其他国际义务相矛盾(21)俄罗斯、巴西等国拒绝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原因是这些国家解释的《海洋法公约》和《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的义务不符;美国拒绝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部分原因是其尚未加入《海洋法公约》,且在签订《国际救助公约》时并没有对“水下文化遗产不适用的条款”即第30条第1款(d)项作出保留。;二是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或同本国的政策和法律不一致(22)代表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美国不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原因还有:未建立水下文化遗产报告制度、允许商业开发水下文化遗产、允许对水下文化遗产适用救助法和发现物法等海事法,以上均和《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不符。而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均有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案,如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则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案均需要修改,程序较为繁琐。,有待系统性修改,而进行此项工作将带来繁重的行政负担。[15]综上,短期内吸纳各海洋大国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并不现实。有鉴于此,借助国际海底局的相关制度在现有框架下实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协调是必由之路。
(二)增强国际海底局划区管理工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效能
《开发规章草案》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已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考量因素,但综合整个制度来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仍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附带性事项,这势必会影响相关划区管理工具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方面效用的发挥。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节约规则变动的成本,有必要通过国际海底局内部制度的渐进式变革以增强划区管理工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效能。在《海洋法公约》及《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为国际海底局创设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中,担保国责任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之一。[16]这一制度要求承包者(自然人或法人)在同国际海底局签订勘探或开发合同时,必须取得其所属缔约国的担保以确保承包者依法开展相关活动。承包者在资源勘探与开发过程中对“区域”造成损害的,除其本身要承担过错责任外,担保国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17]担保国义务包括尽责义务和直接义务两部分,这在《开发规章草案》中也有突出体现(23)尽责义务的目的是确保承包者遵守勘探开发合同和“区域”制度,担保国对承包者因没有履行《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义务而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但是当担保国已经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以确保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遵守“区域”制度时,则其对于承包者的未遵守行为而造成的损害没有赔偿责任,此即为担保国的尽责义务。直接义务则主要涉及“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并对担保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和最佳环境做法等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以及确保管理局向承包者发出紧急命令时提供保证等。。但是,上述义务仍仅限于海洋环境保护,并未拓展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笔者认为,正如前文提及的“区域”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线水下遗址,“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或已沉睡近百年,早已与所处的海洋环境融为一体。部分水下文化遗产甚至已成为某些海洋物种的栖息地,形成了一类独特的生态系统。因此,保护“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同保护“区域”海洋环境并非泾渭分明,上述保护海洋环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可适用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18]综上,为加强《开发规章草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同担保国责任制度内在的协调和一致,在这一草案后续的修订和谈判中,担保国义务不应仅限定于海洋环境保护,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以进一步提高国际海底局划区管理工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效能。
但应予特别关注的是,在现阶段,对水下文化遗产的积极保护并非国际海底局的职权范畴,这一点无论是在《海洋法公约》还是国际海底局出台的三部勘探规章中都一以贯之。目前正在修订的《开发规章草案》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条款上也未作较大突破,仅是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要求承包者在环境影响报告中列出“已知存在于潜在影响区内的任何具有考古和历史意义的遗址”。综上可见,各利益相关方对扩展国际海底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权限仍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但是,“区域”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线水下遗址的保护已迫在眉睫。为减少《开发规章草案》谈判过程中的阻力,国际海底局可采取相应的技术性手段,仍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现有环境保护的框架内,且将内容严格限定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消极保护即维持现状,防止“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行为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进一步破坏。在此前提下,国际海底局应采取渐进式的策略,首先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纳为担保国的尽责义务,待时机成熟再拓展其为担保国的直接义务,以此来逐步提高划区管理工具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效能。
(三)达成谅解备忘录推动划区管理工具的有效结合
无论是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区管理工具的适用范围还是适度增强国际海底局划区管理工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效能,虽然可根本性地解决国际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在“区域”适用的困境,但在短时间内均难以实现。可是,“区域”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已不再遥远,加强“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已是大势所趋。而就国际海底局目前已出台的勘探规章和正在制订中的《开发规章草案》来看,在其中已明确规定国际海底局秘书长要将勘探或开发过程中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转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且在决定继续勘探或开发之前要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见(24)参见2019年3月版《开发规章草案》第35条。。此类规定为这两大国际组织开展深入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有鉴于此,为回应现实需求,在国际海底局现有的相关制度框架内实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协调是必由之路,国际海底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深入磋商及合作必须提上日程且需要以一定的结果作为支撑。事实上,国际海底局已同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电缆保护委员会、国际水文组织等诸多国际组织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在“区域”事务上的合作(25)参见ISA: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访问网址:https://www.isa.org.jm/legal-documents。,这为国际海底局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成就“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专项谅解备忘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具体到操作层面,鉴于《世界遗产公约》暂无法适用于“区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根据《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由这一公约的执行机构即秘书处作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主体。在合作的具体安排上,谅解备忘录应以国际海底局现有的规定为框架,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及其附件《规章》中的各项制度为内容,就双方如何进行“区域”矿产勘探和开发过程中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的评估以及划区管理工具上的协调作出程序上的设置。此举既可以解决因《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数量较少而导致的适用困境,又可充分发挥国际海底局在“区域”事务上的作用,因此应予以重点关注。
(四)注重同公海保护区的耦合和同区域海洋组织的互动
近年来,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简称BBNJ)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2015年举办的第69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决议,启动了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就BBNJ拟订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执行协定的进程。[19]随后,联合国大会第70届会议发布的《第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技术摘要》中指出,“区域”的水下历史和考古地点(包括沉船及其自然环境)构成世界水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同BBNJ有关的其他裨益。[20]因此,BBNJ同“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目前BBNJ的谈判进程中,建立公海保护区的议题受到了较多关注。[21]在对这一议题的谈判中,有立场认为公海保护区的定义应尽可能宽泛,且文化价值也应纳入。目前,在国际法层面,关于公海保护区虽然尚无统一的定义,但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自然保护区指南中的“保护区”的概念为例,海洋保护区的客体包括“与生态服务和文化价值相关的自然环境”(26)参见Nigel Dudley: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访问网址:https://www.iucn.org/content/guidelines-applying-protected-area-management-categories-0。,这与《世界遗产公约》中规定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之间存在些许差异,但是也存在着重合的现实可能,因公海保护区所要保护的具有生态和文化价值的区域也有可能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区。[11]179此外,在地理空间上,“区域”的上覆水域即为公海,二者在地缘上的结合性决定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公海保护区的相关管理与保护措施之外进行,[7]197这也就为未来国际组织“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同公海保护区的有机结合奠定了现实基础。基于上述分析,在国际组织“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完善和协调中应密切关注BBNJ公海保护区议题的进展,注重其同公海保护区的耦合。
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BBNJ谈判的政府间会议阶段,各方虽然就划区管理工具的关键要素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就公海保护区同其他行业性划区管理工具的关系以及公海保护区设立的程序、管理、监测和评估问题仍存在分歧,在短时间内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仍难以预估。[22]而在目前全球零散空缺的公海法律与治理框架下,鉴于区域海洋组织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公海保护区管理体制,因此在划区保护“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海底局同区域海洋组织要加强互动,并率先在区域层面实现突破。具体来说,在合作过程中,各组织间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模式,首先就共同管辖的海域底土上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实现信息共享,进而在多边体制内部参照已有的区域保护机制制定相应的指南或准则。此外,各组织也可就合作的程序性事项达成专项谅解备忘录,为合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
五、中国的主动因应
现有的机制和成功实践虽为国际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完善和协调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但这一工作仍面临着各方利益难以平衡等现实困境,且“区域”内矿产勘探和开发的主要参与国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关注也较少,因此可以预见到相关进展将较为缓慢。根据国际海底局新拟订的路线,《开发规章草案》将不迟于2023年7月9日完成,[23]留给“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完善和协调的时间已然不多。作为“区域”矿产开发大国和水下文化遗产大国,中国应当通过以下方式在“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完善和协调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促进水下文物保护区同海洋保护区的协同
截至目前,中国国内立法中关于海洋保护区选取、设立及管理的法律规定见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修订)、《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及《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体系较为完备。在前三项法律文件中均将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遗迹纳入了划区保护的范围之中(2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修正)第8条、第21条至第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修订)第10条,《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第6条。;在《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海洋历史遗迹列为了保护对象(28)参见《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第10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原国家海洋局出台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指南》所呈现出的诸多管理手段却仍偏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未能体现对遗迹文化价值的兼顾(29)参见《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指南》中“三、规范化管理要求与内容”和“四、保护与开发利用活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再通过对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的观察,笔者发现目前在中央层面有关于此的规定仅见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4]且暂无同海洋保护区类似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以及保护规划建设与管理指南。在实践中,虽在地方层面已有某些水下文物大省(如广东、福建)先行先试为水下遗址设置了水下文物保护区,开启了以保护区模式进行水下文化遗产管理的先河,[25]21但时至今日仍处于初级阶段,与欧美国家开展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实践存在较大差距,[26]且在中央层面尚无水下文物保护区的总体规划,同海洋保护区的协同更无预期。作为水下文化遗产大国,中国应大力完善国内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的建设,并注重水下文物保护区同海洋保护区的互动,以此带动“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的完善和协调。由于水下遗址多已成为海洋生物资源的栖息地,水下文化遗产与所处之海洋环境早已融为一体,[25]22且目前中国海洋保护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保护与管理模式,因此未来在中央层面进行的水下文物保护区模式的规划与建立可参照和借助现有海洋保护区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首先,国务院应尽快出台“水下文物保护区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文物局应出台“水下文物保护区管理办法”等部门规范性文件,水下文物大省也需相应地对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行修订,形成完备的水下文物保护区法律体系。其次,国家文物局应出台中央层面的水下文物保护区整体规划以及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指南,并加强同国家海洋局的沟通和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文物局一方面应借鉴《世界遗产公约》及《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相应的划区管理手段,实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协调,同时也应借助中国现有海洋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完善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各项管理措施;另一方面,应对已被纳入海洋保护区的具有突出历史文化价值的海洋遗迹进行评估,探讨同国家海洋局合作保护的可行性,减少重复划区以降低成本。此外,国家海洋局在这一过程中也应对《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指南》进行适当调整,纳入对海洋遗迹文化价值保护的措施和手段,实现同水下文物保护的互动。
(二)进一步提升中国深海能力以争取话语权
中国参与“区域”矿产资源勘探的时间虽然晚于西方发达的海洋大国,但时至今日,中国不断追赶海洋大国的步伐,已走到“区域”舞台的中央。与此同时,中国的深海勘探能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装备技术层面同西方海洋大国的差距已大大缩小。[27]但是,在深海开采设备层面,中国同其他“区域”开发大国仍存在较大差距,对未来中国“区域”矿产资源的商业性开发形成了阻碍。再通过对中国水下考古能力的观察,可以看出,中国水下考古的机构设置不断完善(30)2014年,旨在保护、研究中国水下文物的中央层面的专业机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获批独立建制,标志着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也在2014年正式投入使用,与此同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南海基地、西沙工作站、北海基地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一批近海和远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重大项目得以开展,影响力不断扩大。然而,中国至今尚未在“区域”开展水下考古项目,深海考古能力仍然不足。随着“区域”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的逐步深入,未来如在中国承包者的勘探开发区内发现了水下文化遗产,中国政府的应对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如前文所述,就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是首选,划区管理工具是关键,但中国目前在国内仍尚未建立完备的关于水下文物保护区的法律和管理体系,就地保护“区域”内水下文化遗产只能是空谈。有鉴于此,中国作为“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大国和水下文化遗产大国,除了在国内层面要积极完善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制度建设外,还要进一步提升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能力和深海水下考古能力,探索在“区域”开展水下考古项目,实现“零”的突破,以自身能力的提升带动和引领国际海底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在“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划区管理工具上的完善,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争取话语权,努力实现二者间的协调,在强化中国海洋硬实力的基础上着力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
(三)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划区管理工具的协调
海上丝绸之路自汉唐形成,是古代中国与海外交往的贸易之路。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交往中,受到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的影响,很多往来的船只难免发生意外葬身海底,经过日积月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下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起源于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作为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更是中国灿烂的海洋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包括水下文化遗产在内的海洋遗产的保护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应成为共享共赢的活动。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南印度洋海域属于“区域”的范畴,且中国也已获得西南印度洋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勘探矿区,未来在这一区域内,极有可能发现起源自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如何就地保护这些中国海洋文化的瑰宝值得深入探讨。为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因应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应在国际层面加强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第一,无论是在“区域”矿产资源开发还是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均应作为国际规则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全程参与BBNJ公海保护区议题的谈判,[28]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的“话语驱动”和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的战略依托,[29]积极调和各方在这一议题上的分歧,求同存异,争取早日达成有拘束力的协定;同时,积极协调国际海底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区域海洋组织就划区管理工具在“区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适用上达成谅解备忘录,主动提出中国方案,增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对内深挖包括水下文化遗产在内的海洋文化遗产资源,对外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申报世界遗产,加快“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进程,扩大中华海洋文化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关注。令人振奋的是,在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功申遗,这是中国首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洋文化遗产。未来,中国应继续在海洋文化遗产事项上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交流,利用这一国际性平台展示中国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增强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与海洋文化的影响力,促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区管理工具的完善。同时,未来如果在中国所属的包括西南印度洋在内的“区域”勘探矿区内发现水下文化遗产特别是起源自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时,在多边机制暂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形下,应积极借鉴现有区域公海保护区设立和管理的成功实践实现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
第三,鉴于《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划区管理工具适用于“区域”时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的问题,考虑到已有相当部分的学者主张中国应积极加入《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国在后续应加大对加入这一公约的具体程序和在中国适用的研究和论证力度,以早日加入该公约,[30]体现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担当。同时努力促成各“区域”矿产开发大国加入这一公约,凝聚共识,在未来共同积极利用《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划区管理工具,早日实现对“区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