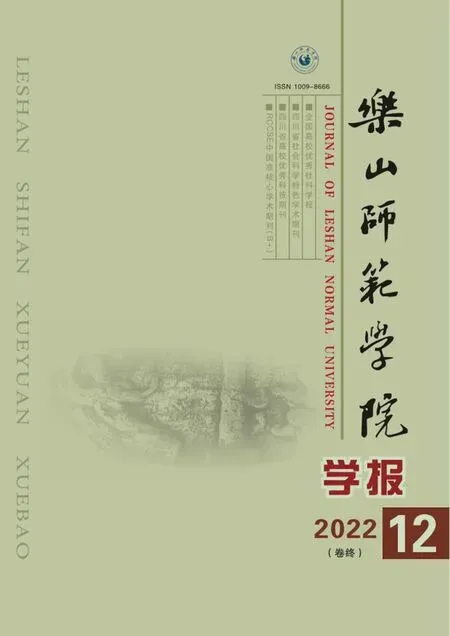苏轼的乐园意识
——以《双石》为中心
郭江波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北宋是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发达的经济带动美学思潮的转型,这时期士大夫对“美”的追求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跨出以往的范围,冲破以往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1]2,例如传统文化中岁寒三友才是文人墨客关注的焦点,而北宋文人却关注国色天香的牡丹。苏轼作为一代文豪和文坛领袖,一生酷爱石头,这种不同凡响的审美观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对苏轼嗜石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苏轼嗜石为出发点,探究北宋文人的审美兴味和精神世界,如《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2];第二,将苏轼的嗜石放置在整个北宋大时代背景下,研究“石”意象的类型与相关诗歌,如《北宋诗歌中的石意象研究》[3]。而关于苏轼喜爱石头的相关论述较少,且已有的成果也存在诸多局限性:从研究对象来看,都没有将苏轼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是以苏轼为切入点或者将苏轼作为一个典范例子置于整体研究;从研究的作品来看,多流于泛化而缺乏针对性,没有挖掘出某些代表性作品的深刻内涵和底蕴;从研究角度来看,仍然局限于意象、审美等传统维度,较为单调。可见,目前对苏轼爱石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
笔者选取苏轼青睐的仇池石为研究对象,以《双石》诗作为典型研究文本,结合苏轼的成长地域环境、哲学思想和生平经历,具体阐释《双石》的意象、结构和思想,进一步探究苏轼在《双石》中表现出的浓重乐园意识。据《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载“殷勤峤南使,馈饷扬州牧”①,这双仇池石是表弟程之元从“珠浦”带来送给他的,而得到石头的苏轼“得之喜无寐”,在此诗中他赞美仇池石有“幽光先五夜,冷气压三伏”的特点。看似这块石头因为本身的美感特质才获得苏轼的青睐,但根据他为仇池石所作的《双石》诗序来看,苏轼对仇池石的喜爱更来自于超越其外在形态的因素,即主体与客体之间内在精神的契合。在《和陶桃花源》序中,苏轼借工部侍郎王钦臣仲称赞仇池“可以避世,如桃源也”,“桃源”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构建了一个安静祥和、淳朴自然的世外桃源。此后,“桃源”便成为人们心中的理想乐园。可见在苏轼眼里,仇池已超脱出外在的表象,化为精神的家园。在《双石》诗中,苏轼通过追求足乐、归家心切、向往隐逸将其乐园情结表现出来。
一、追求足乐,舒放闲适
《双石》第一句“梦时良是觉时非”便以梦幻现实、是非对错形成鲜明对比,旨在强调对梦的留恋和对现实的憎恶。在序中作者指出仇池命名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梦,“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而在《和陶桃花源》序中,苏轼再次提到仇池的起源,“予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值得注意的是,后者通过“而”字以转折关系从两方面对仇池进行了简单的刻画,虽然这里人物与外界并无差异,但是山清水秀,景色诱人,更重要的是有“足乐者”,转折关系的言外之意是俗世中并没有“足乐者”。因此,苏轼对仇池由衷地喜爱正体现了他对梦境中“足乐”的追求。“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乐的观念,因此有必要探究苏轼“乐”的哲学。这不仅有助于厘清苏轼的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苏轼在追求“乐”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对乐园向往的痕迹。
(一)乐的态度:可观皆有可乐
在《超然台记》中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可见,苏轼的“乐”并非是主观情感的喜怒哀乐之乐,而是抛弃分别之心,以齐物的眼光来看待万事万物,此时“乐”已转化为一种面对人生的态度,成为与现实和谐相处的方式。
庞朴教授指出:它是“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4],而身心与宇宙合一的观点与庄子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李泽厚又认为“他(庄子)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长生的另外一套”[5],庄子对生命的关注对苏轼“乐”的追求有深远的影响。庄子认为对功名利禄、生老病死等问题过分的追逐是痛苦的根源,要求与世俗决裂,摆脱一切俗尘杂念,从世事的纠纷和困扰中挣脱出来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即无所待的逍遥。对外界的否定正是体现了对自我生命的关注,以回归自然的方式纠正走向歧路的人性,让人回到乐土,回归乐园。
虽然苏轼也多次表明类似的观点,如“人生识字始忧患”“人生不才果为福”等,颇有庄子绝圣弃智的特色,但实质上苏轼并不否认现实社会,也并不认为必须要与世隔绝,如包弼德所说的“苏轼毫不怀疑,那些构成人类社会环境的事物是真实的,要成功地度过此生,人们必须留意这些事情”[6],他在继承庄子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在《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中苏轼否定了脱离世俗以求“超然”的观点,他说“世之所乐,吾亦乐之”,这里的“世”应指没有侵害到个人身心的日常生活,所以在世俗中苏轼同样可以得到乐趣,这归于他“游于物外”的态度,在“有待”中仍然能够获得逍遥自由。
(二)乐的途径:抛却繁琐世事
苏轼否定的是那种束缚身心的世事和拘束个人心性的枷锁,尤其是在遭遇挫折和磨难后表现得更加强烈,由此萌发了对乐园的向往之情。王水照先生总结了苏轼一生中的三种磨难:与至亲好友的生离死别、政治前途的阴晴交替和病痛的反复煎熬[7]。其实,不少文人墨客都经受过三种人生磨难的考验,但他们各有不同的化解方式:有的走向寻仙访道的道路,炼仙丹、吃仙药,乞求长生不老超越苦痛的现实;有的沉湎于酒色,倒向消极的享乐主义;有的抛弃政治,远离现实,企图保全本真自我。苏轼没有采取类似的方式,而是在歌唱悲哀歌曲的同时关注个体的自我命运,转而寻求超越现实悲剧性的出路。
苏轼贯穿了传统文化中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壮志未酬的感慨,他写“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表达命运的多变无常,胸怀抱负不得实现,感慨“谁道人生无再少”(《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哀伤“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类似的诗词比比皆是,但苏轼诗歌的意义不在于对苦难的书写,而是面对如此苦难、悲痛、不圆满的现实世界,应该怎样才能超越悲苦,实现自由无碍的人生境界,摆在面前的困扰自然而然地促使苏轼反省自身、审视现实,最终转向对乐园追求。
元丰二年(1079),李定、李宜等多次弹劾苏轼,刻意曲解苏轼诗文,指责苏轼讽刺时政,愚弄朝政,随后皇甫遵奉神宗之命从汴京出发至湖州逮捕苏轼,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在历经四个月的监狱恐怖后,苏轼最终被贬谪至黄州,任黄州团练副团使。在狱中他写给弟弟苏辙《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只就题目来看苏轼已经有了生死之忧,并对前途悲观失落,但经各方人物极力营救最终保全性命,在出狱时他写道“余年乐事最关身”,所谓“乐事”正是抛开繁琐无聊、束缚身心的世事,努力追求“足乐”的境界。
(三)乐的追求:寻觅精神乐园
苏轼“梦时良是觉时非,汲井埋盆故自痴”(《双石》)的感慨建立在渴望“足乐”的基础上,只有“足乐”才能消解现实世界种种的不圆满,才能以平静淡然的眼光看待一切变化,以不喜不悲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起伏跌宕,而“足乐”的实现又必须抛却损人身心的枷锁,保持自由的身形和自然的心态。同时,“足乐”既是乐园成立的基本要素,也是乐园建构成功之后的外在表现。欧丽娟教授归纳了乐园的几点要素,其中就包括丰饶愉悦[8]8,而丰饶愉悦既体现在有美丽怡人的自然环境、物产充裕的物质基础,还体现在自然身心舒放、闲适、和谐,即精神的足乐。总之,苏轼对仇池的喜爱体现出他对“足乐”世界的渴求,即对精神乐园的憧憬。
二、追忆故土,乐在其中
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土地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解决温饱的物质需求来源,而且是建立精神家园的基础。在外人看来再朴素不过的乡野之地成为孕育诗人精神世界的家园,由此衍生出浓重的家园意识,家园成为每个中国人内心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而对家园的依恋也成为人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家园意识渗入文学中表现为浓烈的思乡情感:一方面,思乡是对传统意义上血缘关系的认同,另一方面,思乡也符合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苏轼作为传统士大夫,对家园的依恋之情伴随了他整个生命历程,而在《双石》中家园更多带有精神乐园的意义。
(一)意象:寄托乡思
《双石》颔联和颈联对仇池石进行描绘,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在无奇的外表下掩盖着诗人浓重的怀乡情结。“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分别对白石和青石进行刻画,但苏轼所选择的意象却有深长的意味。
所谓“意象”首见于《周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9],因此,象形文字是意象最原始的状态,陈植锷在《诗歌意象论》中提出:意象是诗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词语为物质外壳的诗意形象——意象,也就是诗歌艺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基本单位”[10],意象是文学中表情达意最常见的手段之一,能取得言近旨远、回味无穷的效果。当时苏轼在扬州任职,从扬州到巴蜀有千里之遥,但他通过“太白”“峨眉”将扬州与巴蜀巧妙地连接起来。峨眉在四川,本来就具有典型的家园象征性,但太白与家园的关系似乎相差较远。实则不然,蜀道从长安出发经太白山再到剑门关,太白是通向巴蜀的必经之地,且李白也惊叹“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蜀道难》),太白山成为蜀道中的关键一环,是沟通蜀中与外界不可或缺的媒介和桥梁,在某种程度上,太白山也成为在外游子家园的寄托和精神的故里。
(二)地域:恋乡传统
西蜀士子从唐五代以来,就有不愿出仕的传统[7]76,这是苏轼《双石》中怀乡思想的又一依据。葛立方注意到:“苏东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归蜀,怀归之心,屡见于篇咏。”[11]在苏轼笔下屡屡出现对巴蜀的依恋,如“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初发嘉州》)、“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巫峡》)等无不将巴蜀地理写得雄奇秀美,表达对巴蜀由衷地热爱。在出蜀入仕的三十多年中,异样的地理环境、不断变更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激发苏轼对巴蜀的思念,在黄州观长江他写道“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南乡子·春情》),这完全是移情的表现,将对家乡山水的深情投射在所见之物;在润州,当他看到浩荡奔涌的长江,将思绪飘回万里之遥的故乡,写下“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一个“我”字生动地将对故乡强烈的归属感传达出来。
(三)故乡:乐园化身
或许可以说,蜀人不仕所引起的深刻的乡土之恋,促成了苏轼人生思考的早熟,也预伏和孕育着他整个的人生观。[7]77这个人生观就是对家园的追寻和依恋,而这里的家园不仅是血缘关系上的家园,还是在外漂泊之人心灵的故乡,只要精神回到故乡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避风的港湾,隔绝一切烦扰和毒害。因此,《双石》中蕴含着强烈的怀乡情感,而苏轼心中的故乡早已成为在外游子满足精神需求的符号,成为乐园的化身,与其说苏轼对故土缠绵依恋,不如说是对精神乐园执著的追求。
无论是从诗歌意象还是西蜀文化背景分析,苏轼对家园的热爱和依恋是不可否认的,但强烈的思乡情结源于自我精神的需求,这种需求在远走异国他乡、感受别样风貌的环境和文化习俗的背景下趋于极端,为了弥补飘零心理的缺憾,诗人自觉地追忆故土,而对故土的追忆实则是对乐园的追求。
三、追寻桃源,自然和谐
“仇池”一词本身便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带有丰厚的文化意蕴。在《双石》和《和陶桃花源》中苏轼除了以梦作为解释之外,他还提到“曰‘公何此问,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这句话大有深意,包含着浓浓的乐园色彩。
(一)藏石动机:追求诗意人生
只就苏轼收藏一块仇池石的举动来讲,就体现出苏轼对乐园向往的倾向。苏轼爱石是出了名的,喜欢收藏石头是他的爱好之一,但他并不是以经济价值作为衡量收藏与否的尺度,而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评判。他在《宝绘堂记》中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 虽微物足以为病, 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王世德指出苏轼这一思想来源于老庄,继承和发展了老庄有关的美学思想,同时与康德的审美无利害相似,即审美快感既不在私人的欲念或利害计较,而只能在一切人所共有的非物质利害欲念的审美态度上[12]。因此,通过审美的眼光审视手中的仇池石,获得的只是单纯的美感和愉悦的精神享受,而这种美感与快感又是共同构成人生乐土境界的基本要素。陆庆祥以存在哲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他认为无论是寓物还是留物,只是人生持存的方式,“寓意于物”只是处物不伤物,外化而内不化,因此物没有被主体占有,是自由的,主体的心也是自由的,得到了保护,人与世界和谐融洽,但“留意于物”却使物与我双重异化,人占有物而迷失了自己,物被占有而难以彰显本来形象[13]。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审美角度还是存在哲学角度来分析,苏轼收藏仇池石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追求诗意、和谐、完美、融洽的人生境界,构建自由、无碍、闲适的人生乐园。
(二)石头命名:向往理想世界
仇池的名称具有浓浓的乐园色彩。序中提到杜甫的诗句“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秦州杂诗二十首·第十四》。这组组诗写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举家逃亡的途中,在社会动乱、命如草芥的年代,非但无法实现致君尧舜上的理想,连保全性命也成为奢侈。杜甫无疑借此表达对安宁祥乐生活的向往,对远离纷争、隔离生死的桃源世界的渴望。
艾诺朗指出,他(杜甫)提及了“桃花源”,和文学世界中这个著名的乌托邦不同。因为仇池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并非出于虚构[1]178。很明显他以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为标准进行划分,并结合现实地理状况得出结论。仇池山,又名百顷、仇夷、仇维、瞿堆,位于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城以南约六十公里处,因其上有池而得名,传说仇池穴就是伏羲诞生的地方,因此仇池山带上神话色彩。山上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环境封闭,人们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闲适生活,颇有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桃源气息。艾朗诺的论断有一定道理,但他所以为的现实的仇池实际上也是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因此,仇池在此诗中仍然具有虚构想象的成分。
其实,此处的仇池不是乌托邦,而是偏向于乐园。欧丽娟认为虽然乐园和乌托邦都具有超越现实、愉悦舒适的特点,且都是出于想象虚拟构建的产物,但乐园更倾向于个人主义生命的实践,所构建的理想世界突出个人性适意自足的一面,而乌托邦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提升和弥补,具有倾向于群体主义的社会实践的性质,所建立的理想世界彰显群体性安和乐利的一面[8]12。欧丽娟不仅区分了乌托邦与乐园,还指出乐园个人性的主要特点,反观杜甫这首诗,后两句为“神鱼人不见,福地语传真”,杜甫结合伏羲神话与仇池实地,以“福地”代指仇池,表达了对仇池的无限向往。此处杜甫并没有表达“安得广厦千万间”般的博爱精神,他心中的仇池只是个人精神的避难所和灵魂栖息的圣地。苏轼引杜甫此句正是表达同样的愿望,即寻求个人理想中的乐园。
(三)石头文化:寻觅人间福地
仇池山与宗教文化的联系也为它带上乐园色彩。据赵逵夫先生考证《西和县志》与《列仙传》中仇生和仇维的分歧,他认为《西和县志》是依据传为汉代刘向所编的《列仙传》记述的,因为当时编者对其中有些文字不能作出较明确的说解,故未征引原文,也未注明材料出处。因此,仇生与仇维本指同一个人。仇池山本名“常羊山”,后来演变为仇池山,也与仇维的传说有关,仇生是战国至汉初的仙人。[14]可见仇池山与道教的密切联系。另外,仇池山在道教中有“福地”之称,更强化了它作为乐园美丽愉悦、摆脱生死的特质。
(四)石头寓意:摆脱精神苦难
从整首《双石》诗的结构框架来看,首句以判断的语气明确得出现实不如梦境的结论,中间六句则对现实的仇池石进行描绘,而在末尾处又以“老人直欲住仇池”作结,与首句遥相呼应。整首诗以首尾两句奠定思想的框架,中间简单描绘,但重点表达对梦境的向往,即对仇池世界的向往。对仇池石的描绘只是作为抒发主题思想的陪衬和辅助,而仇池石的意义也并非停留在仅供赏玩的物件的地位,他成为诗人精神的避难所。“小仇池”和“小洞天”总在提醒他,只要依凭精神上的自律,只要对当下生活保持审慎而从容的疏离感,摆脱苦难就是有可能的。[1]222在晚年被贬的政治生涯中,仇池石已经成为苏轼相依为命的精神伴侣,当然,他不可能真正的进入仇池的极乐世界,但他通过想象在仇池的世界中找到自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日益渗透在他的心中,使仇池石成为自己精神的寄托。
四、结语
苏轼除了是一代文豪,还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慧眼如炬的收藏家,但苏轼收藏并非盲目之举,他的藏品与他的内心世界遥相呼应。因此,所藏之物已成为他个人内在精神的寄托和心迹的外化表现。《双石》中描绘的仇池正是苏轼向往的乐园,仇池石也就成为乐园的寄托。苏轼对乐园的期盼不仅是对其坎坷一生反思的结果,更是对未来自由无碍生活的憧憬。
通过对《双石》词语、意象、序文等全面系统地解读,厘清了苏轼对乐园向往的复杂原因,从而挖掘苏轼心中深厚的乐园思想。因此,对《双石》中苏轼乐园意识的探析,使得我们将视野缩小,聚焦于乐园这一焦点,拥有一个新的角度来切入苏轼爱石的研究,而且能更深入地了解爱石的内在实质,即外在之物与内在之心的契合,而不是外观美丽或经济价值等原因。当然,这也更有利于了解苏轼的哲学观念以及观照整个北宋的审美风尚和石文化,了解时代风气。
注 释:
①本文所选苏轼诗句依据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所选文句依据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后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