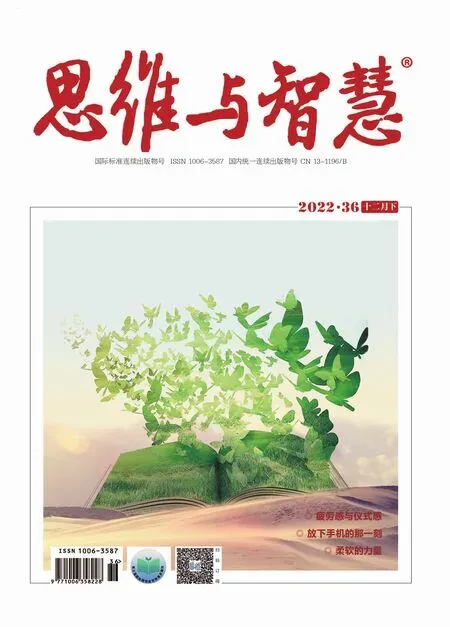秋风起
◎ 沈艺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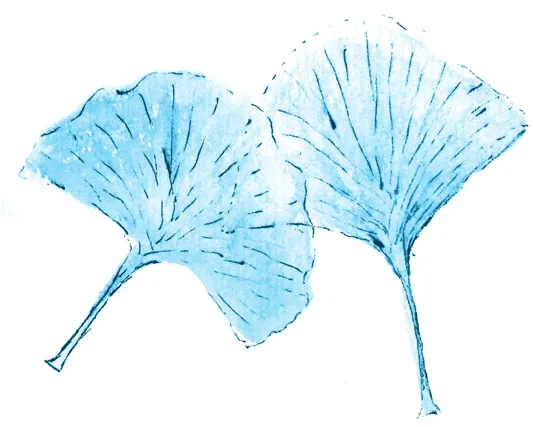
蓬勃的生命,在秋天枯黄了。秋风扫落叶又一次在院子里重演了。一年一年扫落叶,我有点烦了。两个女儿的看法是:别管,反正你没有秋风扫得快。是啊,我在捡拾秋风的杰作,但不捡拾,院子就凌乱得如荒芜的宅子。不赞同她们的看法,也无心和她们争辩,只有自己不停地捡拾,抢在秋风的前头得来片刻的纯净。
风萧索,叶子沙沙。在我的印象里,春暖花开并不多,也许是我在这个季节里感觉失灵了吧,我只记得秋风雪月。
少时喜欢在秋野里玩。农田静寂,偶尔有人走过,那是在田地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零星果实。天地干裂,人踩在上面,尘土很快缠住了人们的裤脚。
成年后的我喜欢站在秋风中回忆,在回忆的幽径中常常会不小心碰触一些看似卑微的荒蒿、枯树、败叶,还有它们脆弱的低吟。叶子蓬勃时的生命无人敢比,衰败后的叶子也是无人敢比。人走在上面,如同踩在生命的脉络上,无论是平凡还是辉煌,最终都会生长起一种莫名的忧伤,谁敢和自然抗衡?
站在秋风中,回忆的镜头被拉得很远。在一片即将丰收的葵花地里,我的小伙伴向看园子的人说了好多好话,想得到那一株还长满花的葵花头,想把那束明媚的花留住。她没有要结满果实成熟的向日葵,而是要了那株花,用她的话说:过不了几天就留不住这花了。话中满是悲秋之意和对白驹过隙的感慨。
也许从童年起,我们就开始和时间赛跑。但我们终究跑不过时间,我们不能走在时间的前面。转瞬间,老了的是我们,时间依旧笑吟吟地前行着。
回忆里的马莲河畔,是我们的乐园。在这儿没有贫富巨差感,只有平等。离开了家,离开了饭桌,谁知道谁家今天吃的是鸡鸭鱼肉还是玉米糊糊就咸菜?我们天南地北地乱侃,最多的是想象。想象着长大后要做什么、到哪儿去。那时的想象是纯净的,也是酸涩的。果腹的是一把玉米榛子,掩体的是妈妈缝补的衣服,而想象却能走到那久远的天边,浪迹欧式花园,看到哥特式屋顶上的鸽子。
其实,我们真正清晰认识的风景是,一条向东流淌的马莲河、马莲河上寂寞的大桥,以及桥边那些寂寞的杨槐树。它们填充了我们童年的真实。在马莲河边长大的我们,忙于奔波、忙于挥霍。我们挥霍着长长的时间,即使时间里有各自的内容与心绪,我们也将其挥霍成回望时的那一瞬间。
人生没有退路,没有谁为我们打开新的大门,就如这条马莲河,它只有一路向东,不会流回到最初的源头。人也不可能像草一样在秋天枯黄,在春天重新再活一回。属于我们的,只有在奔跑之时的短暂留意。留意时光的背后大地的秘密,抢拾这一路的秘密,或许能找到生活静若处子的真谛。
秋风再次旋起,与我擦肩而过。我突然担心,它是否会用枝丫将我狠狠抽打?
(王传生摘自《解放日报》2022年9月12日/图 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