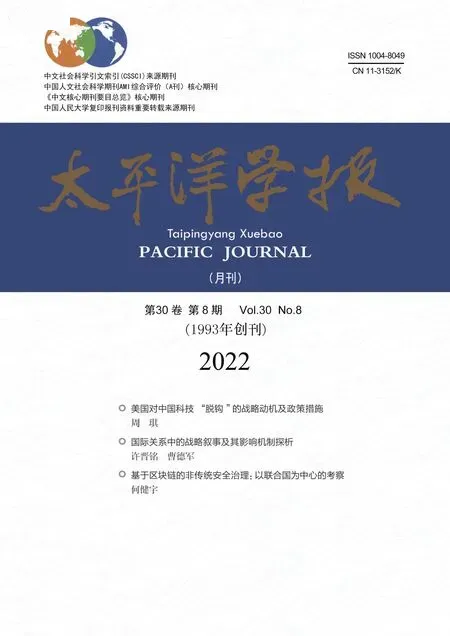“冷内战”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加速态势分析
潘亚玲
(1.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地理安全危机、经济安全危机和制度安全危机相继爆发,美国政治文化转型态势日渐明显。①相关讨论可参见:Pan Yal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Impact on Foreign Strategy,London:Routledge,2022;潘亚玲著:《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及执政,更是推动美国政治文化转型进入关键时期。特朗普总统刷新了美国历史上的多项纪录,例如: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过两次的总统,第一位拒绝参加继任者就职典礼的总统,第一位坚持使用推特(Twitter)而非传统媒体发布信息的总统,第一位整个任期内支持率从未超过50%的总统,第一位没有任何政府或军事经验的总统等。总结起来,特朗普总统与包括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内的所有其他美国总统的根本差异在于:其他总统在执政后都会放弃竞选时期的分裂性言论,转而追求全美团结;而特朗普从其进入白宫的第一天直到离开白宫的最后一天,都在尽最大能力地使美国“四分五裂”。相比之下,拜登的当选和执政对美国显得意义重大。①Paul Butler,“Why Biden as President is so Important at This Time,”The Frontier Post,November 16,2020.但是,拜登能否有效扭转特朗普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使美国政治文化重回正轨?答案极可能是否定的或至少是高度不确定的。原因在于,自21世纪初启动的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其核心特征是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从“共识政治”向“对抗政治”的转变,②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政治文化始终在“共识政治”与“对抗政治”之间摇摆。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是美国建国后对抗政治首次达致极端的表现,内战后重建至1931—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很大程度上也为对抗政治所主导。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为美国带来了以共识政治为主导的较长时期。以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等为代表的美国“共识史学家”更多是将罗斯福新政后的特殊经历当作整个美国史的基本特征。相关讨论可参见:Bernard Sternsher,Consensus,Conflict,and American Historians,Bloomington:Indianan University Press,1975;David S.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而由特朗普持续撕裂而来的“冷内战”(cold civil war)或“国内冷战”(civil cold war),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对抗政治”在整个美国社会的扩散,从而加速了美国政治文化转型进程。尽管拜登执政后的确使“冷内战”有所降温,但仍严重缺乏有效应对“冷内战”——特别是其核心要素即政党对立、族裔对立和城乡对立——的有效方案。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仍是个长期和缓慢的进程,仍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一、“冷内战”的意涵
面对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高度分裂,“冷内战”概念于2017年初被正式提出。③Angelo M.Codevilla,“The Cold Civil War:Statecraft in a Divided Country,”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Vol.17,No.2,2017.需要强调的是,“冷内战”概念并非只是特朗普当选后才出现的,但此前更多使用“野蛮战争”(uncivil war)描述类似事态发展。④尽管“冷内战”与“野蛮战争”很大程度上都基于美国高度分裂的客观事实,但“冷内战”一词更强调客观事态,而“野蛮战争”则重点强调手段“不文明”。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厘清“野蛮战争”概念的指点。事实上,每当美国国内陷入高度分裂时,总有政客、学者、评论员提醒美国人内战爆发的风险。例如,有学者对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辞职前60年里美国“野蛮战争”的历史演变作了考察。作者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围绕新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产生严重分歧,越南战争导致的抗议活动规模和烈度都在增加,城市内的种族暴力也持续升级;在1967—1968年间,所有上述力量更是实现了大联合,使美国社会的分裂程度甚至超过内战时期,“野蛮战争”开始了。⑤Mark Hamilton Lytle,America’s Uncivil Wars:The Sixties Era from Elvis to the Fall of Richard Nix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特朗普带来了重大的威权统治危险,政党极化大幅加剧并朝向整个美国社会蔓延。当前,尽管特朗普已经下台,但“冷内战”已然成为讨论美国政治发展的流行术语,有评论人员甚至认为,到2024或2025年,美国将可能陷入第二场内战。⑥Shelt Garner,“A Second American Civil War&The Congressional Certification Crisis of 2024,”The Trumplandia Report,April 1,2021;Shelt Garner,“Imagining Life in America During the Second Civil War,”The Trumplandia Report,April 7,2021,https://www.trumplandiareport.com/category/cold-civil-war/,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3日。
尽管对“冷内战”的具体内涵仍存在争议,但它总体上表现为美国正日益为相互敌对的两种宪政、两种文化和两种生活方式所撕裂。拜登在其就职演讲中就强调,“我们必须结束这场红蓝对立、城乡对立、保守自由对立的野蛮战争”。更为抽象地,美国现在正面临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al)和政权政治(regime politics)的斗争。前者是手段之争,而后者则是原则之争。也就是说,常规政治在目的或原则方面已取得一致,政治竞争发生在宪政框架内,而政权政治关注的是谁出于何种目的或基于何种原则来进行统治。⑦Charles R.Kesler,“America’s Cold Civil War,”Imprimis,Vol.47,No.10,2018.除认可“冷内战”是场路线斗争之外,并不存在更多共识,相关争论主要可分为三种立场。
第一,“冷内战”一开始被用于描述所谓“进步派”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的攻击。①John J.Tierney,Jr.,“The Civil Cold War:What’s it All About?”IWP,November 27,2018,https://www.iwp.edu/articles/2018/11/27/the-civil-cold-war-whats-it-all-about/,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3日。这一立场在2018年前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克莱蒙特书评》在2017年春季号推出有关“冷内战”的系列文章,其目标直指自由主义左派。在其开篇之作中强调,2016年大选及其后续发展,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与其他阶层间的差异甚至敌意——这种敌意在过去25年里呈指数级增长。文章认为,问题出在左派和民主党:政府机器几乎一致性地赞同民主党,使美国变成了一个“党派国家”(partisan state),其目的根本上是削弱被统治者影响政治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特朗普当选的愤怒,迅速兴起的草根抵抗运动的实际目标是推翻2016年大选结果,否认特朗普的当选。因此,这是一场针对大多数美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冷内战”。②Angelo M.Codevilla,“The Cold Civil War:Statecraft in a Divided Country,”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Vol.17,No.2,2017.
根据这一派的观点,在这场覆盖政府、国会、法院、大学、媒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冷内战”中,关于美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全面交锋:保守派尊崇宪法,认为必须在社会广泛接受的情况才能修改宪法;而进步派则强调宪法是社会变革的引擎,并视其为自由主义议程的空白支票。③Robert Knight,“Keeping the Cold Civil War from Getting Hot,”The Washington Times,December 2,2018.由此,激进左派以变革为名持续对反对者使用暴力和审查,媒体也“并非真正的媒体,不过是在媒体工作的民主党人”。④Victor Garcia,“Rush Limbaugh:America is in the Middle of a‘Cold Civil War’,”Fox News,September 27,2019.因此,这场“冷内战”更多是为了保卫华盛顿建制派,推翻特朗普政府。对他们来说,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加上几乎半个国家被剥夺言论自由——保守派人士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被挤出社交媒体,其后果不言而喻。⑤Paul Mirengoff,“A Cold Civil War or a Hot One?”Power-Line,June 13,2020.他们认为,正是特朗普大胆暴露了长期存在且持续发酵的分歧,不仅刺激了激进左派的强烈抗议,也强化了其支持者的信念:“我们非常愿意做出谨慎的选择,在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政治新手唐纳德·特朗普,而不是变动的宪法和无限政府的化身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因为特朗普具有常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官僚现状不屈服的态度”。⑥Ryan Williams,“As America Resolves Its Cold Civil War,We Must Ensure It Doesn’t Get Hot,”The Federalist,June 7,2018.
第二,随着特朗普对“政治不正确”(political incorrectness)的 无底 线 操 作,进入2018年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越来越相信,特朗普才是“冷内战”的罪魁祸首;而这某种程度上恰好印证了保守派的攻击,从而使两派对抗升级。⑦Greg Sargent,An Uncivil War:Taking Back Our Democracy in an Age of Trumpian Disinformation and Thunderdome Politic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8.“冷内战”概念被提出后迅速得到普及,参与讨论的既有保守派人士、也有自由派人士,既有政治学家、也有历史学家、更有国家安全专家。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这场“冷内战”中,尽管斗争双方相互仇视,但保守派和共和党人更具侵略性,更愿意从事反民主甚至暴力攻击。⑧Perry Bacon,Jr.,“In America’s‘Uncivil War,’Republicans Are The Aggressors,”Five Thirty Eight,February 8,2021.而特朗普则大肆玩弄政治,将“政治不正确”扭曲为“政治正确”:在面对大量批评时,他往往将自身塑造为能够直面世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真相揭露者,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的“政治不正确”的候选人和总统,从而公然将白人种族主义和偏见堂而皇之地置于社交媒体的前台,并美其名曰“真相揭露”。⑨Jessica Gantt Shafer,“Donald Trump’s‘Political Incorrectness’:Neoliberalism as Frontstage Racism on Social Media,”Social Media+Society,Vol.3,No.3,2017,pp.1-10.正是这一政治手法,推动特朗普自身及其支持者日益迈向极端,直至2021年1月6日的骚乱发生。这场骚乱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广泛的右翼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是自由主义左派的报复;二者结合更是使美国原本脆弱的公民文化被进一步摧毁。而有关“团结和治愈”的言论更多是掩盖了美国易于陷入自我崩溃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正处于第二次内战边缘。①Harrison Pitt,“Will America’s‘Cold Civil War’Turn Hot?”Spectator,March 5,2021.
尽管如此,依然有评论认为,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煽动“冷内战”的揭露并不彻底,对特朗普煽动“冷内战”的批判过于抽象。他们指出,特朗普对“冷内战”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有早于常人的更加深入的认识,而且还想方设法地煽动甚至试图引爆“冷内战”,这在美国历任总统中都是绝无仅有的。②Douglas Ernst,“CNN’s Carl Bernstein:America’s‘Cold Civil War’Almost‘to the Point of Ignition’due to Trump,”The Washington Times,July 8,2019,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9/jul/8/carl-bernstein-americas-cold-civil-war-almost-to-t/,访问时间:2022年2月24日。曾担任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顾问的史蒂夫·施密特(Steve Schmidt)认为,特朗普是在“煽动冷内战”:他的集会充满了威胁,他给记者贴上了人民公敌的标签。③Michael Martin,“Former Top GOP Adviser:Trump has Inflamed‘Cold Civil War’in America,”Metro,October 25,2018.也有人认为,美国政治发展的整体趋势不是平息政治分歧,而是强加对抗甚至引爆分歧。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掌握并利用了美国内部有关身份、种族、性别、宗教及阶层等的分歧,打造了一个极其忠诚的联盟,尽管该联盟代表着少数群体,但却拥有重要的投票权。④James Joyner,“Cold Civil War or Civil Cold War?”Outside the Beltway,October 6,2018,https://www.outsidethebeltway.com/cold-civil-war-or-civil-cold-war/,访问时间:2022年2月24日。更多的人相对具体地讨论了特朗普的煽动策略,如特朗普有关非法移民的煽动性言论将美国带入“冷内战”⑤Tim Hains,“Princeton Professor Eddie Glaude:Trump’s Anti-Immigration Rhetoric Has Led America into‘Cold Civil War’,”Real Clear Politics,August 4,2019,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19/08/04/eddie_glaude_trumps_immigration_rhetoric_has_led_american_in_a_cold_civil_war.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24日。,或者强调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设法阻止更多人参与投票⑥David A.Love,“A Cold Civil War is Being Waged by Republicans,”Al-Jazeera,March 31,2021.,等等。
第三,始终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居间立场,认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均对“冷内战”的发展负有责任。例如,有观察人士认为,左派和右派都有其暴徒,都会制造恐怖;两者都是由政治阶层内部的派系策划的。⑦Joshua J.Whitfield,“Is America on the Brink of Civil War?More Like a Coming Reign of Terror,”The Dallas Morning News,December 8,2019.也有人指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每次冲突或对抗都不是最后一击,而是达致其理想目标的中间步骤。特朗普的支持者对其颠覆华盛顿的好斗方式大加赞扬,认为这是对精英政治的理所当然的反抗。他们担忧的是,如此极端的两极分化会导致政府无法正常运转,从而形成了对规范的系统性抛弃。⑧同④。
一些美国人真正担忧的是,“冷内战”会变“热”,上升成为真正的“内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公开警告,美国正处于一场“冷内战”之中,这场战争可能由于特朗普总统而升级。⑨同②。在2020年大选前的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56%)的受访者相信,无论哪位候选人获胜,暴力冲突的风险都会上升。⑩Ledyard King,“‘The Country’s Lost Its Mind’:Polls Warning of Civil War,Violence Shows Deep Partisan Chasm over Election,”USA Today,October 7,2020.而2021年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美国人对政治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令人担忧,对“冷内战”的到来高度恐惧。媒体记者、政府和商界领导人在知道信息错误的情况下仍刻意误导公众,受访者对此认可比例分别达到59%、57%和56%。⑪Jennifer Harper,“A‘Cold Civil War’is Brewing in America,”The Washington Times,January 21,2021.拜登执政后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公众对政府、商界和媒体的信任度分别下降3个、5个和6个百分点。⑫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2,Edelman,January 2022,p.24,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edelman-trust-barometer-2022-report/,访问时间:2022年2月24日。
“冷内战”话题变热,很大程度上是在警醒美国各界,要避免重蹈内战覆辙,因为内战是美国历史上从“共识政治”到“对抗政治”的政治文化转型的最极端案例。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事实上正因“冷内战”的发展而加速,最为明显地体现为政党对立、族裔对立和城乡对立等三个方面。
二、政党对立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制度僵化
自冷战结束后,居于政治极化中心的政党极化便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然渗透到社会层面,进而使极化和对立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换句话说,美国政党极化不仅体现为精英极化,也体现为大众极化或社会极化。①Adam M.Enders,“Issues versus Affect:How Do Elite and Mass Polarization Compare?”Journal of Politics,Vol.83,No.3,2021,pp.1872-1877.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草根反对政治发展明显成为两党体制内极化与对立的社会性体现,无论是奥巴马(Barack Obama)还是特朗普都遭到另一政党的草根团体的强大抵抗。因此,拜登总统所继承的政治极化,已远超以往,这使得短期内有效扭转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方向变得希望渺茫,因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僵化极大地限制了政治文化转型的灵活性。
2.1 政党意识形态对抗和相互仇恨持续上升,并产生了长远的选举政治后果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党的意识形态对立日益尖锐,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达到新的高潮。特朗普总统上任后,皮尤研究中心围绕民主共和两党相互间的消极认知启动了一项持续调查;它以冷温度得分衡量,得分越高意味着对另一政党的认知越消极。结果显示,两党的相互认知日趋“冰冷”:2016年3月,民主党人对共和党人的冷温度得分为61,到2019年9月已经达到79分;而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冷温度得分同期也从69分增至83分。②“Partisan Antipathy:More Intense,More Personal,”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10,2019,p.6.两党的相互消极认知甚至仇视度持续增长,并努力通过“非人化”(dehumanize)手段抹黑对方。例如,在1980年时,两党的相互仇视度均低于15%,到1996年时均达到20%的水平,到2012年更是达到接近50%的水平。③Marc Hetherington and Jonathan Weiler,Prius or Pickup?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8,pp.125-126.拜登总统上台并未重大缓解美国的政党对立:97%的民主党人和87%的共和党人高度支持自己的党;93%的民主党人和96%的共和党人讨厌对方党派。这样,高达60%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过于极端,也就毫不奇怪。④“Biden Viewed Positively on Many Issues,but Public is Less Confident He Can Unify Country,”Pew Research Center,March 11,2020.
政党极化乃至对立产生了长远的选举政治后果,最为明显地体现为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的大幅下降。所谓分裂投票是指,在总统大选年,一个选民在总统选举和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分别投票给不同的政党候选人。⑤有关分裂投票的讨论可参见:Barry C.Burden and David C.Kimball,Why Americans Split Their Tickets:Campaigns,Competition,and Divided Governmen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Kenneth Mulligan,“Partisan Ambivalence,Split-Ticket Voting,and Divided Government,”Political Psychology,Vol.32,No.3,2011,pp.505-530;V.V.Chari,Larry E.Jones,and Ramon Marimon,“The Economics of Split-Ticket Voting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7,No.5,1997,pp.957-976;Mark A.Zupan,“An Economic Explanation for the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Political Ticket Splitting,”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4,No.2,1991,pp.343-369。分裂选票意味着选民层次的两党制衡,大选中的分裂选票比例越低,说明政党极化水平越高。在2020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78%的受访者表示将在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投同一个党的票,其中投民主党的占43%,共和党的35%。⑥“Large Shares of Voters Plan to Vote a Straight Party Ticket for President,Senate and House,”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21,2020.选举结果印证了这一调查,最终仅有16个选区出现分裂投票,占435个国会选区的3.68%。这是自192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大选中的分裂投票更是显著下降,并在长达20年时间里处于20%以下。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类似情况仅发生在1952年以前。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大选年中总统得票与同一政党众议员得票之间的正相关性正在持续上升。在2000年时,在特定选区,来自同一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众议员候选人同时获胜的概率仅为30%;而到2020年,这一概率上升到85%。①Geoffrey Skelley,“Why Only 16 Districts Voted For A Republican And A Democrat In 2020,”Five Thirty Eight,February 24,2021;Nathaniel Rakich and Ryan Best,“There Wasn’t That Much Split-Ticket Voting in 2020,”Five Thirty Eight,December 2,2020.
2.2 政党极化正逐渐渗透到整个社会层面,使大众极化或社会极化也上升到新的水平
美国政党极化不仅为两党所承认,也为整个美国社会所感知。事实上,两党都注意到其相互分裂,有85%的共和党人和78%的民主党人认为,两党分裂正在持续;两党也都认为,党际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有73%的人——77%的共和党人和72%的民主党人——认为,两党不仅无法就规划和政策达成一致,甚至连基本事实也无法达成共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两党都“过于极端”;两党支持者都对另一党持敌对态度,大多数民主党人期待能出现一个寻求共识的总统候选人。②“Partisan Antipathy:More Intense,More Personal,”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10,2019,p.7.
到2020年总统大选时,两党及其支持者的情感极化和意识形态极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③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一向认为情感极化与意识形态极化是对立的,但二者事实上仍是密切相关的。相关讨论可参见:Steven W.Webster and Alan I.Abramowitz,“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S.Electorate,”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Vol.45,No.4,2017,pp.621-647;Yphtach Lelkes,“Affective Polarization and Ideological Sorting:A Reciprocal,Albeit Weak,Relationship,”Forum,Vol.16,No.1,2018,pp.67-79;等。例如,21%的拜登支持者和23%的特朗普支持者强烈批评对方阵营的候选人和选民;只有18%的拜登支持者和22%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他们共享美国的价值观和目标;80%的拜登支持者和77%的特朗普支持者都认为,他们在美国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拜登的支持者在大选前表现得更加激进:如果拜登竞选失败,他们不仅比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加愤怒,而且也会比2016年时希拉里的支持者更加愤怒。而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认为,如果是对方支持的候选人获胜,对美国而言都将是长期伤害;有89%的特朗普支持者和90%的拜登支持者认同这一观点。④“Amid Campaign Turmoil,Biden Holds Wide Leads on Coronavirus,Unifying the Country,”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9,2020.另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民主共和两党的相互认知高度对立。例如,有81%的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已经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而民主党内部持这一观点的人只有12%。类似地,有78%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已经被种族主义者所主导;而共和党内部只有9%的人认同这一观点。⑤“Dueling Realities:Amid Multiple Crises,Trump and Biden Supporters See Different Priorities and Futures for the Nation,”PRRI,October 19,2020.
2.3 自2008年以来,草根反对运动正推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混合性政党极化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政治出现一个奇特现象,即草根反对运动日益成为在野党反对执政党的急先锋。迄今为止的草根反对运动主要有四个共同特征:其一,绝大多数草根运动都源于在野党的基层人士对执政党或执政总统的反对。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茶党运动,还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抵抗运动,抑或拜登上台后围绕“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展开的带有某种制度色彩的全国性抗议运动,都是在总统就职后短时期内迅速兴起的,并以反对在任总统为政治追求。其二,绝大多数草根反对运动都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特质,并非由任何政党自上而下地组织。例如,茶党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纳税人对救援行动的反对。⑥Ronald P.Formisano,The Tea Party:A Brief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p.1.而以“不可分割”(Indivisible)网络为代表的抵抗运动,其原始目的是鼓励并为地方性集体行动提供建议。其三,草根反对运动的地理覆盖范围相当广泛乃至全国性的。⑦Theda Skocpol and Caroline Tervo,“How Indivisible’s National Advocates and Grassroots Volunteers Have Pulled Apart—and What Could Happen Instead,”The American Prospect,February 4,2021.例如,“不可分割”网络配置了全美互动地图,所有地方性的抵抗团体均可注册。高峰时期,有多达6 000余个团体在“不可分割”网络上注册,实际开展活动的也有2 000~3 000个;相比之下,茶党运动在高峰时期的活跃团体仅有1 000多个。而围绕“批判种族理论”的抗议活动已波及全美28州,35个州议会提出相关立法提案。其四,草根反对运动的影响力均在其针对对象下台后甚至执政后期就快速衰退。
民主共和两党的草根反对运动存在重大差异,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潜在影响。
其一,共和党一侧的草根运动能够迅速进入体制内,而民主党的草根运动则更多维持体制外活动。茶党运动在获得最初影响力之后,不仅帮助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赢得63个国会众议院席位,自身也赢得了10余个席位。①Tom Cohen,“5 Years Later,Here’s How the Tea Party Changed Politics,”CNN,February 28,2014.茶党运动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原因在于,它主要采取传统的政治游说和国会的不记名投票方式等手段。②Michael A.Bailey,Jonathan Mummolo,and Hans Noel,“Tea Party Influence:A Story of Activists and Elites,”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Vol.40,No.5,2012,pp.769-804.而围绕“批判种族理论”的抵抗运动本身就带来明显的制度化色彩,不仅大量州议会提出立法倡议,就连国会也提出了10余项相关提案。相比之下,民主党一侧的抵抗运动具有更加明显的自下而上性质,成员自愿性更高,且地理分布更加均衡。因此,抵抗运动不仅可为民主党更依赖挨家挨户拉票的传统模式提供帮助——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肆蔓延的背景下,还可帮助民主党逐步恢复已趋萎缩的基层组织。③Theda Skocpol and Caroline Tervo,“How Indivisible’s National Advocates and Grassroots Volunteers Have Pulled Apart—and What Could Happen Instead,”The American Prospect,February 4,2021.但问题在于,抵抗运动更强的自下而上特征,使其始终未能进入民主党的政党体制之内,这对其自身及民主党的未来发展有着重大制约。
其二,共和党的草根运动更加全面和复杂,而民主党的草根运动则相对单一。在共和党一侧,在茶党之外还有重要的政治资本支撑,即科赫兄弟——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所组建的科赫政治网络。它不只是个政治捐献网络——拥有四五百名保守主义的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更是个政治行动网络——为政策研究、选举活动、基层运动等提供资金及其他支持。④Theda Skocpol,“The Elite and Popular Roots of Contemporary Republican Extremism,”in Theda Skocpol and Caroline Tervo,eds.,Upending American Politics:Polarizing Parties,Ideological Elites,and Citizen Activists from the Tea Party to the Anti-Trump Resist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p.3-28.而民主党一侧的抵抗运动,尽管也曾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相对单一:其活动中心从未远离首都华盛顿,其成员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年女性为主,其议程更多集中于反对特朗普本身。
其三,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草根运动很大程度上推动共和党朝向更加保守的极端方向发展,而民主党并未受拥有较为激进的抵抗运动的重大影响,其选举胜利更多来自党内温和派,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拜登在2020年初选中的获胜。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去10余年里,草根运动更多推动美国政治文化的光谱右移,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力便是例证。如果来自共和党的草根反对运动在拜登政府时期再度蓬勃发展的话,美国政治文化的光谱极可能继续右移,因为在共和党变得更加极端的同时,民主党却仍在原地踏步。
三、族裔对立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社会分化
特朗普对种族主义的刺激,被认为推动“冷内战”升温、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加速的重要原因。⑤牛霞飞、郑易平:“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危机:表现、原因及发展”,《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2期,第36页。的确,自特朗普于2015年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后,美国社会内部的种族主义情绪便持续高涨。例如,在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的一年内,美国网络上共计出现260万条含有种族主义言辞的推特,其阅读量达到100亿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包括“特朗普”“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白人”等。①ADL,Anti-Semitic Targeting of Journalists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A Report from ADL’s Task Force on Harassment and Journalism,ADL Report,October 19,2019,pp.5-8.又如,有学者对特朗普2016年竞选集会对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刺激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举行过与没有举行过竞选集会的县相比,前者的仇恨犯罪水平在随后一年增长了226%。②Aris Folley,“Hate Crimes Rose by 226 Percent in Counties Where Trump Hosted Campaign Rallies in 2016:Study,”The Hill,March 23,2019.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不少人认为,“冷内战”很大程度上就是种族主义回潮、族裔对立和社会分化。尽管有代际更替和白人主导的潜在抵消作用,缓解族裔对立仍相当困难,特别是在美国极可能在人口结构多样化背景下重归种族主义的背景下。
3.1 由身份政治而来,少数族裔支持民主党、白人支持共和党的族裔对立格局正在固化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族裔的政党认同往往长期稳定,并体现出“少数族裔整体支持民主党、白人整体支持共和党”的态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比1994年和2017年不同族裔的政党认同发现,认同共和党的白人选民总体保持不变(51%),同时认同民主党的略有增长(从39%增至43%);同期,认同共和党的非洲裔从11%降至8%,而认同民主党的从81%增至84%;认同共和党的拉丁裔也从29%降至28%,认同民主党的从57%增至63%;亚裔也总体认同民主党,从53%增至65%,而认同共和党的下降最为明显(从33%降至27%)。③“Wide Gender Gap,Growing Educational Divide in Voters’Party Identification:College Graduates Increasingly Align with Democratic Party,”Pew Research Center,March 20,2018.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对美国选举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非常不利于共和党。据统计,在移民聚居县中,移民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就会下降0.58个百分点;在人口超过5万且在1980—2008年间移民人口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的县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其中62%的县得票率明显下降;在移民人口增长超过4个百分点的县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其中74%的县得票率明显下降;在移民人口增长超过6个百分点的县中,共和党候选人在其中83%的县得票率明显下降。④James G.Gimpel,“Immigration,Political Realignment,and the Demise of Republican Political Prospects,”CIS,February 2010.这一族裔分裂或族裔对立格局在新近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同样明显。在2012年、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支持民主党的白人不超过45%,而非洲裔、拉丁裔、亚裔及其他族裔均整体支持民主党(参见表1)。

表1 各族裔选民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情况(2012—2020年大选)
尽管族裔动员策略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运用较少,但出于对2016年大选的记忆及由此而来的自1908年以来的最高警惕性⑤Muzamil Wasti,“America amid the Tumultuou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Paradigm Shift,November 3,2020.,支持种族主义和抵制种族主义两个阵营的选民都被动员了起来。与2016年相比,美国参加2020年大选投票的选民数量从1.39亿增至约1.6亿,增长12%;同时也创下了自1900年以来的最高投票率纪录,超过66%。虽然所有族裔的投票率相比2016年都有增长,但不同族裔增幅明显不同:亚裔投票率增长最多,达到39%,其次是拉丁裔(31%),其他族裔(26%),非洲裔(14%),大学本科及以上白人(14%),高中及以下白人(11%);由此,相比2016年大选,白人选民在全美选民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非洲裔下降了0.1个百分点,而拉丁裔增长最多(1.2%),亚裔增长0.8个百分点。正是这一选民结构变化,使得拜登在所获少数族裔选票相比希拉里略有下降的情况下,仍赢得了2020年大选。
3.2 在族裔对立持续加剧的同时,代际更替和白人主导也可能形成某种抵消
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代际更替有着深远的政治后果,特别是对那些采纳选举政治的国家来说。由于不同代际人口群体的出生和成长背景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其政治信仰也可能完全不同;研究表明,不同代际人口群体的意识形态差异更多基于该群体的独特成长经历,与其年龄本身关系不大,尽管随着年龄增长其政治态度可能发生某种变化。①Richard Braungart and Margaet Braungart,“Life Cours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2,No.1,1986,pp.205-231;Ronald Inglehart,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June Edmunds and Bryan S.Turner,Generations,Culture and Society,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因此,静态的族裔对立逻辑极可能因为动态的代际更替而被抵消。对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对比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假设。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代际分类②皮尤研究中心识别出当前美国社会5个最主要的代际群体;每个代际的时间跨度大致相等,即在16—19年间。这5个代际群体具体包括: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1928—1945年生),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1946—1964年出生),X一代(X Generation,1965—1980年出生),千禧年一代(Millennium Generation,1981—1996年出生),及Z一代(Z Generation,1997—2012年出生)。“The Whys and Hows of Generations Research,”Pew Research Center,September 3,2015;Corey Seemiller and Meghan Grace,Generation Z Goes to College,San Francisco:Wiley,2016.中最年轻的一代即Z一代的政治倾向与此前历代均存在重大差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Z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更高:2016年大选时初次投票的选民共计1 370万,而包含Z一代(700万)在内的新增选民共计约1 090万;2020年大选中初次投票的选民共计2 170万,而包括Z一代(1700万)在内的新增选民共计约1 900万。在两次大选中,新增选民与实际初次投票的选民数量差距均达到270万以上,因此,即使其他代际有较多选民被动员出来,Z一代的初次投票率也必然相对较高。事实上,Z一代选民的投票率在2020年相比2016年增长了近300%。③Yair Ghitza and Jonathan Robinson,“What Happened in 2020,”Catalist,May 2021.另一方面,Z一代远比更年长代际选民更加倾向自由主义: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希拉里的初次投票选民比支持特朗普的高19个百分点;而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拜登的是支持特朗普的2倍(64∶32)。此外,2020年大选时Z一代人口最高年龄为23岁,而18—24岁年龄段选民中,支持拜登的比支持特朗普的高出34个百分点。④“Exit Polls,2016 President Election,”CNN,November 9,2016;“Exit Polls,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CNN,November 9,2020.
在族裔对立持续发展的同时,由于其人口数量优势,白人仍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尽管族裔变量的砝码作用可能明显增加。事实上,无论是2016年还是2020年大选,决定特朗普的胜利或失利的都是白人选民。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所获白人选票相比2016年大选增长了1个百分点,但由于白人选民实际增长了约750万,同时拜登所获白人选票相比希拉里增长了4个百分点,因此特朗普相当于输掉了144万张选票。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期间经济表现不佳,大量家庭的年收入从2016年时的10万美元以上降至5~10万美元,使家庭年收入在5~10万美元之间的选民新增约2 000万;在这些新增选票中,有1 410万投票支持拜登,只有520万投票给特朗普,差距高达近900万张。⑤Eric London,“2020 Election Results Explode the Identity Politics Narrative,”WSWS,November 6,2020.由于白人占此类家庭中的多数,因此对特朗普的选举失利的影响可谓是决定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代际更替还是白人主导的抵消作用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代际更替尚在进行之中,Z一代的政治信仰远未稳定,而白人的数量优势仍被持续削弱,更遑论其整体支持共和党的倾向本身仍是对族裔对立的肯定。对美国政治文化转型而言,族裔对立和社会分化的风险因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口增长而进一步上升。已有美国学者明确警告,美国正回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种族主义的当代回潮与那一时期高度相似:从数量上看,1920年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13.2%,2017年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3.7%;从认知上看,无论是1920年还是2016年或2020年,普通大众和知识精英都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不少人对其充满敌意和恐惧;从制度设置看,两个时期都出台了大量限制移民的立法和具体举措。①Julia G.Young,“Making America 1920 Again?Nativism and US Immigration,Past and Present,”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Vol.5,No.1,2017,pp.217-235.因此,“冷内战”仍被认为是少数种族争取尊重与尊严的持久斗争,因为美国根本上被“白人种族叙事”框架所主导。②Reggie Jackson,“America’s Cold Civil War:The Enduring Fight for Respect and Dignity by People of Color,”Milwaukee Independent,June 16,2020.正是由于“白人种族叙事”的主导地位,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道德压制仍相当严重。例如,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高涨之际,白人打出“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作为反制;尽管在道德上站得住脚,但却在事实上为种族主义提供了更大空间。③Lewis R.Gordon,Bad Faith and Antiblack Racism,Amherst,NY:Humanity Books,1995,p.85;Robin DiAngelo,White Fragility: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Boston:Beacon Press,2018.
四、城乡对立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空间异化
随着政治极化和族裔对立的发展,选民依据政治偏好而聚居推动了新的选举地理即城乡对立(urban-rural divide)的形成,对“冷内战”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冷战结束后,美国选举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从州的层次上看更多是红蓝对立;但有大量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红蓝对立所能解释的。例如,除2004年外,民主党事实上赢得了冷战后历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多数选票。④自1992年起,共和党三次赢得总统大选,但2000年和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所得选票数量都比民主党候选人要少。又如,尽管选票几乎始终占优,但民主党所赢得的选区面积却在持续缩小。依据美利坚大学美国社区研究项目对美国3 000多个县的分类⑤这15类县分别是:南方非洲裔县(African-American South),老龄农村县(Aging Farmlands),大城市县(Big Cities),高校县(College Towns),福音教徒聚居县(Evangelical Hubs),远郊县(Exurbs),灰色美国县(Graying America),拉丁裔聚居县(Hispanic Centers),摩门教徒县(LDC Enclaves),中部郊区县(Middle Suburbs),驻军县(Military Posts),土著美国人县(Native American Lands),中部农村县(Rural Middle America),城市郊区县(Urban Suburbs)和工人阶级县(Working Class Country)。See“County Types,”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http://americanco mmunities.org/county-types,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3日。,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仅赢得15类县中的3类,即大城市县、高校县和城市郊区县。这些现象事实上凸显了美国选举政治中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即日益明显的城乡对立现象。⑥Emily Badger,“How the Rural-Urban Divide Became America’s Political Fault Line,”New York Times,May 21,2019.在城乡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况下,郊区的选举政治重要性便得以凸显,地理空间已经完全异化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变量之一。
4.1 政党对立和族裔对立正日益被选举地理所固定,体现为日益加剧的城乡对立
观察美国城乡对立的指标主要是特定地区的人口密度与该地区在政治选举中对民主党的支持情况:如果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越支持民主党,那么城乡对立就越严重。美国城乡对立很大程度上是二战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人口密度与民主党的支持度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一种正相关关系开始显现;但到2016年大选中,人口越密集、对民主党的支持度越高这一关系已高度明显。⑦Jonathan Rodden, “Polarization:The Urban-Rural Divide,”Stanford Magazine,May 2018.另一项聚焦美国中西部选区的研究发现,民主党获胜选区面积呈持续缩小态势,也印证了城乡对立假设。整个美国中西部面积约为75万平方英里。2008年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所赢得的选区面积相当,分别是38.6万和36.4万平方英里;就选区平均面积而言,两党相差不大,民主党为7 154平方英里,而共和党为7 749平方英里。但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共和两党所赢得选区面积分别为10.9万和64.1万平方英里;选区平均面积的差距也相应拉大,民主党缩小至2 731平方英里,而共和党则扩大到11 875平方英里。①David de la Fuente,“In the Midwest,Dem Districts are Marching to the Suburbs,”Third Way,July 10,2020.
观察2020年大选结果,可以更为明确地看到城乡对立的加剧。根据彭博社城市实验室(CityLab)的研究,拜登选票增长的地区大多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是在人口最密集的市中心、人口密集郊区(dense suburb)和城郊结合部(urban-suburban mix);而在人口稀少郊区(sparse suburb)、农 村—郊 区 结 合 部(ruralsuburb mix)及纯农村地区,特朗普占据着绝对优势。②CityLab-Bloomberg,https://www.bloomberg.com/citylab,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3日。事实上,在2020年大选中,除农村外的所有地区都比2016年更加支持民主党了:郊区对拜登的支持率上升了4.3个百分点;在除农村地区外的其他地区,包括中等城市、小城镇、微型城镇及城市中心,拜登的支持率都比民主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要高,分别高出3、2.8、0.7和0.5个百分点;特朗普在农村地区的支持率相比2016年增长约1个百分点。③Linda Poon,“How Suburbs Swung the 2020 Election,”Citylab Daily,November 18,2020.而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在2020年大选中,城乡对立不是缓解而是强化了:民主党在大城市的优势从2000年的3个百分点增长至2020年的14.4个百分点;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民主党的优势一升一降,变化幅度相差不大;但在农村地区,民主党的劣势拉大了近20个百分点。④Alexandra Kanik and Patrick Scott,“The Urban-Rural Divide Only Deepened in the 2020 US Election,”City Monitor,November 13,2020.
城乡对立还反映出美国政党重组(partisan realignment)的一个趋势,即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基础正发生重大变化;民主党正变为资本家的政党,而共和党日益代表工人阶级。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全国83%的县(2 497个),其经济产出只占全美30%。尽管拜登只赢得了17%的县(477个),其经济产出占全美71%。相比之下,2016年时特朗普在2 584个县获得胜利,其经济产出占全美36%;而希拉里赢得的472个县的经济产出占全美64%。⑤Niall MacCarthy,“Biden Voting Counties Equal 70 of America’s Economy: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Na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Divide,”Brooking,November 9,2020.彭博社城市实验室数据也显示,仅从所赢得的选区数量看,拜登甚至不如特朗普(41%∶59%);但从选票数量看,拜登高出特朗普10个百分点(54%∶44%)。与人口密度相关,随着大都市的人口规模下降,拜登所获得的选票相应下降,而特朗普所获得的选票则相应上升:拜登获胜的大都市平均人口为130万人,而特朗普的只有30万。这样,拜登获胜的大都市的人口占全美57%,经济产出占全美79%。⑥Richard Florida,“How Metro Areas Voted in the 2020 Election,”CityLab Daily,December 4,2020.
4.2 在城乡对立加剧的背景下,郊区正日益成为美国选举政治的决定因素
二战后的郊区化曾帮助共和党赢得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绝大多数总统选举。在1968—1988年的六次大选中,民主党仅赢得1976年大选。这导致民主党对自身选举策略的重大反思,并在冷战结束前后启动了自身的郊区化战略。但需要强调的是,郊区化的快速发展与城乡对立是一对相伴而生的现象。例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于2018年的一项调查,城市选民中支持民主党的达到62%,是支持共和党选民数量(31%)的2倍;而在农村地区,支持共和党的选民(54%)比支持民主党(38%)的高出16个百分点;而在郊区则呈胶着状态,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分别占47%和45%。农村、城市和郊区的选民相互疏远的态势也高度明显:城市选民认为65%的郊区选民和农村选民不理解其所面临的问题,郊区也有52%的选民认为另两类社区的选民不理解其所面临的问题,而农村地区持这一观点的更是高达70%。⑦Kim Parker,et.al.,“What Unites and Divides Urban,Sub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Pew Research Center,May 22,2018.这样,在民主共和两党基本选票相当稳定的背景下,中部郊区县、远郊县等日益成为决定美国选举政治结果的关键变量。
郊区选举重要性的上升在2016年大选及之后体现可谓淋漓尽致。在2016年大选中,帮助特朗普获胜的县都是以白人工人阶级为主的县,包括老龄农村县、工人阶级县、中部农村县、福音教徒聚居县、灰色美国县及中部郊区县等。①“How Trump Became President,”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January 18,2017.这些关键性的中部郊区县相对分散但却是蓝领选民的聚居地,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路泽恩县(Luzerne)、俄亥俄州的斯塔克县(Stark)和密歇根州的马科姆县(Macomb)。这些县在1980年时帮助里根赢得了大选,此后一直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大选中,密特·罗姆尼(Mitt Romney)赢得了77个中部郊区县中的45个,但这并不能保证他获得这些相对分散的县所在的州的选举人团票。但特朗普却赢得了62个,特别是赢得密歇根的6个、宾夕法尼亚的14个、威斯康星的7个中部郊区县,最终成功入主白宫。②“For Trump,It’s All About The Middle Suburbs,”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January 30,2017.
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导致共和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恰好是郊区的“叛变”。中期选举前,共和党在郊区共计有69个席位,但选举后只剩下32个。在11个竞争性的农村选区中,共和党仅输掉1个;在19个接近农村的中远郊选区中,共和党输掉4个;在30个人口稀疏的中远郊选区中,共和党输掉了16个;在15个人口密集的中近郊选区中,共和党输掉了12个;而在9个城市近郊选区中,共和党输掉了6个。这样,美国的选举地图不只是单纯的自由主义城市孤岛与保守主义农村海洋,更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在郊区的犬牙交错的防御工事的拉锯战。③“Uncivil Wars of Civil Religion,”Law Liberty,October 29,2020.
2020年大选结果进一步表明了郊区的选区重要性。正是由于丢掉了郊区地带的高校县、远郊县和驻军县,特朗普最终输掉了整个连任选举。高校县一向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在2016年更支持特朗普;驻军县同样由于人口流动大且族裔混杂,因此其投票倾向也可能变化快。因此,真正导致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败的是远郊县。相比2016年,拜登在远郊县所获得的选票比希拉里高出约5个百分点,选票数量净增长约6个百分点。拜登获得此类县43.3%的选票,创下了民主党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仍以12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远郊县,但却是2000年以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此类县中的最低纪录。其核心原因在于,远郊县居住着大量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他们对特朗普的选举策略特别是族裔动员策略高度反感。④Dante Chinni,“Final Presidential Results Show Substantial Shifts in Exurbs,Hispanic Centers,and Military Posts,”American Community Project,December 21,2020.整体上看,特朗普赢得了15类县中的12类,且在部分县的获胜优势继续扩大。例如,在老龄农村县,特朗普的优势增加1.6个百分点,达到56%;在福音教徒聚居县,增加了7个百分点,达到51%;在工人阶级县的优势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此外,特朗普在中部农村县、摩门教徒县、灰色美国县等的优势都超过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拜登在城市郊区和大城市县的优势都不到25%,而在高校县的优势不足10%。⑤Dante Chinni,“The 2020 Results:Where Biden and Trump Gained and Lost Voters,”American Community Project,November 9,2020.这充分说明,农村仍坚定支持特朗普,而大城市及中近郊都是民主党的票仓,郊区才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
五、结语:难以逆转的美国政治文化转型态势
拜登的执政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能走出“冷内战”,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既有态势难以被全面逆转。在拜登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的同时,怀疑者认为这一口号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样,不过是种妄想。⑥Liam Kennedy,“Why Biden’s Refrain of‘America Is Back’is as Delusional as Trump’s‘Make America Great Again’,”The Conversation,January 25,2021.只有48%的民众相信他能将整个美国团结起来,而不相信的达到52%。①“Biden Viewed Positively on Many Issues,but Public Is Less Confident He Can Unify Country,”Pew Research Center,March 11,2021.公众的怀疑是合理的,要重大地缓解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分裂,拜登及民主党仍面临着至少两个方面的重大阻力。
第一,特朗普或类似的极端力量仍有强大的反扑能力。尽管输掉了连任选举,但特朗普的选举收获比2016年更好,这不仅是他坚持不认输的重要理由,也是美国制度僵化、社会分化、空间异化的重要表征。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在下台后仍表现出强大的政治生存能力:在2020年大选前,共和党人内部支持特朗普的比支持共和党的还高出16个百分点,即使在大选之后仍高出6个百分点。②Amy Walter,“Whose Party Is It?”Cook Political Report,January 8,2021t.随着距离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间缩短,共和党内部已形成基本共识,即特朗普应当参选。③Alex Isenstadt,“DeSantis Dominates Trump In Fundraising As 2024 Hopes Surge;Teacher Union Admits He Beats Them On Education In Swing States,”Daily Wire,July 19,2022;Trump Discussing 2024 Plans at Secret Donor Dinners,”Politico,July 13,2022.尽管2022年上半年选举筹资节奏有所放缓,但截至2022年7月,特朗普已为2024年总统竞选筹集了近1.6亿美元选举资助,④Ryan Saavedra, “Gabby Orr and Fredreka Schouten,“Trump Team Announces$122 Million War Chest,”CNN,February 1,2022.而在2021年上半年,共和党依赖特朗普也筹到1.34亿美元。⑤Shane Goldmacher,“Hooked on Trump:How the G.O.P.Still Banks on His Brand for Cash,”New York Times,July 27,2021.对此,拜登政府不得不围绕中产阶级展开其内外政策——如提出《美国就业法案》《美国家族法案》以及推出“中产阶级外交”等⑥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第10-18页。,但这种被动应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阻止特朗普及其志同道合者仍有待观察。
第二,尽管民主党拥有的普通选票创下自1992年以来的新高,但共和党对国会选区划分的把控能力仍然很强,这意味着民主党要获得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选举的胜利仍困难重重。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国会选区重新划分;而掌握国会选区重划权力的是各州议会。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事实上输掉了不少州议会席位。尽管相比2010年,民主党形势有所改善,但共和党的优势仍相当大:共和党控制着17个州187个选区的重划权力,而民主党只控制8个州75个选区。即使不考虑选区重划的因素,因人口变化而来的选区调整本身,也足以使民主党输掉202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⑦Chris Matthews, “Redistricting Alone could Give Republicans Control of the House in 2022,Experts Say,”MSN News,April 27,2021.而即使所有选民的投票不变,由于选区重划,拜登在2024年的选举人团票也会减少3张。
这样,“冷内战”仍在持续,美国政治文化转型步伐未被打断。尤其是,共和党持续推动政治文化转型、重获选举主动权,重大地调整了选区重划策略,从2010年时以农村“进攻”郊区战略,转变为当前的“守住”农村选区的战略。⑧Rachael Dottle and Allison McCartney,“Republicans Have a Redistricting Problem as Suburbs Shift Toward Democrats,”Bloomberg,October 1,2021.这一战略改变的结果是,两党的安全选区将进一步增加,而竞争选区则明显减少。⑨Laura Bliss,“MapLab:How Republicans Are Dominating the Redistricting Process So Far,”Bloomberg,November 19,2021.在截至2022年6月10日已划定的429个选区中,有187个选区强烈支持拜登,仅比2020年增加1个;竞争性选区79个,比2020年减少了11个;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有163个,比2020年增加了11个。⑩“States are Redrawing Every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n the U.S.,”Politico.com,June 10,2022.在严峻的选举压力面前,拜登政府及民主党人在短期内彻底扭转美国“冷内战”、使美国“重归正常”显然相当困难,集中体现在当前美国国内围绕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性质的调查斗争中。⑪Ryan Goodman,“8 Top Experts on Strength of Dominion Suing Trump for Defamation,If It Wants To,”Just Security,July 19,2022.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依然是个长期而缓解的进程,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对更为长期的美国霸权维持产生消极影响。用一位政治评论员的话说,“美国正诡异地在重蹈罗马的覆辙,走向衰落;它会在为时已晚 之前扭转局面吗?”①Tim Elliott,“America Is Eerily Retracing Rome’s Steps to a Fall.Will It Turn Around Before It’s Too Late?”Politico.com,November 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