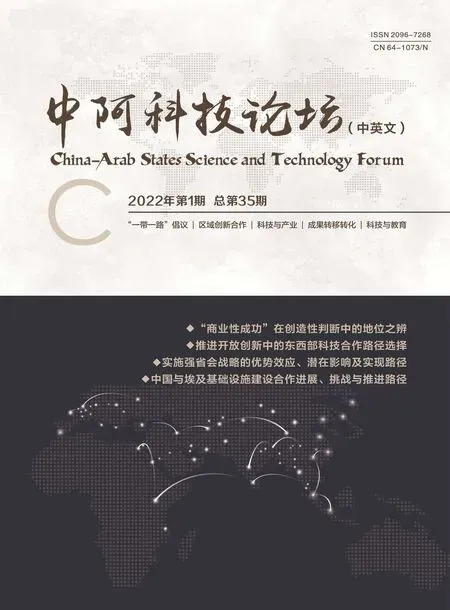“商业性成功”在创造性判断中的地位之辨
马舒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1 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发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是判断发明创造性时需考虑的其他因素①。基于此,在实践中当事人常通过主张“商业性成功”以支持对其发明的创造性判断,但得到成功适用的概率微乎其微,其一大成因正在于当前对“商业性成功”与创造性主要判断方法间的适用顺序尚缺乏统一的认知。
从一般逻辑来看,在讨论“商业性成功”与“三步法”②间的关系上,大体包括两种可能:(1)运用“三步法”足以肯定或否定技术特征的创造性,进而适用“商业性成功”加以分析,即两者间乃先后适用的关系;(2)运用“三步法”尚不能明确是否具有创造性,通过“商业性成功”的平行适用以辅助结论的得出。考量我国当前实践,上述不同逻辑均有所体现。如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胡颖、深圳市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中,最高院指出:“当采取‘三步法’……得出技术方案无创造性的评价时”,即当“技术方案本身与现有技术的区别在构成可授予专利权的程度上有所欠缺时”……“从社会经济的激励作用角度出发,商业上的成功就会被纳入创造性判断的考量因素”③。这一观点亦得到了实践中的较多支持④。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一般在采取‘三步法’难以判断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时,才将商业上的成功纳入创造性判断的考虑范围”⑤。对比两种观点,看似仅有细微的差异,但对创造性结论的得出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更进一步来看,这两种观点的背后系对“商业性成功”,乃至辅助判断要素本质认识的差异,反映了对专利激励理论认识的不同:当立足于上述前一观点的视角,某一技术特征对社会经济的激励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技术贡献的不足;而若基于后一观点,商业上的成功应被认为系针对技术进步的侧面证明,其在本质上并未突破对发明的技术评价范畴。
综观我国当前实践,可以发现“商业性成功”作为辅助性判断因素被主张的概率却非常之高,乃至有美国学者认为其为最重要的辅助性判断因素⑥。那么,我国在创造性判断中应采何种逻辑?尤其当已得出“无创造性”的结论时,是否可基于“经济激励”的理论,运用“商业性成功”对该结论加以突破?本文拟加以探究。
2 “难以判断创造性”和“无创造性”间的内涵界分
在探讨“商业性成功”在创造性判断中的地位之时,首先应明确“难以判断创造性”和“无创造性”的内涵及两者间的本质界分,否则后续讨论将失去意义。
对此,存在意见主张并不存在“难以判断创造性”的状态,其主要认为:首先,创造性判断中的主观性源于其法律适用过程的性质,“大可不必因存在主观活动就认为这一判断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过程”;其次,若“不能通过‘三步法’对某一技术方案作出否定评价或者找不到可以使用‘三步法’对某技术方案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文献或其他事实依据”,在实践中通常“推定具备创造性”[1]。这一观点系站在结果的角度,认为不论过程如何,对创造性的判断最终都将得到明确的结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结果的确定性并不必然等于结果的正确性,因专利审查终将产生确定结果而否认判断过程的不确定性并不合理。
首先,正如上述意见所述,适用“三步法”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尤其对于“三步法”中的“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而言是否显而易见”,其中对“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标准的尺度把握、技术启示的确定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判断主体主观意志的影响,当这些因素最终叠加到一起时,在诸多复杂的案例中,专利的创造性都将成为不确定的命题。在实践中,除了在个别情形下因发明的创造性程度很高或很低(例如在所涉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或系对两种现有技术手段的简单组合等),可直接得出确切结论外,在多数情况下,对创造性的判断系介于有和无之间的模糊地带,更涉及一种主观上对程度的衡量,这就导致不同的判断主体在面对同一客体时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即便如意见所指,在无法确认时通常应当采取推定的态度,但判断者可能已在推定前得出了关于创造性的错误结论。
其次,按照上述意见,推定具有创造性的前提是找不到否定的事实依据或无法“作出否定评价”,即在客观的事实判断层面或主观的价值评价层面无法得到否定性的结论。但一定创造性高度的要求决定了主观评判的模糊性,因此在大量案件的判断过程中均无法直接得出确切的否定性结论。若依照推定具备创造性的逻辑,那么辅助判断要素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根据《专利审查指南》,当申请存在辅助判断要素时,审查员“不应轻易作出发明不具备创造性的结论”⑦,可见其意义在于辅助肯定发明的创造性,但既然当无法得到确切结论时可以推定发明的创造性,那么即意味着无论辅助判断因素存在与否,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由此,“难以判断创造性”系建立在判断过程的视角上,而“无创造性”则关乎创造性的判断结果,单纯从某一视角出发否定另一视角的论断缺乏合理性。
3 对基于“经济激励理论”的“突破说”立场之证否
“难以判断创造性”和“无创造性”概念均有其存在的意义且并非同一概念,由此,对“商业性成功”与“三步法”间适用顺序的讨论确有必要。在当前关于“商业性成功”适用地位的争议背后,反映着对专利制度“经济激励说”与技术激励间的不同态度。
综观目前实践及理论,关于“商业性成功”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创造性不足的论断(以下简称“突破说”)均系基于对社会经济的激励角度。基于“经济激励说”,专利制度的价值除在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以外,还在于“作为经济激励的政策性手段推动社会发展”,故对发明应予以经济评价,“商业上的成功正是发明创造经济价值的直接体现”[2];对此,学界亦有意见认为“商业成功的判断逻辑……并非基于技术上是否构成贡献来考虑”,根据该说,“商业性成功”并非对发明技术贡献的证明,而是在经济范畴内的评价。相比之下,认为“商业性成功”系在根据“三步法”难以判断创造性时始得适用的观点则并未突破技术评价的范畴(以下简称“辅助证明说”),正如美国法院所指,辅助判断要素应被认为属于“事实调查(factual inquiry)”的范畴,即“间接证据”,其作用在于防止法院陷入“事后诸葛亮”的主观判断⑧,就“商业性成功”而言,其意在说明“在消费需求相当大的情况下”,若发明显而易见,则竞争对手应早已“成功取得该发明”[3]。可见,两种观点背后存在着对理论理解的根本冲突。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侧重于在技术层面上对“三性”的判定,由此,当基于“经济激励理论”意图对此加以突破时,应存在相应的正当性基础。那么,何为“经济激励理论”?对其内涵及其在专利制度中的意义应作何理解?当基于该理论,又是否可必然推导得出“突破说”?本文拟回归专利制度的本源,通过对“经济激励理论”的讨论,以期厘清在创造性判断过程中经济因素、技术贡献等考量因素间的关系。
3.1 “经济激励理论”的内涵及意义之析
对于专利制度下的“经济激励理论”,首先应明确其并非意味着基于一项创造活动在经济上的成功而应对其进行激励。否则商业秘密同样可以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但其并未通过公开技术方案等方式作为对价,无须在制度框架内予以激励。
无论是基于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财产论,抑或是功利主义学说,“经济激励理论”均应被理解为通过经济上的收益以激励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等相关活动。而在“突破说”关于经济激励理论的主张与论断中,其更立足于结果的角度,侧重于专利制度对社会经济的价值,即通过创造、运用等知识产权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认为“商业性成功”正体现如此,故应予以认可。该观点并非不无道理,正如有学者所指,“专利制度所激励的,是通过专利将技术成果市场化的商业行为。不考虑市场的专利行为,是对专利与专利激励作用的误解”[4],在技术价值以外,对专利整体价值的评判不应遗漏商业价值,完善的专利制度在激励发明创造产生的同时,更应促进其推广运用,进而推动社会整体经济的进步。
“经济激励理论”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据此即可肯定某一技术特征在商业上的价值可弥补技术上的不足,两者并不存在直接必然联系。当基于该理论肯定“突破说”的成立,仍应经过逻辑上的层层推导。
3.2 “经济激励理论”对“商业性成功”适用地位的影响与限制
关于“经济激励理论”对证明“突破说”的意义,笔者认为:一方面,“经济激励说”的价值并不意味着需通过包括创造性判断在内的整个专利制度加以满足,这不仅不具备现实性、还将导致专利制度体系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在专利整体制度内,经济激励理论不应优先于对发明的技术评价以适用。
首先,在专利授权过程中,对新颖性、创造性的评判均系与现有技术相比较而言的技术性评价,即便对于实用性,也仅强调在产业中具备能够被制造或使用的“可能性”⑨。至于对发明实施、运用的激励,可通过授权后的年费、强制许可等机制予以实现。由此,“经济激励说”与“商业性成功”适用地位间也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联系,而若基于“经济激励”说简单认可“突破说”,将可能导致在专利授权审查阶段和获得授权后的复审、无效阶段中对同一技术方案创造性水平的认定标准、结果的不同。基于新颖性的要求,技术特征可能通过使用等方式公开,因此对于实践中的大量技术方案而言,其在申请专利前并未投入市场,这就导致其在申请过程中尚未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在获得授权后的复审、无效制度在本质上均系对技术方案的再次审查,其审查的基础、标准应与授权审查时具有一致性。若某一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系对部分现有技术特征的简单替换,若因其之后商业上的成功即对授权审查时的错误予以认可,将造成对公有领域内技术或他人技术的吞噬,并不合理。
其次,“经济激励说”下技术成果市场化实现的前提应为技术成果的“创造”,因此,脱离技术层面对商业价值的强调将成为“空中楼阁”,技术判断相比于经济判断应具有优先性。正如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一条的规定,“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均至关重要,若因经济评价而对创造性水平较低的技术方案赋予垄断权的保护,并不利于提高发明人的创造积极性,反而不利于专利制度目的的达成。
综上,“经济激励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与“技术激励说”存在先后的顺位关系,更不得基于“经济激励说”突破发明的基本属性。由此,“商业性成功”似乎更像是在“三步法”判断过程中的一个证明要素,能够证明技术方案本身的创造性水平,当某一技术特征导致商业上的成功时,基于“经济激励理论”应予以周密慎重的考量与论证,不宜轻易作出发明不具创造性的论断,但不得因此直接肯定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水平。
3.3 “突破说”所致的可能不利后果
此外,正是因为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同建立在“经济激励说”上的适用框架,导致了“商业性成功”条款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极少被成功适用。在笔者检索的判决及审查决定中,几乎所有均是在运用“三步法”明确得出技术特征不具创造性结论的前提下,再进一步分析“商业性成功”的主张能否成立。在此种情况下,裁判机关已经在逻辑上接受了发明实质上未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此时无疑难以再通过辅助性判断因素推翻既有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最终几乎所有的案件均认定发明没有取得“商业性成功”或“商业性成功”与技术特征间不存在直接关系。
综上,无论从“经济激励理论”与“商业性成功”间的关系出发,抑或从“突破说”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来看,当前实践中普遍关于“突破说”的立场均不具有合理性。基于此,本文拟进一步分析对于“商业性成功”在创造性判断中的应有地位。
4 对“辅助证明说”之理论与实践证明
4.1 “商业性成功”作为辅助判断要素的起源及发展
对于“商业性成功”在创造性判断中的适用地位之析,仍应回归其作为辅助判断要素的产生及在各国的发展路径,借此可在我国现行《专利审查指南》关于辅助判断因素适用地位的规定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厘清其本源及在适用过程中的应有态度。
一般认为辅助判断要素的提出源于美国,在美国早期汉德法官的诸多判决中,其将辅助因素“看作专利性的鉴定性证明,没有这些证据,法院仅仅能够依靠朦胧的‘发明’标准”[5];之后在著名的“Graham”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商业性成功、长期存在但未能解决的需求、他人的失败等辅助判断因素可以被用于解释想要寻求专利保护的客体创造性的一些情况。作为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性的指征,这些探寻可能具有相关性⑩。在“Graham”标准确立之后,在众多判决中又进一步深化了该认识,如在“Stratoflex”案中,法院指出:“事实上辅助性因素常常是最具证明力和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它应被视为所有证据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当裁判者在审查后仍然有疑问时适用。”⑪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实践发展过程中,辅助性判断因素是在创造性判断过程中的证明,如上文所述,其是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间接证据”。在欧洲,辅助性因素则被认为是对创造性主要判断标准的补充,如根据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的观点,“只有在利用‘问题—解决方法(Problem and solution approach)’等评价专利创造性存疑(对现有技术是否给予教导的客观评价尚未明晰)的情况下,辅助判断因素才是重要的”[6]。
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地区对辅助判断要素的适用顺序存在着些微不同。单纯从逻辑来看,在美国“证据说”的观点下,辅助判断要素作为证据的一部分,只要当事人提出,即应在创造性判断的整体过程中加以考量;而在欧洲“补充说”的背景下,只有在无法明确得出创造性结论时,辅助判断要素才会被纳入考虑,在技术方案创造性极高或极低的情况下,即便辅助判断要素被提出,也没有考量的必要。
但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当聚焦于实践中的适用,两者是否还存在显著的差异?以我国对创造性的判断过程为例,“三步法”作为主要的判断方法,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例如对最接近现有技术的确定过程中,涉及与现有技术领域的远近、技术特征的复杂程度等多方面的要素;在确定区别特征及其实际解决的问题中,也涉及对某一特征在发明中事实上起到的效果的认定;而在对显而易见的判断过程中,主观因素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对各种因素的确定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审查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在此情形下,即便秉持美国的“证据说”,其本质亦在于认为专利创造性判断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外在的辅助证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判断的客观性,正如在美国的“Washburn”案中所提出的,“专利发明的优劣不应该在所有周围环境真空的情况下确定,而应该在行业内周围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评估”⑫。从这一角度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证据说”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补充说”都是建立在创造性的主观判断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基础之上,而辅助判断因素的介入虽然在逻辑上存在先后的差异,但其本质上都是借助外在环境的因素为最终创造性结论的得出提供客观性的证据,在实践中并不存在顺序的差异。
由此可见,各国实践中关于辅助性判断要素的适用顺序正是建立在运用“三步法”得出有关创造性的结论可能模糊不清的基础之上,这对我国“商业性成功”适用地位的判断具有启示意义:若从辅助判断要素的产生及其在各国的发展来看,均持此观点,那么我国实践中关于“突破说”立场的合理性也将受到怀疑。正如《专利审查指南》中所指出,当出现辅助判断要素时,“审查员应当予以考虑,不应轻易作出发明不具备创造性的结论”⑬,可以认为辅助判断要素是“三步法”判断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其在本质上即是对于创造性要求的具体表现,而通过将“商业性成功”等典型表现列为辅助判断要素,在有助于实现判断相对客观化的同时,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4.2 我国实践发展中对“商业性成功”态度之梳理
基于上述对辅助判断要素从产生到在各国发展的梳理,笔者拟通过对《专利审查指南》历次修改的版本进行比较,以考量我国在实践发展中对“商业性成功”适用地位态度的变化,以期帮助厘清对“商业性成功”适用的应有地位。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在辅助性判断因素的表述上各不相同:除却上文所述的我国现行《专利审查指南》中的表述,在1993年版本中,其规定“评定发明有无创造性,应当以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为基准。为有助于正确掌握该基准,下面给出一些参考性判断基准。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判断基准仅是参考性的,审查员在审查具体的案子时,不要生搬硬套,而要根据每项发明的具体情况,公正地做出判断”⑭;而在2001年版本中,其规定“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通常应当依据本章第3.2节所述审查基准进行审查。为了有助于创造性的判断,下面给出一些特定情况下的辅助性判断基准”⑮;而在此之后的修改中,相关表述与当前《专利审查指南》中的表述趋同。单从辅助性判断要素相关规定的字面来看,我国的态度似乎较为偏向于上文中欧洲的代表观点,即认为辅助判断要素系对于较为复杂的创造性主观判断的补充,当运用“三步法”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时,辅助判断要素的存在可帮助其结论相对客观。
4.3 小结
总结而言,当讨论辅助性判断要素的适用地位时,不论是美国的“证据说”,抑或是欧洲的“补充说”,其均是建立在创造性主要判断方法的主观性基础之上,毕竟技术特征的创造性并非绝对有或绝对无,其更多情况下是处于0~1间的一种程度的衡量。也正因此,上述两种学说的本质均是运用辅助判断因素为创造性判断提供一定的客观证据,至于与“三步法”间适用顺序的差异则更多属于逻辑层面。但与此同时,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其仅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切不可因某一因素的出现而断然肯定某一绝对不具创造性的技术特征,而“商业性成功”也并未脱离这一适用框架。通过对“商业性成功”适用地位的厘清,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的适用困境,当运用“三步法”能够确定得出一个特征不具创造性的结论时,显然“商业性成功”没有适用的必要,而这正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这一规定适用的成功率,也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这一适用顺序可能会影响到有关最终“创造性”正确结论的得出。
5 结语与讨论
目前我国成功主张“商业性成功”的比例非常之低,尽管这一现象的产生系基于多种原因,如对于商业成功、商业成功与技术特征间相关性等问题的举证困难等,但也应认识到,目前实践中普遍认为只有在运用“三步法”否定创造性之后才有“商业性成功”的适用可能性,而正是这一观点,从根本上切断了“商业性成功”得到成功主张的道路。尽管“商业性成功”背后确有“经济激励”的考量,但该考量也绝不可突破专利的技术本质。而当在技术层面否定专利创造性乃至新颖性后,始得适用“商业性成功”显然难以突破这一结论。
“商业性成功”虽然在浩瀚的专利制度中如同沧海一粟,但其与专利制度的本质密不可分;同时,创造性判断作为专利法中的重要命题,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而通过对“商业性成功”等辅助判断要素的厘清和正确理解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创造性判断过程中的“事后诸葛亮”问题。
注释:
①参见2020年《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5节判断发明创造性时需考虑的其他因素:“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通常应当根据本章第3.2节所述的审查基准进行审查。应当强调的是,当申请属于以下情形时,审查员应当予以考虑,不应轻易作出发明不具备创造性的结论。”“5.4 发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②根据2020年《专利审查指南》中的3.2.1.1判断方法,“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通常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1)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2)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3)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此为对创造性判断的主体方法,笔者在本文中将其称为“三步法”。
③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
④如在实践中的大量法院直接指出“商业性成功”乃当采取“三步法”难以判断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或者得出技术方案无创造性的评价时适用,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2509号行政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2940号行政判决书等。同时,大量判决虽未明确指出,但判断的逻辑顺序亦是首先运用“三步法”认定某一技术特征不具创造性,再进一步分析“商业性成功”的要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北京高级法院(2017)京行终5610号行政判决书等。
⑤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行终237号行政判决书。
⑥See Robert P.Merges,“Commercial Success and Patent Standards: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76(4)California Law Review 816(1988).
⑦参见2020年《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5节。
⑧See Vandenberg v.Dairy Equip.Co.,740 F.2d 1560.
⑨参见2020年《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第5.3节。
⑩Graham v.John Deere Co.,383 U.S.1.
⑪Stratoflex,Inc.v.Aeroquip Corp.713 F.2d 1530.
⑫George M.Sirilla,“35 U.S.C.§103:From Hotchkiss to Hand to Rich,The Obvious Patent Law Hall-of-Famers”,32 J.Marshall L.Rev.437(1999).
⑬参见2020年《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5节。
⑭参见1993年《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节。
⑮参见2001年《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