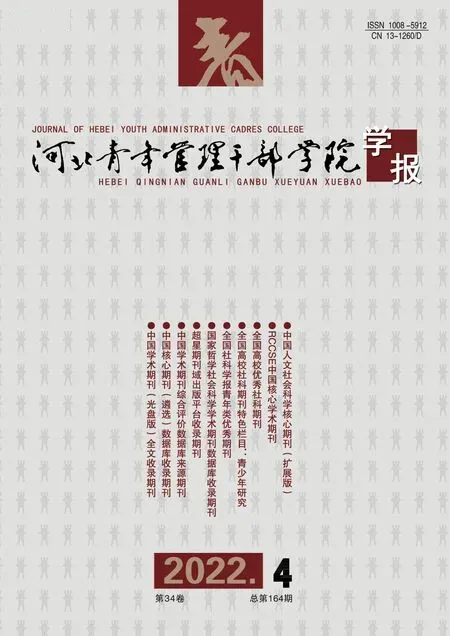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历史考察
白 贤
(咸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柳宗元是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际遇,使其在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吏为民役”观点,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至今依然不失借鉴意义。本文对这一思想的内涵及其生成、演变的历史作一粗浅考察。
一、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提出及其内涵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柳宗元虽然不能完全突破自身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但由于身处唐朝日渐衰败之际,加之早年科场得志、中岁仕途受挫的跌宕经历和士大夫所特有的忧患意识与人文情怀,使他得以深入地方基层社会,对唐代民间不断激化的官民冲突感同身受,并对饱受摧残压迫的下层普通劳动人民抱以同情态度。针对一些地方官吏欺上瞒下、鱼肉百姓的做法,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借范传真之口提出“吏为民役”的主张。
(一)“吏为民役”思想的提出
柳宗元《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所提到的范传真,新旧《唐书》有传,皆作范传正,字西老,是唐代颇有声名的“良吏”。当时吏部办事的胥吏利用手中权力“为奸以立威,贼知以弄权,诡窃窜易,而莫示其实”,范传真以“端悫而习于事、辩达而勤其务”[1]595的口碑入职吏部,与吏部衙门中胥吏的不良风气形成鲜明对比。因其任内获得较好声誉,三年期满后担任武功县尉,同样因政绩突出而升任为宁国县令。当时众人都认为他得到了一份美差,他却对弟弟说出了如下这段话,一般为被视为“吏为民役”的最初表述:
“夫为役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侮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1]595
范传真的弟弟将这番话告知同僚,备受推崇,众人纷纷写诗为他赴任送行,并请柳宗元为之作序。于是就有了这篇《送宁国范明府诗序》。由此可见,“吏为民役”的思想虽然不是柳宗元首先提出的,但确是通过柳宗元之文而得以发扬光大,并因其所具有的影响力而广为世人所知。更重要的是,“吏为民役”代表了柳宗元的一贯立场,一般也将其视为柳宗元自己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当范传真弟弟将其告知同僚时,大家“咸悦而尚之”,可见“吏为民役”思想在唐代士大夫群体中有着一定的反响和共鸣。
(二)“吏为民役”思想的内涵
在柳宗元看来,官与民的关系应该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因为官吏的俸禄来源于百姓,先有百姓的供给,才有官吏的衣食,当官之人一定要为民办事,对民常怀感恩之心。一方面,地方官吏绝不能残暴地对待民众,而是要引导他们通晓礼节;另一方面,还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给老百姓以真正的实惠。在《送薛从义之任序》一文中,柳宗元更为深入地阐释了“吏为民役”的思想。文曰: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民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拥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1]616
按,薛从义是永州零陵县令,在任时“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1]616,与柳宗元为同道中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对“吏为民役”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含义:
第一,民众自食其力,是自己养活自己的。官吏是民众雇佣来的,是仰仗民众而存活的。作为官吏的职责就是“司平”,即维护社会公平,主持民间公道,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粗暴对待百姓,损害百姓的利益。
第二,为官之人不能善待百姓,就如同偷窃、抢夺别人财物的强盗,是违背天理良心的。天下的官吏多不能善待百姓,既侵夺了他们的财物,又不能担负起为官的职责。
第三,对于官吏评判、罚赏的权力应该掌握在民众手里,民众之所以不能实现这种权力,对作恶的官吏敢怒不敢言,是因为处于劣势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势”一旦改变,百姓就有可能实现对官吏获得处置的权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柳宗元对“吏为民役”的分析和认识是极为深刻的,在封建地主阶级中确属难能可贵。
二、“吏为民役”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其中,历史因素是唐代士大夫对儒家“民本”思想中关于“官民关系”的继承和发展,现实因素则是中唐以来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和官民冲突不断加剧使然。
(一)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由于宗教信仰始终未能在中国早期的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有其鲜明的“人文性”特征。在推翻了殷商王朝后,周代统治者吸取了商朝残暴虐民的灭亡教训,提出“敬天保民”的主张,开启了中国古代的“重民”“爱民”传统[2]25。《尚书·泰誓》中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说法,实际上是将“天”与“民”统一起来,将“民意”上升到“天意”,堪为早期“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总之,周代统治者意图通过人民的安居乐业来彰显其“德性”,以完成代天理民的国家和社会治理[3]。
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家“民本”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希望统治者能够善待人民,严格要求自己,“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置于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甚至认为不能善待人民、背弃仁义的统治者即为残贼之“一夫”,人民可以组织起来推翻他,而不必背负犯上作乱的恶名。孟子的“仁政”“保民”“革命”思想,使三代以来的“民本”思想达到空前的高度。
秦汉以来,由于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民众的权利和地位受到相应压制,但作为重要政治文化传统的“民本”思想依然不绝如缕。汉初的陆贾、贾谊等人总结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倡导统治者调整官民关系,实行仁政,与民休养。董仲舒虽提出“屈民而伸君”的主张,但同时倡导“屈君而伸天”,依然不失为以“天意”行“民意”,具有典型的“民本”色彩。
隋唐时期,历经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的儒家更加注重对“民本”思想的阐发,王通提出“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说法,足以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相比肩,代表了隋唐时期“民本”思想的新高度。唐太宗不但倡导“国以民为本”,还是“民本”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正因为此,才有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并下启后来之“开元盛世”。
通过以上关于“民本”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可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周秦汉唐以来有识之士的共识。而这些认识,无疑成为柳宗元产生“吏为民役”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未尝不是传统“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二)对中唐以来社会矛盾激化的回应与反思
唐立国之初,最高统治者充分吸取了隋朝役使民力、二世而亡的教训,长期奉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人民所承受的赋税徭役相对较轻,吏治也较为清明,整个国家的各项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在此期间,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官民关系也较为和谐。然而,传统帝制时代高昂的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使这种“盛世”局面注定难以长久维持,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和深层矛盾逐一显现,曾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盛极而衰的“下坡路”。
柳宗元的一生,历经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正是唐王朝走向衰败之时。平定“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虽然得以苟延残喘,但深陷各种社会危机和矛盾中。中唐以来,藩镇之祸从河北四镇扩展到内地,这些跋扈的武夫悍将控制诸多州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他们连年割据混战,抢夺兵源,极大破坏了唐朝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而连续不断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更是加剧了唐朝政治的腐化堕落。为维持其腐朽统治,唐政府对民众的赋役盘剥不断增加,上下吏治之腐败日甚一日,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随之激化。为了扩大朝廷收入,统治者不仅广开税源,而且不断提高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盐价格,使很多贫苦百姓买不起盐而选择“淡食”。如果说唐前期的农村中尚有一定比例的相对富裕农民,中唐以后民众的苦难则不断增加,生活质量大不如前,失业、逃亡者甚多[4]15-16。即使遭遇灾害之年,一些官吏继续征收租税,而不许百姓上报灾情。总之,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受奴役,经济上受剥削,官民矛盾不断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与此同时,一些皇室、贵戚、官僚、地主仰仗权势,不断侵夺民众利益,造成“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端对立。在苛税杂役之下,不堪重负的农民要么选择放弃农业、逃往他处;要么铤而走险,发动武装起义。公元762年,也就是距柳宗元诞生的11年前,由于黄河流域战乱频繁,朝廷对江淮百姓的负担骤然增加,即导致台州人袁朝发动唐代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5]327。此后的140多年间,农民起义连绵不绝,直至黄巢起义最终埋葬了唐王朝。
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日益尖锐的官民对立,已经开始动摇唐朝统治的秩序和根基,并最终影响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的柳宗元,看到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官民对立很可能会失掉民心,进而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唐朝统治的终结,自然会深入思考巩固政权之道。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官民关系,保障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呢?柳宗元认为,只有从观念上建立“吏为民役”的认识,让唐朝的官员对民怀有感恩之心,真正为民服务,才能彻底改变官民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使政权真正得到民众拥护。
三、“吏为民役”思想的历史价值及现代回响
柳宗元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时代和阶级局限,提出“吏为民役”思想,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传统帝制时代,这样的主张永远不可能在政治实践中变为现实,但在理论层面还是对唐宋以降的政治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吏为民役”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传统帝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垄断一切,但皇帝又不可能亲自去处理国家的一切大小事务,于是不得不利用庞大的官僚集团来行使权力,具体表现为代天子管理百姓和征收赋税。由于天高皇帝远,官僚们的所作所为多依赖自我管理和约束,但在缺少制衡的权力面前,他们往往会难以避免地走向腐化,与之相伴而生的还有专制与残暴。考察古代社会的民变历史,大多数是“官逼民反”所致,可见官民冲突往往是引发王朝政局动荡甚至改朝换代的重要诱因。
在传统帝制的政治框架内,该如何处理好官民关系呢?若依儒家的“民本”思想,皇帝“代天保民”,与民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然如此,作为皇帝仆从的官吏阶层理应也是民众的仆从,为民服务。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柳宗元在以往“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思想。但柳宗元并没有看到帝制框架内官、民在根本上的对立,更看不到专制君主才是官员役使和残害百姓的真正罪魁祸首,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苛求的。
实际上,随着君主专制的日益加强,宋元以降的官民冲突有增无减。儒家士大夫只能将改善官、民关系的希望寄托于皇帝一人身上,极力鼓吹君主“仁政爱民”。程颐指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希望皇帝能实行仁政,善待百姓。王阳明劝诫当权者要“明德亲民”,视天下人“如一家之亲”,使四民各安其业,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但其注定是一种幻想。直至清明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由于遭遇“亡天下”之痛,对产生君民对立的君主专制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尤其是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将人民视为国家的主人,君主视为临时的客人,直指传统帝制荼毒民众的症结所在,其对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发展和升华的同时,也达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最高程度。
(二)“吏为民役”思想的现代回响
近代以来,随着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在神州大地的不断传播和拓展,如何处理官民关系也成为革命者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思想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吸收和实践,成为他们打破阶级压迫、改善“官民”关系、建立民主政权,并最终走出“官逼民反—改朝换代—矛盾激化—官逼民反”怪圈的重要资源。
毛泽东特别推崇柳宗元,生前曾多次阅读柳宗元的著作。章士钊先生在耗尽心力撰写《柳文指要》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指点。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方关照下,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才得以在“文革”期间出版,并经周恩来的推荐而传播至海外[6]。从现有的资料看,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思想,但作为熟读柳文的专家,受其影响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毛泽东关于人民和政府关系的很多论述,也能印证这一点。
1945年,黄炎培等国民政府参政员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邀访问延安,曾有一次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对延安的民主景象和军民关系备受鼓舞,但同时对历史上众多团体功成名就后的败亡心存疑虑。他提出:一部中国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148-149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以真正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显然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理性思考。一方面,他认为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真正树立起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与广大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从根本上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在此意义上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人民民主”模式,终使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思想从理论变为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看重儒家的“民本”思想,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习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8]142。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甘为“人民公仆”,奉行“执政为民”,坚持“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的根本宗旨和光荣使命。从此意义上说,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思想依然没有过时,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于欢案“官民”互动和江歌案的中日舆论反差说起